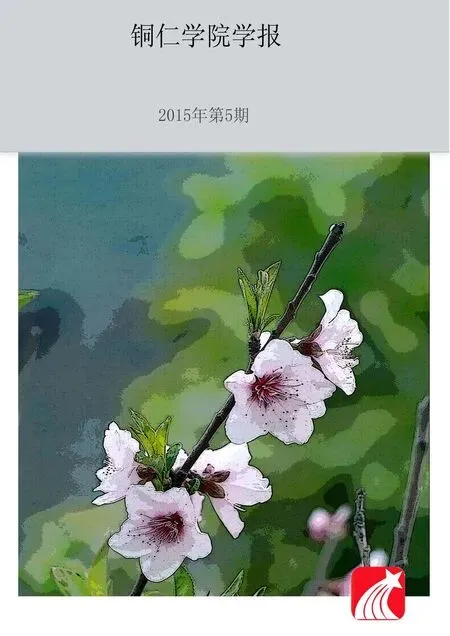南宋理学家编选《左传》风尚的形成及其文化成因
李 昇
( 贵州民族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
南宋理学家编选《左传》风尚的形成及其文化成因
李 昇
( 贵州民族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
自《文选》不编选经部著作始,这一选本的编纂传统便延续了下来,然而到了南宋时期,《左传》作为经部著作却被编入了诗文选本之中,且主要是南宋理学家所为,这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其背后必然隐藏了深刻的文化原因。大致而言,北宋的“疑经弃传”思潮、南宋理学家对《左传》文理文风的推崇、南宋进士科的现实需求以及宋代“《文选》学”的衰落等都对编选《左传》风尚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
《左传》选本; 南宋理学家; 疑经弃传; 科举; 《文选》学
中国儒家典籍的称谓自孔子称其为“六经”始,其内容便不断神圣化,这带来的直接结果便如《文心雕龙·宗经》所云:“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1]21儒家典籍已成为“不刊”之经典了,故现存最早的诗文选本《文选》便不录儒家经典,萧统在《文选序》中还特别作了解释:“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裁!”这“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便是泛指儒家所尊奉的经典,萧统亦认为经典不可芟夷剪裁,自此选本的编纂不录经部之文便成了惯例。然而,事情发展到南宋之时却发生了变化,原先为经传的《左传》经过唐代时列为《五经正义》之一,北宋时为“十三经”之一,其学术地位不断提升,由“传”成为了“经”,按选本不录经部之文的惯例来说《左传》也不应入选,南宋之前的选本也确实未见录有《左传》之文的,但到了南宋时期,《左传》突然成了南宋理学家选文的对象,如此一直影响到了明清,使得编选《左传》之文蔚然成风,这种既关联文学史又关联思想史的独特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预设问题。
一、南宋理学家编选《左传》风尚的形成
最早编选《左传》的南宋理学家及选本一般都认为是真德秀及其《文章正宗》,此观点最早是由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提出的:“总集之选录《左传》、《国语》,自是编(按指《文章正宗》)始,遂为后来坊刻古文之例。”[2]1699然而,据笔者发现,最早编选《左传》的选本,就现存文献来看应是林之奇的《观澜文集》。该书未收入《四库全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该书的通行本是清人阮元影宋本《东莱集註类编观澜文集》三十二卷,后收入《宛委别藏》,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8年影印出版,不过《宛委别藏》乃残本,仅甲集二十五卷全,乙集存七卷(卷一至卷七),丙集缺,此本未见录入《左传》文;但清代光绪十年(1884)巴陵方功惠碧琳琅馆影宋翻刻本《东莱集註观澜文集》为稀有足本,甲、乙二集各二十五卷,丙集二十卷,三集凡七十卷完整,现藏于浙江省义乌市图书馆和武汉大学图书馆,今有黄灵庚、吴战垒主编的《吕祖谦全集》第十册《东莱集註观澜文集》,此据碧琳琅馆本整理,由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笔者翻检该本乙集卷十一,发现一篇题为《吕相绝秦书》,乃《左传·成公十三年》中的文章,所以就现存文献而论,最早编选《左传》的选本应是林之奇的《观澜文集》。
林之奇(1112~1176),字少颖,号拙斋,侯官(今福建闽侯)人,学者称其为“三山先生”,谥号文昭,《宋史》卷四百三十三《儒林三》有传。林之奇是吕本中的学生,《宋元学案》将其归为《紫微学案》,清代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七《文昭林拙斋先生之奇学派》亦云:“先生(林之奇)学于紫薇吕公本中,本中学于尹公和靖”[3]460册,126,知明清之人已普遍将林之奇看成是理学家,其学渊源有自,可追溯至北宋理学家尹焞。关于林之奇为何要编纂《观澜文集》,诚如业师杜海军先生所言:“《观澜文集》是林之奇为自己教学需要而编的文学选本”[4]2,林之奇在《观澜集前序》中说:“言,可闻而不可殚;书,可观而不可尽。人之以其蕞尔之闻见而对万古浩博之书言,将以穷其无穷,极其无极,虽末世穷年,曾不足以究马体之毫末,而耄及之矣,此《观澜》之编所由作也。‘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澜,活水也,水惟其活,是以智者得师焉”[5]1140册,496,可知林之奇编《观澜文集》是想示人读书之门径,他认为自己所选之文乃“活水”,可当作范文以为师,故而《观澜文集》乙集卷十一选录《左传·成公十三年》中的文章,并将该文作为乙集之中“书”体首篇,其目的显然是想借《左传》之文起示范作用。
那么《观澜文集》又编于何时呢?这关系到现存古代诗文选本编选《左传》最早时间的确定,所以需要讨论一番。但是就目前仅有的相关文献而论,只能推断出《观澜文集》编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至绍兴二十六年(1156)之间,以下述论之。
《观澜文集》是林之奇在教学活动中编纂而成的,而林之奇的教学活动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绍兴六年(1136)至绍兴二十六年(1156),后期是其晚年。据文献记载,《观澜文集》在林之奇晚年教学活动中已经成书,南宋人姚同为乡贤林之奇写的《行实》中说:“先生家居,弟之邵之子子冲能嗣先生之学。士子会者坌集,先生时乘竹舆至群居之所,诸生列左右致敬,先生有喜色,或命诸生讲《论》、《孟》,是则首肯而笑,否即令再讲;或令诵先生所编《观澜集》而听之,倦则啜茗归卧,率以为常。未几,先生病革,不浃日而逝。”[5]1140册,537林之奇于晚年即宋孝宗淳熙年间用《观澜文集》教学,但“未几”而逝,教学时间很短,《观澜文集》似不大可能编于此时期,故其最有可能编纂于林之奇早年为官之前在福州教书育人之时,也就是林之奇教学活动的前期。
姚同在《行实》中记述了林之奇前期教学活动的起止时间,他说:
绍兴丙辰,以贤书将试南宫……及先生(按:林之奇)西上,日夕以膝下温凊为念,行至北津驿,慨然作诗,有“耿耿一寸心,不能去庭闱”之句,遂改辕以归。先生爱亲之心重于利禄,非学识过人畴克尔。先生声名由此益重,士类归仰如水赴壑,其知向正,学宗正论,皆先生指踪之力。吕紫微(按:吕本中)犹子仓部公(按:吕大器)莅宪幕时,吕成公(按:吕祖谦)未冠,以子职侍行,闻先生得西垣(按:吕本中)之传,乃从先生游……绍兴己巳,先生奏名春官,注长汀尉,未上。乡枢陈公诚之荐试馆职,除正字。[5]1140册,535-536
据此可知,林之奇于绍兴六年(丙辰)弃省试而改辕以归后,声名鹊起,慕名前来求学的学子如水赴壑;至绍兴十九年(己巳)中进士,但待次长汀尉,并未做官;吕祖谦的侄子吕乔年编的《(吕祖谦)年谱》“绍兴二十五年乙亥”条云:“三月,(吕祖谦)从三山林先生少颖之奇游。先生(按:指林之奇)时待次汀州长汀尉”[6]1150册,441,知林之奇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时还在“待次”未做官,也就是说从绍兴六年(1136)至绍兴二十五年(1155),林之奇一直在福州教学。陈诚之(1093~1170)举荐林之奇试馆职的时间应是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七十三记载,林之奇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六月乙酉“召试馆职”(327册,434页),卷一百七十四记载是年九月庚申“左迪功郎林之奇为秘书省正字”[7]327册,456,所以,绍兴二十六年(1156)时林之奇才离开福州前往南宋行在临安做官,故林之奇为官之前在福州教学的时间近20年,《观澜文集》应该编纂于此时期。
又,成书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的《郡斋读书志》未著录《观澜文集》,由此推知,《观澜文集》在绍兴二十一年(1151)前可能还没有成书,所以《观澜文集》应编纂于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至绍兴二十六年(1156)之间。故现存选本最早编选《左传》的时间就是这一时期,而此后不久,也就是公元12世纪中期至13世纪中期,即南宋后期,在南宋理学家群体之中形成了一股编选《左传》的风尚,这首先表现为林之奇的学生吕祖谦(1137~1181)编纂的《左氏博议》二十五卷,该书成书于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虽然目录学家往往将该书归为经部《春秋》类,但该书的性质其实是带有注释的选文,共选《左传》之文 168篇,其内容是“每题之下附载《左氏传》文,中间征引典故,亦略注释”(《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六),这与吕祖谦另外一部经部《春秋》类著作《左氏传说》阐释经旨是大不一样的。
南宋编选《左传》之文影响最大的选本是真德秀(1178~1235)的《文章正宗》二十四卷,该书是我国古代首部大量编选《左传》的文学选本,共选《左传》之文133篇(辞命部分卷一39篇、议论部分卷四32篇、卷五33篇、卷六1篇、卷十三7篇、叙事部分卷十六 21篇),每篇自拟篇名,该书编成于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其编纂体例影响深远;之后,真德秀的门人汤汉(约 1198~1275)编有文章选本《妙绝古今》四卷,也选录了《左传》之文8篇,未自拟篇名,该书编成于宋理宗淳祐二年(1242),其影响不大,至明代时已不知该书编纂者及始末,后四库馆臣据元代赵汸《东山存稿》方才考证出《妙绝古今》的作者乃汤汉;尽管如此,南宋理学家编选《左传》之文的风尚还是为宋人所接受了,其证据便是南宋人王霆震编的《古文集成》七十八卷,四库馆臣认为该书是“南宋书肆本”[2]1702,即民间坊本,该书大量引用吕祖谦《古文关键》、真德秀《文章正宗》、楼昉《崇古文诀》中的评点语,说明南宋民间书坊对南宋理学家文学思想的接受,该书虽只选录了《左传》之文 1篇,但该篇正是林之奇《观澜文集》中所编选的《吕相绝秦书》,此亦能说明南宋理学家编选《左传》之文对南宋民间坊本产生了影响。
凡此种种,均表明在南宋后期理学家编选《左传》之文已形成风尚,该风尚对明清两代选本编选《左传》之文产生了直接影响,透过此种现象探讨背后的过程原因,可发现一段尘封已久的文化事实。
二、北宋“疑经弃传”思潮:《左传》编选的学理基础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在宋代经学史上便有这样一种有相当价值的“思”,即“疑经”,其在中唐之前已有发展,至中唐啖助、赵匡、陆质《春秋》学的产生,“疑经”终于由“思”成“潮”,成为中唐以后及宋人治经的一大特色,南宋王应麟《困学记闻》卷八《经说》引陆游的话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8]1095这是被学者经常引用的一段材料,其内容反映了北宋整个经学界对经典和传注的非议。按照当今的观念,“疑经”是一种创新意识,创新意味着对传统的反拨与超越,也正因为此,编选儒家经典之文才有了学理方面的支撑,这反映在经学上便如南宋理学家朱熹编选《四书集注》,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选出,因其本人对《礼记》的内容有所怀疑,他说:“今只有《周礼》、《仪礼》可全信。《礼记》有信不得处”[9]2203,显然《大学》、《中庸》在朱熹看来是信得的,但也不是全信,因为朱熹还对《大学》、《中庸》的内容进行了改定,如此大胆的疑经思想反映在文学上便是南宋理学家编选《左传》之文。
《左传》虽然在唐初编入《五经正义》,“经”的地位得到官方的确立,但从中唐啖助、赵匡、陆质反驳《春秋》三传开始,《左传》在民间知识阶层中的地位就不断受到挑战。四库馆臣在经部《春秋》类序中说:“说经家之有门户,自《春秋》三传始,然迄能并立于世。其间诸儒之论,中唐以前,则《左氏》胜;啖助、赵匡以逮北宋,则《公羊》、《谷梁》胜;孙复、刘敞之流,名为弃传从经,所弃者特《左氏》事迹、《公羊》《谷梁》月日例耳。”[2]210可知,舍弃《左传》而直寻经义是从中唐啖、赵二人开始的,而整个北宋也承袭了这个传统,“弃传”已成为当时普遍的风气,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六月,司马光在所上《论风俗札子》中便说:“新进后生,未知臧否,口传耳剽,翕然成风……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10]1094册,390,可见《左传》的儒家经典地位在北宋民间早就变得不那么神圣了,尽管北宋官方将《左传》列入了十三经。
或许正因《左传》在北宋民间文化圈中的地位受“疑经弃传”思潮的影响而有所下降,而且北宋人似乎也未将《左传》当成儒家经典看待,只是看成为传,这种环境在南宋又得以延续,故南宋时的文学选本选录《左传》之文也就顺理成章了,因其未违反选本不剪裁“经书”的传统。
三、南宋理学家对《左传》的推崇:《左传》编选的文化背景
北宋“疑经弃传”思潮不仅贬低了《左传》的经学地位,使得编选《左传》成为了可能,同时对《春秋》三传的另外二传《公羊》、《谷梁》的编选也产生了影响,《文章正宗》卷十三便录入《公羊传》之文11篇,《谷梁传》之文10篇,但为何《公羊》、《谷梁》的编选没有形成风尚,而《左传》却成了南宋理学家编选的主要对象呢?这得从南宋理学家推崇《左传》的文化背景入手加以解释。
北宋学者普遍怀疑《左传》是不争的事实,上引四库馆臣之语“啖助、赵匡以逮北宋,则《公羊》、《谷梁》胜”便说明《左传》在北宋的地位甚至不及《公羊》、《谷梁》,要知道唐初编《五经正义》,于《春秋》三传独取《左传》,至北宋时,其地位反不及另外二传。刘敞是北宋怀疑《左传》的第一人,他的理论依据是认为“《左氏》不传《春秋》”,同时,刘敞还反驳《左传》的作者左丘明与孔子的师生关系,他说:“仲尼之时,鲁国贤者无不从之游,独丘明不在弟子之籍,若丘明真受经作传者,岂得不在弟子之籍哉?岂有受经传道而非弟子者哉?以是观之,仲尼未尝授经于丘明,丘明未尝受经于仲尼也。然丘明所以作传者,乃若自用其意说经……”[11]147册,172,也就是说《左传》的经学地位并不如前人所认可的那么高,其内容不是传《春秋》,而是左丘明“自用其意说经”,如此一来,便要“弃传从经”了。宋代理学奠基者之一的程颐也怀疑《左传》,有人问程颐“‘《左传》可信否?’(程颐)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12]266,故有人问程颐“‘宋穆公立与夷,是否?’(程颐)曰:‘大不是。《左氏》之言甚非’”[12]285,可知程颐对《左传》内容是不全信的。同时程颐对《左传》的作者为左丘明也表示了怀疑,有人问“‘左氏即是丘明否?’(程颐)曰:‘《传》中无丘明字,不可考’”[12]266,虽然程颐没有给出肯定的答复,但怀疑之思毕现。由此可见,程颐对《左传》的怀疑程度甚于刘敞,刘敞只是贬低《左传》的经学地位,而程颐直接就否定了《左传》的部分内容,而且对《左传》的作者为左丘明也表示了怀疑。从程颐对《左传》的态度可以看出,北宋理学家是不推崇《左传》的,然而到了南宋,这种情况却发生了逆转,南宋理学家明显表现出对《左传》的普遍推崇。
南宋理学家吕本中(1084~1145)首先从文学创作上对《左传》予以了肯定,他说:“《左氏》之文,语有尽而意无穷,如‘献子辞梗阳人’一段,所谓一唱三叹,有遗音者也。如此等处,皆是学文养气之本,不可不深思也”。又说:“文章不分明指切而从容委曲,辞不迫切而意以独至,惟《左传》为然。”[13]323《左传》文的优长被吕本中拈出而大加推扬,标志着两宋对《左传》态度差异的开始。
之后,林之奇将《左传》之文首次编入选本应该是受到了他的老师吕本中推崇《左传》思想的影响。后来,吕祖谦选《左传》之文说明他对其老师林之奇选《左传》之文的认可和继承,也表明吕祖谦对《左传》的推崇。
与吕祖谦关系甚密的朱熹对《左传》的态度要分两方面来谈,一方面朱熹认为《左传》的作者是左氏,而不是左丘明,上文引程颐的话表明程颐对左氏是否就是左丘明这一问题还不能做出肯定回答,到了朱熹则已然将左氏与左丘明分别看待了。朱熹说:“左氏必不解是丘明”,“左氏叙至韩魏赵杀智伯事,去孔子六七十年,决非丘明”。因为论证了左氏非左丘明,所以左氏是孔子弟子的光环便被抹掉了,于是朱熹对左氏的为人便大加贬斥起来,朱熹说:“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尝谓左氏是个猾头熟事、趋炎附势之人”。正因为朱熹对左氏为人的贬低,故凡《左传》中为左氏议论的部分,朱熹便对其加以扬弃,朱熹说:“《左传》‘君子曰’,最无意思”,“如《左氏》尤有浅陋处,如‘君子曰’之类,病处甚多”,“左氏见识甚卑,如言赵盾弑君之事,却云:‘孔子闻之,曰:“惜哉!越境乃免。”’如此,则专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计,圣人岂有是意!圣人‘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岂反为之解免耶!”[9]2150-2151这是由疑《左传》作者而怀疑《左传》中“君子曰”的内容;但另一方面,朱熹对《左传》的纪事部分还是比较相信的,这尤其表现在《春秋》三传中,朱熹独信《左传》,他说:“《春秋》制度大纲,《左传》较可据,《公》、《谷》较难凭”,“《春秋》之书,且据《左氏》”,又说:“《左氏》所传《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公》、《谷》专解经,事则多出揣度。”[9]2151所谓的“八九分是”指的便是《左传》中除“君子曰”以外的内容了,所以,朱熹对《左传》的纪事部分还是比较推崇的。
同时期的陈骙(1128~1203)则是在古文创作上极力推崇《左传》,他在《文则》中大量例举《左传》之文作为古文准则,如《文则》戊条七云:“若《论语》虽亦出于群弟子所记,疑若已经圣人之手。今略考焉。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质之《左传》,则此文简而整……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质之《左传》,则此文缓而周。”[14]161陈骙以《左传》为标准,将《论语》与之比较以定《论语》行文特点,其推崇《左传》之意甚明。
总之,南宋时无论是在古文创作,还是在经学领域都形成了推崇《左传》的文化氛围,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南宋理学家编选《左传》便是理所当然。
四、南宋理学家的古文观与《左传》文体风格的符契:《左传》编选的内在理路
南宋理学家中形成的推崇《左传》的文化氛围,其形成是有一定的内在理路的,那就是《左传》的文体风格符合理学家的文学鉴赏观。理学是一种讲究道德心性修养的学问,其修养法门之一是观物以体贴“天理”,《二程集·遗书》卷三中记载:“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12]60,这里周敦颐是将窗前之草当成自己以体悟天道,其后学程颢也有相同的做法。张九成《横浦心传录》记载:“程明道书窗前有茂草覆物,或劝之芟,曰:‘不可,欲常见造物之生意’”,可见观物体物是理学家必修的功课,而一旦理学家将目光由外物转移到文学,则这种理学修养方法很自然地便找到了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追求韵外之味的体味观的默契。所以,当有人问程门弟子杨时“诗如何看”,杨时便回答说:“诗极难卒说。大抵须要人体会,不在推寻文义”,“惟体会得,故看诗有味,至于有味,则诗之用在我矣”(《龟山先生语录》卷三)。那怎样的文学作品在宋代理学家看来是可以体会出有味的呢?大凡物以类聚,理学家追求一种洒落、纯净的道德修养,则其崇尚的文风就是与之相近的自然、平淡一类的文风,这类文风在理学家看来是有味的。如黄庭坚《濂溪诗序》评价周敦颐:“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好读书,雅意林壑,初不为人窘束世故”[15]255,而周敦颐的代表作《爱莲说》是追求道德纯净的议论散文,其文风是自然清新的。可以说,自然、平淡并带有余味的文风是南宋理学家普遍的追求,下面举三个例子说明之。
吕祖谦编的《古文关键》是南宋很有名的一部理学家编选的古文选本,该书卷首为“看古文要法”,其中说:“看韩文法‘简古’”,“看柳文法‘关键’”,“看欧文法‘平淡’”,“看苏文法‘波澜’”,这“简古”、“关键”、“平淡”、“波澜”便是吕祖谦在“要法”中提到的“文字体式”,显然“简古”、“平淡”与“关键”、“波澜”相对,前者是自然,后者是余味,均是被吕祖谦所看重的古文“体式”。与吕祖谦交游甚深的朱熹也有同样的古文观,他说:
今人作文,皆不足为文。大抵专务节字,更易新好生面辞语。至说义理处,又不肯分晓。观前辈欧、苏诸公作文,何尝如此?圣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后世由此求之。使圣人立言要教人难晓,圣人之经定不作矣。[9]3318
显然,朱熹也是推崇“坦易明白”亦即简古、平淡的文风,并举欧阳修、苏轼与圣人之文为例。朱熹又说:“前辈文字有气骨,故其文壮浪。欧公、东坡亦皆于经术本领上用功”,也就是说朱熹还推崇欧、苏二人文字的气骨,这种文字风格即吕祖谦提到的“关键”、“波澜”,所以朱熹与吕祖谦在推崇古文文风的观点上是相同的。同时期的陈骙在现存我国第一部文话著作《文则》中也提出了相近的古文观,他说:“文作而不协,文不可诵。文协尚矣,是以古人之文,发于自然,其协也亦自然”,又说:“且事以‘简’为上,言以‘简’为当。言以载事,文以著言,则文贵其‘简’也。文‘简’而‘理’周,斯得其‘简’也。”[14]137-138这里的文协、自然与吕祖谦提倡的平淡相近,文简又与简古相同。故南宋的理学家对于古文文风中自然、平淡又饶有余味的喜好是相近的,而《左传》文体风格恰好又符合南宋理学家的古文鉴赏观,很多理学家便对《左传》之文的风格提出了赞赏,下面亦举三例说明之。
吕本中是南宋理学家中较早对《左传》文体风格予以肯定之人,上文第三部分已引述吕本中的话,“所谓一唱三叹,有遗音者也”,这是对《左传》之文有“波澜”、有余味特点的一个概述。陈骙对《左传》文体风格也有相同观点,他说:“文之作也,以载事为难;事之载也,以蓄意为工。观《左氏传》载晋败于邲之事,但云:‘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则攀舟乱刀断指之意自蓄其中”,陈骙也发现《左传》之文有含蓄的特点,读之须慢慢体会。二人对《左传》之文特点的概括并不是理学家的独到见解,以文学著称的苏轼早有如此的看法,苏轼说:“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尽,尤为极至,如《礼记》、《左传》可见”,则《左传》之文含蓄有味的特点应是宋代理学之士与文学之士的共同认识,而这种认识又恰与理学家对于古文之简古有味、平淡波澜的要求相一致。所以,南宋理学家编选《左传》便有了内在的文学理路。
五、南宋进士科的介入:《左传》编选的现实需要
科举考试一向是古代文士读书的风向标,所以古代科举考试制度的转变必然影响士人读书的内容。下面就宋代科举考试所涉及《左传》的部分进行简要论述,以说明南宋进士科考试与《左传》编选出现在南宋的关系。
宋代科举中除制科、博学宏词科和常科中的明法科外,常科中的进士科、诸科和明经科的考试内容大都涉及《左传》,只因宋代科举考试经常改革而情况会有所变化。《宋史·选举志一》中说:“初,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16]2410,《九经》至“学究”7科总称为“诸科”,其考试内容很明显包括《左传》;而明经科的考试内容是“并试三经,谓大经、中经、小经,各一也。以《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谷梁传》、《公羊传》为小经”(《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三三),《左传》作为“大经”被设于明经科考试中,可见《左传》在北宋官方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地位,但这两科在宋神宗时被废罢,“神宗熙宁四年(1071)二月,罢明经、诸科”(《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一)。也就是说,与《左传》联系最大的考试科目就是宋代最被看重的进士科了。
北宋的进士科向来存在诗赋取士与经义取士之争,南宋人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三《四科》中对这一史实进行了概括(因内容较多,不在此引述),祝尚书先生据此总结说:“要之,宋初沿唐、五代之旧,试之以诗赋。熙宁时改为经义而罢诗赋。历元祐诗赋、经义兼收之制,再到绍圣罢诗赋而用经义的反复,于南宋初才敲定为诗赋、经义两科分立,得到近乎‘双赢’的结果。”[17]44宋初进士科以诗赋取士,“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16]2410,可见宋初至熙宁时王安石变法之前,诗赋取士不涉及《左传》。等到王安石变法,改诗赋为经义取士,并以《三经新义》作为考试用书,与《左传》更无关联,加之又罢明经、诸科,则《左传》在宋神宗时便被彻底排挤出北宋科举考场之外了。至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乃立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凡诗赋进士,于《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内听习一经……凡专经进士,须习两经,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书》、《易》、《公羊》、《榖梁》、《仪礼》为中经……”[16]2420-2421则《左传》在元祐时诗赋和经义取士考试中均占有一席之地,至宋哲宗绍圣初年(1094)虽改用经义取士,考试内容却仍如元祐时期,《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五五载:“绍圣元年(1094)五月四日诏:进士罢试诗赋,专治经术,各专大经一,中经一”。但宋徽宗时因党争而禁“元祐学术”,经义取士重新以《三经新义》和《字说》为考试用书,故《左传》在北宋末科举考试中又一次被废止了。综观北宋整个进士科考试,《左传》在其中的地位一直不显,仅哲宗朝被列为考试用书,但到南宋时,《左传》与进士科的关系却紧密起来。
宋高宗即位后不久就开科取士,因将“靖康之难”归因于新法,故考试内容尽废王安石《三经新义》、《字说》,而改用宋哲宗元祐之法,《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二一记载建炎二年(1128)五月三日,中书省言:“已诏后举科场讲元祐诗赋、经义兼收之制。今参酌拟定……《元祐法》:‘不习诗赋人令治两经’,今欲习经义人依见行,止治一经。”(《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二一)《元祐法》中所谓的“两经”即“大经”和“中经”,《左传》属“大经”,故宋高宗建炎年间的进士考试涉及《左传》,而这一进士考试制度又被确定下来,一直至南宋末,所以整个南宋时期的进士科考试都与《左传》相关连。既然如此,那么作为绍兴年间因教学需要编的《观澜文集》,其收录《左传》的动因便容易解释了,这显然是受到了南宋初期进士科考试涉及《左传》的影响。至于后来吕祖谦编《左氏博议》,也是出于科举考试的原因,吕祖谦在《左氏博议序》中说:“《左氏博议》者,为诸生课试之作也。始予屏处东阳之武川……居半岁,里中稍稍披蓬藋从予游,谈余语隙,波及课试之文,予思有以佐其笔端,乃取《左氏》书理乱得失之迹,疏其说于下”[18]152册,296,可知吕祖谦编选《左传》之文亦如其师林之奇一般是因教学或者说是因科举考试所需。总之,因为整个南宋时期进士科考试内容都涉及《左传》,故南宋时《左传》的编选便有了现实的需要,这也促进了南宋时期《左传》编选风尚的形成。
六、宋代“《文选》学”的衰落:《左传》编选的历史契机
唐代至北宋中期进士科以诗赋取士,这推动了《文选》的传播,故这一时期也形成了钻研《文选》注释的“《文选》学”,但宋神宗时罢诗赋以经义取士,《文选》学也由此衰落下去,南宋王应麟在《困学纪闻》卷十七中对此作了概括:“李善精于《文选》,为注解,因以讲授,谓之‘《文选》学’……(宋初)江南进士试《天鸡弄和风》诗,以《尔雅》天鸡有二,问之主司,其精如此,故曰:‘《文选》烂,秀才半’。熙丰之后,士以穿凿谈经,而‘《选》学’废矣。”这是历代学者论述宋代“《选》学”衰落时必引的一段材料,笔者据此材料认为王应麟是借“《选》学”衰落而贬斥北宋中后期以经义取士的科举制度。但经义取士毕竟只是《文选》学衰落的原因之一,宋代学者对《文选》“去取失当”(苏轼《题〈文选〉》、“陋于识者”(苏轼《答刘沔都曹书》)的批评也应是《文选》学衰落的重要原因。两宋之际的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便说:“近时士大夫以苏子瞻讥《文选》去取之谬,遂不复留意”[19]60,《文选》因苏轼的讥讽而受到世人的冷落,这显然是当时《文选》学衰落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意味着《文选》经典地位的衰落,南宋理学家编纂诗文选本时便以《文选》为矢的而反拨之,这或许就是《左传》编选的一个契机。
如果说宋代学者批评《文选》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话,那么南宋理学家编纂诗文选本就将这种批评付诸实践了。两宋之际的马永卿在《懒真子》中对《文选》不录《兰亭集序》的批评是南宋之前最为严厉的,他说:
《兰亭序》在南朝文章中少其伦比,或云:“丝即是弦,竹即是管。今迭四字,故遗之。”然此四字,乃出《张禹传》,云:“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管弦”,始知右军之言有所本也。且《文选》中在《兰亭》下者多矣,此盖昭明之误耳。(《懒真子》卷三)
文中“或云”是指北宋学者对《文选》不录《兰亭集序》的解释,马永卿对这种回护《文选》的解释予以了反驳,认为《兰亭集序》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昭明太子萧统之误,录入了很多文学水平不如《兰亭集序》的文章,按照苏轼的话说就是“去取失当”。之后不久,宋高宗绍兴年间林之奇在《观澜集后序》中说:
夫《文选》不收《兰亭记》,《文粹》不收《长恨歌》,识者于今以为二书之遗恨。由其所取乎斯文者,以为尽于其书,故其所遗者,人得而恨之。余方收《选》、《粹》之所遗,其敢自谓无所阙轶乎。[5]1140册,496
林之奇也认为《文选》不收《兰亭集序》乃该书之“遗恨”,遂收其所遗,将《兰亭集序》編入《观澜文集》乙集卷二十二,并把《兰亭集序》作为“记”体文的首篇,这是对北宋学者批评《文选》不收《兰亭集序》的积极响应,将批评付诸了行动。
相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例。苏轼对《文选》的批评是宋代最有名的,他在《题〈文选〉》中说:“观《渊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独取数首。以知其余人忽遗者甚多矣。渊明《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乃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20]2093苏轼认为《陶渊明集》中有很多“可喜”之作,然《文选》只选取了其中几篇而已,“遗者甚多”,尤其是遗漏了《闲情赋》,而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白璧微瑕者,唯在《闲情》一赋”[21]614,苏轼认为此乃萧统对《闲情赋》之讥,是“小儿强作解事者”,按照苏轼自己的话说就是“陋于识者”。或许是林之奇认同了苏轼的观点,遂将《闲情赋》这一《文选》所遗之文收录在了《观澜文集》丙集卷四中,而《观澜文集》也成为了现存选本中最早收录《闲情赋》的选本。
由此可知,林之奇收《文选》所遗之文是林之奇编纂《观澜文集》的思想之一,《文选》未录《左传》文,则《左传》也就有了编选的可能,这是宋代《文选》学衰落的结果之一。
除了《观澜文集》,南宋理学家真德秀编的《文章正宗》也是以《文选》为反拨的对象,真德秀在《〈文章正宗〉纲目》中说:
“正宗”云者,以后世文辞之多变,欲学者识其源流之正也。自昔集录文章者众矣,若杜预、挚虞诸家,往往堙没弗传,今行于世者,惟梁昭明《文选》、姚铉《文粹》而已,繇今视之二书,所录果皆得源流之正乎?
此番言论明显表明真德秀不满《文选》,认为其
未得“源流之正”,这一观念与当时南宋后期《文选》学衰落背景下反拨《文选》的社会思潮是颇为一致的,现有一例可说明之。与真德秀同时期的林駉,他在《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二“《文选》、《文粹》、《文鉴》”条中说:“虽然文章美恶自有定论,去取当否,要终自见,吾平心论之,则曰《选》、曰《粹》、曰《鉴》之所集,有不难辨者……董子之策《贤良》,得伊周格心之学,而例黜之,可乎?”[22]942册,27-28林駧此言是针对《文选》不收董仲舒《对贤良策》而提出的批评,他认为董仲舒之文“得伊周格心之学”,不应被《文选》黜之,这显然是南宋后期理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下的一种反拨《文选》的观念,与真德秀认为《文选》未得“源流之正”的观点接近。而真德秀《文章正宗》卷七录有董仲舒的《对贤良策》三篇,可见南宋后期在理学思想的影响下对《文选》去取失当的批评与《文选》学衰落的背景下反拨《文选》的选文实践几乎形成了统一的步调,加之上文提到的南宋理学家对《左传》的普遍推崇,则《左传》的编选在南宋后期的兴盛也就成了必然的结果。
结言之,南宋理学家编选《左传》风尚的形成受到多重内外机制的影响。就内部因素而言,南宋理学家对《左传》的推崇是《左传》编选的内在驱动力,《文选》学的衰落正好为《左传》的编选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就外部因素而言,“疑经弃传”思潮下《左传》经学地位的下降则为《左传》的编选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而南宋进士科的考试内容包括对《左传》的考查则加速了编选《左传》的形成。
[1](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M].《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杜海军.林之奇《观澜文集》及其对唐宋派形成的影响[J].闽江学院学报,2010,(6).
[5](南宋)林之奇.拙斋文集[M].《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南宋)吕祖谦.东莱集·附录[M].《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宋)王应麟,著.(清)翁元圻,等,注.栾保群,田松青,吕宗力,校点.困学纪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9](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北宋)司马光.传家集[M].《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1](北宋)刘敞.春秋权衡[M].《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2](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3](南宋)张镃.仕学规范[Z]//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一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14](南宋)陈骙.文则[Z]//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一册)[Z].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15]郑永晓.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16](元)脱脱,等,撰.宋史[M].二十四史简体字本,北京:中华书局,2000.
[17]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8](南宋)吕祖谦.左氏博议[M].《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9](北宋)张戒,撰.陈应鸾,笺注.岁寒堂诗话笺注[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
[20]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1]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2](南宋)林駧.古今源流至论[M].《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A Probe on the Style Forming of Zuozhuan’s Compilation by Moralists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its Cultural Factors
LI Sheng
( School of Literature, Guizhou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Guiyang, Guizhou 550025, China )
Since the beginning of Literary Selections not being compiled as the Classics Works, this kind of compilation tradition had been passed down, while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book of Zuozhuan considered as the Classics was placed in the works of poetry anthology mainly done by moralists at that time, which became a unique literary phenomenon in which the profound cultural factors must be concealed. In general, there are such few factors which can contribute to the style forming of Zuozhuan’s compilation as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suspecting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nd discarding the book of Zuozhuan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veneration for the liberal art and style of Zuozhuan by moralists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practical demand of the highest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the decline of the study of Literary Selections.
the anthology of Zuozhuan, the moralists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suspect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discard of Zuozhuan, imperial examination, study of Literary Selections
I206
A
1673-9639 (2015) 05-0030-09
(责任编辑 白俊骞)(责任校对 郭玲珍)(英文编辑 何历蓉)
2015-06-09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理学思想与选本批评:宋明理学家选本编纂研究”(14XZW040)及贵州民族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
李 昇(1982-),湖北孝感人,文学博士,现为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与文学。
——现代新诗选本研究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