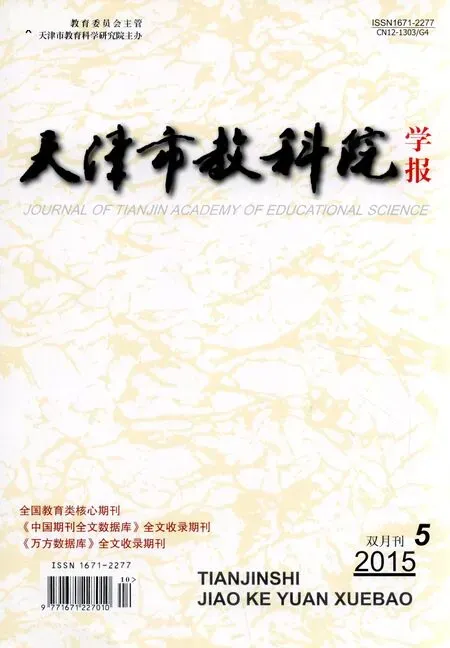宏观教育政策的研究与决策
马开剑 杨春芳
(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宏观教育政策的研究与决策
马开剑 杨春芳
(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国家管理教育的基本手段就是制定和实施教育政策,教育事业发展的“五年”规划,就属于宏观教育政策范畴。
一、好的教育政策必须要有研究支撑
宏观教育政策怎么制定?这似乎并不是问题,我们曾经习惯了领导就是决策者,教育政策就是由领导凭其经验、立场、观点或意见进行决策。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政策的制定走上了科学化和民主化之路,调研、座谈、集体讨论成为了政策制定的常见活动。只是,这些活动仍然是经验性、意见性的为多。
政策都是指向具体实践的,或问题,或目标,或对象,即使是在社会安顺时期,好的教育政策也不可能单凭“拍脑袋”决策,否则,造成“政策祸害”也是可能的。当经济社会正经历剧变、转型时,教育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环境也就更复杂,要使教育政策制定得更加科学可行,就必须依靠高水平政策研究来支撑。
正是因为认识到了好的教育政策必须要有研究支撑,我国早已开始重视政策研究的支撑,重视发挥专家的作用。以2008年国务院启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称《规划纲要》)调研编制工作为例,将所有宏观政策议题分为11个专题、36个课题进行前期研究,动员了约500名专家参与其中,这些专家主要来自国家教育发展中心、教育科研机构、高校和中国教育学会等,每个专题和课题都必须提交正式的研究报告,这些研究成果为最终的规划纲要文本提供了主要支撑。与之类似,天津正在研究的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也将相关问题分作13个课题,动员了全市教育科研机构和高校近百名专家参与其中,同样经典地体现了研究支撑教育政策的理念。
事实上,近十几年来,一些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政策研究,政府无论是要提出政策议题,还是进行政策实效评估,都希望得到研究部门的支持,这正如国际教师工会的发现,“放眼世界,我们会发现制定政策的方式改变了,而且政治决策过程也改变了。最重大的变化之一就是政府非常强调‘证据为本’(evidence-based)的政策和措施”。“证据为本”的政策理念强调教育政策必须立足于科学研究,这里的科学研究不同于前面所说的一般性调研与座谈,而是将政策决策作为一门科学,对相应的政策议题,运用恰当的研究方法和规范的研究过程,最后获得可靠的结论或政策建议。所谓“证据”是指经过研究整理后的数据,是强调政策研究必须有数据和事实的支撑。“没有数据的支撑,你只不过是一个持有观点的普通人”。相比而言,我国政策研究者习惯于对政策议题进行道德和价值判断,而忽略和不善于进行数据或事实分析,这是我国政策研究者的短板。
关于好的教育政策需要研究支撑、而政策研究要有数据支撑的问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文东茅教授2014年10月在华东师大的一个座谈会上,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关于如何合理分配央属高校招生名额,有两种不同主张,一种是全国统一高考,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另一种是按考生人数比例平均分配招生指标,这显然是一项惹人关注的教育政策问题。那么,究竟该怎么办呢?文教授找到了某年自主招生“北约联盟”的成绩数据,这次考试相当于北大组织了一次小的全国统考,统一试题、统一阅卷。这次考试的考生是30131人,北大每年的招生规模大约是3000人,如果从高分到低分取前10%,那么,北京、浙江、江苏、湖北、辽宁五省市录取人数将占到46.4%,而西藏、海南、青海、宁夏、贵州、云南、甘肃、内蒙古、广西、新疆等十省区合计只有60人,仅占1.98%,其中有六个省(自治区)没有一人入围。面对这一数据,就连持第一种主张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不能简单地依据分数从高分到低分录取,这就是数据的说服力。而如果按第二种主张,就会很容易地发现进入同一央属高校但来自不同省市的学生,分数相差巨大,会让人感觉到另一种不公平。这里发现,决策一项教育政策,确实不那么简单,但同时也能感受到,数据有说服力,能说服人。
二、单维研究难以支撑教育政策决策
既然好的教育政策需要研究支撑,那为什么在实践中还常常发现政策研究的成果得不到认可、采纳,甚至还被批呢?政策研究成果不被认可的现象在我国乃至世界各国的确司空见惯。
究其原因,首先要检讨研究成果自身的质量问题,如果研究过程中因权威意见、研究者立场、成见或预期等因素,而选择性地片面使用相关数据,或根本缺乏相应数据,或政策成果的语言体系过于学术,或政策建议的视角过于单一或过于理想化,那么,这样的政策研究成果就容易被批为“看不懂、没法用、行不通”,就不能对政策决策起到应有的支撑作用。更不要说,不少学者还没有走出“意见决策”的窠臼,囿于自己所秉持的理论,本能地以自己所认同的价值观和学术观点来提出政策建议,其价值就可想而知了。
教育政策研究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许多教育政策研究课题所针对的只涉及教育政策决策过程的某一环节,或复杂教育问题的某一方面,是单一维度的研究,强调学术研究的封闭与规范,这当然是学者特别是高校学者的强项。只是,只要是单一维度或片面的,就算研究得再精致,也不能保证产生一个好的教育政策。实际上,没有任何一项教育政策是单凭某一视角或维度的研究成果就决策的,结果是“按下葫芦起来瓢”,于解决教育问题无甚裨益。
现实中的教育实践与相关的教育问题是极其复杂的,或许正是这种复杂性,使得一项教育政策的出台,必然受到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对教育的预期、资源配置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另一方面,从某一项研究报告那里所能获得的政策又往往是单维度的,甚至对同一教育问题,因研究视角的不同,得到互相矛盾或相反的政策建议,都是不鲜见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不会轻易采信某一研究的政策建议,这正因应了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点穴之言:对于政府而言,最可恨的莫过于见多识广,因为它使作出决定的过程更加复杂和困难。
既然单维研究难以支撑教育政策决策,而好的教育政策还需要研究的支撑,那么,政策研究者所能做的就是提高研究质量,将自己的研究置于多维视角和多重数据上,这就要求将教育政策研究建立在大数据之上。1997年到2003年期间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实施了一项名为“学前教育有效供给”的项目,这是一项长期跟踪不同类型学前教育机构中近3000名儿童成长与发展状况的大样本研究,该研究最突出的就是建立了相关数据库,采集了大量数据,包括:这些儿童在历次测验中的成绩、儿童及其家庭背景(出生时体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儿童父母的访谈记录、观察评定量表等。正是借助于这种大数据,他们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结论,有力地促进了英国一系列学前教育政策的出台。这里,我们发现,不是只有数字才是数据,质性的访谈资料、家庭状况描述、个体的心理分析等,都属于数据。相对于传统上的统计数据,大数据强调更精细化地捕捉教育因素动态过程各层面的数据变化,以及由数据变化展现的复杂因果细节,它聚焦政策对象的微观层面,同时,以其信息搜集、交换与反馈过程的迅速乃至自动生成的即时性,实现教育政策的动态调整与预测视野的扩大。
数据库是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科学化的基础工具。遗憾的是,我国的教育数据库信息单薄,数据质量常受干扰,而且“保密”于具体部门,基本不对普通的教育政策研究者开放。能否建立信息丰富、数据可靠的教育数据库,并面向教育政策研究者开放,已成为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和决策科学化的关键。当然,我们不否认观点、意见等仍然具有政策价值。
三、教育政策决策要经历利益博弈
即使是基于丰富的大数据进行了周密的研究,也难以直接地产生最终的政策决策。宏观教育政策一般涉及教育重大政策,类似“十三五”教育发展规划编制这样的政策决策过程,是一项跨部门、跨学科、跨领域甚至跨辖区的重大工程,更重要的,它要跨越不同群体,这就涉及政策决策必须考虑到相关群体的态度与反应,因为一项教育政策的决策一定会带来利益的调整,教育政策决策的背后还有利益博弈。比如,研究《规划纲要》时,曾有设想将民办学校分为营利和非营利两种,进行分类管理,但因为民办教育人士强烈反对,最后在这一问题上模糊化,未明确提及。另一个比较明显的案例领域,就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就学问题,城市当地人与外来务工人员在此问题上存在利益冲突,因而政策主张也相异。故,教育政策的决策过程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过程。教育研究的科学化代替不了教育政策决策的民主化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政策的决策主体被普遍默认为政府,包括各级党委、人大和人民政府,这可看作是决策主体的单一,它容易产生的直接反应是群众对新政策不理会、不关心、不认同。随着社会的文明与进步,除各级教育行政机关的领导外,为政策制定提供咨询的专家智囊和作为政策执行者的下级政府官员以及作为政策承受者的各类公众群体,也逐渐地参与到了教育政策的决策中来,成为了不同程度的决策者。在这方面,《规划纲要》的研究过程就堪称典范。不仅向教育界知名人士咨询,同时也向科学界、经济界等其他领域的人士咨询,还向外国专家咨询,甚至还两次面向社会就重大教育问题公开征求意见,倾听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立场、意见等,体现了宏观教育政策决策的民主化。
以往,我国教育政策研究与决策普遍忽视政策关涉群体的利益分析,事实证明,这不是一种客观态度,利益分析应作为教育政策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政策学家德罗尔认为,“宏观政策研究和政策分析应遵循大致的正确总比精确的错误要强的原则”。因此,如果要在教育政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之间排序的话,那么,政策决策的民主化应该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