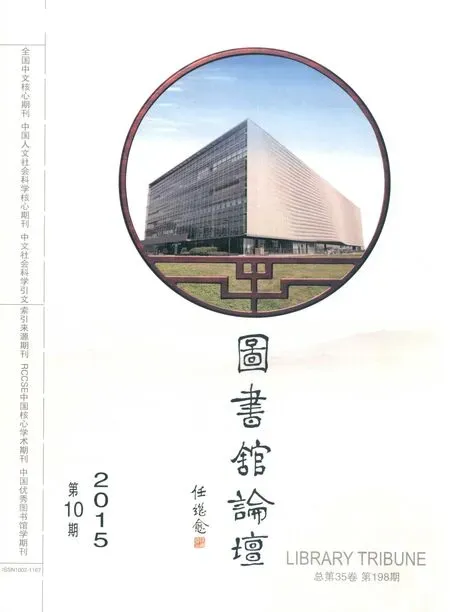公共数字文化的服务主体职能*
马岩,孙红蕾,郑建明
公共数字文化的服务主体职能*
马岩,孙红蕾,郑建明
公共数字文化是社会信息化环境下公共文化发展的新形式。社会信息化使公共文化需求出现新变化,推动数字文化服务主体法律地位的确立。社会信息化环境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体承担新角色——公共数字文化事业的信息整序者、服务提供者和问题反馈者。要转变角色,须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信息的收集、整序与加工、深度整合、安全保护及矛盾调和等方面完善职能。
数字文化 公共文化 服务主体 职能
信息化社会发展进程中,信息资源海量增长,信息技术不断进步,推动公众信息意识不断增强,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向数字化、开放化方向发展。为适应这一转变,公共数字文化事业应运而生[1]。与传统公共文化事业相比,公共数字文化事业构建主体面临更加复杂的公共需求,其在信息社会中的角色和职能定位关乎公众文化信息需求能否很好地得到满足。
1 社会信息化为公共数字文化事业带来机遇与挑战
1.1 社会信息化带来公共文化需求的转变
随着计算机、通讯和网络技术发展,公众在大数据浪潮里接受各种信息的冲击,自由平等意识上升到新的高度,民主意识不断增强,从而要求政府由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型,表现在公共数字文化领域,主要是对政府公共信息的获取方式和服务要求的变化上。社会信息化环境下,公民不仅要求普遍、均等地享受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更要求参与到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去;不仅要求可以自由地分享公共信息和公共服务,还要求有机构能够把公共信息和服务资源充分整合,以便灵活使用。这些要求的转变自然会带来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体工作量的增加,对其工作能力、服务意识的提高是一种挑战,但也为其提供了充分发挥社会价值的机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体应发挥自身专业优势,成为公众对整序后的公共数字文化信息的获取与反馈平台[2]。
1.2 社会信息化推动确立数字文化服务主体的法律地位
海量的信息资源和便捷的通讯系统带来公民政治意识的空前觉醒,而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法制化,公共文化建设要走法制化道路,公共数字文化事业也不例外。就公共信息而言,2007年4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6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向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提供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为档案馆、图书馆这些文化事业单位获取整合、加工政府信息给公民提供灵活利用提供了依据。该条例还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设置政府信息查阅场所,并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这无疑是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给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的重要定位,赋予其新的重要职责——建立提供政府信息资源的平台[3]。文化事业单位参与政府公共文化信息服务工作是在履行法定义务,其有权利且有义务对政府信息资源进行开发,为公众提供全面的政府信息公开与咨询服务,保证公众自由获取政府信息,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权利。同时将公众需求反馈给政府,履行其信息中介者的职责。
2 数字文化事业及其服务主体概述
区别于文化产业的盈利性,公共文化事业的本质在于公益性。公共文化事业主要是指公共文化机构利用公共资源,以普遍、公平、均等地满足大众的基础性文化需求为目的,提供一切文化服务和产品的总和。数字文化事业,顾名思义,即在传播方式、保存状态、利用形式等方面呈现数字化、网络化、开放化特点的文化事业,体现了公众对公共文化权利的数字诉求,是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新形态和未来的主要趋势,其构建主体和服务主体与传统文化事业基本一致。文化事业的公共性决定了其构建的主体必须是政府[4]。只有在政府的主导下,利用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提供的公共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才能保证其普遍均等性[5]。但政府作为决策者和监督者,几乎不会直接为公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6],在欧美,直接为公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被称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7](public service unite,简称PSU),在我国,这一角色由特定文化事业单位承担,这是我国数字文化服务主体在构成上的独有特色。
文化事业单位作为一种依靠政府财政资助而运转的公益性文化机构出现在我国的编制组织系统中,承担着在政府领导下,为公众提供直接的公共文化服务的责任[8]。从资金组织、业务运转和服务目的来看,有学者将其分为营利性文化事业单位和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笔者认为是不科学的,但是我们可以从资金构成角度,将其分为政府“差额投入”和“全额投入”两种类型。“差额投入”的文化事业单位,例如文艺演出单位、国有期刊图书书社、广播电视电影、出版单位等,政府提供其组织、运营的部分资金,其绩效资金则通过为特殊需求人群提供收费服务获取,其在性质上既是事业法人,又是企业法人,并且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这种类型的文化事业单位更偏向于转向企业化,不作为公共数字文化的服务主体。政府“全额投入”的文化事业单位,例如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其组织、运转资金基本上全由政府承担,是国民收入二次分配的产物,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公众提供免费的、均等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是我国当代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主体。这些文化事业单位可收集整合支持上级决策的信息资源,为政府制度设计提供舆情和立法等方面的信息产品和服务,支持各级政府公共数字文化政策的制定、实施和完善,是国家公共数字文化政策制定机构的“智囊团”。
3 社会信息化环境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体的角色定位
社会信息化环境下,公众权利意识觉醒。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最基本的就是保障公众对公共文化和服务信息的知情权,最重要的就是利用这些信息为公众提供高层次的信息服务。在这种形势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体应把握住社会信息化带来的机遇,成为公共数字文化的信息整序者、服务加工者和问题反馈者。
首先,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体要成为公共数字文化事业的信息整序者。公共数字文化自身的数字化、开放性导致其呈现凌乱分散的状态,虽然公众可以从某些网站获取一些关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都是零散的、不完整的。需要一个专门机构对这些公共信息和服务资源进行整理、加工、存储。我国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体,面对信息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和人类具体信息需求的矛盾时,作为信息整序者,完成公共数字文化信息的收集、整理,可以更好地满足公众的需求,也可以节省资源、降低成本、激励创新。
其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体要成为公共数字文化事业的服务加工者。我国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体,本身都属于专门的信息机构,这些机构的任职人员对于搜集、整理、加工、检索信息资源十分精通,能够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检索和咨询服务,此外,优越的硬件设备、丰富的服务经验使其能够熟练地获取有关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信息,并且可以对公共信息和服务资源进行加工整合,使得这些资源充分发挥作用,可以为企业和个人提供灵活的应用。
最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体要成为公共数字文化事业的问题反馈者。我国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公共数字文化事业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加上政务公开工作十分保守,公众的信息知情权、文化参与权长期得不到保障[9]。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体应抓住社会信息化带来的技术和法律机遇,承担起公共文化服务问题反馈者的职责,建立公众文化参与和反馈平台,为公众提供公共数字文化事业信息的检索与利用服务的同时,预留公共发言空间,并及时整理反馈给相关文化部门,以满足公众参与公共数字文化事业建设的需求。
4 社会信息化环境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体的职能分析
社会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为公共数字文化信息资源的整合、开发利用提供更为先进的技术条件和更加完善的政策法律环境,也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体服务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围绕其信息整序者、服务加工者和问题反馈者的角色定位,其职能拓展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1)全面准确及时收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信息。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最基本的就是保障公众对公共文化和服务信息的知情权。对公众而言,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信息的获取还是很困难的。传统上,我国政府政务是非公开不透明的,政府很大一部分信息处于封闭状态,非机构人员无法掌握,这自然会对公众获取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信息造成阻碍。近年来,尽管随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推进,情况有所改善,一些政府信息可以在政府官网上得到公开,但是数量较少,数据粗糙,更新不及时,甚至出于政府形象考虑,已公开的数据有失真情况[10]。所以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体需要发挥其专业优势,利用其在获取公共信息方面的天然条件,尽可能全面准确及时地收集政府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信息,以促进其社会价值的实现。
(2)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信息进行整序加工,以供公众方便地检索利用。我国政府对各类公共信息普遍缺乏细致的集约化经营,使得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信息以无序状态零散地堆积,令公众很难找到想要的信息。要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需要有机构对这些信息进行组织整序。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体作为专业的信息整理、组织、加工机构,应该承担这一职能,对公共文化服务信息进行登记并编制分类办事指南等,利用自身的专业性为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检索服务。除了能够检索到相关信息,为公众提供公共数字文化高水平的信息服务,还需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体对信息内容进行深加工,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信息的开发和利用。公众在其工作、生活中,经常会遇到不知道哪些公共数字文化信息资源能够再利用,如何获取这些资源,可以享受哪些优惠政策等问题[11]。以生产活动为例,企业在没有信息分析技术的情况下,对于其获取一些涉及公众生活、娱乐的直接宏观数据根本无法理解,更不必说获取信息以达到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体需要利用自身专业优势对政府公共数字文化信息进行深加工,以达到服务公众的目的。
(3)针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信息的数字形式,开展数据挖掘,进行深度整合。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信息的数字形态使得高技术的应用成为可能,数据挖掘便是一个值得应用的技术。数据挖掘是从泛在的、巨大的模糊数据集合中,发掘出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对某种活动有利用价值的知识的过程[12]。把数据挖掘技术运用到政府公共数字文化信息再利用中去,使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体在整合其获取的政府信息过程中,一方面为公众提供尽可能精确、全面的对口信息,提高信息获取效率;另一方面,它可以通过信息分析结果为政府部门提供制定信息策略的建议,促进政府科学行政。此外,这个过程对其自身而言也是信息化水平的提升。总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体应该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把对公共数字文化信息的整合从形式整合逐步向内容整合转化。考虑到个体单位无法很好地整合所有的公共数字文化信息资源,全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体可以联合起来,采取分层建设、分工合作、共建共享等模式进行合理地整合公共数字文化信息资源。
(4)合理审查,加强技术,保障公共数字文化信息安全。公共数字文化信息资源不仅是重要的国家资产,而且还是需要精心管理的资产。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体在利用公共信息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要注重保障公共数字文化信息安全。一般而言,公共数字文化信息安全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从涉密性角度而言,政府公共数字文化信息的保密性与公众获取信息的要求是互相冲突的,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体协助政府做好信息审查、分级工作,界定公共信息的密级程度,将涉及国家安全和机密的信息进行分类剔除,以更好地提供公共信息服务;二是从技术角度而言,公共数字文化信息与传统文化信息相比,其开放度、透明度有了明显提高,面对公共信息利用者数量增多、网络信息环境风险加大等等的挑战,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体应主动学习,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专门网站的改版、专题数据库建设和数据自动化系统的建设等方面加强技术支撑,保障公共数字文化信息安全。
(5)做好中介调和者,平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信息与个人信息间的利益冲突。由于一些具有开发价值的公共数字文化信息资源,往往会和个人文化活动行为相关,因此,在开发公共数字文化信息资源为公众服务过程中,不可避免会触及一些个人的信息权利。怎样做到既能挖掘出公共文化信息资源的价值并加以利用,又保护好公众个人信息权利是文化信息服务主体要解决的问题。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指出涉及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必须是个人申请后依法公开。也就是说,对于涉及个人信息的公共信息,只有经过当事人授权后才能公开乃至加工利用。个人对使用方的信任度决定了其提供个人信息的意愿程度。因此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体应在信息收集、发布、整合过程中及时主动与当事人联系,沟通获取其授权意愿,并尽可能只公开统计数据或者提供统计工具方式,保护个人信息源数据不被泄漏;实在无可避免时,应该把对个人利益的损害降到最低。
5 结语
公共数字文化事业是以服务公众为目的,以共享为手段的新型公共文化事业,核心价值目标是最大限度地保障公众获取公共数字文化信息权利、享受公共数字文化信息服务。信息化时代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体应抓住发展机遇,围绕公共数字文化事业的信息整序者、服务加工者和问题反馈者的角色定位,把自己的工作重心由过去时态转变为现在时态,一方面要积极收集、处理、加工公共数字文化信息,帮助公众及时地获取优质的公共数字文化信息资源,保障公众的知情权,还要利用专业优势,提供公共数字文化信息服务,促进公共数字文化信息资源利用的健康、科学发展[13];另一方面,应积极参与政府公共数字文化事业决策和制度制定工作,提出专业性建议和意见,承担自身的社会责任,体现专业价值。
[1]胡唐明,魏大威,郑建明.公共数字文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图书馆论坛,2014(12):20-24.
[2]王鹤云.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研究[D].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14.
[3]刘陆军.图书馆参与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实践的历程[J].图书情报工作,2011(7):126-129.
[4]姚贱苟.公共服务中的责任机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4.
[5]马俊.多中心治理理论视角下公共文化服务问题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2012.
[6]熊伟.高度重视公益文化事业运行制度设计研究服务区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政府决策——以参与宝鸡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制度设计课题研究为例[C] //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创新服务方式,加强智库建设——陕西省社会科学界第六届学术年会社会分会场论文集.西安:[出版者不详],2012:6.
[7]胡唐明,魏大威,郑建明.国内外公益数字文化建设路径与模式比较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3(20):21-25.
[8]林凡.加强文化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对策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商业大学,2013.
[9]陈兰杰.政府信息商业性再利用的概念、方式与流程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11(23):78-82.
[10]马珂.社会信息化进程中公共图书馆管理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11.
[11]王筱俊.公共图书馆政府信息公开服务机制研究[D].湘潭:湘潭大学,2012.
[12]李善青,赵辉,宋立荣.基于大数据挖掘的科技项目查重模型研究[J].图书馆论坛,2014(2):78-83.
[13]杨峰,胡琳.公共产品视野下的图书馆服务效率:属性、损耗与回应[J].图书馆论坛,2012(5):126-129.
The Main Functions of Public Digital Culture
MA Yan,SUN Hong-lei,ZHENG Jian-ming
Public digital culture is a new form of public culture under the context of social informatization,which changes the needs of citizens in public culture and pushe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digital culture service providers’legal status.To deal with such challenges,service provider of public digital culture,as the information collator,processor and respondent to resulting problems in the public digital culture undertakings,should improve its functions in respect to the arrangement,processing,deep integration,safety protection,and contradiction harmonization of services and resources.
digital culture;public culture;service providers;function
格式 马岩,孙红蕾,郑建明.公共数字文化的服务主体职能[J].图书馆论坛,2015(10):30-34.
马岩(1989-),女,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孙红蕾(1990-),女,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郑建明(1960-),男,博士,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2015-05-19
*本文系2014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创新江苏社会数字文化治理体制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4ZDAXM001)和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图书馆大众化服务模式定位和建设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4BTQ019)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