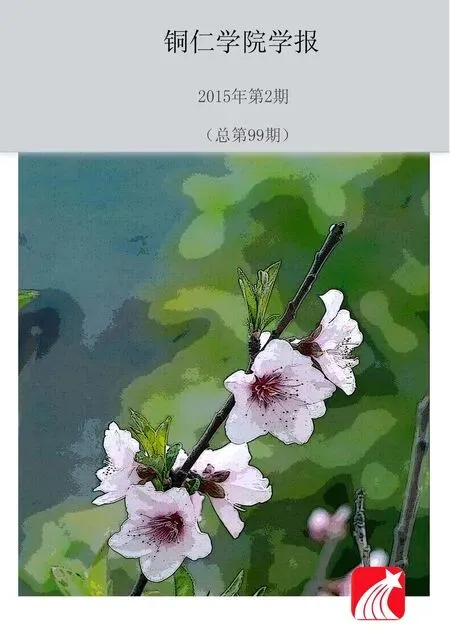论三都水族自治县怎雷村苗族语言与婚俗的变迁
赵尔文达,石本钰,吴大旬
( 贵州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
论三都水族自治县怎雷村苗族语言与婚俗的变迁
赵尔文达,石本钰,吴大旬
( 贵州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
致使民族文化变迁的因素有很多。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怎雷村苗族文化的变迁,与当地的地域环境、民族融合乃至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息息相关。以田野调查为依据,借助有关学科理论,解析其文化的变迁与缘由。
苗族; 语言; 婚俗; 变迁; 怎雷村
笔者于2013至2014年的两年间,对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怎雷村的苗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田野调查。通过田野调查发现,这里的苗族受到外部社会以及当地其他民族的影响,其原有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民俗活动、传统节日等正在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特别是语言及婚俗上的变化尤为明显。
一、怎雷村概况
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怎雷村,距三都县城41公里,与都江古城垣排常寨隔河相望,据有关资料记载,至今已有300余年的历史。“清清正九年(1731),原都尚县境改设都江原通判,怎雷寨为其其地。民国年二年(1913)12月,改都江县。民国年三十年(1941),都江县与三合县合并,置三都县”[1]1。1957年,撤三都县,设三都水族自治县至今。无论行政区设置怎样改变,怎雷村的归属均没有改变。2010年,怎雷村入选第五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2012年,怎雷村作为水族和苗族同胞和谐共生的自然村落,被列入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怎雷村坐落在半山坡中,上为陡峭的山崖,下为层层梯田,左右均为深浅不一的沟壑。居民为水、苗两种民族,以农业耕种和林业为主要生产方式。怎雷村由上寨、中寨、下寨、排常寨四个自然寨组成。据统计,其中上寨由68户水族组成,中寨共有75户居民(其中十多户为水族,其余全是苗族),下寨共有52户居民(除几户苗族外,其余全是水族),排常寨26户居民全由苗族构成。可以说,怎雷村是一个苗族、水族交错杂居的村寨,这为两个民族各自原有的思想观念、交流方式、生活方式、民俗活动、传统节日等方面的变迁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二、怎雷村苗族语言与婚俗变迁的表现
(一)语言的变迁
在怎雷村,苗族与水族两个民族日益频繁地互动,两种民族的文化也不可避免地相遇碰撞。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变迁在所难免。
怎雷村居民在日常交流过程中,族内交流的时候,都会用自己民族的语言进行交流。而当这两个民族进行族际之间交流时,会不约而同地选择用水语交流。其原因是,相对于水语,苗语的音节较多,学习起来较为复杂,经两个民族居民长期磨合,出于方便的缘由,怎雷村的苗族居民几乎都会说水语,能与水族居民用水语无障碍地交流。
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以及普通话的普及,怎雷村的小孩,青少年都能说普通话。教师是当地较为主动关注社会环境变化的群体,也是比较善于表达和便于与外族沟通的群体。据怎雷小学的韦刚辉老师介绍:“这里的小学老师都会用普通话教学,但当出现学生不能理解的情况时,老师会用水语进行解释。因此,这里的老师几乎都是会说水语又会说普通话的。”苗族学生在学校这一多种语言共存的环境内,接受着汉语语言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也在与师生、同学交流中进行着汉语以及当地水语的非正式学习和运用。这种方式是学生学习和掌握汉语及水语的除家庭教育外的另一基础性条件,孩子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能在苗语、水语以及汉语之间转换自如,也是毋庸置疑的。
中老年人也有少部分能说普通话的,但在与非本村寨人交流时,会自觉用当地通用的贵州方言。当地人在使用汉语和使用自己民族语言之间的转换看起来是件很自然的事情。总的看来,当地人一般都会说汉语,只有山上未上学的小孩和少量年纪大的老人才不会使用或不能熟练使用汉语。这种状况表明怎雷村已经完成并正在经历着的深刻语言变迁。
(二)婚俗的变迁
1.从族内婚到可与当地他族和外族通婚
自怎雷村村民的先祖将村寨迁到怎雷这个地方以来,这里的水族与苗族始终团结和睦;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两个民族间的文化风俗习惯的差异等原因,都各自严格遵循族内婚,不仅水族与苗族之间不能通婚,而且与其他民族的婚姻在当地来说也是不被允许的。以前,当地的水族和苗族的婚姻形式以父母包办,强迫婚姻居多。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以来,族内婚的限制也逐渐被新的婚姻观所取代,族际通婚率有明显地提高。当地的苗族也出现了和水族及与其他民族通婚的现象。迄今为止,怎雷村的苗家姑娘嫁入水族的就有五例,其中多是苗家姑娘嫁到上寨,而且都是通过男女双方自由恋爱后,将自己的意愿告诉家长,由家长出面请人提亲和订婚,最后安排婚嫁。随着外出务工的人口日益增多,自由恋爱的理念深入人心,怎雷村的苗族也出现了外地其他民族姑娘嫁到本地、苗族姑娘嫁到外地的现象。
2.聘礼方面的变化
中国向来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婚礼仪式不仅是完整的婚姻的组成部分,而且从中还可明显看到怎雷村苗族的婚俗文化的变迁和发展。男方把聘礼送到女方家,是对女方家抚养女儿长大成人的一种补偿,有时也是男方炫耀经济财力的一种方式。中华民族传统的聘娶礼仪基本上按照《仪礼·士婚礼》中的“六礼进行”[2]1,但在怎雷苗族先前的婚俗习惯中,是没有“下聘礼”这一仪式过程的,“都江一带苗族提亲不带礼物,空手前往问话,允不允婚嫁都要招待酒饭。”[3]195婚礼仪式中只有“议婚、定婚、选定婚期、亲迎”这些过程。在长时间跟水族的交往和融合过程后,苗族男方也会学习水族“下聘礼”的方式,提着猪肉、糖等物去女方家下聘。
3.结婚后禁忌方面的变化
怎雷村的水族在过最隆重、历时最长的端节时,人们会在第一天把家里的锅碗彻底洗刷一遍,忌吃油、荤腥的食物(鱼、虾等水产动物被水族视为素菜。在此期间,鱼、虾等是可以食用的),在端节的第一天结束后,才能吃动物的油和肉。在家中老人去世的时候,主人家和同宗族的人同样要忌吃油、荤腥的食物,直到把去世的老人安葬以后,才恢复以前的饮食。这样的禁忌在怎雷村的苗族是没有的,但在跟水族通婚以后,嫁到水族人家的苗族姑娘,必须遵守其忌油、忌荤的禁忌;而苗族的男子娶了水族的姑娘,在过端节或者女方长辈过世的时候,水族的姑娘可以继续遵守她本民族的禁忌,但她没有权利要求苗族男子同样跟她忌油、忌荤。
三、怎雷村苗族语言与婚俗变迁的原因
(一)对各自身份的认同感
社会文化是一个整体,其中一部分的变迁,必然引起整体中相关部分的联动。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以及与怎雷村水族的不断融合,都对当地苗族的语言及婚俗文化,乃至整个民族的文化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旧的文化逐渐消亡,新的文化构成因素正在形成。
一方面,族际交往日益频繁与民族文化变迁有着一定的相关性。怎雷村的苗族,不仅仅是与当地水族交往频繁,还与其他民族交流交往密切,特别是近年来青年男女外出打工数量增多,以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受外界文化影响较大,外界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不断冲击,使得怎雷地区苗族的传统文化,包括其服饰、语言、饮食、婚姻、丧葬等方面等文化都有着显著的变化。另一方面,变迁的主体追求其自身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摒弃与现实生活不相适应的文化习俗,寻求更符合现代社会价值取向的文化方式。从严格遵循“内婚制”到“可与外族通婚”、“聘礼”的从无到有,以及对婚后的禁忌的改变,都是怎雷地区的苗族作为文化变迁的主体在文化接触和文化整合的中的主动选择。
“婚姻是自然进化和社会进化的结果。”[2]76怎雷地区的婚俗文化身不由己地向当地的主体民族--水族的文化靠拢。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受汉文化的影响,怎雷地区的苗族在维护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在选择适合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现代文化途径,根据自身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传统习俗进行选择,调整其传统文化去适应现代生活,以文化变迁的方式传递出文化选择和创新的意图。
(二)共同的经济生活
聚居在怎雷村的苗族和水族,由于紧密的地缘关系,共同的物质生产生活与交换,使得两个民族之间的差异日益减小,他们的经济生活也日趋相似或相同。这是长期历史复合作用的结果,也是怎雷村民族和谐共存、融洽相处的先决条件。
怎雷村上、中、下寨以及排常寨,四个自然寨中苗族、水族交错杂居,紧密的地缘关系为当地水、苗两族关系和睦提供了先决条件。在这里的居民,都种植水稻、玉米、红薯等作物。在饮食方面,都偏好酸辣。因此,辣椒和西红柿也是必不可少的作物。在家禽家畜方面,都饲养鸡、鸭、鹅、猪、牛等,来满足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物质需要。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生产技术基本相同, 住房形式、生活用具、食物烹饪及公共卫生等方面基本相同,唯一明显差距主要表现在服装饰物和某些生活方式上。共同的物质生产和商品交换,促进了两个民族的互动和其文化的不断渗透,并逐渐形成了地域认同意识和相似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生活方式也呈现出趋同的倾向。“可见,共同的经济生活是各民族形成地域认同心理、共同价值取向以及团结互助精神的先决条件, 是和谐民族关系的重要成因。”[4]
(三)民风淳朴,治安良好
良好和睦的民族关系使得两个民族互相吸收对方的风俗习惯,而这种互相学习吸收反过来又促进了两个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在怎雷村的水族以及苗族,粮仓都独立于房屋修建,甚至有些在路边的粮仓经常不上锁也不会出现偷盗行为。不论民族内部之间还是民族之间都很少有摩擦矛盾出现。当偶尔出现摩擦矛盾,当地村委会或者长老会依据村落里制定的“法榔”来调和或做出裁决。
村委会成员由苗族、水族共同构成。他们都是当地各自民族的带头人,根据本地方本民族的风俗习惯、民族心理和价值取向管理本地区的事务。不同民族的人在一个领导班子中共事,许多有差异的民族生活习俗和不同的民族信仰等文化成分通过自己的领导得以调节适应。村委会还组织了“便民服务站”,并本着“便民利民,富民安民”的宗旨,为当地群众解决困难群体生活、健康问题及社会救助的办理;协调处理民事纠纷和群众生产生活中的有关矛盾和问题;普法、宣传科学知识等等。村委还自发组织了“护村护寨队”,及时传达办理公安派出所交办的各项任务、在发生案件事故时,及时报告管片区民警和村委会、定时巡逻执勤还制定了夜间巡逻制度、制定了“自然寨住户公约”、创建“安全文明村寨标准”等等。这一系列举措都为当地民族和睦提供了保证。
怎雷地区的两个民族经过长期的接触、互动,族际交往的频率逐渐增加,族际交流的程度不断加深。首先,小孩从小在一起学习,加上国家营养餐制度的推行,早午餐都在一起食用,除了放学后在家之外的大部分时间,小孩子们都在学校接受无差别对待,感情日益深厚,都接受汉文化以及其他外来文化的教育。这种族际间文化的互动,使得不同文化元素出现相互渗透、融合的状态,民族间的文化差异便逐渐缩小,大家都能宽容地理解他族。因此,衍生出互助友爱、和谐共处的价值理念,这为今后怎雷村和谐民族关系提供了基础。其次,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怎雷村几乎没有发生过族内或族际的大争端或不可调和矛盾。在怎雷村,人们由于对本族和他族都有所认知,能够不仅从精神的角度,同样也从物质的角度都给予对方充分的尊重,自觉地维护自己和他人的利益,并逐渐形成了地域认同意识和相似或相同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生活方式也呈现出趋同的倾向。再次,民族平等的政策是形成民族关系和睦的的重要保障。怎雷村治安良好,“法榔”制度的存在以及村委会的努力,也是这一地区民族关系和谐必不可少的条件。
四、结语
民族间的文化了解程度越深,就越能从客观的角度去看待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不同,促进对他族文化的尊重和学习,从而维持民族关系的和谐。与此同时,和谐的民族关系也促进了两个民族紧密地了解、学习,共同发展。这种良好民族关系的形成,不是靠个人或单个民族决定的,而是经过长期磨合,结合各种因素的结果。美国人类学家特恩沃尔德认为:“涵化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孤立事件,是一种文化从另一种文化获得文化元素,对新的生活条件的适应过程。”[5]223怎雷村苗族文化的变迁和涵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与当地水族的和谐相处之上的。只有在双方和睦、融洽相处的条件下,双方对彼此文化的认可、接受才使得文化的相互借鉴、学习,使文化变迁成为可能。从宏观上说,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基调下,各民族间文化交往、交流日益频繁,更促进了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学习,怎雷村苗族的传统文化必然会越来越多地吸收外族文化,越来越多地改变自身。在此过程中,不仅要客观地审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借鉴及吸收其它文化的精华,促使其婚俗和语言文化向积极、进步方向发展。
[1] 中共三都水族自治县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三都水族自治县历史(第一卷:1949-1978)[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2] 汪石满.中国婚姻家庭[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3] 三都水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三都水族自治县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4] 杨昌儒.民族关系模式初探:一个民族乡镇的考察[J].贵州社会科学,2004,(02).
[5] 黄淑娉,等.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Changes of Miao People's Language and Marital Custom in Zenlei Village of Sandu Shui Nationality Autonomous County
ZHAO Erwenda , SHI Benyu, WU Daxun
(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China )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changes of ethnic cultures. Changes of Miao's culture in Zenlei village of Sandu Shui Nationality Autonomous County are related to local environment, ethnic fusion and even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Based on fieldwork, using theories of related disciplin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se changes.
Miao People, language, marital custom, changes, Zenlei Village
G127.73
A
1673-9639 (2015) 02-0104-04
(责任编辑 黎 帅)(责任校对 白俊骞)(英文编辑 谢国先)
2015-02-01
赵尔文达(1991-),女,苗族,贵州思南县人,贵州民族大学2013级中国民族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石本钰(1988-),男,水族,贵州榕江县人,贵州民族大学2013级中国民族医药专业硕士研究生;吴大旬(1962-),男,侗族,湖南新晃县人,贵州民族大学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