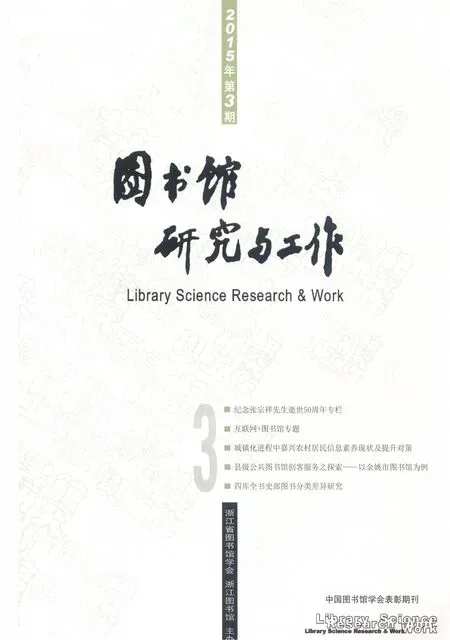外公留下的财富
徐 洁
(浙江图书馆,浙江 杭州 310007)
外公离开我们已经有五十年了。他在世的时侯,我和他只共同生活了三个年头,而这还是从我出生开始算起的。虽然我的名字是外公给取的,但我的记忆里并没有外公清晰具体的印象,那时的我实在太小。一些残存模糊的片段,也可能只是听家人的描述、我自己的想象。比如我父母老是提到那时的我经常会跌跌撞撞地闯入他的书房,伸手所及之处,总会一片狼藉。那时的家里总是有很多客人,有他的朋友、学生、同事,还有一些曾被他接济过的、家人也不清楚关系的人。他们有的来谈论古籍校勘,有的来讨论书法,有的来鉴定字画和玉器,也有的是来讨要墨宝的,真可谓是“三教九流”,络绎不绝。外公精力旺盛,边谈论,边抄书,边抽烟,一样也不耽误。那时的家里,满屋书香……这样的场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清晰,以至于有时错以为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
外公是在一九六五年罹患肺癌离世的。不久之后文革开始了,我家从宽敞的祖宅迁居进了陋室,记忆里屋子的墙上总挂着这几样:一是外公无偿捐赠的奖状。二是“岂能尽如人意 但求无愧我心”的对联,那是外公写给外婆的。再是外公书写的文天祥诗碑文拓片(该碑至今依然在温州江心屿,供后人欣赏和凭吊)。睹物思人,这是我们全家对外公的思念。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进入浙江图书馆工作,我与外公的关系开始密切起来了。每每遇到一些老同志,看到我就说,哦,是老馆长的外孙女。一句老馆长,足以见同事对他的尊重,也让我体会到,在这个单位工作,我要对得起外公,千万不能给他抹黑。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对外公生前作为的闻见越来越多,他对我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些影响,既有外公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又有对人生的豁达态度,更体现了外公一生的价值取向,是外公留给我们后辈的最大财富。
运筹帷幄谋大事。1951年元旦,外公写下一段话:“人为群众服务而来,不是为个人权利享受而来。学问、政治须时时去其陈腐,发起精义,方能有益于世、有益于己。此七十年来处世持躬之旨也。”我想,这就是外公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有了这样的宗旨,决定了他一生坚守信念,坚持操守,坚定做对浙江文化有益的事。外公一生,做了两件浙江文化史上的大事。第一件,在1923年担任浙江省教育厅长一职时,组织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外公对补抄一事,酝酿已久,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工作时,对四库书就有了全面的了解。虽然是大工程,但外公开始时就能运筹帷幄,在最难的经费筹措上,他事先就明确三点:不是浙江人,哪怕富可敌国,也不去募捐。本省各地区都有捐助。每500元为一股,不成股的不募。最后,当时的督办、省长都募了款。这也为文澜阁《四库全书》留在浙江埋下了伏笔,当时的政府在抗战胜利后,欲将书运往南京,因为当初只接受本省籍人士的捐款,文澜阁本才得以安全运回。第二件,恢复西泠印社。1951年11月,西泠印社将社产和文物,全部移交给了政府,从此完全停止了活动。在毛泽东主席双百方针的号召下,1956年5月26日,外公在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提交建议,希望恢复西泠印社中的篆刻印泥,兼售书画和西湖的碑帖等。1957年11月17日,在外公的寓所,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成立筹备委员会,外公担任主任,陈伯衡、潘天寿为副主任,沙孟海、诸乐三、阮性山、韩登安为委员。筹委会共召开了六次会议,但筹建工作并不顺利,到1959年,筹委会名存实亡。期间,先恢复了西泠印社营业部。外公利用自己的影响,继续积极争取,他认为西泠印社的学术活动,应该继承下来,浙派发展势力较大,不仅是浙江的特产,而且是在东方及世界上独具的。1963年,西泠印社建社60周年之机,外公当选为复社后第一任社长。担任社长后,外公第一个建议就是要每月一次社员聚会,讨论学术问题。同时,外公自己带头,将藏品捐赠给印社,并联络许多名家慷慨相助。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陈振濂认为外公是:百年西泠印社存亡继绝的第一代中兴功臣,从而使西泠印社的历史得以赓续,文脉得以延伸。没有他,今天早就没有西泠印社了。
踏踏实实做学问。外公有一句名言:凡人要治学、做事,必当先有傻劲,有傻劲,然后可以不计利害,不顾得失,干出一点事业,成就一点学问。外公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工书法,善诗文,精医药、戏曲,生前著有《书学源流论》、《论书绝句》、《铁如意馆题画诗》、《本草简要方》、《中国戏曲琐谈》等。虽然多才多艺,但他毕生致力于古籍校勘,抄校古籍六千余卷,已出版的有《说郛》、《罪惟录》、《越绝书》、《洛阳伽蓝记》、《国榷》等十余种。
外公一辈子做的最多的事就是抄书,他读的书多,知道书籍对人的影响,因此担心“人生多歧路,歧路在书中”。外公三十二岁点读二十四史时,见到刘子庚父亲所校的四史,深知读书应先雠校。三十五岁时,校《资治通鉴》,“见秦使大良造伐魏吴氏注数百字,考定其为必是商鞅后得蜀宋本,方知原有二字,刻本偶脱。乃知胡氏,元人所见,已非善本;而读书贵精校,又须得善本。自此,乃益用力于雠校及搜抄善本、孤本。是年,抄本已积三四百卷矣。”三十八岁,任京师图书馆主任,“日拂拭灰土中,以求遗逸,检查旧目,修整残编,检校谬误。……故两年之间,抄校时间,虽因而减少,所见奇书,实为毕生最富之日。”四十岁,外公欲把抄校古书籍,作为一生的事业来从事,有自书对联为证:分明去日如奔马,收拾余年作蠹鱼。八十岁寿辰时,他作诗一首,对自己几十年的抄校生涯作了总结:四五十年事抄校,每从长夜至天明,忘餐废饮妻孥笑,耐暑撑寒岁月更。窃写真同无赖贼,劫余剩书半边城。天怜手眼今如故,料是偿书债未清。
外公刻有两方印章,“手抄千卷楼”和“著书不如钞书”,足以表明他对校雠古籍的钟爱和决心。外公每日可抄书一卷,影抄则三日一卷,如果书主催交急迫,则夜以继日,可抄二万四五千字。因为一天能写小楷一万五六千字,朋友间戏称他为“打字机”。如果遇到友人来访,他能与友人边谈边抄,从不脱误。他的抄书方式兼具表演性质,抄书时,就象摆棋谱一样,从一页的中心先抄写几个字,然后以这几个字为中心进行布局,能一字不差。有时又能在一页的四角抄写几个字,然后进行布局,一字不漏,可谓出神入化。
开朗宽厚度人生。新中国成立前,外公带着家人颠沛流离,经历过战乱,饱尝过失业。一生从事过很多职业,既有解决温饱所为,更有多种特长的展示,林林总总,外公一直坦然面对,并秉持着“学问要向好的学,生活要向不如的看”的态度。新中国成立后,外公的生活才渐渐稳定下来,虽然年事已高,但一直致力于古籍校雠和图书馆事业,度过了一个幸福的晚年。
外公性格开朗,待人宽厚,做事光明磊落。有几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文革结束后,我家来了一位客人,自报家门,说是外公曾接济过他家,现在日子好过起来,特意来看望我妈,并问有啥事可让他帮忙做。后来,逢星期日,他常来我家帮助换煤气,共进午餐后才告辞而去。
我到浙江图书馆工作后,碰到姜东舒先生,他看到我就说:你外公对我很好,在书法和工作上都有帮助和扶持。他还特意去看望我爸妈,表示对外公的敬仰。每次见到他,他总是要我替他问候我爸妈好。我结婚的时候,他送我一幅他的书法作品:最爱孤山雪后来,野梅几树水边栽。着花不过两三朵,独向人间冷处开。这是外公的诗作,姜东舒先生告诉我这也是他最喜欢的作品,今天以这种方式传递给我,这样的情谊,让人难以忘记。
图书馆和昆剧团都属文化系统,我经常有机会和昆剧团的领导在一起开会。也因为在一起开会的机会增多,大家也渐渐熟悉起来,当他们知道我和外公的关系后,告诉我:你真应该来听听昆曲。原来外公很喜欢昆曲,被演员们称为“张老”。“传字辈” 在上海刚出道时,外公就去看他们演出,并且常常是拿着曲本去看戏,逐字逐句,细细品味。外公对周传瑛等几个年纪小的尤其喜欢,每当手有闲钱时,演出结束后,外公常邀请周传瑛和其他几个同科“小囡”一起喝点小酒,讲讲昆曲戏文,但毕竟曲高和寡,周传瑛他们一知半解,似懂非懂。最后,外公点名了五个学生:姚传芗、张传芳、刘传蘅、华传浩、周传瑛,在自己家里给他们上国语课,特意挑选《幼学琼林》作为课本。为此,外公还请了一位广东人许月旦先生做助教,每天两个小时的课,在外公家吃中饭,下午不耽误演出。1954年,为纪念洪升逝世250周年,外公提议周传瑛排练《长生殿》,并把排练场地放在文澜阁内,每天去听演员们坐唱,新排的《长生殿》在杭州市人民游艺场首演,这是新中国戏剧舞台上第一次演出昆曲版本,非常值得纪念。田汉、洪深等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十五贯》,也是经过外公过目后敲定文本。
今年是外公离世50周年,浙江图书馆为他举办了系列的纪念活动,我想,单位为他举办活动是表示了一种敬意,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图书馆历史中的一些人物。作为后人,我在缅怀之余,更要学习外公的优良品质,既要做好事,更应该做好人。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外公谢世50年,但他一直并未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