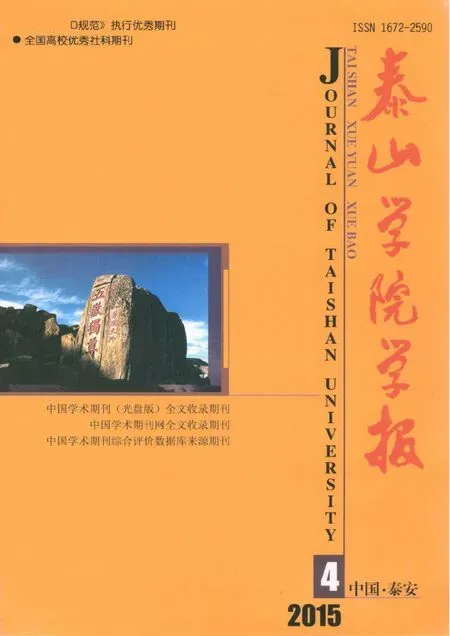2014年鲁迅作品研究中的几个亮点
崔云伟,魏 丽
(1.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管理学院;2.山东艺术学院戏曲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2014年鲁迅作品研究中的几个亮点
崔云伟1,魏 丽2
(1.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管理学院;2.山东艺术学院戏曲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2014年鲁迅作品研究呈现出异彩纷呈、创意不断的局面。吴义勤、周南、张克、张全之、杨义等皆对鲁迅小说发表了极为精彩的看法。钱理群的《野草》研究,杨义、宋剑华、王国杰的《朝花夕拾》研究,汪卫东的早期文言论文研究,皆可称得上别具一格。杂文研究中,魏建、刘春勇、宋剑华的阐释不乏亮点。邵宁宁的鲁迅诗歌研究,韩大强的鲁迅日记研究,谭桂林、曾锋的鲁迅作品整体研究,皆有其新颖独到之处。
鲁迅作品;研究;述评
在历年来的鲁迅研究中,有关鲁迅作品的研究总是异彩纷呈、创意不断。2014年度的鲁迅研究亦不例外。笔者在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的基础上,特意从中概括、梳理出有关鲁迅作品研究的几个亮点。现述评如下,以与学界同仁共同探讨。
一、鲁迅小说研究
与《呐喊》研究有关的文章主要集中在《狂人日记》、《阿Q正传》、《故乡》。
现代进入中国,意味着“人”的发现,同时也意味着“吃人”的被发现。“吃人”由一个经验性历史事实而成为一个文化政治问题,由是成为中国现代性的重要表征。吴义勤、王金胜[1]认为,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首先将“吃人”的观念化表达熔铸为一个重要的文学命题和一个经典的文学意象。这个命题和意象同时是对中国历史与文化之本质认知的隐喻性表达。莫言《酒国》延续并转换了这一“吃人”叙事传统。如果说《狂人日记》是一则反抗者的寓言,《酒国》则可视为沉沦者的见证。《狂人日记》呈露出鲁迅孤绝的现代性生命体验,《酒国》却将诸种狂欢性因素杂糅一处,熔铸成一个狂欢的世界。《狂人日记》在主旨、意象营构、人物塑造及话语风格等方面均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酒国》。但是,作为传达某种当代文化隐喻的小说,《酒国》是莫言在特定的现实政治和市场经济语境中,循着自身创作内在的思想与艺术脉络,借助颇具民间色彩的先锋性叙述所完成的个性化美学创制,小说对“吃人”的再叙述也由此成为转型期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寓言和主体命运的见证。
在《狂人日记》“吃人”意象生成中,有外来文化元素与中国文化元素影响,但学界百年来囿于鲁迅周作人的述说,一直忽略了对前者的探究。2012年李冬木提出:《狂人日记》“吃人”意象的生成,“是从日本明治时代‘食人’言说当中获得的一个母题”,日本学者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将明治时代文明开化背景下的“支那”“食人”言说引进国民性话语,与“吃人”意象生成有着决定性关联。此说引起研究界强烈反应。李有智、王彬彬、祁晓明皆发表文章,对之提出了强烈质疑。本年度,周南[2]再次发表文章,对于上述文章再次进行了细致辨析。他认为,鲁迅获取吃人信息来源于中国,主要得自古书记载,这根本无需争论。李冬木将《狂人日记》研究纳入日本明治时代的“支那食人”言说,以及由此切入国民性研究话语框架,以后者作为《狂人日记》诞生的外国现代思想文化背景,这是“狂人学史”实质性研究推进。在《狂人日记》所包含的象征性真实的层面上,鲁迅对于“吃人”意象的发现,已经超出了进化论人类学,进入了对于中国文化的批判,而这则是日本的人类学和国民性研究都无法提供可资借鉴与模仿的东西的。因而,李冬木的结论:《狂人日记》从主题到形式皆诞生于借鉴与模仿,引起鲁研界的争论,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了。此次关于“吃人”意象生成的争鸣探讨,推动着《狂人日记》和中国鲁迅研究突破一国史观走向多国史观,并重视对鲁迅创作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思想基础研究,这对于切当理解《狂人日记》跨文化跨学科视野下的思想艺术独创是大有益处的。
“游民与越文化”是《阿Q正传》研究中的一个独特视角。张克[3]认为,从周氏兄弟对绍兴风俗中的“流氓风气的蔓延”的记忆来看,阿Q的行止做派实则根植于“游民”气氛浓郁的晚清越地风俗。阿Q作为一个“游手之徒”,其精神世界是一个文化溃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真正起作用的是人的动物本能、是弱肉强食的力量对抗,一切原有的文化符号都在溃败中走样变形,失却其原本的严肃性。阿Q生命的“微尘似的迸散”可以说正是越文化本身溃败的象征。小说最具刻骨铭心之处在于对阿Q这样一个失去任何文化庇护的卑微的游民难以挣脱“对他的整个存在怀着恐惧”这一根本生存处境的揭示。通观“游民与越文化”这一命题,已是一个测量当下学院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之间精神距离的现实性命题,其中的幽暗与真相,对诸多学院知识分子来说都会是一个沉重的拷问,但这无疑是真正来自鲁迅特有的精神力量的挑战。
藤井省三《鲁迅<故乡>阅读史》在中国出版以来,学界对之一直好评如潮。本年度张全之[4]则一反众议,认为该书有着十分重要的缺憾,概括起来即:局部分析十分精彩,但整体构架存在瑕疵。他认为,为什么是《故乡》的阅读史,而不是其他作品?《故乡》的特殊性表现在哪里?《故乡》被重构、被改写,与其他作品有什么不同?这些疑问在该书中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这就暴露出该书在构思和写作中的巨大漏洞。藤井试图通过《故乡》这一个案的考察,寻找现代中国文学空间的演化轨迹及其对读者阅读产生的引导或制约作用。但是,相对于“现代中国的文学空间”这一庞大的概念而言,《故乡》这一文本的支撑力显然是不够的。该书借用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的理论框架,形成了一个“两面”支撑“一点”的论述结构。但是这一结构看似严谨,实际处于分离状态。“两面”无法支撑“一点”,结果就使“国民国家想象”这一核心点处于悬置状态。
杨义则对《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作了精彩的生命解读[5]。其《鲁迅<彷徨>的生命解读》认为,《彷徨》一以贯之的精神脉络是反思,反思乃是在彷徨中的思想深化。《祝福》反思启蒙运动,已是“后五四”了,但乡镇上的士绅骂的还是康有为的新党,似乎五四的启蒙尚不及康梁的维新更触及基层社会。《在酒楼上》反思同代知识者,它们何以陷入“蝇子怪圈”,不能飞得更高更远?《长明灯》反思“救救孩子”,为何这里的孩子们也和《孤独者》中犯了同一个“症候”——赤膊小孩将苇子向疯子一指,清脆地发出“吧!”的枪声。《孤独者》反思进化论和易卜生主义,既然说“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独的人”,为何这里的孤独却连结着人生价值的放弃,连结着送敛和死亡。《伤逝》反思易卜生的“娜拉走后怎样”,涓生如何走出人生新路支撑新式家庭,子君如何不再重回旧家庭的严威和黑暗中,直至走到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这些反思,都推动着纸面上的抗争和改革,走向实践的抗争和改革,在鲁迅彷徨的精神世界中,令人隐隐然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
其《<故事新编>的生命解读》认为,《故事新编》称得上是现代小说史上的一部奇书。奇就奇在鲁迅的书袋虽然是鼓鼓的,却无意于掉书袋,而是驾轻就熟地出入古今,把现代社会的诸多官场丑态、文界乖谬、民间陋习和掺和着奴性及流氓性的国民心理,糅合在神话、传说、历史的著名故事之间。这就有如女娲拔起一株从山上长到天边的紫藤,搅动地上的泥水,溅出一班能笑能哭的生灵,即鲁迅所谓“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是也。二者的糅合与搅拌,构成了复调叙事,构成了民俗性的狂欢。古人和今人打照面,互相消解对方的神圣的灵光或装模作样的摆谱,令人看见他们的不尴不尬而窃窃发笑。小说自身也由此超越纯文学传统而向杂文开放,小说与杂文杂糅,兼具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功能,开创了一种古今杂糅的“杂小说”新文体。
二、《野草》研究
钱理群在为汪卫东《探寻“诗心”:<野草>整体研究》[6]所作的序[7]中,探讨了一个学术研究中的当代性问题,即:当代中国文学距离《野草》已经达到的高度还有多远?我们能不能借《野草》反思自己,进而寻找摆脱当下中国文学困境的新途径?钱理群认为,在中国当代文学经历过“两次绝望”之后,我们至今仍未走出绝望,更不用说如鲁迅那样走向新的生命与文学的高地。原因全在我们自己。我们很少象鲁迅那样把外在的困境内转为自我生命的追问:我们既无反省的自觉,更无反思的勇气与能力。这样,我们就失去了一次鲁迅式的逼近生命本体、逼近文学本体的历史机遇。我们无法收获丰富的痛苦,只获得了廉价的名利、肤浅的自我满足或怨天尤人。在这样的生命状态下的写作,就根本不会有鲁迅那样的语言突破、试验的冒险,也只能收获平庸。于是,当代中国文学就在作家主体的生命深度、高度和力度和语言试验的自觉这两个方面和鲁迅曾经达到的高地拉开了距离;而“生命”和“语言”正是文学之为文学的根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许多当代文学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文学性。这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境所在。
2008年,汪卫东撰文《<野草>与佛教》[8],论证了鲁迅与佛陀在更深层次上的精神相遇。本年度,崔云伟[9]从此出发进一步论证了鲁迅与佛陀的同与不同。他认为,鲁迅在《野草》中最终并没有通达佛陀所说的悟的彼岸,而是仍然站在了坚实的大地上,这是鲁迅与佛陀的最大不同。如果说佛陀的超越是对于涅槃寂静的执意追求,我们可以称之为“向上超越”,那么,像鲁迅这种执意活在人间,在无物之阵中一直战斗到死的超越,则可以称之为“向下超越”。虽则鲁迅与佛陀在最终追求目标和超越模式上是根本不同的,但是在其他三个圣谛,即“苦谛”、“集谛”与“道谛”上却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相似乃至相通。从鲁迅与佛陀的相同之处,我们看到的是鲁迅与佛陀的精神相遇,而从其不同之处,我们看到的则是鲁迅与佛陀各自的伟大。
对《野草》作出精彩解读的还有李培艳和张娟。李培艳[10]认为,鲁迅《野草》是清理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寻求自我创生过程的产物。鲁迅通过失语与死亡的临界点打开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并以象征化的方式,完成了内在世界的客观化,进而使其自我意识的展开成为可能,死亡的张力随之亦被化解。张娟[11]则认为,反观《野草》写作,和鲁迅的北京生活体验息息相关。其中的一部分作品可以看到鲁迅作为“都市漫游者”对城市灰暗面的思考,对市民社会世态人情的揭露和城市发展中物质至上的诙谐批判,另一部分偏重灵魂表达的作品则以现代性的思想、西方式的表现方式体现出城市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三、《朝花夕拾》研究
杨义[12]认为,“朝花”是鲁迅的童年经验,童年经验连结着生命的原始,刺激过天真无邪的好奇心,左右着终生的意象选择。包括老祖母讲的猫是老虎师父的故事,长妈妈渲染的女阴能使敌军大炮变哑,《山海经》刺激神话兴趣,百草园窥探自然生命,无常散播着鬼世界的诙谐,父亲的病埋下了中医现代化的质疑,《天演论》建构了现代思想的新维度,辛亥畸人范爱农引发了对革命变味的反思。这些早年经验,都提供了鲁迅思想母题的最初萌蘖。鲁迅在“后五四”,拾起了“前五四”的思想母题之花蕊,把玩思量,与中年时的人事藤蔓纠结翻滚,蹦出了许多“嘎嘎”乱叫的生命。《朝花夕拾》遂成了现代中国最有生命趣味的回忆散文。
宋剑华[13]则认为,《朝花夕拾》中的“旧事重提”隐喻性地表达了鲁迅精神还乡的一种姿态。“百草园”是一个“乡思”意象的艺术符号,鲁迅于此获得了个人成长的经验。鲁迅从“长妈妈”那里感受到慈祥的母爱,从“藤野先生”那里感受到父爱的温暖,从“范爱农”那里体悟到做人的道理,这一切都拉近了他与“故乡”的亲密距离。在如何对待民俗文化方面,鲁迅也已不再是单一性地给予否定,而是更趋于一种理性思辨的科学态度。这说明鲁迅已开始告别文化虚无主义的历史观,进而在精神返乡的过程中呈现出他文化寻根的心灵轨迹。
2013年,张显凤撰文[14]从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惟独缺少了对于母亲的回忆出发,认为“母亲”的缺席直接导致了鲁迅将恋母情感不自觉地移向了衍太太,从而使其具备了代理母亲与准情人的双重特征。本年度王国杰[15]认为,综合《朝花夕拾》中的诸多事例,不难看出鲁迅对衍太太并没有好印象。大概是鲁迅回忆中运用的双重视角:童年视角和成人视角,扰乱了张显凤的判断。鲁迅既已熟知衍太太的为人,又怎么可能对她产生情人心理。鲁迅外出求学亦并非因为什么“俄狄浦斯式的移情及其幻灭”,确是由于家境困顿至极,加之受到谣言攻击,伤了自尊。母亲形象亦并非如张显凤所说是缺席的,而是一直存在,隐藏在细节处或故事背后。她对少年鲁迅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鲁迅在小说中也没有表达怨恨母亲的情绪。王国杰继而对张文所显示的文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当前学术界仍然存在着一种对于西方新潮理论的盲目跟从和胡乱套用倾向,张文即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这种浮躁的学术风气,不利于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学术研究理当尊重史料,并以史料为基础,小心求证,让史料与文本相互印证学术观点。
四、早期文言论文研究
2008年,汪卫东、张鑫撰文[16]发现《文化偏至论》中有关施蒂纳的材源,是一篇发表于日本明治时期杂志《日本人》上的署名蚊学士的长文《论无政府主义》。本年度,两位作者继续撰文[17],在材源考证的基础上,围绕无政府主义问题,进一步深入考察鲁迅所受材源文章的影响。他们指出,蚊文对鲁迅的启发和影响,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施蒂纳在蚊学士之文中,是作为无政府主义之一脉络——哲学上的个人无政府主义的代表来介绍的,强调的是施蒂纳基于个人而反对任何束缚的无政府主义哲学。鲁迅对施蒂纳的介绍,是把施蒂纳放在“重个人”的思想谱系中来加以介绍的,视其为十九世纪末“重个人”思想的首要代表,描述了一个施蒂纳—叔本华—克尔凯郭尔—易卜生—尼采的“极端个人主义”谱系。(二)尤可注意者,是鲁迅和蚊文对暴力活动的态度。蚊文对实行无政府主义的暴力活动颇不以为然,认为那些主张暗杀、提倡暴力的无政府主义者,坚持以暴乱杀害为义务,令人感到恐惧。这与鲁迅对暴力活动的暧昧,与当时的革命语境并不一致,倒有颇多契合。无政府主义和暴力主义言说,都是当时的主流话语,鲁迅避而不谈,体现了其卓而不群的个性和抱负。蚊文对于鲁迅的影响,由此亦可见一斑。
五、杂文研究
《上海文艺之一瞥》是鲁迅的一次重要演讲。80多年过去了,学界甚至连这次演讲的时间、地点、版本等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搞清楚。魏建、周文[18]认为,关于学界所形成的一则共识,即:“二心集版”是鲁迅在“文艺新闻版”的基础上“略加修改”而成的版本的说法,其实是不正确的。这两个版本的差别在于“作者”的不同。关于学界所形成的另一则共识,即:“二心集版”的演讲时间“八月十二日”是鲁迅记错了的说法,其实也是站不脚的。7月20日和8月12日这两个演讲时间的存在,本来就包含着鲁迅以同一题目分别做了两次演讲的可能。再从演讲的不同地点即“暑期学校”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相关资料来看,两次演讲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上海文艺之一瞥》除了上述两个版本之外,还有一个“郭译日文版”。通过细致比对这三个版本,论者发现,鲁迅对《上海文艺之一瞥》的修改距离演讲并未相隔很长的时间,因此,断言鲁迅误记演讲日期甚或地点,要冒很大的风险。同时,从“郭译日文版”与“二心集版”的差别亦可以看出,鲁迅修改后的定稿不是对其演讲内容的精准再现,从某种程度上说,应是更深一层的再创作。论者继而对“文艺新闻版”等演讲笔录稿进行了正名,指出从还原演讲历史现场、体验鲁迅演讲原味的角度来说,“文艺新闻版”要优于“二心集版”。并认为,对鲁迅演讲的研究应充分利用那些最初发表的他人之记录稿,而不能唯鲁迅修订稿是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近真实而丰富的历史现场。
在刘春勇看来,鲁迅作为世界级文学大师的意义,不在《呐喊》这样的纯文学创作,而在丰富的杂文写作。那么,鲁迅的杂文是怎样发生的?刘春勇[19]认为,“现代”可以说是一个虚无主义盛行的时代。身处其中的鲁迅虽然留日时期怀抱理想主义,但回国后却认同“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并做绝望的反抗,这都在虚无主义的范畴当中,但通过写作《野草》鲁迅逐渐扬弃了“虚无”而向“虚妄世界像”挺进。对“虚妄世界像”的体认使得鲁迅在1925年前后逐渐放弃了“主题性”极强的纯文学创作,而选择了一种文学体制外的、基于“有余裕的”写作观念之上的杂文写作。这就是鲁迅的“留白”美学观。留白的写作不是剪去枝节,只留与主题的写作,而是相反,留白是一种散漫性的、将一切“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的写作。并且,鲁迅的这种“留白”美学观还同时成为其生活的伦理学。
宋剑华、王苹[20]则通过对于鲁迅早期杂文的研究发现了鲁迅早期思想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他们认为,“听将令”使鲁迅早期杂文呈现出一种激情主义的战斗姿态,同时也构筑起鲁迅积极参与中国现代思想启蒙的正面形象。透过鲁迅与“正人君子”的骂战,可以发现东、西洋留学生,在对待中国社会变革的认识方面,产生了自五四结盟以来,最为严重的思想分歧。但毫无疑问,他们都是中国现代社会当之无愧的知识精英。鲁迅早期杂文的创作,还展现出一个神情黯然的背影形象。鲁迅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原本就不抱有什么信心。他认为“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这说明重功用而讲实效的儒家思想,恰恰正是鲁迅思想中“毒气”与“鬼气”的精神资源。
1993年,李欧梵在其《“批评空间”的开创》[1]中,认为鲁迅杂文妨碍了人们的“言论自由”。对此,袁良骏[21]着意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黑暗中国的“白色恐怖”下,谈何“自由”,又谈何拓展“公共空间”。即使象鲁迅这样的著名作家,也根本没有什么言论自由。李欧梵不向蒋介石要“公共空间”“自由天地”,却向鲁迅大要特要,似乎中国当时没有“自由天地”“公共空间”,都是鲁迅之罪。这样的逻辑不能成立。即使就事论事,李欧梵的言论也根本无法成立。没有“自由、平等、博爱”,奢谈什么“公共空间”?广大中国劳苦大众呻吟在死亡线上,有什么“公共空间”?至于责怪鲁迅有什么“两极分化的心态”,也根本不能成立。莫非蒋介石们的乱杀乱捕不是“两极分化的心态”,倒是反对他们乱捕乱杀的鲁迅却成了什么“两极分化的心态”吗?
对鲁迅杂文作出精彩解读的还有李怡、张铁荣[21]等。
六、诗歌研究
《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是鲁迅旧诗名篇,数十年来有关该诗诗意的解说,堪称层出不穷。邵宁宁[22]认为,究其根由,则多因阐释者误将诗中“眉黛”一词硬解为“女性”而起。实际上,“眉黛”一词在该诗中喻指“远山”,更进一步说,是指古诗文中常用来与洞庭对举的“九嶷”。关于该词种种捕风捉影式的解说,不但使该诗原有的屈骚情致变得晦蔽,而且使其深刻的现实忧愤变得浅薄、庸俗。类似的错误,同时也存在于对包括《无题·一枝清采妥湘灵》《赠画师》《湘灵歌》等在内的其他一些鲁迅诗作的解说中。如何在本属史学的方法的考据与文学作品的审美诠释之间找到恰当的结合点,以保证这种实证的努力不致因捕风捉影式的“索隐”误入迷途、沦为笑谈,这是当前现代文学研究(包括鲁迅研究)必须警惕的问题。
七、日记研究
鲁迅日记是鲁迅一生经历的生动写照,其中有文化、有民俗,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公务活动以及人事往来、书账记录等。近年来,鲁迅日记,包括其他一些名人的日记(如吴宓日记、胡适日记、顾颉刚日记)都受到重视,研究者开始利用鲁迅日记从中挖掘文化信息、民俗信息,以更好地推进文化研究和民俗研究。
20世纪初叶政府以融入世界现代化的名义,对传统民间节日尤其旧历年进行改造,出现了中国各阶层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的碰撞与分化。韩大强[23]认为,作为时代思想先锋的知识分子们既响应政府的号召,力行新历法,又在行动上、心理上与传统节日习俗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藕断丝连;而普通民众尤其下层百姓,则依然以旧历节庆为生活实践,显示出难以割舍的精神情怀。通过检阅鲁迅日记中关于“阳历新年”与“阴历新年”的记录,可以窥视出20世纪初期中国传统节日观念的变迁,以及精英知识分子们对传统节日习俗疏离与妥协的心路历程。传统文化尤其是民间重要节日内容与仪式是民众的现实与精神的生活世界,而且代代相传,与他们的人生、家庭融为一体。简单、粗暴地否定与改造是难以奏效的。经过近百年的碰撞与交锋,各种力量更加理性地认识到:一种健康的多元节日文化格局应是互相尊重、相互融合、互相改造、和合而成。
八、鲁迅作品整体研究
以上文章着眼于鲁迅作品各分集及文类研究,本年度还有一批论文是从各种视角和层面对于鲁迅作品的整体透视研究。较具代表性的视角和文章主要有:
1.鬼文化视角。谭桂林《鬼而人、理而情的生命狂欢》[24]认为,鲁迅文学世界中的“鬼魂”叙事,充分体现了“鬼”文化在语义上的丰富性与形态上的多样性。鲁迅对乡间赛神、社戏这些民间节日中的鬼魂扮演中所显示的“狂欢化”特征的赞美,是因为他深切而独到地看到了底层民众在这些狂欢活动中所获得的心灵感觉的复苏与精神力的张扬。从鲁迅的“鬼魂”意象的描写,可以看到但丁《神曲》等西方文化的影响痕迹,而更多的则是对中国古代文学中丰富深厚的鬼魂叙事传统的继承,并在这种继承中体现出五四新文化的时代精神。
2.母题学视角。谭桂林《现代中国文学母题的发展与鲁迅创作的经典意义》[25]认为,在现代中国文学中,鲁迅是最早开辟童年母题文学园地的作家,他对上海生活与文化的直接介入不仅对现代文学、对现代上海都市文化的发展直接产生了影响,而且切实地促进了中国现代都市母题文学的应运而生与积极发展。鲁迅的文学创作不仅提供了许多人物形象给新文学作家们以启示,而且提供了许多精致、隽永的原型意象给新文学家们作为模仿的范本。从母题角度切入到鲁迅研究,不仅让我们深入地认识到鲁迅文学世界的创造性的资源由来,更可以让我们看到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中,鲁迅的文学创作是如何成为经典的。
3.音乐学视角。曾锋《鲁迅的文学创作和音乐》[26]指出,对国外艺术学、音乐化文学的译介和研究,使鲁迅接触到了丰富的音乐知识和文学音乐化技巧。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中,渗透着丰富多样的音乐化成分和手法,如化用动机的重复与变奏、复调音乐、主导动机手法等,其创作也完满地印证了T.S.艾略特关于语义的音乐的理论。该文把对鲁迅与音乐的分析最终落实到了一个具体的可以进行实际操作、分析论证的层面,不但进一步展示了鲁迅语言艺术的独特魅力和成就,而且使人进一步确信,鲁迅作品确实是一个由声音、语义、意象、思想等诸多层次、因素组合而成的相互生发、相互呼应的整体艺术结构。
[1]吴义勤,王金胜.“吃人”叙事的历史变形记——从《狂人日记》到《酒国》[J].文艺研究,2014,(4).
[2]周南.狂人日记.“吃人”意象生成及相关问题[J].东岳论丛,2014,(8).
[3]张克.游民与越文化:《阿Q正传》的启示[J].江苏社会科学,2014,(4).
[4]张全之.对《鲁迅<故乡>阅读史》的阅读与思考[J].粤海风,2014,(4).
[5]杨义.《呐喊》的生命解读[J].广州大学学报,2014,(3).鲁迅《彷徨》的生命解读[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4,(1).《故事新编》的生命解读[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4,(2).
[6]汪卫东.探寻“诗心”:《野草》整体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7]钱理群.《野草》的文学启示——汪卫东《探寻“诗心”:<野草>整体研究》序[J].书城,2014,(1).
[8]汪卫东.《野草》与佛教[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1).
[9]崔云伟.鲁迅与佛陀的同与不同——由汪卫东《<野草>与佛教》所想到的[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4,(6).
[10]李培艳.“自我”与“世界”的双重“他者化”——关于鲁迅散文诗集《野草》的思考[J].现代中文学刊,2014,(5).
[11]张娟.都市视角下的鲁迅《野草》重释[J].南京师大学报,2014,(4).
[12]杨义.《朝花夕拾》的生命解读[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1).
[13]宋剑华.无地彷徨与精神还乡:《朝花夕拾》的重新解读[J].鲁迅研究月刊,2014,(2).
[14]张显凤.母亲的缺席与隐秘的伤痛——再读《朝花夕拾》[J].鲁迅研究月刊,2013,(3).
[15]王国杰.衍太太是少年鲁迅的梦中“情人”吗?——与张显凤商榷[J].社会科学论坛,2014,(3).
[16]张鑫,汪卫东.新发现鲁迅《文化偏至论》中施蒂纳的材源[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5).
[17]汪卫东,张鑫.由《文化偏至论》中施蒂纳的材源看鲁迅对无政府主义的接受[J].鲁迅研究月刊,2014,(1).
[18]魏建,周文.《上海文艺之一瞥》的谜团及其国外版本[J].鲁迅研究月刊,2014,(7).
[19]刘春勇.留白与虚妄:鲁迅杂文的发生[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1).
[20]宋剑华,王苹.“热风”与“寒气”——从杂文看鲁迅早期思想的复杂性与矛盾性[J].鲁迅研究月刊,2014,(4).
[21]李怡.大文学视野下的鲁迅杂文[J].鲁迅研究月刊,2014,(9).张铁荣.探究词语里面的深意——鲁迅杂文中的两个关键词刍议[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2014,(6).
[22]邵宁宁.鲁迅诗作的屈骚情致与现实寄寓——兼论现代文学研究的索隐、考据及审美诠释问题[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11).
[23]韩大强.疏离与妥协——鲁迅日记中关于年的意识[J].鲁迅研究月刊,2014,(3).
[24]谭桂林.鬼而人、理而情的生命狂欢——论鲁迅文学创作中的“鬼魂”叙事[J].扬州大学学报,2014,(2).
[25]谭桂林.现代中国文学母题的发展与鲁迅创作的经典意义[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2).
[26]曾锋.鲁迅的文学创作和音乐[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1).
(责任编辑 闵 军)
Several highlights of the Research of Lu Xun's works in 2014
Cui Yun-wei1,Wei Li2
(1.School of Arts Management, Shandong College of Arts, Jinan, Shandong, 250014;2.School of Traditional Opera, Shandong College of Arts, Jinan, Shandong, 250014)
In 2014, the study on Lu Xun's works took on a splendid and innovative situation. The following scholars gave their wonderful opinions about Lu Xun's novels such as Wu Yiqin, Zhou Nan, Zhang Ke, Zhang Quanzhi and Yang Yi. Qian Liqun's study of Wild Grass, Yang Yi, Song Jianhua and Wang Guojie's research on Life is A Moment and Wang Weidong's study of classic thesis at early time have a unique style. In the study of Lu Xun's essays, Wei Jian, Liu Chunyong and Song Jianhua's interpretation is fantastic. Shao Ningning's study of Lu Xun's poems, Han Daqiang's study of Lu Xun's diaries, Tan Guilin and Zeng Feng's holistic study of Lu Xun's works all have their novelties.
Lu Xun;review
2015-05-10
崔云伟(1974-),男,山东邹平人,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管理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I210
A
1672-2590(2015)04-009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