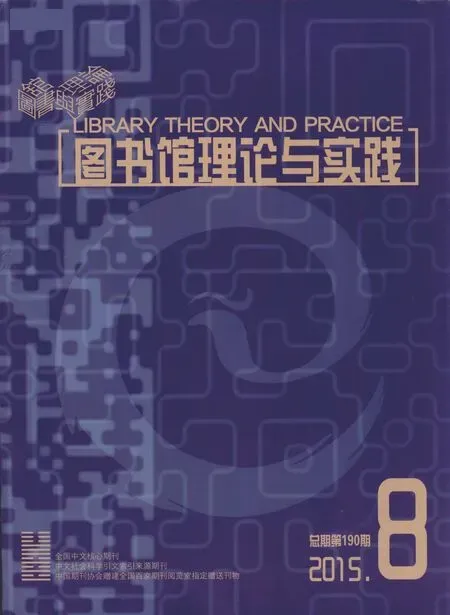重庆图书馆藏郑振铎《纫秋山馆行箧书目》考略
●景卫红(重庆图书馆,重庆400037)
重庆图书馆藏郑振铎《纫秋山馆行箧书目》考略
●景卫红(重庆图书馆,重庆400037)
[关键词]郑振铎;纫秋山馆行箧书目;重庆图书馆
[摘要]重庆图书馆藏《纫秋山馆行箧书目》,作为郑振铎藏书的重要部分,历来为外界少知。本文主要从郑振铎出售《纫秋山馆行箧书目》的原因、《纫秋山馆行箧书目》的珍贵性、重要版本举要、与《西谛书目》的比较等几方面揭开《纫秋山馆行箧书目》的神秘面纱。
1952年前后,重庆图书馆(当时为西南人民图书馆)接收了一批公私藏书捐赠,李文衡先生捐赠的郑振铎藏《纫秋山馆行箧书目》就在其中。
1 郑振铎出售《纫秋山馆行箧书目》原由
研究郑振铎及其藏书的专家学者,对《西谛书目》都不陌生,但对《纫秋山馆行箧书目》就不甚了解。主要是由于这套书自收藏进重庆图书馆后,长期珍藏于善本书库,从未开放,也未作系统的编目整理出版,更没有作进一步的研究。
《纫秋山馆行箧书目》收录的是郑振铎生前随身携带的常用古籍,此目录编成于抗战时期的上海,据《郑振铎日记全编》“写在1944年台历”中有1月8日“阴,冷。在寓午餐。写行箧书目跋”[1]的明确记载。
所谓行箧,即旅行用的箱子。郑振铎的行箧书目,也即是他随身携带随时查阅的书。实际上,郑振铎随身携带的这些书花费了他无数的心血,收藏眼光异于常人。其中,很多都是四库存目和四库未收书,价值难以估量。无论是从版本价值还是从文献价值来看,对我们研究郑振铎的收藏及治学,都是大有裨益的。
这套书为什么出售并辗转到达重庆图书馆,说法不一,以黄裳在《惊鸿集》一书中的说法最为流行,“去岁冬,郑西谛质于某氏之纫秋山馆行箧书将出售矣,余为谋所以赎归之道,商于文海,以黄金八两议定……(四九年十一月)”“后韩贾士保以金价微涨,余本已谐价付款,终乃悔约,郑氏藏书终归四川商人李某,捆载入蜀矣……时三十八年五月七日夜也。”[2]但通过查找《郑振铎年谱》《郑振铎日记全编》及《回忆郑振铎:纪念郑振铎诞生90周年和逝世30周年》,黄裳记述的郑振铎卖书时间前后混淆矛盾较多,也没有说清楚卖书的前因及后果。
如此爱书的郑振铎,在卖掉一切可卖之书的抗战艰难困苦时期,都没舍得卖掉《纫秋山馆行箧书目》中的书,却在抗战胜利后的1948年底,一次卖掉200多部珍贵古籍,必有重大缘故,绝非一句“亟需旅费”能够解释。但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郑振铎日记全编》恰好缺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上半年的日记,书中没有郑振铎本人的记录,也从未见于他人的回忆录。
经过认真查询,从《郑振铎:狂胪文献耗中年》中发现了一些端倪。该书第十二章《相思两不忘》中记述了1948年9月20日,中共中央给党的香港分局和上海局发来密电,提出再邀请参加全国新政协会议的名单,其中就有郑振铎的名字。不久,上海地下党就把中央的这一邀请秘密地传达给他。1949年元旦来到之际,上海地下组织又派党员来通知郑振铎,要求他秘密去香港,再转道北上,去筹备与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转告说:“党了解您为编印书籍,欠了不少债。让我们替您还吧!”郑振铎感动得热泪盈眶,但坚持认为:“‘不,不!现在正是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一分钱都是很可宝贵的,我怎么能接受党的这笔钱?’他坚持不要,随后卖掉了几部心爱的古书,还清了部分欠债,做好了出发的准备。”[3]
据购得这批书的李文衡事后回忆,1948年冬,韩士宝为李文衡拿来《纫秋山馆行箧书目》,并告知郑振铎先生亟需旅费,愿以书目中的书出让。李文衡毫不犹豫,当即照数全收。
根据当事人李文衡的回忆,参照黄裳在《惊鸿集》中的说法,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郑振铎卖掉这
套书,还清欠款并筹得旅费,最后利用这些旅费赶赴北京参加全国新政协会议,只有这样的大事,才有可能让他一次卖掉这么一大套心爱的好书。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李文衡主动把从郑振铎手中收购的这些珍贵古籍,连同郑振铎亲笔写的书目和跋文,全部捐献给了当时的西南人民图书馆,即现在的重庆图书馆。
2 《纫秋山馆行箧书目》的重要性
2.1《书目》多为四库存目、四库未收之书
《纫秋山馆行箧书目》的收录原则,据郑振铎在书前的长跋中所讲,这套随身所携书目包括明刻本212种,元刻本2种、明稿抄本12种,都是郑振铎30年来节衣缩食,在南北坊间书肆搜访而得到的。
郑振铎的收书原则与普通藏书家收书完全不同,普通藏书家注重版本收藏,特别是对宋元本的刻意追求,如收购郑振铎藏书的李文衡,就以重金购得一部南宋刻本《名公增修标注隋书详节》为荣。郑振铎却认为如果公私藏书处可以借得的,他往往弃而不顾,主要是因为财力的原因让他不能做到兼收并蓄。像《十三经》《二十四史》和《九通》之类的古籍,郑振铎也只收通行本、近刊本,而不收宋元本,他认为“近刊本卷帙不多,易于庋藏,便于行箧也。予所亟于访求,每见必收者,凡有二类,一为四库存目之书,一为四库未收之书”。[4]
2.2郑振铎随身携带,不愿卖出
在抗战最艰难的1944年、1945年,郑振铎卖掉各种各样的收藏古籍,就连他最看重的戏曲、小说等都面临被卖出的命运时,《纫秋山馆行箧书目》也未被卖掉,可见其对郑振铎的重要性非同小可。
《纫秋山馆行箧书目》所收,虽然不及《西谛书目》丰富与全面,但也基本体现了郑振铎的收藏以历代诗文集、戏曲、小说、弹词、宝卷、民间文艺、版画和各种经济史料为主的原则。并不是像黄裳在《春回札记》所写的:“西谛所去之书,多为常见的明本书,并无惊人秘籍。当时见识不广,不知此事,难怪这些被肆估称为‘大明版’的东西,价值如此,也不知这并非西谛十分珍惜之物,挥手斥去,不以为意。如以两种书目并观,可易知也。”[5]
据郑振铎自己在《永在的温情——纪念鲁迅先生》一文中讲道:“我所藏的书都是很辛苦的设法购得的……一部部书都可以看出自己夏日的汗,冬夜的凄粟,有红丝的睡眼,有右手执笔处的指端的硬茧和酸痛的右臂。”[6]郑振铎在收这些书的时候,他一定不会想到日后会卖的。
在“售书记”中,郑振铎写道:“谁想得到,凡此种种,费尽心力以得之者,竟会出以易米么……特别在最近的两年中,光景更见困难了,差不多天天都在打‘书’的主意,天天在忙于编目。假如天还不亮的话,我的出售书目又要从事编写了。总是先去其易得者,例如,四部丛刊百钠本二十四史之类。”[7]
2.3《书目》中多为明刻残缺本的孤本秘籍
作为一个研究者而不是藏书家的郑振铎来说,他收购的古籍多为别人不屑的残缺卷,对他却是研究的重要资料,卖掉任何一种书都是割舍不了的事。在《劫中得书记》里面,郑振铎也写道:“我不是一个藏书家,我从来没有想到为藏书而藏书。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书,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头应用所需的。”[8]在《劫中得书续记》里,郑振铎还写道:“综余劫中所得于比较专门之书目,小说及词曲诸书外,以残书零帙为最多……且残书中尽有孤本秘籍,万难得其全者。得一二册,亦足慰情。藏书家每收宋元残帙,而于明清刊本之残阙者多弃之不顾。余则专收明刊残本,历年所得滋多。”[9]
从这些可以看出,在短短的1944~1945年的一年多时间中,郑振铎从易到难,卖去了大批书,包括最舍不得卖掉的词曲书、版画书等。剩下的,都是万万舍不得割弃的,为使这批书不致被卖掉,郑振铎甚至到了剜肉补疮的时刻。“而先所质于某氏许之精刊善本百二十余种,复催赎甚力。计子母须三千余金。不欲失之,而实一贫如洗。彷徨失措,踌躇无策。秋末,乃以明清刊杂剧传奇七十种,明人集等十余种归之国家,得七千金。……立持金取得质书。”[9]
3 《纫秋山馆行箧书目》部分珍贵版本举要
1948年底,郑振铎一生中最后卖掉的书即是重庆图书馆所藏的这批被黄棠认为的“大明本”,正是郑振铎在抗战胜利前舍不得卖掉,千辛万苦留下来的书。即使从单纯的版本来看,虽然都是些明版书,但“嘉靖以前刊本,固然古朴可喜,即万历以下,特别是天启、崇祯间的刊本,曾被列入清代禁书目录的,哪一部不是国之瑰宝,哪一部不是有关民族文献或一代史料的东西!”[9]这些书里,很多都是四库未收书,如明万历十二年刻本《唐十二家诗选十二卷》,明晏良棨刻本《镌李及泉参于鳞笺释唐诗选七卷》。其中的稿钞本也是极其珍贵的,如明钞本《古今寓言不分卷》、清光绪稿本《湖乡分志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红豆庄杂录不分卷》《红榈书屋杂体文藁》《志
雅堂杂钞十卷》、清稿本《爱吾庐公余偶笔不分卷》、清稿本《汉碑文考释不分卷》、明永乐精钞本《天运绍统不分卷》。《天运绍统》是明宗室宁献王朱权永乐四年撰成,目前,最早的版本是浙江图书馆藏明天启元年梁鼎贤刻本《天运绍统二卷》。
令黄棠意外的是,1956年,他来到重庆图书馆,首次见到《纫秋山馆行箧书目》,还是感到非常激动。他认为《西谛书目》早已印行,这批书目如作“外编”增附其后,就像《天一阁书目》之有内外编一样,是可行的。李致忠先生在看见这批书的时候,认为这可能为国内仅有的。《纫秋山馆行箧书目》编写于1944年,是郑振铎为维持生计准备卖书而编写的,《纫秋山馆行箧书目》的所有书能留下,可见这部分书在郑振铎心目中的重要性。全书由郑振铎用荣宝斋稿笺写成,并附有长跋,讲明这批书的来之不易。每册书后都有郑振铎亲自手书“长乐郑振铎藏”。
这批书中珍贵者如:(1)《湖乡分志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清)常春锦纂,清光绪三年(1877)稿本,四册,半叶八行,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单鱼尾,四周双边。常春锦,清末江苏阜宁贡生。此书是他在前人基础上所写成的稿本。湖即射阳湖,湖乡分志即是阜宁县的邑志,因已有前人编的南乡、北乡志,本书所记部分着重为西部地区。此稿本是用溪花馆稿笺所写成的誊清稿本,价值极高。
(2)《唐诗十二名家不分卷》,(明)杨一统辑,明万历十二年刻本,十四册,半叶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明代选编唐诗的人很多,但合刻数家诗的却不多见。每册书钤有“御赐天存阁”“南海康氏万木草堂藏”“南海康有为更生珍藏”印,可知此书是从康有为散出。
(3)《重刻枫林小四书五卷》,(明)朱升编,明嘉靖元年于氏家塾刻本,五册,半叶八行,上下两栏,上栏小字双行,行九字,下栏九字,小字不等,白口,四周双边。《小四书》是元明之际朱升对宋、元时期成书的四种儿童读物的命名。它包括宋人方逢辰编撰的《名物蒙求》、程若庸编撰的《性理字训》、黄继善的《史学提要》和元人陈栎的《历代蒙求》。这四本书在宋、元时期各自作为教育儿童的单独的专科读物,至元末,由朱升把这四本书汇编在一起,成为一套五卷本的儿童蒙养教材,总称为《小四书》。书中钤有“独山莫祥芝图书记”,莫祥芝,贵州独山人,晚清金石学家、目录版本学家莫友芝之弟。
4 《纫秋山馆行箧书目》与《西谛书目》之比较
《纫秋山馆行箧书目》共收书126种。以诗词、文集类居多,如《申公诗说一卷》、崇祯刻本《明诗平论二集二十卷》、明万历《诗隽类函一百五十卷》、崇祯刻本《皇明诗选十三卷》、明末陈于京刻本《杨铁崖文集五卷史义拾遗二卷西湖竹枝集一卷香奁集一卷》、明崇祯三年董庭刻本《容台文集九卷别集四卷》等。另外也有少部分其他类别的,如万历间刻本《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十卷》、万历十九年郑昭服刻本《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万历间金阊天籁堂刻本《福寿全书六卷》。从相关资料看,这些书大多都是郑振铎早期所得。
从《纫秋山馆行箧书目》中还可以看出郑振铎收书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注重残篇断帙的收藏。此目录中共有36种书是缺卷的,这正好印证了他在《劫中得书续记》中所说:“综余劫中所得于比较专门之书目,小说及词曲诸书外,以残书零帙为最多……且残书中尽有孤本秘笈,万难得其全者。得一二册,亦足慰情。藏书家每收宋元残帙,而于明清刊本之残阙者多弃之不顾。余则专收明刊残本,历年所得滋多。”[10]这批书如元好问辑《中州集十卷首一卷乐府一卷》,明汲古阁毛晋刻本,是郑振铎在中国书店分两次收全。
《西谛书目》共计7740种书。其中,“明清版本居多,手写本其次,宋元版最少,仅陶集、杜诗、佛经等数种”。[11]此书目经史子集丛全都包括了,特别是有关藏曲、散曲、戏曲、宝卷、弹词、鼓词、版画和清人诗文集,耗费了郑振铎毕生心血的宝贵资料都包括在这里。从版本方面看,《西谛书目》约三分之二的都是清刻本,只有三分之一是明刻本,而明刻本中,又以明代中晚期居多。从这里也可看出,郑振铎收书的目的,是以研究为重,而不是以版本为重。
《西谛书目》中的这种情况,跟郑振铎后期对清代文集研究的兴趣大增是密不可分的。1941年,郑振铎到达上海后,“那时对于清朝人的文集忽然感到兴趣”。并且,“嘉道刊本,经洪杨之乱,流传绝罕的,得其一帙,也足以拍案大叫,浮白称快”。[10]由于这些原因,郑振铎的藏书中大部分以清刻本为主也就不足为奇了。
[参考文献]
[1]郑振铎.郑振铎日记全编[M].陈福康整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179
[2]黄裳.惊鸿集[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13.
[3]陈福康,南治国.郑振铎狂胪文献耗中年[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219.
[4]郑振铎.纫秋山馆行箧书目[M].稿本,1944:2.
[5]黄裳.春回札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174.
[6]郑振铎.幻境郑振铎散文选[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0:237.
[7]曾煜编.雪夜话读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361.
[8]郑振铎.劫中得书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
[9]郑振铎.西谛书话[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271-274,200.
[10]郑振铎.郑振铎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46.
[11]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西谛藏书善本图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8:5.
[收稿日期]2014-10-23 [责任编辑]李金瓯
[作者简介]景卫红(1968-),女,重庆图书馆馆员,主要从事古籍整理及修复工作。
[文章编号]1005-8214(2015)08-0063-03
[文献标志码]E
[中图分类号]G25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