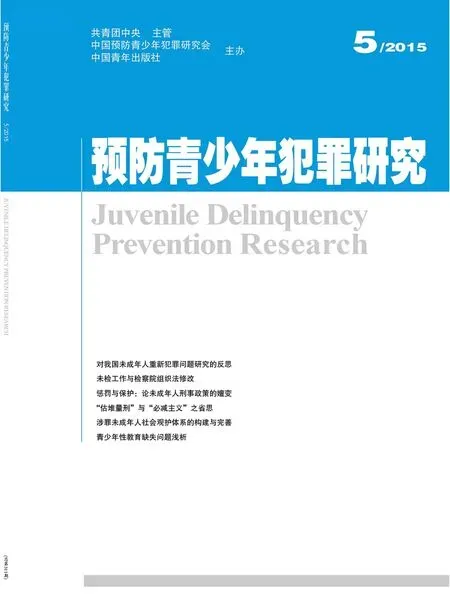国家亲权理念下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监护干预浅析
摘要:作为“重点青少年群体”及“困境儿童”双重语境下的未成年弱势群体之一,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自父母服刑之日起便开始经历着与同龄人不同的生存困难、监护困境和成长障碍。因国家亲权所系,在父母服刑而无法或不愿承担监护责任时,国家需紧急介入与干预未成年人生活。在构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监护时,应进一步巩固父母监护为主、社会监督为补充及国家监护为兜底的“三位一体”监护体系,并将由此衍生的各项干预落到实处。
收稿日期:2015-08-15
作者简介:张丽君,广西大学硕士研究生。
项目基金:本文系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资助课题《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机制探索》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兹事体大,对家庭、社会及国家发展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无须讳言,一些身处困境之中的未成年人,受制于一系列不利因素而成长坎坷。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因其父母服刑这一特殊境遇而使其监护关系面临着诸多不堪与窘境。急迫需要多方面监护干预破局,以改变目前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保护失衡的问题。
针对在社会中处于相对弱势的未成年人这一边缘群体,中央综治委与民政部通过大量前期调研,先后提出“重点青少年群体”及“困境儿童”概念。“重点青少年群体”最早于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200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提出。 ①从2010年起,中央综治委、团中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等中央部委共同开展了全国重点青少年群体服务管理和预防犯罪试点工作,将“重点青少年群体”分为有不良行为青少年、闲散青少年、流浪乞讨未成年人、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农村留守儿童等五类群体。 ②相比之下,“困境儿童”最早于2006年提出。民政部在2013年儿童福利制度试点中将儿童群体分为孤儿、困境儿童、困境家庭儿童、普通儿童等四个层次,其中困境家庭儿童包括父母长期服刑在押或强制戒毒的儿童等。 ①显然,无论是“重点青少年群体”还是“困境儿童”都无例外地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列入重点需要特别帮扶和关注的弱势群体。
按服刑场所不同,服刑人员大体可分为社区矫正人员与入狱矫正人员,前者是指因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而于社区内服刑的罪犯,后者是指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而于监所内服刑的罪犯。据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2005年底的抽样调查报告显示,46万在押服刑人员有未成年子女且子女总数超过60万人,监护缺失下的未成年人生存状况令人堪忧。 ②截至2012年末,我国在押服刑人员几近166万人; ③而截至2014年5月,在册社区服刑人员亦达70.9万人。 ④换言之,200余万服刑人员在监狱或社区服刑,其未成年子女绝对数量较2005年调查可能会有较大增加。
尽管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数字庞大,但目前学界及实务界对其监护干预的研究仍然稀缺,以致对该特殊群体的数量、年龄分布、心理历程、经济现状及亲子接触等相关信息常无从查起。2014年,我们曾对A省B地级市126名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及103名现任监护人进行访谈,其中监护人的基本情况可从几个方面予以描述:监护人年龄普遍偏大,监护子女较多、家庭经济贫困、负担繁重,隔代监护现象屡见不鲜,且普遍呈现出监护人文化低能化、生活赤贫化的特点。 ⑤以管窥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监护常处于游离状态,教养质量下降,亟需基于“国家亲权”理念和“儿童最佳利益”法则对需要救助和帮扶的未成年人实施监护干预,以促其健康成长。
二、亲权与国家亲权下的未成年子女监护
在儿童福利与照管上,各法域无一不视发展健康、有序的亲子关系(parentage)为构建与维系和谐家庭关系的基石。因身心尚未成熟,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有效监护。然而,具体到服刑人员,即便其愿意继续承担对其子女的监护义务,该义务的现实履行随其入狱服刑而变得举步维艰。即便是社区服刑人员,因其生活境遇立转而亦可能面临着不愿或愿意但无力承担监护的窘境。此刻,便凸显出亲权行使现实障碍与国家亲权介入时机及力度间的直接冲突与深刻矛盾。
我国《民法通则》、《婚姻法》、《收养法》及《继承法》等法律法规虽涉及亲权规定,但未明确“亲权”(parental rights)这一专业术语。而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均将亲权视为亲属法或家庭法中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对亲权概念的界定,中外学界及实务界原则性分歧并不大。如依美国《布莱克法律词典》解释,亲权为父母做出有关子女所有决定的权利,包括终止子女照管及监护权、教育及惩戒子女权以及控制子女收入及财产权等。 ⑥亲权一般系指父母有决定有关孩子事项的权利,包括决定孩子的照顾与监护、教育与惩戒以及对子女的财产进行控制和处分。 ⑦
不同于亲权,国家亲权概念及理论主要源自英美,特别是美国普通法。依《布莱克法律词典》解释,少年司法语境下的国家亲权法则主要系指作为主权者的国家,应作为终极关爱者竭尽所能向无法照顾自身的公民提供保护。 ①伴随国家亲权的深入与践行,国家愈来愈扮演着儿童利益的最终监护者的重要角色。一旦父母无力或不愿承担照管子女义务时,国家应援用公权力剥夺父母、法定监护人或其它监护者的监护权,强制干预儿童成长的过程,以弥补其生活上、心理上或人格上的缺失。由此,儿童与国家之间构建出类似父母亲权的拟制关系,而这种由父母亲权移转至国家的特殊权利通常被称为“国家亲权”。 ②
“国家亲权”理念为国家介入和干预未成年人特别是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生活提供了法理依据。国家亲权不仅关注对未成年犯罪人的行为矫正,使其知错悔改、迷途知返,还对广义的未成年被害人予以救助,防止因遭受重大家庭变故而深陷困境。“国家亲权”理念以保护弱势群体为出发点,认为未成年人不是其父母的私人财产而是国家的未来资产,当未成年人父母无法保护其合法利益时,国家便有义务和责任及时介入以代位保护其未来资产—未成年人。历史上,基于血缘关系的亲权曾长期赋予父母对子女拥有绝对的权力与义务,继而认为对子女教育管教乃国家公权力所不能染指之“家事”,而将国家亲权排除在家门之外。然而时过境迁,现代“国家亲权”理念以现实社会的发展需要为其孕育与发展的土壤,与父母亲权针锋相对。伴随家庭权威日趋渐微,国家从家庭“攫取”了更多的权威,这使得两者之间日益衍变为剑拔弩张的一场博弈。 ③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随着国家亲权理念的传播与践行而得到广泛重视,国家也逐渐承担起未成年人终极监护人的重要角色。
作为我国民法理论的一项重要制度,监护是指监护人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利益、财产权利等其他合法权益予以照料、管护与监督的制度。作为对未成年人与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予以照料与管护的民事法律制度,监护一般可分为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 ④虽然对监护权性质的争议由来已久,主要有权利说、义务说、权利义务一体说与职责说,但有一点为主流学说所接纳,即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存在照顾与被照顾、管护与被管护的关系。 ⑤《民法通则》第16条规定,未成年人父母为其监护人,并详细规定了在父母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情况下可担任监护人的人与监护顺序。可见,父母作为子女首要监护人正是基于亲权乃维系父母与子女照管关系最为直接与重要的伦理与法理纽带而来。在外来风险影响及社会监督乏力下,这种以血缘关系和拟制关系建构起来的监护范式有时不堪一击。如未成年人的父母因犯罪而危及亲权的现实及有效实现,其权利亦因此而较难予以保障。这时,国家需要行使拟制亲权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进行干预,涵盖对服刑人员监护权及服刑人员与未成年子女间亲子互动的监督干预。当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国家监督状态下仍然无法有效履行亲权与监护职责时,国家因“国家亲权”理念应挺身而紧急动用公权力指定有关个人、组织及职能部门代位履行监护职责,实为国家监护之兜底保护。国家监护是指国家为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在国家亲权的理念下由政府主导干涉处于监护缺失状态下的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对失当或失依未成年人及其家庭提供生活帮扶、心理谘商、教育辅导、监护随访等服务。 ①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纳入困境未成年人进行国家监护干预和救助,使得其权利受到保障。国家始终扮演着儿童终极监护人的重要角色,对其保护和帮扶的福利延续至其成年。正是在国家亲权的理念下,通过巩固父母监护、强化社会监督及兜底国家监护等途径,来实现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监护干预。
与此相对应,家庭干预、社会干预、行政干预与司法干预等共同构筑了立体化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体系。其中,司法干预是指包括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进行帮扶、探视与救助的干预。行政干预是指民政部门及其下属福利机构、教育部门、卫生部门、监狱等在内的职能部门对其进行物质救助、心理谘商、教育及医疗保障等干预。除此之外,社会干预也是援助困境家庭、保护未成年子女权益的利器,包括志愿服务、慈善机构及社会捐助在内的民间帮扶活动。
三、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监护干预的现实困境
(一)法律规定实操性有待显现
根据《婚姻法》第21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当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此为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中对亲权概念最为直接的描述。《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3条规定,“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可依申请请求法院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规定变更监护关系的应按照民事特别程序处理。而《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四部委意见》)中专设申请撤销监护人监护资格一节,并将因服刑而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作为可被申请撤销监护权的情形之一,以上法律、文件大体勾勒出监护干预的主要法律框架。
悉数国内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在救助、教育、管理和保护等方面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规定,主要散见于国务院和民政部下发的各项法律文件中。深究发现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保护主要是以困境儿童为直接对象,且多以国家政策居之。多数情况下,未成年人父母一方服刑并不意味着亲权监护的缺失,而是面临单亲监护的困境,而这些困境正是法律较难虑及的。《四部委意见》出台之前,《民法通则》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中的监护权干预条款因缺乏具体程序的规定而被戏称为“僵尸条款”。《四部委意见》出台后,虽然在虐童案件上已经迈出了巨大一步,但涉及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干预仍面临着一定的实操困境,如是否需要考虑服刑人员服刑种类与刑期长短、无障碍一方当事人的意愿以及家庭经济实力等现实问题。
(二)前置性预警机制缺位
目前,尚未构建有效的前置预警程序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纳入监护干预体系。有关数据显示,约2.5%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在社会上流浪、乞讨;北京在押未成年犯中父母一方或双方服刑的占未成年犯总数的9%。 ①可见,未成年子女在父母服刑时由于亲权缺失极易出现流浪、乞讨、犯罪等情况。提前发现这些心理压力巨大、境遇窘困即处于或者已经处于困境中的儿童是立法者与实践者应当优先考虑的问题。
前置性预警机制的缺失只能让我们处在个案优越中,这与普适性救助和福利国家建设不相容。极不利于相关政府部门及时掌握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监护现状,可能致使公权力无法及时介入并予以有效干预。简而概之,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监护干预往往是在其已处于深度困境,甚至食不果腹、流浪街头,或者误入歧途走上犯罪道路之后。预警机制的缺失,较易导致国家亲权无法及时介入未成年人的成长以弥补亲权的不足。
(三)监护干预救助范围有限
考虑到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心智尚未成熟、生活状况欠佳、家庭功能结构缺失,易失去自我调节功能,产生自卑情绪。家庭的变故使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变得更加敏感,当遇到歧视或者冷落时,极易封闭自我。若得不到及时的心理疏导,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正常生活、精神状态,甚至出现行为偏差、犯罪倾向化意识。因此,国家基于生存而施行单一的物质救助并不能满足未成年人成长所需。尤其在现代福利社会对生存和健康的发展已不局限于解决温饱和身体免受侵害,还包括基本的社会保障、在困境中的救济,更高意义的建立在心理、精神、心智等需求层次上。 ②
我国相关法律虽有提及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不同的方面提供救助,但无专门性规定予以释之。根据《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儿童保护应符合依法保护、儿童平等发展、儿童利益最大化等基本原则。 ③因此,有必要突破国家监护干预范围,对其进行亲职教育、心理谘商和精神安抚。
(四)监护转移配套机制缺失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转移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依据法律发生的监护权转移,带有明显的公权力特征;另一种是享有监护权的监护人将部分或全部监护权委于他人。监护权转移作为儿童监护干预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虑及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最佳场所,监护权转移应慎而用之。
现实情况中,当司法者被迫选择移转监护权时,却面临着转移配套机制不畅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父母一方服刑,另一方往往会离家出走、不知所踪或者无能力监护,此时是否需要转移监护权?规定是由未成年子女的其他监护人承担监护责任,然而现实会出现因户口问题无法为孩子提供医疗、教育等基本生活保障。如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法院就曾对父亲服刑母亲患病的未成年人以司法裁定书的形式进行了监护权的协商转移。 ④其次,在其他法定监护人均不愿承担监护责任时,应当如何选择指定监护人。实践中,浙江省仙游县法院在一起虐童案件中,将监护权最终移转给村民委员会,是否需要一个托底机构已经成为立法与实践者共同关心的问题。 ①最后,在政府兜底监护的情况下,又如何集中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监护机制建设。除此之外,监护权转移的起诉主体是谁、举证责任如何分配等问题依旧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监护权转移机制之上。
四、构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监护干预机制
(一)完善社会调查报告制度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数量庞大,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理应受到关怀,广义上的监护干预实施有赖于对这一群体信息的持续掌握。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建立不仅有利于掌握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基本生活状况,还为选择何种干预措施提供有力的参考依据。
笔者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建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首先,明确实施主体。共青团、妇联有维护妇女和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职责,通过顶层制度设计,赋予其社会调查报告实施主体的地位,深入基层了解基本情况。村民委员会与居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配合共青团与妇联的工作;基层司法所承担普法职责,亦应对共青团与妇联工作予以协助。其次,明确调查范围。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监护现状的调查不能停留在形式层面,如是否存在其他监护人及其与被监护人之间的身份关系。《民通意见》第11条规定,“监护人的监护能力应考虑身体健康状况、经济条件、教育程度及其与被监护人关系密切程度等因素。”社会调查报告应以此为依据,必要时可对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以及周围关系紧密之人、社区、基层组织机构进行调查。最后,明确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当确有必要移转监护权时,笔者认为从调查报告的制作主体以及调查报告的具体内容来看,起诉主体可以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证据使用。
(二)扩大国家监护内容范围
国家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监护范围过于狭隘,通过物质救助保障其基本生活得以持续已不符合未成年子女身心发展的要求。应将身体健康的外延扩大至情感认同、文化交际与社会认知等方面的心理谘商与亲职教育。 ②扩大监护干预内容宜坚持儿童最佳利益原则,《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第1款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为,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 ③这里的一切行为是指在保证儿童能正常和健康发展的前提下,即处理有关儿童事务的政府性活动应以儿童最佳利益为首要。
为防止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因家庭问题产生反社会化行为,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进行监护干预须虑及其身体、心智和精神等方面,改变传统的物质救助范式,从单一的国家监护干预向综合性国家监护干预迈进。在制定政策、提供福利等方面,优先考虑困境儿童的利益和需求并坚持根据不同儿童群体需求特点,提供分类保障,适度普惠。儿童福利是对儿童进行专门的救助、教育与感化的社会福利,包括教育、医疗、就业、收养与反家庭暴力等内容,特别包括应对儿童遭受虐待、遗弃与照管不良的社会福利。 ①尤其针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其自身和家庭的特殊性,需要国家在行使亲权过程中酌情考虑实施临时照料、教育辅导、心理疏导、监护指导、亲职能力培训、帮扶转介等服务,定期适当安排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探视其父母以恢复可能僵化的亲子关系,这也是儿童福利对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国家干预的具体践行。
(三)建立健全信息沟通平台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监护状况的恶化通常是从其父母犯罪时开始,特别是监护人侵害被监护人案件更是如此。从程序上讲,刑事案件从立案到审结少则需要数月多则数年,而其子女的生活与监护状况是瞬息万变的,稍有不慎就会产生影响终身的遗憾。2014年,课题组在A省B地级市调研时发现不少未成年子女不知道父母是否犯罪与所犯罪名,甚至出现了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负责人员不了解所辖区服刑人员及家庭的基本信息。
笔者认为应当完善以下几个沟通机制:首先,在各级综治委特别是县区级及地市级综治委建立健全司法系统信息交流平台,用以收集本辖区内所涉刑事案件中当事人是否有未成年子女的基本信息。其次,明确公检法司等机关的具体职责。处理刑事案件时,要了解涉罪人员是否有需要抚养的未成年人并记录在案。公检法司等机关在移送案件、提起诉讼和审判阶段须在案件材料中另附未成年子女信息材料,并分别向综治委汇报。最后,综治委将统筹的信息及时传达给未成年子女所在基层社区组织以及民政部门,以期尽快干预涉罪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成长与监护。同时,因我国刑事案件的属地管辖会导致涉罪人员案件受理地与其子女居住地不一致的情况,各级相关部门还需加强跨区域信息交流,及时将案件审理进程反馈至涉罪人员未成年子女所在地的综治委。
(四)完善监护权移转机制
在儿童福利与照管上,各法域均将发展健康、有序的亲子关系作为构建与维系和谐家庭关系的基石。依国家亲权理念,国家应扮演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终极监护人的角色。当监护人履行不力,或者不能履行监护职责时,国家作为监护人就应挺身而出对原监护权进行及时干预,保障儿童健康成长。该理念要求国家在已有资源下,最大限度的履行义务。
现有法律机制下,剥夺监护人的监护权看似轻而易举,实则因缺少“下家”而变得举步维艰。笔者认为在监护权的移转过程中有以下几点需要明确:首先,长效干预机制优先于监护权撤销。家庭是儿童成长的最小社会单元,当简单的救助或者干预可以起到完善监护的目的时,应当尽可能尊重。国家对家庭监护的干预须慎之又慎,遵循“穷尽规则”。其次,进一步明确监护转移的主体。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化解社会矛盾是民政部门的本职要求,《四部委意见》也同样指出,民政部门可作为兜底部门并由其下属儿童福利机构履行监护职责,故而将民政部门作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终极监护人于法有据。再者,完善监护权移转机制。国家亲权理念下的监护救助机制应是多元的,福利性国家的建设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群策群力。
(下转第47页)
王自然.要加强对重点青少年群体的教育管理服务[N].人民公安报,2006-1-21(01).
桂榕,张武明.全国重点青少年群体教育帮助和预防犯罪试点工作推进会举行[N].江西日报,2010-10-29(01).
魏铭言.民政部:保障困境儿童基本生活[N].新京报,2013-7-2(18).
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课题组.监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基本情况调查报告[N].中国青年报,2006-7-4(02).
国家统计局.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2/indexch.htm
国家统计局.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4/indexch.htm.
张鸿巍.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生存状现状实证研究-以广西A市为例[J].(未刊载)
Bryan, Garner A (editor).(2009).Black’s Law Dictionary (9th edition).St. Paul, MN: West Publishing Company,p.1224.
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867.
Dwyer,James G.(2006).The Relationship Rights of Children.New York,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82.
张鸿巍.少年司法语境下的“国家亲权”法则浅析[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4(02):81.
张鸿巍.儿童福利法[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2012:86-88.
魏振瀛.民法(第四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0.
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875-876.
陈翰丹,陈伯礼.论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中的政府主导责任[J].社会科学研究,2014(02):81-83.
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课题组.监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基本情况调查报告[N].中国青年报,2006-7-4(02).
张鸿巍.儿童福利法[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2012:31-33.
《中国儿童福利发展纲要(2011-2020)》.
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父坐牢母患病法院协商一致变更监护权[EB/OL].http://www.lyghzfy.gov.cn/qsnwq/2015-04-01/186.html.
仙游县人民法院.仙游一女子不履行监护职责被撤销监护权[EB/OL].http://fjxyxfy.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4/09/id/1449045.shtml.
王永明.儿童权利保护的国际法研究[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09.
《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第1款(1989-11-20).
张鸿巍.儿童福利法[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2012:38-40.
——从虐童事例切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