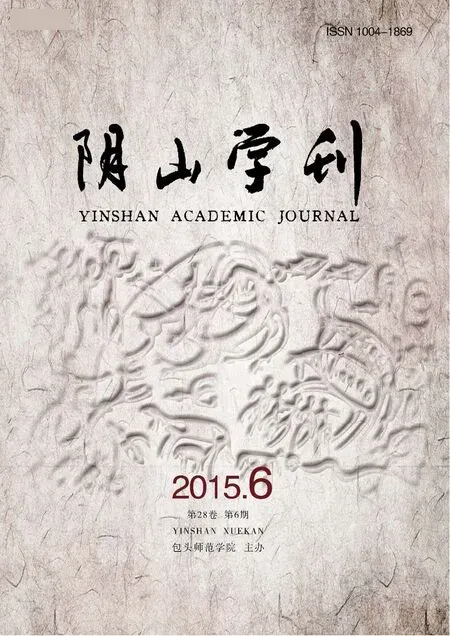以实践辩证法透视“三个有利”与“四个全面”的逻辑关联
以实践辩证法透视“三个有利”与“四个全面”的逻辑关联
张 海 燕
(内蒙古大学 哲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国梦”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实践,以实践辩证法所内含的总体性思维、主体性精神和以自否定促发展的精神来透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与“三个有利”的逻辑关联,为“改革促进派”提供符合实践辩证法的理论支持,应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内在要求和焦点问题。
关键词:四个全面;三个有利;实践辩证法;总体性;主体性
2015年1月23日,第一次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主题就是辩证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维方法对于促进当前改革开放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是纯粹思想的逻辑演变,而是立足于实践的辩证思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为实践辩证法。习近平总书记继“四个全面”的总体设计之后,又提出了以“三个有利”为标准争做“改革促进派”。这些都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思想中所蕴含的实践辩证法的总体性、主体性和以否定促发展的精神。如何在实践辩证法透视“三个有利”与“四个全面”的内在逻辑关联,为“改革促进派”提供理论支持,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四个全面”的顶层设计体现了实践辩证法的总体性特质
(一)总体性是实践辩证法的重要思维原则
总体性是辩证法的重要特质,辩证法又可以称之为辩证逻辑。作为辩证法的大师,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逻辑学》等著作中就已经提出了辩证逻辑是对非此即彼形式逻辑的扬弃。而黑格尔扬弃形式逻辑的重要思维原则就是总体性,只有借助于总体性而且是历史的总体性,形式逻辑的非此即彼才能被扬弃。通过“实体即主体”的绝对精神的运动,黑格尔尝试祛除康德哲学里的“物自体”以及“物自体”与“现象界”的鸿沟,在体系和方法的统一中达到历史的总体性。马克思十分赞赏黑格尔的历史总体性,但他反对黑格尔将历史总体性展现为绝对精神的自否定性运动。当马克思将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看作是现实的人的存在时,他也同时将辩证法转换为现实的人基于实践的历史总体性,换句话说,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是实践的辩证法。
马克思将辩证法的视域从绝对精神转换到了现实的人及其在社会关系中所进行的实践活动,但总体性依然是马克思实践辩证法思想的重要特质。不论是前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是后期的《资本论》,总体性思维如都贯穿马克思思想的始终,构成马克思考查社会历史问题的重要思维特质。马克思实践辩证法思想中所包含的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价值诉求,以及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道路的科学探索,既表明了马克思的辩证法是立足于实践的辩证法中求真和求善的统一、科学与价值的统一,也表明总体性思维在马克思实践辩证法中的重要性。《资本论》作为马克思的集大成之作,绝非仅仅是经济学论著,这部著作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思维渗透到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性考查之中,而二者的有机整体性融合又以在批判和革命中探索更加美好的“自由王国”为社会诉求。
针对资产阶级和当时“第二国际”存在的将现存的一切看作是“第二自然”的非历史立场,卢卡奇考查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从中发现并再次重申了历史总体性是辩证法的核心范畴和思维特质。“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到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1]( P78)当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垄断阶段,“物化”成了整个社会的普遍性现象,“物化意识”渗透到社会各阶层之中,局部之间看似合理的计划和行为在局部与局部却出现了无法对接的问题,使得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由于缺乏总体性而导致的危机。而要走出这种由“物化”和局部无法衔接而导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危机,卢卡奇把历史总体性重申为辩证法的特质十分重要,“辩证法不管讨论什么主题,始终围绕着同一个问题转,即认识历史过程的总体。”[1] (P86)而在思想观念领域,要走出“物化意识”,批判仅仅局限于某一领域、某一方面、某一条件下的条块式思维,培育基于主体-客体的历史总体性辩证法思维就显得至关重要。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实现了马克思总体性历史辩证法与中国优良文化传统中的整体辩证思维的恰当融合。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毛泽东在《实践论》、《矛盾论》中格外强调了辩证法的实践特性。这两篇辩证法著作绝不是闭门造车的逻辑分析和概念推演,而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实践中集体智慧的理论表述。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实践性是毋庸置疑的,而通过“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辩证统一,对复杂事物中所存在的复杂矛盾来进行统筹安排、战略把握,也体现了辩证法的总体性思维。而在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所做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也是基于新中国建设初期实践经验教训的总体性总结,是研究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辩证法思想不可忽视的文本。可见,不论是在革命还是建设时期,实践性和总体性都是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重要特质,也表明了重视辩证法的实践性和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传统。
(二)“四个全面”是当代中国实践辩证法的总体性表述
从理论上来说,实践内在地要求合理的理念引导,纯粹经验性的试错并非实践的唯一形式。实践作为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内在地要求富有创造性的设计理念。虽然马克思驳斥了将自我意识、绝对精神视作哲学主题的思辨哲学,但是马克思却十分重视理论的作用。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提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2] (P15~16)合理的理论对于实践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重要的,这不仅是因为经验试错不是实践的唯一形式,而且是因为经验试错本身也需要理论的引导,任何试错本身都不会是毫无目的,而这种价值判断恰恰是经验试错本身无法提供的。与波普尔立足于经验论的传统,强烈反对进行总体性规划的社会工程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片面强调单一的实证性和经验主义有它自身的局限性,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需要具备历史总体性思维。《共产党宣言》在谈到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时强调,“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2] (P285)
从实际的社会发展阶段来看,中国改革也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期,这是新时期既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同时也是“面临诸多风险的矛盾凸显期”。当前时期的许多矛盾凸显出来,已经不能靠“摸石头过河”方式解决。在改革开放初步探索的时期,“摸石头过河”的试错式方式对于激发主体的积极性是十分有效的,切合当时实践要求的。但是“摸石头过河”一方面以一种空前的主体热情开创出了很多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措施,另一方面也使得各种社会矛盾呈现出来。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当改革已经从浅水区越来越步入深水区之时,已经没有石头可以摸,经验试错已经不能满足当前改革实践的复杂性需要,从总体性思维对改革这盘大棋进行顶层设计已经势在必行。“马克思主义正统决不是守护传统的卫士,它是指明当前任务与历史过程的总体的关系的永远警觉的预言家。”[1] (P76)重大机遇和风险并存的时刻最能考验个体和政党的洞察力和勇气。“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统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艰巨繁重的系统工程。”[3] (P21)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月16日提出的“四个全面”就是以他为首的党中央在改革关键时期,立足改革实践的实际情况,从运筹帷幄从战略高度做出的总体设计,在这个顶层设计中,总体性思维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首先,总体性思维首先意味走出条块分割的机械论思维,更加注重整体的有机联系,注重从系统、整体和协同的视角来综合设计改革的各个相关方面。现代科学的系统论、协同论以及过程论哲学等进一步发展了总体性辩证思维。作为新时期顶层设计的“四个全面”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整体统筹、协调各方的总体性思维提出来的。“四个全面”是一个协调统一的系统,四个方面缺一不可,旨在克服以GDP为单一衡量标准的发展模式,“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构建全面和谐可持续的发展理念。这就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具体的工作中,必须秉持总体性思维,不能顾此失彼,为了GDP等个别方面而忽视了社会发展的总体关联,更不能在已经对社会总体发展已经造成危害的情况下仍然坚持片面追逐某一方面利益的不良发展道路。“四个全面”的顶层设计是对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总体性思维的战略运用,当代中国实践辩证法的总体性表述。
再次,总体性思维还意味着走出静态思维,以历史性的思维和视野看待事物。从实践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历史绝非仅仅关涉过去留存下来的史料这些物质性的东西,而是从传统中走来,又面向未来,在传统和未来之间的主体在当下所进行创造性活动。作为历史行动的主体,既不能一味地强调顺从过去的经验和传统,也不能对之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是要在量变和质变、连续和跃迁的统一中思考和行动。“四个全面”既是对以往改革经验的归纳总结,又是基于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但所有这一切并非仅仅是为了评价以往历史的功过是非,而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致力于把中华民族带向更加美好未来的出发点,是志向于未来的新设计。只有将对“四个全面”的理解提升到历史性的维度,我们才能更加清楚地看到实施“四个全面”的重要性;只有把“四个全面”作为一项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大政方略,并真正按照这个大政方略去实践,我们才能在历史性行动中创造新历史。
二、以“三个有利”打造“改革促进派”体现了实践辩证法以否定促发展的精神
“四个全面”的顶层设计不仅仅是简单的理念倡导,而是体现时代要求的全面战略方针,如何把“四个全面”从设计层面进入具体的实践层面,使之从一种应然的理念变成实然的现存,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值此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5月5日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指出,“只要对全局改革有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利、对本系统本领域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有利,都要自觉服从改革大局、服务改革大局,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共同把全面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做好。”[4]这些讲话被概括为“三个有利”,“三个有利”的提出恰好旨在打造致力于“四个全面”的实践主体。
(一)以自否定促发展是实践辩证法的精神实质
以自否定促发展是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内在要求和精神实质。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论述辩证法的否定性精神时说,“精神所以是这样一种力量,乃是因为它敢于面对面地正视否定的东西并停留在那里。精神在否定的东西那里停留,这就是一种魔力,这种魔力把否定的东西转化为存在。”[5] (P76)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独具慧眼地辨识黑格尔思辨辩证法体系中所蕴含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精神实质。而《资本论》则更明确说明了马克思本人在考查资本主义社会时所彰显出的辩证法的否定性精神。马克思在《资本论》1872版跋中关于辩证法的论述经常被人们用“颠倒论”来描述,以为马克思辩证法的历史贡献是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这个说法主要基于本体论改造的说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却容易被误解从而把辩证法形式逻辑化,从而遮蔽了马克思辩证法的实践性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批判的和革命的”的论断。事实上,《资本论》真正发扬了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革命性因素,将辩证法的问题域由概念的自我否定性转换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否定性。可见,马克思辩证法的真正理论旨趣在于突破旧制度的牢笼,以自否定促发展的问题。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具体谈到了无产阶级自我改变的重要性。无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也需要经历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才能完成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而革命就是通过自否定完成从自在到自为的主体生成性实践。“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身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2] (P91)这就意味着实践主体绝不能固步自封,而应当不断地以否定性精神来审视其所面对的实践对象、实践环境、实践条件和实践结果,同时也不断地以否定性精神审视自身实践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进一步的实践来推进问题的呈现和解决。马克思实践辩证法中所蕴含的以自否定促发展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得到一以贯之的重视和践行。不论在革命岁月还是在建设年代,重视开展批判与自我批评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正是凭借这个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人才做到了及时发现问题、直面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在实践过程中增强了自身有机体抵抗疾病、健康成长的能力。
而今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和重重诱惑,清醒的自我意识是正确面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的前提。执政日久的中国共产党更加需要秉持实践辩证法以自否定促发展的精神,保持勇于自我剖析、自我批判、自我改革的优良作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重提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所讲的“进京赶考”的话题。“赶考远未结束”,赶考永远在路上,“‘考试’仍在继续,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6]这番话告诉我们,对于作为实践辩证法践行主体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实践辩证法的否定性精神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主体性的。
正是基于此,“四个全面”的顶层设计才需要特别注意“全面从严治党”,雷厉风行且持续进行的反腐倡廉运动旨在清除病毒,为党的有机体的健康提供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而最近提出的以 “三个有利”激励党员干部争当“改革促进派”恰好与之前的“全面从严治党”共同组成了锻造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在品格方面的正反两重维度。在“四个全面”的时代,党员干部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个人利益与改革利益之间的冲突问题。党员干部不仅有自己的个体利益,更是党和人民利益的直接关联者和协调者。作为各方利益的统筹和协调者,党员干部不可避免地要在面临很多利益抉择问题。尤其是当小局影响了大局,局部影响了全局,改革影响到了个人和单位利益,各级领导干部能否立足改革大局,做到“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就成为对党员干部的直接考验。“三个有利”的“只要……都要……”既是伦理价值诉求,有在一定意义上是党组织对各级党员干部的“绝对命令”,是价值引导和组织纪律的双重要求。
(二)理想与现实间距需要以否定促发展的实践辩证法精神
1.实践需要以否定促发展的精神。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绝不是正反合形式的随意套用,而具体的实践辩证法。辩证法的实践性本身就意味着其不是先验的,而是具体的。在马克思之后,克西科在《具体的辩证法》中提出了实践的两种形式,一种是批判的、革命的或者立足于改变不合理的现存状态的实践,另一种则是纯粹处于追逐利益的、功利的行为。“从实用的观点出发,或者从操控、操持和支配的实践的观点出发,人们可以为实践辩护,也可以对它进行批判。然而,这里肯定的态度和否定的态度都为超出伪具体领域,因此永远不能揭示出实践的真实性质。”[7] (P167-168)克西克秉承了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具体性精神,批判了出于功利主义的拜物教实践,认为只有前一种实践即改变不合理现存的创造性实践才是“真正的实践”,而后一种是“伪实践”。
我们这个时代比任何时候都渴望创造性的实践,渴望以“真正的实践”改变不合理的现存状态,并通过历史的行动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生活。不论从国家和民族层面,还是从个体层面,我们都渴望创新、创造。当这种渴望作为一种普遍性的观念呈现出来,它就可能成为一种现实的活动,而如何把这种普遍性的客观转化为真正富有激情的行动性力量,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改革无疑就是一种立足于改变不合理的现存状态的“真正的实践”。实践作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必然意味着主体的愿望与现存的社会现实之间的不同一,这种不同一形成了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自否定作为实践辩证法的内在精神,体现了实践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间距,而缩短这个间距的过程就是通过实践逐渐弥合目标所体现的合目的性与社会的有待更加合理化的现存之间的间距。
改革作为当代中国的重大社会实践面临着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间距问题,而在中国梦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的间距就是以改革谋发展所需要跨越的距离。“中国梦”的理想正是致力于用一种更加合理的理念对现存社会不合理方面进行纠偏和改善,这个过程毫无疑问要对之前存在的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利益进行触动。在这个过程当中,利益分配重新进行调整在所难免,而这里的关键是利益调整必须秉持总体性辩证思维,以总体统摄局部,不能允许个别团体利益凌驾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之上。
2.“全面从严治党”与“正当改革促进派”是党打造健康有机体的自否定性环节。历史的规律性和客观性不同于自然必然性,在这里不存在自然科学研究实验中被净化的环境,在这里行动主体都是以其自身的目的性去参与社会活动,但历史的结果作为各怀目的诸多行动主体的合力结果,呈现出来的确实一种客观的规律性。人类历史不同于自然史的地方在于它有具备主体能动性的现实的人的现实的、具体的活动展现出来。马克思指出现实的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现实的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也是历史的演员。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做纯粹的旁观者。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者,一方面是因为它代表了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进力量,另一方面这种先锋队地位是由于其自为性而形成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凭借其超前的思想观念和艰苦卓绝的行为才最终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包含“全面从严治党”在内的“四个全面”是中国共产党自己提出和自己践行的,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能力通过行动完成从自在到自为、并进行自我超越的领导集体。
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生命力来自于这个有机体能够适时地进行自我批判、自我改造,通过这种自我否定性来促进自身的健康发展。当党内出现贪腐或者一些干部以个体、小集体利益拒绝或对抗中央的总体性方针时,“全面从严治党”就势在必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同时也是直面存在的问题,在自我反思、自我调整中实现自身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正是这种不遮不掩地直面问题的优良传统,恰恰证明了党在全面改革时期能够遵循实践辩证法的内在自否定性精神,直面与党的有机体健康发展相冲突的反题,并在对这些反题的承认、分析和解决中进一步清洁自身,增强自身免疫力。
增强党的生命力从生命有机体的内在矛盾来看,一方面需要注意加强自身免疫力,防止外在不良事务对党的生命有机体的侵蚀;另一方面也需要秉持自我否定性的精神,进行自我审视、自我批判,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审查自身存在的问题,并加强自身锻炼。如果说严惩腐败、 从严治党体现了党对党员干部在行为的规诫准则和最低要求,“三个有利”则意味着除了这些规诫准则类的要求之外,党员干部还不能以不作为、消极怠工的方式阻碍改革的全面深化,而应当立足改革大局,正当“改革促进派”。
三、以“三个有利”为“四个全面”打造“改革促进派”体现了实践辩证法的主体性精神
(一)“三个有利”是推进“四个全面”的主体总动员
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各种矛盾尤其是利益矛盾凸显出来,国际舆论和社会各界都在密切关注着中国改革将如何进行的问题。“四个全面”在实施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力和阻力,而如何使得这些压力和阻力成为深化改革的动力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三个有利”之后,在传统媒体和网络新媒体迅速引起了广泛传播和热议,这一方面说明了“三个有利”提出的及时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广大干部群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人民日报》的《再论“矢志改革者”:以三个有利标准选人》从选人标准角度首先进行了解读。从实践辩证法的角度看,以“三个有利”为标准为“改革促进派”提供支持,是改革实践在主体方面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实践辩证法的主体性精神。明确“为了谁、依靠谁”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国梦的前提性和关键性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关键。
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时,我党就预计到了全面深化改革所面临的巨大压力、阻力,“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最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8] (P7)在复杂的历史性实践活动中,通过理论形成目标聚焦和价值共识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马克思在批判资产积极意识形态和用彻底理论的理论激发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工作,列宁更是十分注重对“先锋队”的锻造,毛泽东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者们更是将思想政治工作视作党的“生命线”。在“四个全面”的新时代背景下,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难度,就更需要凝聚党员干部形成最大共识,打造一支“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生力军。只有具备这样的主体性力量,“四个全面”才能真正践行下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指出的“三个有利”并以此引导各级党员干部争当改革促进派,旨在用三个有利激发广大干部成为改革主体的积极性,用“三个有利”凝聚改革最大共识。大局意识和把握复杂局面的能力是党员干部尤其需要具备的核心理念和关键能力。在“四个全面”的时代,面对广大群众越来越热切的期望,如何在工作中贯彻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多地分享改革成果的正确利益观,成为对党员干部政治正确的直接考验。党员干部必须立足于大局,直面问题,在处理各个利益的矛盾中,自觉以正确的利益观对待利益关系调整,正确看待利益调整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的考验。改革的攻坚性和艰巨性意味着凝聚力量、达成共识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二)“改革促进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真正生力军
对于当下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就其合目的角度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要“符合最广大群众利益的新方法新举措,替代原有束缚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合理条条框框,调整旧有的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让改革红利惠及最广大的群众。”[9]这个提法既是唯物史观中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观点的当下阐释,也说明了党深化改革的价值诉求。价值诉求是实践不容忽视的维度,党所领导的深化改革实践绝非“怎么都行”,绝不应该忽视“为了谁”这个问题。“最广大群众”作为辛苦劳动者应该成为改革的收益者,这是实践辩证法的价值诉求,体现了改革实践的合目的。这说明利益调整的新目标是要让之前改革开放已经取得的成果惠及最广大的群众,而不能被贪腐分子和利益集团所操纵,因为后者已经在实际地削弱党执政的群众根基,这一点早就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重拳出击、严惩腐败表明党“从严治党”,清除自身病菌,恢复健康有机体的决心和能力。
除了要明确“为了谁”这个前提性问题,也需要格外重视“依靠谁”的问题。而毋庸回避的是,党内确实存在一批为了功名利禄等私人利益而从事“伪实践”的人。这些人只是在组织上入党,却并没有在思想上真正成为一个共产党,而是仍然秉持一种以个人私欲、家族私欲、集团私欲的满足为标准的庸俗的价值观。这些人不仅不能更好地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而且还有意无意地腐蚀党的有机体,危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这些“伪实践者”不仅不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生力军,而且是阻力,是对党和国家政权具有非常大危害的蛀虫,是必须加以惩戒的对象。
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积聚了有志于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更加繁荣,将中国建设得更加美好的有志之士,这些就是优秀的党员,是中国的“改革促进派”。 习近平提出,“要着力强化敢于担当、攻坚克难的用人导向,把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激励干部勇挑重担。”[4]习近平的“重用改革促进派”的说法,提出了一种新的干部任用标准,以此为激励,很多致力于深化改革的有为青年干部的“热血”更加沸腾。要想成为“改革促进派”,首先要有“想改革”的价值取向,自觉地在价值上认同包括深化改革在内的“四个全面”的大政方略。但是只有“想改革”的价值诉求还不行,还需要有“谋改革”和“善改革”的能力,这种能力要求是对“改革促进派”的理论能力和工作经验、洞察力与执行力、创新力与协调力等处理复杂问题能力的综合能力要求。要想成为“改革促进派”,成为“四个全面”的实践生力军,除了在实践中具备学习能力、创造能力、执行能力之外,还需要强大的信念力量和心理素质。“改革促进派”必须在价值诉求和综合能力的双重标准下将自己锻造为践行“四个全面”的真正生力军,这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人才是“真正的实践”的践行者,是历史向前发展的真正的主体-客体。
(三)“三个有利”是衡量谁是“改革促进派”的新标尺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如何衡量何谓改革促进派、何谓改革阻力派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健康的有机体,但也难免存在老虎、苍蝇等有害成分,因此如何衡量谁是“改革促进派”就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亟待一个衡量标准。当小局影响了大局,局部影响了全局,改革影响到了个人、单位、领域、区域利益时,领导干部能否做到“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成了衡量干部的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三个有利”适时地找到了一个新标尺。当然这个标尺的具体刻度还需要在具体的改革实践中进一步具体化、细化,使之更加具有可量化、可操作性。
以“三个有利”为标准甄别是否“改革促进派”为识别和选拔干部确立了新标尺,同时在如何促进改革的具体问题和对策上为“改革促进派”发挥主体能动性留下空间,这就体现实践辩证法在主客体方面的辩证统一,体现了实践辩证法所内在的要求的发挥主体能动性与遵循客观规律的辩证统一,体现了主体实践活动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如何在“从严治党”中推进“四个全面”的总体设计,使得这项蓝图能否顺利实施,就有必要对党员干部的领导观进行重新审视。“三个有利”为“四个全面”的实施提出了主体标准,也为领导干部提出了开展工作的准绳。这个准绳有一个最低的要求,那就是无害加有利。
贪污腐败的蛀虫之类当然是不能姑息养奸的,但是对于“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温水煮青蛙式不作为的领导作风,也不能视而不见。任性的胡乱作为和懒惰的不作为,都与新的领导观背道而驰。如果说禁止任性作为体现了“从严治党”的最低底线,而摒弃“懒惰的不作为”的领导观显然也是“从严治党”的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而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提出“三个有利”正可以看作是对两种不恰当领导观的审视、批判和纠正。
“三个有利”一方面对于如何做改革促进派提出了正面标准,为愿意和勇于做改革促进派的同志提供了鼓励和支持,另一方面也为那些乱作为和不作为的党内存在问题的人员提出了警示。因此,“三个有利”是对“四个全面”中的主体因素即“从严治党”问题的进一步深化,也是推进“四个全面”过程中对干部进行评价的“标尺”。当然这个标尺的具体刻度目前还不是十分明晰,需要在具体的改革进程中具体细化、量化,让“改革促进派”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探寻具体可以操作的标准或许更符合实践辩证法的具体性原则,也可能取得更好的效果。无论如何,“三个有利”新标尺的提出已经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党干部的领导观提出了要求,体现了新的领导观的新要求。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和“三个有利”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梦”的“一体两翼”,共同体现了实践辩证法的总体性、具体性、以自否定促发展的主体性精神。作为一个自在自为的党,中国共产党必须要以“改革促进派”为生力军凝聚最大力量,进行一场改变现存不合理状态,全面改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真正的实践”。而“有机知识分子”应该致力于通过自己的理论力量倡导一种符合“三个有利”、争当“改革促进派”的新价值观,促进“真正的实践”由潜在变为现实。
参考文献〔〕
[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出版社,199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人民日报社评论部.“四个全面”学习读本[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4]习近平首提“三个有利”标准:把“改革促进派”用起来[EB/OL].http://news.china.com.
[5]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北京:商务出版社,1979.
[6]李斌.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习近平总书记再访西柏坡侧记[N].人民日报,2013-07-15.
[7]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欧和苏联学者卷)[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8]全面深化改革学习读本[C].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
[9]闫祥岭,杨绍功.用“三个有利于”凝聚改革最大共识[EB/OL].http://news.xinhuanet.com.
〔责任编辑韩芳〕
Viewing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ree Favorables”
And “Four Comprehensives” in Praxis Dialectic’s Perspective
ZHANG Hai-yan
(College of Philosophy,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21)
Abstract: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social practice to 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s, and make “China Dream” true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 is ought to be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and focus of Marxism Study to observe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ree Favorables” and “Four Comprehensives” provide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Praxis Dialectic’s ,which includes totality thinking, subjective spirit and the spirit of self-denial and development. Through that, we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to “Reform promoters”.
Key words:Four Comprehensives; Three Favorables; praxis dialectic; totality; subjectivity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869(2015)06-0084-07
作者简介:张海燕(1980-),女,山东曹县人,博士,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当代课题与形态研究”(13BZX006)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5-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