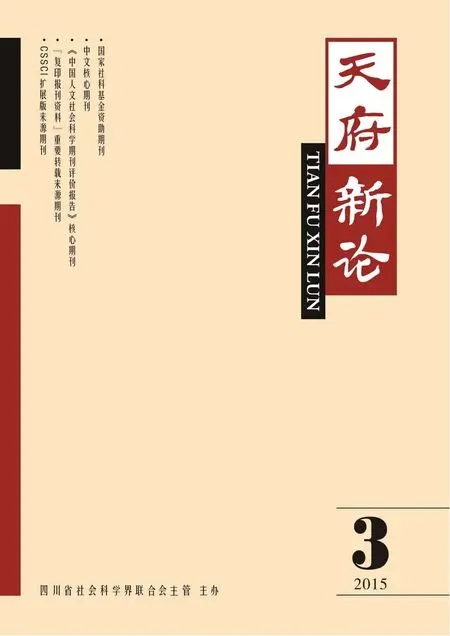数字艺术的创新美学本体论分析
谭力新
数字艺术的创新美学本体论分析
谭力新
[摘要]由于数字媒材对现今艺术文化的广泛影响,促一种新的美学理解形成。数字艺术的主题和主体,不必指涉审美主体的真实重视;数字艺术研究也不限于生活实际的生产文化价值。如何利用数字艺术的超联结社会网络扮演起个体之间的感情联系网络,进而创造出不断强化的共同体生命意志,不断扩大审美想象领地以及人性关怀共识,才是研究数字艺术创新方法的本体论的核心意义。
[关键词]数字艺术;美学;本体论;审美想象;审美主体
一、前言
在美学研究领域中,数字艺术的本体论一直是许多当代研究者探讨的重要问题。因为依循着本体拆解,彷佛可以从中得知数字艺术背后所隐藏的根本结构,进而找到驱动其创造的原初动力。但是,在这个问题的背后,却隐藏一个变动的危机意识。因为“本体论”( Ontology)暗中指涉了探讨艺术背后不可改变的意义。但艺术是否本身仍有西方美学源流如柏拉图以来所追究的本质追问,就成为理解这种本体研究的核心意涵。姑且不掉入这个美学的基本悖论,单就个别艺术类型的实质内容进行美学分析,想要了解当代新兴的数字艺术的本体论和美学创新特质为何,那我们就需要开辟一个具有时代新思维的美学方法视域,对这种方兴未艾的艺术类型,进行一种新的方法学实验,而其中的意图正是指向这种新的艺术审美感知理解方式之形成。
本文着重从哲学上对于观看与审美认知的不同论点,以几种历史演变的代表性思想为轴线并且描画出差异,藉此说明数字艺术的时代创新意涵何在。这种界定主要是以区隔、划分其中的差异为前提,指出数字艺术在以本体论为前题的美学设想下,如何从根本上解构并且终结了过去观看审美的静态假设,而引发关于美学本体如何在数字艺术时代得到新的启发和关注目标的思考。
二、数字艺术的历史美学语境分析
目前对数字艺术本体构成的定义中,要项包括了作品的生产,传播过程,它是指一个系统构成。〔1〕从定义之中,我们可以理解到数字艺术研究方法的特殊之处。首先,数字艺术很难用追溯历史源头的分析找出其本体根源。因为从一开始,数字艺术就是嫁接在别的原创艺术,如绘画和摄影的基石之上,而产生的复合艺术美学体质。再者,由于数字艺术的审美方法和历程也与过去的艺术门类差异甚大,对这种艺术不能进行传统意义上的审美判断。比如说,形式主义方法审美思维试图借着形象所做出的形式意图分析,这对数字艺术是一种失效的方法。在数字艺术的影响方面,它不是传统艺术所采取的传播策略,因为数字艺术中的观者意识显然不是过去传统的个人主体表征方式,这自然使数字艺术研究方法本身的特质得到强烈的彰显。
数字艺术的审美特殊性,必须要到它所身处的现代“观看”史观的语境脉络中比较,才能得到具体的呈现。在这里,笔者要提出两位对对现代影像的哲学背景最为深邃体察的哲人进行讨论。首先要提的是19世纪法国哲学家博格森( Henri Bergson),他在《材料与记忆》中表达了现代感知体现。他认为,吾人对于外在形象的理解与感知的主要模式,在于利用一种排除多余讯息的行为所产生的特殊意识,而这种感知意识,被以一种“隐喻”性质的摄影技术带出。①参见博格森在《材料与记忆》第一章的论述。Bergson,H.《材料与记忆》,肖聿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博格森所指的“隐喻”的摄影,其实是在说明我们对于一件事或一个物质的理解与记忆,必须是像照相机捕捉形象的瞬间一般,把视线外的景象排除掉,而只留下框里的形象供记忆之用。如此一来,博格森所做的知觉运行解释中,必不可缺少相机镜头这种性质的工具,只不过这个“相机”是一个隐喻的词汇,而不是实质的机械物件;而知觉、记忆的本体也必然是处于一种“虚拟”的情境。如果博格森的思想有助于我们理解数字艺术的表征美学方式,也是建立在这种虚拟的基础之上,因此不难看出,数字艺术的作品,往往有相当程度的虚构以及相对性特质。这也形成了数字艺术所描绘的对象,和以前对于再现对象与影像所赋予的“真实的摹本”的美学认知有极大差距。
其实,这种现代美学的视觉思维,同时也是数字美学的奠基磐石,它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对于西方主体的哲学建立。因为笛卡尔对于主客体的界分,是通过彼此的对立与相互确认过程产生,这使得西方视觉文化从此被框架进入了一个具有象征主体地位的固定视点之中。在这种观点中,观者所处的位置外在于客体对象,主体是与客体区隔开来的,观看者则是外在于景观的固定视点。〔2〕笛卡尔甚至质疑通过视觉所感知到的知觉基础,认为体验到的真实基础也具有相当程度的虚拟性。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这种模式的建立,从某种程度上同样促进了现代视觉体系的发展。这也就是说,借着主客体的划分,从本体论上看去,整个理性的主体意识被高举并且明确化起来。从此之后,借助一种视觉感知的体现过程,对象世界变得可以被规画与丈量,以及通过怀疑而进行合理的描述。当一个原先不能理解的世界,进一步变得可以通过理性技术来理解,甚至可以运用现代技术再造,这也就成为当前数字艺术的本体论证基础。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对这种世界观的存有状态之本体论提出根本的质疑。海德格尔在1938年的《世界图像的时代》一文中,将现代科学研究的特质诠释为一种将对象化实现于表象﹙Vor-stellen﹚的过程,这个过程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将真理转换为表象的确定性,因为这个确定同时意味了现代的本质,这也就是笛卡尔主义下的真理即是表象的确定。〔3〕正如同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思考一样,一旦客体对象能够通过一个表象再现,那它同时也被我们安置在一个体系之中,在“图像”之内,从而能被我们确认甚至解释。在这个顺理成章的现代理性思维中,形象的再制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而且,即使它的衍生变化能力极为强大,甚至像数字影像一样能够无限繁衍扩充,但是,我们依旧能够通过技术语言驾驭它。因此,海德格尔认为,当表象的机制成形之际,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对某物的具体掌握,这种掌握是一种无意义的理性暴力,它强化、合理化技术理性的行使权力,而任何违背它的思维框架,必定会招致一种排除,或者被理解为无意义的对象而予以否定。
回到数字艺术所产生的本体论基础来,数字艺术代表了任何形式的形象延展,因为从根本上,整个数字化的技术基础,也同样是一种表象化的世界观、世界图像体系的一个分支,数字的本体无非只是一个复制理论的前沿,它的本体论不可能具有变革性表述。尽管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图像在根本上并不是指一个具体的形象图像,他甚至认为这种世界图像在现代技术科学基础上完成,必然会出现问题。由于他们限定了存在的形而上可能性,妨碍了为讨论提供一种美学的视角,必然会使本体的意义受到限制,没有办法提供具有创造性的解释,这也会使我们对于数字艺术的创新本体定位产生极大的怀疑,所以,我们在此必须短暂暂停,改以现象学式的还原方法来看待数字艺术的本体意义。
三、数字艺术的现象本体分析
当我们生活在一个以技术指导文明的时空中,任何过去的事物,包括物质与精神层面,都会受到技术的影响,甚至遭到无情的抛弃。从这个视角审视审美与对象的关系,一些旧有的艺术物质现象,必然也会受到严苛的检视。作为以现象学美学为立足点的学者,保罗.考什尔( Paul Crowther)在试图回答并分析数字艺术的美学本体到底为何时,利用历史分析论证,认为艺术演变的内在逻辑主要是因为艺术表现结构无法应付内在新的经验感受所带来的变化结果。他强调,数字艺术并非是一种移植科技的结果,它具有源于艺术美学内在本体辩证的一贯性。它的特色在于认为,传统表现三维空间的绘画,在面对二维为主的抽象艺术时,已经明显无法应用旧有的语言构成体系,因此产生了在语用学层次上的空间链接变化和语意学层次上的三维再现的变革。在语用学方面,这种空间暗示由原先的透视投影移至利用形状、轮廓和色彩的暗示,而语意学则将强调体感的表述代换成利用线条来暗示轮廓的置换。如此一来,传统艺术的语法就被以“形─量”为轴心的语意语法取代。在这个发展条件下,数字艺术的创新就在于,一方面能结合新的形象再现语法,另一方面,能加入视觉书写和听觉材料形成特殊且独特的本体论意涵。他进一步把数字艺术的美学本体论放在计算机所产生的形象特质,以及对视觉再现表征认知的扩展来看待。他强调数字艺术中互动和进化的硬件和程序,以说明这种艺术的新领域,包括视觉再现和艺术创新的双向性结构,〔4〕并描述数字艺术所创造的可能新领域与其本体“氛围”。
数字艺术的形象本体必须借助投影频幕等与计算机链接,并且产生异于实质物质光学粒子的影像,它们的特质是透过数字化过程产生艺术品,而且能做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清晰细致。数字化影像和技术控制是其中最特别的策略之一。它们无论如何必须藉由计算机产生,而且因为技术的干涉,它与过去的艺术形式产生根本的差异。因为数字影像性格的高度“模拟”性,它具备了无论何时何地皆能呈现出与原初一样的图像,这种高度的复制能力,呈现出与手写和计算机打印字体差别般的本质差异。换言之,数字艺术的影像就如非手写打印出来的字体一样,具有高度的“非地点”( Nonlocal)的形象符号特质,藉以与传统艺术再现相区别。通过数字艺术所呈现出的地方场景,往往会使我们丧失独特的空间真实感受。数字影像形成像是一个数学程序般地不断变化、生成的过程,和传统影像如摄影不同的是,它可以无限次地介入窜改。而且,在介入以时间作为叙事结构后,情形就更为复杂。如果我们说它和电影时间叙事不同,那是因为传统时间叙事的先决条件是他们具备了一个原初的影像(如传统胶片)为其认知本体,而数字影像所涉及的大量复杂数字讯息,却是没有原初影像的。一旦被数字化,“影像”就和原先的影像脱离了。
另一个重要的本体差异事项则是所谓的“互动”视角,因为数字艺术必须采取一种动态行动的审美逻辑去理解其本体。想到互动性审美时,我们就不由会想到观看者的审美角色认知。在传统艺术如绘画、雕塑中,互动性是一种心理状态,审美对象并不会在观看者面前产生任何的实质物理变化。但在数字艺术中,观者原则上行动式参与了作品本身的生成,而非仅仅处于被动的观察,毕竟它是通过软件的中介操作完成。对于互动性而言,它是通过一连串的过程达成,互动发生在不同层次的内涵之中。首先是实际地点与虚拟地点的界面差异。其次是根据计算机接口的特性,互动产生于两方面,其一是观者有觉察的互动,另外则是根本不知道已经参与了互动;基于计算机本身仰仗接口作为浏览的互动设计,这是用户的超经验界面,造就参与者使用后被动参与到了影像程序所设计的互动之中。最后则是因为本身事前规划的计算机程序,它能够产生自身的进化,这样的过程让数字艺术中的时间意识具备强烈的创新美学意义。〔5〕
数字艺术开启了一个高度细致和复杂的表征三维空间的纯幻觉审美经验。数字艺术的本体创新是一个超真实的视觉审美经验,不像过去艺术建立在对现实的再现基础上,它是一种异变的再现系统,亦是一种超越现实因果律的创新关系。它能够创发一种另类的知觉和实境般的感受,使审美主体去体验环境,更能够启动想象力产生魔幻的美学,挑战“真实”在过去被赋予的视觉意识,进一步展延了再现与表征美学范式的创新方向。这意味了数字艺术是一种激进的创造美学,它也像是一个科学的“程序设计”,让艺术创造将空间工具化和结构化,想象出可视化的叙事结构,进而创发新的想象创新文化程序。
此外,回归人的本质,过去艺术的艺术主体在于艺术家,后人无法改变原初艺术作品的处境。但数字艺术的互动艺术特质,则将作品最终意义变为可改造的创新,可经由互动之中去产生千变万化的视角和审美格位,彻底改变视觉艺术的封闭结构。在诠释的角度上,过去的艺术作品常会因为经验论述者不同的立场而改变视角,但是,数字艺术所着重的“导航”( navigate)式过程,借助接口不断将原初意涵与参与者互动,进而避开改变原先固定主体视角的根本问题。〔6〕或许在这个意义上,导航所引导的叙事者可能比原创者来得更为重要。就像作曲者与演奏者的关系,这其中演奏者可能比原作曲者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对于“操作者”位置的拔升。而数字艺术尽管在原初创造意义上不如传统绘画等艺术能够彰显原创性,但就如前所说,对“操控”的强调正是数字艺术的本体意义之重点所在。
我们可以说,在美学本体意义上的作者神圣性,在数字艺术中被瓦解和改变。数字艺术作品可以是不同人在不同时段、地点在接口上集体参与完成。但是,在过去的艺术创作形式中或许也有如此的情况发生。举例而言,像是一张中国的绘画历经数个朝代经由不同人的题款标注,如此一来,也具备了集体性创作的实践,但是,这必定不同于数字艺术的连续性,因为它仍是可以辨识区分的。从此延伸来看,本雅明在论述《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时,就提出机械复制的作品(如摄影和印刷)和原创式的绘画相比,少了一种带有神秘独特的“光晕”。但是,在数字艺术的本位角度思考此问题,可以说本雅明的论点被瓦解了,真实的情况反而是复制放大和延展了原创,光晕并未随着机械复制而消失。数字艺术在不经传统意义的复制基础上,反而体现了神圣的原初性,这正是数字艺术所呈现的双重吊诡悖论。一方面,数字艺术无法展现如传统艺术的实存物体特质,但另一方面,数字艺术却又通过使用价值展现了每个使用观看者所能拥有之亲密的接触。由此可以看出,对数字艺术的本体分析,彰显了数字艺术的结构性视觉意义,它将视觉再现引入一个新的领域、新的本体结构。
如果重视数字艺术的审美主体问题,并且进一步把数字艺术视为一种艺术客体,那么,影响这种艺术的特质往往不在其自身的形式,而是在进行审美活动的观赏主体。因此,在这种研究视角下,数字艺术本质上不具有自身独立的艺术形式特征,这就应验了我们先前所说的使用过去美学研究方法的不可行,甚至会被误导到一个错误的轨道之上而无法返回正途。反之,如果强调的重点是审美主体性问题,但同时强调数字艺术的虚拟性、交互性特征,使得数字艺术进一步地营造了现实之外的另一个层次的“现实”,则它不仅是模拟的,更是拟真的,而且是比现实更加真实的超现实世界观。因为这种复杂的虚拟空间体验感,可以成为连接身体和实体空间关系的媒介,让身体在其中体验而非实际进入或消散于某个实体空间之中。〔7〕
四、结语
数字艺术的研究方法必然会建构数字艺术评价中美学的重点领域。当我们着重于利用区分数字艺术与其他类型艺术的本体差异来显示数字艺术的特质时,则采用了一种典型的相对主义立场。它可以很有条理、层次地利用美学原理的元素区别数字艺术和传统艺术差异,但是,却也有可能在区分的论述过程中,因为要做出区别而不得不对过去的艺术做出封闭式定义,这也就间接成为一种独断论的思维范式,掉入一种批评的循环里面。相对而言,如果避开前面的方法论陷阱,而采用开放性的论述风格,就有可能会使例证过于松散,而无法彰显出主题的系统性。总之,要想理解这种新领域的研究思维的核心意涵,并且就个别艺术类型的实质内容进行美学分析,当我们从不同面向,试着想要了解当代新兴的数字艺术的本体论和美学特质为何时,确实进入了一个具有时代新思维的美学本体论的创新方法视域,在进行一种新的方法学实验。事实上,对于数字艺术的研究途径,并非一定要采取比较法和主题式的研究方式。
基于这样一个共识,在最后的结论中,我们不妨将数字艺术的认识论拉回哲学中的美学感性认识传统,例如先前提及的博格森对于影像知觉的理解视域之中,通过他所强调的身体理解图像历程,即将生命意识中流变不定的图像集合,给予一种经过主体身体的投入,聚焦于单一形象的过程,作为理解数字艺术图像的前提。而数字媒体之异于先前艺术的地方,往往就在于将旧媒体的独立物质差异,经过高度技术化手段抹去,使得作为统整的审美主体得到充分的强调。所以,在比较方法上,问题的重点并不在新旧艺术的媒材差异,那是古典美学的思维意识。相反地,人的主体也就是身体的中心,反而成为应该关注的重点;并且,通过对身体的中心关注,将美学的研究从物质技术分析的基础移往人文认知精神层次的标注。
回到先前停滞的海德格尔问题之中,借着海德格尔向我们提示的希腊哲学中对存在的思考,替除以现代性深植于我们心里的表征系统化规范,把不可规范和算计的对象回复保存到真理的范畴中。〔8〕或许沿此脉络,数字艺术的主题和本体,当不必指涉及关注审美主体的真实重现;数字艺术研究也不限于生活实际的生产文化价值。数字艺术的文化产值重点还有一项未被充分开发,那就是如何利用数字艺术的超联结社会网络,积极地扮演起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感情联系网络,进而创造出不断强化的共同体生命意志,不断地扩大我们的审美想象领地,以及人性的关怀共识,这才是研究数字艺术创新方法的本体论的核心意义。
【参考文献】
〔1〕刘桂荣,谷鹏飞.数字艺术中的美学问题探究〔J〕.河北学刊,2008,( 8).
〔2〕Hubert Damisch.The Origin of Perspective,John Goodman trans.( Cambridge,Mass.: MIT Press,1994),xv.
〔3〕〔德〕海德格尔.图像时代的世界〔A〕.林中路〔C〕.孙周兴译.上海艺文出版社,2004.88.
〔4〕Crowther,Paul.“Ontology and Aesthetics of Digital Art.”Journal Of Aesthetics&Art Criticism 66,no.2 ( Spring2008 2008) : 162-3.
〔5〕Crowther,Paul.“Ontology and Aesthetics of Digital Art.”166.
〔6〕Crowther,Paul.“Ontology and Aesthetics of Digital Art.”167.
〔7〕Hansen,Mark.2004.New Philosophy for New Media.( Cambridge: MIT Press.) : 39-41.
〔8〕〔德〕海德格尔.图像时代的世界〔A〕.林中路〔C〕.孙周兴译.上海艺文出版社,2004.96-98.
(责任编辑:田府)
[作者简介]谭力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美学博士研究生,台湾玄奘大学艺术与创意学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美学﹐现代艺术。北京100872
[收稿日期]2015-01-20
[文章编号]1004-0633 ( 2015)03-116-4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B835; J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