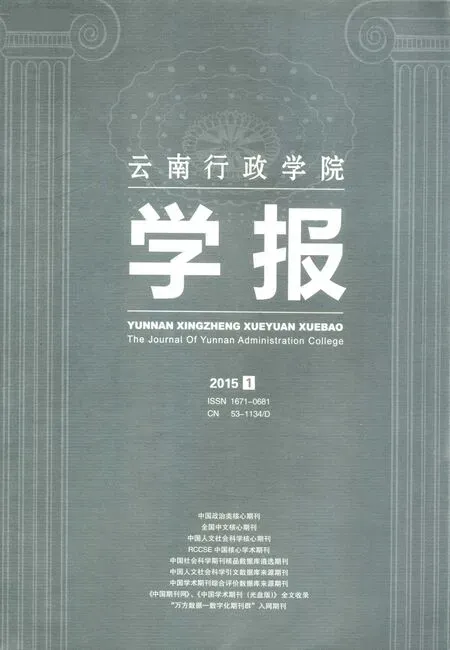西方民族主义:理论流派与政治主张
郑黔玉,张剑
西方民族主义:理论流派与政治主张
郑黔玉,张剑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贵州贵阳,55OO25)
民族主义历史源远流长。随着民族主义学说的发展,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发展日臻成熟,产生了不同流派的民族主义理论,而在学术界对其理论流派的研究亦不容小觑。概而论之,当代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流派可以分为:原生主义、永存主义、现代主义、族群-象征主义及后现代主义五大理论流派,上述民族主义理论来源于18至20世纪波路壮阔的民族运动与实践,涵盖了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大部分内容,梳理其流派对当下有着直接的借鉴作用。
民族主义;民族认同;派别;政治主张
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可以追溯至18世纪的启蒙时代,近来民族主义的复兴正在改变人们对正义、民主、身份、文化等相关问题的分析视角,并推动了政治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对其展开研究。美国历史学家卡尔顿·海斯曾经断言,对民族性和民族主义的属性和历史的完整且系统的研究,在任何语言中都不存在。随着对民族主义研究的深入,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影响力愈发突出,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和研究范式也映入了更多研究者的眼帘。然民族主义研究者们由于各自选择的角度或层面相异,考虑因素的主次差异,对民族主义现象和理论的分析也就可能得出各具特色的结论,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民族主义理论流派。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有关民族主义的研究汗牛充栋,而对民族主义理论流派的研究更是众说纷纭。概而论之,当代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流派主要可以分为:原生主义、永存主义、现代主义、族群-象征主义及后现代主义五大理论流派。从民族主义理论中可以衍生出三个基本理想:民族自治、民族统一和民族认同。在某些方面,各民族主义理论流派更为特定的目标就是建立在这三个理想之上的不同变量,而其中民族认同,可能最难以捉摸。一般而言,认同的概念表示社会成员对自己某种群体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并且是一种较长期的。但是民族认同的理想可以说是跨时间和文化的常量,因集体的特征和历史文化基础而与众不同,因此,民族认同始终是被每一代人重新解释和重新塑造的。这也是为什么对于各民族主义理论流派始终无法达成共识,彼此互相争论与批判,但是各民族主义理论流派在民族认同方面等问题也存有超出想象的密切关系。
一、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派别
原生主义被认为是当代西方最早形成的民族主义理论流派。该理论流派认为民族仅仅存在于自然秩序中,是自然形成的,而不是人为建构的;本质上是原生的,在时间上处于第一序位,并且是之后一切发展和演变过程的根源,具有的历史久远性,也就是说民族、民族主义与社会性和现代性之间是不相联系的。往往一个民族群体,彼此之间很容易从语言、外貌、信仰、习俗等方面辨认出他们是“一类人”,并因此产生认同感,而十分狂热的有机论民族主义者更甚要求真正的文化一致性以及民族的原生性。社会生物学的引入,使得原生主义理论流派认为生物进化的结果致使族群更加倾向于和那些与自己具有基因联系的群体相联系或结合,而为了识别自己的亲属,文化的象征逐渐作为民族认同的标记。范·登·伯格认为文化群体被视为一种广泛的血缘网络系统,而语言、宗教等文化象征则是被用来作为生物亲和力的标记。这也是为什么没有直接亲缘关系的人们会将并不相识的同族群体视为亲属,逐渐将人们之间的自然感情转移到了具有相同或相近文化象征的共同体之中,即使没有直接亲缘关系的人们也倾向将不相识的族群视为亲属。格尔茨也指出:“新兴国家的人民不是通过理性化社会的公民纽带连接在一起的,而是基于语言、习俗、种族、宗教以及其他既定的文化属性的原生纽带”。因此,原生主义对于民族认同是以对亲缘、种族和语言等与生俱来的以及具有持久力量和影响的依赖为基础的。
永存主义引入宏观历史的分析模式作为自己的基本方法,不视民族为自然的、有机的和原生的,认为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是现近的,也就是其认可民族具有一定的现代性;坚持民族始终存在于历史的每一个时期,同时民族主义有着长久的、持续不断的历史,许多民族的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其中,休·希顿-沃森论证了某些民族的前现代起源,记录了民族持久的生命力和民族的持续性。虽然受到进化论强调渐进主义因素的影响,民族的历史被证明存在间断和断裂,但是同时受到社会和文化的积累思想的促进以及群体等观念的支持,通过强调民族的共同的文化认同则可以相对化这一断裂。永存主义理论流派认为民族本身的理念具有普遍性,并且这样的理念可以适用于任何时期和地域的许多文化的政治共同体。勒南在《何谓民族?》这一演讲中认为,民族并不是永恒的东西,它们有其起始,也有其终结。但是总体的民族,作为人类共同体的范畴,则是永存的和无处不在的。因此,永存主义对于民族认同则主要体现在文化认同上,通过对持续不间断的文化进行积累,民族间从而达到相互认同,反之又论证了民族主义具有的永存性和持久性。而在新永存主义的解释中,民族认同的根源在于大众的情感和文化。
2O世纪6O年代,现代主义民族理论崛起,该理论流派认为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即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民族主义的发展也是现代化的产物。而且现代主义不仅认为民族主义是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是国家主权不可避免的伴随物;同时还认为民族主义不仅在时间顺序上是新近的,在本质上也是新的。虽然霍布斯鲍姆承认深刻的历史延续对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但是他认为在民族主义原型与近代民族主义之间,并没有一脉相承的关联,如果有的话,也一定是人为虚构出来的。盖尔纳也认为前现代不存在民族和民族主义,因此,现代主义理论流派在民族认同上的观念则从根本上不同于其他理论流派。安德森认为民族认同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之上的,民族是通过语言构想出来的政治共同体,同时否定了民族认同中的血缘因素;并且触及到了民族认同深刻的宗教基础问题。可以看出,在早先的农业社会,人们常常通过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制度结构而相互认同聚合在一起。而在现代社会,文化替代了这种结构,反之现代社会则以失去根基、非传统化的个人为基础,将语言和文化作为认同的唯一基础。现代主义民族理论流派的民族认同基础可以说是由于人们共同的价值观念所产生的认同以及对所享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产生的一种特定的政治认同。
到了2O世纪8O年代,族群-象征主义兴起,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永存主义民族理论和现代主义民族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并逐渐成为与现代主义民族理论相比肩的民族主义理论流派。族群-象征主义不否定民族主义是现代现象,并十分注重民族的历史性和族群性。安东尼·史密斯主张从民族历史的连续性来建构民族认同,认为“文化”和“认同”不必由现代制度来提供,我们也不必提出文化不能为后来的民族提供基础的先决条件。族群-象征主义认为民族得以形成的基础是根植于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族群,并且揭示了现代民族对今天产生影响的原因,正是民族的记忆、神话传说与象征符号等主观因素使得民族和族群获得了大众的情感认同。族群-象征主义强调象征符号对于族群研究的重要作用,认为族群的神话、记忆和象征符号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稳定的,民族起源的反神话和民族文化的不同记忆始终都存在,是一种“深层次”的体系和规范。史密斯指出,神话、记忆、价值和象征符号等是族群产生的必要条件,没有神话和记忆就没有认同、没有认同也就不存在族群。族群-象征主义将民族主义理解为一种集体行为类型,以道德群体的集体意志和拥有假设的同一祖先群体的共享情感为基础。因此,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流派认为现代民族是在前现代时期的集体文化认同语境中兴起的,并分享祖先和历史记忆的神话,以及拥有共同文化因素的、具有名称的人类大众群体。这一民族认同是一种注重民族认同的公众的、道德的和情感的维度的集体文化认同。
2O世纪8O年代后期,民族主义获得了新的推动力和力量,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进入民族主义的研究领域,后现代主义民族理论流派逐渐产生。通过后现代的视角和分析模式,后现代主义民族理论不断对其他的民族主义理论进行解构和批判,并在被忽视的领域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后现代主义民族理论是伴随着对民族情感逐渐稀薄化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不断消除化的“后民族”社会的想法,建立在不断地包容和侵蚀民族文化和认同世界主义全球文化正在兴起的论点基础之上的。正是大众消费主义的文化稀释了民族文化的差异以及新的数字革命和计算机信息技术的普及破坏了以前存在的文化,威廉·麦克尼尔提出在后民族时期不同族群与文化混合以及不同文化认同的杂交,产生的是一种能够克服所有文化壁垒的大众传播的和后现代的全球社会的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文化。霍米·巴巴认为,在这“多种文化的民族”中,历史和认同的感受变得分裂和重叠,民族也被碎片成为原先组成它的各个部分,而民族认同也随之变成“混合的”了。在后现代时期,那种小规模族群运动和其他的区域和地方的环境保护运动一起扩大,并都是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转向新的“认同政治”运动的一部分,包括女权运动和绿色和平运动等。因此,在后现代主义民族理论流派来看民族认同,则是将其视为在民族主义逐渐枯萎的现象中逐渐混合化和碎片化的。
二、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政治主张
任一理论流派都不可能包含民族主义所有的内涵,对民族主义做出尽善尽美的诠释。西方民族主义五大理论流派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民族主义给予的解释,而它们并不是试图全面论述民族主义。要比较完整地来理解民族主义,就必须参照、吸收其他民族主义理论流派中有价值的部分,并进行必要的分析与整合。
从分析的主客观因素来说,原生主义与现代主义在民族认同意识问题上的差异最为明显。原生主义强调民族及民族主义的客观性,将民族看做客观世界自然发展的结果,而人们在血缘、语言、习俗等方面的统一性则构成了民族的现实存在。对于原生主义来说,个人的民族属性是一种与自身民族群体及其文化之间自然的,与生俱来的,实质的联系,它是人类本身所具有的客观实在。而民族也具有一种天生的,通过代代相传得到的特性,是具有相同血缘、传统、生活习惯和心理特征的人类的共同体。因而原生主义民族理论流派所认为的民族认同也只能是通过相似个体之间的交流才能产生,而不是在社会联系的客观实际中产生。所以原生主义则自然较多强调了民族形成的一脉相承的血统联系和历史文化传统这一方面,将种族、血缘、语言、宗教及文化传统等视为特定民族认同的标识。原生主义理论流派看重民族的自然形式,强调民族的文化、血缘、地域、语言等属性,也当然是文化民族主义理论的延续。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主义民族理论流派则更多地禀承了政治民族主义理论的理念。现代主义民族理论主张把民族和民族主义完全归结为是近代社会出现的现象,实质上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社会学教授米切尔·赫克特认为这一时期的学者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依附理论的影响,指出民族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明显特质,从而对原生主义民族理论予以否定。在吉登斯看来,现代国家不同于传统国家,认为“民族主义”是个人在心理上从属于那些强调政治秩序中人们的共同性的符号和信仰。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主义是经过想象过程起源的,是特殊类型的文化人造物,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民族是情感和意志的群体,也是想象的和认识的群体,社会结构与文化根源则一起构成了民族认同的基础。这突出反映了现代主义比之原生主义注重民族认同中的政治文化性因素。汤姆·奈恩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大众化的,依靠大众的族群情感来维持,提出了精英们在民族认同中所具有的能量,这则反映出现代主义较之原生主义强调了社会经济因素在民族认同中的作用。因此,现代主义民族理论流派所论述的民族认同则完全不同于原生主义。代之原生主义忽视文化、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以及否定民族认同中的现代性因素所具有的潜在影响,现代主义民族理论流派的民族认同是一种特定的政治认同,并且是基于在社会经济、意识形态转变以及社会文化等作用下形成的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观念。
族群-象征主义是在永存主义和现代主义基础之上发展和继续的,因此,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对于民族认同的论述较之于永存主义民族理论有相近之处。休·希顿-沃森宣称,可以将“古老而持续的民族”与后来创造出来的民族区分开,认为它们的持久生命力为公众的民族不朽意识提供了历史证据。永存主义更认为如果不注重由这样的文化-政治形式所提供的地域和记忆,是无法解释后来出现的现代政治民族。而族群和政治的纽带及情感的长久历史即作为后来现代民族认同的基础。因此,永存主义对于民族认同则主要体现在大众的情感和文化认同上,通过对持续发展演进的文化进行积累和沉淀,民族之间从而达到相互认同。这一点族群-象征主义与之不谋而合,族群-象征主义也注重研究民族的历史性,民族的族群基础及其文化特征,尤其特别强调民族的重要历史地位和持久的生命力在民族认同中所具有的影响。史密斯认为,历史记忆对于认同非常重要,历史记忆不仅是形成个体特征的关键,同时也是形成民族这一集体的关键。但同时,族群-象征主义虽然注重前现代的族群联系和情感对于现代民族的影响,也注意到了前现代民族和现代民族之间存在着断裂,这对于民族认同的影响则是永存主义所忽视的。而且族群-象征主义所注重的神话、记忆、价值和传统等主观象征符号以及集体意志和感情在民族认同中的作用也不是永存主义民族理论所着重强调的因素。
此外,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的部分也是产生于他们对于现代主义民族理论流派的批判,这也是产生族群-象征主义与现代主义在民族认同问题意识上不同观点的地方。一方面,现代主义则主要强调现代性的重要,认为在民族主义民族认同中起着决定的作用的是一些现代性的因素。而族群-象征主义并不否认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现象,但同时更为强调民族的历史性与族群性。族群-象征主义考察象征、神话和记忆等因素在民族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民族的核心是有着历史文化基础的族群,民族和民族主义不是仅仅与现代性相连接的,而是集体认同及族群-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族群-象征主义比较注重对民族的形成过程进行长时段的历史分析。安东尼·史密斯认为,要真正了解民族和民族主义,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之为一种思想或政治形式,还要将之作为文化现象来对待,坚持主张现代民族与前现代族群之间的连续性。在史密斯看来现代民族主义基本还是一种“历史产物”。另一方面,与现代主义民族理论不同,族群-象征主义致力于理解民族和族群的内在世界,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十分强调神话、记忆、价值和传统等主观象征符号对民族认同的作用。史密斯指出,神话、记忆、价值和象征符号等是族群产生的必要条件,没有神话和记忆就没有认同、没有认同也就不存在族群。可以看出族群-象征主义本质上是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强调,是对现代主义民族理论流派的反叛。加之,族群-象征主义将更多地关注集中在民众的整体力量对民族认同的影响,认为现代主义具有缺乏关注集体意志和感情的特征。正如史密斯认为,知识分子和其他人要逐渐与传统的文化因素相黏附,将民族的群体感政治化,并且把那些传统重新解释成为民族认同所需要的深刻的文化资源。
至于后现代主义民族理论,主要是解构现代社会,瑞典隆德大学人类学教授奥瓦·勒夫格伦认为民族的想象不能只靠意识形态的建构来维持。①而其他民族主义流派主要是建构。因此,后现代主义对于民族认同的理念既有相似于其他民族理论的部分,亦有自己独特的理念。既然后现代主义是在前述各理论流派的基础上发展的,自然与其他理论流派有所共鸣。后现代主义民族理论与现代主义民族理论一样都十分强调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现代特性。正是由于现代性的因素,如计算机技术和大众传媒等稀释了文化差异,对民族认同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英国拉夫堡大学教授米歇尔·比利格指出民族主义并不是已有民族的一种周期性的情感,而是一种地方的、长期流行的状况。也就是说后现代民族主义者更加注意到媒体等手段对民族主义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是后现代主义民族理论的建构基础则是在包容和侵蚀民族文化和认同世界主义全球文化之上的。于是,在后现代主义民族理论流派来看民族认同,则是将其视为在民族主义逐渐枯萎的现象中逐渐混合化和碎片化的。通过后现代的视角和分析模式,后现代主义民族理论不断对其他的民族主义理论进行解构和批判,后现代主义对民族认同的主要论述也完全不用于其他民族主义理论。
小结
整体来看,现代主义和族群-象征主义代表着西方民族主义理论流派的主流。各理论流派虽各有千秋,但都存在争议、来自各界的批判以及各民族主义理论流派之间的争论。对原生主义的批判来自多个学科,由于其忽视了文化对人们行为乃至意识形态改造的巨大影响,原生主义无法对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新的民族认同做出合理解释,因此原生主义民族理论对民族认同观的论述被认为的静止的和片面的,缺乏理论解释力。现今已经含有固定不变、实在论和本能主义等轻蔑的涵义。永存主义也受到很多批评,认为其在许多方面夸大了古代的共同体与现代民族的相似性,没有考虑群体对于民族认同的内心感情和集体意志。现代主义民族理论也并非面面俱到,至臻至善,它的许多理念和结论也存在一定的偏颇,受到其他民族主义理论流派的批评与反驳。例如认为现代主义对认同的阐述主要表现在缺乏厚重历史、文化的元素。在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流派看来,现代主义理论过分强调了民族主义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权力等客观因素,而较少注重价值观、传统习惯和情感等主观元素的重要性;现代主义也割裂了它与前现代民族现象的联系,造成了民族主义的断裂,使得民族主义的发展与演进过程的不完整性。同样,族群-象征主义也同样没有逃脱批评,如有的学者认为,族群-象征主义忽视了政治机构对民族认同的作用,有的则批评族群-象征主义和永存主义民族理论过于接近。如约翰·布茹伊立就认为史密斯的理论把前现代的族群认同与现代的民族间的关系拉得太近了。相较于其他理论流派,后现代主义因发展时间短,理论发展不成熟,目前后现代主义民族理论只是将当代西方的民族主义研究进行了深化,尚待进一步的发展。史密斯认为后现代主义依然太分散和太粗略。但后现代主义仍在成长之中,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自身理论,以多视角及多深层次的分析民族主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并与世界热点问题有较多的联系,进而拓宽了民族主义研究的范围,为民族主义理论研究提供了更多理论依据,完善了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体系。
因为认同的存在相对恒定,认同的因素和表现不会随社会和民族的变化而有质的改变,但利益追求却处在不断变动之中,它会因社会和民族的发展择度不同而有着极不相同的内容。无论对各民族主义理论流派做出的批评有多么正确,各民族主义理论流派并没有完全失败。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流派研究迄今依然在延续,而所有的这些民族主义理论流派也还都在不断的充实和发展中,没有一个理论流派可以完全囊括民族主义所包含的所有成分,也并不存在一个研究民族主义的统一的理论体系,上述五大理论流派基本上反映了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研究的脉理。虽然五大理论流派对民族主义的分析不同,但他们之间并不是相互矛盾,也没有相互取代,而是并存、修正,补充和各自发展的关系,在民族主义的不断发展进程中逐渐得到扬弃,共同对民族主义提供了多元化阐释。诚如哈斯所说,民族主义是头大象,每个民族者只能摸到民族主义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随着各派理论的争辩与交流,各西方民族主义理论流派沿着“和而不同”的脉络对民族主义继续进行着探索与完善,相信学术界会对于民族主义这头“大象”有更加完整的认知,才能更好地来理解当代民族主义理论发展的最新状况,从而对当今世界的国家、民族问题有更好的认识与理解,探寻更好的解决方法。
[1]Carlton J.H.Hayes,Essay on Nationalism,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8.
[1]E.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
[2]J.Hutchinson and A.Smith(eds.),Nation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3][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胡宗泽,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6][英]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M].张明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OO2.
[7][英]盖尔纳.民族主义[M].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OO2.
[9][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OO5.
[1O][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M].叶江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OO6.
[11][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M].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OO6.
[13]闫伟杰.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研究流派述论[J].民族研究,2OO8,(4).
[14]叶江,沈惠平.民族主义:过去、现在和未来[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OO8,(1).
(责任编辑 刘强)
C95-O6
A
1671-0681(2015)01-0153-05
郑黔玉(1954-),江西玉山人,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剑(1987-),内蒙古呼伦贝尔人,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硕士研究生。
2O14-O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