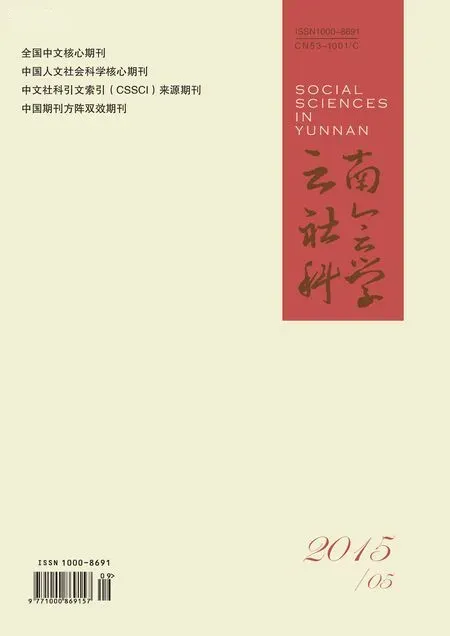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发展困境及突破路径
吴青荣
2014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收入是民生之源,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努力缩小收入差距,多渠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路径,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源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具体要求,也是实现“橄榄形”社会结构的转型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支撑点。研究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的现实困境和未来的路径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
经济学家倾向于采用收入指标来测度中等收入群体。居民收入是一项综合性指标。人们收入水平的高低往往取决于其就业能力和所从事的职业、所达到的文化程度和专业技能水平。反过来,一定的收入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又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投资行为、价值观念等。用收入指标来测度中等收入群体,不仅能够表征中等收入群体这一概念的内涵,客观地反映中等收入者的现实经济生活,也能够与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接轨。从国外的研究来看,Thurow选择收入中位数附近75%~125%区间内的群体为中等收入群体,测算出1967的美国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比重为28.2%。*参见Thurow,L.C.,“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middle class,”New York Times,February 5,1984.Blackburn和Bloom将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范围扩大到中位数附近60%~225%区间,结论是美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从1967的62.4%,下降到1983的55.9%。*参见Blackburn,M.& Bloom,D.,“What is happening to the middle class? ”Am.Demogr,7(1),1985,pp19-25.James E.Foster和Michael C.Wolfson分别测算了收入中位数附近75%~150%区间、75%~125%区间和 50%~150%区间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认为无论采用哪一个区间范围,加拿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从1981年到1987年有温和的增长,而在同一时期,美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却呈现萎缩现象。*参见James E.Foster & Michael C.Wolfson,“Polariz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the middle class:Canada and the U.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June,2010,Volume 8,Issue 2,pp247-273.Burkhauser等学者采用两种不同的收入区间来研究中等收入群体。狭义的中等收入群体是指贫困线两倍到五倍区间的收入群体。广义的中等收入群体的下限临界值是贫困线的75%,上限临界值是贫困线的五倍。*参见Burkhauser,R.V.,Crews,A.D.,Daly,M.C.,& Jenkins,S.P.,Income mobility and the middleclass,Washington D.C.:A.E.I.Press,1996.由于广义的中等收入群体包括部分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人群,因此该分类方法值得商榷。Joseph G.Eisenhauer提出,所谓中等收入群体是指既非穷人也非富人的群体。以家庭为例,P代表一定人口家庭的贫困线,Y代表家庭的总收入,W代表家庭的净资产,r代表实际税后利率。由此,穷人就是指Y 1.中等收入群体在稳定地成长,但比重偏低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结构比较单一,呈现的是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固化的社会结构。改革开放之后,经济体制的变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拓宽了社会流动渠道,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分化和重组,并孕育出中等收入群体。1978年的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激活了农民专业户、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在农村的蓬勃发展;1984年,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等纷纷在城镇建立或落户,中等收入群体开始萌芽。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在中国掀起了科技人员的“下海”热潮,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不断扩大。进入21世纪,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先后强调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中等收入群体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总体而言,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发展态势较好,但比重仍然偏低。据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测算,2010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仅为21.25%。 2.中等收入群体存在城乡和区域间的异质性 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565元,农村居民纯收入为7917元,城乡收入比为13.10:1;东部地区人均GDP为57722元,是中部地区的1.78倍和西部地区的1.84倍。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收入结构差异决定了中等收入群体存在城乡和区域空间发展的异质性。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对城乡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测算结果表明, 2010年城镇和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分别为36.78%和5.75%,城镇中等收入者人数是农村的6.4倍。*参见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实证分析和政策建议》,《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5期。常兴华等研究发现,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区域排序类似,我国城镇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也大致表现为由东部向西部递减的态势。*参见常兴华、李伟:《现阶段我国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构成和地区分布——以城镇居民为分析主体》,《中国物价》2013年第5期。 3.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观认同率偏低,群体陷入恐慌性焦虑 李培林等对“2006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观认同率只有41%,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中等收入群体主观认同比重(如联邦德国为62.5%,美国为60.7%),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群体主观认同率(如印度为57.5%,巴西为57.4)。*参见李培林、张翼:《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社会》2008年第2期。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工资性收入扣除高昂的房贷、车贷、孩子的补习费、教育费、医疗费等之后的可支配收入大幅减少。过重的生活负担压力使得中等收入群体的财富积累能力大幅下降,也使得部分中等收入者感觉到生活并不宽裕,认为自己被“伪中产”。 1.收入分配的困境 我国政府、企业和个人对利益关系失衡。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2012)对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格局的测算结果显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中,企业所得份额增长较快,政府次之,居民所得居最末; 再分配格局中,由于各种制度外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的快速增加使政府所得份额上升明显,企业所得次之,居民所得呈持续下降趋势。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为劳动报酬。2001年,劳动报酬占GDP 的比重为51.5%,此后逐年下跌,2007年达到最低值39.7%,此后又开始回升,2012为45.6%,劳动者报酬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发展和营业盈余的增长速度。*参见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12年第21期。 2.城镇化的困境 2013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3.7%,城镇常住人口为7.31亿人,其中流动人口为2.45亿人,因此,按城镇户籍人口核算,我国真正的城镇化率仅为35.7%左右,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城镇化的本质或核心是农村转移人口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转变为真正的城市居民。目前我国亟需解决的是农民工的城镇化问题。农民工城镇化的主要障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收入障碍。2011年,外出农民工月平均工资是城镇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58.83%, 2012年回落为58.76%。2013年外出农民工与雇主或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比例仅占41.3%。大部分农民工从事的是劳动条件艰苦、高强度、甚至有一定职业风险的工作岗位,与城镇同岗位就业人员相比,存在一定的同工不同酬以及较低的社会保障待遇现象。第二,制度障碍。从整个国家层面而言,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实质性的突破,但是户籍及附着在其上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系列权利仍然成为横在农民工和城镇居民之间的一道“隐形篱笆墙”,尤其是对于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而言,这道墙更是固若金汤,难以逾越。 3.创业的困境 创业活动是一个国家技术创新的驱动力和经济增长的活力源泉,而青年群体则是我国创业大军中最活跃的主体力量。调研数据显示,青年群体在创业中面临的最主要困境为创业资金短缺。其创业的启动资金主要来源于个人或家庭自有资金,部分来源于亲戚朋友的借款。很多青年并不知晓政府对创业的金融支持政策,或者即使知晓,对于具体的申请条件、申请细则、申请程序也是一头雾水。在具体的申请过程中,申请项目要求的门槛太高,申请程序繁琐,因缺乏有效的人脉资源而找不到合适的担保人,或者项目审批时间太长,这些因素都使得申请者望而却步,或中途放弃。此外,青年群体的创业能力不足也成为一大制约因素。青年群体具有较强的创业意识和创业热情,但由于缺乏创业经验,尤其是缺乏商业网路和人脉网络,容易在创业初始阶段陷入困境,步履维艰,甚至面临创业危机。 4.社会流动的障碍 从中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中分化的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长缓慢,其向上发展的空间狭窄,社会流动存在代内向上流动趋缓和代际流动的身份和职业的继承性。这种社会流动的不公平性和歧视性可以追源至基础教育阶段。我国基础教育存在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城市内部空间的异质性。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系列报告会”中指出,农村教育经费投入依然不足。2011年,农村普通小学生和中学生人均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支出与城市(含县城)相比,分别相差近700元和900元。在城市内,义务教育资源的分布也呈现空间的不均衡性,优质教育资源更多集中在重点学校。具备更高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家庭的孩子入读重点学校的机会显著高于来自较低资本的家庭尤其是弱势群体家庭的孩子。知识的累积性加重了由家庭背景所产生的教育不公平的后续延伸,一方面,孩子所获得的基础教育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在高中教育阶段、甚至高等教育阶段的教育机会的获得和学业成就的取得;另一方面,家庭背景在孩子职业获得中继续发挥一定的影响力。张翼通过对2008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以父母亲为表征的家庭背景不仅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教育获得,而且还影响了人们的阶层地位;教育和职业地位获得的双重不公平,使中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及其后代始终徘徊在教育、职业和社会经济地位的边缘位置,社会向上流动路径受阻。*参见张翼:《家庭背景影响了人们教育和社会阶层地位的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学报》2010年第4期。 1.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 在初次分配中,政府和企业分配份额的增加压低了劳动者的收入,致使我国消费低迷,内需不振。因此,在初次分配中应做到:第一,适当提高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的利润上缴比例,适当提高国有资本收益用于社会保障和民生改善项目的支出比例;第二,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探索国有企业红利的全民分红模式,让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全体公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能因国有资本增值而获得一定的财产性收入。第三,提高职工在企业中的劳动报酬占比,加强工会在劳资谈判中的主导作用,实现职工工资和福利水平与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的同步提高。第四,政府要加强对相关劳动法律实施的监督,对于违反劳动法律、侵犯职工利益的企业和人员要进行严厉惩处。同时,在再分配领域中应做到:一是政府要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方向,增加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民生项目支出,并向农村、中西部地区倾斜;二是深化税收体制改革。目前,我国工薪阶层税收占比超过50%,中低收入群体是个人所得税的主要承担者。要发挥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就必须尽快建立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税税制,完善对高收入者的个税征管。要加大对财产税的征收力度,适时开征赠与税与遗产税。 2.推动人口城镇化 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和企业用工成本的上升,处于企业关键技术岗位上的农民技工、熟练技工以及在城镇中艰苦打拼的农民工创业者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特长、勤奋、捕捉机会的能力和智慧成长为蓝领中等收入者。要推进农民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具体路径是:第一,政府不仅要积极推动农民工户籍身份的转化,更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保障农民工享有均等的社会保障权利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权利。第二,加强对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经费投入,积极开展对其城市融合能力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使其在城市安家立业的同时获得向上的职业拓展空间。第三,探索农民工的宅基地、土地承包权等资本要素的合理流转,让农民工能够获得土地权益财产收入。 3.提升青年的创业能力 李克强总理指出,“青年愿创业,社会才生机盎然;青年争创新,国家就朝气蓬勃。”激发青年群体的创造力和创业激情的路径有两条:一是政府完善既有的激励和帮扶青年群体创业和创新的制度体系,对于青年群体创立的小微企业尤其是创新型小微企业,要给予信息咨询服务、税收、财政、金融贷款和风险投资支持,帮助其顺利度过创业阵痛期。二是青年群体积极参加创业项目、创业技能和创业素质培训,以提升自身的创业意识能力、创业机会辨识能力、创业信息资源整合能力、团队合作协调能力、创业风险管理能力和创业抗挫折能力;还要多和创业专家和优秀企业家进行创业思想交流和相关商业合作,获取创业实践指导、创业经验传授、项目技术支持、业务人脉拓展等好处,成功企业家永不言败的乐观态度和勇于承担的精神会激励青年创业者勇于直面创业的艰辛,最终实现和企业的共同健康成长。 4.建立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 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就必须畅通社会的向上流通渠道,使更多的中低收入者享有公平的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通过自身的奋斗和学习改变命运,实现由下而上的流动。具体应做到:第一,贯彻落实教育公平的原则。一方面要推进城乡教育公平,改善贫困地区薄弱学校的教学设备和生活设施;优化农村地区的师资结构,建立农村中小学校长和教师的定期培训机制;大幅度提高农村教师的薪酬水平,吸引优秀人才留在农村。另一方面要推进城市地区的教育公平,加大对城区薄弱学校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平衡校际师资差异,建立强、弱学校的教师定期流动机制;优化城区学校布局结构,鼓励强校兼并弱校或跨区创办分校。第二,贯彻落实就业公平的原则。从制度层面上加强对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的招聘流程的监管,杜绝招聘腐败和近亲繁殖;消除各种招聘歧视和岗位歧视,确保劳动者有平等的就业权利和工作权利;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公共就业服务均等化和城乡一体化。 5.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 政府要从税收、社会保障等方面降低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支出。第一,降低企业的税负负担。2014年,由中国光大银行和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联合发布的《中小企业税收发展报告》指出,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较重,其中,新三板企业综合税负高达138.89%,创业板企业的综合税负由2007年的40%上升至2012年的71%。为了减低税负压力,企业会将大部分税负转嫁到产品价格上,最终由消费者来买单。因此,要稳定物价,尤其要稳定与人民生活戚戚相关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政府一方面应加大对已经出台的结构性减税政策的落实力度,扩大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成立专业的中介组织来为中小企业提供税收政策解读、税务咨询等优质服务,使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降低综合税负和税收遵从成本,最终降低经营成本和商品价格,让利于消费者。第二,完善住房社会保障体系,使中等收入群体“居者有其屋”。我国社会保障性住房的保障对象主要是城镇低收入群体,尤其是特困群体。因受支付能力限制而无法购置高价商品房的中等收入者被排斥在住房保障范围之外。为了解决中等收入群体的住房困境,一方面要放宽保障性住房的准入条件,各地政府可借鉴北京市即将出台的《基本住房保障条例(草案)》的积极做法,摒弃对受保障对象的户籍和收入限制,而以城镇常住居民的实际居住条件为基准,将中等收入群体纳入住房保障体系;另一方面,要构造健全的租房市场,对房地产中介行业加强监管,规范其服务质量,扩大其服务网点,提高租房居住条件,保护租房者的合法权益。第三,加大对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的后顾之忧。 6.中等收入群体应构建属于自己的生活形态 中等收入群体在收入增长有限的情况下,面对高昂的房贷、车贷、子女的教育费等,时常感到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从而终日惶惶不安。中等收入群体的这种焦虑既反映了其对自身经济地位的不满意,也折射了其在未能实现自己的消费预期时的心理失衡。要降低乃至消除中等收入群体的焦虑不安,一方面需要政府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和经济政策来“扩中”和“稳中”,另一方面要求中等收入者摒弃世俗的“中产阶级消费意识”,根据自己的实际收入水平合理选择生活形态,打造属于自己的生活模式。具体来说,第一,要改变执着的买房置业理念。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的房屋租售比远远超过国际上公认的1:300~1:200的合理标准,房地产市场价格虚高,存在严重泡沫。在此背景下,中等收入群体可以转变购房观念,理性地选择租房为自己减压。第二,抛开世俗的买车情结。在城市公共交通便捷的情况下,中等收入群体可以理性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或租车出行,由此省下的不菲购车款和汽车养护支出可以用于自我培训投资,以增强在职场中的竞争实力。第三,改变僵硬的教育理念。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一书中指出,“不管是学校还是补习班的老师,其社会经验值大都等于零,无法教导孩子人生的意义及生活方式”。“从小即被刻意栽培的人非常脆弱”,“并不适合未来时代的需求”。*大前研一:《M型社会》,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126-127页。年轻家长与其花费大量的金钱和时间在孩子的学业补习上,不如多花点精力和孩子进行心灵沟通,与孩子分享自己的社会经验和人生哲学,聆听孩子的思想,培养孩子直面困难的阳光性格,这样既能减轻年轻家长的经济负担,又有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二、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现状
三、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困境
四、中等收入群体的未来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