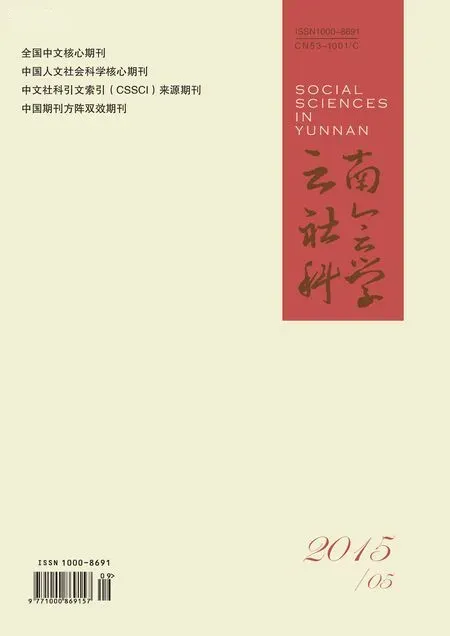传统孝道的近代化历程
李 怡 倪新兵
近世中国,门户大开,欧风美雨浸沐。面对西方列国的强劲冲击,中国传统文明被迫转型。中国传统社会由此拉开向近代转型的序幕,开启其近代化的历程。在这一前所未有的历史激变中,传统儒家文化发生了体系上的转移和整合,而作为儒学体系的基本内核的孝道,亦发生千年以来的首次根本性变异。这一变异过程当中,中、西、新、旧文化之间激烈冲突与融合,而孝道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力”的冲击,逐渐脱下传统的外衣,完成其近代化转型。本文拟以纵向的时间脉络为线,依次分启动、暂缓、加速以及完成四个阶段对传统孝道的近代化历程加以论述。
一
第一阶段,自19世纪40至60年代,是孝道初次受创和孝道近代化的启动阶段。
孝道自经过先秦儒家的重新整合,并完成与封建政权的连体之后,便逐渐形成一套相当完备的孝道伦理政治体系,渗透到封建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似乎还没有哪一种社会观念能像孝的观念那样,对人们的行为和心理具有如此牢固、持久和广泛的支配力、威慑力、约束力、感染力。它不仅从未被王朝的更迭所湮没,而且始终作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布衣平民的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共同竭力尊崇奉行的准则。”*李文海、刘仰东:《近代中国“孝”的观念的变化》,收录于《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13页。难怪有的学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文化可称为孝道文化。
正是因为孝道在中国传统社会有如此的地位,所以在鸦片战争以后的10年以内,还无法听到任何哪怕是十分微弱的触动孝道的呼声。西方基督教虽然凭借着战争以后的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在中国公开传教的权利,但是面对中国严密的孝道伦理体系,也显得束手无策。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西方凭借着武力一时都无法击破的孝道伦理体系,却受到了来自中国内部的冲击,而这次冲击又恰恰是打着基督教的旗帜,这便是与清王朝划江而治长达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之所以与传统的农民起义有所区别,正是因为它披上了西方基督教的外衣,从而使其充满了神秘感。这一问题曾引得诸多学者争论不休,笔者在此不想加入争论的行列,只想就其对孝道的冲击做客观的探讨。太平天国运动对传统孝道的直接冲击除了战乱导致的社会行为失范以外,无疑是在其统治区域内曾一度将孝道赖以存在的基础——家庭,加以摧毁。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崛起于偏僻的两广山区,但是却占据了中国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因此,其对孝道的冲击力可想而知。
但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勇敢叛逆行为表象的背后,并没有一种科学的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意识。他们摧毁家庭,不像后来维新者和革命者那般是站在追求自由、平等和民主立场上的。在思想意识还远未达到同等程度的时候,太平天国运动所实施的种种过激措施,必然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超出了当时人们现实生活的承受力,遭到江南民众的顽强抵抗。《金陵纪事》曰:“是时贼令男女分居,有同室者斩以徇。于是有室不能保,有家不敢归,坐此阖门殉节者甚多。”*胡恩燮:《患难一家言·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第335页。因此,太平天国所实施的极端措施很快就趋于崩溃,不得不恢复传统的生活模式。而且,在没有一种更为进步的理论意识作指导的情况下,他们不仅不能以更加科学文明和合乎实际的方式摆脱封建孝道的束缚,反而倒退到封建阵营里,甚至成为其最卖力的鼓吹手。太平天国运动虽然最后归于失败,其所实行的毁灭家庭的激烈措施也很快被取消,甚至到后来退回到传统孝道鼓吹者的角色,但我们却无法抹杀其在孝道近代化过程中的启动作用。正是有了太平天国的14年划江而治,才使得孝道遭到千年来的首次创伤,绑缚在人们身上的孝道枷锁开始稍稍有所放松。不仅如此,这场运动直接导致了汉族地主武装势力的崛起,而这些汉族地主势力又恰恰是随之而来的洋务运动的主导者,这便与以往封建社会地方势力的崛起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因此,在第一阶段中,对孝道产生冲击并启动孝道近代化进程的不是来自上层的知识界,而是来自基层的民众,同时由于这场运动的特殊性,又使得孝道近代化的启动带上了西方宗教的色彩。
二
第二阶段,自19世纪60至90年代,是孝道短暂休养和孝道近代化的暂缓阶段。
太平天国运动以后,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难得的相对平静的30年。这30年是近代中国第一次试图证明自己的时期,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展开,真正吹响了中国近代化的号角。但是,这场由当权者发起的运动,是以军事上的自强和实业上的求富为目标,虽然实业的兴办在客观上冲击了作为孝道经济基础的自然经济,但是从直接效果上看,遵循着“中体西用”原则的洋务运动对于传统孝道伦理不仅没有大的冲击,相反,却大有维护和加强的趋势。不仅曾国藩曾有“读尽天下书,无非是一个孝字”的言论,张之洞的《劝学篇》中更是不乏教人孝悌的内容。在洋务者们所兴办的各种军事学堂中,除去专业知识以外,孝道教育是不可缺少的根本部分。比如,严复14岁(1868)时,正值沈葆桢创办的马江船政学堂招生,他作应试文《大孝终身慕父母论》,得沈氏欣赏,以第一名录取。严复之所以能以此文获得第一名,我们从沈葆桢的奏折中可以窥探其原委:“每日常课外令读《圣谕广训》、《孝经》,兼习策论,以明义理。……盖欲习技艺,不能不藉聪明之士,而天下往往愚鲁者尚循规矩,聪明之士非范以中正必易入奇邪。今日之事,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沈文肃公政书》(卷4),转引自田汉云:《中国近代经学史》,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492页。《圣谕广训》是清政府宣扬孝道的思想纲领,而《孝经》则是孝道的主要教科书,它们的授受在当时各种洋务学堂都是必不可少的。由此可见,西方的技艺可以学习,而西方的伦理却唯恐避之不及,中体西用的思想逻辑彰显无遗,亦说明在洋务者的意识中还没有变革孝道伦理的初衷。
再来看这一时期作为中央政权清政府的态度。在经历了两次对外战争以及一次国内起义之后,清政府倍受惊吓,苦寻救世之法,一面有限制地放任洋务运动的开展,一面不断加强伦理纲常的宣传,试图在学习西方技艺的同时,以传统儒家救世之法来挽救颓势。因此,在这一阶段,孝道就成为清政府整顿世风、挽救人心的主要武器。在种种宣扬孝道的举措中,孝道旌表力度的加强无疑是最为显眼的。旌表制度大约在帝尧时期已经产生。秦汉以降,历朝历代大力推崇忠臣、孝子、顺孙、节妇以及累世同居等,朝廷一般会赐予匾额予以褒奖或者由朝廷拨银建坊。孝子、孝孙、孝女孝妇(一般受旌表妇女多节孝并称)的旌表在历朝旌表史上都占有相当的地位。清入关以后承继了汉族的旌表制度,对于孝子、孝妇亦是给予建坊旌表,但是一直比较谨慎,审查也非常严格。然而,在这30年间,清政府的孝道旌表力度却迅速加强,不仅旌表的人数增多,旌表的次数频繁,而且对于之前曾明令禁止的“愚孝”行为*“愚孝”一词,乃是近代学人在批判孝道时提出的,主要是指割股疗伤等极端行为。这种极端行为由于直接对身体产生伤害,因此顺治时期曾明令禁止:“割股或致伤生,卧冰(笔者按:二十四孝之一)或致冻死,恐民仿效,不准旌表。”(《清会典事例》(卷四○三),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501-502页。)康熙年间也曾予以禁止。当然,其后也有打破成例而给予旌表的例子,比如雍正六年(1728),“福建巡抚常赉奏称,罗源孝子李盛山割肝救其母病,母病愈后,李盛山伤重身故,请加旌表。部议以割肝乃小民轻生愚孝,向无旌表之例,应不准行。联念割肝疗疾,事虽不经,而其迫切救母之心,实属难得,深可怜悯,已加恩准其旌表矣。” (《清会典事例》(卷四○三),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505-506页。)但是,总体而言,对于这种极端行为,晚清以前是以不予旌表为主流原则的。,此时却是“一经大吏报闻,朝上疏,夕表闾矣。”*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96页。其迫切心情可见一斑。
由此,孝道在太平天国运动以后的30年间,基本没有受到大的外力冲击,而当权者对孝道的维护和宣扬也在一定程度上抚平了太平天国运动给孝道带来的创伤。因此,这一阶段是孝道获得短暂休养和孝道近代化的暂缓时期。言其暂缓,并非等同于停滞,因为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式学堂以及留学风潮的兴起,使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正在日渐成型,这无疑为即将到来的孝道近代化浪潮做了前期准备。
三
第三阶段,自19世纪90年代至清政府灭亡,是孝道遭受重创和孝道近代化的加速阶段。
洋务运动这场中国的第一次自强运动,在中日甲午海战这颗试金石面前将其褪去伪装后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救亡图存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而在同一个时代主题下却导演出不同的运动,既有知识界导演的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亦有起自下层的义和团运动,还有清政府一手操办的清末新政运动,这些运动对孝道或批判,或维护,但却共同促成了孝道近代化的加速。
甲午海战的失败让一些年轻的思想家开始对愈来愈泥足深陷的中国社会进行更加深刻的反省,而不仅仅困囿于学习西方坚船利炮的肤浅水平,他们开始对传统孝道伦理体系发起直接冲击,其中尤以康有为和谭嗣同为最。康有为的《大同书》就是一部向封建家族观念挑战的宣言书,他对封建家族的流弊进行深入剖析,在其《大同书》中还结合中国古代大同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勾勒出一幅带有空想色彩的未来大同世界,究其核心,乃是毁灭传统家族。只是由于康有为是站在一个对中国社会更为深刻剖析的基础上,因此他的毁灭家族与洪秀全的拆散家庭却又有天壤之别。相比于康有为温情脉脉的理想式大同世界,谭嗣同对孝道伦理的批判显得更为激烈。首先,他提出“父子,朋友也”的平等命题,认为“子为天之子,父亦为天之子,父非人所得而袭取也,平等也”。不仅如此,他还重新阐释庄子的“相忘为上,孝为次焉”的思想,提出“相忘则平等矣”,“非相忘者遂不有孝也。法尚当捨,何况非法?孝且不可,何况不孝哉?”*谭嗣同:《谭嗣同文选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86页。表现出十足的“孝固不足以言之”的思想逻辑。同时,他对孟子所提出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也进行了否定,他说:“中国百务不讲,无以善,无以教,独于嗣续,自长志以至弱幼,自都邑以至村僻,莫不视为绝重大事,急急矣图之,何其惑也?徒泯于体魄,而不知有灵魂,其愚而惑,势必至此。向使伊古以来,人人皆有嗣续,地球上早无容人之地矣,而何以为存耶?”*谭嗣同:《谭嗣同文选注》,第187页。谭嗣同正是从种种封建道德假象背后揭示了更多孝道伦理的实质,所以他才能提出“冲决网罗”的口号。
如果说维新思想家们是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对传统孝道大加批判的话,那么,义和团运动则是对以孝道伦理为核心的传统生活方式的维护,而其所反对的对象也恰恰是东来之外国人。义和团将中国的苦难一股脑归因于外国的入侵,因此对于外国的一切,不分良莠,一律加以反对和毁坏,这恰恰是对孝道伦理生活方式的维护。戊戌维新运动与义和团运动都是由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导演出来,只是前者的主体为少数新型知识分子,他们的着眼点是国家危亡大势,同时又身兼启蒙重任;而后者的主体为农民,他们的救亡却是来自于对外国的切身感受。立足点的不同,导致其所实施救亡的途径也不同。维新派试图通过学习西方以达到救亡目的,而义和团则是试图以维护传统来抵抗外来的危机。两者群体与救亡途径的不同,使得他们对于传统孝道的态度截然相反,前者予以猛烈抨击,后者则极力维护。由于维新运动的主要群体是少数新型知识分子,而且其存活时间相对较短,就其影响范围而言,始终徘徊在比较狭小的圈子里,因此对于传统孝道并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冲击。倒是义和团运动,因为其主要群体是农民,因此其影响范围比维新运动要大得多,因此,它的失败及随后签下的《辛丑条约》无疑宣告以孝道伦理为核心的封建传统最终被打开了缺口,也预言了这种传统的激烈表现模式不会再次出现。*笔者按:义和团运动的主体虽然是农民,这场自发的民间反洋教运动与中国北方地区的民间信仰如天理教、白莲教、八卦教、一贯道等有着直接的关联。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忽视,那就是义和团运动的兴起除此以外,儒家知识分子长期以来的鼓励、宣传乃至直接参与却又构成了义和团运动的精神助因。自传教士获得在中国传教的合法性以来(太平天国运动虽然也有一定的儒学与基督教冲突的成分,但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基督信仰冲击毕竟不是直接来自西方传教士,而且其纯粹性和正宗性也大打了折扣。),中国儒家知识分子就直接感受到了来自异质文化、信仰体系的威胁,为了捍卫自己的固有文化,他们宣扬反洋教就是反侵略,在民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民的社会生物链条中,他们与民众连成一气,共同对付基督教的文化入侵。从某种意义上说,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正是儒家知识分子这种长期舆论宣传、反教情绪的一种总爆发,也可以说是先有“文化上的义和团”,才会有“行动上的义和团”。同时,义和团运动也是中国传统为挽救其行将崩溃的生活模式所做出的最后一次、也是最为激烈的一次集体抗争。因此,其影响远非维新运动所能比拟。从此,西方文明的输入因再未遇到如此阻力而变得一路畅通,孝道所受到的冲击也就越来越大。因此,从政治意义上讲,孝道之所以能在步入20世纪以后被迅速摧毁,与义和团运动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借助义和团以对抗外国梦想的破灭,使得清政府不得不再次进行一场自救运动,以挽救行将崩塌的帝国,这便是清末新政。清末新政对于传统孝道极力维护,然而始料未及的是诸种举措在客观上对一直被奉若神明的孝道伦理体系产生致命冲击。科举制度的废止导致教育体制不得不实施最终的变革,教育的变革则培养了一大批新型的知识阶层,并且渐次瓦解了传统孝道教育最坚固的堡垒——私塾。
在这一阶段内,对孝道冲击最大的莫过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一举将维系几千年的封建君主制度推翻,这相当于在孝道的心脏捅了一刀。因为,传统孝道之所以能在封建社会久盛不衰,正是因为它与皇权连为一体,得到皇权的庇佑。因此,如果说晚清修律运动破除了孝道的刑罚保障,那么封建君主制度的崩溃,则是直接打掉了孝道赖以存在的政治和权力基础。只是在看到辛亥革命的直接效果的同时,也要看到在此之前革命派对孝道伦理所做的理论批判。
近代思潮,此起彼伏,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曾经一度领潮时代的维新思想,渐次成为过眼浪花,取而代之的则是以革命派思想家为主力的时代思想。如果说维新时期对于孝道观念的再认识还仅仅存在于一两个人或者某一类先进知识分子群内的话,那么,进入20世纪以后,这个狭小的范围被突破并得以扩延。而且,相比维新思想家的学究气,革命派思想家更愿意用简明短促,犀利如刀的言辞去倡导孝道变革。他们将康、谭等人的星星之火,变为了燎原之势,毁家说成为风靡一时的思想潮流。“家之外无事业,家之外无思虑,家之外无交际,家之外无社会,家之外无日月,家之外无天地”*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第834页。,“家庭中之最愚谬者,更莫甚于崇拜祖宗”,*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978页。诸如此类,数不胜数。此时,《毁家论》《毁家谈》《祖宗革命》《三纲革命》《家庭革命说》《女子家庭革命说》等类文章,充斥于辛亥革命期间政论之中。毁家说的盛行,无疑是对传统孝道的一次巨大冲击。
这一阶段,短短20年,却是孝道连续遭受重创的时期,同时也是孝道近代化不断加速的时期。正是这一时期的一系列运动,使得孝道的保护圈被逐渐打破,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的精神内容被用来作为批判孝道的武器。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孝道批判是附属于封建家庭批判、封建专制批判的,对于孝道直接的、单独的批判并不多见,所见的往往是对三纲五常、封建家族制度的批判。因此,在这一阶段内孝道所受到的冲击政治性要高于思想文化性,其近代化也就更多地带有了政治色彩。
四
第四阶段,自民国建立至20世纪40年代,是孝道最后衰落和孝道近代化的完成阶段。
民国初建,破旧立新。新成立之“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打破传统、彰显共和的政策措施,废孔罢经、改革陋习等等,都对传统孝道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是,任何力量都是冲击性与反弹性并存。民国政府虽然对传统孝道给以冲击,然而这种冲击一旦碰上经过两千多年历史硬化的儒家文化阵营的坚韧壁垒,便会在思想文化界产生莫大的现实反弹性。随着袁世凯窃取共和果实的成功,一股尊孔读经的复古思潮渐次泛起。在民初尊孔读经复古思潮下,传统孝道也一度得到官方和不少思想家的维护。袁世凯就曾先后颁布《整饬伦常令》《褒扬条例》,与官方交相呼应的是,一批守旧学者趁着尊孔读经思潮的泛起,极力维护传统孝道,其中以孔教论者势力为最大。甚至有的孔教论者将《孝经》看作是中国的宗教,比如朱领中指出:“故我国古圣人的教是真能治国平天下的,而且顺乎人心,容易通行,不消权利压迫,但只要在上的人肯提倡耳。证诸历朝帝王,都以孝治天下,又证诸《论语》有子曰,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的话。又按《孟子》,谨序庠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的话。确定这《孝经》是中华的宗教,将来即是全球的宗教。……且欲知孔教之尊,又必人人诵读《孝经》始耳。”*朱领中演说,许止净编:《孝经白话解说》,国光印书局,1938年,第44-45页。
鉴于这种情况,中国的思想界意识到需要对传统给予更广、更深的冲击,方能真正改变中国。于是,一场最初以《新青年》为主力,后来扩展到整个思想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着民主与科学的旗帜,轰轰烈烈地在中国开展起来。此时转变社会伦理观念并没有游离民主与科学这两大主题,有时甚至就是它们的核心内容。只是,相对于戊戌和辛亥时期思想家略带空想的孝道批判,五四新文化时期的知识分子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高度上,批判更深刻,也更系统。由此,孝道的变革已经从毁家的空想中走出,开始步入一个更高层次理性的非孝时期。他们已经逐渐摆脱了变与不变的简单争论,而是深入到伦理道德的本质中,对孝道加以理论化探讨。
陈独秀从政治角度指出:“现代立宪国家,无论君主共和,皆有政党。其投身政党生活者,莫不发挥个人独立信仰之精神,各行其是,子不必同于父,妻不必同于夫”,*《五四运动文选》,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62页。认为旧道德体系的核心孝道观念已经不再适应现代生活。李大钊则从社会演变的角度指出狩猎时代“老人反以为自己的儿子所食为福,儿子亦以食其亲为孝”,到了畜牧时代、农业时代则“衣食的资料渐渐富裕,敬老的事渐视为重要”,*李大钊:《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65页。这显然受到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实际上否定了孝道在中国历史上长久以来被赋予的神圣意义,称得上中国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孝道进行分析的思想家,实为难能可贵。
陈独秀、李大钊等《新青年》作者群,虽然对孝道进行了批判,对于孝道观念的转变也做出了相当贡献,但是,查其文,观其言,他们关于孝道的论述,仅仅是他们所思考许多宏观问题的一个侧面,往往是将其置于家庭、伦理、政治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而依然没有直接对孝道问题做出系统的论述。在他们批判传统孝道的基础上,大约五四前后,思想界涌现一股“非孝”思潮,甚至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事件,其影响可谓至深至远。
1919年,对于中国传统孝道而言,是一个噩梦般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以后,孝道就真正开始迅速衰落而无可挽回了。吴虞写下《说孝》、胡适发表《我的儿子》、鲁迅写出《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矛头直指传统孝道。吴虞对儒家孝道的批驳比较多,然查其所论,皆不出《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与《说孝》两篇文章之范围。首先,他对孝的含义做出了重新分析。他认为孝有两种含义,即孝之本初之义与儒家所讲之义。孝的本初之义,他认为是感恩,是子女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他在《说孝》中说:“孝字最初的意义,是属于感恩。”*《吴虞文录(卷上)》,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2页。对于孝之本初之义及孝养父母的内容,吴虞是表示认同的,认为其符合人性,具有合理性。其次,他对儒家孝道学说展开猛烈抨击,认为儒家孝道学说是家族和君主专制的理论根据,其最根本的精神是维护专制和不平等。再次,他还分析了孝与忠的关系。他指出孝与忠一气相连,忠建立在孝之基础上,忠是孝的直接推行,也是孝的最终实践。基于以上分析,吴虞对封建孝道的危害大概总结了以下几条:(1)孝道学说造成了纳妾、溺女等社会陋习的盛行;(2)造成了重男轻女观念的产生和婚姻不自由的悲剧;(3)导致杀子、割体等悖于人道的愚孝行为的产生;(4)造成了人格的虚伪;(5)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他对孝道的分析和批判应该说已经达到了一个很系统、很深刻的水平,已经将孝道的本质揭露出来。
相比于《新青年》时期而言,此时孝道已经跳出家庭的附属而成为思想家们专门研究的对象了。然而,1919年还不止如此。这一年最引人瞩目者则属浙江一师风潮,该校学生施存统在《浙江新潮》发表《非孝》一文。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发表,是因为当时浙江一师是新思潮盛行的学校。它就像一篇战斗檄文一样引发了这样一场事件,究其原因,实是新旧之间积怨很深、很久的总爆发。正是在这次事件尔后,“非孝“思潮才产生了其社会效应。非孝,几乎成为每一个新时代青年所追求的目标和践行的准则。
如果说传统孝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所受到的冲击是政治性的,那么这一时期其所受到的批判却是文化性的,是思想家们在对中西文化进行对比以后所做出的抉择。他们不仅对孝道的封建性给以系统的批判,更为重要的是真正将西方孝道生活理念嵌入到中国孝道中,从而使孝道得到升华。只是,五四时期思想家所采用的仍大多是简单的中西是非二分模式,因此难免取代性高于融合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知识界出现两个不同的思想理路,一支承继五四精神,并成功寻找到马克思主义,从而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另一支则在纯学术理路上更深入地融合中西之学,致力于重建传统儒学。前者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尤其是土地革命,将传统孝道在广大农村的封建残余扫荡殆尽;后者则使传统孝道获得了新生,如果说前者是批判,后者则是维护*关于现代新儒家的孝道维护和重建,读者可参读肖群忠的《论现代新儒家对孝道的弘扬发展》,《齐鲁学刊》2000年第4期。,两者对孝道的近代化有着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意义,孰轻孰重,难分伯仲。
这一阶段,孝道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批判,受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洗礼,最终衰落下去,即使蒋介石在形式统一全国后再怎么试图恢复传统孝道伦理,也是无济于事,孝道衰落的结局已经无法避免,反而是现代新儒家更为理智一些,虽然也是对孝道的维护,但却没有蒋介石法西斯集团的独裁目的,因此也就能从文化的角度对孝道做出客观的评析,又借助西方文化对其进行重新整合,从而使孝道得到升华,孝道近代化也得以最终完成。
传统孝道自与封建制度结合以后,一直处于发展上升中,大约到宋明时期达到顶峰,其后便开始有所下滑,只是这种下滑在没有受到先进异质文明冲击之前,仅仅局限在其自身惰性的范畴之内,并没有结构性瓦解的危险。但是,步入近代以后,西方文明的强行输入,使得传统孝道遭遇了千年来未曾遭遇的巨大冲击,并使原先的惰性下滑转变成为结构性变异。孝道的衰落和结构性变异过程,也就是其逐渐摆脱封建等级政治控制,剔除封建等级压迫内容,向原始孝道还原的过程。只是,这个如剥竹笋般的还原,却不等同于简单的复古,而是逐渐被赋予了近代文明的内涵,因此是升华性的还原。传统孝道经过千年的封建渲染,日渐成为关涉封建社会方方面面的伦理基础,一切违背礼教伦常的行为都可以被冠以不孝的罪名;近代110年的冲刷,逐渐将其身上的封建政治性、压迫性内容洗涤殆尽,使其变得如本初般纯粹和简单,重新成为人间道德的一维,同时又被赋予西方自由、平等的内涵,成为“爱”的一种表达。如果说封建社会的孝道是以孝为中心,不断向四周辐射和推衍的过程的话,那么,近代以来,孝道所经历的正是由四周不断向孝中心收缩和升华性还原的过程。因而,孝道于近代中国衰落的过程正是它发生近代转型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恰恰是近代中国历次社会运动所伴随和导演的。同时,孝道的近代遭遇正是儒学近代命运的缩影,孝道近代化只是儒学近代化的组成部分。
在近代110年的孝道还原中,由于孝道与封建制度连为一体的特性,人们在长期的反封建斗争中,逐渐形成一种封建的即是糟粕、即是愚昧落后的思想逻辑,因此,孝道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是被视为文化糟粕,在学术界孝道问题也是无人敢涉足的禁区之一。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多少年来的斗争,斗来斗去却将自己斗成了文化的沙漠。正是因为如此,当下中国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几乎完全颠倒过来,这恐怕也不是近代思想家们想看到的景象。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面临着来自全球各种价值观的挑战,如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保持我们民族的文化特色,成为当前国人关注的焦点。“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无疑是给国人一个传统文化复兴的讯号。孝道,作为儒学的内核,如何发挥其现代价值,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当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儒学自身优势促进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更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