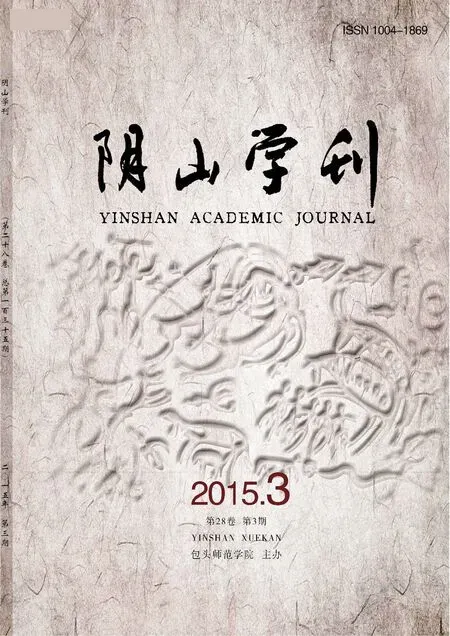论新故事的叙事模式
——以《故事会》为例*
马 圆 圆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论新故事的叙事模式
——以《故事会》为例*
马 圆 圆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20世纪60年代“新故事”应社会主义运动而生。它由口头文学演化而来,与时代、社会紧密相连,其叙事模式一方面承袭中国民间文学传统,另一方面充分吸收现代小说写作技巧及时代特征,使文学在新时期呈现出新特征。《故事会》作为新故事发展传播的主要阵地,其作品具有毋庸置疑的典型性。
新故事;叙事模式;《故事会》
故事伴随着人类的语言而发展,是我们最自然的叙事方式,可以说只要人能说话,这种文化就有存在的基础。鲁迅在论及小说的起源时谈到:“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1](P194~195)事实上,这也可看作故事的起源。1962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讲革命故事活动风起云涌。《故事会》是这一运动的直接产物,以革命传奇与农村叙事为主要内容的《故事会》故事立即席卷全国。讲革命故事的运动受到姚文元的极力推崇,他先后撰写两篇文章《创作更多优秀的革命故事》和《向革命故事学习》,将“革命故事”形象地称为“新故事”——“新故事”(此名称不准确,为与民间故事相区别,姑妄称之)由此而来。由于不受场地、语言、形式等限制,新故事以通俗灵活、丰富多样的特点迅速在全国蔓延。但这里的“新”与当时的“新秧歌”、“新歌剧”分享同一个“新”的范畴,即以政治意识形态为唯一导向。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四人帮”退出历史舞台,新故事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下,走入市场,逐渐放弃革命血统,继承民间文学叙事方式,同时吸纳现代小说叙事技巧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力求新奇、趣味和娱乐的通俗文学。上世纪80年代后,新故事以完全市场化的通俗文学刊物《故事会》为依托,逐步成为以受众为导向的文学形式,经过近30年的发展,其叙事模式渐得成熟。
一
新故事大多采用传统民间文学第三人称客观叙述,也称全知叙述,这一模式也为现代小说广泛使用。这种无限制深入任何人物活动,对任何人物的感情、思想、细微的意识了如指掌的叙述模式无疑顺应了通俗大众的阅读习惯。故事开始就对人物、地点等信息一一交代:“在江南沿海有一个小镇,镇上有爿滨海理发店,店里有位3号理发员,叫江海,二十五六岁的年纪。小伙子心灵手巧,待人和气、热情,所以很受镇上群众的欢迎。”[2](P12~17)。叙述者像上帝一样站在人物与故事之上观察着一切,全然知晓所有人物的所作所为与所思所想,他似乎是理发员江海,又似乎是顾客李二保,但又比故事人物甚至听众读者知道得更多:他一开始就知道县委江副书记与3号理发员江海同名同姓。因而赋予了这个普通的生活小故事以不平凡的丰富内涵:在这对同名同姓的人之间究竟会发生怎样离奇的故事?但叙述者又不满足于充当见证人静观事态,在贴近主人公理发员江海的同时又似乎是随李二保一起来供资股办事的亲密伙伴,目睹了胖股长在拿到理发员小江条子前后对李二保称呼从“唔,老头”到“老伯伯”、“您老人家……”的变化。这时的叙述者似乎是李二保,又似乎是胖股长,话语之间,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叙述者的强烈情感。然而随着情节发展的需要,叙述者又从人物身上跳了出来,以俯瞰者的姿态、权威的口吻告诉人们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下故事的结局:江副书记赞扬了冒名顶替自己写条子的理发员江海,胖股长顿时全身颤抖起来……[2](P17)胖股长前后态度、境遇的巨大差异构成鲜明对比,对其以权谋私的行为给予了辛辣的讽刺。
在全知型叙述模式下,叙述者既在人物内部(他洞悉人物的所有心理),又在人物外部(他区别于作品中的任何人物),其视点可以进行任意转移。有时叙述者与人物相重合,故事的一切都以聚焦人物为转移,《新女婿》一开始便将聚焦只身在香港的打工仔李亚民。美妙的琴声使他邂逅了住在对面的姑娘陈云娥。两人就这样你来我往,一步步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婚后的生活滋润而甜蜜,陈云娥母女对李亚民关怀备至,还为没有工作的他购买了人寿保险。在李亚民为陈云娥挑选结婚戒指的过程中,却“意外”在珠宝店丧命。[3](P22~25)通常当聚焦人物消失或死去之后,叙述也就中断。然而由于全知型的叙述模式无所不知,即使在主人公死后仍可继续对故事的后续进行描述,原来陈云娥母女是靠设计毒害单身打工仔获得大笔赔偿金的职业骗子。
除第三人称叙述外,第一人称视角体验也是新故事叙述的重要方式,它放弃文本在长于文字媒介揭示人物内心活动的优越性,具有很强的戏剧性,以不断产生悬念为重要目的适应以读者为导向的文学形式。例如《难忘的顾客》[4](P26~32)采用第一人称体验视角,叙述者知道这个故事“当时把我整得蛮恼火,事后一辈子也忘不了”,但在原文中,他放弃了目前的观察视角,改为从主人公当年体验事件的角度来聚焦。读者只能跟着“我”走,跟着当年还是新手的“我”一起在肉摊上卖肉,一起招徕形形色色的顾客,逐步发现那个让“我”难忘的顾客究竟是谁,这就造成了悬念,产生了较强的戏剧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故事的发生背景是粉碎“四人帮”的前夕,上世纪70年代末进入新历史时期人的视角随着环境的巨变而蕴含着他们独特的思维风格以及对“四人帮”的畏惧情感。然而,“视角”并非单纯的感知问题,因为感知往往能体现出特定的情感、立场和认知程度。这种视角将读者直接引入“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内心世界。“我”看着后面排着几十百把人的长队,业务不熟练再加上众口难调,规定:不将就个人需求,肥瘦全靠运气。这一视角直接生动、带有强烈的主观性,较易激发同情心和制造悬念。由于没有“我当时想”这类引导句,因而读者能够直接接触当“我”听到老头那句“这肉店是国家开来为人民服务的唦”时虽“冒火连天还是镇不住台子”,不觉对他上下打量一番:“上身穿一件褪了色的中式棉衣,下身穿制服棉裤”——“我还以为是啥大官儿呢!”。叙述语与人物想法之间不存在任何过渡,读者也便直接进入人物内心。但与第三人称叙述展示人物内心相比,第一人称体验视角中,读者仅能看到聚焦人物视野之内的事物,如此便容易产生悬念。读者脑海里难免出现一连串问号:这老头有怎样的社会背景?他手上抱着的中药是给谁的?他究竟从事什么职业以至于有如此娴熟的割肉技法?对于这些问题,读者不仅无法从聚焦人物的心理活动中找到答案,也难以从人物语言中找到任何线索。正是由于这些问号的存在和答案的不确定,读者需要积极投入阐释的过程,不断进行探索,以求形成较为合乎情理的阐释,从而在大众文化与社会体验相关性的基础上生产意义与快感。这种大众参与式的阅读是一种不受规范约束的行为,读者的在场感是所有片段中最强的,仿佛一切都正在眼前发生,选择的行为与过程恰恰使大众文化得以再生产。但此过程中读者与人物之间的情感距离却是最大的,这主要是因为人物对读者来说始终是个谜,读者作为猜谜的旁观者无法与人物认同。这种感情上的疏离恰恰与在“四人帮”当道的故事背景下人与人之间感情上的戒备与疏离相呼应,“我”与老头之间谜一样的关系也无疑增加了两人之间的距离,这对体现“四人帮”践踏财贸战线好作风、摧残青年的主题起了积极作用。
二
新故事采用线状叙事结构,通过强化口头性最大限度扩大受众群体,以达到易记、易讲、易传。这种结构少有旁枝叠叶,各情节组成部分按时间的自然顺序、事件的因果关系顺序连接起来,呈线状展开,由始而终,首尾相接,具有极强的生命力,符合人们自然记忆的习惯,契合了通俗大众的审美需求。实际生活中故事发生在一定的时空内,许多有关联的事件常常同时发生,但当人们用话语叙述故事时,故事的人物和时间就被投射到一条直线上,除按自然顺序外还通过倒叙、插叙与补叙等技法达到一定的美学目的,从而影响听众和读者的心理。广为流传的《彩蝶》就是其中一例:中年丧妻的华铁成与两个女儿相依为命,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与妩媚婀娜的赵爱娜一见钟情,但这个女人性格乖戾冷酷,以除掉华铁成的两个女儿作为他们结婚的条件。华铁成两度害女,终于小彩蝶为保护妹妹献出了年幼的生命。整篇故事以懂事的彩蝶姐妹俩盼新妈妈的到来为主线,以插叙手法从华铁成情绪波动引出他与赵爱娜情感发展,使整个故事脉络清晰明了,人物丰满生动。为突出并升华故事主题给读者以心灵的震撼,结尾的安排也别出心裁,它没有通过群众为孤苦无依的两个小姐妹捐款来触及华铁成灵魂,而以病床上的小蜓蜓声嘶力竭哭喊着“我要姐姐”达到艺术效果,使悲剧的净化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5](P2~9)从整体上来说,《彩蝶》按照时间顺序的连贯叙述,构成曲折丰富的故事情节,逐步深化矛盾冲突,层层递进,形成高潮。
新故事叙事结构同时呈现出一种潜隐的圆形,结局往往是大团圆式的,这与传统乐观主义民族心理,中庸和平的伦理道德以及轮回宿命的哲学观念等有关。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新历史时期,社会价值观念亟待重建,以民间文学面貌复刊的《故事会》所表现的对真善美的追求,以及对邪不胜正信念的坚守。《奇婚记》山坳大队胡会计以权谋取上海插队青年龚小弟钱财,为消除龚小弟家人对他巨额开支的疑虑,胡会计谎说龚在农村找到了对象并准备结婚。父母如何能见儿子根本不存在的女朋友,胡会计自作聪明让自己的女朋友王桂花以到大上海见世面为由冒充。[6](P5~11)整个故事以胡会计以权欺压龚小弟为主线,遵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观,按时间的自然顺序,胡机关算尽最终却换来鸡飞蛋打:女朋友王桂花认清了他的真实面目,与善良的龚小弟喜结连理,留他“天旋地转,眼冒金花,抱着电视机‘扑通’跌坐在地上”,对美丑的爱憎情感跃然纸上。类似《奇婚记》弘扬人性之美主题的新故事无疑打开了人们情感的闸门,宽慰了人们久被压抑、被践踏的内心与尊严。这种追求人与自然、宇宙、社会的和谐相融,在十年动乱结束后迎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下成为一种较之前更为强大的来自精神的力量召唤。在此背景下,反映新时期新人物新气象的故事就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紧贴时代,以实现国家“四个现代化”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有《陈大妈家的“怪事”》一证,陈大妈一家四口,女儿毕业做护士,但到谈婚论嫁的年纪却也不急,并且一改以往讲卫生、爱打扮的习惯,每天都“身上弄个稀脏,脚上是泥巴,衣服上是药浆浆,有时头发上还粘起了棉花毛毛”[7](P27~35),变成了“最不爱卫生的脏丫头”。老伴和儿子也一改以往不拘小节的生活习惯,反而都像个姑娘一样整天捧着镜子照。待到瓜熟蒂落,才知道三口人都在为早日实现“四化”而贡献力量,女儿忙着研制新药,老伴忙着革新技术,儿子对镜纠正嘴型,苦学外语。以再现一个小家在有限时空中的生活原貌折射出整个社会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欣欣向荣的景象,对真善美的笃信,坚信付出终会得到回报,读者阅读、观赏、倾听的过程,就是他们的心理期待不断兑现和落实的过程,以小窥大,从一朵小花看到国家未来的整片花园,显示出在人民努力下历史的发展趋向。
三
粗细结合、简捷明快是新故事叙述语言最突出的特点。如前所述,新时期以来的新故事是以受众为导向的文学体裁,其受众也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变的过程:即由创刊初“以农村故事员为主,兼顾工厂和其他方面”[8](P1)面向成人、面向基层到“还故事于民”[9](P25)面向比较成熟的中年人再到“年龄结构开始出现由中年向高龄和低龄两头辐射”[9](P78)几乎覆盖整个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社会群体,直至最后打开低幼儿童市场实现老少咸宜,其叙述语言无疑具有普遍性。《藏金记》老木匠王登山外出做工一年,挣得九百元,老伴建议盖房子,王登山“脑袋摇得像拨浪鼓,连连说‘不行!不行!’”。由于对“四人帮”心有余悸,老两口决定不动声色地把钱先藏起来,三卷钱分别藏三个不同地方。正当藏最后一卷时,儿子一声“桂英,你在阿爹房门口看啥”惊得王登山人仰马翻。钱还没来得及再藏,生产队长和社员不合时宜的又来了,只得顺手放在门口的稻谷袋里。人物语言不仅是观察他人的手段,更是揭示聚焦人物自己性格的窗口。被客人问及收入,王登山轻描淡写“除了生产队的,再抽支烟喝杯酒的,就差不多罗”。中国农民的那种含蓄谦虚的性格特点跃然纸上。谨小慎微的性格决定了当他听到“吃光用光,身体健康”、“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策常变化”这些话时不禁“头皮发麻,端着的酒杯象有千斤重”,但又暗暗庆幸没露富“有先见之明”,“没下雨我就进凉亭,看你还能淋湿我的脑袋”。当客人散了,才发现藏钱的麻袋也跟着不见了,两人顿时呆得像“一对菩萨”,好容易找到了麻袋翻了几遍却不见钱的影子,老两口浑身瘫软,“又成了一对菩萨”。往往越怕人知道的秘密,越容易在所有人都在场的时候被公之于众。最后队长找来警犬帮忙,看热闹的人更是挤满了王登山的小院。原想把钱藏在身上是万无一失之策,却一一被警犬找到,王登山两次哭丧着说“丢掉的是……另外三百块”,最后那丢失的三百块戏剧性的从碾米机里一张张飞出。[10](P1~7)《藏金记》的语言在新故事中是十分典型的:有叙述也有描写,运用白描手法,只讲了一件事:藏钱。粗线条勾画了两个核心人物:王登山夫妇,几乎没有任何对周围环境特点的描画,叙述性的语句约占三分之一,描述性的语句约占三分之二,其着眼点在用简练传神的笔法对人物行动和语言进行刻画,尤其是人物语言十分精彩。
新故事语言很大程度上承继了民间文学的叙述语式,尤其在通俗大众市场趣味性的导向下,对民间笑话加以发扬,运用夸张手法编织故事,勾画人物性格特征,较多使用歇后语、俗语等带有鲜明民间特征并渗透着叙述者强烈爱憎情感的语言,以突出故事的主题。富于喜剧性的语言,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契机,无论是对“丑的暴露”,还是“误会巧合”或“荒诞畸形”,都通过不协调来引起笑的爆发,此过程中读者不仅能“听其声而知其人”,亦能从三言两语中想象出人物的音容笑貌与性格特征从而引发自身对事件的认知看法。
通俗文学之所以为人们广泛接受,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的模式化,只有为大众所熟悉的模式才可能被大众青睐,“中国老百姓一向是要求有头有尾、布局周到的”[11]。新故事作为一种模式化的文学体裁,从未脱离这种传统的审美需求,“如何做人”是其唯一的主题,围绕这一主题要做到经久不衰其秘诀就在于情节与叙述模式之间的组合变换,就像一盒缤纷的七巧板,它的精彩在于变换的过程而非结果。
[1]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A].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张红兵.吃得开的理发员[J].故事会,1980,(3).
[3]伍庆琴.新女婿[J].故事会,1980,(6).
[4]吕红文,谭英权.难忘的顾客[J].故事会,1979,(1).
[5]陈希元.彩蝶[J].故事会,1984,(1).
[6]萧金.奇婚记[J].故事会,1980,(3).
[7]刘俊敏.陈大妈家的“怪事”[J].故事会,1979,(2).
[8]编者的话[J].故事会,1963,(1).
[9]沈国凡.解读故事会[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0]赵和松.藏金记[J].故事会,1981,(6).
[11]杨犁.争取小市民层的读者[N].文艺报,1951,(1).
〔责任编辑 韩 芳〕
On the Narrative Model of the New Stories:A Case Study onTheStories
MA Yuan-yuan
(School of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The new stories emerged with the socialist movement in 1960s. It evolved from the oral literature, and there had a close link with the age and society. The narrative model of the new stories, on one hand, inherited traditional Chinese folk literature, on the other hand, absorbed modern fiction writing techniqu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imes. It shows some new features in current era. Moreover, The Stories take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pread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ew stories.
new story; narrative model;TheStories
2015-03-25
马圆圆(1990-),女,山西忻州人,苏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研究。
I206.7
A
1004-1869(2015)03-003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