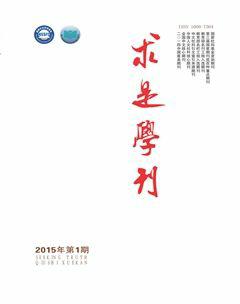《明孝宗实录》记载纠误及其在历史文献编纂学上的启示
摘 要:《明孝宗实录》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是研究明孝宗在位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然而其记载亦有人名、地名、时间、史实等方面的失误,以及史实漏载等不足,甚至有歪曲史实,刻意诋毁人物的现象,影响了其编纂质量。文章特选取其部分失误事例加以纠正,并予论列。以上失误现象从历史文献编纂学角度给后人留下了如下重要启示:编纂者具备严谨认真的写作态度,制定完善的凡例以及坚持秉笔直书的史德,是历史文献编纂成功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明孝宗实录》;失误;启示
作者简介:程彩萍,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明清史研究。
基金项目: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之子项目《明史》修订工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明实录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3&ZD090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1-0158-07
《明孝宗实录》(以下简称《孝录》)卷帙浩繁,所载内容丰富,是研究明孝宗在位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但其记载亦存在失误、失实、失详等不足,需要对其进行纠正、辨析与补充。本文兹对其以上不足进行初步探究,并由之从历史文献编纂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一、记载失误
1. 姓名记载错误。有些为姓氏错误。例如《孝录》卷七记载“致仕佥事张懋”[1](卷七,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巳,P137)。而本卷甲子条载御史姜洪推荐“佥事章懋”[2](卷七,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甲子,P151),《明宪宗实录》卷一百一十六载“升南京大理寺左评事章懋为福建按察司佥事”[2](卷一百一十六,成化九年五月壬辰,P2242),《孝录》卷五、卷十三、卷一百七十五皆记作“佥事章懋”。[1](卷五,成化二十三年十月戊子,P89;卷十三,弘治元年四月辛丑,P297;卷一百七十五,弘治十四年六月壬午,P3190)林俊为其所撰行状载:“枫山章先生讳懋……迁福建按察佥事……致仕以去。”[3](卷二十四《明文懿公枫山章先生行状》,P276)黄佐撰《南京礼部尚书章懋传》记载其“擢福建按察佥事……疏求谢事”[4](卷三十六,P720)。以上所引皆记其为“章懋”,可见《孝录》卷七记作“张懋”为误。《孝录》卷三十二记载弘治二年因剿除“回贼”功,赏赐镇巡等官,其中镇守太监记为“殴贤”[1](卷三十二,弘治二年十一月乙丑,P714)。而据《明宪宗实录》卷二百八十六记作“镇守陕西太监欧贤”[2](卷二百八十六,成化二十三年正月乙丑,P4839),《孝录》卷二十七记作“陕西守臣欧贤等”[1](卷二十七,弘治二年六月癸丑,P601),倪岳在奏疏中称“镇守陕西御马监太监欧贤题称”[5](卷十二《灾异二》,第1251册,P129),杨一清上疏时称“陕西镇巡等官太监欧贤等题”[6](卷四《为经略紧要地方边务事》,P124),余子俊论地方事时亦称“陕西镇守巡抚等官太监欧贤等所奏”[7](《本兵类·地方事》,史部第57册,P582)。故可判断“殴贤”当作“欧贤”。
有些为名字错误。如有冒充孝穆皇太后宗亲者,《孝录》中多处记其为“李文贵”,如其卷四十一记载:“况前日已误信李文贵等滥受官爵。”[1](卷四十一,弘治三年八月庚寅,P854)其卷五十一记载:“初李文贵之冒孝穆皇太后宗支。”[1](卷五十一,弘治四年五月戊寅,P1009)“李文贵等事败,所赐尽归之官。”[1] (卷五十一,弘治四年五月戊寅,P1010)而本书卷四十记作:“纪贵者亦本李姓,名父贵……改父贵为纪贵。”[1](卷四十,弘治三年七月乙丑,P835)王恕《议侍读曽彦久任隆治奏状》提及李父贵:“多不知土俗民风,如李父贵等冒认皇亲,而巡抚官与布政使、按察使俱因年浅不能周知。”[8](卷十二《议侍读曽彦久任隆治奏状》,P659)《弇山堂别集》卷九十三、《皇明从信录》卷二十四、《西园闻见录》卷一百一皆记载:“有李父贵者与其弟祖旺谋于田主邓璋……太监蔡用往访求无所得,里老遂妄举父贵兄弟以对。”[9](卷九十三《中官考四》,P1178)[10](卷二十四,P412)[11](卷一百一《内臣中》,P334)其兄弟二人之名,“父贵”、“祖旺”,恰相对应,由此可判断当为“李父贵”。
又如《孝录》卷七载“南京工科给事中章应玄”[1](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巳,P137),而本条下文记作“(章)玄应”,查《明宪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五记载:“授进士王盛、章玄应南京给事中。”[2](卷一百八十五,成化十四年十二月癸巳,P3318)同书卷二百○八、《孝录》卷十五及卷三十六、《国榷》卷四十一皆作“给事中章玄应”[2](卷二百○八,成化十六年冬十月丙辰,P3624)[1](卷十五,弘治元年六月庚子,P366)[12](卷四十一,弘治元年六月庚子,P2569)。此人后升参议,彭簪记载:“(弘治六年)湖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左参议章玄应致祭于南岳衡山之神。”[13](卷四《御祭南岳祝文》,P285)《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亦作“章玄应”。由此可见此人之名当作“章玄应”。
2. 地名记载错误,包括地域、地方机构名称错误等。如《孝录》卷四十二记载:“裁革……临邑、禹城、荏萍、郓城……十二县税课局大使各一员。”[1](卷四十二,弘治三年九月戊寅,P878)此处所记“荏萍”于其他文献中未见相同记载。查《明太宗实录》记作“茌平”:“革……东昌府之茌平、高唐,恩县、巢陵九递运所。”[14](卷一百三十二,永乐十年九月丙午,P1627)《明武宗实录》记载:“免山东德州……高唐、茌平、东阿……等州县正官朝觐。”[15](卷一百八十,正德十四年十一月癸巳,P3499)《明一统志》记有“茌平”:“茌平县在(东昌府)府城东北七十里。”[16](卷二十四,P563)《孝录》校勘记卷四十二同条记载之校勘记称“阁本‘荏萍作‘茌平”[17](P119)。由上可判断“荏萍”实应作“茌平”。
有些地名记载错乱。《孝录》卷五十二记载:“(六月)戊申广东广德州等处猺贼邓饭主等自成化间聚众二千余人,流劫州县。”[1](卷五十二,弘治四年六月戊申,P1025),而《全边略记》与《五边典则》记载:“六月广东德庆州等处猺贼邓饭主作乱。”[18](卷八,P474)[19](卷二十,P541)《国榷》卷四十二记载:“六月戊申广东德庆州猺贼平。”[12](卷四十二,弘治四年六月丙午,P2619)据李贤《明一统志》卷十七记载:“广德州东临湖州府,西至宁国府,直隶京师。”[16](卷十七,P385)可见其属于南直隶,而同书卷八十一记载德庆州属于广东肇庆府[16](卷八十一,P704)可见《孝录》此处所记误将广东之“德庆州”记作“广德州”。
3. 时间记载错误。有些为误记干支,如《孝录》卷四十二弘治三年九月第二页下第九行记载“南京刑部左侍郎阮勤乞致仕”之事发生的日期为“丁丑”,而据本卷上下文记载,此处“丁丑”前一日记为“乙卯”,此后一日记为“戊午”,显然“丁丑”当为“丁巳”,且《国榷》卷四十二将此事正记于“丁巳”。[12](卷四十二,弘治三年九月丁巳,P2607)故可判断应为“丁巳”。《孝录》此处所记有误。
《孝录》卷八记载“丙申岁暮享太庙”,又载:“(丙申)加吏部尚书王恕太子太保,恕上疏辞,上曰:‘吏部重任,朕特起卿用典铨衡以图治理,加升职事,卿不必辞。”[1](卷八,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丙申,P183)而本卷卷首记载“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丙寅朔”,下卷卷首记载“弘治元年正月丙申朔”,可见“丙申”当为弘治元年正月初一日,而上引《孝录》卷八却将“丙申”视为成化二十三年之岁暮,此当为误。按,《王端毅奏议》卷八记载丙申日王恕所上上引奏疏时称:“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具奏,次日奉圣旨:‘吏部重任,朕特起卿用典铨衡,以图治理,加升职事,卿不必辞。”[8](卷八《辞太子太保奏状》,P584)此记载说明王恕于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奏此疏,明孝宗于当年当月三十日给予批复。《孝录》卷八所记时间为明孝宗下旨时间,即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查《二十史朔闰表》可知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干支记日为“乙未”,由此可知,《孝录》此条所记“丙申”当为“乙未”之误。
4. 官职记载错误。其中有官员隶属机构记载有误者,《孝录》卷四十四记载:“升礼科左给事中孙圭为本科都给事中。”[1](卷四十四,弘治三年十月乙亥,P902)而据《孝录》卷十九记载孙圭在弘治元年十月,由礼科给事中升为户科左给事中。[1](卷十九,弘治元年十月丙午,P449)本书卷三十一、卷四十皆作“户科左给事中”[1](卷三十一,弘治二年十月辛亥,P709;卷四十,弘治三年七月乙丑,P836),《国榷》卷四十一记作“户科左给事中”[12](卷四十一,弘治二年十月辛亥,P2594),《孝录》卷七十三记载“孙圭由户科都给事中升为为右参政”[1](卷七十三,弘治六年三月癸巳,P1373)。由此可知,孙圭所任左给事中、都给事中皆在户科,而非礼科,《孝录》卷四十四记载有误。
《孝录》卷十四记载:“升太常寺右少卿李介为左少卿。”[1](卷十四,弘治元年五月戊寅,P343)王恕曾上疏建议此次任命,所记为“大理寺”:“十五日奉圣旨大理寺右少卿李介升本寺左少卿。”[8](卷八《调除官员奏状》,P607)据《明宪宗实录》卷二百九十记载:“升大理寺右寺丞李介本寺右少卿。”[2](卷二百九十,成化二十三年五月丙辰,P4905)《孝录》卷十四记载:“升大理寺左少卿李介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宣府。”[1](卷十四,弘治元年五月己丑,P354)《孝录》所载李介传记,记载其曾任“大理寺左右少卿”[1](卷一百三十三,弘治十一年正月戊戌,P2343),未曾在太常寺任职。故《孝录》卷十四记载有误,“太常寺”当为“大理寺”。
有官职“左、右”记载错误者。《孝录》卷七十五记载:“(弘治六年)都察院左都御史白昂应诏陈言。”[1](卷七十五,弘治六年五月乙酉,P1433)而《孝录》卷四十八、卷七十九皆作“右都御史”:“升刑部左侍郎白昂为都察院右都御史”,“升都察院右都御史白昂为刑部尚书。”[1](卷四十八,弘治四年二月乙丑,P968;卷79,弘治六年八月丙寅,P1511)白昂墓志铭记载其“辛亥(弘治四年)摄都察院事,遂擢右都御史”,且白昂未曾担任左都御史。[20](《文后稿》卷二十六《明故光禄大夫柱国太子太傅刑部尚书致仕赠特进太保谥康敏白公墓志铭》,P1280-1282)由此可知《孝录》卷七十五记载有误,应为“右都御史白昂”。
5. 史实记载错误。《孝录》卷六第四页下第八行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甲辰记载:“开设浙江湖州府孝丰县,割安吉县之九乡及长兴县之三乡隶之。”(同治)《长兴县志》卷一记载:“弘治元年分安吉之孝丰等九乡置孝丰县,割长兴南境□零、晏子、荆溪三区属焉。”[21](第196册,P165)三乡之属,不甚明确。而据程敏政记载当时分县之议:“割长兴之三乡隶安吉,则地之远近适宜。”[22](卷十七《浙江湖州府新置孝丰县记》,P288)(弘治)《湖州府志》卷一记载知府王珣奏疏:“将安吉县等九乡五十余里添设一县,就取彼处相应地名改称县号,照例选官置吏分符治理。其长兴县顺零、晏子、荆溪三乡割附安吉县就近管辖。”[23](卷一《沿革》,P81)(万历)《湖州府志》卷一记载:“知府王珣疏请长兴顺零等三乡附辖安吉,仍析安吉孝丰等九乡置孝丰县。”同书卷三《安吉县》记载:“弘治元年知府王珣奏割孝丰等九乡置孝丰县,复以长兴县荆溪、顺灵、晏子三乡割附安吉。”同卷《长兴县》记载:“弘治元年割县之荆溪、晏子、顺灵三郷以附安吉。”同卷《孝丰县》载“弘治元年始立为县,凡九乡共五十四里”[24](卷一《郡建》,P18;卷三《乡镇》,P60,P61,P63)。以上皆记载长兴县三乡割与安吉。同治《孝丰县志》卷一记载:“弘治元年知府王珣以安吉孝丰等九乡崎岖险远,民艰输役,奏请分县曰孝丰,以孝丰、天目、鱼池、灵奕、金石、广苕、浮玉、太平、移风九乡为所辖管。”[25](卷一《沿革》,P81)其所辖仅有原安吉县之九乡。正德二年议升安吉县为州,时孝丰县知县韩光表呈称:“臣照得该县地方原系安吉县所辖。”[24](卷一《郡建》,P19)亦未提及长兴县三乡。《大清一统志》记载:“晏子乡本属长兴,明宏(弘)治元年与荆溪、顺□二乡共割属州界。”[26](卷二百二十二《古迹》,P124)此处“属州”乃安吉州。故《孝录》卷六所记“割长兴县三乡隶孝丰县”有误。
二、歪曲史实
《孝录》所载内容大多精练准确,有些还附有编纂者对事件、人物的分析与评论,这有助于更深刻地了解其发生的原因背景及当事人相关信息。然而有些评论歪曲了事实真相,反而影响了《孝录》记载的准确度。
弘治元年,御马监左少监郭镛奏请预选女子于宫中,以备明孝宗选妃广衍储嗣,而谢迁上疏反对。由此,《孝录》评论此事称谢迁为谋私利,妨碍广衍储嗣之大事:
初郭镛请预选女子于宫中,或诸王馆读书习礼以待服阕之日册封二妃广衍储嗣,不为无见。而谢迁乃进此谀词献谄以误孝庙继嗣之不广,皆此邪谋启之也。比观正德改元,即立三宫,时迁适当国柄,略无一言,论及其奸鄙之迹甚明。盖以今日之立为是,迁实不能复肆昔之邪谋矣,且古者诸侯尚一娶三姓而备九女以广继嗣,况孝庙以万秉天子,独不得立三宫,可乎?小人图势利而不为国谋如此,识者恨之。[1](卷十一,弘治元年二月丁巳,P259)
此段激烈批判谢迁之言,实为诬陷。此时明孝宗即位不久,其后来继嗣不广与谢迁此言关系甚小。王世贞认为:“泌阳(焦芳)之忿笔盖阴刺中宫之擅夕而讥谢公之从臾也,殊不知上春秋甫十九,中宫仅踰年,何以有擅夕之声于外?而谢已逆知权之在中宫而从臾之,且谢以山陵未毕谅闇尚新为词,其义甚正,胡可非也。小人哉,泌阳其无心惮一至此。”[9](卷二十五《史乘考误》,P454)可见焦芳有借此发私忿之嫌,其此番论述不足信。
《孝录》在某些事件中对人物之分析有不合实际者,如弘治十一年授翰林庶吉士吴蕣为吏科给事中,戴铣为兵科给事中。《孝录》预述二人晚年结局:“二子晚年言事多矫枉过情,遂为国之厉阶,贻缙绅之祸,言官举动可不慎乎。”[1](卷一百四十四,弘治十一年闰十一月己巳,P2509)吴蕣因预知自己考核当黜,诬劾马文升以自救,所奏确有矫枉之处1,然戴铣则为正直敢言之人,且所言甚当。戴铣于正德朝对抗刘瑾,上疏请保留刘健、谢迁,嘉靖时御史王完曾奏请优恤戴铣:“正德间守正被害,诸臣如南京给事中戴铣以保留刘健、谢迁为民……今铣已故,当优恤。吏部覆奏得旨……铣光禄寺少卿,各赐祭一坛。”[27](卷十二,嘉靖元年三月癸丑,P424)王守仁曾因疏救戴铣等而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降兵部主事王守仁为贵州龙场驿驿丞。时南京科道戴铣等以谏忤旨,方命锦衣卫官校拏解,未至,守仁具奏救之,下镇抚司考讯。”[15](卷二十,正德元年十二月乙丑,P582)可见戴铣为正义之士,非矫枉过情之人。正德年间曾有旨斥责戴铣,《明武宗实录》记载此旨或为焦芳起草,刘瑾矫诏:“戴铣、徐蕃……递相交通,彼此穿凿,曲意阿附,遂成党比,或伤残善类以倾上心,或变乱黑白以骇众听,扇动浮言,行用颇僻……以后毋蹈覆辙,自贻累辱,国有昭典,朕不轻贷,故谕。是日早朝罢,传宣群臣,跪于金水桥南,刘瑾以敕授鸿胪宣读之。其文乃瑾私人属笔,或曰焦芳为之。”[15](卷二十四,正德二年三月辛未,P663)可见戴铣曾为焦芳所不容,《孝录》此处对戴铣矫枉过情之评论,不可信。
三、史实脱漏
《孝录》记载范围广泛,有些重大事件记载详细,甚至有很多为其他文献所不载者,从而为后人了解相关史实提供了珍贵史料。然而其中亦有史实脱漏、应载而未载者,影响了《孝录》记载之全面性与准确性,兹举两例说明。
克复哈密事。弘治六年四月土鲁番速坛阿黑麻侵袭哈密,杀头目阿木郎,劫忠顺王陕巴后,令酋长牙兰据守哈密,自称可汗,侵掠沙州等地,周边部族不安。马文升等建议用兵袭斩牙兰,收复哈密。此役由巡抚甘肃都御史许进、镇守甘肃都督同知刘宁等领之。弘治八年十二月果收复哈密,虽牙兰逃逸,但亦斩首六十余级,获牛马羊只三千有竒。[28](第433册,P269)此次针对哈密之军事行动为前此所未有,令西域诸部族瞠目结舌,明朝自此军威大振,可谓弘治朝一件大事,应详细记之。而《孝录》对此役只记载赏赐有功官军之事:“(弘治九年七月)己未,录克复哈密功官军五千五百三十九人升赏有差。加镇守太监陆訚禄米岁二十四石,升总兵官右都督刘宁为左都督,仍岁加俸一百石,巡抚左佥都御史许进为右副都御史,右少监沈让为左少监,副总兵都指挥佥事彭清为都指挥使,督饷郎中杨奇、佥事孟准及验功御史张恕、副使李旻、佥事葛萱各给赏有差。”[1](卷一百一十五,弘治九年七月己未,P2088)对克复哈密之过程却漏而不载,包括克复时间、出兵部署、斩获人数等皆不详。2按,《孝录》凡例规定“命将平反叛书,征讨边夷亦书”[1](P9),其对于战事报捷一般皆予记载,而克复哈密如此重大之事竟略而不载,对其过程只字未提,从《孝录》凡例要求之角度看,《孝录》的上述记载也有不妥。
郑旺造妖言案。弘治年间有名为郑旺者,怀疑其女郑金莲入宫生皇子,将为皇亲,并设法与乾清宫内使刘山相通,刘山又得知王女儿者曾入深宫,蒙混称访得郑旺之女。郑旺遂累持果食之类送入,而刘山回有衣靴布绢诸物。久之,郑旺以皇亲自居,夸其里族,后被缉事衙门以妖言访获。《孝录》记载:“王女儿实周姓,非郑旺女,而虚喝以规货利,皆出刘山之奸,拟刘山造妖言律,郑旺、妥刚、妥洪传用惑众罪皆斩,其余徒杖有差,狱上。得旨刘山交通内外,妄捏妖言,诳诱扇惑,情犯深重,其即凌迟处死,不必覆奏,仍令诸内侍往视行刑,余从所拟。”[1](卷二百一十九,弘治十七年十二月丁丑,P4127)由此可知,郑旺被拟为死刑,而事实上郑旺之死刑未被执行,只是收监。明武宗即位遇赦得还,后又被逮获,至正德二年十月方被处以极刑。[15](卷三十一,正德二年冬十月己亥,P784)郑旺之案涉及国本,事体重大,明孝宗对其实际处理情形如何,郑旺本人免死之事,《孝录》应载而未载。据《治世余闻》所记,该案之卷宗在刑部福建司,人多录出,其所见明孝宗批词云:“刘林(刘山)使依律决了,黄(王)女儿送浣衣局,郑某(郑金莲)已发落了,郑旺且监着。”[29](下篇卷四,P63)《万历野获编》认为:“当时目击其事者所纪较国史更确。”[30] (卷三《郑旺妖言》,P87)在此且不论有关明武宗身世之谣言是否可信,郑旺是否果为皇亲,即仅就此案审讯与判决之实情观之,《孝录》记载模糊并有遗漏,需其他文献补充之,显示出其记载之不妥。
四、记载失误留在历史文献编纂学上的启示
1. 处处留心、时时谨慎是保证历史文献编纂正确不误的基本条件。《孝录》记载有很多文字上的错、脱、衍、倒现象,影响了其准确性。从上述各类记载失误看,有因人名、地名、数字等形近、音同或音近而误记者,有因官职机构、官名相近而混淆者,如官职“左、右”记载互误者甚多。有些则在编写文句时,处理不慎,出现漏字、颠倒等失误。此等失误往往多因编纂者责任心不强,粗心大意造成。故编纂历史文献,尤其当官方组织集体编纂时,应特别强调每位编纂者要皆做到谨慎细心,一丝不苟以求提高质量。
2. 凡例规定详细是保证历史文献编纂准确明晰的重要一环。《孝录》为编年体文献,按时间记事,然而凡例却未详细规定如何系时记事。如某件事情之发生、发展、朝廷处理过程,皇帝下达旨意等环节,往往涉及多个时间,凡例却未规定应将有关史实系于上述环节中哪一个,于是造成了编纂者随意为之,出现时间记载不清之弊病。
如某些军事行动延续时间较长,《孝录》记载相关事宜时,往往出现时间不明的现象。平定某处“叛乱”,往往在某时间之后记载“某贼被诛”,或接以“某处贼平”之句,而该时间往往并非诛杀此人、平定“叛乱”之时间。如《孝录》卷八十六记载:“(弘治七年三月)癸巳贵州苗贼平。镇守贵州太监江德、总兵官顾溥、都御史邓廷瓒,都督佥事王通等会调官军土兵征剿都匀长官司寨苗乜富架、长脚等,分路并进……凡破一百一十余寨,斩首俘获万余。捷闻,命降敕奖励德等。”[1](卷八六,弘治七年三月癸巳,P1598)本条记载句首为“贵州苗贼平”,下文涉及讨平乜富架的过程与结果以及报捷到朝廷、明孝宗下旨降敕等环节,由此无法断定弘治七年三月是哪一环节之时间。而《贵州图经新志》卷八与《皇明经济文录》卷三一详细记载了该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明年癸丑(弘治六年)秋八月,监督偕总兵与协同咸来会军……(九月)越翌日壬子,师分道以进。孟冬上旬,我师一鼓遂缚其酋乜富架……仲冬中旬,师再鼓,又缚长脚……斩级若干。至季冬下旬,师三鼓,又缚阿利、鸡选,阵杀阿脚,斩级仍若干……明年甲寅春正月丁未(十七日)班师奏捷。二月庚申俘献。皇情悦怿,降敕奖谕。”[31](卷八《都匀府·公署》,P94)[32](卷三十一《贵州·平蛮碑》,P349-350)《国榷》记载:“弘治七年正月,邓廷瓒平都匀、清平蛮,班师。”[12](卷四十二,弘治七年正月丁未,P2655)由此可判断弘治七年三月当为明孝宗降敕奖励立功官员的时间,而非平定贵州“苗贼”的时间。若无这些记载,仅读《孝录》,即会使读者在该事各环节发生时间上,不知底细。
《孝录》卷七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壬戌条所载礼部尚书周洪谟会五府各部都察院翰林院等衙门议祧迁之制及孝穆慈慧皇太后奉享之礼的奏疏[1](卷四十二,弘治七年正月丁未,P2655),内容极为详细,然而具体时间记载模糊,所涉礼部等衙门上奏时间、明孝宗第一次批复时间、 礼部等覆奏时间、明孝宗第二次批复时间等皆未明记,“壬戌”为上述哪一环节的时间亦不能确知。倪岳撰《礼仪一》记载:“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西角门题奏(上引礼部等衙门所上奏疏),本月二十三日奉圣旨‘是。奉先殿旁近无宫室堪改别庙,恁还再议来说。钦此。钦遵。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礼部会官议拟题,奉圣旨‘你每既考论明白,准议。”[5](卷十一《礼仪一》,第1251册,P106)可见礼部尚书周洪谟等上奏时间当为本月二十一日。上引《孝录》同条所载明孝宗命礼部等衙门“再议以闻”之时间当为本月二十三日,“礼部覆会官上议”之时间当为本月二十六日。而“壬戌(二十七日)”当为皇帝准议的时间。
3. 秉笔直书是编纂高质量历史文献的灵魂。上述对刘健、谢迁之诋毁,对曾铣之诬陷,皆为焦芳所为。焦芳其人作为编纂《孝录》之总裁官,任意笔削,造成对某些事件发生的原因、结果记录不实,对人物分析与评论或溢美或诋毁,贻误后人。董玘曾参与编纂《孝录》,亲见焦芳操笔:“肆其不逞之心于亡者,欲遂以欺乎后世,其于叙传,即意所比必曲为揜互,即夙所嫉,辄过为丑诋,又时自称述,甚至矫诬敬皇而不顾。凡此类皆阴用其私人誊写圈点,在纂修者或不及见,惟事之属臣者黾勉载笔,不敢有所前却,而其它则固非所及也。”[33](卷一百五十二,P1517)焦竑亦记载焦芳曲笔:“焦芳为孝庙实录总裁官,笔削任意,尤恶江西人,一时先正名卿无不肆丑诋以快其私忿,所书多矫诬不根,往往授意所厚,若段炅辈使笔之,挟瑾威以钳众口,同官避祸皆莫敢窜定一字。”[34](卷八,P284)徐乾学修《明史》时,曾撰《修史条议》,对于明代的历朝实录,分别论其优劣:“明之实录……莫详于弘治,而焦芳之笔褒贬殊多颠倒。”[35](卷十四,P490)史书之重要价值,在于为后人留下可信的历史记载,以便了解真相,发现启示。焦芳之歪曲史实使《孝录》蒙羞,此从反面告诉后人:凡执笔为史者,其首要的信条应为“秉笔直书”,此四字是编纂出高质量历史文献的最重要的保证。
[1] 《明孝宗实录》,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
[2] 《明宪宗实录》,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
[3] 林俊:《见素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 焦竑:《国朝献征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5] 倪岳:《青溪漫稿》,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 杨一清:《杨一清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
[7] 余子俊:《余肃敏公奏议》,四库全书禁毁书丛刊本.
[8] 王恕:《王端毅公奏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
[10] 沈国元:《皇明从信录》,四库全书禁毁书丛刊本.
[11] 张萱:《西园闻见录》,续修四库全书本.
[12] 谈迁:《国榷》,北京:中华书局,1958.
[13] 彭簪:《衡岳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4] 《明太宗实录》,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
[15] 《明武宗实录》,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
[16] 李贤:《明一统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 《明孝宗实录校勘记》,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
[18] 方孔照:《全边略记》,续修四库全书本.
[19] 徐日久:《五边典则》,四库全书禁毁书丛刊本.
[20] 李东阳著,周寅宾点较:《李东阳集》,长沙:岳麓书社,2009.
[21] 赵定邦:(同治)《长兴县志》,《中国方志丛书》本.
[22] 程敏政:《篁墩文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 王珣:(弘治)《湖州府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4] 栗祁:(万历)《湖州府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5] 刘浚:(同治)《孝丰县志》,《中国方志丛书》本.
[26] 和珅:(乾隆)《大清一统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 《明世宗实录》,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
[28] 许进:《平番始末》,续修四库全书本.
[29] 陈洪谟:《治世余闻》,北京:中华书局,1985.
[30]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
[31] 赵瓒:(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32] 万表:《皇明经济文录》,四库全书禁毁书丛刊本.
[33] 董玘:《较勘实录疏》,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
[34] 焦竑:《玉堂丛语》,北京:中华书局,1981.
[35] 徐乾学:《憺园文集》,续修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 王雪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