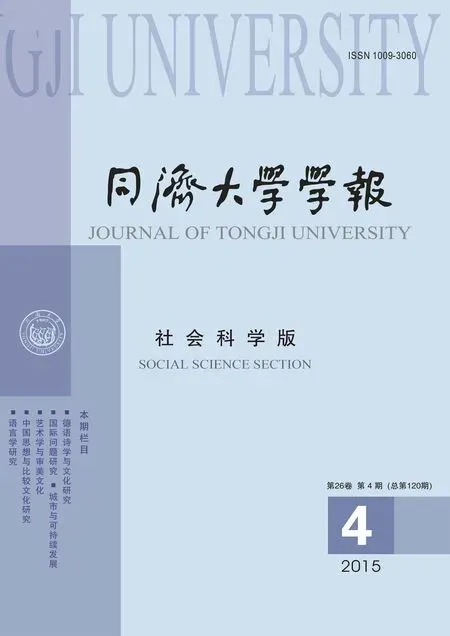适度启蒙与人类教育
——莱辛的启蒙反思及其对理性与信仰冲突的调和
叶 隽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一、 莱辛的启蒙反思:适度启蒙与绝对真理是否可能?
如果说,对于启蒙的问题,莱辛无疑是最早具有反思意识者之一;可反思启蒙的目的究竟何在呢?当1784年,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以一种大无畏的姿态高呼,追问《什么是启蒙》(Was ist Aufklärung)的时候,莱辛已然辞世三年。对他的同代哲人的“启蒙”概念,他会怎样想呢?康德是这样说的:
启蒙就是人结束他咎由自取的未成年状态。所谓未成年,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假他人的引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头脑。倘若其原因不在于缺乏头脑,而在于没有他人的引导就没有决心和勇气使用自己的头脑,那么这种未成年就是咎由自取。鼓起勇气去使用你的头脑!这就是启蒙运动座右铭。*Kant, Beantwortung der Frage: Was ist Aufklärung? Quellen Philosophie: Deutscher Idealismus, S. 1702 (vgl. Kant-W Bd. 11, S. 53). 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QP03.htm. 中译文参见李伯杰等:《德国文化史》,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3页。
莱辛是否会对此加以赞同?应该说,自文艺复兴以来,高举人的旗帜,将理性的光辉洒满人间,让人自己成为“主人”,这可就是要替代“神”的位置了。可问题在于,康德在18世纪后期再度旧话重提,并将“启蒙”的大旗扬起,究竟是何以然?如果仔细分析这段经典话语,会发觉康德并没有走向极端,他要求的并非是绝对依赖“头脑”,而只是针对此前的蒙昧状态而鼓起勇气使用头脑。或者更干脆地说,就是:“启蒙以后怎么办?”为打鬼而借助钟馗,乃是历来人类斗争所必须采取的必要手段,故此不值得大惊小怪。启蒙之所以能勃然兴起,主要还是与基督教在欧洲的绝对统治地位有关,虽然西方之源从根本上来说是二元的,即两希文化之合力作用,但相比较希腊的理性思维主导方式,由希伯来系统而来的基督教因其宗教形式和神秘主义而往往颇受质疑。故此宗教改革的爆发,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场域博弈因素的话语权力争夺,但另一方面也未尝不可理解作其渊源有自的观念冲突之延续。
说到底,启蒙是个舶来概念,最初提出的当属法国人,所谓“启明世纪(光明世纪)”(Lumiere),说到底还是那个“启蒙”的意思。南欧文化之所以强调人的重要意义,乃在于突破神的禁锢和束缚。应该承认,在那个神性至上的时代,尤其是神不但在信仰空间占据了绝对的神圣位置,而且在世俗生活中占据一种压倒统治地位的时代,将其请下神坛无疑极为必要。可问题在于,“请神以后怎么办”,将神驱逐只是一种凸显人之地位的必要手段,可一旦打鬼结束,如何处置“钟馗”却是个大问题。因为一旦处置不当,钟馗自己就变成了神,新官上任,旧规不改。这才是流遍亿万人民血,换汤换药道脉绝。
或认为“莱辛确有一套自身完整和结构严谨的‘体系’”*Hans Leisegang, Lessings Weltanschauung(《莱辛的世界观》), Leipzig: Felix Meiner Verlag, 1931, p. 97.,或强调莱辛“并非是有体系的学者”,而更多属于即兴思想家之列,*Leopold Zscharnack, “Vorwort des Herausgebers,” Lessings Werke, Band 20, p. 24.但无论如何,在德国思想史上,莱辛绝对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而且是启蒙思脉极具个性的代表人物。如果说康德这代人以哲学话语确立了现代性的强势地位,并祭起启蒙的大旗为号召,从而将启蒙思脉不仅在哲学层面予以充分肯定,而且波及整体的思想文化场域;那么,在这一旗帜下呼应的莱辛,则以其文学话语的特殊形式,有意味地深入到时代大潮中去。
就欧洲思想与社会发展的整体轨迹来看,作为西方思想之源泉,其基本思维模式仍是二元论,也就是说是一种势不两立的二元对立。既如此,则身在启蒙思脉之列的莱辛的启蒙反思则别有意味。这意味着那种绝对的二元对立已然消解。其实,这在莱辛的真理观上就可看出来:“人的价值不在于占有或自以为占有真理,而在于他为探寻真理所做的真诚的努力。因为人的力量不是靠占有真理,而是通过对真理的追求而得到拓展,人的不断增长的完善性就在于其能力的增长。”*Lessing, Materialien zu Leben und Werk: Leben und Werk, Lessing: Werke, S. 8 (vgl. rororo-Lessing, S. 8). 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band5.htm. 中译文参见李伯杰等:《德国文化史》,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42页。这样一种绝不以真理占有者自居的态度,显示了莱辛的高明之处,因为只有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我们才有可能不断接近真理,而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更可能获得道义上的“求真之真”。因为,“获得真理”与“追求真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重要的,前者强调一种目的追求的功利性,而后者似乎更立足于一种表现理想状态的西西弗斯努力。人之所以可贵,或许并不在于简单地去信仰与实践,而是显示自己为万物灵长的理性、辨识和行为能力;就此而言,玄奘取经的意义则更在于借助西土佛经的知识资源意义而获得中国知识创生的意义,而不是简单的取经归来。
有论者明确指出:“一部西方文明(以科学和法律为中心)的发展史,就是上帝逃离尘世的历史,就是统一的宇宙分裂的历史。在这种文明看来,上帝不是居住在这个世界中,关爱着这个世界,而是居高临下地居于这个尘世之上。这种‘二元的对立’是西方文明走向失败的根本原因,西方人就生活在一个两极对立的疯狂的世界中。”*刘杰:《在哲学与宗教之间——马丁·布伯的哲学和宗教思想简论(代译序)》,见[德]马丁·布伯(Buber, Martin):《论犹太教》(On Judaism),刘杰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9页。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二元论毕竟是西方世界占据统治地位的元思维模式,不仅有其上述偏执的一面,而且也有其优点,否则西方不会至今为止仍占据人类社会的主导性地位。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也是,诚如所论,过于偏激甚至极端化的二元对立倾向,确实导致了西方世界发展的瓶颈性难题。
信仰的拥有是西方的一大幸事,当民众沉浸在一个充满信仰、精神有所皈依的世界里的时候,社会生活是安宁而有序的。由秘索思(古希腊,如《荷马史诗》时代)这一元思维模式延展出神话、宗教的倾向,其实与日后基督教的思维模式有暗合之处,其核心在于对终极的一种信仰。而这一点当基督教出现之后,就变得日益彰显。宗教信仰的出现及其日后的极端化,使得宗教成为必将被反抗和抛弃的神坛偶像;而宗教—神学的结构性架设,并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则使得一种一元独大的强势过于强烈;而启蒙之所以出现并以一种摧枯拉朽的方式最终摧毁了宗教权力的绝对统治,就在于“物极必反”的道理,而随之出现了一种对抗性的知识架构,即哲学—科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哲学本身也就成了一种信仰的可能,即对人自己决定自己的信仰的权利的肯定。文艺复兴的出现及其力量,当作如是看。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来理解莱辛的“适度启蒙”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二元对立的方式已然对莱辛的思维模式不再产生决定性作用的时候,那么他自然就会寻求一种折中的方案。即便他要对宗教有质疑,甚至对教权神权反感抵抗,但也不想走到绝对对抗的位置上去;因为他理解和抵抗的,其实已经是背后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当然,莱辛的“适度启蒙”并不是中庸之道,他并没有截然提出一种取中的方法,就像日后歌德、席勒开辟的“古典图镜观”那样,使得古典思脉最终得以成形。所以即便是他的基本思想立场,也只能归入到启蒙思脉之中。
霍克海默其实多少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文明的思想基础很大,一部分的崩溃在一定程度上是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后果。然而这个进步本身又产生于为某些原则所做的斗争——这些原则现在岌岌可危,比如个人及其幸福的原则。进步有一种倾向,即破坏它恰恰理应实现和支持的那些观念。技术文明危及了进行独立思考的能力本身。”*②④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反对自己的理性:对启蒙运动的一些评价》,见[美]詹姆斯·施密特(Schmidt, James):《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对话》,徐向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68、368、369页。在这里,霍氏清晰地给我们梳理出一条发展轨迹链,即理念(如个体原则)—科学—技术—理念之间的复杂关系,进步成为一种并不可以绝对视为褒义的概念。大致说来,理念、科学(学术)、技术在文化层级中构成了又一个上中下三分的结构,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值得深入探讨。按照霍克海默的观点:“理性似乎正经受着一类疾病。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都是如此。个人为现代工业的巨大成就,为自己增进了的技术能力和获得物品和服务的机会付出的代价是,他越来越无法对抗社会的集权,而那本来是他理应控制的东西。”②这个判断太准确了,我们甚至可以直接提出这个“理性病”的概念*诚如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 1925-1999)提出“法国病”(1976)的概念,参见[法]佩雷菲特:《官僚主义的弊害》,孟鞠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因为理性之所以被启蒙运动高涨起来,为的就是对抗在神权统治下的感性的绝对优势地位,获得个体的解放,可一旦自由成为一种过度神圣的东西时(伯林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区分可以参考),它就不再是一种正面概念,而是有可能走向反面。个体自由的悖论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正因为无法把握一种中庸之度,所以西方对自由的寻求导致了目前现代性的整体危机。而莱辛可以说是最早意识到“理性病”问题的前贤,他在那个时代就以启蒙人的身份开始适度调和的努力,就是一种“自我疗治”的措施,值得特别重视。
霍克海默继续将这种思考放置入具体语境:“在个人那里,独立思考败坏了;在社会那里,科学真理和宗教真理分离了。这只是标志我们时代的同一个困境的两个现象。”④这个判断很重要,尤其是后者提出了“科学真理”、“宗教真理”的概念,极具区分力和协和力。大道万条,条条通向罗马,但其中毕竟有要道和小路之别,即便在要道之中,一统天下是可怕的。所以,追求真理应当允许有不同的路径,而且应注意到主要的追索之道的互补功用。就这个意义而言,其实感性路径与理性路径,乃是皆不可忽的两条元路径。具体言之,则秘索思思维和逻各斯思维的互补功用极为重要,宗教之路有其真理天赋,科学之路亦有其真理使命。但两者本应是缺一不可、相辅相成,而非道不同不相往来的。但在事实的场域运作之中,则恰恰形成一组仿佛你死我活的悖论,教士和神学家持一端真理,以为自己是“代上帝立言”,绝对有一种至高无上的话语霸权意识;而科学家与启蒙者亦持一端真理,认为自己由大自然实证出发,手中掌握的才是真正的科学真理*当然也有极少数有大智慧的科学家会超越这种思维方式,譬如爱因斯坦就曾毫不掩饰地表达其作为科学家的思想家雄心:“我想知道上帝是如何创造这个世界的。对这个或那个现象、这个或那个元素的谱我并不感兴趣。我想知道的是他的思想,其他的都只是细节问题。”参见《前言》,见[美]阿·热:《可怕的对称——现代物理学中美的探索》,熊昆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1页。入手处是具体的科学探索,但背后试图追究的仍是宏观宇宙之谜,这正是爱因斯坦作为一代大师的伟大之处。随着学科划分日益细密,有这样雄心壮志的学者恐怕越来越属凤毛麟角;可所幸则在于:“正当当代绝大多数物理学家忙于解释特定现象之际,少数爱因斯坦的理性的后继者却变得更加雄心勃勃了。他们进入了夜幕笼罩着的森林,探寻着自然的基本设计,并且狂傲不羁地宣称,已经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参见《前言》,见[美]阿·热:《可怕的对称——现代物理学中美的探索》,熊昆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1页。。只是未免让后来者困顿之极,究竟谁是真理?
启蒙的立场在于,鼓起个体自身的信心和勇气,而排除外来的影响。当康德以一种决绝的勇气和决心,要求人类在个体意义上使用自己的头脑时,其实也难免“纠枉过正”的成分,因为任何个体都非“生而知之者”,甚至作为整体的人类都不是,我们发明了那么多的科学技术,真的就认知了大自然的规律了吗?“敬畏自然”、“敬畏生命”其实非常必要。设若如此,那么莱辛发明“适度启蒙”的理念就显得十分重要,这是启蒙思脉内部对启蒙原则的自我反思,它意味着不以一种绝对的眼光和口吻来看待和解答问题,任何情况都保持一种“守中”的可能*关于启蒙思脉的内部区分问题,已有学者予以关注,譬如有论者就将启蒙一分为三,曰:激进、保守、中立。参见Jonathan Israel, Radical Enlightenment: Philosoph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ity 1650-17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实事求是地说,启蒙确立人的主体立场是有必要的;但将神的地位做一种根本性的颠覆是绝对有问题的,而最关键的问题是“信仰”的淡逝。其问题就在于“过犹不及”。
其实,故代时期对神的树立,其主要功能是树立起人心中的一种信仰,从根本上说就是确立起一套宇宙观范畴的伦理观。这对人类作为整体的安身立命是非常重要的。而现代时期对人的“人神”地位的确立,其实不过是以人代神,固然有其特定的时代进步性,也不是完全没有必要,但总体来说,这是一种僭位的人,这从日后的历史发展的悖论中就可看出来,正如歌德的讥讽那样:“我见证人类的自我折磨。/ 世界小神总那样秉性如故,/ 宛如开辟的首日般神妙奇异。/ 得之于你的天光圣辉,/ 反而将他的生命搞得更糟”*Goethe, Faust. Eine Tragödie, Goethe: Werke, S. 4541 (vgl. Goethe-HA Bd. 3, S. 17). 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band4.htm. 此处为作者自译。中译本参见[德]歌德:《歌德文集》第1卷,绿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9页。,这很明显地表明了他对人类的理性及其滥用的不屑。在这个问题上,莱辛与歌德虽是两代人,见解可谓相通。
要知道,在莱辛看来,真理绝对不可能被“拥有”,最多不过在某个时候可以被“获取”。这意味着,“在热衷于唯一正确的、政治上有效的真理的人当中,只能十分小心谨慎地谈论真理,一个对真理的矛盾性感兴趣的人,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可以讲述童话,并且在真理受到威胁时,沉默比不受保护的表达更明智”*[德]瓦尔特·延斯:《纳旦的思想一直就是我的思想》,见汉斯·昆(Küng, Hans)、瓦尔特·延斯(Jens, Walter):《诗与宗教》(Dichtung und Religion),李永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99页。。既然对真理如此质疑,那么莱辛的启蒙立场也就同样值得揣摩。毕竟,启蒙的基本思路是绝对的,它就是要将神坛颠覆,将人类扶正;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启蒙运动,它更以一种相对明确的目标为设定,试图对原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彻底否定。正因为此,后世来者如孔汉思对莱辛的评价甚高:
莱辛——一个直言不讳和思想敏锐的人——今天看来也许是第一个要求对启蒙进行启蒙的人,也是第一个为了认识真理和塑造人道的生活,而警告人们不要盲目相信人类理性和科学的人……*[德]汉斯·昆:《启蒙进程中的宗教》,见汉斯·昆(Küng, Hans)、瓦尔特·延斯(Jens, Walter):《诗与宗教》(Dichtung und Religion),李永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93页。
诚如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所认识到的那样:“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但事实上,盲听轻信,满腹疑虑,草率结论,夸夸其谈,惧怕反驳,不思进取,漫不经心,咬文嚼字,一知半解——所有这些都阻碍人类心灵与事物本性的和谐一致;相反,却使人类心灵与空洞的观念及盲目的实验结合起来;不管这一结合有多么体面,其后果与结局都是不难想象的。”*Theoder W.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3,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Begriff der Aufklärung, S. 1105 (vgl. GS 3, S. 19). 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band97.htm. 中译本见[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页。这里就将启蒙目标的崇高性和执行者——作为“世界小神”之人的不成熟性之间的矛盾充分揭示出来了。或者,进一步可以追问的是,即便是这样的崇高目标,它有无一个限止之处?如果有的话,那么它的界限在哪里?战胜盲目与愚昧无疑是必要的,但将自己奉为神祇是否也同样值得质疑?人在祛除迷魅之外,也还需要心存敬畏,这种敬畏乃是人类保持其伦理底线的必要支撑,那个时代的人们有多少意识到了?李泽厚说过这样一段话:“道德秩序超越经验情感而普遍必然,人应该在经验世界中服从履行,以之统领、管辖、主宰自己的行为、活动,并由之生发出道德情感。这道德感情,就如Kant所说,不是同情、怜悯或爱,不是什么‘恻隐之心’,而只是‘敬重’。同情、怜悯、爱或‘恻隐之心’都与动物本能性的苦乐感受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敬重’却是一种与动物本能毫无关联而为人类所特有的情感。”*《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2004年),见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67-68页。无论是“敬重”,还是“敬畏”,都是一种“敬”的表现。对于人类来说,表现出“敬畏自然”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而“道德秩序”的建构和维持则是在制度层面非常关键和必要的,这首先就表现在应当控制或限制人类的“权力运用”上,“人类为其权力的膨胀付出了他们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不断异化的代价。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独裁者了解这些人,因此他才能操纵他们;而科学家熟悉万物,因此他才能制造万物。于是,万物便顺从科学家的意志。事物的本质万变不离其宗,即永远都是统治的基础”*Theoder W.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3,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Begriff der Aufklärung, S. 1115 (vgl. GS 3, S. 25). 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band97.htm. 中译本见[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7页。。这段话讲得实在是精辟,这也可以从一个拉长焦距的视角让我们可以清醒地来反思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我们往往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二、 人类教育命题的提出:中庸之道的具体定位
对于莱辛来说,他之转向宗教,并非是一种简单地向右转的问题,正如他在历史语境中之选择启蒙,并不会排除其早期接受的宗教教育的影响,这也是他的知识和信仰基础。但在莱辛的思想之中,教育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值得充分关注。他深刻指出:“教育给予人的,并非人凭自己不可能得到的东西;教育给予人的,仅仅是人凭自己可能得到的东西,只是更快、更容易而已。同样,启示给予人类的,并非人的理性凭自己达不到的东西;毋宁说,启示仅仅更早将这些东西中最重要的给予人类,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Lessing, Die Erzieh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Lessing: Werke, S. 4951 (vgl. Lessing-W Bd. 8, S. 490). 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band5.htm. 《论人类的教育》(1777-1780),见[德]莱辛:《论人类教育——政治哲学文选》,朱雁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02页。在这里,“教育”与“启示”成为一种二元构造,即“有神的启示”与“无神的教育”。那么,我们要追问的自然是,“教育”究竟是什么?它对我们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教育在莱辛的话语体系中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它扮演了在宗教(信仰)和哲学(理性)之间的调节器角色,它就是那个居于中道的东西。
莱辛将人类分为三个时代,即“孩提时代”(das Zeitalter der Kindheit)、“少年时代”(das Knabenzeitalter)、“成人时代”(das Zeitalter des Mannes)。*转引自范大灿主编:《德国文学史》第2卷,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78页。这自然让我们想起了费希特对人类的划分。费希特从时代本身开始剖析,《现时代的根本特点》(Die Grundzüge des gegenwärtigen Zeitalters)作于1806年,按照他的理论,将人类世俗生活分为五个基本时期:(1)理性借助本能进行绝对统治的时期;(2)合理本能变成外在强制权威的时期;(3)直接摆脱专断的权威、间接摆脱合理本能和任何形态的理性的统治的时期;(4)理性科学的时期;(5)合理技艺的时期。*③ [德]费希特(Fichte, Johann Gottlieb):《现时代的根本特点》(Die Grundzüge des gegenwärtigen Zeitalters),沈真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11、17页。
他将自己身处的时代称之为“罪恶完成的时代”(恶贯满盈的状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现时代正处在全部时间的中点”,“现时代就把两个根本不同的世界——黑暗世界与光明世界、强制世界与自由世界——的两端连接起来了,但又不属其中的任何一端”。③这样他就将自己的理论推向了三段式:“盲目的理性统治—中间点—光明的理性统治”。应该说,这一思路与莱辛的三时代说是有共通之处的,也就是都将理性作为一种基本的、通向真理的合法性路径。所以,莱辛的时代划分,对于德国18世纪知识精英传统来说具有“标立杠杆”的功用,毕竟,他是后来者的前驱。更为重要的是,莱辛将教育与基督教联系起来:
上帝要将人类的一个部分纳入一个教育计划中——但上帝只想将人类的这个部分纳入这一个计划,他们已经通过语言、行动、治理和其他自然的、政治的环境维系在一起;人类的这一部分已然成熟到迈向教育的伟大的第二步了。
这就是:人类的这一部分在其理性的运用上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他们的道德活动需要更高贵、更有尊严的动因远胜过此前引导他们的一时的赏罚。孩子成长为少年。甜食和玩具让位于正在萌发的要求,要像其兄长那样享有自由、尊重、幸福。*Lessing, Die Erzieh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Lessing: Werke, S. 4972 (vgl. Lessing-W Bd. 8, S. 501-502). 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band5.htm. 《论人类的教育》(1777-1780),见[德]莱辛:《论人类教育——政治哲学文选》,朱雁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17页。
其实这里的上帝未必就是上帝,而多少具有泛神论的意味,即远指那种世俗之外的创造性力量。莱辛努力将“教育”作为一种更高层次的伦理和知识规训,他想在人类教育与上帝教育之间构建一座桥梁,于是如此描绘人类教育的一般途径:“人们向少年展示的诱人前景,向他展示的荣誉、成功,无非是教育他成人的手段,使他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即便没有荣誉、成功一类的前景仍能够履行其义务。”*Lessing, Die Erzieh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Lessing: Werke, S. 4983 (vgl. Lessing-W Bd. 8, S. 508). 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band5.htm. 《论人类的教育》(1777-1780),见[德]莱辛:《论人类教育——政治哲学文选》,朱雁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25页。他接着比较追问道:“人实施教育的目的既在于此,上帝实施的教育达不到此一目的吗?技艺对于个人所做到的,自然对于整体会做不到吗?”*Lessing, Die Erzieh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Lessing: Werke, S. 4984 (vgl. Lessing-W Bd. 8, S. 508).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band5.htm. 《论人类的教育》(1777-1780),见[德]莱辛:《论人类教育——政治哲学文选》,朱雁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25-126页。如此则所谓“上帝”之意义豁然显焉,在尘俗人类社会之外,应该有一个更高的力量存在,因为它对于人类其实是一种积极的正面的存在。所以,莱辛故意设置困惑,他会追问:“人类难道永远无法达致这一最高的启蒙和澄净阶段?永无可能?”*Lessing, Die Erzieh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Lessing: Werke, S. 4983 (vgl. Lessing-W Bd. 8, S. 507).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band5.htm. 《论人类的教育》(1777-1780),见[德]莱辛:《论人类教育——政治哲学文选》,朱雁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25页。此处为作者自译。这显示出莱辛的理想主义的一面,他似乎对人类的终极目标设定葆有信心,但其中的不确定性也隐约可见。在这种矛盾之中,他似乎还是倾向于乐观主义的:
那个完成的时代将会到来,一定会到来;到那时,人的理智愈是怀着信念感觉到一个日益美好的未来,人便愈无须向未来乞求自己行为的动因;到那时,人行善只因其为善,而非由于给行善规定了任何报偿,而在以往,只有这报偿才吸引和固定住人的疑惑不定的目光,使之认识到善的更高的内在报偿。*Lessing, Die Erzieh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Lessing: Werke, S. 4984 (vgl. Lessing-W Bd. 8, S. 508).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band5.htm. 《论人类的教育》(1777-1780),见[德]莱辛:《论人类教育——政治哲学文选》,朱雁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26页。
在这一点上,莱辛无疑更立足于描绘一个美丽的人类未来,这一点倒是充分体现出启蒙思脉人物的理想主义精神。对人性的问题,门德尔松似乎比莱辛要悲观得多,他说:“人继续向前走,人类却总是摇摆于种种规定的藩篱之间,时起时伏。从整体看来,在所有历史时期,人类大体上仍停留在同一道德阶段,保持着宗教与邪教、美德与恶行、幸福与不幸的同一尺度;维持着同样的结论,如果以同一尺度考量同类事物的话;从所有这些善善恶恶中,对个别人的经历的要求不会减少,以便他们在尘世受到教育,从而能够按赋予和分配给每一个别人的程度接近完美状态。”*转引自[德]莱辛:《论人类教育——政治哲学文选》,朱雁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27页注释1。应该说对人类的这种自我控诉,其实并非没有道理。无论时代如何变化,衣着如何光鲜,但人类始终不能改变其孽根的人性。而歌德则干脆做出人类终结的预言:“人类会变得更聪明,更具识别力,但不会更好,更幸福,更有力,或者至少在某些时代如此。我似已预见到某一时刻的来临,上帝不再能从人类身上获得乐趣,那就必然会毁灭一切,求得更生冲创之力。我相信,这一切都已在冥冥之中早有注定,在遥远未来的某个时日,必将开始又一轮新的恢复冲创之力的时代。但距离那刻肯定仍有漫长的时日,我们依旧可在成千上万的年头里在这块可爱的、古老的土地上享受生活,就像现在这样。”*1828年10月23日谈话,Johann Peter Eckermann, Gespräche mit Goethe — in den letzten Jahren seines Lebens(《歌德谈话录——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年头》), Berlin und Weimar: Aufbau-Verlag, 1982, s. 600.所幸到最后,歌德还是回到较为乐观的态度上去,让我们依旧可以对人类保持一定的希望;从这点来说,莱辛的表述中多少可以见出其矛盾心态,但其通过“人类教育”之手段来提升人类道德伦理水平的努力却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赫尔德虽然思脉有异,但却赞同这一思路:“我们可以谈论人类的教育(Erzieh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因为每个人受了教育才能成人,而人类整体只存在于单个人组成的链条之中。”*《历史哲学思想》,见[德]赫尔德:《反纯粹理性——论宗教、语言和历史文选》,张晓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8页。通过教育使人成为人,这似乎是精英分子承认的不二法门,他更强调了“个体链条”的人类悖论。一方面,人类有其共性特征,但另一方面人类毕竟不是一个完全抽象的概念,而是由具象的个体组成,可一落实到个体,就纷繁复杂,异象纷呈了。所以既要关注个体,又要关注个体成链之整体形成,大致近似我所谓的“网链点续”。
莱辛进一步指明教育的功利性:“教育有其目的,不论对人类还是对个别人。凡被教育者,都将被教育成某种东西。”*Lessing, Die Erzieh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Lessing: Werke, S. 4983 (vgl. Lessing-W Bd. 8, S. 507).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band5.htm. 《论人类的教育》(1777-1780),见[德]莱辛:《论人类教育——政治哲学文选》,朱雁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25页。如此,则既有个体的受教驯化,也有人类整体的面对上帝的教育问题。这也是一种双刃剑,个体既要作为被动者接受教育,也不可回避其作为主人翁自我成长的一面。这种“教育规训”的二元性不仅表现在个体身上,对人类的整体教育也同样如此,而适度启蒙的意义在这里就凸显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莱辛明确提出关于真理的问题就很有价值了:
人的价值并非来自一个人所掌握或者妄自认为掌握的真理,而是他为探索真理所付出的真诚努力。一个人要增长自己的完美品格的力量,不能靠占有真理,只能靠探索真理。占有只会使人静止、怠惰、骄傲。
假若上帝的右手握着所有真理,左手握有唯一的、不断躁动的追求真理的冲动,而且带有时时甚而总是使我陷入迷误这一附加条件,然后对我说:选吧!我会恭顺地扑向他的左手,并说:我父,给我吧!纯然的真理只属于你自己!*[德]莱辛:《第二次答辩》,见[德]莱辛:《历史与启示——莱辛神学文选》,朱雁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79-80页。
这其中其实隐含着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上帝的不可信,因为如果真理是客观存在的话,那么又胡为不取?所以,真理之价值,或许正在于其可表述而不可获得,真理或许更可以理解为启蒙运动树立起来的又一尊大佛,用以取代上帝而已,但真理毕竟不是上帝,不是那么明确可见可得之物,所以也就有了让人向前不息的探索冲动。如果一切都是有形可触的,反而不是人类需要的了。莱辛的高明之处,也正在此,他小心地汲取基督教的负面经验,希图化解启蒙问题于无形,如此则将真理设置为一种始终处于过程中的象征性符号,就是最佳策略。只要冲动,而不取目标,岂非舍本逐末?岂非买椟还珠?然而,在莱辛,非也,这是大智慧的表现,也是他处于启蒙思脉而游离于正宗或极端启蒙者,对宗教始终抱有同情、理解和融通的原因。
三、 对理性与信仰冲突的调和:在“故代性”与“现代性”之间
至少就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来看,二元相对固然存在,但彼此之间的关系应当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和西方二元论极为不同。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现代对故代是有继承亦有发展的。
如果要充分理解“现代性”的概念,我们一定要提出作为其二元对立面的“故代性”(区别于“古代性”,作者杜撰)概念。“故”与“现”两者之间的对立,主要表现在一为过去的背景,一为当下的语境。当然在具体的语义阐释上,也有意义深度的差别。“现代”对“故代”的方式是否必须以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和对抗出现,这或许仅是西方思维方式中特有的“二元对立”产生的一种逻辑结果,并非就是客观的那层真理(如果存在的话)。我想,必然是有一种东方现代性的方式,它所理解和诠释的“现代性”应当是有别于西方的,甚至连表述的话语都是不同的。但现在我们却不得不仍停留在习用与占据话语权力的西方话语表述中,有论者所以提出“现代性多元方案的发展可能”,认为在像日本这样的非西方社会中产生了不同的文化方案,而它们“带来了对现代性基本文化方案的不同解释;带来了对这些方案不同成分的不同强调——诸如人在宇宙中的积极作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宇宙时间的概念及其与历史时间的关系;进步的信念;进步与作为进程、贯穿了进步方案的历史间的关系;与主要的乌托邦图景间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理智与情感、理性与浪漫及感情之间的关系”等,更重要的是,“在许多这类文明中,‘现代性’的基本含义——它的文化历史方案——是与其西方的原始图景相当不同的。西方的现代性,根源于启蒙运动、进步、理性和个人自我实现的展开、社会和个人解放的理念”。*[德]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156页。这确实有道理,我倾向于在西方的整体现代性(这确实可成立)之外,应当存在一种“东方现代性”的东西,它们构成一组二元。
或者,进一步追问,我们是否应该建立一个三元的概念,借用佛家之语,佛有三生,过去、现在、未来。故代、现代、后代。但在宏阔的历史宇宙空间,这些概念又只能是相对的。相比较以往故事的逝去性,那么现代强调的是我们身处其中的一个相对长时段概念,而不仅是一个短期概念;即便如此,相较故代的明确纪年,后代的漫漫无际,现代始终是一个有限时段。格拉斯对此有绝妙的概括,他提出了“过现未”(Vergegenkunft)的概念,但这种概念在学理层面上则难以充分阐述,也难以译成合适的中文。我觉得二元三维的概念比“一分为三”要更细腻一些,但仍是从此中发展而来。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周易·系辞上》),朱熹进一步发明其意义强调“阴阳非道也,一阴又一阳、循环不已乃道也”(《朱子语类》卷七十四)*庞朴进一步解释说:“一个‘阴’、一个‘阳’两个对立者,它们共居于一个统一体内;但是这不够,还必须把它们理解为时而阴时而阳,或一时阴一时阳,理解为动态的存在;但是,简单的动态也还不够,这种动态事实上是循环,叫作‘始终之变’,终就是始,始就是终;这样仍然不够,必须把这个‘始终之变’理解为循环上升。”参见庞朴:《中国文化十一讲》,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1页。。这其中强调的主要是阴阳调和、互动、循环构成“道”之所在。说到底,“‘阴阳’本身不是‘道’,‘阴阳’的变化和变化之理才是道”*③④⑤⑥⑦ 庞朴:《中国文化十一讲》,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1、126-131、126、133、132、127页。。这样的阐释就很精辟了,把握住作为二元的阴阳固然很重要,但只有加上其第三维,就是阴阳鱼之间的流力因素,其变化之理,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元结构,就是所谓的“道”,大道侨易也可从这个层面去理解。再所谓“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中庸》)。这段话将几个二元关系都揭示出来:德性—问学,广大—精微,高明—中庸,温故—知新,敦厚—崇礼。这些二元维度对我们理解“道”之形成都很重要,但其基本立足点或在作为第三维的“中庸”。庞朴归纳了中庸之道的表现形式,其实可以简约为三种,即:A而B;A而不A;不A不B(亦A亦B)。③其本质,“A与B是对立的两个方面,形成某种对立的思想或状态。中庸的基本思想就是把对立统一起来。这也是辩证法的实质。辩证法是什么?是把那些常人看来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东西统一在一起,并指出他们统一的条件、统一的状态,说明统一的原因,这就是辩证法。实际上,‘中庸之道’就是这样一种思想”④。这可以说是中庸思想的最通俗简明而取其本质的解释,而更简明的解释张力或许就是“二元三维”。同样,我们要想深入理解,则必须把握其中二与三的关系。
孟子说:“君子反经而已矣。”(《孟子》第三十七章)按照庞朴的解释,“‘反经’就是回到常道上去,回到标准原则上来”⑤。这里的二,就主要表现为正—反之间的二元关系。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孟子》第三十七章)如果按照一分为三的原则,设置三个点的话,狂者为左(激进),狷者为右(保守),庸者为中(中庸),但这个中仍有困惑,并非所有的各种关系都是可以通过取中来解决问题的,那么这个中还可能不是中庸,而是乡愿。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第十七》,乡愿原作“乡原”)庞朴解释说:“乡愿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既反对狂,又反对狷。他装着好像达到中道的样子,实际上离中道最远。”⑥那么,居中者未必就是得道者,他是一种“伪中者”,或者叫作“中伪”。这是一个必须区分的维度。按照这样一种原则我们来看德国文化史中的思脉结构,二元三维的维度应该是这样的,启蒙思脉作为一元,浪漫思脉作为一元,看是否可能结出第三维的果来,第三维作为流力因素始终存在,就是处于两种大势力之间的东西,但是否能不断化生,在二元之间起到调和的平衡力作用,则很难说,后来歌德、席勒在魏玛的古典时代已经开出一种古典思脉的途径来,但终究未能形成长期的平衡性结构,很可惜。符合“A而不A”的表现形式,具体说来,“A指的是极端化的A。‘A而不A’就是说,处在A的状态,但是不要让它走向极端。趋极是事物的一种属性。任何事物如听任其发展,都有极端化的趋势。走到极端之后,如果继续下去,物极必反,就走到了自己的反面。为了避免事物走到极端而反向发展,应该提出一种‘A而不A’的中庸形式”⑦。面对启蒙问题,其实正好用此来作解,启蒙而不极端启蒙,是最重要的一个维度。但任何事物的发展惯性都是趋极,走向极端启蒙是非常正常的事物发展规律。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调控它。德国精英显然尚未能在这一层面认识这个问题,虽然如黑格尔已经发明出辩证法的利器,在方法论上技高一筹,但后来的哲人思想家似乎并未充分意识到二元三维的平衡结构意义,再加之场域运作的推力,使他们义无反顾地通向A的道路,这是一个非常无奈的事实。在下代人身上表现得则更为清楚。海涅已然深受启蒙路径的影响,而马克思更为下代精英之翘楚,他沿着黑格尔的道路前进并可谓集大成者。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由于场域惯性,他更将这种思想之争引入到现实的政治场域,使之终于在秩序层面展开了博弈竞存。在马克思早期生活的年代里,德国尚未统一,普鲁士仍在发展强权,所以作为同代精英,俾斯麦、马克思的出路迥然不同,这也就导致他们面对统治阶级的态度大相径庭。而追根溯源,与这种思想理念上的差异是密切相关的。
庸有三义,用、平常、大常。第一义:“庸者,用也”*庄子也说:“庸也者,用也”(《庄子·齐物论》),不过此处是指“不用之用”、“大用”。参见庞朴:《中国文化十一讲》,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22页。;第二义:平常,普通;第三义:大常,常道。“天降大常,以理人伦”(郭店楚简《成之闻之》),指某种绝对法则*参见庞朴:《中国文化十一讲》,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22-125页。。所以我们在关注道的元概念意义时,也绝对不能忽视“庸”的意义。对于欧洲语境来说,必须要处理的一个关系是“信仰与理性”,实际上,对莱辛这代人来说,这并不是太大的问题。有论者很明确地指出:
启蒙哲学家们对狭隘的信仰和权力的滥用做出的共同抵抗可谓不容小觑。如果只是简单地解构“启蒙运动”,结果必然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启蒙运动表现出的激进趋势,比如反帝国主义,往往被视为要么是一种历史变异,要么是这个或者那个思想家的个人兴趣。我们也很容易忘记,甚至在1789年以前,反启蒙的反对派哲人们就已经忙于“跨越与对手之间的鸿沟,与对手和解、联合,与他们达成共同的目标和结果。如果不是有点饶人的话,所谓是反启蒙发明了启蒙运动的说法中并不乏真知灼见”。*作者的引文自Darrin M. McMahaon, Enemies of the Enlightenment: The French Counter Enlightenment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32. 此处引自[美]斯蒂芬·埃里克·布隆纳(Bronner, Stephan Eric):《重申启蒙——论一种积极参与的政治》(Reclaiming the Enlightenment: Toward a Politics of Radical Engagement),殷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可见,启蒙诸子反对的也并非是简单的信仰(甚至权力)而已,而是“狭隘的信仰”与“权力的滥用”,也就是过犹不及的成分。任何事情都必须在一定的限止范围之内,否则必然难免“物极必反”。其实,很有趣的是,青年莱辛也从基督教本身思考问题,他甚至提出一个“理性基督教”(Das Christentum der Vernunft)的概念,在他看来:“上帝自永世以来便思考着自己的所有完美;这就是,上帝自永世以来便为自己创造一种不缺乏自己所拥有的任何完美的本质。”*Lessing, Das Christentum der Vernunft. Lessing: Werke, S. 4654 (vgl. Lessing-W Bd. 7, S. 278). 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band5.htm. 莱辛:《理性基督教》,见[德]莱辛:《历史与启示——莱辛神学文选》,朱雁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1页。这就接近“庸义”了,还是一种调和的思路,将启蒙理性与基督教经义相协调,使之接近某种普遍适用的法则。
不过,相比较具体的路径调和,我还是更看重莱辛在思维模式上的获得:“两种事物相互间共同之处愈多,它们之间的和谐便愈大。可见,最大的和谐必然存在于相互在一切方面一致的两个事物之间,即同为一个东西的两个事物之间。”*Lessing, Das Christentum der Vernunft. Lessing: Werke, S. 4655 (vgl. Lessing-W Bd. 7, S. 279). 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band5.htm. 莱辛:《理性基督教》,见[德]莱辛:《历史与启示——莱辛神学文选》,朱雁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2页。这个思路很关键,就是一与二的关系问题,以及“和谐”(Harmonie)自何而生,又以何种方式而存?这里的“取同求和”的思路自然让我们想起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论*具体思路是:众多单子经由连续性定律的规范,便使得构成世界的无数单子和谐地形成了一个整体。这种和谐秩序是由上帝(这是在无数单子之上的最高单子)安排的。上帝在创造每个单子时,预先规定了其本性,并规定它在以后的全部发展过程中自然地与其他单子的发展过程相一致。上帝这样创造出来的世界是许多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是预先确定的最为和谐的世界。这就是所谓“前定和谐”系统。据安文铸、关珠、张文珍编译:《莱布尼茨和中国》,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5-57页。,不过前者更近演绎,而莱辛则偏重归纳。莱辛严格区分“基督的宗教”(die Religion Christi)与“基督宗教”(die christliche Religion)的不同概念,强调“基督的宗教”的意义“是基督作为人本身所认识和实践的宗教;是每个人可以与基督共有的宗教;谁从作为纯然的人的基督身上得到的性格愈高尚、愈可爱,谁必然愈渴望与基督共有这种宗教”*Lessing, Die Religion Christi. Lessing: Werke, S. 4945 (vgl. Lessing-W Bd. 7, S. 711-712). 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band5.htm. 莱辛:《基督的宗教》,见[德]莱辛:《历史与启示——莱辛神学文选》,朱雁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295页。。莱辛在此处之所以区分这组概念,乃在还原基督作为人的身份,强调其乃人的常态行为,而非单纯的神的世界。其意义甚为重大,他是想在保全基督教的前提下使其成为“人间宗教”。信仰是必要的,但不能以绝对之神高高在上的方式出现,这或许也是其“适度启蒙”的一个策略。另一个核心观念的转变是“等级制”—“平等化”*关于欧洲在新教、天主教区域围绕这两个概念而形成的制度模式,参见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114-115页。,在“故代”中,等级制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它当然有其负面效应,但更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而在“现代”里,平等化显然是一个核心诉求,当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要求“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会转让自己的自由”*Jean-Jacques Rousseau (1762), DU CONTRA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 Dans le cadre de la collection: “Les classiques des sciences sociales”. http://www.uqac.uquebec.ca/zone30/Classiques_des_sciences_sociales/index.html.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6页。。然而,完全地将现有制度(传统)打倒在地,其实并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基本利益。或许比较能够接受的是,“人格平等,格物有级,社会制序”。一个社会的日常运作,必须有它内在的运作规则、运转秩序、社会结构,否则一切都会乱套。在人格意义上应当承认平等,但在现实社会的运作层面基本不太可能做到,所以就必须寻找到一套能抚慰人心灵的信仰安排,这样也才能维持一个社会的正常秩序,使得众生宁静、社会安定。
“对真理的追求比对真理的占有更重要”*⑤ 梅林(Franz Mehring)语,参见Lessing, Materialien zu Leben und Werk: Zeugnisse. Lessing: Werke, S. 236 (vgl. rororo-Lessing, S.155,S.155-156). 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band5.htm.,莱辛的这一基本思路,决定了他不可能走向极端化的自命真理握有者,但同时也不可能走向近乎中庸的中道寻求,而是一种以寻道者身份始终在求道路上的苦苦跋涉身影,但这更接近于现实场域的真实。莱辛的方案就是,留于启蒙思脉之内,但其维度在于方寸之间,用一个具体概念来表达即“适度启蒙”。这其中至少包含三层含义:其一基本定位在于启蒙,即是归属于启蒙思脉之中的;二是启蒙不能代表真理,所以不是一种绝对性的真理概念,那就必须与其他思脉进行互动,这首先应当是包容、直面乃至汲取;三是其回旋之力在于“适度”,即既意识到过犹不及,也警醒就此失去启蒙旗帜的倒退危险。适度启蒙也就意味着更立定于追求真理的基本定位。所以难怪梅林对莱辛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德国市民阶级的精神前卫斗士中,莱辛不是最具天才的,但却是最自由的、最真诚的,首先是最具有市民性的。”⑤诚哉斯言,若论诗性天才的挥洒自如,歌德、席勒都可当得其选,就文学话语的妙手天成而言,莱辛作品仍要稍逊一筹。但若论及在思想立场上的中庸自觉和实践贡献,则莱辛的贡献则大焉,而他开辟范式的意义更是后来者必须致敬的。
海涅曾借“拜伦之喻”说出了面对现代性时的不同观点,一位侯爵批评海涅说:“别扫我的兴!您压根儿就不懂得什么是纯真的自然感受。您是个破碎的人,有一个破碎的灵魂,这么说吧,您是一个拜伦。”*Heine, Reisebilder. Dritter Teil. Heine: Werke, S. 2251 (vgl. Heine-WuB Bd. 3, S. 286). 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band7.htm. 《卢卡浴场》(Die Bäder von Lucca),见[德]海涅:《海涅全集》第6卷,章国锋、胡其鼎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8页。海涅接着发表了这样一通高论:
亲爱的读者,或许你也是那些唱惯了拜伦的破碎之歌的虔诚小鸟中的一只?十年来,这支歌以五花八门的腔调在我耳边鸣响。正如你所听到的那样,它甚至在侯爵的脑袋里也引起了共鸣。唉,尊敬的读者,假如你想抱怨这破碎,还不如哀叹世界本身早已破碎了呢。由于诗人的心是世界的中心,它如今必定也可怜地破裂成碎片。谁若炫耀他的心依然完整,那无异于承认,他拥有的不过是一颗平庸、偏狭、封闭的心而已。无论如何,那条分裂世界的大裂缝正从我的心中穿过,因此我知道,伟大的神对我倍加恩宠,分外赞赏我那诗人的殉道精神。
在古代和中世纪,世界曾经是完整的,尽管外部纷争延绵不绝,但世界仍具有一种统一性,有完整的诗人。我们尊敬这些诗人,由衷地赞美他们,但对他们完整性的任何模仿都不过是谎言,一种明眼人立即能看穿的、注定要遭到嘲笑的谎言。*Heine, Reisebilder. Dritter Teil. Heine: Werke, S. 2251-2253 (vgl. Heine-WuB Bd. 3, S. 286). 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band7.htm. 《卢卡浴场》(Die Bäder von Lucca),见[德]海涅:《海涅全集》第6卷,章国锋、胡其鼎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8-119页。
这里实际上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就是诗人与时代的关系问题,还有诗人是否能超越其时代而独特存在的问题。如果说席勒那代人已经非常明确时代所给人性造成的极大损伤:“……如今已被一架精巧的钟表所代替,在那里无限众多但都没有生命的部分拼凑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个机械生活的整体。现在,国家与教会,法律与道德习俗都分裂开来了;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都彼此脱节。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只好把自己造就成一个碎片。他耳朵里听到的永远只是他推动的那个齿轮发出的单调乏味的嘈杂声,他永远不能发展他本质的和谐。他不是把人性印在他的天性上,而是仅仅变成他的职业和他的专门知识的标志。……死的字母代替了活的知解力,训练有素的记忆力所起的指导作用比天才和感受所起的作用更为可靠”*Schiller, Über die ä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 in einer Reihe von Briefen. Schiller: Werke, S. 4013 (vgl. Schiller-SW Bd. 5, S. 584). 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band103.htm. [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见冯至:《冯至全集》第11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7-38页。,那么黑格尔、蒂克、施莱格尔兄弟等人——就是从1770年前后出生的这代人来看——基本上就是在这种语境中成长起来的;再下一代如叔本华、兰克(1790年前后生人)等已经明显地不得不在此中挣扎求生,而海涅作为文学话语的主导者,则更不得不以身心之苦将席勒对现代性的洞察在实践层面加以表现,“碎片时代”是不可避免的命运,是任何一个大时代产生后不得不降临的悲哀结局。
如果说莱辛还在努力尝试这种信仰与理性之间的调试,那么席勒即便意识到现代性对知识精英的彻底束缚也只能通过“审美教育”来做精神上的抗争;而到了海涅这代人,已经命中注定地宣告了西方现代性的全面确立,知识精英虽然“有心杀贼”,但绝对是“无力回天”。然而莱辛毕竟留下了“教育”法宝,这个包涵了教养、修养、养成等精神意味的整体性概念,这不仅为德国人日后坚守精神自我提供了资源,其实也是属于人类整体的精神宝藏,否则为什么叫作“人类教育”呢?无论如何,向18世纪的现代思想之源回归,“重拾被遗弃的、断裂的思想线索”或许已是当下之要务。*Alfred Cobban, In Search of Humanity: The Role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60, p. 27.对于莱辛的思想史位置,我倾向于以下的判断:
莱辛始终都是启蒙运动最后一位伟大哲人、柏林的门德尔松的朋友,可是如果后来门德尔松将莱辛与雅柯比相比,自认为可以用莱辛来维护自己对斯宾诺莎所作的无害的神学诠释,他非常可能会彻底失望,因为,不论是否借助斯宾诺莎,莱辛早已稳稳地走在通向歌德之路的中途,他至少从带浓厚无神论色彩的观点将上帝理解为人类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内在原则。莱辛处处站在其同时代人行列的最前面,是他们最雄辩、最受敬重的代言人,但也处处准备超越其同时代人的典型立场。所以,人们只应从由此而决定的种种倾向的辩证关系中理解莱辛。*[瑞士]巴特:《论莱辛》,见[德]莱辛:《历史与启示——莱辛神学文选》,朱雁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301-302页。
这里对莱辛的高度评价倒在其次,将其放置在时代精神的精英光谱中的比较则确实有重大意义,而且其中非常关键的一个判断是莱辛—歌德之路,这是德国精神史的必然逻辑链条,也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德意志精神”薪火相传的香烟不断。就思想史而言,1750年前后生人的精英中没有出现启蒙思脉的集大成者,但这种意义在康德、莱辛那里已经有太辉煌的表现。在歌德那里,左承莱辛、康德,右继哈曼、赫尔德,虽有所拒让,但基本上很善于“博采众家”。莱辛的“适度启蒙观”必然导致歌德的“古典图镜观”,而其内在之追求“和谐”的路径则基本一致,甚至可以进一步上溯至莱布尼茨处,由“前定和谐”—“适度和谐”—“古典和谐”,和谐之路可谓一以贯之。但问题当然在于,最后的德国模式,并未走出和谐之路,而是一派山河沧桑的凄凉悲壮,其道理安在,值得追问,这且容日后深究。就德国精神的传统相继中的莱辛意义,尼采的这段话比较精辟:
即便是歌德的诗作,因把生硬和造作混为一体,也概莫能外,像是“古老美好时代”的一面镜子,它属于这个时代,而且作为德意志审美的表达方式,在尚存一种德意志审美的现时:因为,它是一种罗可可式的审美,在风情和艺术中。莱辛来了一个例外,这多亏了他那演员般的天性,他所知甚多,而且精通这许多:他,并非枉然地成了培尔的翻译者,而且乐于待在狄德罗和伏尔泰的身边,更愿意扎进古罗马的戏剧诗人堆里——莱辛也飞速爱起了自由精神的玩意儿,逃出了德国。但是,德语的作为如何,甚至在一个莱辛写的诗歌中也不得不效法马基雅弗利的速度,他以他自己的原则呼吸着来自佛罗伦萨的干燥而细腻的空气,而且不得不以一种放荡不羁的纯粹快乐来报告最郑重的事务:因为,也许离了某种恶毒的贵族情感就不行,他敢于揭露任何矛盾——思想,冗长、滞重、强硬、危险,而且是一种急驰速度和最佳而恶意的心境。*Friedrich Nietzsche, Werke und Briefe: Zweites Hauptstück. Der freie Geist. Friedrich Nietzsche: Werke, S. 6853-6854 (vgl. Nietzsche-W Bd. 2, S. 593-594). C. Hanser Verlag, 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band31.htm. [德]尼采:《超善恶》,张念东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37-38页。
应该说,对于时代发展造成的精神界代表人物的精神损伤,尼采是洞察秋毫的,他对前辈大贤的无情批评和精神认同并无内在之根本矛盾,因为诚如上述,上帝退位,小神登基,资本时代已经滚滚而来;人造物,尤其是从货币到资本的力量更将成为新的神祇,一个个体,即便再伟大,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抵御和坚守?要知道,“一个人只要有了闲暇时间,就不得不接受文化制造商提供给他的产品”*Band 3: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Kulturindustrie. Aufklärung als Massenbetrug. Theoder W.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S. 1323 (vgl. GS 3, S. 145). 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band97.htm. 《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见[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9页。。甚至,“整个世界都要通过文化工业的过滤”*Theoder W.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3: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Kulturindustrie. Aufklärung als Massenbetrug. S. 1326 (vgl. GS 3, S. 147). 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band97.htm. 《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见[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1页。。这里揭示出一个非常值得警醒的现象,就是人类是怎么被再造就的,或者说怎么通过被自己作为世界小神的力量造出的“物器”而重新制造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论者认为20世纪上半期“见证了宗教、道德和伦理原则与观念的教育、理解与实践的日渐衰落。贪于金钱与物质、意欲出人头地、妄想从政治经济上控制他人、生物与环境,这些已成为现代文明近年来发展的特性”。面对这样一种悲凉的世界现状,究竟该如何认识?“这一发展与平常的、正确的、合理的人性背道而驰。其结果是人类今天面临极大的破坏力。这力量如此强劲,以致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与心智虚弱者,无法应对他。相反,他们屈从于这力量。他们皈依于冷漠、无政府、毒品、酗酒以及其他行为,以获得肤浅的安宁感,但不能有任何长期实质的幸福。宗教、道德和伦理水准的衰落导致人类社会组织的衰弱。”*[英]H. 萨达提沙:《第二版序言》(1987年),见[英]哈玛拉瓦·萨达提沙(Saddhatissa, Hammalawa):《佛教伦理学》(Buddhist Ethics),姚治华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1页。问题在于,人类何以走到了这一步?作为宗教家,作者其实更想说的是,信仰的失落。而相比较信仰(尤其以宗教为支撑)的普遍衰逝,主导人类的是理性进步的逻各斯思维,也就是启蒙思脉的势力。可问题在于,为什么启蒙竟会走出如此的后招?中世纪确实有其宗教力量独大的问题,可一旦纠正,则物极必反,使得后世需承受极为沉重的代价,人之不知敬畏自然,是为大谬也。
所幸,人类有精英为灯塔。歌德、席勒所试图开辟的第三条道路,所谓“古典图镜”,其实早在启蒙时代就已开启端绪了,作为启蒙旗手的莱辛,已经明确意识到反信仰或启蒙的正面意义及其反作用力,并努力地“补偏救弊”,而对理性与信仰这两大路径的调和,其本质不外乎逻各斯—秘索思之间的调和,“向中靠”是一种可行的策略,但这又绝非是简单的“骑墙”或“和稀泥”,所以“适度启蒙”的标示仍表现出莱辛的基本立场,而“人类教育”方案的选择则显示了他脚踏实地的探索姿态,更体现出他所选择的中庸之道的具体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