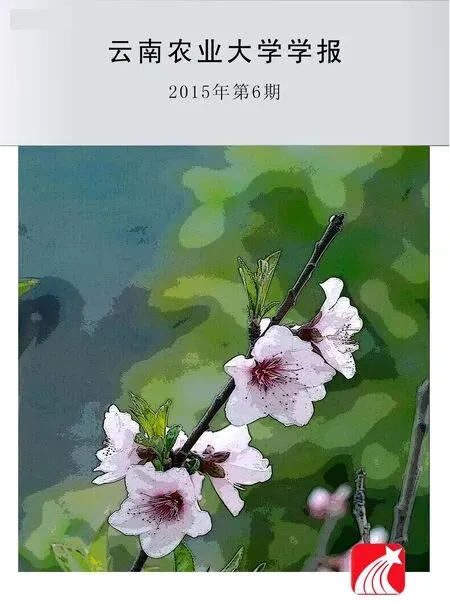返影入深林:女性社会性别的多元建构与实践
——基于永宁摩梭人女性社会性别建构的分析
许瑞娟
(1.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士后流动站,云南昆明650031;2.云南民族大学东南亚学院,云南昆明650031)
返影入深林:女性社会性别的多元建构与实践
——基于永宁摩梭人女性社会性别建构的分析
许瑞娟1,2
(1.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士后流动站,云南昆明650031;2.云南民族大学东南亚学院,云南昆明650031)
性别观念是镶嵌在社会整体文化中的有机部分,它与传统、习俗、语言、宗教等文化事项紧密联系在一起,是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永宁摩梭人对女性性别的多元建构为我们研究女性性别建构提供了一个独特的、难得的个案。从空间分类、语言基础、亲属隐喻、宗教影响的多元视角与多重维度把女性性别建构放在整体文化脉络中了解与把握,试图为世界女性性别建构提供一份独特的民族志资料,为民族学家、人类学家进行跨文化的性别研究与比较提供一个与 “常识”相悖的独特案例。
女性社会性别;空间分类;语言基础;亲属隐喻;宗教影响
性别研究是当代人类学最活泼、最具开创性的领域之一,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作为人类最基本的认知范畴之一,各个民族 (族群)对性别有着不同的情感认知,体现了文化分类与价值观的差异。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认为性别具有相当大的可塑性。人类学家罗伯特·墨菲提及:“在某些社会里,妇女可以占据宗教职位但在其他社会却绝不可能;在某些社会里,妇女是独立的、十分自信的,而在另一些社会里她们就不得不保持谦卑和端庄,不过,即使在妇女声望低下的地方,也有补偿的机制。在许多群体中,妇女在老年时得到较之从前更高的地位;在另一些群体,妇女们 ‘垂帘听政’,通过丈夫和儿子施加影响”[1]。有学者指出:“生物决定论者认为男尊女卑是与生俱来的天经地义。但近二十年的性别论述提醒我们,社会性别只是一场竭力伪装出来的化妆舞会,每个人自出娘胎起就每天被 ‘化妆’,所谓 ‘男’与 ‘女’的性别本质,只是特定历史时空的建构过程。社会性别并非只有男、女两种,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性别”[2]。性别的建构与实践反映了不同文化体系对两性分工与社会地位的规范,由此衍生的性别隐喻则体现了不同文化建构与实践的差异。社会性别观念的形成固然有生理基础,但更多是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
摩梭人是分布在中国西南部川滇交界以泸沽湖为核心区域的一个族群,摩梭人独具特色的母系家庭结构、两性异居走访制度与尊母崇女的伦理道德观念构筑了摩梭文化的独特性。独特的文化特质,使摩梭人自进入公众视野起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关于摩梭人的社会性别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关注的热点领域,不同时期、不同学者呈现出不同的研究旨趣与学术关怀,研究成果一时蔚然成风,研究结论却莫衷一是。蔡华认为摩梭社会的性别建构基于 “社会血亲性排斥 (血缘关系和血亲之间的性禁忌)”的约束机制[3]。施传刚认为摩梭个案在文化性别方面的独特性是女性在传统文化中的中心地位[4]。翁乃群则把摩梭社会性别的文化结构体系概括为 “女源男流”[5]。周华山指出摩梭社会的性别结构是 “重女不轻男、褒女不贬男”的两性平等、互补互助、阴阳相谐[6]。和钟华认为摩梭母系家庭的性别分工有 “男主外女主内”的特点,但由这种分工所形成的对两性角色的规定并没有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的社会内容[7]。近年来有学者研究旅游的发展对摩梭地区社会性别关系的影响,认为受旅游的冲击与影响,摩梭男性性别意识崛起,而女性则面临社会地位丧失的困境[8]。面对众说纷纭的结论,最接近摩梭文化真实的究竟是什么?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是本文进行探讨的初衷。
长期以来,文化人类学界普遍认为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处于屈从地位。伊文斯·普里查德在田野观察的基础上做出论断:“几乎在所有的社会制度中,无论这些社会属于什么结构,男性都处于优势的地位”[9]。唐纳德·布朗在概括文化的基本特征时也宣称:“在公共政治领域,男性普遍处于主导地位”[10]。性别观念是镶嵌在社会整体文化中的有机部分,它与传统、习俗、语言、宗教等文化事项紧密联系在一起,是社会文化造就的结果。“男性的主导地位是否真的具有普遍性?性别不平等是否真的普遍存在?导致两性在权力和地位方面差异的具体原因是什么?”[11]摩梭社会关于女性性别的文化建构与实践或许可以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提供一个难得的、独特的视角。社会性别研究应该置于多维度的研究范畴中,而不只是聚焦于单一的某一方面。唐代大诗人王维有一首诗 《鹿寨》:“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整首诗创造了一种幽暗而光明的象征性境界,表现了作者在幽深的修禅过程中豁然开朗的心境。本文通过对摩梭社会女性性别进行多维度的分析与研究,试图对女性社会性别建构与实践有一个豁然明朗的认识。
一、女性性别建构的空间分类
空间在人类学中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它赋予人类认同感、关系性及历史性。通过社会空间的建构,不仅可以确认自己的出身,还能置身于以亲族为主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而共享共同的历史记忆。人们对生活空间的分类隐含着其所处社会的文化想象与习惯准则。从人类学的角度对空间向度进行研究,通过观察社会群体对居住空间的配置与安排,可以揭示出该社会的性别观念与文化秩序。
家屋是摩梭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单位,是摩梭人身份认同的重要标识,摩梭人对家屋空间的分配体现了摩梭文化独特的性别建构。摩梭家屋设计以正房为中心辐射至四周,呈一个规矩的“回”字型。正房是全家人活动的中心,尤其是女性活动的重要场所。摩梭家屋中老祖母的生活起居、女性操办厨事、供奉祖先、生育孩子都在正房里进行。而男性很多时候处于 “游离”与“边缘化”的状态,他们白天在外赶马划船、跑车经商,夜晚 “走婚”至“阿夏”家,基本上只有三餐的时间才留在家屋。按照摩梭社会的传统,男性成年后夜晚 “走婚”至别家,天亮后才能返回自己家中,除非他是一个喇嘛,可以住在家屋的经堂里,否则在家屋中没有独立的房间,如果“走婚”途中不幸遭遇冷落,那么只有在草料上或与年迈的舅舅挤着度过一夜。女性则不同,她们作为延续母系家庭的关键人物,每当夜晚来临时,可以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待着心上人的来访,享受着私密与舒适的种种好处。年老后,女性成为家屋的核心人物,受到全家人的尊敬与爱戴,生活在正房里直至过世,男性成为家屋成员尊敬的长辈,终于在正房的外层——上室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房屋空间的占有与使用体现出家庭内部权力的大小与两性社会地位的高低,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化规则与性别文化观念”[12]。摩梭人对家屋空间的分配与使用凸显了摩梭社会 “以女性为中心”的性别意识。
美国人类学家罗撒尓多建议从 “家户领域”和 “公众领域”的二元对立结构来探讨社会性别问题[13]。在大多数社会中,男人侧重公众领域,女人偏重家户内部。摩梭社会则不一样,摩梭文化强调以家屋为核心,家屋把原本属于公众领域的行为,如每日三餐前的祭祖、达巴举行法事活动、喇嘛念经祈福等都内化于家屋中。 “摩梭社会缺乏公众领域的社会角色,摩梭女人的社会可为性就是扮演好母亲的角色,摩梭男人的社会可为性就是扮演儿子的角色。因此,摩梭社会的性别观念即 ‘女人为母,男人为子’”[14]。人类学家布迪厄曾以 “上:下”、 “外:内”、 “亮:暗”、“男人:女人”等二元概念描述卡比尔人家屋的空间划分与象征意义[15]。无独有偶,摩梭人对家屋空间的分类也有着独特的象征隐喻意义。女性在正房的活动区域主要靠近前室一侧,祖母的卧床也位于靠近前室门的位置,而男性主要在靠近后室的一侧活动。女性在正房里靠近前室门的台沿下进行分娩,男性必须回避。如果家屋有成员离世,尸体摆放于后室,包裹尸体由男性完成,女性必须回避。摩梭人对家屋空间的配置与使用构建了 “前:后”、“光明:黑暗”、“生命:死亡”、“女人:男人”的二元隐喻观,女性占有靠近前室门的空间,她们生育后代为家屋增添生命与活力,带来光明与希望。男性在靠近后室的空间活动,后室是家庭成员生命结束后的暂时安息之所,是黑暗的象征。女性通过生育给予一个新生命周期以开始,直面出生的喜悦,男性通过料理丧事来终结一个生命周期,直面死别的悲痛[16],折射了摩梭文化在女性性别建构中蕴含的独特的象征意义。
二、女性性别建构的语言基础
语言与社会性别建构有密切的关系。语言反映社会文化,性别关系会在日常语言表达中得到呈现,同时,“作为一种文化要素,语言参与性别分工的建构”[17]。
摩梭语中有一个独特的词汇 “mi33”,不仅在语言使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充分显现了特定的文化内涵。作为单音节词,“mi33”指称人类最伟大的女性——母亲;冠于其他女性称谓后是女性性别的通称义;用于动物名称后既是雌性动物的标识,也表示 “成群、繁殖能力强”的附加意义;用于自然景物、鬼神名称后是原始崇拜的表征;用于某些名词后表示 “大的、主要的、首要的”引申意义。动物与人类有着相同的性别区分,因此用 “母亲”的性别代表 “女性”和 “雌性动物”的性别。动物的特点是繁殖能力强,它们与母亲之间有着某种相似性,将母亲繁衍后代并且子女众多与动物成群、繁殖能力强进行类比,体现了摩梭先民的认知思维和造词理据。摩梭先民在认识水平低下及生产力极度落后的情况下,对不能解释或理解的自然万物持有一种敬畏心理,从而产生了 “万物有灵”的原始崇拜。 “母亲”作为最伟大和神圣的女性,不仅繁衍、养育了后代,当先民们面对客观世界的无常与恐惧时,只有 “母亲”是精神情感的最大寄托,母亲因此被赋予神性并受到顶礼膜拜。这种原始的宗教信仰反映在语言中,表现为在自然山川、鬼神等名词后冠以 “mi33”。对女性尤其是对母亲的尊崇是摩梭文化的核心内涵。母亲不仅在养育后代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且还是家庭的重心与支撑,母亲常被视为伟大的象征,摩梭人尊敬母亲进而尊奉女性,这种文化实践反映在语言中凸显了摩梭社会对女性主体地位的认同。
语言本身是无阶级性的,任何一种语言可为不同阶级、性别、年龄的人所使用,但语言反过来折射了使用者的文化意识形态,某种文化对男女两性地位的建构,会在语言中留下深刻的印迹。随着父系社会的发展与强盛,语言中无不显露出对女性的歧视,与母亲和女性有关的词汇在语义的演变发展过程中都出现了 “贬降”,反映了父系社会女性地位低下、男性居于主导地位的传统。而摩梭社会对母亲与女性的尊崇一直延续至今,“尊母崇母”是摩梭文化最重要的伦理准则,母系大家庭的构建与延续离不开母亲,母亲在大家庭中享有最高的威望,受到特别的尊崇和爱戴。尊母、敬母、恋母,成为摩梭社会的一种集体潜意识,是一种道德伦理风尚的内在延伸。摩梭社会歌颂母亲的民谣、谚语、习语数量之多,充分体现了摩梭人对母亲的深厚感情与尊崇心理,让人强烈感受到 “母亲”在摩梭人心目中的崇高与伟大。
摩梭人 “尊母崇女”的民族心理与以 “父权制”为中心的主流社会有很大的不同。主流社会对尊敬母亲的行为大力宣扬与赞赏,但在其文化中却有意或无意地传达出歧视女性的信息,尽管母亲也是女性。主流社会的文化实践与性别建构不时地透露了这样的信息:尊重自己的母亲但不一定尊敬别人的母亲,甚至要想辱骂一个人可以通过辱骂其母亲而达到最佳的泄愤效果。而摩梭社会对母亲的尊敬已经泛化成为一种优良的社会风尚,摩梭人除了尊敬自己的母亲之外,但凡与自己母亲年龄相当或比自己母亲年长的女性都受到尊敬。值得一提的是,摩梭语中找不到任何一个辱骂母亲或以母亲的生殖器官以及性隐私作为攻击对象的词汇[18]。摩梭语中也没有 “处女”、“贞节”、“寡妇”、“未婚妈妈”、“剩女”等在主流社会中以 “男性中心”为基点来评判、衡量女性的词汇。
“许多文化中都普遍存在 ‘月经禁忌’之类的话语,将女性排斥在神圣的祭祀仪式之外,女性的月经成为各种文化中压抑女性的关键”[17]。摩梭语称月经为 “ma31ʂu31ɡv31”,字面意思是“不方便”,并非人类学家指出的 “女人不净是因为月经,月经不洁是因为从生殖器官中流出,生殖器官是不洁净的”[19]。女性经期血流出体外引起不便,摩梭社会并没有主流社会 “女人与月经不洁”的忌讳。摩梭人通过母语实践展现了摩梭社会在建构女性主体地位时所体现的文化逻辑。
三、女性性别建构的亲属隐喻
早期人类学对亲属关系的研究忽视了社会性别关系。因此,女性主义人类学强调: “社会性别视角是分析亲属关系的一个重要工具,亲属关系是社会性别分析的主要内容,不应该把社会性别和亲属关系看作是两个相互分离的研究范畴”[20]。
“每一种文化中的亲属制度都是高度个性化的,是各个文化特有的、具有历时稳定性的文化价值、社会关系和性别观念的集中体现”[21]。摩梭亲属称谓体系有其独特的特点:整个体系中除了 “夫”、 “妻”、 “伯/叔”外没有对姻亲的称谓;整个体系中除了 “父”、“伯/叔”外没有对父系亲属的称谓;对上一辈和上两辈的亲属区分性别,但对上三辈的亲属不区分性别;对与自我一辈并且比自我年长的亲属不区分性别,但对与自我一辈并且比自我年幼的亲属则要区分性别;不区分直系和旁系亲属,即不区分母之母和母之母之姐或妹,不区分母和母之姐或妹,也不区分兄弟姐妹和母之姐或妹之子女等;下一辈中 “女儿”和 “儿子”这两个称谓只适用于女性自我或正式结婚的男性自我;下一辈中的 “甥女”和“甥男”这两个称谓只适用于没有正式结婚的男性自我使用;“父亲”的称谓一般不用作直接称谓,大多数情况下只用作间接称谓或只用于表明亲属位置,除此以外对比自我年长的所有其他亲属的称谓都可以用作直接称谓。
尽管绝大多数的摩梭人都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但在摩梭社会中,生父与子女间并不一定存在彼此的责任与义务等社会关系以及文化为其定义的社会行为准则。“从跨文化的角度考察,‘父亲’的概念可以包含下列三种角色中的一种或多种:(1)自我的生父,或由各文化定义的生物意义上的父亲;(2)自我在上一辈中的主要抚育者和男性楷模;(3)母亲的配偶。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要求三种角色必须集于一身”[21]。摩梭社会中,“父亲”所包含的实际语义更多指的是生物意义上的父亲。而 “自我在上一辈中的主要抚育者和男性楷模”主要是由母亲的兄或弟,即“舅舅”来充当。严格来说,只有生父和亲子女在一个家屋中共同生活时,父亲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及其责任、义务才存在,而这种情形在摩梭家屋中不是规范只是例外。摩梭人有一句谚语:“天上不下雨,地上不长草”。谚语有着独特的隐喻含义:“父亲碰巧是在那个特殊时候让母亲怀孕的人,但他的角色可以由其他适合的男子来扮演。父亲不像母亲,母亲与孩子通过脐带紧密相连,而父亲与孩子之间从来没有任何物质纽带。在摩梭人的观念中,生母对孩子来说是命中注定的、无可取代的,而生父则是偶然出现的、可以替换的”[21]。
另外,对比自我年长的母系亲属称谓,都可以用来称呼年龄相当的非亲属,而对比自我年幼的母系亲属称谓,则没有这种用法。原因在于比自我年幼的母系亲属称谓一般只用于间接称谓或指称亲属位置而不用作称呼。“这一使用规则表明在社会交往中,上段的亲属称谓实际是被当做尊称来使用。这反映出年长者在摩梭社会中被当做维护和谐与凝聚力的重要因素,也显示了摩梭社会的社会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轴心的。用亲属称谓来称呼非亲属的这种想象用法完全弥补了摩梭亲属制中缺乏对非继嗣集团亲属之不足,实际上把非继嗣集团亲属称谓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社会”[21]。“母亲”称谓已经提升为摩梭人整体文化的核心符号,一种集体潜意识,不仅代表着对妇女主体与地位的肯定,更是一种以感情和谐、家族团结、敬老爱幼为本的思想模式与价值观[16]。
摩梭人认为只有与母亲有着同样血缘关系的人才是最亲近、最可信的,要实现并维护家屋的和睦,最自然、最合适的方式就是和那些与母亲有同样血缘的人组成家屋。按照这一准则,摩梭人的继嗣是通过母系血统来进行的,家屋的成员是由有母系血缘关系的一群人组成,两性的伴侣都来自自己的家屋之外。反映在亲属称谓中就表现为强调母系称谓,忽略父系和姻亲称谓。由此可见,社会性别和亲属关系都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摩梭社会 “母尊女贵”的文化传统规范了其亲属制度,这种亲属制度又折射了摩梭社会对女性性别的独特建构。
四、女性性别建构的宗教影响
宗教信仰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意识[22]。宗教信仰的广泛影响必然会参与到社会性别的建构过程中。
女神崇拜为我们研究摩梭社会女性性别建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传说泸沽湖畔的格姆山是女神的化身,摩梭人世世代代敬颂尊奉着她,称之为格姆女神。格姆女神是众山神之首,周围的男山神都归她管辖。格姆女神非常漂亮,外出时骑着白色的骏马,十分威风。她自己也过着走婚生活,有 “瓦如普那”男山神 (在四川盐源境内)作为长期阿夏,还与永宁境内的 “瓦哈”、“则枝”、“阿沙”等男山神结交临时阿夏。格姆女神不仅主管着永宁地区人口的兴衰、农业的丰歉、牲畜的增减,而且还影响着妇女们身体的健康与生育。因此,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摩梭人都举行隆重而热烈的朝拜格姆女神活动,祈求女神保佑人口兴旺、农业丰收、牲畜发展、百事顺昌,这个节日被称为 “转山节”[23]。在摩梭人的宗教信仰和节日仪式中,女性被赋予了女神的角色,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
传说中的格姆女神最先是人的化身,她起初是人世间一个聪明美丽的姑娘,而后摩梭人将其神化,死后灵魂变成了女神,接下来又将女神人格化,说格姆女神有许多男神阿夏,成为摩梭人心目中最美丽多情、最聪明智慧、最富有魅力的爱与美之神。传说影响了摩梭人的伦理道德观,崇拜女神的宗教信仰进而形成了尊奉女性、爱戴妇女的民族心理,女神作为摩梭文化最高守护神的地位延续至今[16]。“宗教信仰与女性社会性别建构的关系极为微妙,它不仅积极地参与到女性社会性别角色的建构中,还在某些方面强化了女性的性别角色特征”[22]。摩梭人把女神崇拜与民俗节日结合在一起,这种凸显女性角色的宗教信仰与民风成为摩梭社会 “尊女崇女”性别建构的一个主要方面。格姆女神的传说成为摩梭人母系大家庭和两性走访制得以维护和巩固的因素之一。
“文化性别不仅仅体现在社会制度和社会实践中,它同时也体现在人们的观念和信仰中,世代相传的神话传说和宗教信仰透露着人们对宇宙和自身的终极认识”[24]。摩梭文化女性优势 (female superior)的观念深深植根于创世神话中。神话隐喻了很多信息,其中有一点尤为重要,妇女不仅是人类的始祖母,而且是智慧和力量的源泉,是远古时代摩梭先民的组织者和管理者。首先,女子在精神上比男子更强大,在智力上比男子更聪明。面对一桩桩看上去难以完成的考验,男始祖曹直路衣衣总感到一筹莫展,而女始祖柴红吉吉米却智计百出,总能轻松化解困难。其次,女子在心理上也比男子更加坚强。曹直路衣衣在每次考验面前都手足无措,轻易就打退堂鼓,而柴红吉吉米却总能保持冷静,沉着应对。正因为她的不屈不挠,困难才能一一被克服。第三,是女性而非男性,带给了人类生存的基本工具和技术。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不仅是人类的始祖,而且也是摩梭社会的重建者。摩梭人的 《创世纪》神话故事,反映了女性在摩梭社会中的崇高地位,体现了摩梭社会文化对女性的强调与重视。
五、结束语
在摩梭传统文化中,女性处于整个文化的中心位置。虽然几个世纪以来,藏族和汉族文化对摩梭人有很大影响,但这种以女性为中心的观念在摩梭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仍然清晰可见[16]。透过摩梭人对居住空间的配置与安排,揭示了其背后蕴藏的 “尊母崇女”、“女留男走”的文化规则与性别建构。摩梭人的亲属制度强调母系亲属,极度缺乏父系称谓和姻亲称谓,解释了摩梭文化对女性地位与性别意识的强调与凸显。“语言体现着一个民族 (族群)对世界的分类与组织,适从于该民族 (族群)文化的需要”[1]。摩梭语对“母亲与女性”的语义隐喻与褒扬反映了摩梭文化在女性性别建构方面的独特性。摩梭人的信仰和宗教仪式中,女性被赋予了女神的角色,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同时被赋予了母祖的角色,为家屋成员所敬重,她们还以母亲和姐妹的身份,通过生育诞生新生命以开始一个生命周期,并将新生命抚养成人,为家屋的繁衍生息作出了最大贡献,因此受到最多的尊敬与爱戴。与妇女不同,男子则被赋予了后裔的角色,他们以儿子或兄弟的身份,通过在葬礼中的送魂仪式将死者灵魂送回祖源地来终结一个生命周期。这种 “女本男末”的文化建构诠释了摩梭社会对女性性别的终极认识。
本文基于对摩梭社会女性性别建构的分析研究,试图为世界女性性别建构提供一份独特的民族志资料,为民族学家、人类学家进行跨文化的性别研究与比较提供一个与 “常识”相悖的独特案例。长久以来,性别研究一直难以摆脱 “公共与家庭、自然与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等一系列以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和结构来阐述文化性别差异的限阈[25],忽视了性别研究的多元建构与多维视角,本文恰是对此进行的一次有益尝试与探讨。只有当我们运用多元的视角和思维来审视研究对象的时候,才能更接近事物的本质与真相。
[1]罗伯特·F·墨菲.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83-84.
[2]周华山.子宫文化 [M].香港:香港同志出版社,2003:38.
[3]Cai Hua.A society without fathers or husbands:the Na of China[M].USA New York:Zone books,2001:37-38.
[4](美)施传刚.永宁摩梭[M].刘永青,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4.
[5]翁乃群.女源男流:从象征意义论川滇边境纳日文化中社会性别的结构体系[J].民族研究,1996(4):46-53.
[6]周华山.无父无夫的国度 [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16.
[7]和钟华.生存和文化的选择——摩梭母系制及其现代变迁[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7.
[8]杨丽娥.论摩梭母系文化的变迁 [J].思想战线,2005(6):79-82.
[9]Evans-pritchard E E.The Position of Women in Primitives Societies and other Essays in Social Anthropdogy[C]//Eugenics Review.London:Faber and Faber Ltd,1965:125.
[10]Donald Brown.Human universals[M].New York:McGraw-Hill,1991:113.
[11]特德·C·卢埃林.妇女与权力[J].何国强,张婧璞,译.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93.
[12]许瑞娟.摩梭家屋空间建构的隐喻象征意义解析[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49-54.
[13]Rosaldo,Michelle Z.Woman,Culture and Society:A Theoretical Overview[M]//Michelle Z.Rosaldo,Louise Lamphere.Woman,Culture and Society.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17-43.
[14]翁乃群.女人为母,男人为子——纳日人的人观[M]//王铭铭.中国人类学评论:第6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84.
[15]Bourdieu Pierre.The logic of practice[M].Cambridge,UK:Polity Press,1990:88-89.
[16]许瑞娟.摩梭母系文化词群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2013:224.
[17]沈海英,沈海梅.社会性别的语言建构——基于云南三个少数民族社会的分析 [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37-43.
[18]袁焱,许瑞娟.永宁摩梭詈语的文化阐释[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32-36.
[19]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M].黄剑波,卢忱,柳博赟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7-13.
[20]白志红.女性主义人类学视野下的亲属关系研究[J].云南社会科学,2004(4):84-88.
[21](美)施传刚.摩梭亲属制的人类学价值 [M]//瞿明安,施传刚.多样性与变迁:婚姻家庭的跨文化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9,15,17.
[22]侯艳娜,李凤缓,孙鑫煜.民间宗教文化与女性社会性别的建构——以河北涉县女娲信仰为例 [J].河北学刊,2011(6):225-228.
[23]陈烈,秦振新.云南摩梭人民间文学集成 [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0:469.
[24]施传刚.西王母及中国女神崇拜的人类学意义[J].青海社会科学,2011(1):119-124.
[25]白志红.女性主义人类学对二元论的挑战——跨文化妇女地位研究[J].云南社会科学,2003(5):74-78.
M ulti-Construction of Female Gender:Analysis of M osuo People Based on Female Gender Construction
XU Ruijuan1,2
(1.Postdoctoral Station of Ethnology,Yunnan Minzu University,Kunming 650031,China;2.China School of Southeast Asia,Yunnan Minzu University,Kunming 650031,China)
Gender concept is an organic partof thewhole culture,which i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traditional,custom,language,religion and other culturalmatters.It is the result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Multi-construction of female gender of the Mosuo people provides a unique,rare case for us to study the construction of female gender.This paper is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female gender construction in the whole cultural contex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classification,language foundation,kinship metaphor,religious effect and multiple dimensions,trying to provide a unique national history of the world′s women′s gender construction,and to provide a unique case of“common sense”that is a unique case of cross cultural gender research and comparison.
female gender;spatial classification;language foundation;kinship metaphor;religion effect
C 91;C 95
A
1004-390X(2015)06-0063-06
10.3969/j.issn.1004-390X(s).2015.06.012
2015-09-19
2015-10-20
时间:2015-11-25 9:13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文化多样性与构建和谐世界研究”(12AZD006)。
许瑞娟 (1983—),女,云南昆明人,讲师,博士,博士后在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53.1044.S.20151125.0913.02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