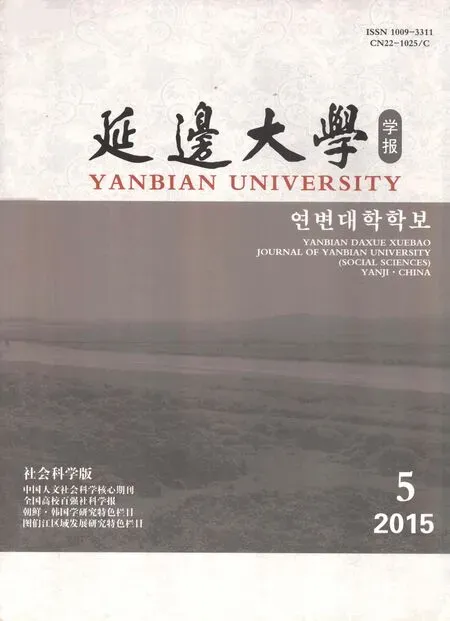论德川幕府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
张 波
(延边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吉林 延吉 133002)
论德川幕府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
张波
(延边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吉林 延吉 133002)
自然经济是幕藩体制的生存基础,商品经济是幕藩体制的天敌。然而江户时代中后期,以大阪、江户、京都为代表的大都市和大量的城下町得以空前发展,都市消费的需求促使商品经济得以迅速发展。首先发展起来的是满足幕藩领主需求的领主商品经济,它是幕藩体制赖以支撑的基础,但是它的发展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商品经济发展,即农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农村的传统生产关系受到了挑战,进而产生了新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瓦解幕藩体制的温床。
领主商品经济;农民商品经济;幕藩体制
以幕府和藩主共同占有领地、以石高制为基础的自然经济是德川幕藩体制建立的经济基础,只有建立在以本百姓为根基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才能保证幕藩体制下各种政策的实施,如将军与大名、大名与家臣团之间通过“御恩”主从关系的确立,领主与农民关系等的确立,都依赖于自然经济的确立和发展。作为与自然经济相对立的商品经济则是幕藩体制的天敌,是幕藩体制的腐化剂。然而江户时代的中后期,商品经济以不可阻挡之势发展起来。
一、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性
幕藩体制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但该体制自身却存在着矛盾性,一方面排斥商品经济,另一方面又必须依赖商品经济。导致这种依赖性的主要原因在于石高制和年贡米制的实施。由于大名、家臣及武士都以领取年贡米作为自己的俸禄,但是他们为了获取生活中除米以外其他必需品及购买军事备品,就必须将年贡米卖掉。而士农工商的四民等级秩序又迫使他们无法自己从事卖米等商业活动,因此他们必须将年贡米交给商人,换取货币,商业活动和商品经济成为幕藩体制下不可缺少的要素。日本学者伊东多三郎指出:“幕藩体制下的商品经济不是与封建制度相对立,而是作为封建制度成立的必要条件成长于封建制度的胎内。其发达的原因,不是对外贸易的关系,而是由整个国内的情况决定的。”[1]因此,从幕藩体制建立之初,就已经具备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市场条件。
首先,作为全国中央市场的大阪市场的形成,并成为商品交换的中心和集散地。大阪经过庆长十九年(1614年)到元和元年(1615年)间的冬、夏大阪之战,城市被破坏,町人四处流散。但是当年从伊势龟山入封到大阪的松平忠明开始复兴城市建设,将离散的町人聚拢到大阪城的三丸地,幕府以此为契机,将大阪作为直辖都市建立起完备的支配组织。到了家光时代,宽永十一年(1634年),免除大阪三乡(即北组、南组、天满组)11183多石的地子银来繁荣大阪。从元和到宽永年间一个崭新的大阪被建立起来,成为全国中央市场;以大阪市场为媒介连结周边诸大名的城下町市场,形成了一个全国市场体系。由于大阪是全国商品疏散基地,因此号称“天下的厨房”。元禄二年(1689年)大阪拥有人口33万,由于全国物资集散,经营这些物资的商户数量,正德年间,问屋5655家(轩)、仲间8765家(轩)、其他的商业2343家(轩)、职工9983家(轩)、城代付用达(供应商)481家、藩用达(供应商)483家。[2]因此,大阪以输入原材料、输出油、绵制品等手工业制品为主要内容的全国商品集散地的中央市场成立了。由于大阪市场是为满足幕府官方的需要并由幕府扶持而出现的,因此具有独特性:第一,它是使诸侯的年贡米交换成货币的场所;第二,它是最大的政治都市江户庞大的日常消费必需品集散地;第三,大阪的市场构造是以与幕藩体制下的社会相适应的领主封建地租的贩卖市场为中心形成的,这个市场成为周边腹地生产物的集散地。[3]
其次,以江户、京都等为代表的大都市和大量的城下町的显著发达,都市消费生活的必要性,使商人活动和商品经济发展成为可能。相对于大阪的“天下的厨房”,江户被称为“天下的城下町”、“大江户八百八町”等。江户作为幕府政权所在中心地蓬勃发展起来,特别是参觐交代制度化,诸大名及家臣团长期居住在江户,使其发展成为巨大的消费都市。18世纪初的江户人口已达到100万,成为世界上第一大都市。如果说大阪人口绝大数是商人的话,江户的人口约半数以上是武士,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2]以纺织技术著名的京都人口也超过50多万,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重要都市。另外,金泽、长崎、名古屋、堺等都市人口都达到6万多,1万人左右的城市达50多个,这些城市的规模与当时欧洲城市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百万人口的江户已经超过欧洲最大城市。城下町的发展也不容忽视。由于幕府颁布“一国一城”令和武士、町人都聚居城下町,因此各藩国都致力于建设自己的城下町,这既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也是提高军事防御能力的需要,同时也是藩主炫耀自己实力的需要,城下町得到讯速发展。
总之,在幕藩领主的主观需求下,在以大阪为中心的市场带动下,商品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而这一时期的商品经济被称为是领主商品经济,它是幕藩体制赖以存在的支撑,是幕藩领主生活的必然要求。但是,在领主商品经济的带动下,农民商品经济的发展成为幕藩体制的掘墓人。因此,江户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领主商品经济和农民商品经济两个阶段。
二、领主商品经济的发展
领主商品经济是指以大阪、江户、京都为中心的代表领主经济的都市商品经济,它是以维持领主生活甚至是奢侈生活及幕府和藩政府工作的正常运转为目的,交换的实体不是以交换为目的而是作为税收生产的粮食。即在领主商品经济中,农民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纳税,农民无法决定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如何处理,无论是作为使用价值消费品消耗掉,还是作为商品投放到市场,都由领主来决定。而领主所进行交换的商品是以石高制为基础获得的年贡米,也就是他们一年内所获得的薪俸,不是用来交换生产的产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商品经济要求“物品生产出来不仅是为了供生产者使用,而且也是为了交换的目的,就是说,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使用价值来生产的”。[4]因此,领主商品经济仅仅是流通领域的商品经济,不能算是完整意义的商品经济,它是应幕藩体制本身的需要而产生的。
在幕藩领主的保护下,领主商品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不仅出现了大阪、江户、京都等大都市,而且都市内商业机构林立,商业发达,专业商人与日俱增。正德年间,大阪有批发商5655人,经纪人8765人。[5]与此同时特权商人也得到了较大发展,“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初,出现了许多特权商人的行会组织,仅大阪一地就有100多个”。[6]特权商人不但控制了城市经济,还控制了城市周围的商品生产和流通,如大阪商人就控制了大阪周围的棉花和菜种生产,他们与生产者签订合同,依靠地方官吏强制性地向农民征收农产品。[7]到公元18世纪下半叶的时候,日本已有200多家商业组织的资产总值超过了20万两黄金。因此,此时商人已经完全可以在经济上和大名分庭抗礼了。日本许多现代的商业和金融大企业都可以追溯到德川幕府早期,这其中就包括创建于公元1620年的三井家族企业。[8]
由于领主商品经济代表的是封建领主的利益,因此使其高度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德川幕藩体制本身。首先幕藩体制下的石高制导致了领主商品经济的发展。从理论上讲,幕藩体制是排斥商品经济的政治体制,它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是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下的以稻米为基础的自然经济。但是幕藩体制本身又是矛盾的,因为这种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建立在以石高制为基础的年贡米上,为了让大名及武士离开土地,居住城下町,但又要保证其合理的收入,幕府实施了石高制,即按照土地年产量的五五或六四比例,以年贡米的形式作为大名及武士的收入。同时,幕府又以法令形式规定武士不得经商,所以领取年贡米的武士及幕府和藩都要将年贡米在市场上销售后,才能获得各种必需品,领主商品经济应运而生。
其次,幕藩体制下的参觐交代制度刺激了领主商品经济的发展。幕藩体制是建立在幕府居于最高统治地位基础上并与诸藩共同管理全国土地的统治模式,这就要求幕府必须强本弱末,因而幕府采用了参觐交代制度有效地弱化了诸藩的力量。但是大规模的参觐交代却带来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众多的人马一路上长途跋涉,食物、马的饲料准备、驿站的住宿等庞大的花费,这些都直接刺激了沿途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参觐交代过程中有时要必须经过个别藩的领域,那么这些藩就要打开藩门,提供过路的方便。为此,参觐交代的藩主要给途经的藩主赠送本藩特产,以示感谢,这个礼物一般都很厚重,有时还要购买或交换一些急需的用品。而接受礼物的藩主一般也要回敬具有本藩特色的礼物。因此,参觐交代过程中各藩之间严禁交往的藩界被打开了,藩和藩之间的交易也逐渐开始了。另外,参觐交代制度要求大名及其陪臣每一年或半年居住在江户,而妻子、儿女及相当多的家臣长期生活在江户,使江户人口高达百万,大量人口居住在江户,带来了庞大的消费需求,商品经济的发展势在必行。
最后,幕藩体制下的四民等级制度孕育了领主商品经济的发展。四民等级制度要求武士远离农村土地,居住在城下町,专门以习武和从事幕藩政治管理为主要内容,不得涉足经商、种地等行业,只是靠领取年贡米为生。武士阶层为了满足生活的多方面需要,必须卖掉手中的年贡米,获取其他的生活资料。而农民则世代被固定在土地上耕作,但他们耕作的内容一般都由领主确定,由于年贡米的原因,也使他们必须以种植稻米为主。这样农民也需要将自己剩余的粮食卖出去,以换取生产工具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町人阶层则是不折不扣的从事商业的阶层,他们是根据幕藩领主的需要被固定下来的一个阶层,他们的存在直接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由于町人专门从事商业活动,他们成为幕藩领主的主要代言人,经常出入于幕府和藩中。在得到幕藩领主支持的情况下,又由于积累了宝贵的经商经验,逐渐形成商业领域必须操守的职业道德,商业规模也逐渐发展壮大。从这一点来说,四民等级制度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土壤。
总之,幕藩体制是以自然经济为根本的,但是制度本身的矛盾性又必须依赖于商品经济(领主商品经济)的存在。而领主商品经济的发展势必带来全国范围内的真正的商品经济(农民商品经济)的发展。正如日本著名史学家井上清所指出的:“幕藩体制存在这样的矛盾,即它虽是以农业和自然经济为其固有基础的封建社会,但它又存在着同它本身互不相容的、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商品经济。”[9]因此,领主商品经济是应幕藩体制本身需要而产生的,是在封建领主的控制下实现的,代表的是封建领主的利益,反映了德川封建领主生活的状况,象征着封建制度的发展。领主商品经济的发展只能反映封建领主势力的强大,领主商品经济越是发达,就越反映出农民受剥削的严重,越能巩固封建领主等级制的统治。
三、农民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领主商品经济的刺激下,农民商品经济得到迅猛发展。所谓农民商品经济是农民以交换和获得财富为目的进行的生产,农民在商品交换中换取剩余价值,获得利益。生产出来的产品不是作为使用价值生产出来的,而是作为交换价值来体现,是真正意义上的商品经济,即实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统一体。
农民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从商业性农业逐渐发展起来。随着领主商品经济的发展的,农民开始在自己的房前屋后、荒山野坡种植桑、茶、褚、漆和红花、蓝靛、麻(即“四木三草”)以及棉花、油菜、烟草、大豆、甘蔗等经济作物,到17世纪末,畿内、山阴、摄津、河内等多地区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已达半数以上。这些经济作物主要是为了出售而种植的,它标志着日本商业性农业的兴起。而商业性农业的兴起一方面促成了地域分工,有专门生产甘蔗的地域、专门生产亚麻的地域、专门生产棉花的地域等;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农村手工业的发展。自18世纪中叶开始,商业资本日益深入农村,手工工场逐渐增多。到19世纪初,在丝织、陶器、酌酒、造纸、采矿、冶金等部门,先后出现了集中的工场手工业。农村中商户数量逐渐增多。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畿内地区,很多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都转化成了农村商人,以畿内下小阪村的棉商为例,文正年间(1818-1829年),10个棉商中有4个是拥有10石土地以上的富裕农民,有4个是仅有能够维持自家生活土地的一般农户,还有2个是没有土地的;到了嘉永年间(1848-1853年),拥有少量土地甚至没有土地的农民几乎都成了农村商人。[10]如作为农村商人收购棉织品店铺的“木棉寄屋”,1841年大阪附近的若江郡10个村子有木棉寄屋15家,河内郡的9个村子有木棉寄屋18家。[11]1804-1829年间,生产木棉、纹羽织的和泉地区,有织户440户,其中集中的“机屋”20户,问屋制的“赁织”户420户,赁织户是机屋的21倍。[12]这些数据可以反映出农村商品生产已经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农民商品经济已经有了很高的发展。
农民商品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制约。首先,幕藩体制本身是农民商品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一方面,由于石高制和年贡米的实行,促使领主及武士们必须将年贡米交换,并要通过市场去获得吃、穿、住等各种生活必需品,这使江户等周边的农民发现了商机,开始生产除水稻以外的其他经济作物,其生产目的就是为了到市场上交换,这种以农民为主体的商品经济逐渐发展起来,货币关系逐渐渗透到广大农村,进而在农村出现了一些新兴的豪农、商人,他们开始直接在农村收购商品并直接销售到市场上,这对大阪等领主保护下的商人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从而更加速了农民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幕藩体制下的年贡米制度的巩固和贡租赋课制度的稳定,农民只将收入的五五或六四交给领主,其余的留给自己,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不断改进生产工具和改善耕种方法及肥料的使用,使农民的生产逐渐有了剩余,中、上层农民的剩余产品更多,他们将剩余产品拿到市场交换。日本学者八木哲浩指出:“在当时拥有十几石到二十几石耕地的中、上层农民可将收获的50%甚至更多的大米作为商品出售,这表明他们生产的粮食已经超过年贡米的2至3倍。”[13]农民将大量的剩余产品拿到市场上销售,直接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幕藩体制本身就是农民商品经济发展的根源,是市场经济的温床。虽然幕藩体制本身是排斥商品经济的,但“幕藩体制本身是以商品经济的存在为前提的,而幕藩体制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14]
其次,领主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农民商品经济发展的直接原因。如前文所述,在幕藩体制的需求下,领主商品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出现了以江户、大阪等为代表的大中城市。尽管这种领主商品经济是幕藩领主的需求,代表的是封建领主的利益,但是市场经济本身的规律是不能被封建领主所控制和改变的,当交换的需求日益增大的时候,当人们的观念日益改变的时候,当新兴的生产关系逐渐强大的时候,这种市场经济就会破土而出,并逐渐地发展起来。因此,领主市场经济的发展孕育和培植了农民商品经济,并为其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同时,由于领主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农村的贫富差别,加剧了农民的分化,到德川幕府统治末期,分化更严重,其核心部分是拥有20—30石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持生活的本百姓阶层,众多是拥有不足5石的小百姓,他们依靠租种土地维持生活,还有一部分则是拥有100—300石的富豪,这些地方豪农成为市场交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最后,地理条件是农民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因素。日本是一个从东北到西南呈细长状的岛国,中央山脉横贯,地域被山脉和山地分割,没有广阔的平原,气候分成太平洋一侧和日本海一侧,降水量各地差异很大,季节引起的各地差异也很大,容易形成以相对小的面积为单位的地域多样化的地形和气候,使每个地域都能够生产具有自己特色的特产,从而刺激了地域间的分工,构成地域间商业发达的重要条件。例如,从东北地方的日本海沿岸到北路,冬季为多雪地带,农业生产是不可能的,但因有水利之便,稻米生产实行专门化,提高了生产率。本州的山丘地带不宜种稻,但由于利用了高度潮湿的气候,养蚕和制丝业显示出巨大优势,以至成为幕末开港以降的发展基地。濑户内海沿岸地带,利用沙地来推广棉花栽培,提供了平民的衣料和生产工具的重要原料。[15]由于地域和气候的差异,各地域生产的特色产品明显不同,带来了频繁的商品交换,这样直接刺激了农民商品经济的发展。
四、商品经济发展对德川幕藩体制的影响
虽然领主商品经济代表的是封建领主的利益,是幕藩体制建立和延续所依赖的经济形式,是能够被幕府所掌控的,但是领主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对社会的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商品经济,使农村自然经济受到影响,并引发了社会阶级地位的变化。一方面,全国范围商品交换的形成和农村自然经济的破坏。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扩张和领主、武士阶级生活的奢侈,对商业的需求越来越大,于是城市周边的农村率先开始了商品交易,逐渐出现了一些农村商人不经过大阪直接与江户联系,这种商品交换逐步扩大到农村,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市场交换。随着领主商品经济不断在全国范围内的扩展,货币经济逐渐成熟,这种货币经济从元禄年间(1688-1703)开始侵入农村,从宽正(1789-1800)到文化(1804-1829)年间,货币经济在农村得到更大发展,破坏了封建农村的自然经济,并引起了农村阶层的破坏,产生了豪农并使贫农阶层的数量不断扩大。另一方面,领主商品经济的发展引发了社会阶级地位的变化,即武士阶级的没落和商人的崛起。在幕藩体制下,商人的地位尽管低下,但由于幕府对商人只能征收少量税收而不能干预其经营和管理情况,因此在为武士阶级提供生活资料及政府运转的必需品过程中,商人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尤其是一些特权商人的出现,他们与武士官僚阶级联合起来,甚至被赋予一定的官职,依靠武士阶级的保护来获得财富,形成官商结合,即武士阶级依靠特权商人实现商品交换。官商结合使得财富更加集中在特权商人的手中,而武士阶级由于远离生产资料经济每况愈下。据估计,在宽政年间(1790年),“日本国富的十六分之十五,被商人所收,十六分之一,被武家所收”。[16]遇到天灾,武士经济拮据时,不得不向町人借债,债台高筑导致“由大阪的商人借给全国大名的钱6000万两之多,由诸大名运到三都的市场去的米计有400万石,而其中的300万石却是作为这6000万两的利息被取去的”。[17]这种经济地位的变化使得武士和商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逆转,出现“大阪商人一怒,天下大名为之震恐”的社会现象,武士的天下成了町人的天下:“于法是武士治人而商民治于人,实际上而今却是一个町人当家的时代”。[18]因此,领主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货币资本的发展,对瓦解封建经济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领主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客观上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商品交换和市场的形成,破坏了农村自然经济,颠覆了武士在社会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领主商品经济发展对幕藩体制带来的潜在危机,也是幕府所始料不及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前提。”[19]
农民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逐步发展壮大,并渗透到了广大农村,由于商业性农业及农村手工业的发展,旧的流通结构发生变化,改变了过去由领主控制、特权商人掌握的商品流通形式,产生了介于农村小生产者和城市大批发商中间环节上的农村商人。大量以交换为目的的农民商品涌入市场,这不仅改变着商品的结构,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农村的传统生产关系受到了挑战,进而产生了新型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一方面涌现了大商人,他们不仅仅是传统幕府保护下的大商人,而且是根植于广大农村的大商人,代表着新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破产而失去了土地的相当多的农民,成为被雇佣的生产力,代表着新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另一极。因此,这种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面对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幕藩体制出现了艰难的两难选择,既要打压又要利用,幕府进入了一个尴尬的选择境地。一方面的情况是幕藩体制排斥商品经济,尤其是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严重侵蚀着封建制度,瓦解着幕藩体制,同时各藩独立领国经济的发展也日益削弱着幕府作为中央政府的优势,为此必须极力压制;但另一方面,幕藩体制本身又要利用商品经济。当幕府面临财政危机时,幕府企图通过发展农业来解决财政危机,但这种背离生产规律的方法只能是以失败告终,使得幕府不得不重视有着巨大利润的商业,并积极地介入到了商品经济中,以其获得的经济利润来保证幕府的正常运转。因此,商品经济既是幕藩体制的支柱,也是幕藩体制的掘墓人,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幕藩体制越发表现出不适应性,要求用新的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因而幕藩体制的瓦解就称为历史的必然。
[1][日]伊东多三郎:《日本近世史》,东京:有斐阁,昭和27年,第11页。
[2][日]藤野保:《大名和领国经营》,东京:新人物往来社,昭和53年,第127、139页。
[3][日]津田秀夫:《幕末社会的研究》,东京:柏书房,1978年,第232页。
[4]《马克思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81页。
[5][日]坂本太郎著:《日本史》,汪向荣,武寅,韩铁英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93-296页。
[6][日]永原庆二:《日本经济史》,东京:岩波书店,1980年,第188-190页。
[7][日]古岛敏雄:《日本农业史》,东京:岩波书店,1962年,第339页。
[8][美]康拉德·西诺考尔,大卫·劳瑞,苏珊·盖伊著:《日本文明史》,袁德良译,北京:群言出版社,2008年,第13页。
[9][日]井上清:《日本历史》(中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45页。
[10][日]丰田武,儿玉幸多:《流通史Ⅰ》,东京:山川出版社,1981年,第223页。
[11][日]藤村通:《近代日本经济史》,东京:风间书房,1956年,第49页。
[12][日]历史科学大系(第7卷)·《日本从封建制转向资本制》(上),东京:校仓书房,1975年,第173页。
[13][日]八木哲浩:《近世の商品流通》,东京:塙书房,1978年,第170页。
[14][日]速水荣、宫本又郎编:《日本经济史》(第一册),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235页。
[15][日]速水融、宫本又郎编:《经济社会的成立(17-18世纪)》,厉以平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9页。
[16]黎海波、陈泽文:《大历史观下的明治维新》,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4期,第28页。
[17][日]服部之总:《明治维新讲话》,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29页。
[18][日]坂本太郎:《世界各国史14·日本史》,东京:山川出版社,昭和57年,第332页。
[19]《马克思选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65页。
[责任编校:张京梅]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during the Edo Bakufu Period
ZHANG Bo
(IdeologyandPoliticsEducationDept.,CollegeofPoliticalSciencesand
PublicAdministration,YanbianUniversity,Yanji,Jilin, 133002,China)
Natural economy was the fundamental for the Baku-han system, while the commodity economy its natural enemy. However, metropolis like Osaka, Edo and Kyoto as well as their suburbs developed uprecedentedly during the Edo Period. Urban consumption, esp. the needs of Baku-han lords, impell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rd’s commodity economy, which w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feudal system, but brought about the real commodity economy instead, namely the peasant’s commodity economy. The peasant’s commodity economy changed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feudal society, challenged the traditional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hen generated the new capitalist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finally became the hotbed to disrupt the Baku-han system.
lord’s commodity economy; peasant’s commodity economy; the Baku-han system
K313.36
1009-3311(2015)05-0093-06
2015-07-01
张波(1973—),延边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