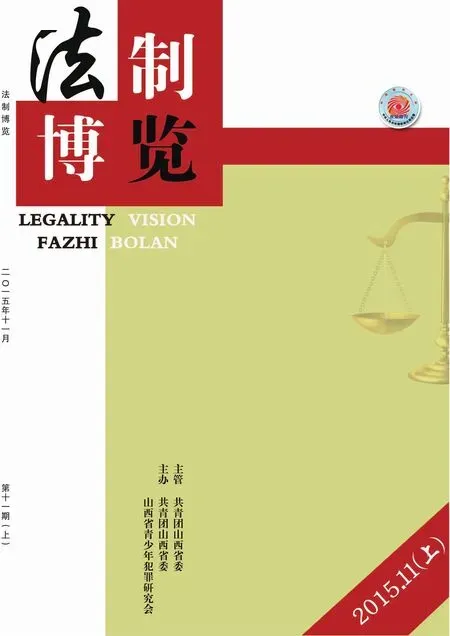刍论“共处法”与“合作法”的逻辑
窦弋翔
贵州大学法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刍论“共处法”与“合作法”的逻辑
窦弋翔
贵州大学法学院,贵州贵阳550001

摘要:基于一对词语:“共处法”与“合作法”,本文对两个用语的运用基础展开论述。从全篇文章的观点来理解,“共处法”、“合作法”并不是严谨而专业的术语,与术语的非术语化相反,它们是术语化的产物。这对词语所涵盖的事物内容不清晰而却宽广,不易被明确定义,也并非所谓的新事物。因为一系列变化的影响,比如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非国家实体实力上升等,在将来,“共处法”、“合作法”的用法可能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关键词:术语化;相互依赖;合作程度

一、国际法学界的一对“专业用语”
对于专业、学术术语,我们要求其具有严格的定义,明确的概念,其内涵、外延被要求得到充分的讨论,除了基于学术严谨之态度外,一个更为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术语对后续的研究进程起着关键性的基础作用。一系列研究的基础层面就要求这些特定词语具有严格的界定,否则可能会对研究的进行产生不可逾越的阻碍。①极有可能的是,研究实践的要求是研究者对特定概念进行明确定义的主要驱动因素,而后成为术语。
“共处法”、“合作法”会时不时地被提及,但它们的应用几乎只存于国际法学界(且主要是中国学界)。显而易见,“共处法”和“合作法”并非术语,因为术语本身要求专业化或严格化。另一方面,它们又并非指称语,因为“共处”(co-existence)与“合作”(cooperation)的意义在其中的表达虽不能被精准理解,但也可以根据词义把握“共处法”、“合作法”的大致意义。这对概念似乎介于通俗概念和术语之间,实际上,它们更像是新设概念的术语化的结果,这与术语的非术语化是相反的过程。虽然“共处法”、“合作法”处在这般境界,但是因为在学者圈内得到传播和更多认同,于是也在一定程度上被一部分学者作为圈内术语来使用,这样的使用可能有一部分是不自觉的。但不论如何,从这些方面来看,可以姑且称它们为“术语”。
从字面上来看,“共处法”和“合作法”所指事物和它们之间的联系很难直接表述,但是当提到它们时,似乎又能够为人所理解。这可能是因为它们本身并非严格意义的学术术语,能够从很多角度去理解,使人产生疑惑,但是另一方面,它们又能够隐约表现出某些方面的性质,透过这两个词以较为形象的方式表达出来,可惜这个过程是词语的借用(借用“共处”与“合作”),而非严格围绕事物本身性质来进行的定义,更像是修辞手法般的借用。所以当中的模糊性得以体现,虽然是一种取代,但是也是相对妥当的取代。
二、关于其背景
“共处法”、“合作法”不是被很正式、严格地提出的,而更像是在系列的过程中被提炼出来的,在这之前,“共处”(co-existence)和“合作”(cooperation)在国际法领域已经有了相关的表达。在冷战阶段,近现代战争的毁灭性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诞生逼迫敌对集团之间保持克制,避免大战。相持状态下,为了突出缓和,国家间寻求“和平共处”(peaceful co-existence)的讲法在一些国际场合、国际平台被提出并接受,涉及国际法领域的平台也是一样,比如在联合国和国际法协会当中。一些法律性事务围绕“和平共处”而展开,“共处”当然不是一个恰当的法律性表述,很明显,它是一种善意的政治话语,是倡导和平的宣传语,以它作为标题倒是非常合适。可再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宣传性语言的脆弱性,当发展中国家在国内事务处理中渐渐稳定后,越来越积极地为自己在国际场合争取更多,它们强调了不公平的过去以及未来的和谐合作,一些发达国家很大程度上达成了共识。“合作”被渐渐接受,在某些方面替代了“共处”。②在一部分讨论中,“共处”被冷战所感染,曾经所宣扬的“共处”只是权宜的,它似乎代表了冷战时的恐惧式、互相威胁式的那种极度令人不安的“共处”,所以要连同它一道排除。在这种环境中“共处”一说因政治需求被启用,因政治需求被“抛弃”,即便是被排除了,作为中性词,它仍被人为地赋予某些色彩,之后被“合作”所取代。③这种认识只应被部分领域的个别团体接受,而无法在更广阔的范围达成共识,也许在其他人眼中,“共处”是善意的,而且是较理想的状态。④
“共处法”、“合作法”可能是从国际事务的实践当中提炼出的说法,而且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它们被应用于国际法学领域,但是它们并非从国际法领域的法律实践提炼而出,更不是从国际法学内部延伸出的概念。一般而言,类似概念与国际法学强扭在一起,可能会不适当,但是它们的确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可,这就与国际法学构筑了一定关联。
三、不易明确的标准
国内的国际法学界中,“共处法”和“合作法”一般都会在学者的笔下一同出现,估计是因为它们的联系紧密,具体分析的过程则先以二者的区别方面来进行,然后再分析其他方面。⑤从区分上来看,一方面是时间段的角度的区分,另一方面则是所面向的领域及议题的区分。从时间,即国际法的演进方面来看,“共处法”主要指传统国际法,而“合作法”是指国际社会发展到近现代时期才突出,并呈一定独立性的新兴国际法。⑥没有明确的时间界限,但是在大致判断中,“合作法”的涌现应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最晚就算是冷战之后。⑦“共处法”和“合作法”在时间方面所表现的区别就在于国际法的传统性议题和近现代所出现的议题之间。⑧
当然,如果只是单纯从时间方面的考虑,那是简单而无意义的,因为没有任何理由就凭空分别出“共处法”、“合作法”将是伪命题。单独考虑时间变化,就不会存在传统与非传统的问题,于是更不用提“共处法”和“合作法”这样的概念。所以真正重要的,能够提出“共处法”、“合作法”并表现二者区别的,是其分别所指向的领域和领域的性质上面。从通常情况下来看,“共处法”应是国际法中规定国家相互行为中,基本方面的规范,试图处理以国家主权、国家独立为核心下,国际往来的根本性事务。“合作法”则不同于此,它并非针对国家往来的基本行为,而是一种国家交往深化后的表现和要求,国家主权和国家独立仍然是主要的,但是因为社会文明的演进,其基础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⑨
通过淡化以单纯的时间角度区别“共处法”、“合作法”的方式再来看待问题,而着重通过议题性质来加以分析。⑩若是通过这种方式,则要先着眼于“共处”、“合作”两个词语的意义,且对议题进行分门别类,这时难免会发现“共处法”和“合作法”之间的界限显得更加模糊,但是进一步仍然有必要。不论是“共处法”还是“合作法”,在很大程度上都反映着某种程度的国际合作关系,但是这里的“合作”是复杂的,合作的状况、领域、程度显然是不同的。另一方面,这些不同“合作”状况的成因均有待探讨,其中较为重要的一方面应是“认同”,认同的状况很大程度上引导这国家之间的合作,比如国家之间主权、身份及地位的认同,外交关系的认同与建立,合作事务的认同与进行等等。以此判断,可以有一些粗略结论,“共处法”可以认为是合作事务的必要性很高,而合作程度不深,要求不高的国际法领域。“合作法”当然都是合作程度较深的国际法领域,但是其中合作事务的必要程度则不尽相同,若能够简单地分为两种,那第一种就是事务必要性较强的合作法,比如核武问题、环境问题等领域的国际法事务,另一种则是事务必要性较弱的合作法,这种合作法一般是针对发展性合作事务,并非基本方面又非紧迫问题,但却是发展合作进程中不可或缺的。这类似的观察方式,既没有十分明确的标志,又没有量化过程,必要程度的划分,认同、合作状况都是不明确的,所以模糊视角下的观察方式所得到的结论也并非是严格的。虽然没有严格的界限,“共处法”与“合作法”之间难划界限,而且其内部也有诸多变数,但是,这也许就是这两个词语本身的描述极限,内在事物的探讨要更庞大的信息背景。
“生存法”和“发展法”,是与“共处法”、“合作法”情况较为相似的一对词语。这一对词语同样体现了国际法的某些重要性质,可若用“认同”、“合作”的逻辑来对应,这对词语与“共处法”、“合作法”不同。同样是从一般语义上来理解,“生存法”、“发展法”集中表达了合作事务必要性程度上的区别,但是割裂感过强,有些脱离现实。在“认同”、“合作”方面不易描述,“生存法”、“发展法”虽然表达了重要的方面,但是相对单一。
所谓的“合作事务必要性”,“认同”、“合作”状况与程度范围很广,不易做出准确描述的,只能在具体情形下得出一些相对性的结论,但似乎确有一定的解释力。只要存在“共处法”或“合作法”,那么一定会有其得以出现的基本必要性,国家之间存有基本的“认同”与“合作”。一般来讲,“认同”、“合作”的影响更为明显,若完全不存在“认同”与“合作”,那么其情形就类似两个不曾接触的文明之间的初期接触的状况,“共处法”、“合作法”不可能存在。主权国家间交往,较容易产生的是“共处法”,首先是由于“认同”、“合作”要求不高,其程度较低,有力地保证国家主权和独立之情形下进行基本事务往来,其二是“共处法”具有较高的合作事务的必要性,有更强的驱动力使国家对其作为,这一点可以从议题性质上看出。“合作法”不像“共处法”那样容易出现,或是容易取得相对较好的效果,因为不论是必要性议题的合作法还是发展性议题的合作法都首先国家间“认同”和“合作”有很深的程度,体现得更为融洽甚至相互依赖。不得不承认,在当下,国际社会以及国家主权和独立性较过去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但是基本结构仍然稳定,变化还未到达革命性的程度。互相认同和合作的行为在全球范围会有很多表现,比如欧洲地区和亚洲地区就有着明显的差异。“合作法”相对“共处法”而言,有不同的“认同”、“合作”状态,因而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易发展。若再比较必要事务合作法和发展事务合作法,则必要事务合作法的实践往往更让人产生失望感。比如核武器不扩散的实践,环境法的实践等方面,其目标较为明确,而要到达这些目标不得不进行程度较深的合作,但是中间阻碍力度大,这个过程就容易造成实践效果与既定目标之间相差甚远,使人感到非常棘手。发展事务合作法的目标不如必要合作法那样明确,在我们考虑轻重缓急时也次于“共处法”和必要事务合作法,就算同样对认同和合作程度要求较深,但是在发展事务合作法的发展过程中,反而不至产生过度的失落感。
以所谓的“认同”、“合作”状况来观察“共处法”、“合作法”仅是一个角度,而且是模糊性视角,所以我们必须还要拓展研究,并且以开放、灵活的方式进行。实际上,事务必要程度,“认同”、“合作”程度也只是相对条件之下的提炼,对于“共处法”、“合作法”来讲,可以与之建立逻辑关系。但是,真正的重要以及复杂之处还在于多方面的探究,比如国际关系,社会学、历史等多方面结合的跨学科研究,比如国家体制,领导人,文化、历史因素的影响下,对相关的事宜的必要程度,对国家间的认同、合作程度都会造成巨大影响。因此,所谓的必要程度,认同、合作程度,只是有着一定参考意义的中间环节,对于“共处法”、“合作法”的认识可以从各方面予以深化,可这的确也远远不够,仍需要补充很多。
四、人文精神的表现和使用的便利
笔者认为,在学者们对“共处法”和“合作法”的运用表达当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了某种人文气息。国际法学的学者们对这两个词语的借用,一定程度上是在描绘他们眼中的国际法发展之趋势,当中透出了某种期待,期待着国际法的未来乃至文明世界的未来正朝着良好愿望的方向发展,朝着更好的未来演变。字句中可以感受到细微的人文精神的气息和对期待的表达。⑪这种情况其实不仅体现在“共处法”、“合作法”上,还有很多概念的表达方式受到人文气息的影响而出现,探其细节末梢,当中各有利弊。⑫
就“共处法”和“合作法”这两个词语而言,由于学术研究当中实践需求的原因,因此也就不需要严格定义这两个词语。“共处法”和“合作法”仅作为标签,其本身并不重要,但是重要的是它们所指向的事物之性质,以及逻辑。即使算学者们把“共处法”和“合作法”两个词语作为真正的术语来使用,也并没有明显的不良之处,因为它们的使用情景并不是严格的,学者们很少将“共处法”和“合作法”当作真正的重点去考察,从这一点上来看,国际法的学者也能够感知这对词语存在的界限。“共处法”和“合作法”虽然不是严格的术语,但是它们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同,学者对它们的使用不仅没有显得别扭,反而是便利的。简单的“共处法”、“合作法”两个概念就可以表达很多,有变化的展现以及性质的判断,甚至包含了人文的期待,也许正是因为包含得太多,而表达却简便,所以更难去精准地定义它们,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共处法”、“合作法”来代替当中的复杂表达。同时,相对环境下,一味要求对某些词语进行严格定义,反而会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对这部分用语而言,权且保留模糊性未必是件坏事。可以想象,若在“共处法”、“合作法”的术语使用问题上太较真,是件浪费学术资源的事情,如果要创造新的,严格的术语,来代替“共处法”、“合作法”,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五、共处法、合作法在当下的变化
现代以来,国家之间的共处已不像曾经那般,国家间的共处需要比以往更深层次的合作,而国家之间的合作会有很多是基于国家间的共处,这个过程还在继续发展。由于此过程,也许我们不能太过武断地用“共处法”、“合作法”来描述,因为这可能会影响学者的判断,共处法和合作法正在变化。
共处法与合作法之间的界限的模糊,除了“认同”、“合作”程度,合作事务必要性本身具有模糊性以外,“共处法”、“合作法”所囊括的事物在当代社会也变得更加复杂。当代社会正处于一场剧烈的变化当中,比如全球化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反映。⑬国际社会在整个变化过程中将使共处法、合作法等一些原本模糊的事物变得更加模糊,当然,其中很多问题也能够反映在“认同”、“合作”程度以及合作事务必要性上。
当下,“全球化”(Globalization)已是一个被广泛运用至极致的词,若从广义方面理解,全球化过程比这个词语本身的经历时间要长很多,目前看来,这个过程却也是人类文明必经的一个环节。⑭这个过程的进度却并不是均匀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都是非常缓慢地进行着,可在近几十年以来这个过程的进行速度大幅提升,于是,表现出的相对变化也显得十分明显。在整个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国际社会的变化,这也要求研究者对国际格局的观察突破以往的古典现实主义视野。现实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变化,国家主权的实践表现以及主权理论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动,这些都是系统性地影响国际法变化的一些重要部分。
国际法体系所发生变化的背后,是整体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科学技术和经济活动方式的突变使全球化进程越发具有质变的特性,使得原本就模糊不清的“认同”、“合作”程度和合作事务必要性变得更加不定,非国家行为实体正在崛起,成为不可忽略的实际力量。国际法体系内部发生变化,“认同”、“合作”程度以及事务必要性的复杂与混乱,使得“共处法”和“合作法”的原本逻辑更加远离处于变化中的实情。
全球化背景下,政治议题已经扩散,不再局限于一隅,“高政治”(high-politics)、“低政治”(low-politics)的说法被更多人所接受,并认为“低政治”领域和“高政治”领域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低政治领域有高政治化的倾向。这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国际社会大量涌现的各种国际组织以及公民团体对政治的影响,环境、人权、文化等低政治议题开始受到高层政治人物的注意,并且被慢慢加入议程。“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⑮经济领域的问题可以说是最为突出的,现在来看,经济问题很难绝然局限于“高政治”还是“低政治”这样并不严格的二分类别方式当中。全球化以科学技术为支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发展为主要驱动力,国家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很高,政治认同、国际共识以及合作程度全都发生了巨大改变,众多事务在复杂化过程中性质在相应改变,必要性事务已经不再止是曾经那些,现阶段的合作事务的“必要程度”无法衡量。在国际政治领域,经济的政治意义极强,经济筹码可以在外交谈判桌上发挥强有力的作用,这是表现经济问题“高政治”性质的一大标志。在当今政治学者、国际关系学者和社会学者的表述中,经济问题的深刻性具有绝对的战略意义,尤其是国家经济控制权力被极大削弱的当前,这一点可能体现得更为明显。⑯
“共处法”的逻辑对应着最为传统的国际法领域,其“认同”状况、“合作”程度的衡量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在现如今,不考虑时段划分,而直接去考虑“认同”、“合作”程度、事务必要性,就会出现错误。当代的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之间界限并不具有以往那般的明确性,这与之前提到的“高政治”与“低政治”领域界限模糊的情形相仿,几乎是一个整体变化过程中,分别于此二领域所发生的变化的表现,同时也侧面印证了法律对政治的反映之特性,以及国际法对国际关系的反映。“共处法”也相对发生了变化,不再那么“封闭”、“独立”,而是开始表现出“开放”与“融合”等特性。原来的领域也许保持着原本的性质,但难免不被新事物所冲击并发生改变,虽然滞后,但是国际法会随之发生变化,比如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问题方面,“认同”、“合作”程度,事务必要性上,可能的倾向预示未来在这一领域会有更多的法律层面合作,这些都牵扯着国际社会的安全与未来。⑰
“共处法”、“合作法”所描述的事物的基础会变化,这些事物也会变化,形式上,共处法、合作法的界限也会趋于模糊。而对于这对词语而言,可能在用法上会变化,或者被淡
化,虽然不易预测,但是它们会发生某些变化。
六、结语
本文从作为“术语”的“共处法”、“合作法”作为论述开端,对共处法和合作法做出更多探究,以求其逻辑。也许“共处法”、“合作法”在国际法学界的应用是术语化的成果。这种应用目前是利好的,但是也是有局限性的,尤其是在国际法的持续变化状况(这些变化也应是论述的重点)下,要有意识地避免其过度的术语化,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自我误导,这种误导是一种浪费,是认识上的错误,这也是其模糊性的潜在弊端。
[注释]
①这样的术语有很多,其中有一些比较典型,尤其是在几个相似而又有区别,且又必须予以明确的术语之间学者们会投入更多时间精力去定义这些术语,这个过程中又会产生很多争论.就国际法领域而言,国际人道法、国际人道主义法、武装冲突法、战争法几个术语之间任存有很多可讨论的空间,而国际经济法方面,国际商法、国际经济法等几个术语之间也任存有可讨论的空间.
②Edward McWhinney,“The ‘New’ Countries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Law:The United Nations’ Special Conference on Friendly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Among States”,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60,No.1,1966,pp.1-33;Edward McWhinney,“‘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Soviet-Western International Law”,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56,No.4,1962:951-970.
③John N.Hazard,“Co-Existence Law Bows Out”,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59,No.1,1965:59-66.
④Antanas Mockus,“Co-Existence as Harmonization of Law,Morality and Culture”,Prospects,No.1,2002.
⑤笔者主要以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准,进而分析共处法和合作法的逻辑.
⑥如国家间平等、国家主权、公海航行自由、外交规则等,被归于共处法中;如国际环境法、国际人权法,包括国际经济法则被归于合作法当中.这些在<国际法的概念和渊源>和<国际公法规则之冲突>中也有所提及.
⑦Michael Reisman,“International Law After the Cold War”,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84,No.4,1990:859-866.
⑧[美]约斯特·鲍威林著.国际公法规则之冲突[M].周忠海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李浩培.国际法的概念和渊源[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⑨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行为主体.通常来讲,共处法中的行为主体可认为是国家,合作法中的行为主体也是国家,但部分非国家实体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其中,其中的大部分的非国家实体对于很多合作框架形成以及合作事务实施起到了推动作用.当然,笔者认为国家实体依旧是主导性的,本文描述的合作法也侧重国家实体作用下的合作法,关于非国家实体的影响,由于篇幅和文章主题等因素的限制,没能够纳入过多考虑.但是从多个方面来看,非国家实体也是很重要的,国际环境的演进中,共处和合作的主体将越来越不会只限于国家之间.
⑩这一点应是可行的,其一是由于“共处”、“合作”二词本身并不体现也不表达时间影响,除此,还因为模糊性视角下,观察方式的作用.
⑪以中文著述来说,<国际法学专论>、<国际法理论的新发展>都用专用部分章节,以共处法和合作法为名来阐述有关内容;鲍威林所著.<国际公法规则之冲突>的第一章内容中,就提到了共处法和合作法。除了专著当中,如<向共进国际法迈步>、<现代国际法的人本化发展趋势>等论文、文章也都不同程度地借用共处法、合作法这样的术语阐述问题.不论如何,我们可以发现,文献中几乎不会单独提出“共处法”或“合作法”,它们基本上都会让这对术语一同出现.使用这对术语的学者们都借此含蓄地表达了国际法的变化,而且要让这对术语一同出现进行对比,在对比中才能让读者更明晰地感受到国际法的突兀变化.
⑫Piet-Hein Houben,“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Concerning Friendly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Among States”,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61,No.3,1967:703-736.
⑬哲学家赵汀阳在<文化纵横>杂志社和北大元培班主办的‘文化纵横杯’书评大赛中,以<游戏改变之时的反思>为主题发表演讲[EB/OL].http://news.ifeng.com/exclusive/lecture/special/zhaotingyang/,2015-1-18.
⑭Thomas L.Friedman,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99.93.
⑮俞可平等.全球化与国家主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9.
⑯任丙强.全球化、国家主权与公共政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7.
⑰赵晓春.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化与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研究[J].国际安全研究,2003.3.
作者简介:窦弋翔(1990-),男,汉族,贵州贵阳人,贵州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学专业硕士生,研究方向:国际公法,国际法理论。
中图分类号:D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5)31-00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