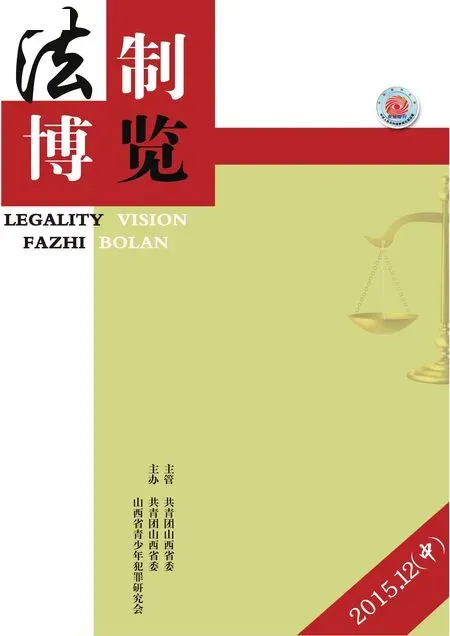浅谈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完善
郭 薇
哈尔滨市医药工程学校,黑龙江 哈尔滨150000
一、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重要意义
(一)有助于避免“贴标签”现象
标签理论告诉人们“前科的存在导致甚至是促进犯罪人再次犯罪。”一旦一个人有前科,社会上的其他人往往会先入为主地认定这个人的品质存在重大缺陷,而不会去关注他被教育改造的是否成功。“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习惯以有色眼光看待罪犯,做出一些有损犯罪人人格尊严的行为,而这些行为的后果不仅容易引起社会的周围人对犯罪人有意无意的歧视,就连犯罪人本身也久而久之失去了自尊自爱。”这就给那些存在前科,经过改造,且改造成功的人关上了重新融入社会的大门。尤其是当一个人处在未成年的阶段时,他的心智还不够成熟,如果仅仅因为一次严重的错误就否定了其整个人生,不免过于严苛。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可以给失足的青少年一个重新洗白的机会,为他们撕掉不客观的标签,帮助他们重新回归社会。mm〛
(二)有助于实现刑罚的教育目的
刑罚的目的不仅仅是惩罚,更是教育,只停留在惩罚的层面,是没有意义的。通过教育使罪犯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从而改过自新,重新生活,这才是根本。如果始终打着罪犯的烙印,其实是很难开始新的生活的。法律如果想要实现刑罚的教育目的,就要为他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后环境。指责、歧视、质疑绝对不是一个良好环境,这些负面的能量容易诱发新的犯罪思想萌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致力于给有前科的年轻人创造一个欣赏、鼓励、友善的教育后环境,希望能够持续教育改造成果,避免犯罪思想反复发作,从而真正实现刑罚教育目的。
二、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几点构想
我国2012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进行了首次规定。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的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可见该条对适用的条件、效果、例外情形均作了规定。然而由于规定的较为概括,在实践中不免操作性较差。针对这一制度,结合我国现状,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构想。
(一)扩大适用对象
目前我国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对象是: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员。笔者认为应该将这一适用对象扩大为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员,去掉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限制。法律之所以设置刑罚的限制,目的是要区分开较轻的罪与较重的罪,较轻罪适用封存制度,较重罪不适用。但是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初衷是为了给年轻的犯罪人提供一个更好的回归社会的机会,这一制度是否适用的关键区分点应该是年龄,而不是犯罪程度的轻重。一个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罪犯未必就比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罪犯主观恶性更大。因此,将年龄作为该制度是否适用的条件,将犯罪轻重作为设置考验期长短的参考,笔者认为比较合理。
(二)设置考验期限
我国目前并没有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考验期的设置。按照《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后,对犯罪记录予以封存。”可见,在实践中,我国采取的是判决生效后,司法机关自动启动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而不需要考验期的考察。笔者认为这种做法过于急躁。不考虑罪犯的实际情况,不考察罪犯的改造过程、悔罪表现,而直接启动封存制度,有可能导致这一制度的滥用。对于有悔罪表现的罪犯来说,这一制度无疑是他们重回社会的一把保护伞,有其现实意义;然而对于毫无悔意的罪犯,这一制度则成了他们掩盖过去的一块遮羞布,不利于群众对他们的监督。笔者认为,在判决生效后,司法机关可以将犯罪记录暂时封存,同时规定一定的考验期,在考验期内考察罪犯的主观恶性、悔罪态度、现实表现,考验期满后自动启动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如果在考验期内,犯罪人有违规违纪的情况发生,则对其不再适用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三)明确保密责任
我国刑诉法规定“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该条只规定了义务,并未明确说明如果违反保密义务需要承担的责任有哪些。不需要承担责任的义务是毫无意义的。立法者应该站在犯罪人的角度考虑违反保密义务可能给犯罪人造成的伤害,例如:舆论的压力、升学就业的障碍等,从而规定泄密主体应该承担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以确保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价值得以实现。
[1]于志刚.刑法消灭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6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