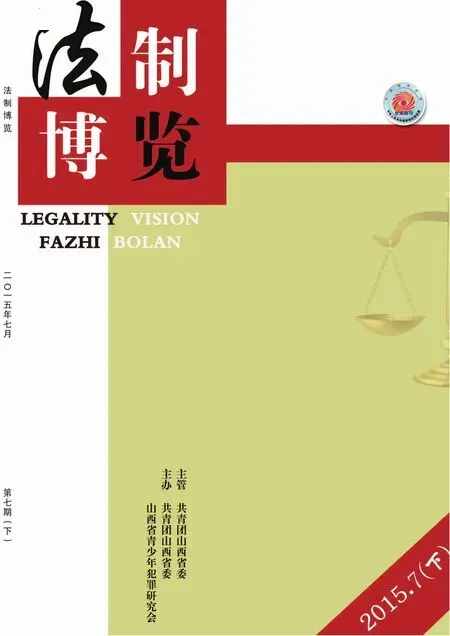“性质模糊”案件中的盗窃与抢夺区分
张鑫慧
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检察院,天津300380
一、“性质模糊”案例及其争议
案例一:甲驾驶摩托车,以需要打电话为名,向路人乙借手机。当乙将自己的高档手机(其价值金额已达到该地区盗窃罪入罪金额标准)交给甲后,甲佯装打了一会电话,见乙放松警惕,便突然发动摩托车,迅速逃走。
案例二:甲从乙家楼下经过,恰逢乙在阳台晾晒衣物,不小心将黄金手镯(其价值金额已达到该地区盗窃罪入罪金额标准)掉到楼下,甲迅速抓起手镯逃走。
案例三:在案例一或案例二的情况下,甲同时随身携带了凶器。
对上述三个案例的争议主要有两点:(1)案例一、案例二中,甲的行为应定性为盗窃还是抢夺?(2)案例三的情况下,对甲的行为,是否应适用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定性为抢劫罪?
造成上述争议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刑法对于盗窃罪和抢夺罪的规定尚不够细化,而司法实务中区分二者的标准也仅是笼统的“窃取”和“公然夺取”,且对盗窃罪能否由公然行为构成、抢夺罪的行为对象范围等问题,尚有疑问,因此在遇到如案例一、案例二中所涉的“性质模糊”的行为时,对该行为的定性便存在不同的观点,并影响到案例三中所涉的具有特殊情节的行为的定性。
因此,对上述类型的案件进行合理定性,关键在于解决两个疑问:(1)“秘密性”是否是盗窃罪客观构成要件中的必备要素?(2)抢夺罪的犯罪对象范围应如何界定?
二、疑问之一:“秘密性”是否是盗窃罪客观构成要件中的必备要素
传统的刑法理论一直认为,盗窃罪在客观上表现为“秘密窃取”,即对于盗窃行为而言,“秘密性”不可或缺。那么,“秘密性”到底是否应当作为盗窃罪客观构成要件中的必备要素呢?笔者认为,传统刑法理论认为盗窃必须以秘密性为要素,是有其重要的合理性的。这种合理性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点:
首先,对被害人或第三人而言,秘密行为与公然行为所蕴含的危险有很大的差异。如果行为人系秘密窃取被害人的财物,此时被害人不知情,不会急于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财物,也不易引起行为人的抗拒;而如果行为人如案例一、案例二中所述,当面非法占有被害人的财物,被害人一定会迅速采取呼救、追赶等措施尽力追回财物,而附近的过路人、居民等第三人也有可能参与帮助,此时行为人对被害人或第三人实施抗拒行为的可能性极大,且很有可能使用暴力,对被害人或第三人造成伤害甚至死亡结果。因此,公然非法占有财物行为的危险性比一般的秘密窃取行为要大得多,即使其在取得财物时手段是“平和”的,也极易引发暴力行为,不宜与秘密窃取行为一同被划入盗窃范畴。
其次,秘密行为与公然行为所反映的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也有着很大的不同。“选择采用秘密的方式窃取财物……说明行为人对社会秩序的维护还存有一定的顾及……因此主观方面的可责性相对较小。而采取无所顾忌的公然方式强取他人之物……说明行为人主观方面对公共伦理规则、法律秩序和社会善良风俗的藐视,其主观可责性明显大于前者。”这种更大的主观恶性和因此带来的更大的可责性,也使得公然非法占有财物行为不宜被定性为盗窃。
因此,当面地、公然地非法占有财物行为和秘密窃取行为之间,在客观的危险程度方面和其所反映的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以取得财物时的手段是否“平和”作为区分抢夺与盗窃的标准,而忽视了行为的实际危险性与行为人的可责性,显然不妥。即使公然行为在取得财物时并未直接使用暴力,也不宜与秘密窃取一样被定性为对被害人、第三人的危险相对较小的盗窃行为,将“秘密窃取”作为界定盗窃行为的客观标准之一,仍然是必要的。
三、疑问之二:抢夺罪的犯罪对象范围应如何界定?
目前,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于抢夺罪的犯罪对象范围,存在着这样的争议,即抢夺罪的犯罪对象,是否必须是被害人“紧密占有”的财物?如果是,“紧密占有”究竟应作何解释?“有学者曾指出:抢夺行为应当是具有伤亡可能性的行为……行为人所夺取的财物必须是被害人所紧密占有的,如财物由被害人提在手中、背在肩上、装在口袋里等。”这种观点将抢夺罪的犯罪对象限定为被害人“紧密占有”的财物,并将“紧密占有”解释为财物与被害人的人身存在紧密的接触。如果用这种观点来评价本文第一部分中案例一、案例二所涉的情况,则一定会将行为人的行为定性为盗窃而非抢夺,因为在案例一、案例二所涉情况中,当取财行为发生时,手机、手镯等财物并未紧密接触被害人的人身。
但这种将抢夺罪的对象限于紧密接触人身财物的观点,其实仍与“将手段是否平和”作为区分盗窃与抢夺标准的观点不可分割。但如果不考虑是否采取平和手段,而以行为的客观危险性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作为区分盗窃与抢夺的重要标准,则对抢夺罪的犯罪对象范围也应重新界定。
此时,抢夺罪的对象范围应有适度的扩展。在案例一、案例二当中,手机、手镯等财物虽然并未紧贴被害人人身,但在行为人非法取得时,这些财物仍然在被害人视线范围内,被害人明知财物被非法取走,也明知取财者及其逃跑方向,且仍然可以通过呼救、追赶等方式及时追回自己的财物,即财物被取走时仍然处于被害人的实际控制之下。正是因为被害人对财物的实际控制和对行为人取财事实的明知,使其有条件立即采取追回财物的行动,并进而带来了行为人抗拒、使用暴力等危险;同时,行为人明知财物并未完全脱离被害人控制,却仍在被害人视线范围内作案,也表现了其更大的可责性。因此,抢夺罪的犯罪对象应界定为在被害人视线范围内且被被害人实际控制的财物,而非仅限于紧密接触被害人人身的财物。
四、对本文第一部分中案例三所涉行为的定性
本文第一部分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对于案例三是否应当适用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定性为抢劫罪?
笔者认为,如果将案例一、案例二定性为抢夺罪,则对案例三应适用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携带凶器抢夺”的规定,定性为抢劫罪。其原因在于,立法者将携带凶器抢夺的行为定性为抢劫罪,正是由于携带凶器的抢夺行为的危险性比普通抢夺行为要大得多。行为人公然夺取财物,已经体现出其对被害人人身安全及法律权威、社会秩序的漠视,并且极易引发连锁反应,即行为人实施抢夺——被害人、第三人竭力追回财物——行为人抗拒。如果行为人随身携带了凶器,则很有可能在被害人、第三人追回财物或对其抓捕时,用凶器进行抗拒,对被害人或第三人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甚至死亡结果。因此,基于其重大危险性,携带凶器抢夺被定性为抢劫罪,这符合刑法“预防更加严重犯罪”的目的。
而将案例一、案例二定性为抢夺罪,同样是由于行为人的公然非法取财行为反映了对被害人安全及法律秩序的漠视,且容易引发上文所述的连锁反应,具有比盗窃罪更大的可责性和更严重的危险性。此时,如果行为人同时随身携带了凶器,则其使用凶器进行抗拒并造成伤亡结果的可能性很大,因而适用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将其行为定性为抢劫罪,也是合理的。
[1]高国其.公开盗窃理论构建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质评[J].重庆大学学报,2014(03).
[2]张兴.从一则案例看盗窃罪与抢夺罪的界分[J].法制博览,2012(12).
[3]胡胜.盗窃被发现后公然夺物的行为定性[J].中国检察官,2010(01).
[4]华颖霖.公开盗窃之边界[J].当代法学论坛,20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