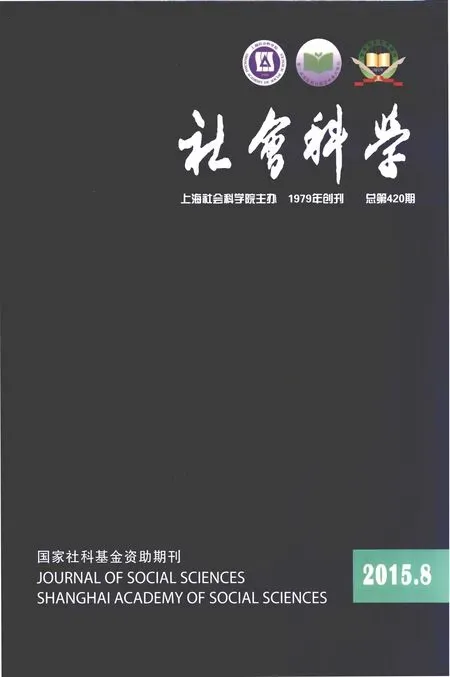文化解释学的考察:网络语词文本的生成与传播*
李 敬
网络语言的流行作为互联网时代的新现象,受到各学科的广泛关注。然而,语言的问题从来不只是符号的表意问题,它与人的存在样态、意识形态、权力运作方式都有着根本性的关联。由此,对于网络语言的研究,必然引起语言学、社会学、文学、传播学等不同学科视角的讨论。但作为研究对象的“网络语言”,其外延过于宽泛,包括了从“表情符号”到“淘宝体”的各类符号形式。然而,从动态语用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网络语词、句式和语篇之间有着内在的、不易觉察的差异:它们所依赖的语境类型(context type)不同。也就是说,文本(text)之意义(meaning)生成所依据的语境有着层级上的差异。尽管研究者可使用宏观理论视角对作为网络语言进行总体性分析①我们可以使用文化场域理论对网络语言的流行做象征性权力的分析;或以权力理论进行民间—官方叙事的研究等。,但通过对研究对象的限定(在特定语境层次上限定文本类型),有利于对语言生成进程中的社会语境与传播机制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本文采用文化解释学②当代解释学理论主要有四大流派,作者理论、解构理论、交往理论和文化理论。作者理论把作者的用意和理解视作解释和认识文本的合法依据,意义总是由作者赋予的,其代表人物是荷斯科(E.D.Hirsch);解构理论则认为文本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言语是多义的,它们被理解的方式是不确定的,解释者对文本理解的约束仅仅来自于文本内部,外部的解释是没有限制的。其代表人物是德里达;交往理论和文化理论是对这种读者之无限自由的拒绝,艾柯(Umberto Eco)就提出了“解释的限度”。由费师(Stanley Fish)所代表的交往理论认为,解释群体的释义角色和法定地位决定了他们对文本的理解,这种角色也将随着群体的愿望而发生变化;而以乔治·格雷西亚(Jorge J.E.Gracia)为代表的文化解释学认为,文本的文化功能决定了合理的解释,而文化是一个不轻易被改变的、由社会发展出来的复杂系统,社会决定着文化,而不是由解释群体的亚文化系统决定着解释的激情。资料参见欧阳康《文本型、解释和解释学哲学——访美国解释学家乔治·格雷西亚教授》,《哲学动态》2004年第11期。本文使用的理论分析框架主要采用文化解释学的观点。的方法对“背景语境”层级的作为“文本(text)”①这里的“文本”有两重维度,其对立项分别为“符号”及“语言”。关于“文本/语言”的区分,文中第一部分会有说明。此处对“文本/符号”进行辨析:前者的意义在最低限度上至少依赖于构成其的单个符号的意义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而后者的意义则并非是组成符号的那些构成要素之意义叠加的结果。诸如“(有钱,)任性”,它的意义至少是与“有钱”、“任性”两个符号相关联,即便在它的传播扩散中,“有钱”被省略了,只留下“任性”,它的使用者和读者依然明白,它被如此使用的依据就在于其内在地包含了两者间的关联,无论“有钱”被替换成其它的状态,作为流行语的“任性”都是始终在一种关系之中的情感表达。而诸如符号形式的代表笑脸的网络语“:)”,它的意义并不由构成该符号的元素“冒号”和“右括号”的意义所决定。因此在本文中,符号类型的网络语不属于本研究对象。的“网络语词”进行讨论。
一、研究对象界定:“背景语境”中的作为“文本”的“网络语词”
以语言为对象的研究,总体上看,可以从语义学和语用学的两条进路展开。前者聚焦于“句子意义“(sentence meaning),对语言的分析是在静态的、脱离语境的、非交往的抽象语言层面展开;后者则关注动态的、交往中的“话语意义”(utterance meaning)。我们知道,在语义学之语用学转向的大背景下,话语意义的分析成为主流:相对于从符号规则、句式特点、语篇结构等静态层面的语义学分析来说,网络语言的“话语意义”分析,可以对社会文化语境下的网络文本之意义生成与传播进程一探究竟。
大量的、不间断生产出的网络语词随处可见,其中有些得以较长时间使用、有些则在快速遗忘中被消解。诸如“有钱,就是任性”、“萌萌哒”、“弱爆了”、“杯具(悲剧)”、“土豪”、“屌丝”、“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神马都是浮云”、“俯卧撑”等诸多网络文本正在或曾经被广泛使用,这些“语词文本”的意向意义(intended meaning)②在当代分析哲学中,文本的“意向意义”受到强调。“意向”总是指向对某个意义的表达,但意向主体未必要对此意欲具有充分的意识。对于文本的“意向意义”来说,任何一个文本,作者在生产它时总是具有某种清晰或模糊的“意向”,即充分意识到或只是有一种模糊的观念——要传达给读者某种意义,并为此选择和排列符号以构成文本。本文关注的是网络语言在生成和传播过程的意义增强、叠加、变形和妥协的内在张力,因此聚焦于“作者”与“读者”之双方的意义生产进程,由此从分别诉诸这两方面的“意向意义”和“阐释意义”的维度来展开分析。和阐释意义(interpreting meaning),所依赖的“语境”层级不同:有些在狭义的“语篇环境(texture environment)”中即可被理解,并获得相对稳定的意义,文本的阐释空间是有限的;而有些意义只有在“背景语境”(background environment)中才得以生成和理解,文本的阐释更具开放性。
作为意义系统研究框架的“语境”概念的正式使用,以上世纪20年代初马林洛夫斯基(B.Malinnowsky)的语境概念作为开端。他区分了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和情境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前者指说话者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背景,后者指涉语言行为的具体发生场景。此后,系统功能语言学家韩礼德(M.A.K.Halliday)又具体界定了情境语境的构成因素。总的来说,语境的分类依据语言学家的分类视角不同,术语指称各有不同,但基本采用二分法③虽然有些语言学家,诸如马赛罗·达斯卡尔(MarceloDascal)、维泽曼(EWeizman)把语境分为三类,特定语境、表面语境、背景语境,但实则也是二分法的强调与延伸。,即以“情境语境—文化语境”;“局部语境—整体语境”;“物质语境—社会语境”等对物质符号的语篇语境和语篇之外的社会文化环境进行区分。④王冬竹:《语境与话语》,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页。
本文采用“背景语境—语篇语境”来指称文本意义所依赖的不同语境层次。“背景语境”,指涉与新生语词现象相关或直接导致其产生的事件与文化背景。“语篇语境”强调的是意义所依存的由文字符号组成的上下文语境。对于“网络语词”,我们从动态的、“文本”的维度展开,目的在于对作为“文本”的网络语词之意义生成、意向意义、意义阐释、“作者—读者”身份等展开探究。对于某些语词,诸如“萌萌哒”“弱爆了”“楼主”“顶”“沙发”“潜水”“灌水”“给力”“汗”“雷人”“草泥马”“闪(人)”“小白”“粉丝”“腹黑”等网络语词,读者对此类文本意义的阐释,可以仅通过语篇语境即可获得,甚至在离开语境的情况下,这些文本本身的符号结构方式,也使得读者对其意义的理解成为可能。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文本总是开放性的,但意义的开放限度是有差别的。意义限度与文本本身的复杂程度、语境层级、文本功能等条件相关,语境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因为语境是文本同一性及意义同一性的一个因素……相同的实体(ECTs)在不同的语境中可被赋予迥然不同的意义”①[美]乔治·J·E 格雷西亚:《文本性理论:逻辑与认识论》,汪常砚、李志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115页。。
语境是文本意义阐释的重要依托,或者说语境是文本意义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文本”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依赖于语境,这也是“文本”与“语言”的重要差异:作为语言的语词,其意义可以脱离语境而被理解,即“字面意义(literal meaning)”;但作为“文本”的语词,则不存在所谓的“字面文本意义”,因为文本总是作者为了某个特定目的的语言集合②Ricoeur,Paul,Stucture,Word,Event,In Charles E.Reagan and David Stewart,eds.,The Philosophy of Paul Ricoeur:An Anthology of His Wok,Boston:Beacon Press,1978.p.114.,目的只能在语境中被理解。在我们区分了“文本”之后,另一个要点是,“文本”的阐释意义与语境层级(level of context)相关:愈少的“背景语境”渗透进文本,文本的意义明确性程度就越高。诸如“给力”这样的网络语词,其字面意义较清晰,即“很棒,很有效用”,读者在特定的语篇语境中将获得更确切的意义理解。如“出台这样的政策,真是给力!”“给力”的意义被理解为“很有效,很贴合当下需求”。同理,“灌水”“雷人”“粉丝”等文本也是如此,依赖于语篇语境的文本的意义限度高,读者很难对该类文本的意义作出过多的阐释。
与之相反,对某类文本意义的理解与背景语境密切相关,读者只能在“背景语境”中作出对文本意义的解读。诸如“屌丝”“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宅”“神马都是浮云”“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俯卧撑”“高富帅”“土豪”对于此类文本意义的理解,在语篇语境中,意义仍是模糊的、不确切的,甚至无法进行解读。对于“屌丝”这个文本意义,只有对当下中国社会中的普通人,尤其是年轻人之生活境遇、生活态度和生活背景有一定程度的理解,才可能去获得它的文本意义。这个网络语词,几乎是横空出世并快速弥漫于生活之中的,从传统语义学来看,它只是一个单纯词,所指是某一类人。但动态的、作为文本层面的语词,它的意向意义、功能与阐释意义生成,以及“作者”与“读者”的身份关系,绝非只是一个音译的能指符号与指涉对象间简单的对应关系,而是在复杂的社会语境中的话语进程。同样,“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这样的看似意义简单的文本,实则也必须在背景语境中进行理解,它的意向意义与阐释意义,并不如同其符号字面意义看上去的那样简单,简单到几乎无所指涉的程度——它无实质意义,只是一种自嘲式的情绪表达。然而,这种“自嘲”的根,则是生长于复杂的背景语境之中的,我们只有刨开当代社会文化的土壤,才能看见意义看似“游离飘渺”的网络语词文本下深层的脉络。
二、有生命力的“网络语词文本”③“网络语词文本”在这部分皆指涉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背景语境”下的网络语词文本。文中以此简称。分析:功能与目的,作者与读者
明确了本文的研究对象,我们将对“网络语词文本”进行语词的功能与目的、意向意义、阐释意义与文本意义展开分析,来探究两个核心问题:什么样的网络语词文本能够获得生命力?推动网络语词诞生和传播的机制是什么?
文本依据功能进行普遍范畴的分类,可分为五种类型:信息类(informative)、指示类(directive)、表达类(expressive)、评价类(evaluative)和执行类(performative)。④[美]乔治·J·E 格雷西亚:《文本性理论:逻辑与认识论》,汪常砚、李志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115页。对于网络语词文本,我们发现,它们大多是表达类文本,即语言用作发泄或引起情绪的功能。诸如“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贾君鹏,你妈喊你回家吃饭”“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等文本,它们的功能并不同于信息类文本或执行、指示类文本,即用于信息的交流或引发行为的执行。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些文本如“贾君鹏,你妈喊你回家吃饭”,看似是指示性文本,它的表层意义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行为指令,但有意思的是,这并非作者的意向性意义。回溯该文本的事件性背景:它最初只是2009年一个游戏论坛的无内容标题帖。发贴后几小时竟得到近40 万人次阅读和近2 万次回帖,它被大量转发和模仿,大家对“贾君鹏”产生浓厚兴趣;事件性热潮过后,“贾君鹏”是谁已不再重要,但该文本不仅未被冷却,反而得到持续性、“创造性”使用,这种使用伴随着大量的“修改变形”①修改变形的文本更换了人物对象和行为目标,但不变的是“…,你…喊你回家(吃饭)”的文本格式。后的次生文本的诞生和传播。逻辑上很清楚的是,对于一个甚至是“假想的”“陌生人”、常规行动的指示对象,显然绝无受到他人广泛关注的理由。只有一种解释可以成立:情绪的共鸣推动了文本的传播与衍生,文本的意义也因此获得高度同一性的理解。一种对家庭温情的回忆延伸至爱情、友情等一切美好怀旧的情绪,文本传播的背后是情绪的相互感染与认同;怀旧心情和喧闹景象的背后,也许正是现实存在中的挫折和寂寞②一个被网友们反复引用的跟帖是“我们跟的不是帖子,是寂寞”。该帖的回帖已达上限。在统计日期(2011年1 月,“贾君鹏”主题帖于2012年被完全删除)截至前,共有近40 万的回帖。资料出自“百度百科”中的“贾君鹏事件”。。
美国解释学家格雷西亚(Jorge J.E.Gracia)认为,在许多情况下,文本的目的在于引起/防止作者/使用者之外的某人的行为和感情,或是发泄作者/使用者的情感并给他们带来快乐。为了做到这一点,对文本的一定程度的理解是必要前提。这种理解即是“阐释”(interpretation),合理的、有限度的阐释(the Limits of Interpretation)依赖于文本的文化功能,因为文化是一个由社会发展出来、不易改变的系统。文本在社会中的作用决定了它们怎样被对待。③欧阳康:《文本性、解释和解释学哲学》,《哲学动态》2004年第11期。对于某个受到持续、热烈关注的网络语词文本来说,它必然强调、透露或暗示了某种社会文化,而这种文化被视作“读者”所共享和共有的。文本从而超越个体的作者,成为群体的情感表达方式,反之,该文本在“意向意义/阐释意义”高度“同一性”④高度同一性,在这里并不指涉着意义理解的完全一致,而是意味着一种方向性的、总体情感上的统一与和谐。的情境中,获得强大的传播动能。
除了“表达类文本”外,网络语词文本中还有很多是“评价性文本”。有意思的是,这些文本的评价是“含蓄的”,它们看上去属于“信息类文本”,即提供用于交流的或明确指涉对象的“信息”。诸如“高富帅”、“土豪”等,文本有明确的指涉对象,即拥有某一类特征的人。但文本的目的,显然并不仅是缩略的指称,文本作者指涉特定对象,是为了表达一种感性的判断和评价——对“高富帅”、“白富美”的社会认同或向往,这样的群体成为当下“成功人士”的理想、生动的典范,这些文本的意向意义与阐释意义高度重合,从而得到广泛的传播。在广告文本、电影电视剧文本,甚至传统媒体的新闻标题⑤诸如2014年2 月27 日《广西日报》的新闻,标题为《争当时代“高富帅”》,内容为某石化工业园的产业链的新闻访谈;20013年9 月30 日《信息时报》的人物报道,题为《高富帅的优质生活》。里,该类文本频繁出现,它们大多指涉或象征“成功”和“优秀”,以及对此的认同和追求。对于此类网络语词的流行,主流文化价值对之表露了担忧:我们看到,有主流媒体把“高富帅”的意义阐释为“人品、知识和行为的优秀”,主流媒体间以“互文(Intertextuality)”的方式意欲对“新”的阐释意义进行传播,从而达到对网络语词的“改写”或“收编”的目的。但我们必须承认,这种“互文”的范畴和效果,是极其有限的,它根本无法“构成一件新的编织物”⑥原文为“构成了一件编织物”。出自Julia Kristeva,Desire in Languag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1.p.36.,无法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同。对于背景语境中的网络语词文本,在文化的共通经验和理解基础上所进行的价值评判,是“深入人心的”,它有其根系,很难被阻断或修改。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还有一类网络语词文本,既是“信息类文本”,又是“表达类文本”。但更重要的是,它的表达功能建立在信息功能的基础之上,一旦所传递的信息模糊或被遗忘,其对相关事件的情绪表达功能也就失效了。如一度流行的网络语“俯卧撑”是一个依赖于“事件情境”的“背景语境”文本。⑦在2008年的新闻发布会上,贵州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把李树芬的死因解释为:“…当陈走后,刘见李树芬心情平静下来,便开始在桥上做俯卧撑。当刘做到第三个俯卧撑的时候,听到李树芬大声说‘我走了’,便跳下河中…”资料出自“维基百科”。当它成为网络热词时,很多人根本不理解它的意思。但这个文本无疑是颇具感召力的,因为它不只提供事件信息,更表达、宣泄了情绪——一种颇具代表性、感染性、有“舆论”意味的不满情绪。①在该解释发表几个小时后,其合理性便受到质疑,并招致网民们的调侃乃至讽刺。资料出自“维基百科”。对于此类网络语词文本(如“躲猫猫”、“周老虎”等),当情绪表达功能所依赖的信息事件被淡忘时,文本自然也就失去了传播的动力:它们迅速的生长,也迅速的消亡。
我们知道,“网络语词文本”主要集中于“表达类”与“评价类”两种类型。这两类文本还有一个意义特点,即作者“意向意义”的不明确性。对于任何一个文本来说,作者生产它时总是有某种“意向(intentions of authors)”,即意欲传达给读者某种意义,并为此选择和排列符号以构成文本。这就是文本的“意向意义”。但重要的是,这种意向并不总是指向某个特定的、明确的意义。格雷西亚指出,拥有意向的作者未必能充分意识到被意欲的东西,也即是说,作者具有做某事的意向,但未必对此有充分明确的意识。②[美]乔治·J·E 格雷西亚:《文本性理论:逻辑与认识论》,汪常砚、李志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43页。对于情感的宣泄表达,以及某种感性的价值评判类文本,尤为明显。诸如“不是……是寂寞”、“…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只是个传说”等文本,原作者在生产它们的时候,其意向性并不明确:作者意欲表示、传递某种情绪或进行某种感性的价值判断,但他们自己也说不清这种感情的特定指向,或判断的依据和对象的界定是什么。作者只是具有模糊的观念,但这种观念是“模糊但确定的”:作者不必对特定意义有充分意识,也不必知道传达意义所需的语言表达方式。但作者很清楚,他想要表达的意义的限度在哪里;也就是说,尽管文本的意义空间是开放的,重要的是,这必定是有限度的开放。
因此,我们对“网络语词文本”的研究,不能忽略一个现象:一方面,虽然语词文本的意义空间是高度开放的,允许“读者”对意义进行自主理解,但对于一个流行的语词文本来说,它的意义总是能获得“约定俗成”般的理解。另一方面,对于这些意义“约定俗成”的文本来说,它们的所指虽“指向”同一个方向,但却始终无法勾勒出某种具体清晰的样态。也就是说,对于这些文本而言,既是“很有限度的理解”,同时又给予了“意义生产”充足的空间。这是“有限度中的无限”。诸如,网络语词文本“屌丝”,它指涉的总是与“成功人士”、“高富帅”相对立的群体。这一点是清晰的、可达成“共识”的;但同时,对于这样的一个群体,我们总是很难进行确切的描绘,其所指又总是含混的。“屌丝”所指涉的群体特征——习惯于自我解嘲;不放弃努力;缺少雄心壮志;保守挫折;追求生活乐趣的体验;不懂自尊;常使用某类品牌的生活物品……——它们被不断的“书写”出来、“填充”进这个文本之中,其中有些是细枝末节的,有些是含糊不清的,有些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但这个“获得共识的、有限的”意义空间却总有“无限的罅隙和留白”,等待被新的特征填充。
前面所谈到的,网络语词文本具有意向性意义模糊的特征,这可以解释文本意义在传播中不断增值的现象。正是这种模糊性,给予了阐释的足够空间。另外,从文本性理论来看,作为“生产式文本”的网络语词文本,它可以被打散、分离,在永不终止的(infinie)差异的区域内进行。③[法]罗兰·巴特:《S/Z》,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由此,新的意义被不断充实进文本,但我们如何理解以下的问题:相对于其它类型的文本,网络语词文本的符号构成非常简短(多为词语和单句),能指的选用随意性极强(如“屌丝”“土豪”等),缺少历史连贯性的解释以及语篇语境的束缚,对于这样意义模糊的文本,“解释的有限性”只能依赖于情境语境,因此,它必然比其它的文本类型更难获得意义认知上“共识”。但恰恰相反,网络语词文本却正因其“共识”而得以流行,原因何在?“作者”与“读者”的高度“同一性”(identity),它意味着“元文本”始终处于既“在场”又“缺席”的状态,这是“网络语词文本”与传统文本类型的最大区别,也是造成这种“有限—无限之融合”现象的重要推动力。
解释学对文本“解释”(interpretation)的讨论主要有三种方式。其一,欧陆哲学家倾向于把“解释”视作对文本意义的理解,它不是文本的唯一有效性理解,理解总是与主体性和文化的因素相关;其二,作为文本之理解过程的“解释”,是对文本信息的译解(decode),并不等同于信息本身。它主要在方法论层面上被讨论。最后,“解释”即可指称文本,它意味着包含了“互文”和“对话”的动态进程。“解释”意味这文本的组合,而不只是文本的添加(added text)。也就是说,“解释”是在原文本(T0)的基础上添加另一个新的文本(T1)之后,构成的那个文本(T2)。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T1 总是不能等同与T0,T1 永远是一个“新的”文本,只有这样,解释才能真正发生。否则,发生的只有重复。
对于一个添加文本的“新”,它意味着“解释者开始将文本及其元素分解成文本中并不明确的词和概念”①[美]乔治·J·E 格雷西亚:《文本性理论:逻辑与认识论》,汪常规、李志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0页。,诸如一种文本的语言翻译就是解释。因为新的语言符号具有与之前不同的外延和内涵。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除了“新的”构成文本的语言符号以外,原文本在“新的”语篇语境中的“新的”使用,也同样意味着“解释”的真正发生。在此使用过程中,文本的外延和内涵总是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即文本与其它事物之间会发生新的“关联性(relevance)”,或改变。诸如,对于“宅”这个语词文本,在语境1“他总爱宅着,沉迷于虚拟的网络社区”和语境2“与她活泼的外表不同,她其实很宅,内心安静”中,“宅”的文本意义是不同的,在1 中,它与“某种亚文化的沉迷”相关,具有负面的意义;而在2 中,它与“自主的生活方式”相关,具有中性或正面的意义。因此,我们看到,对于网络语词文本“宅”的文化意义来说,“宅文化”一直是有争议的,它潜在的评判和评判对象,一直是隐约存在但模糊不清。
对于网络语词文本来说,这种意味着“新”的真正的“解释”,它每发生一次,文本就被重新书写了一次。也即是说,网络语词文本与其它文本不同的地方在于,T2 总是替代了T0,成为新的T0(其它文本解释:T2=T0+T1;网络语词文本:T2=T0')因为网络语词文本的“读者”与“作者”是高度重合的:与“作者”相匹配的“元文本(metatext)”,对于网络文本来说,既是“在场的”又是“缺席的”——它始终“在场”,因为它唤起了人们对某种情绪的认同或回应的意欲,才得以在一次次的使用中传播扩散;同时,它又永远“缺席”,因为在它被生产出来的一瞬间,它将来的命运就与它最初的生产者之间断了关联,它仅能依赖于新的“读者/作者”的每一次使用,才能获得生命。因此,读者的每一次解释,同时也是新的作者的每一次文本生产。读者与作者在这种高度同一性之中,进行着不断的争议和强烈的认同,但争议与认同,并非泾渭分明,它们总是面临着在新的文本解释中被转化或修改的可能。诸如前文谈到的例子,主流价值对“髙富帅”所做的修改,正是一种新的“解释”。但这种解释,必须建立在对元文本潜在引用(即“在场”)的基础之上:这种修改,只能建立在对“髙富帅”这个元文本的原作者之意向意义理解的前提之上。如果新作者完全不能理解这个意向意义,他也就谈不上要去给予这个文本一种新的解释了。同时,他有权力、也的确生产了一个新的意义的文本,在他这里,原文本T0 消失了,T2 作为新的文本诞生。然而,如果T2 不能被大范围的作为T0',为新的作者所使用,它就将很快死亡。这种“争议”也将随之消失,被“认同”覆盖,或干脆转化为“认同”。因此,元文本在某种意义上的永恒“在场”,保证了文本意义总是“有限度的解释”。
结语
我们对网络语进行分类,聚焦于其中更具社会文化性的语词;再以动态的话语视角,对“背景语境下”的网络语词进行“文本”层面的分析:从文本的功能与目的、文本意义的“有限—无限性”、文本“作者/读者”的身份同一性、元文本的永恒“在场”与“缺席”几个角度来理解这样的语言现象。
我们发现,仅聚焦于网络语言的符号表象,为其贴上“粗俗”或“恶搞”的标签,是很不充分的,它阻碍了我们对语言展开更深层的认知。这种观点认为,网络语词现象是对传统语言文化的负面威胁。诸如有学者谈到,“……不利于文化的发展承传……对文化经典和传统的尊重欠缺……使得语言文化的运用呈现一种凌乱的倒退状态…我们要对越来越泛滥的‘语言秀’‘文字秀’‘恶搞秀’保持一定警惕……”①李昌文:《全媒体时代的传播语言研究》,《现代传播》2012年第12期。网络技术的广泛使用打破了规范语言自上往下的传播模式,网络语言既是“特殊的”,也是“常态的”:语言萌生于网络,从语言的诞生地和“源作者”来说,它是“特殊的”;但它一旦在意义理解上获得广泛认同,它就超出了网络的边界融入语言使用的长河之中,成为“一般的”语言,这是语言本身的内在规律。当我们在谈论所谓的“对语言文化的守护”之际,这意味着,我们已不自觉地在传统语言与网络语言之间划上了清晰的分界线,“文化”被视作历史性的、作为物的传承,而遗忘了它活生生的“在场”:“文化”本身就是流体的,它时刻处于流转之中(我们使用“过去的”和“现在的”文化的指称,只是为了对一定历时空间中所积累沉淀的习俗与样态进行更方便的比较)。网络语言的每一次生成、接受和传播,都是对由社会发展出的复杂的社会系统之表征的文化的一次突显、巩固和强调。②参见本文开头关于“文化解释学”的注释。正如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网络语词之元文本在某种意义上的永恒“在场”,保证了文本意义总是“有限度的解释”。诸如“有钱,任性”、“高富帅”、“屌丝”等网络语词的背后的推动力是社会情绪的一次次碰撞与共振,它之所以难以被消解和修改,在于社会系统的现实性。因此,网络语言现象并不是对传统语言文化的威胁,它们的区隔在网络技术的背景下只是幻想。在本文中,文化解释学的方法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支撑。
这种文化解释学的视角,内置了存在论立场的语言观,这也是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在解释问题上的融合之道:它既采用分析哲学严谨细致的方法,又立足于欧陆哲学的语言观,即语言并非作为表达思想的工具,其本性只在发生学的维度之中,“收拢着、滋养着和保存着我们的生存世界”③谢地坤主编:《西方哲学史(学术卷·第七卷):现代欧洲大陆哲学(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7页。,人的存在样态表征为语言,同时语言又滋养着存在。“思想通过语言而体现自身,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语言制约思想的发展”④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页。。因此,我们看到,网络语词文本的生成和扩散揭示的是现代人的存在样态:消费主义的热情、对物质的崇拜、替代行动的情绪宣泄、理性判断力的衰退……反过来,这些语词文本在人们对它的使用中,又悄悄构建、强化着某种价值判断。与此同时,文本意义的重新阐释、文本间的勾连,又揭示出充满差异和竞争的文化样态。语言的“增生”意味着“文化”中某个环节的突显与强调,因此,我们需要“谨慎的”,并不来自对想象中的语言之“纯粹性”的守护,而是促成广泛社会认同情绪的社会系统之内在摩擦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