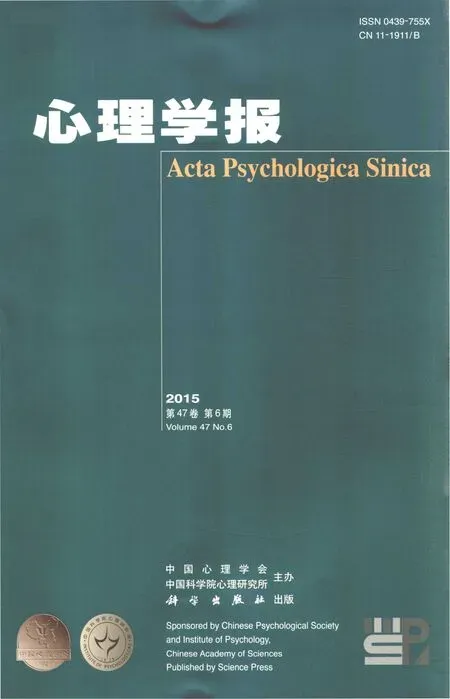三人问题解决中的惯例:测量及合作水平的影响*
张 梅 辛自强 林崇德
(1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心理系, 北京 100081) (2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875)
1 引言
在任何组织生活中, 均存在多人共同完成某项工作的情境:生产线上工人们的流水操作, 员工按照标准操作程序(SOP)完成工作……这些行为由于多次重复, 变得程序化和自动化, 意志努力逐渐减少。上述现象称为组织惯例(organizational routines)或简称惯例。惯例在组织研究中具有较长的历史。自1926年由经济学家熊彼得将其作为“组织日常工作的大杂烩(如项目清单、行政管理工作、自动化行为等)”提出之后(Becker, 2007), 许多研究者均对惯例进行过界定, 如视其为“对特定刺激的固定反应” (March & Simon, 1958)、“组织中重复的活动模式” (Nelson & Winter, 1982)等。尽管惯例的定义纷繁复杂, 但从操作定义的角度可将其界定为两人或多人在面临重复性的问题解决任务时习得的、互相依赖的、可识别的、行为模式或策略(张梅, 林崇德,辛自强, 2012; 张梅, 辛自强, 林崇德, 2013)。目前,惯例已成为组织行为学、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的研究热点, 其研究内容涉及惯例与组织结构、技术、革新、社会化和决策等变量的关系(Feldman &Pentland, 2003; Grodal, Nelson, & Siino, 2014; Salvato& Rerup, 2011)。
惯例作为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研究热点, 总体上缺乏实证研究尤其是实验研究。例如, 国际主流管理学杂志《管理研究杂志》(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和《管理科学》(Organization Science)分别于2009年和2013年设置专题征稿, 呼吁学者开展实证研究探讨惯例的起源及变革等问题。目前, 依赖于具体组织情景的诸多质性分析法仍是当前惯例研究的主流, 这包括案例分析、工作流程分析、档案分析等(Becker, 2008; Becker & Lazaric, 2009;De Boer & Zandberg, 2012; Labatut, Aggeri, &Girard, 2012)。造成上述实验研究缺乏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首先, 实验任务上的局限。惯例的实验研究起源于1994年Cohen和Bacdayan发明的扑克牌游戏(Target The Two, 简称TTT)。这是由两人用6张扑克牌合作完成的40局测验, 每局需要多步完成。随着局数的增加, 人们会用固定的行为或策略完成每局游戏, 即使有更好的方法也不再采用。随后, 惯例的实验研究大多基于TTT扑克牌游戏进行, 并发现:惯例具有路径依赖性(Egidi & Narduzzo,1997), 其形成有赖于行动者对问题空间的有限搜索(Egidi, 1996), 它与团体决策中的认知陷阱和心智模式密切相关(Bonini & Egidi, 1999), 基于时间的奖励方式要比基于步数的奖励下惯例化程度更高(Garap & Hollard, 1999)。在国内, 王建安和张钢(2008, 2010)将经典的TTT扑克牌游戏扩展为三人,证明了三人集体问题解决中也存在惯例。然而, 由于TTT扑克牌游戏任务规则(如两人分饰不同角色)、完成过程(40局游戏, 每局需多步完成)及结果分析(需要分析每局和每步的动作)较为复杂, 使其超过两人便难以进行实验操纵和结果解释, 也很难操纵和控制相关变量探讨惯例的影响因素, 由此极大地影响了基于本任务的实验研究的继续深入。自2000年以来, 仅有极少研究仍采用这一任务研究惯例。因此, 未来只有探索规则和测试简单且易于实施的实验任务, 才可能深化和拓展惯例的实验研究领域。
其次, 测量指标上的局限。这又体现为三个层面:第一, 原有测量指标不完整。Cohen和Bacdayan(1994)提出, 惯例可以从可靠性增加、速度提高、重复行为序列和偶尔的次优性四个指标进行衡量。其中, 前两个指标表明了惯例带来的问题解决效率的提高, 其表现为完成任务所用步骤和时间减少;后两个指标表明了惯例的路径依赖性, 其表现为个体在完成任务时会逐渐从“一次考虑一步”发展为“一次考虑一个组块”, 并且可能会被锁定于某行动序列,即使有更有效的方法也不会去探索。上述四个指标均是从“行为”层面阐述惯例的表现, 并未考虑虽然行为不同但采用的策略相同的情况。由此,Egidi (1996)提出了从策略即“认知”层面分析惯例的思路。至此, 惯例的评价指标实际仍不完善, 因为还缺乏“情感”方面的指标。随着惯例的形成, 个体的满意度是否在逐渐提高?其对未来的预期是否越来越积极?这在复杂的TTT扑克牌任务中均无法通过对每局的分析进行研究。第二, 原有测量指标过于复杂, 不适合在探讨惯例与其他变量关系的研究中采用。最初惯例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描述这种现象, 此时复杂的验证和描述指标较为适用, 可以全面了解惯例在不同实验任务中的表现。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 必然涉及惯例本质及其影响因素的探讨, 此时, 验证和描述惯例已不是重点, 惯例在不同条件下的表现(即惯例化程度的问题)更为重要。因此, 需要更为简洁的测量指标迅速判定惯例的存在及其程度。第三, 缺乏惯例化程度的描述指标。惯例不是一个“全或无”的概念, 它有程度的上的差别。以往, 国外惯例的诸多实验研究均未专门针对惯例化程度提出系统的量化指标, 国内王建安和张钢(2008)提出的指标仅探讨了群体认知层面(策略)的惯例化程度。然而, 从惯例的涵义上来看,它应包括认知和行为、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
针对惯例研究中测验任务的局限, 意大利认知和实验经济学家Novarese (2003, 2005, 2006, 2007)在研究团队学习时创造的“加10游戏”可能提供了解决思路。该测验由三人合作完成(其中两个或一个可为假被试), 测验规则及流程简单。游戏中, 被试分别在五个数字(0, 2, 3, 4, 10)中选择一个(
D
),然后将三人所选数字相加(和为S
), 每人每局游戏的获益(I
)基于如下规则:
游戏每局最高分为40, 最低分为‒4, 一般进行28局, 被试得分区间为[‒112~1120]。每局游戏完毕后, 被试须对本局游戏得分的满意度和对下一局的预期进行反馈。与TTT扑克牌游戏相比, “加10游戏”规则简单, 易实施, 还可设置假被试进行变量操纵。与以往的囚徒困境等博弈实验相比, 游戏中三个玩家以合作为主, 也存在一定竞争, 因而具有更强的生态效度(Novarese, 2003)。这一游戏情境是社会和组织生活中许多情境的有效隐喻(Novarese,2007):团队任务的完成需要成员间不同程度的合作; 在组织中, 个体可以以不同方式贡献力量, 即选择不同的数字, 而且可能某些人需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例如有人需要选择更大的数字(意味着本人获益相对较小)保证小组获益; 个人的努力可能对组织会影响不同, 但整体上或多或少对集体是有益的; 不同成员之间的分工提前没有计划,需要成员间自己协调(谁选择哪个数字需要自己去探索)。
以往以加10游戏为基础的研究主要用于探索团队学习过程及其对团队有效性等因素的影响, 惯例现象本身不是研究的重点。这些研究(Novarese,2005, 2006, 2007)的实验设置大多分为两步:首先让被试在前14局游戏中形成某种策略, 之后改变测验场景研究被试如何将既定策略迁移到新的情境中。研究发现, 在这种三人合作游戏中, 个体倾向于形成高度惯例化的行为, 并把以往习得的策略扩展到新的情境中去。这类研究并未对惯例本身进行描述, 仅仅研究了惯例形成后带来的后果, 认为它是学习过程的产物, 可以减少认知努力和环境的不确定性。这从侧面证实了加10游戏中存在惯例,只是缺乏对其本身的描述和验证。
针对惯例研究中测量指标上的局限, 首先, 以加10游戏为基础, 可构建相应指标体系使其测量指标更为完整, 也更为简洁。由于加10游戏每局仅需一步即可完成, 每局结束后添加对结果的情绪反应的测量并不会破坏测验的简洁性。事实上, 该任务发明之初就带有满意度和未来预期的评价指标。如果结果表明惯例在两指标上有所体现, 即可构建认知、行为和情感三方面联合的测量指标体系。其次, 对于惯例的简洁测量指标, 可从个体与群体层面依据之前研究(张梅 等, 2013)提出的利用猜测率原理分析惯例的思路构建。依据惯例的定义, 它同时包含行为和策略两个层面, 结合加10游戏本身特点, 惯例的个体层面体现为被试对不同数字的选择, 这可能存在行为上的惯例; 群体层面体现为对策略的使用, 这反应了团队间的差异。相同的惯例化行为可能体现了不同的策略。例如, 某人一直选择数字4, 可能源于集体基于“4,3,3”策略形成的惯例, 也可能源于集体基于“4,4,2”策略形成的惯例。由于加10游戏每局仅能选择一个数字或采用一种策略, 可分析所有28局游戏中选择某数字(个体)或某策略(群体)多少局就可视为形成了惯例, 而不是偶然猜到本数字或策略?利用二项分布原理, 可计算偶然选择某数字或策略的概率, 利用概率加法可求得猜得某数字或策略X次以上概率超过0.05 (或0.01)的临界点。再次, 基于加10游戏任务简洁性的特点, 惯例化程度的测量可相应简化为个体行为和小组策略两个层次, 它分别指个体选择的数字和小组采用的策略。
通过更为简洁的加10游戏任务构建出惯例的简洁测量指标后, 便可顺利开展惯例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往研究发现, 合作经验是惯例形成的重要来源, 它甚至主导着惯例的形成(孙永磊, 党兴华, 宋晶, 2014)。但这些研究仅限于理论描述, 并未通过实证研究证实。现实生活中, 不合作的情况普遍存在, 如Novarese (2005, 2007)曾证实, 惯例形成过程中会受他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广泛影响, 即人们在加10游戏中会选择5个数字中较小的数字, 以获得个人的最大收益。这种不合作的情况与完全合作、或者部分合作的情况下形成的惯例有何不同?此时形成的惯例是否仍体现出学者们(Pentland, Feldman,Becker, & Liu, 2012)普遍认为的协调控制、决策辅助和学习存储3方面的功能?这些问题在以往实验研究中均未进行探讨。这一方面是由于TTT扑克牌任务每局需多步完成, 是较为复杂的动态互动过程, 无法通过设置假被试操纵成员本身的合作水平。另一方面, 虽然以往应用加10游戏的研究(Novarese, 2007)大多通过假被试的设置让被试习得某种策略(实际上就是惯例), 但由于研究重点均未放在惯例现象上, 从未分析过它对惯例的影响。因此, 本文有必要在加10游戏中探讨合作水平这一重要变量对惯例的影响。
综上所述, 本研究的目的为:(1)验证以加10游戏为基础的三人问题解决中的惯例现象, 并构建惯例及惯例化程度的测量指标体系。(2)探讨合作水平对惯例化程度的影响, 并验证惯例及惯例化程度测量指标的有效性。为此, 本研究拟开展两项实验研究。实验1验证三人问题解决中的惯例现象并构建相应测量指标体系。实验2利用实验1提出的测量指标探讨合作水平对惯例化程度的影响。
2 实验1:三人问题解决中的惯例现象
2.1 实验目的
验证以加10游戏为基础的三人问题解决中的惯例现象, 构建惯例的测量指标体系, 并对惯例化程度进行测量。
2.2 实验方法
2.2.1 被试
通过网络招募本科生93名, 其中, 男生37人,女生56人, 涉及英语、化学、教育学等12个专业。实验时, 计算机将被试随机分到31个三人小组中,每组完成28局加10游戏。
2.2.2 实验平台设计及实验流程
在国外, 加10游戏一直采用基于PHP这种服务器脚本语言搭建的网络平台进行测试。然而, 以往测试平台只有一个页面, 包括数字选择、满意度反馈、对下一局的预期多项任务, 游戏的互动性体现不明显, 难以形象地展现三人合作解决问题的过程。因此, 本研究采用LAMP (即Linux+Apache+Mysql+PHP)软件开发技术, 重新搭建动态的网络平台, 将数字选择与结果反馈分页呈现, 使界面更友好、动态性更强。
本实验开始前, 向被试简要说明实验流程, 并重点说明实验的获益规则, 即依据被试28局游戏的得分区间, 给予被试5~15元不等的奖励, 具体为:得分在区间[‒112~196]得5元, 在[197~504]得8元, 在[505~812]得12元, 在[813~1120]得15元。之后, 新测验平台将依次呈现如下页面:
(1)注册及指导语页面。向被试说明实验流程及获益规则后, 向其提供服务器IP地址, 让其进行用户名注册。注册成功后页面自动跳到指导语页面,点击相应超链接即可查看游戏指导语。点击“正式实验”超链接便可跳转回注册页面进行登录。
(2)测试页面。被试登录后, 会进入有多个房间的界面, 被试可随机进入某房间, 每个房间满3人方可开始测试。正式实验页面分为3部分:上半部分包括房间号、局数信息、“试玩游戏”超链接、“游戏说明”超链接。被试在正式实验开始前可试玩一局游戏, 并在实验中随时查看游戏指导语; 中间部分为5个数字选项, 被试需选择其中一个点击“确定”按钮, 此时若其他两人还未选择, 界面将显示“等待其他玩家……”, 直至3人均做出选择系统将跳转到反馈界面, 结束本局游戏。整个过程3人无法交流。下半部分为3名被试头像的矢量图, 被试头像位于中间且下方高亮显示其用户名, 其他两名玩家分别显示为“匿名玩家甲”和“匿名玩家已”。
(3)反馈页面。3名被试依次在5个数字中选择后, 电脑给出包含3部分内容的反馈页面:上半部分为说明三人相加所得和、各自得分和各自累计得分的收益表格; 中间部分为对本局结果的满意度评价, 让被试对本局满意度进行0~10的星级评定, 选择的星星越多, 表示越满意; 下半部分为对下一局的预期, 让被试对下一局三人相加所得的和在“等于10”、“大于10”、“小于10”三个选项中进行选择。
实验过程中, 电脑自动记录每个玩家所选数字、所用时间(秒)、小组相加所得和(
S
)、本局得分(I
)、对本局满意度、对下一局的预期。测试完毕后,让被试填写包含个人(如性别)和实验信息(如房间)的问卷, 并对其游戏过程中采用的策略及其与组员的互动过程进行访谈, 题目为“你们三人在游戏过程是否形成了一定的策略或方法?它是什么?你们如何合作达到?”
表1 31组被试28局游戏表现描述
2.3 实验结果
2.3.1 各组被试惯例表现描述
在验证三人小组及被试是否形成惯例前, 应客观分析他们的表现在28局重复的问题解决任务中是否存在一定规律。若存在, 则可视为惯例的表现。
首先, 对31组被试在28局游戏中的各项指标进行了描述。表1为较有代表性的几组被试以及31组被试整体上各项指标情况。其中,
M
为各小组人均得分, 其由三名被试28局游戏累积得分除以3得到, 区间为0至1026.67;M
为各小组整体满意度, 由三名被试所有28局游戏满意度的和除以84(28×3=84)得到, 区间为0至10。由表1可知, 31组被试在28局游戏中三人相加所得和等于10的平均局数为16.77, 小于10的平均局数为4.9; 所有被试组28局游戏平均得分为775.53, 总平均满意度为8.08。其中, 第10、20和23组被试28局游戏均相加所得和均等于10, 其累计得分1026.67分, 这是最低组305分(第14组)的3倍多, 而第6组三人相加所得和等于10的局数最少; 第7组平均满意度最低, 第20组最高, 在对下一局的预期上, 第20和23组预测等于10的次数最多, 第6组最少。
其次, 研究对28局游戏中31组被试的表现进行了分析。图1为28局游戏中93名被试对5个数字的选择(a)和对下一局预测(b)的情况。经计算, 5个数字中选择4的人数最多, 均值为35.46, 选择10的人最少, 均值为6.86; 对下一局预期选择等于10的人数最多, 均值为64.75, 小于10的人最少,均值为5.75。

图1 每局游戏中93名被试的数字选择(a)及对下一局的预测(b)
再次, 研究通过事前分析, 加10游戏中采用的所有策略有如下5种(见表2)。其中, 最优策略是使三人所选数字相加所得和等于10的4,3,3、4,4,2、10,0,0策略; 次优策略是使相加所得的和大于10的策略, 此时, 可以至少一人选择10, 或者至少两人选择4。除上述4种情况外, 其余所有三人相加所得和小于10的情况均可视为不明确的策略。由上述分析可知, 每人每局的最优策略是选择数字4,因为4,3,3、4,4,2和>10的策略均与4相关; 次优的策略是选择3或10, 因为4,3,3策略会用到3, 而选10三人相加所得的和必定会等于或大于10。

表2 三人合作游戏中的策略描述
图2显示了31组被试每局所采用策略的情况。经计算, 第1局时, 有11组被试采用了最优策略4,3,3 (5组)、4,4,2 (5组)和10,0,0 (1组), 有14组采用了次优策略>10, 有6组被试无明确策略。第28局时, 22组被试采用了最优策略, 其中12组采用4,3,3策略, 7组采用4,4,2策略, 3组采用10,0,0策略; 采用>10策略的组数下降为3组, 未形成明显策略的仍有6组被试(但它们与第1局的6组不同)。

图2 各组被试每局游戏所用策略分析
2.3.2 惯例的验证和描述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 经过28局游戏, 大多被试及三人小组均形成了解决问题的策略。他们不仅会选择最容易达到最优策略的数字4和3, 还会坚持先前采用过的策略。这是否意味着惯例的存在?下面分别采用不同指标进行分析:
首先, 采用上述5个验证指标进行描述:(1)可靠性增加。以被试每局得分(
I
)为因变量, 以局数为自变量的回归分析表明, 随着完成局数的增多, 被试每局得分逐渐增加(β
= 0.12,t
(2603) = 6.09,p
<0.001)。(2)速度提高。以被试完成每局游戏的时间为因变量, 以局数为自变量的回归分析表明, 随着完成局数的增多, 被试完成每局游戏的时间逐渐减少(β
= ‒0.15,t
(2603) = ‒7.23,p
<0.001)。(3)重复行为。28局游戏中, 被试选择4的频率最高(38.21%), 选择10的频率最小(7.37%)。事后访谈进一步证实了数字选择的重复性。例如, 有被试说“我们有一次组合为10之后就不变了。我一直选4他们一直选3” (4)基于特定策略的行为模式。如表2所示, 三人小组在28局游戏中逐渐形成了最优策略4,4,2、4,3,3、10,0,0和次优策略>10。事后访谈表明, 被试在有意识地采用不同策略, 如有人这样描述他们策略的发现“起初的几轮都是处在摸索环节, 有时大于10, 有时小于10, 后来大家发现4-2-4的组合, 可以达到最优配置, 就不变了”。(5)偶尔的次优性。这主要体现为三人小组坚持现有能获益的策略, 不去探索获益更大的策略。例如, 第6组28局游戏中有22局采用了>10策略, 而不去尝试探索其余3种等于10的策略。5个指标中, 前3个是从个体表现层面, 后2个是从群体策略层面验证和描述惯例表现。
其次, 结合加10游戏的特点, 还可构建如下情感方面的指标:(6)满意度。以被试每局的满意度得分为因变量, 以局数为自变量的回归分析表明, 随着完成局数的增多, 被试组对每局游戏的满意度在逐渐增加(
β
= 0.15,t
(2603) = 7.49,p
<0.001)。(7)预期。分别以每一局游戏中预期下一局大于、小于、等于10的人数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表明:随着局数的增加, 对下一局预期大于和小10的人数均显著减少(β
= ‒0.94,t
(2603)= ‒140.14;β
= ‒0.96,t
=‒166.21;p
s <0.001); 对下一局预期等于10的人在显著增多(β
= 0.98,t
(2603) = 238.40,p
< 0.001)综合上述7个指标, 可以全面验证和描述加10游戏中的惯例现象。然而, 若研究仅需粗略判断惯例现象的存在而非对其详细描述, 则需要更为简洁的方法。延续以往(张梅 等, 2013)利用猜测率分析惯例的思路, 可从如下两个层面进行判定:

表3描述了93名被试惯例形成的情况。由表可知, 绝大多数人均形成了惯例, 数字4和3上形成的惯例最多, 数字10上形成的惯例最少, 有5人同时在两个数字上形成了惯例。
(2)群体层面。计算每局由表2所示的4种选择的28局游戏中, 三人小组选择某策略多少次, 才能证明小组形成了惯例, 不是偶然猜测?依据上述计算方法,
n
= 28,p
= 0.25,q
= 0.75,np
> 5, 此二项分布接近正态分布, 故:μ
=np
=7,σ
= 2.29。根据正态分布原理,μ
+1.645σ
= 10.77 ≈ 11。即完全凭猜测,28局游戏, 偶然猜测选择某策略11至28次的概率只有5%。因此, 可推论28局游戏中某小组采用某策略11次及以上就不是凭猜测, 而是形成了惯例。
表3 93名被试在所选数字上惯例的形成情况
表4为31组被试策略的使用情况, 由表可知,大多数三人小组均形成了策略惯例, 采用最多的是4,3,3策略, 最少的是10,0,0策略。

表4 31组被试在所使用的策略上惯例的形成情况
2.3.3 惯例化程度的测量
由上可知, 个体和小组在以加10游戏为任务的三人问题解决中存在惯例行为。如何衡量个体及小组之间惯例水平的差异?这涉及惯例化程度的概念。它是一个连续变量, 代表了惯例从无到有的不同水平。与惯例的描述对应, 惯例化程度也涉及个体与群体、行为和认知两个层次, 共四个方面。结合加10游戏自身特点, 个体层面仅能测量数字选择的行为表现无法分析具体策略, 群体层面仅能测量三人共同采用的策略, 无法分析具体的行动序列, 因此, 惯例化程度的测量指标可分为如下两个层面:
个体层面——数字惯例化程度。它是每个被试在28局游戏中坚持的数字, 其计算方式为每名被试在28局游戏中选择最多的数字的次数除以28再乘以100。经计算(见表5), 93名被试惯例化程度最高的为100% (16人), 最低的为32.14%, 在50%以下的有11人, 90%至100%间有42人, 其中100%惯例化的有16人。此外, 将小组内三人数字惯例化程度平均即为小组的惯例化程度。只有3组被试的平均惯例化程度在50%以下(见表5)。
群体层面——策略惯例化程度。它是三人小组在28局游戏中坚持的策略, 其计算方式为三人小组在28局游戏中采用最多的策略除以28再乘以100。经计算, 有9组被试的惯例化程度在50%以下, 最小值为21.43% (见表5)。

表5 不同惯例化程度的衡量
3 实验2:合作程度对惯例的影响
由实验1可知, 在加10游戏为基础的重复问题解决中, 通过多轮游戏, 三人小组无论数字选择行为还是所采用的策略均形成了惯例, 并表现出满意度和未来获益预期的上升。这一过程不允许进行言语交流, 被试的获益完全取决于三方的合作程度。而当合作水平不同时, 所形成的惯例会有何不同?对于这个问题, 由于以往对惯例这种现象仅限于描述和解释, 未曾进行过实验验证。本研究在实验1提出的惯例及惯例化程度测量指标的基础上, 探讨了合作水平对惯例的影响, 以回答上述问题。
3.1 实验目的
通过应用惯例及惯例化程度测量指标, 探讨不同合作水平, 即完全合作、有条件合作和不合作对惯例化程度的影响。
3.2 实验方法
3.2.1 被试
通过网络招募本科生96名, 其中, 男生45人,女生51人, 涉及日语、通讯、法学等16个专业。正式实验时, 将所有被试随机分配到3个实验组。每种实验条件下32人。
3.2.2 实验设计及步骤
研究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 自变量为两位假被试的合作程度, 分为3种水平:(1)完全合作:不论真玩家选择哪个数字,
S
(i
)均等于10; (2)有条件合作:一个假玩家固定选择数字4, 只有当真玩家选择数字3时, 另一个假玩家才会选择数字3, 使S
(i
)等于10, 否则另一个假玩家会选择0, 使S
(i
)<10。(3)不合作: 一个玩家固定选择0, 另一玩家随机选择2,3,4, 且保证S
(i
)小于10 (仅选择10时大于10), 真玩家只能尽量避免获得负收益。在实验1搭建的网络平台基础上, 本实验继续应用LAMP技术重新搭建一个实验平台。被试的登录步骤同实验1所述。被试登录后, 进入反映上述3种处理水平的房间。A房间为完全合作, B房间为有条件合作, C房间为不合作。进入每个房间后, 实验页面同实验1, 以体现实验的真实性。反馈界面与实验1不同的是不显示其他两位玩家的得分及所选数字, 以增加实验的真实性。实验开始前向被试告知实验的简单流程并说明获益规则为“得分越高,获益越多, 依据得分将获得5~15元不等的奖励”。
所有被试需在计算机上完成28局游戏, 游戏过程中计算机自动记录被试进行数字选择的反应时、选择的数字、每局的获益, 满意度和对下一局的预测得分。由于存在不同的实验处理统一给予被试10元报酬。测试完毕, 被试填写实验1中的反馈问卷。

表6 各组被试不同实验处理下的基本表现
3.3 实验结果
3.3.1 不同实验处理条件下的惯例表现
表6显示了不同实验处理条件下, 各组被试的表现。由表可知, 3种不同实验处理条件下, 各项指标得分存在一定差异。分别以每局游戏平均得分、时间和满意度为因变量, 以3种实验处理条件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3种实验处理下三项指标均差异显著。事后检验表明, 在每局平均得分上, 三组之间两两差异显著; 在所用时间上, 不合作组所用显著低于其他两组, 完全合作组与有条件合作组之间无显著差异; 满意度上, 完全合作组显著高于其他两组, 有条件合作组显著高于不合作组。对下一局预期的卡方检验表明, 3种处理条件下,对大于、等于、小于10的3种情况及预期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上述各组差异是否意味着3种实验处理下均存在惯例?按照实验1中提出的简单指标进行分析。即判断28局游戏中选择某数字是否大于等于10次。由表7可知, 96名被试中, 只有6名被试没有形成惯例。完全合作条件下, 有15组被试在数字0上形成了惯例, 有条件合作条件下, 25组被试在数字3上形成了惯例, 不合作条件下, 27组被试在数字10上形成了惯例。上述惯例表现在同一实验处理条件下经卡方检验, 均较其他策略的惯例更显著,
p
s < 0.001。
表7 不同实验处理条件下不同数字上形成惯例的人数

表8 不同实验处理条件下的数字惯例化程度

表9 不同实验处理下策略描述
3.3.2 不同实验处理下的惯例化程度比较
由实验1可知, 加10游戏中的惯例既可表现为对不同数字的选择, 还可表现为对不同策略的固着。但由于只有一个真被试, 所以策略与对数字的选择指标基本重合, 例如, 被试选择0, 代表他想采用的是10,0,0策略; 选择3代表4,3,3策略。
首先, 研究分析了不同实验处理下, 被试选择最多的数字的次数, 以及据此计算出的惯例化程度的差异, 结果见表8。
为检验上述差异是达到显著性水平, 对3种处理条件下对不同数字的选择次数进行了卡方检验。结果表明, 3种实验条件下惯例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χ= 65.90,
p
< 0.001。通过三个小组的两两卡方检验比较发现, 完全合作组与有条件合作组、不合作组均达到显著差异χ= 49.62,p
< 0.001; χ=57.04,p
< 0.001; 但后两组之间无显著差异χ=0.27,p
> 0.005。这说明, 不合作或有条件合作间惯例化程度无差别, 但两组与完全合作组相比, 惯例化程度更高。其次, 研究从各组所采用策略(即惯例)的优劣程度分析了惯例化程度的差异。如表9所示, 每种实验处理条件下均有最优策略、次优策略和最差策略。例如, 在完全合作条件下, 由于不论真玩家选择哪个数字, 两个假玩家会全力配合他的选择, 因此被试选择最小的数字0, 个人获益最高, 为40分;选择2时, 获益次多, 为38分; 而选择10时, 获益最少, 为30分。选择3, 4则为其他策略。
在上述事前分析的基础上, 统计了3种实验处理条件下不同策略的使用情况。表10显示了不同策略在同一实验处理下的使用次数, 以及同一策略在不同实验处理下的使用次数。
首先, 经卡方检验, 最优、次优、最差和其他策略中同类策略的使用次数在不同实验处理条件下的差异均达到了显著水平(见图3), χ= 65.90, χ=65.67, χ= 51.70, χ= 350.64,
p
s < 0.001。在最优策略的使用上, 不合作条件下使用次数最多, 为61%, 完全合作条件下最少, 为36%。在次优策略的使用上, 有条件合作的条件下使用次数最多, 为21%, 完全合作条件下最少, 为8%; 在最差策略的使用上, 不合作条件下最多, 为16%, 完全合作条件下最少, 为5。在其他策略的使用上, 完全合作条件下最多, 为51%, 有条件合作条件下最少, 为10%。其次, 不同策略在同一实验处理条件下使用的次数的差异也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p
s < 0.001。结合表9可知:在完全合作条件下, 被试使用最多的是其他策略, 具体表现对数字3和4的选择上, 其次为最优策略, 即选择0。在有条件合作条件下, 使用最多的是最优策略, 即选择3, 其次为其他策略,即选择10。在不合作条件下, 使用最多仍然是最优策略, 即选择10, 其次为最差策略, 即选择4。
表10 不同实验处理条件下的策略使用次数

图3 不同实验处理条件下被试不同策略的使用频率
4 讨论
4.1 加10游戏中的惯例现象
本研究通过实验1发现, 加10游戏不仅可用于研究团体学习, 也非常适合作为惯例实验研究的任务。本任务虽然简洁, 但提供了惯例描述和测量的多层面指标:
首先, 沿用之前研究(张梅等, 2013)采用的利用猜测率分析惯例的思路, 可对加10游戏进行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的简单判定。个体层面的惯例判断反映的是惯例涵义中March和Simon (1958)等认为的行为模式的方面。通过计算发现, 在每局有5种选择的28局加10游戏中, 选择某数字10次及以上就不是猜测, 而是形成了惯例。沿着这一思路,即可快速分析在不同实验条件下个体是否形成了惯例(见表3)。群体层面的惯例反映的是Egidi (1996)等认为的策略的方面。通过计算发现, 在每局有4种策略选择的28局游戏中, 某小组采用某策略11次及以上就不是猜测, 而是形成了惯例。据此, 可如表4所示描述不同小组或团队策略层面是否形成了惯例, 及其采用情况。同理, 未来还可计算数字选择及局数不同的改编版加10游戏中个体惯例化行为的量化描述。这相比Cohen和Bacdayan (1994)提出的四个描述指标更易操作, 也更利于推广。
其次, 基于以往研究, 惯例的详细刻画可以从7个方面, 3个层面进行。行为和认知两个层面的5大指标已在以往研究(Cohen & Bacdayan, 1994; 张梅 等, 2013)中得到广泛验证。行为层面的指标包括可靠性增加、速度提高、重复的行动序列; 认知层面包括基于特定策略的反应模式及偶尔的次优性。情感层面的2个指标属于加10游戏中特有。本研究发现, 随着局数的增加, 被试对每局得分的满意度在逐渐增加, 对下一局的预期变得更加积极。这说明, 随着局数的增加, 三人组成的小组解决问题的效率不仅体现为客观指标, 如收益、速度等, 还可体现为主观指标如满意度、预期。这3个层面可与当前组织行为研究中有关团队有效性的研究相对接, 团队有效性可从绩效、满意度和团队生命力三方面测量(林绚晖, 卞冉, 朱睿, 车宏生,2008)。其中, 团队生命力指团队能否保持良好的态势继续存在和运行, 加10游戏中对下一局的预期反映了这项指标。
4.2 惯例的刻画:指标体系及惯例化程度
结合以往以TTT扑克牌任务为依托的一系列研究(Bonini & Egidi, 1999; Egidi, 1996; Garap &Hollard, 1999; Marques Pereira & Patelli, 1996)及本研究可知, 两人以上的重复合作问题解决任务中,普遍存在惯例现象, 即随着任务的重复进行, 合作者们会逐渐形成固定的行为模式或策略。与非合作的问题解决情境不同, 合作问题解决强调的是集体主义和团体理性, 惯例现象的本质是为了群体获益。合作者们在长期的无限合作任务中会根据自身和竞争对手过去的策略, 不断调整自身的策略, 以取得长期的收益率(张朋柱, 薛耀文, 2005)。只要存在两人以上团队重复性解决需合作完成任务的情景, 均可分析惯例的表现。在本研究及以往研究(Cohen & Bacdayan, 1994; Egidi, 1996; 张梅 等,2013; 王建安, 张钢, 2008, 2010)的基础上, 可尝试建立一个全面的指标体系描述和测量惯例现象由图4可知, 惯例现象的判定和描述分为2个层次:(1)整体判定和描述。若研究需要快速确认问题解决任务中是否存在惯例现象, 且目的不是为了详细刻画各层面的表现, 则可采用利用猜测率分析惯例的思路, 从个体和群体两个角度来刻画惯例。(2)详细判定和描述。这又可分为行为、认知和情感三个角度若干个指标。依据上述指标即可描述惯例在相应问题解决任务中的详细表现。
惯例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思维现象, 仅建立相应验证和描述指标对其进行刻画还不够, 科学研究终极目的是实现预测和控制, 这就需要了解惯例在不同情景下的程度差别, 以便实现对其的操纵。因此, 需要构建惯例化程度的测量指标。本研究在以往研究者(王建安, 张钢, 2008)提出的思路的基础上, 从量化指标的角度, 提出了衡量惯例化程度的衡量指标, 它与惯例的涵义及其整体判定的指标一致的, 分为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 取值范围在1%至100%之间。前者采用合作者个人行为(如选择某数字)的频率来衡量, 后者采用合作者群体共同采用的策略的频率来衡量。实验2即是在实验1构建的惯例化程度测量指标基础上比较了不同合作水平对惯例的影响。

图4 惯例现象测量和描述的指标体系
4.3 合作程度对惯例化程度的影响:危机情境下的最优选择
综合上述分析, 惯例作为一种普遍的思维现象,是认知、行为和情感的统一。弄清楚这一现象的实质后, 进一步的问题是:其存在的价值体现哪里,它是否和个体思维中的定势一样阻碍问题解决策略的探索?
本研究通过实验2对合作情境的操纵探讨了上述问题, 结果发现惯例化程度在不合作或有条件合作的情况下更高, 在完全合作的条件下最低。上述结果一方面源于对风险的规避。在有条件合作和不合作条件下, 被试选择其他策略的风险较大。例如,在有条件合作条件下, 被试如果不选择数字3, 而选择4或2, 便会获得负分。因此, 被试会逐渐固定选择3而形成高惯例化行为, 不再探索新策略。相反, 在完全合作条件下, 无论被试选择哪个数字风险均较低且均可获益, 此时被试会不断探索不同策略, 表现出惯例化水平低的现象。另一方面, 上述结果体现了Simon (1991)提出的有限理性理论所示的原理, 即人们在决策中会追求“满意”的而非“最优”的结果。在合作氛围较好的情况下, 被试不去坚持理智上最优的问题解决方案(即10,0,0策略), 而去不断探索其他既有利于团队又有利于个人的(即4,4,2和4,3,3策略)满意策略, 进而表现出应用的策略分散, 惯例化程度低的现象。这一过程与实际生活中团队的创新行为类似, 均体现为突破原有思路局限探索新的问题解决方案。从结果上看, 通过创新行为, 团队最终获得了更多收益和满意度, 例如,完全合作比有条件合作条件下仅使用4,3,3策略的获益要高。这与以往研究发现的团队合作或创新氛围通过影响员工个体的态度、动机、创新行为, 进而促进整个组织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的提升的结论相一致(方来坛, 时勘, 刘蓉晖, 2012)。由此可见, 惯例与思维定势常起到负面作用不同, 它在多人问题解决任务中一般作为最适宜策略存在, 尤其当合作氛围不好时, 它会成为危机情境下的最优选择, 更多起到正面积极作用。上述发现不仅为未来合作问题解决中惯例现象影响的研究提供了启发,还为团队创新研究从组织惯例及其变革入手提供了思路。
Becker, M. C. (2007). Routines——A brief history of the concept. In S. Ioannides, & K. Nielsen (Eds.),
Economic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Boundaries,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Becker, M. C. (2008).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Cheltenham, UK: Elgar.Becker, M. C., & Lazaric, N. (2009).
Organizational routines:Advancing empirical research
. Cheltenham, UK: Elgar.Bonini, N., & Egidi, M. (1999).
Cognitive traps in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 CEEL Working Papers 1999-04, Computable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Trento, Italia.Cohen, M. D., & Bacdayan, P. (1994).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are stored as procedural memory: Evidence from a laboratory study.
Organization Science, 5
(4), 554−568.De Boer, E. A., & Zandberg, T. (2012). Decision-making by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The influence of agency and personality traits on deviating from formal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Journal of Quality Assurance in Hospitality &Tourism, 13
(4), 316−325.Fang, L. T., Shi, K., & Liu, R. H. (2012). Review on team innovation climate.
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 33
(6),146−153.[方来坛, 时勘, 刘蓉晖. (2012). 团队创新氛围的研究述评.
科研管理,33
(6), 146−153.]Egidi, M. (1996). Routines, hierarchies of problems, procedural behaviour: Some evidence from experiments.. In K. Arrow,E. Colombatto, & M. Perlman (Eds.),
The ra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behaviour
(pp. 303−333). London:Macmillan.Egidi, M., & Narduzzo, A. (1997). The emergence of path-dependent behaviors in cooperative contex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5
, 677−709.Feldman, M. S., & Pentland, B, T. (2003). Reconceptualizing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as a source of flexibility and chang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8
(1), 94−118.Garap, A., & Hollard, M. (1999). Routines and incentives in group tasks.
Evolutionary Economics, 9
, 465–486.Grodal, S., Nelson, A., & Siino, R. (2014). Help-seeking and help-giving as an organizational routine: Continual engagement in innovative work.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7
(1), 5−52.
Labatut, J., Aggeri, F., & Girard, N. (2012). Discipline and change: How technologies and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interact in new practice creation.
Organization Studies, 33
(1), 39–69.Lin, X. H., Bian, R., Zhu, R., & Che, H. S. (2008). Team personality composition and team effectiveness: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team process.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40
(4), 437−447.[林绚晖, 卞冉, 朱睿, 车宏生. (2008). 团队人格组成、团队过程对团队有效性的作用.
心理学报, 40
(4), 437−447.]March, J. G., & Simon, H. A. (1958).
Organizations
. New York: John Wiley.Marques-Pereira, M. A., & Patelli, P. (1996).
The emergence of cooperative playing routines: Optimality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Nelson, R. R., & Winter, S. G. (1982).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Novarese, M. (2003). Toward a cognitive experimental economics. In S. Rizzello (Ed.),
Cognitive paradigms in economics
. Routledge, London.Novarese, M. (2005). Individual learning and team functioning.
TheICFAI Journal of Managerial Economics,
(2), 29−45.Novarese, M. (2006). The possible contribution of empirical analysi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organizational complexity.
Journal of Social Complexity, 2
(2), 6–19.Novarese, M. (2007). Individual learning in different social contexts.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36
(1), 15−35.Pentland, B. T., Feldman, M. S., Becker, M. C., & Liu, P.(2012). Dynamics of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A generative model.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49
(8), 1484−1508.Salvato, C., & Rerup, C. (2011). Beyond collective entities:Multilevel research on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and capabiliti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37
, 468–490.Simon, H. A. (1991). Bounded rationality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Organization Science, 2
(1), 125−134.Sun, Y. L., Dang, X. H., & Song, J. (2014).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routines formation and future prospects.
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36
(3), 56−64.[孙永磊, 党兴华, 宋晶. (2014). 合作组织惯例形成影响因素研究述评与未来展望.
外国经济与管理, 36
(3), 56−64.]Wang, J. A., & Zhang, G. (2008). Knowledge, routines and performance in collective problem solving.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0
(8), 862−872.[王建安, 张钢. (2008). 集体问题解决中的知识、惯例和绩效.
心理学报, 40
(8), 862−872.]Wang, J. A., & Zhang, G. (2010).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behavioral routines and dynamic capabilities in collective problem solving.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2
(8), 862−874.[王建安, 张钢. (2010). 集体问题解决中的认知表征、行为惯例和动态能力.
心理学报, 42
(8), 862−874]Zhang, M., Lin, C. D., & Xin, Z. Q. (2012). Advances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Studies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10
(4),313−319.[张梅, 林崇德, 辛自强. (2012). 惯例的实证研究进展: 心理学的视角.
心理与行为研究, 10
(4), 313−319.]Zhang, M., Xin, Z. Q., & Lin, C. D. (2013). The measurement and microgenetic study of routines in two-person problem solving.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5
(10), 1119−1130.[张梅, 辛自强, 林崇德. (2013). 两人问题解决中惯例的测量及其微观发生研究,
心理学报, 45
(10), 1119−1130.]Zhang, P. Z., & Xue, Y. W. (2005). Analysis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yer perception style and willingness to cooperate.
Journal ofManagement Science in China, 8
(5), 1–9.[张朋柱, 薛耀文. (2005). 博弈者认知模式与合作意愿度分析.
管理科学学报, 8
(5),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