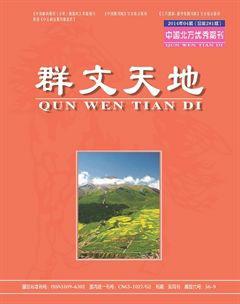草原王国吐谷浑(三)
任玉贵+解生才
茶马互市
从秦汉时代开拓边疆,到隋唐的大一统,中国疆域便有了扩大。众多的兄弟民族,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但由于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版图广大,地域辽阔,社会发展阶段自然很不一致。一般来说,边疆地区生产发展比内地较为落后,缺乏粮食和日常用品,而他们所生产的大量牛、羊、马匹和畜产品,又是内地所特别需要的。古时候内地与边疆物品的交流,一般是通过“进贡”“赏赐”两种方式来进行的。
日月山,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所使然,长期以来经济是以自给自足的牧业经济为基础的,从诸羌时代起、各民族牧民群众就繁殖适应高原气候特点的耐寒畜种,青藏高原的藏系羊,个头大而耐寒、长期以来解决牧民的主要食物———肉食,主要服装———皮袄,以及毛织等用品;他们牧羊、犏牛以解决蓄力驮运,住房———牦牛帐篷,油料———酥油,饮料———牛奶等生活问题;他们饲养马匹、解决了交通工具问题。历史上与中原地区进行“茶马互市”以换取必须的日用生活,如粮、油、布、丝、茶、瓷等,也是提高生活质量的必然追求和实际需要。
茶,尤其是湖南益阳出产的砖茶和出自四川的松潘茶,一向都是高原民族的生活必须品。时至今日,这种茶需求有过及无不及。据《西宁府新志·文艺》记载:青海少数民族“人喜啖生物,无蔬茹醋酱,独知用盐为滋味,而嗜酒及茶。”对这种现象,清初大学者顾炎武这样解释:“茶之为物”西戒、吐谷浑,古今皆仰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看来,居住在青藏高原民族喝茶主要是为了消食和健胃。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之说。
吐谷浑与南朝的经济具有非常实用和现实的互补性,南朝经济以农业为主,需要大量的畜牧业产品,吐谷浑是畜牧业经济,需要大量的农业产品和手工业品。这种经济结构造成的互补现象,在封建时期的中国是极其常见的,也是极其正常的。《梁书》中记载:“其(吐谷浑)地与益州相邻,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教其书记,书之辞译,稍桀黠矣。”
唐代青海的畜牧业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青海有良好的畜牧业自然条件。吐谷浑进居青海草原后仍以畜牧经济为主,史称“俗养牛羊、取乳酪供食,兼取毛为褐而衣焉”,“其畜牧、逐水草、无常所”。“其兽,牦牛、名马、犬、羊、天鼠之皮可为裘,独峰驼驰千里”,吐谷浑经营畜牧业的生产技术已相当进步。椐藏文史记载,“俗皆土著,有栋宇,织毛牛及羊毛覆之”,“男女并衣裘褐,仍被大毡,不知耕嫁,土无五谷,气候多风寒、以牦牛、马、驴、羊、豕为食。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降雪”。吐谷浑人世代以畜牧业为生,创造和积累了适应本地高寒气候的生产经验,为青海畜牧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青海畜牧业中养马尤为发达。吐谷浑人培育的“青海骢”在唐代仍驰名于世。吐蕃在河曲之地培育的河曲马也名声远扬。李白的《天马歌》、杜甫的《骢马行》、白居易的《阴山兴》。青海诗人吴栻在《青海骏马行》中写道:“极目西平大海东,传来冀北马群空。当年隋求龙种,果能逐电又追风”,以辉煌的诗句赞美过这些良马的雄姿和超群,反映了吐谷浑时代养马业极盛一时的历史伟业。
据《青海通史》记载:“唐朝初年,在平定了盘踞金城的薛举后,以送回被隋留作人质的吐谷浑王伏允长子慕容顺为条件,遣使约吐谷浑夹击盘踞凉州的大凉王李轨。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伏允出兵助唐灭李轨,唐送慕容顺回青海地区,双方建立了和好关系。”
作为进一步完成大一统事业的唐朝,在削平薛举、李轨的割据后,便在青海东部地区设置鄯州刺史,驻乐都,以今西宁为鄯州县。这种措施,使西陲重地与祖国内地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但对吐谷浑来说,感到有点不安,因此不免有一些小冲突。武德八年(624年),唐派广德郡公李安远来青海(这里青海指青海湖,日月山)与吐谷浑和好,双方达到互市协议。成为青藏高原第一个茶马互市而首拔头筹,这件事情在《旧唐书·李安远传》记载:“使于吐谷浑、与敦和好,于是,吐谷浑。允请与中国互市,安远之功也”。当即《册府》所书者云:“非仅吐谷浑一族,盖此地诸要求于互市于此,边场利之”,足见茶马互市的重要性。在封建社会中,各民族间联姻外,互市又是促进文化与产品交流、加强相互来往的一条重要渠道。从此吐谷浑的龙驹和牛、羊被交换到内地,而内地的丝、茶及日用品。也源源不断进入西部广大地区,满足了边疆地区兄弟各民族的需要,促进了民族间的进一步团结。
又据《青海通史》记载:唐太宗非常重视茶马互市,主动示好,于赤岭(今日月山)设立官方茶马互市。以茶换取战马和耕牛,从贞观到(627—665年)将近40年间,唐朝的官马发展到70.6万匹。唐置八司四十八监以掌之。“跨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犹为狭义,更析为监,布于河曲丰矿之野,乃至容之。于斯之时,天下以缣易一马,秦汉之盛,未时闻也”。文中“河曲丰矿之野”即今青海黄南、海南和果洛藏族自治州北部一带,是当时重要的牧养管马地区。后来,由于河南之地一度划增吐蕃,影响到唐官马的发展,开元初,牧马下降到24万匹。玄宗任用王毛仲为太仆卿主持马政,用心于政,与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在赤岭互市,以茶、丝绢等易马,开元十三年(725年)官马又发展到43万匹。
唐代大规模发展官马,据《新唐书·兵志》记载:最好时陇右马牛驼共60万头,其中马占30万头,当时牧监,随着西域良马引进、转送、杂交及繁育,青海骢等已成为唐马的优良后代。
吐谷浑与唐朝内地的经济贸易时双方都获得了可观的利益,大大弥补了各自经济上存在的不足,大量马匹源源不断入内地,保障唐朝马政的正常运作,支持了边防。而经济落后、物资匮乏的吐谷浑由于得到来自内地的不可或缺少的经济补给“释毡裘,裘纨绮羡慕华风”在经济上得到长足发展。吐谷浑人的生活也蒸蒸日上。在政治上起到与邻安边定民,友好往来的巨大作用,引起双方更多的关注茶马互市,保护它,敬畏它,让它拥有超尘脱俗的仪态和举世无双的容颜,永不消失。
宗教信仰
汉末开始的少数民族大规模内迁,加速了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也促进了不同民族文化的冲突和磨合,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包容性和多样性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历史文化中农耕与游牧两种不同的经济基础的文化类型开始了由相互敌视转向相互依赖、相互融通的新局面。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当在西汉末年,《三国志·魏书》卷三十,裴松之注引《魏略》记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当时大月支佛教极其昌盛,伊存即大胝王派来的佛教国使。到了东汉,上层统治者越来越重视佛教,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明帝夜梦顶有金人,飞行殿庭。乃问群臣,太史傅毅附会为西方的“佛”,明帝便派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18人“使于天竺”,归国后择地建庙,即后世所谓白马寺,此后信奉者越来越多。
据史料记载:古代青藏高原古羌民族、中原汉族和北方阿尔泰语系诸民族在文化上的相互交流明显地表现在宗教信仰文化上的相互融合。从青藏高原南部的冈底斯山到高原北部的昆仑山地区,也是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文化与青藏高原古羌民族古代文化交流延伸的区域。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系统分布于东起大小兴安岭、西到青藏高原西北部的广大地区。这一文化的核心便是萨满教。萨满教应该说是一种世界性的宗教文化,曾为东北亚、北美、北欧等众多民族世代信仰、全民信奉。而中国地处萨满教分布的核心区,信奉萨满教的民族众多。历史上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肃慎、娄、女真、月氏、匈奴、鲜卑、柔然、高车、突厥及近代阿尔泰语系诸民族都信仰萨满教,而属于汉藏语系的夏族、周族、羌、狄、戎、吐谷浑、吐蕃、党项、西夏所信奉的宗教与萨满教信仰都有惊人的一致,至少受过萨满教的影响。
阿尔泰语系各民族萨满教中,沿袭“三界说”上界称巴尔兰由尔查,即天堂;中界称“额尔土土伊都”即地面;下界称“叶儿羌珠几牙几”即地狱。上界为诸神所居,中界为人类所居,下界为恶魔所占。宇宙树也是三界宇宙中的核心象征,宇宙树在世界中心,位于天之柱———宇宙山顶或地球脐上,上接天神,下达下界,沟通三界的联系道,宇宙树通过树、山、河流、彩虹、梯子等等表达。有时宇宙树与宇宙山是指同一体,即联接三界的天柱。萨满教认为该树的顶部为天堂,住着天帝和各种神灵,而树根为地狱,住着魔鬼。树枝上有许多鸟,这些鸟是等待转世的死者之灵魂,所以又称“生命树”“不死树”。因此,对神树的崇拜在各民族中普遍存在。
吐谷浑信奉萨满教,而世居青藏高原的羌族及后来吐蕃信奉苯教。按吐蕃原始的宗教为苯教,与萨满教大致相类。奉天神、魔鬼神等,迷信色彩极为浓厚。
从宗教层面看,不论哪个民族,既然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必然要遵守一定的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宗教信仰上更是如此。这两种宗教都有着古老而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但各自的教义、教规、仪轨都多不相同。但两种宗教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时代背景又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因此,当吐谷浑人把萨满教带到青藏高原时,两种宗教是一种共存相融的状态,这个过程至少延续了数百年,其结果是萨中有苯,苯中有萨,但又各自保持了独一性。把宗教作为一种文化来观察,则其影响是深远的。
东晋十六国以至南北朝是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时期,尤其是在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都大力提倡佛教。而长年的战乱,民不聊生,生命难全的境遇也使普通劳动者希望以求神拜佛解除痛苦。上层统治者的支持、提倡,下层群众的需要、向往,为佛教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丝路交通的畅达为佛法的传播创造了条件,由此汇成了佛教文化向东传播的第一个高潮。五凉割据时的河西地区,佛教尤其流行,《魏书·释老志》云:“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前凉时就曾请西域僧人支施仑、帛延等来凉州与本地沙门共译了《首楞经》《须赖》《金光首》《如幻三昧经》等4种经书。前秦的统治者苻坚笃信佛教,为此还曾发兵攻陷襄阳以迎请高僧道安去长安主持佛事,道安也就此逐渐成为北方佛教的领袖,影响很大。后秦主姚兴,因得一代译经大师鸠摩罗什而使译经,佛教事业都远远超越前代。
藏族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考古发现的材料表明:早在一万年前,藏族的先民先羌先后经历了旧石器时代、细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进入氏族与部落联盟时期。到吐蕃王朝建立之际,藏族已发展成为拥有近百万人口和高原广阔地域的强大民族。藏族先民在旧石器时代就生活在青藏高原。最初信仰崇拜自然的原始宗教,苯教将自然崇拜和人的崇拜结合在一起,提出了系统的宗教教义和仪规。
苯教中的宇宙三界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在古代藏族的宇宙观中,天界是多层的,认为整个世界一般是上有九层,下有九层,或者是上有九层和下有七层,有时也有十三层,这一点是典型的苯教观念。
吐蕃兴起时,苯教已融合了不少萨满教的东西,同样萨满教也融入了苯教和佛教甚至道教的东西。这种宗教上的融合必将影响到各信奉民族的心理状态、行为规范、价值取向、文化艺术直至民风民俗、乡规民约等。流传于今青海东部地区的“梆梆会”,其内容、仪规、法器多是萨满教的遗风,但是也融入了一些道教的东西;民俗中的叠松篷、跳冒火、煨桑、抢婚、小孩从“洗三”到起名等,都是萨满教的遗风或衍生。不朽的史诗《格萨尔》在较长的创作过程中,不少内容是有关北方萨满教的。有民间艺人们加以移植、嫁接和再创造,使其更加完整、鲜明和生动。如有关寄魂母题、化变母题等的应用,使格萨尔及其各路英雄,也包括霍尔王在内,都成为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性格鲜明、人神共一的史诗人物。使史诗具有了无限广度和深度,史诗的境界也显得无比深邃和壮阔。
鲜卑拓跋部进入中原后,寻古思照,大兴佛教,受此影响,吐谷浑在慕利延时引入了佛教。据史记载:梁武帝信佛,吐谷浑伏连筹苦心孤诣在益州特地建造了一座左手揣着金邓寺,右手托着峨眉山。雄伟高大的九层佛塔,有“南联驰脉嵩衡秀,北观天枢斗极辉”之说。吐谷浑上层开始转信佛教,广修佛寺,大彻大悟,迎引众多中原或西域的高僧传教弘法,从此,佛教在青藏高原生根开花,此举对后世影响甚大。《梁书·河南王传》说吐谷浑“国中有佛法”,犍陀罗僧人智藏、智贤等曾长时间在吐谷浑传法。刘宋元嘉二十三年左右(446年),吐谷浑王族改奉佛教,其属下地区的广大羌人都相继皈依了佛教。一度为吐谷浑占据的于阗,是当时佛教最为兴盛的地区,而吐谷浑广大的国土也成为佛教文化东传的必经之道。公元518年,有北魏僧人宋云一行奉命去西域求经,并宣扬国威。宋云一行达到了吐谷浑王城,对吐谷浑国作了最直观的观察和报道。因此,宋云等僧众,无论是出西域还是入王庭,都是一次文化交流之旅,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实现本土化过程做出了贡献。
藏传佛教最早进入青海,影响吐谷浑佛教信仰。而吐蕃攻取吐谷浑后,佛教已成为吐蕃的国教。据蒲文成先生的《青海佛教史》记载: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统一西藏高原,建立了著名的吐蕃王朝,先后从唐朝和尼泊尔两个渠道引进佛教,印度佛教开始在我国藏区传播。但在佛教传入吐蕃后的100年间,西藏尚无僧众组织,佛教还未形成体系,扎根于民间,传统的苯教仍占有相当地位,当时,不少贵族仍然信奉苯教,享有很大权势,苯教实际上控制许多政治活动,在婚姻、丧葬、治病、耕种、放牧等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作战、会盟等各项事务中,一般都由苯教参与解决,苯教所谓“神的意志”决定着一切。这一时期,佛教的传播主要是迎请佛像,修建佛堂、佛塔、引进佛教有关五戒十善方面的教义,推行十善法止恶行善,规定“不淫”“饮酒有度”“要具羞死”等,提倡“寂灭为乐”“因果报应”“求未世福”“报废禁欲”等,规范人们的道德观念。随着佛教的传入,有了初步的译经活动,请来印度、尼泊尔、迦湿弥逻和祖国内地的一些僧人,协调藏族学者,译出大小乘经典数十部和六字真言等陀罗尼。这一时期,佛教也同时传入青海藏区。据史记载早在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松赞干布主动与唐朝通好,始遣使入唐,太宗遣行人冯德遐前往抚慰吐蕃,松赞干布听说:“突厥及吐谷浑皆尚公主,乃遣使随德遐入朝,多金宝,奉表求婚”。“贞观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李道宗主婚、持节送公主于吐蕃”《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唐文成公主于公元641年从长安城启程,《王统世系明鉴》中说,唐王送给公主一尊卧式释迦佛像为嫁妆,命“建造车辆,把释迦牟尼像放在车上,由汉人大力士拉噶和鲁噶二人拉车。又送了大量珍宝、绫罗、衣饰及所需物品,并赐给了马、骡、骆驼等驮畜”。据青海玉树结古寺名僧桑杰嘉措所著《大日如来佛记摩崖释》,文成公主一行途径今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巴塘乡西北约4公里处的贝纳沟南端,休整1月,公主命随行比丘译师智敏负责,由工匠仁泽、杰桑、华旦等在当地丹玛岩崖上雕刻9尊佛像,中为大日如来,梵语谓“摩诃毗卢遮那”,藏语称“南巴囊则”,左右各侍立四尊菩萨,分上下两层,右上为普贤、金刚手、下为文殊,除盖障;左上为弥勒,虚空藏、下为地藏、观世音、共为八大近侍弟子像,十分壮观。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唐蕃再次联姻,金城公主入藏又经过玉树巴塘,见文成公主原刻佛像被风雨剥蚀,遂令随从于佛像上盖一殿堂。唐开元十八年(730年),派人摹刻佛像,重新修缮,寺内僧人修禅,称之为“参巴”。
青海地处青藏高原东隅边缘,是连接西藏、甘川藏区、新疆与祖国内地的重要纽带,历史上一直是内地通往西藏的主要通道和丝绸之路的南路干线。这里曾是唐蕃相争的主战场,吐谷浑国、唃厮啰政权等活跃一时的舞台。西藏萨迦班智达衮噶坚赞即在甘青藏蒙地区活动,使西藏纳入元朝版图,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突出贡献。元代,大元帝师八思巴往返于西藏,多取道青海,在这里广泛传播藏传佛教,并举荐青海籍僧人胆巴、桑哥等,任职元朝,官至帝师和丞相。明代,格鲁派以青海为基础,创立发展,并迅速传播到广大蒙古、土族地区。明末,漠西和硕特蒙古正是看到青海的重要战略位置,从新疆入据青海,支持格鲁派,平定川康,进而控制全藏。因此,历代中央王朝无不把经营青海作为安定边陲的施政方略。特别清代,针对藏、蒙古、土族人民普遍信仰藏传佛教的实际,采取“兴黄教,以安众蒙藏”的策略,封授藏传佛教上层人物,以控制西藏,安定蒙藏地区,从而维护大一统的王朝统治。原为吐谷浑的青海地区聚居地带,宝刹林立,高僧如云,与黄教六大寺院中的塔尔寺(应作塔儿寺,兹且从俗)、拉卜楞寺比肩媲美。如湟源的扎藏寺、从西藏迁来的东科寺、互助的佑宁寺(原称古隆寺,或尔古隆寺),大通的广惠寺(又称郭莽寺)以及甘州的马蹄寺,互助的却藏寺、白马寺;还有最早建立的乐都瞿昙寺,民和的灵藏寺;甘肃永靖的炳灵寺、白塔寺等遐迩闻名。从康熙年间起,设置驻京呼图克图,在京供职者12名,其中因青海格鲁派上层在“安抚蒙蕃”中的特殊地位,竟占到7位。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乾隆帝饮定驻京喇嘛班次是,章嘉为左翼头班,敏珠尔为右翼头班,均为青海大活佛。从文化传统来看,青海处在藏文化、汉文化的文化圈的交汇地带,二种文化虽相对独立,但总体上又互相吸收和渗透,互相影响和融合。特别是藏汉两种文化,因其主体在信仰上的许多共同点和一致性,这种文化上的联系和交流尤为突出,这一特点在青海东部地区各民族杂居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文化形态上呈现出多元性。这种宗教文化造就出无数高僧大德,不少人苦读经论,学有所成,任职京师;有的佛学造诣高深,选任格鲁派的最高僧职噶丹赤巴,成为达赖、班禅的经师;有的博通佛典群藉,著书立说,蜚声学林。许多人弘法讲经于祖国内地和广大蒙古地区,蒙译和满译藏文大藏经,乃至出访世界各国等,为弘扬藏传佛教文化,沟通民族文化和吐谷浑文化交流等,做出过卓越贡献。随着佛教文化的东传西行,大量的佛教艺术被带入青海河湟地区,佛教的建筑、绘画、雕塑艺术表现更为突出。如阚骃《十三州志》载:“西平亭北有土楼神祠”,清代杨应琚《西宁府新志》亦说:“佛教盛行鄯州,曾作结盟龛于土楼断岩之间,藻井绘画”,土楼神祠即今西宁北禅寺,为“湟中古寺第一”,寺内有“九窟十八洞”,洞内有壁画,其中部分即为北魏以前的佛教壁画,线条流畅,甚为精美,而在西宁市湟中县元山尔出土的胡僧骑马铁俑,胡僧深目、高鼻、大眼,身披袈裟、颈戴佛珠、两手合十,端坐马上,有深厚的曼陀罗风格,是魏晋以来众多高僧大德在河湟地区往来传法的生动写照。可以说,青海如同江河之源,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藏传佛教文化形成、发展、传播的过程中,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源头。
吐谷浑,在其原始信仰萨满教和道教合流的基础上,迎请梵音,改信佛教,中原的惠生、法显、慧叙、玄畅、慧叡、法勇、释慧览以及天竺(印度)的阇那崛多等数十位高僧大德都是经都兰前往目的地,早在文成公主之前就将佛教带入青藏高原,使吐谷浑由一个多民族共同体凝聚成为一个信仰共同体。(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