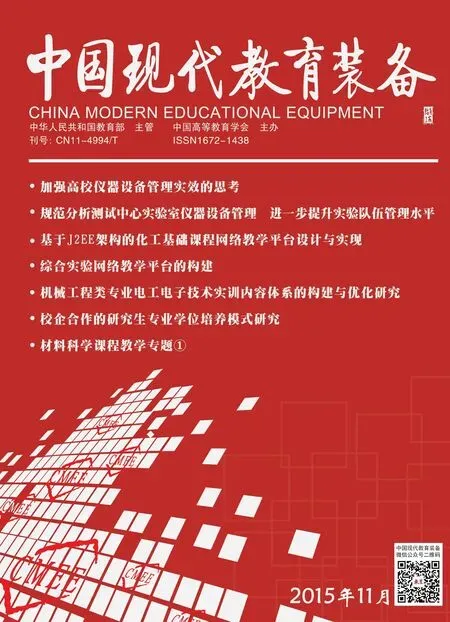将药用植物学教学塑成科学和文化之旅
任建武 胡 青 王 茜 高述民 李虹阳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100083
药用植物学(Pharmaceutical Botany)是以具有医疗保健作用的植物为对象[1],研究它们的形态、组织、生理功能、分类鉴定、资源开发以及合理利用的一门课程。其实质就是利用植物学、化学、药学的有关知识和方法来研究和应用药用植物,在知识的学习和应用方面具有一定综合性。
1 教学现状及存在问题
目前,教学中使用的教材《药用植物学》一般分为形态解剖和分类两大部分,就分类部分而言,内容编排多是依照门、纲、目、科、属、种分类群,其中被子植物门多依据克朗奎斯特(A. Cronquist)系统排列,涉及具体的药用植物种的介绍时,主要包括学名、形态、分布、药用部位、功效等。讲授过程中,若完全按照大纲体例进行讲解,难免枯燥乏味、落入俗套,这种灌输式教学使得学生们在有限的知识积累基础上难以全部消化吸收课堂讲授内容,最终迫使学生们只能选择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学习与实践效果很差。
2 关于改进课程“教”与“学”的探讨
基于药用植物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1],我们做出了探索和研究,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使其充满热情地积极参与思考与创新。
2.1 转变教师主导的“讲授型”教学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会准备大量集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的素材,并结合PPT、视频等多媒体形式进行讲授。这种教学模式其实质无非是教师绞尽脑汁向学生全方位灌输知识,学生的收获却远低于教师的预期。因此整个过程陷于教师费力却不见成效、学生半推半就勉强学习的尴尬境地。究其根源,在于“教”与“学”没有形成无缝对接,教师主动的“教”游离于学生被动的“学”。一般说来,改变这种局面的方法在于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体系。那么,如何实现呢?我们在生活实践中找到了答案。
俗话说,人食五谷杂粮,孰能无疾。在课堂上,可以针对学生日常出现的健康问题,结合药用植物的功效进行讲解。有的学生学习紧张导致失眠,便在讲解柏子仁、酸枣仁时结合对应;而个性急躁多有失眠者,讲到黄连、莲子心时提醒之;对于许多学生视力不佳,邀请这些学生预先搜集决明子、枸杞、菊花等药用植物资料,课堂上学生对症讲解,教师给予补充、纠正。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们注意到了决明子性属寒凉,使用时脾胃虚寒者要谨慎;而菊花分为黄菊、白菊、野菊,功效各有偏重等知识。有的学生甚至在课堂上问到其父母视力下降的治疗药物,则引发了对杞菊地黄丸所涉及药用植物的研究与讨论。学生主动认真地研读了关于枸杞、西洋参、黄精、黄芪养生茶的妙用,使药用植物学知识迅速得到延伸扩展。课堂上学生和教师一起现身说法,根据已有的医药知识尽力辨证药用植物功效,教室真正成为研读医药知识的大课堂。
2.2 梳理教学内容 分级凝练知识点
为了使药用植物学知识系统化,便于学生知识框架的构建,将每种药用植物按照形态、分布、生境、类别、部位(来源)、采收、性味、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道地沿革、禁忌词条对号入座。其中类别按照功效分为解表、清热、泻下、祛风湿、芳香化湿、利水渗湿、温里、理气、消食、驱虫、止血、活血祛瘀、安神、平肝熄风、开窍、补益、收涩、涌吐、止咳化痰平喘、外用药。
另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分类教学法,在有限的课时中,按中药的临床使用率分为一、二、三级药用植物,并重点介绍一级药用植物。
其中一级药用植物包括:人参、黄芪、党参、甘草、白芍、生地、丹参、茯苓、柴胡、黄连、麻黄、桂枝、紫苏、姜、丹皮、荆芥、防风、薄荷、菊花、柴胡、地黄、金银花、板蓝根、鱼腥草、穿心莲、大黄、芦荟、藿香、砂仁、茯苓、泽泻、薏苡、肉桂、橘皮、枳实、木香、山楂、麦芽、莱菔子、贯众、三七、艾、川芎、当归、鸡血藤、牛膝、续断、川贝母、半夏、桔梗、白果、马兜铃、何首乌、杜仲、天麻、山药、大枣、桑、枸杞等。
2.3 寓教于乐 传播文化
中药作为灿烂瑰丽的中华文化,本身带有浓郁的文化属性。植物药是中药的主体,西周至春秋期间的《诗经》和《尔雅》中,就分别记载了药用植物100余种。《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第一部药物专著,记载了252种药用植物,成书于汉代公元元年前后。[2]在中药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孕育了无数趣味史话、著名医案,不少植物药融于历代诗词歌赋之中,成为文化的鲜活载体。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意挖掘药用植物承载的文化内涵,从中提炼学生的兴趣点而加以利用。因此,药用植物学课程的学习,也是一次中华文化的洗礼。
2.3.1 中药史话激发兴趣
多数药用植物名字奇特,看上去很像是人名,其中往往隐藏着一段典故。如萝藦科植物徐长卿的命名源于唐代贞观年间一位民间医生。据说唐太宗李世民外出打猎,不慎被毒蛇咬伤,病情十分严重。御医们用了许多贵重药材,均不见效,只得张榜招贤。民间医生徐长卿看见榜文,便揭榜进宫以该草药医治好了皇帝的病。于是依照唐太宗口谕徐长卿作为药名流传至今。而蓼科药用植物何首乌名称出自唐代元和年间河南顺州乡间农夫姓名;车前草与汉代名将马武的军旅生涯有关;杜仲原来是洞庭湖边一个纤夫的名字。这些典故的穿插,增加了教学过程的趣味性,于无声处浸润了中国传统文化。
有的药用植物因跟历史名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被赋予特殊意义。如禾本科植物薏苡,作为一种中药,有其悠久的历史,早在《神农本草》中即有记载,其性味甘、淡、凉,入脾、肺、肾经。有健脾、补肺、清热、利湿等功效。东汉名将马援(伏波将军)领兵到南疆打仗,军中士卒病者甚多。当地民间有用薏苡治瘴的方法,用后果然疗效显著。马援平定南疆凯旋归来时,带回几车薏苡药种。谁知马援死后,朝中有人诬告他带回来的几车薏苡是搜刮来的大量明珠。遂有“薏苡明珠”的成语流传,这个成语是指无端受人诽谤而蒙冤的意思。
2.3.2 著名医案巩固知识
教学中所列的一级药用植物,屡见诸于传统名方中。课堂上通过具体医案,列举名方配伍,让学生在更深的层次中掌握药用植物知识。六味地黄丸是中医临床常用的一种中成药,三补三泻,配伍精到,始见于宋代《小儿药证直诀》[3],由儿科名医钱乙创制。公元1079年,钱乙应诏入汴京治好太子的病,进入太医行列。一日一位大夫持钱乙开的儿科药方上门质疑,依照张仲景《金匮要略》八味丸,应该有地黄、山药、山茱萸、茯苓、泽泻、丹皮、附子、肉桂,认为不应该遗漏两味药。[4]钱乙解释道,张仲景的方子是给成年人用的,而孩子阳气足,可以减去肉桂、附子这两味益火药,以免过于暴热而流鼻血。这个医案可以一下子阐明八种药用植物的药用部位和功效。如此,课堂上学生学到的知识经过反复思辨,强化与巩固,从而学以致用。
2.3.3 才艺展示中鱼与熊掌兼得
在课堂教学中,抓住年轻学生争强好胜、富于表现欲的心理,在学习重点药用植物时,专门辟出才艺展示专栏,以古体诗词挑战对答。如在学习黄芪时,学生吟出“白发欹簪羞彩胜,黄耆煮粥荐春盘”。则黄芪的补气作用立刻得到领悟。“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梅的形态跃然纸上。而“性温生处喜偏寒,一穗垂如天竺丹”道出了人参的植株形态和生境。
另外通过吟诵诗词,对一些容易混淆的植物做出了很好的辨析,讲到桃金娘科丁香(Eugenia caryophyllata Thunb)时,有人吟出戴望舒的《雨巷》,有学生立刻做出反应,“此丁香非彼丁香,可不是雨巷里结着愁怨的姑娘”。类似于以“遍插茱萸少一人”区分山茱萸和吴茱萸等小插曲,恰当地使用授课技巧,在讲解基本知识的同时,讲活讲妙,内容生动精彩、趣味横生,使课堂气氛活跃,很多知识点同学们都过耳难忘。
2.3.4 巧妙运用药话和谚语
中药的发现和应用以及中药学的产生、发展,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实践过程。随着历史的传递、社会和文化的演进、生产力的发展、医学的进步,人们的用药知识和经验愈见丰富,记录和传播中药知识的方式由最初的“识识相因”“师学相承”“口耳相传”发展到文字记载。这其中,流传了许多名医用药佳话,老药妙用新话,文人吟咏诗话,中药变迁史话,古今轶事趣话,民间传说神话等。这些都称作药话,或者称作药文化,其以诗文传记、典故异闻等多种形式的文字记载,传播药物效用、经验教训;将药学、史学、文学、医学熔于一炉,学术性、艺术性、知识性、实用性、趣味性集于一体。经过教师的精心设计,将此内容合理应用于教学中,使得学生们在体味中国传统文化无穷魅力的同时,学习药用植物知识。
教师在教学中恰当引用有关中药功效和中药采收的谚语,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如“穿山甲、王不留,妇人服了乳长流”“七叶一枝花,深山是我家,痈疽如遇者,一似手拈拿”。《阳春采药歌》有“正月茵陈二月蒿,三月四月当柴烧;茵陈采收宜细嫩,摘起幼苗梗去掉……桑树根皮早春挖,趁鲜洗净泥和沙;纵向皮部刀剖口,除去外皮扎成把……白头翁根宜春采,挖起根茎及时晒;保留头部白茸毛,除去泥土须要卖。”此外,浩如烟海的诗词歌赋也向我们传递了大量的中药文化的信息,如宋代苏轼的《槟榔》诗:“此客初未谙,劝食俗难阻。中虚畏泄气,始嚼忽半吐。吸精得微甘,着齿随亦苦。面目太严冷,滋味绝妩媚。”
中药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一些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特定的栽培工艺,形成了闻名遐迩的优质道地药材,“关药”人参;“川药”川贝母、川芎、黄连;“云药”三七;“四大怀药”(地黄、菊花、山药、牛膝);浙八味[5]等。在学习时,应该将地域文化融入其中,让同学们感受到祖国的地大物博,使其爱国情怀从朴素的认知到发自内心深处的认同。
经过对中药文化宝库中的素材合理吸收与加工,将中药文化引入课堂教学之中,引导学生徜徉在中药文化里学习药用植物,真正做到知识积累和文化洗礼并重。
3 结束语
通过创新施教方法,梳理知识内容,引入中药文化亮点,不但可以活跃课堂气氛,提高教师的亲和力,增强同学们的学习兴趣,还能在传承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在开拓学生视野的同时,体味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药用植物学教学实践说明,若仅仅立足于药用植物的分类和辨识,是枯燥无味的;如果着眼于培养有文化品味的高素质创新人才,药用植物学课堂则可以打造成趣味无穷的缤纷舞台,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教师应该有广博知识储备和阅历积淀,才可以使得药用植物学课程学习沐浴在中华文化的长河里,开启科学之旅、文化之旅。
[1]裴瑾,万德光,马云桐,刘薇.关于优化药用植物学课程知识体系的思考[J].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13(3):23-24.
[2]张登本,孙理军,汪丹.《神农本草经》的成书与沿革[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0,28(5):924-927.
[3]周京燕,韩立新.六味地黄丸的现代研究与进展[J].中国药师,2008,11(6):710-711.
[4]姚佳音.《东医宝鉴》引证《金匮要略》内容考[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25(2):23-24.
[5]王明军.中药浙八味科学性品质文化背景探究[J].时珍国医国药,2007,18(8):1879-18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