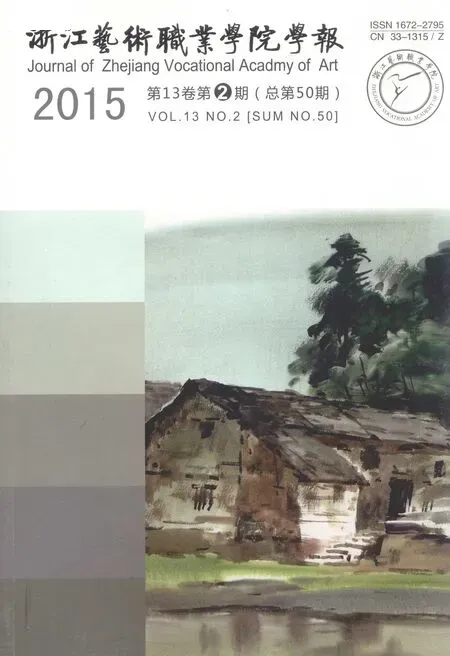“清和”审美范畴辨析
滕春红
毫无疑问, “和”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也是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的审美原则与审美理想。所以,古人以“和”为中心构建了“中和”、“淡和”、“清和”等等审美范畴,用以表达音乐的审美理想。显然,目前学术界对于这些范畴的研究中,前两者属于研究的重点,而“清和”却一直关注者寥寥。事实上,无论是“清”或“清和”都很早就被用来形容音乐,是传统音乐美学中的固有观念。纵观“清”在音乐艺术中的审美化过程以及“清和”审美范畴的成熟,我们可以发现,“清和”范畴在古代音乐美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甚至比“中和”或“淡和”等范畴更适合用来表达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的最高理想。
一、“清和”审美范畴的形成与发展
“清”是中国古代一个非常重要的审美范畴,它的审美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清”在传统哲学美学中的本体化地位使其具有生成性内涵,构词性极强;“清”在传统伦理上代表的纯洁雅正的肯定性价值倾向使它有着极富理想化的含意;同时,“清”在古代音乐美学获得大量艺术实践。[1]这些都使得“清”这个范畴在中国古典美学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在古代音乐美学的实践中,从音乐的基本元素到音乐的创作、欣赏,从声音的基本物理属性“清浊”一直到最高审美境界的“清和”等等环节,它几乎贯穿了古代音乐审美的全过程。①关于“清”的审美范畴在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中的发展演变,笔者已另有专文表述,请参见拙文《从“清浊”到“清和”——试析古代音乐美学中的“清”》,《黄钟》2011年第1 期。
而作为古代音乐美学中的特有范畴之“清和”的形成和发展,也有着一个漫长的过程。
首先,作为声音基本的物理属性的“清浊”之清,是构成音乐之“和”的基本元素。毋庸置疑,“和”已被普遍认为是“古乐审美文化意识中为人追求崇尚的理想境界,或者说是最理想化的审美范畴”,可以被看作是“音乐艺术审美活动的最高境界”,[2]“清和”作为一个独立的词汇虽然至西汉时期才出现,但是,“清”却一直在“和”的审美理想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作为声音的物理属性,“清浊”对举被当作音乐本质之“和”的基础。《国语·周语下》中所记载的周景王与单穆公、伶州鸠等人关于铸钟一事的对话常常被引述。单穆公所云“耳之察和也,在清浊之间”,是在说明人的耳朵能够分辨的音域,只在“清”音与“浊”音之间,如果超过这个范围,声音太高或太低,都不会达到和谐自然的审美效果。《吕氏春秋·适音》中也曾说: “故太巨、太小、太清、太浊,皆非适也。何谓适?衷,音之适也。何谓衷?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小大轻重之衷也;黄钟之宫,音之本也,清浊之衷也”。这里不仅将声音大小轻重的适中作为“和”的标志,而且,它给出了一个更具体的“和”乐的范本—— “黄钟之宫”,宫音之所以能被当作音乐之本,就是因为它的声响符合“清浊之衷”的标准。因此,汉代音乐家在分析声、音区别的时候,也把“清浊相和”当作音乐生成的基础:“声、音者何谓也?声者鸣也。闻其声即知其所生。音者,饮也,言其刚柔清浊,和而相饮也” (《白虎通·礼乐》)即是说,“声”只是各种单独的,不成串的发声,而音则是声音的整体,是有一定的节奏和韵律的整体,是各种声音元素的适度组织。一旦构成了音乐,则必定包含着“清浊”之和。因此,清代的琴家陈幼蒸在论述了清浊二声是自然界中的常见现象以后,又提出“总之则清浊二音,互相配合,使之宣导湮郁而已。是以伏羲制琴,以禁邪心,使归于正”(《琴论·音韵清浊》)。简单说来,清浊是作为声音的物质基础出现在音乐领域的,但是在上升到音乐的阶段以后,“清浊之衷”就成为音乐“和”的基础之一了。
其次,“清和”最早出现于西汉贾谊的《新书·数宁》: “大数既得,则天下顺治;海内之气清和咸理,则万生遂茂”,这里的“清和”即清静平和,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它有时也指人清静平和的心理状态或性格特征,如蔡邕《文范先生陈仲弓铭》云: “君膺皇灵之清和,受明哲之上姿。”“清和”有时也被用于指天气情况的舒适,如曹丕《槐赋》曾云: “天清和而湿润,气恬淡以安治。”等等。可见,无论它被用在哪个方面,它都是一个充满褒义,代表着理想与美好的词汇。
而作为一个音乐审美范畴的“清和”,出现于西汉时期扬雄的《剧秦美新》: “镜纯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声”,指的是听音乐时,要聆听那些清亮雅正之音,可见这里的“清和”,已不再只是声音的物理属性,而是上升到了音乐的审美风格上。东汉时期的王逸在《九思·伤时》中也以“清和”形容美妙的歌声: “声噭誂兮清和,音晏衍兮要淫。”注云,“噭誂,清畅貌”,即是指的歌声清越激扬,响亮和谐。到了魏晋时期,嵇康就已把“清和”当作音乐至高无上的审美理想了,他提出:“琴瑟之体,间辽而音埤,变希而声清,以埤音御希变,不虚心静听,则不尽清和之极”(《声无哀乐论》),他是说,像琴瑟等乐器弹奏出来的音乐,节奏的间隔比较长而且声音轻柔,变化缓慢而声音纯正,用低声轻柔之音去表现缓慢的变化,如果不用心静听,就一定不能体味到纯正和谐的至高境界。显然,在嵇康这里,“清和”已成为琴瑟等音乐的至极境界。
这种清静、淡定、平和的音乐境界在宋代变得尤为重要,北宋琴家崔遵度曾提出琴声“清厉而静,和润而远”的审美理想,如果琴的声音能够响亮高亢而又使人很安静,和谐圆润而又能传播得很远,那么这就是琴的最佳状态。成玉礀也云:“慢商调十数调亦皆清和,不蹈袭群曲,一声声如琼琳瑶树,无一枝杂”(《琴论》),将“清和”当作重要的音乐审美标准。朱长文所论之“尽其和以至其变,激之而愈清,味之而无厌,非天下之敏手,孰能尽雅琴之所蕴乎”(《琴史·尽美》),又将音之“清”当作“和”的一个重要特征。元代的陈敏子则将“清和”与“雅淡”、“峭急”等并列,作为音乐风格的一种:“听雅淡之音者,意多深远;听清和之音者,意多快乐;听峭急之音者,意多悲感”(《琴律发微·制曲凡例》)。这些都说明音乐美学家们越来越重视将“清和”范畴应用于音乐审美的各个方面。
明清时期,“清和”开始成为颇为盛行的音乐观念。“清”、“和”两个概念分别被当时琴家赋予了几乎是同等重要的地位,徐上瀛认为先人制琴,“其所首重者,和也”,在论“清”况时又说: “故清者,大雅之原本,而为声音之主宰” (《溪山琴况》)。冷谦也云:“清者,音之主宰”,“和为五音之本,无过不及之谓也”(《琴声十六法》)。这是一种崭新的提法。前代虽有“清和”之论,但毕竟总是点滴散论。“和”作为音乐之美的核心概念历来有之,而“清”在此时也被提升到了与“和”一样之地位,显然增强了“和”的审美特征,所以,清代的苏王景才会提出,“取音之法,青山言之最精,要之二十四况不外‘清和’二字,古、清、淡、远皆从此出。但句调不明则不清,气脉不接则不和”(《春草堂琴谱·鼓琴八则》),他认为“清和”是徐上瀛《溪山琴况》中的二十四况之核心, “清”主要从音调上着眼,“和”侧重于音乐的整体效果,同时,他还论述弹琴时的要领是: “弹时务令点点清楚,而又一气相生;段段融合,而又泾渭自别。则清而不枯,和而有节,众妙皆归矣”(《春草堂琴谱·鼓琴八则》),就是说如果弹琴时做到了每一个音都纯正,而且全曲又能一气呵成,那么这样的音乐则会美妙无比了。“清和”之音,显然已经渗透进了音乐创作与表演的每一个环节。
二、“清和”范畴的审美属性
显然,“清”与“和”的结合更放大了二者的审美意义。从审美属性上来说,“清”的外延与内涵均比“中”与“淡”要更为广泛和深入。从表现古代音乐的审美境界上来说,“清”更从音乐的审美属性上着眼,而“和”则更倾向于音乐的审美效果。
就“清”与“淡”的比较来说,虽然二者在汉语中是同义词,但是它们在美学内涵上的所指却有很大差异, “清”显然要比“淡”更广泛更深入。“清”不仅在诗歌美学上被研究者称为“诗美的核心概念”[3],也在古代哲学上据有重要地位。在道家哲学体系中,“清”几乎是与“道”、“天”、“气”等本体性概念一致的词汇,老子曾说“清静为天下正”(《老子·第45 章》),“天得一以清”(《老子·第39 章》),庄子不仅视清、道类似:“夫道,渊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 (《庄子·天地》),而且将“太清”与“无穷”、“无极”等视为等同的概念(《庄子·知北游》),《淮南子》中更是将“太清”视为万物存在的终极状态:“太清之始也,和顺以寂漠,质真而素朴,闲静而不躁,……”(《淮南子·本经训》)。正是哲学本体地位的确立,才使得“清”在中国古代范畴体系中成为一个生成性极强的概念,不仅可以应用于中国美学的审美发生领域,也可以应用于审美鉴赏领域,同时又可以成为中国美学的审美理想之一。
蒋寅教授曾经如此描述过诗学史上的“清”的生成性:“它的基本含义就像色彩中的原色,向不同方向发展即得到新的色彩。比如脱俗的倾向会发展为奇峭,……清又可以向不同风格类型延伸,与别的诗美概念相融合,形成新的复合概念,就像原色与其他色彩融合开成间色一样。比如向雕琢方向发展,就形成南宋‘永嘉四灵’辈的‘清苦之风’(《沧浪诗话·诗辨》);而向刚健延伸就产生清刚、清壮,向空灵延伸就产生清虚、清空,向圆熟延伸就产生清厚、清老,向典雅延伸就产生清典、清雅,……”[3]古代历来“诗” “歌”一体,诗学史上的“清”有着如此的包容性与开放性,而音乐史上的“清”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为音乐的基础理论,“清浊”对举构成声音的基本要素,也是和声形成的根本,所以《白虎通·礼乐》云“音者,饮也,言其刚柔清浊,和而相饮也。”从“清”的情感基调上来说,以悲为美的“清音”,使得从《清商》到《清徵》到《清角》的递进中,音越高调越悲, 《清角》得以与《白雪》并列,因此陆机曾说: “悲歌吐清音,雅韵播《幽兰》”(《日出东南隅行》),白居易亦有诗云:“掩抑复凄清,非琴不是筝”(《和令狐仆射小饮听阮咸》)。
从音乐创作的角度看,“清风明月”成为高雅琴音产生所必须的自然条件,杨表正说,“妙不遇知音,宁对清风明月、苍松怪石、巅猿老鹤而鼓耳,是为自得其乐也”(《重修真传琴谱·弹琴杂说》);音乐创作主体是否有“清”之心性,成为作品产生的主体条件,范仲淹记述崔遵度时说其“清净平和,性与琴会”(《与唐处士书》),徐上瀛认为达“雅”况者,必得“修其清静贞正,而藉琴以明心见性”(《溪山琴况》);音乐器材上的材质之“清”、弹琴之手指是否“清”,却又成为作品产生的客体条件,因此朱长文论制琴之取材,必取于“高山峻谷、回溪绝涧、盘纡隐深、巉岩岖险之地”,因为这些地方“其气之钟者,至高至清矣”(《琴史·尽美》),杨表正则说弹琴时指甲要“甲肉要相半,其声不枯,清润得宜”(《重修真传琴谱·弹琴杂说》),徐上瀛也说琴声欲“坚”则必须“然左指用坚,右指亦必欲清劲,乃能得金石之声”(《溪山琴况》)。
从审美风格上来说,“清”与自然恬淡的审美趣味相结合,就形成了“清静”、“清淡”等,所以宋代的崔遵度曾将“清厉而静,和润而远”(范仲淹《与唐处士书》)作为琴音之至。向刚健、阳刚的方向延伸,就产生了清扬、清越、清亮等清脆响亮的审美范畴,因此元代的陈敏子将“清越”之音列为十五理想音乐风格的一种,徐上瀛说“指求其劲,按求其实,则清音始出。手不下徽,弹不柔懦,则清音并发”(《溪山琴况》)。向空灵升华,就产生清远、清虚等玄淡虚远、余音绕梁的审美风格,因此“清远可爱”被当作琴之“润”德(《太古遗音·琴有九德》),徐上瀛又曾释“润”云:“盖润者,纯也,泽也,所以发纯粹光泽之气也”(《溪山琴况》)。向中正平和,温柔敦厚的方向延伸,就形成了“清圆”、“清雅”的趣味,所以南宋吴自牧曾这样形容几种小乐器结合而成的审美效果“其声音亦清细轻雅,殊可人听” (《梦梁录》卷20), “七弦俱清圆”又被当作琴之“匀”德(《太古遗音·琴有九德》)。因此,郭平先生近年提出“琴的最高境界是‘清’”[4]这个论点,是不无道理的。
同样具有哲学本体地位的“和”范畴,也具有极强的生成性。①关于“和”在中国古代哲学美学中的本体地位,学界关注较多,论述已十分充分,此处就不再展开。这种生成性不仅体现于音声相“和”的乐音基础,也体现在乐与人“和”的主客交融,更体现于天与人“和”的至乐境界中。[2]因此,与“清”不同的是,“和”在音乐中的本体地位更多带有终极性的意义。除了“中和”、“淡和”、“平和”、“清和”等观念以外,古代音乐论述中又有“太和”、“至和”等代表音乐终极境界的范畴,所以嵇康曾说“克谐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声,得于管弦也” (《声无哀乐论》),又说“焉得染太和于欢戚,缀虚名于哀乐哉” (《琴赋》),即是将“太和”置于音乐之终极理想的境界,至于明代的黄佐在《乐典》中也说:“乐自天作,乐由阳来,至和之发也。其治心也,德盛而后知乐,其治人也,功成而后作乐,至和之极也,”将音乐的治心、治人而治世的功能看作音乐之根本。因此,沿着“乐和- 心和- 人和- 政和”的由声音而个人而社会的路线,“和”渐渐放大其审美意义,代表了音乐审美的最终指向。
由此看来,“清”、“和”结合而为“清合”是对音乐审美意义的放大,而“清”字更侧重于音乐的审美属性,“和”则更侧重于“乐和-心和-人和-政和”的审美效果。因此,清代苏王景认为《溪山琴况》 “不外‘清和’二字,古、清、淡、远皆从此出”(《春草堂琴谱·鼓琴八则》)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因为围绕着“清和”,可以构筑古代音乐美学的独特体系。
三、“清和”范畴的伦理属性
比起“中和”、“淡和”来,发端于汉代,提出于魏晋,成熟于明清时期的“清和”,显然更有着集古代音乐的伦理、政治、审美于一身的功能。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之所以强调“和”的理想,就是因为它更强调音乐对个人修养与社会治理的积极作用。
对于个人来说,它是道德修养过程中的一个必要阶段,即孔子所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之谓也。所以荀子既说音乐的作用就是“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荀子·乐论》),强调音乐对个人心性的重要意义:“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荀子·乐论》)。
而对于社会伦理来讲,音乐之和显然能达到一般手段达不到的社会效果:“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 (《荀子·乐论》)。虽然“中和”与“淡和”都强调了音乐的这种功能,但是显然“中”更强调社会伦理,故荀子又说“故乐者,出所以征诛也,入所以揖让也。……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荀子·乐论》),意即音乐是达到天下一统、社会平和的理想途径,它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种音乐理论过于依赖伦理而缺乏自足性。所以但凡倡导“中和”之论者,一般都是站在音乐的社会功能上立论,它的性质更像是做人之道与治世方法,而非音乐专属之境界,后世欧阳修、司马光等人之所以倡导“中和”,无不以此意为主。因此,有人说,“中和追求存在的唯一性,而排斥其它的存在方式,是一个具有明确目标的封闭系统,在本质上趋向一统、同一,表现出政教功用的单一化、伦理道德的一元化倾向,两千年来政治大一统、经济重农、文化专制、精神控制就是中和观的最好注脚。”[5]
“淡和”之“淡”的侧重点则在于个人的心性修养,即通过个人的血气平和、恬淡无为而使社会达到平和恬淡的状态。老子所论之“淡”,即着眼于个体感觉,“道之出言,淡兮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所以庄子曾说至乐“无情”,因为人“无情”才离大道之真最近,乐“无情”才更接近于“至乐”,这看上去是对个人情感欲望的否定,实际上却是在论述“乐”的终极关怀。嵇康强调乐“以平和为体”,所以认为琴“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琴赋·序》),也是从个体心性修养的角度立论。周敦颐认为“故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 (《通书·乐上》),首先强调的也是琴对个体平欲心、释躁心的意义。徐上瀛论“淡”况时也说:“使听之者,游思缥缈,娱乐之心,不知何去,斯之谓淡”(《溪山琴况》),等等,无不将目光集中在个体心性之上。虽然他们的论述也有着向社会功能延伸的倾向,但是总有些力不从心。所以明代李贽干脆提出“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焚书·琴赋》)的说法,对“淡和”的这种貌似自然恬淡而其实质是规范压制情感的音乐理论进行了抨击。
因此,无论是“中”还是“淡”,二者的范围与“和”在哲学、伦理、政治、审美中广泛使用的强大功能比较起来显得较为单一,所以有学者在梳理了由“尚和”发展到“中和”的变化后曾指出,“由于中和范畴主要是从政治伦理、情感规范角度发挥‘尚和’理念,因而大大地缩小了‘和’原初意义的范围。从本质上看,作为一种共生状态,‘和’兼容多种可能性;作为一种交互关系,‘和’是一种差别性的存在,多元融合而生新质。”[5]
“清”则不然。“清”的复义与多指向性使得它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使用十分特殊,它在诗歌美学领域近年来已被有关学者称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概念,[6]或者是诗美的核心概念,[3]地位之重要,已渐渐超越了其它范畴。除了在哲学本体性上被赋予崇高的地位以外,“清”在古代政治伦理领域也一直带有强烈的肯定性价值倾向,代表着理想与美好、正直纯粹与高洁雅正。作为“清世”与“清平”之世,它成为美好社会的象征,所以孟子论伯夷时说“伯夷,……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孟子·万章下》),《吕氏春秋·季冬纪》中也说: “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白居易也曾有诗云: “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赠梦得》)。作为“清廉”、“清白”之人格特征,它指公正清廉的为政之道、正直的处世态度与高洁独立的人格,如“故布衣、人臣之行,洁白清廉中绳,愈穷愈荣”(《吕氏春秋·离俗览》)。作为“清静”、“清明”,它一直被用作人格培育与心性修养的最佳状态: “是故达于道者,反于清静;究于物者,终于无为”(《淮南子·原道训》),荀子则将“清明”当作心性修养之根本, “知道察,知道行,体道者也。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荀子·解蔽》)。它同时也被当作人物评价的主要准则,所以孟子论伯夷“圣之清者也”(《孟子·万章下》),魏晋时期更是人物品藻的主要标准之一,如有人品嵇康云: “萧萧肃肃,爽朗清举”(《世说新语·容止》),评嵇绍“清远雅正”(《世说新语·赞誉》),等等。正是因为肯定性价值倾向的使用,使得“清”与“正”、“雅”这一类伦理观念极强的概念地位同一,以至于《清庙》成为宗庙祭祀专属之音乐,“清歌”、“清音”等一直被用来形容音乐之纯洁与正统, “清和”的第一次出现就被扬雄用来形容雅正之声。所以徐上瀛在分析“清”况的时候才会说: “故清者,大雅之原本” (《溪山琴况》)。杨抡在《听琴赋》中也云: “琴声清,琴声清,雨余风送晓烟轻,朱户檐前调乳燕,绿杨阴里啭雏莺。……琴声琴声清耳目,治世正音天下曲……”(《太古遗音》)显然,“清和”不仅吸收了音乐为天下之正的观念,也在审美属性上将音乐推至极致。从这个角度看来,“清和”范畴高度体现了古代音乐美学中的美善合一。
因此,从哲学深度上来说,“清”因为它的哲学本体化的地位而具有了与“和”并列的可能;从音乐形成的基础来说,“清”又因为“清浊”之对举成为音声之“和”的基础;从音乐的审美效果上来说,“清音”又成为美妙音乐的代名词;从音乐的社会功能上来看,“清”又因为自身包含的强大伦理功能而使其比“中”、和“淡”等范畴更适宜于表现雅正的音乐观念以及“和”的社会理想。比起“中和”来说,“清和”更加突出了音乐的审美特性;比起“淡和”来说,“清和”则更加突出了音乐的伦理功能,所以,以“清和”为古代音乐美学的核心范畴,会更清楚地反映出古代音乐美学的全貌。
[1]滕春红. 先秦时期的“清”论及其审美意蕴[J]. 中国文学研究,2012 (4):86-89.
[2]修海林. 和——古代音乐审美的理想境界[J]. 文艺研究,1988 (4):114-121.
[3]蒋寅. 古典诗学中“清”的概念[J]. 中国社会科学,2000 (1):146-157.
[4]郭 平. 古 琴 丛 谈[M]. 济 南:山 东 画 报 出 版 社,2006:77.
[5]夏静. 中和思想流变及其文论意蕴[J]. 文学评论,2007(3):163-168.
[6]韩经太. 清美文化原论[J]. 中国社会科学,2003 (2):162 -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