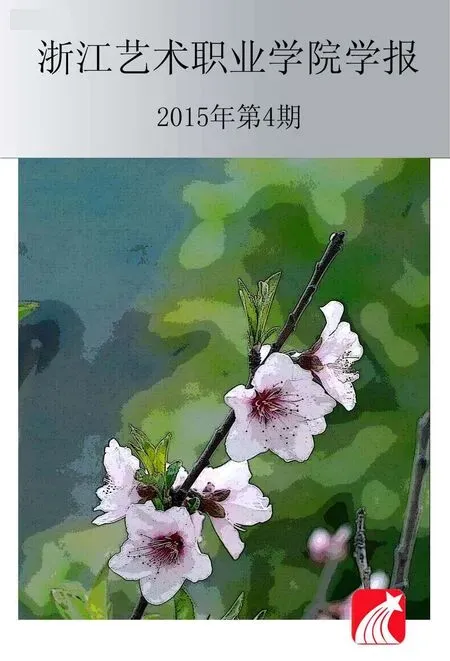南戏舞台艺术在当代的再现与改编
——以“温州南戏新编系列工程”为例
浦 晗
南戏舞台艺术在当代的再现与改编
——以“温州南戏新编系列工程”为例
浦 晗
南戏的产生标志着古典戏曲艺术真正的成熟,南戏在其成型初期便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舞台艺术模式,并影响了后世戏曲舞台艺术的演进,在一定程度上,南戏之后的戏曲形式大多吸收南戏的艺术特征,其自身的舞台艺术也在对南戏舞台艺术的吸收与改编中渐渐自我完善。在当代,南戏故里温州的戏曲从业者与学者也学习了古典戏曲的经验,新旧世纪之交推出的“南戏新编系列工程”就在舞台艺术方面再一次吸收了南戏的舞台与表演模式,同时融合了当代舞台理念与舞台科技对其进行加工,在舞台构造、演出程式、舞台节奏等多个方面再现了南戏的演出场景,并呈现出了新的面貌,最终使演出获得了成功。“新编系列工程”对南戏舞台艺术的成功改编是对南戏艺术的又一次重新认知,对于当前戏曲舞台艺术的实践与研究也具有借鉴意义。
舞台艺术;南戏;发展;再现与改编
“改编”,在现今的戏曲学界早已不是新颖的词汇,各个剧种和剧团对于传统剧目的整理与改编在半个世纪前就已启动,新编的剧本如雨后春笋,蔚然大观。相较于剧本文学的“改编”,戏曲舞台艺术的“改编”则就单薄了许多,古典戏曲舞台艺术的继承与创新问题让很多从业人员感到困惑,其实若考察某种戏曲艺术形式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戏曲艺术进入成熟期之后的,其曲舞台艺术的发展史与对其舞台艺术的改编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步行进的,各时期盛行的戏曲形式都是在对前有舞台艺术的接受与改编中而达到了艺术体系的完善,最早成熟的戏曲艺术形式——南戏就是其中的典型。
一、古代南戏的舞台艺术模式及其发展
南戏的产生是中国戏曲形式发展至成熟的重要标志,其所取得的舞台艺术也成为了深刻的文化基因,一直或明或暗地蛰伏于中国戏曲的根部。南戏演变隆衰的过程也与整个古典戏曲的发展交错在一起,明中期产生的昆曲,清中期兴起的折子戏以及后来百花齐放的地方剧种,在艺术本质与意识形态上刨根溯源,都可以称之为南戏的“后裔”,南戏舞台模式发展和演变过程的也是古典戏曲发展与转型的历史。
宋元时期,南戏在农村与市井的勾栏瓦舍之中渐渐成熟,勾栏瓦舍就是南戏的“戏场”,对于瓦舍,《梦梁录》卷十九条“瓦舍”条云:“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意,易聚易散也。”[1]《东京梦华录》卷二“东角楼街巷”条云:
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2]
从这些描述中,可以大致看出勾栏瓦舍的形制:搭建便利、分布市井各处,多置于露天空地,装饰简单,瓦舍内的艺人流动性较强,具有临时性特点等等,早期南戏在这种形制简陋的“戏场”中进行演出的,而这也是中国戏曲在形成初期的主要“戏场”形态。
除了舞台与表演场所的市井性特征,南戏的艺术本质更是充满了平民化与娱乐化的色彩,如徐渭在《南词叙录》中所云:“其曲,则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南戏虽作者猥兴,语多鄙下,不若北之有名人题咏也”[3],极度市民化是宋元南戏最突出的艺术特征,其舞台表演艺术亦是如此。《张协状元》是现存唯一完整的宋代南戏剧本,为书会才人所编,书会才人多为下层文人,创作基本供戏班演出是其谋生手段,《张协状元》是其创作的舞台演出本,从《张协状元》的剧本中也能窥探出一些典型的宋元南戏舞台表演艺术特征。
首先是虚拟化的舞台时空,第二出外扮演协公出场接唱便可以把舞台场景从大路拉回张协家中;第二十四出丑角一句“这里便是行管”就可将时空场景直接转换;第四十出在众人“不觉过一里又一里”的独唱与合唱中,环境就转到了“长亭共短亭”的路上了,王骥德《曲律·杂论》有云:“戏剧之道,出之贵实,而用之贵虚”[4],虚拟性与写意性一直是古典戏曲的主要特征,而《张协状元》则表明了中国戏曲在其形成之初就已经开始用虚拟手法突被舞台的时空限制了。
其次是简陋与虚化的布景与道具设置模式。《张协状元》整部戏几乎没有用到或提到具体的舞台背景与道具,部分舞台道具被有意地虚化,如王德用所骑之马,贫女所住的庙中之门,在舞台中其实并不存在,皆为虚拟化的表示,此外戏中许多所必用之道具,如门、桌、凳等,甚至直接由演员用身体行为扮演,早期演员地位低下,生活困苦,民间戏班的经费与规模十分有限,早期的古典戏曲便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处理着剧场与生活这一微妙的关系,而演员与舞台布景与道具融合为一,也配合和烘托着场上虚拟化的舞台时空。
再次是“一人分饰多角”的扮演方式。戏班简陋的编制不仅无法在场上完全展现生活真实的图景,甚至在人物的展示上也捉襟见肘,《张协状元》中出场的人物以数十计,但舞台上却仅有七个脚色,即生、旦、外、贴、丑、净、末,已处于配脚地位的净丑来说,其中净须办张协之母、张协之友、山神、李大婆、脚夫、谭节使等;丑须扮张协之妹、强人、小鬼、小二、王德用、考生等等,最多的一人要饰演近十位剧中人物。
最后是滑稽与喧闹的舞台气氛。宋代随着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扩大,市民文化也随之而兴起。勺栏瓦舍、茶坊酒肆是市民文化的摇篮,产生于这个摇篮的市民文化往往带有鲜明的娱乐性的特点,产生于勾栏瓦舍并植根于民间的宋元南戏也被这种特点所浸染,加之其剧本作者多是下层的文人和书会才人,其观众也多为市井乡民,从作者到观众都不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张协状元》中有一半以上的内容是于主要情节无关的“插科打诨”,净、丑、末三个脚色的戏份占据了剧本的主体地位,有时甚至生、旦也加入进来,与净、丑一起戏谑调笑,语言俚俗滑稽,方言众多。此外,剧中角色十分重视各种动作的运用,配角常扮演各种道具,做出各种幽默的形体动作,舞台氛围热闹非常,正如剧本开场“诸宫调”所说:“似凭唱说诸宫调,如何把此话文敷衍,后行脚色,力齐鼓儿,饶个撺掇,末泥色饶个踏场。”语言再好不如举手投足间,说唱不如敷衍。
南戏在明代初年继续呈现出向上的势头,并带来了明初戏文的繁盛,出现了《琵琶记》这样可称为典范的作品,在南戏传播与被接受的过程中,特别是其发展至嘉靖年间,南戏的艺术形态本质也在悄悄地发生改变,同时带动了整个戏曲史质的更迭,其一是南戏声腔流传到各地后与当地的语音方言体系结合继而衍生出了各种地方声腔,如祝允明《猥谈》所云:
自国初以来’公私尚用优伶用事’数十年来’所谓南戏盛行’今遍满四方’辗转改益’又不如旧’愚人蠢工’徇意更变’妄名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之类。[5]
可谓“腔有数种,纷纭不类”,这些声腔进过了长期的发展与互相吸收,最终在清中后期呈现各地方戏种的大繁荣。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情况,便是昆剧的兴起,嘉靖年间的曲家魏良辅,以昆山腔“流丽悠远”的特点为核心,吸取海盐腔的某些长处加以改革,创制出了“转音若丝”的新声,并最终形成了昆腔演唱体系。嘉靖末年,这种新声也伴随着各个昆腔流派传到了各个阶层,渐渐地成为了剧坛的主流。从宏观的角度考察,昆曲的兴盛对于南戏和整个戏曲史是具有深层次意义的,昆曲兴盛之后,不仅使南戏在剧本体制上正式完成了向传奇的过渡,也带来了舞台艺术的巨大变化。
演出的舞台逐渐正规化,明四家仇英所绘《南都繁会图》之中的戏台,其前台为步棚平台,后台则仿歇山顶式塔成尖顶席棚,前后台都搭在高出地面的座基上,舞台上红氍毹铺地,三面彩结栏杆,形制相当规整,这是宋代临时性勾栏乐棚的进一步发展。在士大夫阶层,堂会演出则得到了极力推崇,藩王士大夫在家中府宅铺张戏剧之排场,并普遍饲养家乐,堂会演出在明代风靡全国。厅堂是堂会演出最常见的场所,厅堂作为演出场所一般是在大厅中铺上一方地毯来标示表演区表演区周围则设桌席供主宾坐赏,若有女眷还要另设女座,以垂帘相隔。
步入清代以后,昆曲仍然流行与市井戏台、茶园与士大夫的堂会之中,而且受到了清廷的追捧,进入了庄严的宫廷,也是在此时,宫廷戏台应运而生。清宫廷的戏曲演出在极尽排场之奢华的同时,古戏台富丽堂皇的建制程度也达到了顶点,出现了“水台”、“亭子台”、“行台”等室内戏台,更是出现了楼阁重台式的三层大戏台,高达二十一米,并发展出了如“云梯”、“云勺”、“云板”等一套特殊与三层戏台相呼应的舞台装置,生发了变化多样的舞台效果。[6]
南戏从大众化的勾栏瓦舍,以昆曲的形式被搬演到了士大夫厅堂的红氍毹,而南戏的表演艺术也伴随着演出场地与舞台形制的演进而发生了变化。其一是表演虚拟性的深化与细化,随人物动作展示舞台场景的表演方式,宋元南戏已有之,但昆曲中的运用则更为熟练多样,如行舟走马等动作,在昆曲的舞台上,不仅是以马代鞭,还要分马的毛色,坠马时还要表演翻筋斗的技巧;行舟时,舞台调度与表演也有许多考量,摇桨的动作站位的动作都有规范;就连戏曲舞台上最为普遍的“圆场”,其每一个步伐、姿势、频率对于昆曲艺人来说也都有讲究,南戏虚拟化的舞台处理方式,在昆曲中被进一步深化和细化,表演愈发的具有雕琢性。
其二是艺术风格的高雅化。昆曲“水磨”式的强调与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方式十分对口,并渐渐成为了文人和士大夫赏玩的工具,在这一过程中,接受者对昆曲的演唱方式的专研越来越细致,出现了很多的“清曲”家,对唱演的发音精益求精,“曲子化”的倾向在昆曲的发展中被不断地强化,昆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流淌在书卷间的弦歌流响”与典型的生长在“雅文化圈”的植物。昆曲的这一艺术特点不仅直接的关系到了明代中后期传奇的创作,也使南曲戏文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宋元时期戏谑喧闹的表演特征,表现出了雅化与抒情化的趋势。
其三是脚色行当的专门化。南戏中已经有了生、旦、净、末、丑、外、贴等脚色行当,而在昆曲中,演出角色的分类则更加的规整与细致,有“二十家门”之称,生有官生、巾生、鞋皮生、雉尾生,旦细分为老旦、正旦、作旦,净行分大面与白面,末细分为老生、末、老外,丑行则有副和丑两个家门,行当众多,每一个脚色的发声腔调与舞台程式都各不相同,昆曲脚色行当的专门化与表演虚拟性的细化相呼应,昆曲在这一历程中,最终蜕变出了系统完备的表演艺术体系。脚色行当的专擅与分工,也使昆曲渐渐形成了“寓技于折”与“依行分戏”的表演的特点,并在艺术本质演变过程中直接影响并促生了昆剧折子戏的形态,这种技艺精湛、程式高超的折子戏在明清之际风行全国,在清乾嘉年间达到了顶峰,形成了昆曲折子戏的传统,并且波及了之后几乎所有的地方剧种。
二、“温州南戏新编系列工程”对南戏舞台模式的再现与改编
南戏在虽在昆曲传奇兴盛后完成了其历史使命的交接,但南戏却从未在之后的戏曲艺术发展中消失,其剧本艺术与舞台艺术,对其后世各阶段古典戏曲舞台艺术的变革都发挥着影响力。那若将古南戏的舞台艺术放在当下的戏曲生态中进行考量,是否仍具有意义呢?温州文化界在新旧世纪推出的“南戏新编系列工程”,其改编的六部南戏旧剧《张协状元》《荆钗记》《白兔记》《拜月记》《杀狗记》和《洗马桥》,其在实际演出中所展现的舞美艺术与演出效果,从直接的艺术实践活动中,正面回答了这一问题。
1.虚化的舞台布置与空灵的舞台背景
传统戏曲舞台所用的装置与道具又称之为“砌末”,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认为:“砌末或为细末之讹”,[7]传统戏曲的舞台布置历来都是十分简略的,南戏的舞台布置更是如此,有时甚至不用道具,演员即是道具,这直接造就了戏曲舞台美术的从属性,即其所有的舞台手段都以塑造人物与凸显演员的表演技艺为目的,绝不允许舞台美术喧宾夺主,分散观众对演员表演技艺的欣赏与注意力。
导演在排演这六本新剧本时,在舞台道具的布置与选取上,仍然是以“简约”为原则,整体虚拟化的舞台布置依然是“新编系列工程”舞台美术方面最基本且鲜明的特征,六部戏的演出可以说大都是在观众的“想象”中进行的。
传统的舞台道具如“一桌二椅”也被导演在编排时加以利用,如越剧《荆钗记》的《参相》《惊变》两折,灯光一切,人物一换,桌椅位置稍微一变,舞台上的场景就从相府变成了钱宅,桌椅仍旧是桌椅,但舞台时空却早已大不相同;又如越剧《拜月记》中《住店》一折,老张头与老张婆将两张木凳一拼,凳就瞬间成了床,台上的场景也悄悄地从大堂移到了卧室;而在瓯剧《杀狗记》中,“一桌二椅”更是贯穿全剧的唯一舞台布置道具,一桌二椅从正剧开场一直到剧终都一直被放置在舞台上,但演员动作的变化配合着捡场人对桌椅位置的置换,这简单的一桌二椅却幻化出了孙府、小店、破窑、妓院、雪地、墓地、荒郊、官府等近十处不同的场景,舞台无实景实物,都是借助这简单的“一桌二椅”虚拟化地表现。除了“一桌二椅”,瓯剧《杀狗记》还在剧场中重现了“戏台式”的传统演出场地,南戏在宋元时期大多在临时搭建的勾栏乐棚中进行演出,好一点的演出的场地亦不过是庙台,或临时搭建的戏台,乐队安排在舞台的后部,这种简陋的舞台搭建方式一直被古典戏曲所传承,焦菊隐先生如此描述:
舞台一直是方形的’高出地板五尺。观众可以在舞台的三面看戏’第四面是后墙’是用木隔扇做的’把前后台隔开’舞台的上、下场门是两幅布帘子’右边的是上场门’左边的是下场门。乐队在舞台的后部上、下场门之间。这种布局在传统戏院中流传了好几百年。[8]
瓯剧《杀狗记》的舞台正是按照这一模式架构,舞台为方形,画栋雕梁,后台一排屏风,书画并举,左为“出将”,右为“入相”,台前有两根台柱,上悬黑地嵌金对联,而一对乐师则直接在画屏前就坐,各操乐器,锣鼓闹台,观众在颇具现代感的剧场中观赏到了传统南戏的舞台搭置。
在这六部剧中,《张协状元》的舞台布置应是最为独特同时也是最为简约的,场上除了演员几无旁物,连“一桌二椅”这种最简单的舞台布置都被拿掉,全剧没有出现哪怕一张桌椅,剧情需要的一些道具,如桌、凳、门等,全都由演员用身体表演,场景的变化也是有演员的舞台行动加以传达,除了桌椅,一些大型和活动的道具也是由演员用动作表示,如张协夺魁游街一场戏,胜花手握两面红旗舞动,张协手执一条赶马鞭一挥,舞台上轿、马便“都已具备”,演员几乎是舞台上唯一的中心,这同古南戏《张协状元》极为神似,戏曲舞台布置的虚拟性发挥到了极致,而写意的美感也在这极致的简约中呈现给了观众。
几部剧如古南戏一般,“砌末”不堆砌,不繁琐。它有赖观众的想象,以少胜多,力求“不全之全”的艺术效果,在此过程中,“砌末”协助表演,同时也借助表演,并在相辅相成的过程中使戏曲艺术化为了“不似之似”。
南戏简陋的舞台布置定型并发展了传统戏曲虚拟化的艺术呈现,但在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舞台背景的单调与缺失,旧时舞台的背景多为一块后幕,且多采用百折式的设计方式,缺点很多,梅兰芳先生就曾指出:
台上的后幕’现在一般采用百折式的’从观众席上看去’是很强烈的一条条下垂的直线。这一大组从空而降的直线下端都落在角色的身上’好像台上的人都被这许多直线吊起来似的。[9]
而这一块后幕的设置也并非以充当舞台背景为目的,其作用也仅仅是隔开前台与后台,有些舞台甚至连这一块后幕都没有。现代的戏曲舞台虽多舍弃了百折式的后幕,但舞台背景在舞美上乃至剧情结构上仍相对边缘化,艺术特征也有所欠缺。
在为六部新编剧目构造舞台时,各剧的舞美设计特别注意了舞台背景的设计,他们以中国古典艺术为支点,以此构架了全新的背景设计模式,将舞台背景已和全剧的剧情与演出形式融合为一,成为了构成舞台有机整体重要部分。
越剧《荆钗记》《拜月记》与永昆《张协状元》的舞美设计都由朱吉庆先生担当,他把舞台背景的设计与中国古典书画艺术相结合,将空灵典雅的舞台设计理念融入了设计过程中。
《荆钗记》的舞台背景以“江浪”为主要元素,以绳幕作为结构支点,在舞台上“绘制”了一副巨大的中国水墨画,并构成了全剧的舞台背景,这幅印有滚滚江涛的画天幕巧妙地契合了全剧内容与剧情的发展,王、钱的江边相识,江边分别,钱玉莲闻得休书绝望崩溃投身滚滚江水,最终二人在江心屿的团圆,故事的重要场景大多都发生与江边,因此以“江浪”作为舞台背景无疑是经济且准确的。此外,这幅以“江浪”为主题的画天幕更是充分地强化与调动了观众的舞台感受,十年前王十朋向钱玉莲表明心意,许诺永不相负时,幕布上的“江浪”涟漪荡漾,绳幕参差有致,台上的场景使观众有微风拂面、鸟语花香之感;而此后玉莲接到休书绝望投江,画天幕上的江涛在灯光音乐的衬托下一时“江浪滔天”,而幕檐上重重卷曲的绳幕则酷似乌云翻滚,舞台瞬间给与了观众一种“大祸降临”的感受;数年后王十朋与钱玉莲相见于佛堂,活动的幕绳更是构成了流动却又朦胧的多重表演空间,王十朋与钱玉莲思相见、难相见的内心被形象地展现于舞台;最后二人钗圆江心屿,台上盏盏荷灯亮起,画天幕上的江涛又变得波光粼粼,一道道的绳幕则如轻纱曼帐,舞台仿佛变成了一条沐浴着有情人的温馨爱河。
这种朦胧梦幻的舞台背景设计模式在越剧《拜月记》中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拜月记》的舞台背景主题也是一块巨大的幕布,但这块天幕上却没有绘上图案,仅有一轮由灯光投射而形成的“明月”,这一轮的“明月”在剧情发展、人物描写、舞台表演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随着剧情的发展在天幕上时隐时现,出现于不同舞台位置,从左到右,从右到左,并变化出圆缺盈亏的不同形态,在表现非晴天以及室内的场景,如雪天、店中时,明月便从舞台上隐去;在国家危难、亲人失散时,月缺如钩;在吐露爱意,月下抒情时,月圆如镜;天幕上的“明月”在位移与显隐中,暗示着场景的变化与剧情的发展,并成为了剧中人物内心情感的外化,在舞台上构造了多维的抒情空间。
越剧《荆钗记》与《拜月记》的背景设计结合了中国绘画艺术,而永昆《张协状元》的舞台背景在设计上采用的则是中国的书法艺术,在总体上显得更为古朴典雅。舞台人员在舞台后方支起一面屏风,屏风以墨黑布色,用行书刻印上《张协状元诸宫调》中的部分内容,至此,舞台背景便以搭建完成。而这古朴简单的背景与永嘉昆剧“以人做道具”、“一人饰多角”以及“以生活为出发点”的演出方式化为和谐统一的整体,古典的屏风不仅作为装饰的背景而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全剧“典雅复古”的特征,让观众从剧本,到表演,再到舞美,感受到了原生态的古南戏风味。
不论是《荆钗》中绘上江涛的天幕,或是《拜月》中朦胧变幻的“明月”,还是《张协》中以行书写就的屏风,这些舞台背景已是彻底地在形式与内容上与整部剧融合成为一,如果说虚拟简约的布置是对舞台的“净化”,那么这和谐大气的背景就是对舞台的“美化”,是真正空灵整体的大写意。
2.程式化的舞台行动与检场人的新用
戏曲艺术形成初期的南戏则以开始尝试突破生活的繁琐,将戏剧艺术的“假定性”在舞台上放大,在舞台上创造出“假定的真实”,中国戏曲的写意性也由此不断生发,导演与演员在创造这种“假定的真实”的过程中,一套完备规范的演出程式也由此生发。
对于程式,内涵广泛,有广义的“程式”,也有狭义的程式,但无论程式如何定义,程式对于戏曲的意义是始终无法被忽略的,《荀子·致仕》有云:“程者,物之准也。”[10]张庚先生就曾指出:“离开了程式,戏曲鲜明的节奏性和歌舞性就会减色,它的艺术个性就会模糊。”[11]可以说,有“戏”的地方就有程式,在宋元南戏的演出中,程式已经初见模型,在后来的昆曲与折子戏的演出中被进一步规范与细化,程式使戏曲具有了独立的美学特征与艺术风格,也让演员的舞台行动不会变成而真正“戏曲化”的行动。“新编系列工程”的剧本被导演和演员搬上舞台时仍旧是借助了程式,并取得和很好的舞台效果。
首先是再现原生态南戏表演方式的形式程式。在古代南戏表演时,在正文开演之前,都会先出现一个角色来一段“引戏”,谓之“副末开场”,如《琵琶记》的第一出便是《副末开场》,此外,剧中还会出现一两位角色之外的人担任“检场人”,负责舞台的杂物工作,这是南戏演出形式中重要的程式,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戏改”中被渐渐移除了。在新编瓯剧《杀狗记》中,编剧和导演又重新安排了一位舞台人员,在戏文开始前先登场“引戏”,并在戏曲演出过程中担任捡场人,还原了“副末开场”与“检场人”的形式。
除了副末开场,早期古南戏由于戏班人员与条件的限制,还具有“一人饰多角”和以人做道具的表演方式,这也是程式的一种,但在现今,这些传统的表演“程式”也越来越难看见了,而新编《张协状元》却又一次再现了这些“程式”,剧中六人分饰十二角,有些演员在转换角色时直接在舞台上换装;此外,剧中角色“作凳”、“作门”、“作椅”的表演多次出现,南戏原生态的表演方式被生动地再现于今日的剧场。
其次是虚拟生活状态的动作程式。张赣生曾如此描述程式:“不是把生活的本来面目原封不动地搬上舞台,而是对生活的自然形态进行艺术加工,主要是通过精选和装饰这两种处理使之成为一种规范化的形式。”[12]古南戏在演出时也是选取了生活中常见且具有典型意义的动作,删去其琐碎的细节,对主要流程进行夸张,并最后用假定性的方式虚拟的展现于舞台。
越剧《荆钗记·投江》一出,钱玉莲悲愤投江,演员的动作仅是做一段舞蹈后向后台纵身轻轻一跃,场上灯光一切,“投江”的动作就算完成,舞台上无江无河;瓯剧《杀狗记》开场孙华与胡、柳二人结拜,三人杯中无酒,口不沾杯,只用袖将口一遮,身向后一仰,将空杯底向观众一亮,便示“一饮而尽”;越剧《洗马桥·拜寿》一出,肖月英为宋湘缝补破旧的衣衫,演员面对观众,一手拿起衣服,一手用手指模拟了一个拿针的动作,在空中来回的比划一下,破旧的衣裳便被“补”好了。场上无江无河,演员手中无秤无针,杯中无水无酒,场上实物的缺失完全不会妨碍到舞台动作的展示,演员用假定虚拟的方式,让这些生活的动作在观众的想象中一个个生动地进行着。
最后是延展虚拟舞台时空的时空程式。舞台动作是舞台行动的表现形态,在戏曲众多的“程式”动作中,表现虚拟舞台时空的”程式”无疑是最为鲜明和令人印象深刻的,舞台时空也在这些表现时空的“程式”中被虚拟化并无限延伸。如《白兔记·见子》一折,刘承佑带人千里追猎玉兔,几个人在台上来回几个“圆场”便翻越几十里到了李家村;再如《杀狗记·救兄》一出孙荣在躺在躺于地上的孙华背上轻拍几下,场上再出现几位拿着白旗舞动的演员,舞台便被虚拟成了大雪纷飞的寒天;同样如《张协状元》第一出,张协被劫,衣不蔽体,在舞台上不停的颤抖便暗示天寒地冻,借助于“程式”,舞台的时空得到了最大化的延展,如千年前南戏在勾栏乐棚中展现相府宫宇、名川大山的手法如出一辙。
前面提到的检场人,以广义而言,也是古典戏曲的一种程式,不仅在南戏,可以说在戏班出现后,检场人便以存在,并成为了中国传统戏曲的专有名词,而其意义也在随着戏曲的艺术实践而不断发生变化,其大致含义为游离与剧情角色之外的舞台上负责杂物的工作人员,李斗《扬州画舫录》有载:“小锣司戏中桌椅床凳,亦曰‘走场'。”[13]《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进一步解释为:
检场人就是戏曲舞台上演出的辅助工作者’又称“走场”、“值台”、“打杂师”’其职务为:打门帘、摆桌椅、递砌末、撒火彩、帮演员在场上更换衣装’演员在做高难度动作时进行安全保护等。[14]
检场人虽不直接构成传统戏曲的舞美,但却和舞台密切相关,演员的换装登场,桌椅道具的摆放都要靠检场人完成,是旧时戏班不可或缺的组成人员,因此其本身也成为了舞台的有机组成部分。
20世纪50年代的“戏改”运动中,“检场人”也被认为是旧戏的陋习而从剧场中渐渐移除,这其中固然是有浓厚的政治因素,但也应承认,一些戏的“检场”形式确实带有了旧时不良习气,而其完全游离于剧情之外的舞台职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演出的完整性。在当下一些现代新编剧目中,检场人的价值开始被导演重新发现,如2000年由林兆华指导的京剧《宰相刘罗锅》,在该剧中,林兆华便安排了“检场人”,并创造性的使之成为了舞台“布景”的一部分。
《杀狗记》与《张协状元》两剧皆由谢安平指导,在编排瓯剧《杀狗记》时,谢安平在演出过程中完全恢复了“检场”的形式,在检场人上场摆放桌椅、搬运道具的时候,舞台上也没有使用暗光、换景以及落幕等遮掩的动作,明确地在演出中向观众显示了“检场人”的存在,而除了给“检场人”安排舞台杂务外,导演还赋予了“检场人”全新的职能。在戏开场时,检场人在担任了“副末开场”的工作,他向观众说明剧情大意,与后台伴奏人员配合进行说唱,将观众渐渐引入戏中,而在需要登场搬运道具时,“检场人”更是成为了剧作者的代言人,以绝对全知的视角关照着整部戏,并引导观众进行思索。如演到孙荣被孙华赶出家门,第一出戏结束,检场人上场摆放桌椅准备第二场戏,但他并非匆匆摆好道具便下场,在搬运道具的过程中,他也如演员一样向观众演唱:“忠言逆耳反生嗔,只因引鬼入家门”,暗指孙华与恶人为伍;在第七出戏《扫墓》结束,黄狗被毒死,检场人上场收拾桌椅,并带饰演黄狗的演员一同下场,编剧和导演也为他安排了一段念白:“篱笆破,狗进屋,坏人为伍,终会出大祸”,向观众说明交友不慎,将会使家庭不和。
谢安平将检场人融入剧本剧情与剧场舞台的做法在永昆《张协状元》中表现得更为独特。这种独特便是大多观众在看完全剧时都不会发现检场人的存在,但仔细观察,检场人几乎无处不在,如果说《杀狗记》的检场人是“显性”的,是直接的,那么《张协状元》里的检场人便是“隐性”的,其检场人直接是由剧中的两个角色——庙判与庙鬼担当,完全地融入了剧情,加之二人在帮助其他演员处理舞台事务(如换装)时,导演还是用了暗光等舞台手法,因此其存在便更加难以觉察。作为全戏最先登场的两个角色,在开场时先作为净、丑串场,为舞台暖场,引出正戏,在正戏开始后,二人多次在剧情的衔接段出现,帮助演员在台上换装(帮小二改扮王德用),拿放临时道具(张协游街时吹弹乐器),而在无剧情戏份时,则多次直接充当布景与道具使用,如在古庙中作门,在状元府中作门,演员的换装、台上的杂务、剧情的衔接与圆场等检场人的工作大多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这两个角色相关,但二人同时又是剧情中的人物,更是舞台的“重要部件”。
“检场人”的形式在“新编系列工程”中被重新启用,但不同于旧式的“检场人”,导演和编剧在新戏中给其赋予了全新的职能,“检场人”不再只是游离于剧情之外的舞台杂务人员,不再只是“过场”,他可以充当作者的视角关照着全剧并与观众交流,强化着剧场中“间离”的感受,可以直接成为剧情中的角色,甚至可以作为道具与布景融入舞美,是旧的形式,新的用法。
3.节奏化的舞台灯光与立体式的舞台空间
南戏从剧本到演出都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情节剧烈的冲突,悲喜两条线并行交错,并由此产生强烈的戏剧效果和节奏感,《张协状元》、《琵琶记》等剧皆是如此,在演出过程中,古南戏因条件所限,很多时候只能通过自身的动作和上下场来表现这种冲突,随着舞台科技的发展,当下舞台对戏曲节奏感的表现已呈现多元化的手段,在“新编系列工程中”,最突出的手段就是舞台灯光。
其一是表现场景冷暖交替的节奏。《张协状元》全剧舞台侧部与顶部的照明光的变化其实并不突出,观众大致只能再换场时察觉其存在,但全剧舞台的背景光,即天幕光却十分丰富,开场第一出的天幕光为淡蓝色,衬托出了古庙的寒冷昏暗;到第二出天幕光突然一换变成了亮黄色,场景也立刻跳转至王府;而到了张协夺魁游街走马时,天幕光的的色彩进一步强化,变成了亮绿色;之后张协路经古庙,萌生杀心,舞台色彩又呈现出深蓝色,古庙在杀意的面前阴森可怖。在天幕光的变化中,舞台的场景由冷到暖,又由暖到冷,尽显戏剧效果,但只有变化还不能说是节奏,节奏还包括停顿,在场景冷暖变化间,导演也安排了过渡的衔接,每一次场景将要转换时,天幕光都会暂时熄灭,而只留一两束照明光,并将光源缩小,亮度调明或调暗,打在庙判与庙鬼二人身上,二人或帮助演员完成换装,或引出下一场戏,这使得场景转换的节奏流畅自然,观众毫无突兀之感。
其二是展现人物内心悲喜变化的节奏。《拜月记》舞台灯光总体的基调是暗蓝色,特别是蒋世隆与王瑞兰夜宿林中小店,二人互相交替在月下抒发对对方的倾慕却又无法结和的情感时,舞台又另亮起了两束顶光,衬托幽深的舞台氛围,二人矛盾失落的心境也在灯光中被外化;而后二人解开心结,店中成婚,顶光也渐渐转亮,并最终变成了红黄二色,渲染着场上喜庆的氛围,也表达着二人由失落到欢喜的内心变化,调动了整个剧场的演出节奏与欣赏节奏。
南戏的舞台从勾栏乐棚到厅堂茶楼,再到宫廷庙宇,形制逐渐规整与完备。如今,戏曲已经走进大剧院,演员有了更宽广的舞台,观众获得了更佳的视听效果,但纵观戏曲舞台的演变历史,虽然场所的规模越来越大,建筑的结构越来越复杂,但总体上仍是在平面的横向方面扩展,舞台宽度和深度在加宽加深,但立体纵向的空间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演员的表演依旧大多是在一个单一的平面上进行。温州各剧团的导演在编排新编南戏的过程中,对这舞台上向来被忽视的纵向空间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挖掘,其中几部新戏的舞台都已有了纵向空间上的发展,舞台空间也已超越了单一平面化的视角,变成了多维立体式的呈现。
永昆《张协状元》将舞台的后侧,与舞台背景连接处,设置成了一座最大高度约0.5米、宽度约为整体舞台一半的半圆形“缓坡”,这一“缓坡”在表演过程承担了重要的舞台功能,实际上,这一“缓坡”是作为舞台的第二道“后幕”而设置的,它是舞台上主要剧情人物以及舞台中心转换的过渡区域,如第一出古庙里众人为张协与贫女求姻缘的情境,张协初到古庙,为重点表现张协的窘迫,庙鬼与庙判退于后侧的“缓坡”处,张协便成为了舞台唯一的中心和重点表现的对象,而后来众人为二人的姻缘求神时,张协与贫女则退至后侧,大公与小二、庙鬼与庙判便成为了观众注意力的聚焦处,如此一来即使省去了演员繁琐的上下场,也可以是舞台与剧情的中心自如的切换,演出的完整性大大提升。
越剧《荆钗记》的舞台是“戏中戏”的架构模式,在舞台之上又另设一座并不易察觉的“小舞台”,在开场时,这一“舞台”很好地展现了“序幕”的内容——王、钱二人在江边看南戏,戏中戏的内容也让观众得到了别样的戏曲观感;而随着剧情发展到玉莲投江时,“小舞台”则成为了剧中人物内心空间的外化,十年前南戏中的投江女再现于舞台,钱玉莲心中的绝望与伤感展露无遗,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舞台场景的设置在此时早已超越了纯粹舞台空间的概念而进入了舞台时间的层面,它使剧情超越了传统戏曲一贯顺叙的叙事时间,在舞台上创造性地呈现了回忆与倒叙的叙事时间,是“新”的突出表现。
再如越剧《洗马桥》舞台上临时搭置的石桥,其一方面作为戏主题“洗马桥”的象征而存在,在另一方面也是戏剧矛盾开始积累到完成爆发以及全剧高潮展开的地点,从一开始刘文龙与肖月英在桥上的恋恋不舍、依依惜别,到十六年后二人在桥上重逢时的百感交集,剧情的收束与人物塑造的完成都在桥上加以呈现,剧情的高潮与最终所有矛盾的爆发被放置于舞台最突出的位置,《洗马桥》中的石桥成为了舞台的“最高叙事层”与“最高抒情层”,并强化了剧名的意义。
三、结 论
在现今多数学者的认知中,明中期昆曲走向兴盛,传奇创作步入高峰之时,南戏已趋近衰歇,并最终消亡。但若仔细考察戏曲发展的实际,在近八百年的戏曲史中,南戏其实从未“缺席”,南戏的消亡仅是一个学术名词的消失,它转化成了各种多元化的形态潜藏于戏曲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在剧本创作,而且在舞台艺术上影响着戏曲演进的形态。在后世的戏台结构、角色分类、表演程式以及舞台节奏等各方面,都可以清晰的看见南戏的烙印,是对南戏艺术在某种程度与意义上的改编。
南戏剧场戏台的固定与规范,登场脚色的合理与明确,虚拟性表演程式的深化与细化,声腔的专门化与雕琢性,都直接、间接地影响,甚至促成了之后各地方声腔的产生,昆曲的兴起,折子戏的繁荣以及地方戏的百花齐放,近世各时期的曲论家和戏曲艺人,将南戏舞台艺术的一个或多个方面加以利用,并融合时代的风尚与观众的需求,多次使得某种戏曲艺术形式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兴起和繁荣,现在被学界无数次提及的戏曲“改编”其实在中国戏曲成熟以后便已经成为了戏曲发展的重要途径。
“温州南戏新编系列工程”也借鉴了这一经验,挖掘了南戏艺术宝库中的某些要素,并经改编后重新呈现于舞台,从最终的演出效果来看,《荆钗记》的首演单位温州市越剧团创造了近年来创作剧目演出场次的最高纪录,并在浙江省第七届戏剧节中获优秀新剧目奖;《杀狗记》获得省剧本一等奖,参加了全省艺术节和香港国际艺术节,并入选了由文化部主办的全国地方戏优秀剧目评比展演,在港澳地区大受欢迎;《拜月记》与《洗马桥》以“青春”的方式亮相,从温州一直演到东三省,几乎场场爆满;而永昆《张协状元》更是在2000年苏州举行的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引起了轰动,于2002年荣获中国戏曲学会奖,并使已经消亡的永嘉昆剧重新获得了造血的能力,以“一剧救活了永昆”。
这些成就在当下的戏曲环境中,都可以称之为奇迹,而成功的背后,剖析其原因,其中关键的一点正是“新编系列工程”的编剧与舞台指导人员对古南戏艺术特征的利用与改编。改编不仅包含了剧本文学与舞台艺术两个部分,更应该涵盖艺术的继承与创新这两个更为重要与深层的侧面,对于剧本是如此,对于舞台艺术,亦是如此,“新编系列工程”将南戏的某些开场方式、表演程式、舞台节奏重现于其中的某些新编剧目之中,并用当前新式的舞台理念与先进的舞台科技进行改造,成功地吸引了当代各阶层观众的兴趣,让他们走进了剧场,古南戏之演出盛况在现今之时代,在新时期的瓯越大地上再一次重现。
古老的南戏,其艺术价值在当下也并未完全消失,它艺术特性中的某些闪光点,对于先进的戏曲工作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改编绝不意味着丢弃传统,恰恰相反,对于古典艺术的发掘与再利用,才是改编的基础,郭汉城先生有言:
艺术一经形成有相对的独立性’落后的时代不一定等于落后的艺术’戏曲艺术是产生在封建社会’但贫乏的物质条件与我国的大文化背景和审美理念相结合’就成为历史的、具体的、独特的审美形态。[15]
对于戏曲艺术更是如此,不顾一切的打破与颠覆,必然会造成对戏曲艺术本身的破坏,比起毫无头绪和根据的所谓”创新“,其实对南戏等古典戏曲艺术的学习与研究,并将其中可利用之处在舞台实践中予以全新的再现,对于当下的戏曲工作者而言,无疑更为重要。
[1]吴自牧.梦梁录[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95:298.
[2]孟元老,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6:144.
[3]徐渭.南词叙录[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三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239.
[4]王骥德.曲律[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154.
[5]祝允明.猥谈[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6]高倚华.中国演剧史[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273-277.
[7]王国维.宋元戏曲考[M]//王国维戏曲论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84.
[8]焦菊隐.今日之中国戏剧[M]//焦菊隐论导演艺术:下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460.
[9]朱家溍.梅兰芳漫谈舞台美术[J].上海戏剧,1962(8).
[10]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262.
[11]张庚.中国戏曲[M]//大百科全书.戏曲卷导言.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
[12]张赣生.中国戏曲艺术[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55-56.
[13]李斗.扬州画舫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0:130.
[14]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戏曲曲艺》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145.
[15]郭汉城.温州南戏新编剧本集·序[M]//温州南戏新编剧本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3.
(责任编辑:周立波)
Contemporary Reproduction and Adaptation of the Stage Art of Nanxi—Taking“the Project of New Series of Wenzhou Nanxi”as an Example
PU Han
The emergence of nanxi marks the really mature of classical opera art.In the early stage of its formation,a complete set of stage art pattern is formed,which has influenced the evolution of the stage art of opera afterwards.In a certain extent,most drama forms absorbed nanxi's artistic features,and their stage art also achieves gradually self perfection by the absorption and adaptation of nanxi's stage art.At present,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of nanxi opera's hometown Wenzhou learn from classical operas.At the turn of the new century,they launched“the Project of New Series of Wenzhou Nanxi”.Its stage art absorbs the stage and performance pattern of nanxi,combines contemporary stage ideas and stage technology,and reproduces the stage structure,performance pattern and stage rhythm of nanxi's performance scene with a new appearance.The performance is a success.The successful adaptation of“the Project of New Series of Wenzhou Nanxi”is a new contemporary recognition of nanxi art.It has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practice and research of current drama stage art.
stage art;nanxi;development;reproduction and adaptation
J802
A
2015-10-28
浦晗(1991— ),男,江西新余人,苏州大学戏曲史与戏曲文学方向博士研究生。(苏州215123)
*本文系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南戏文献全编》整理与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3&ZD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