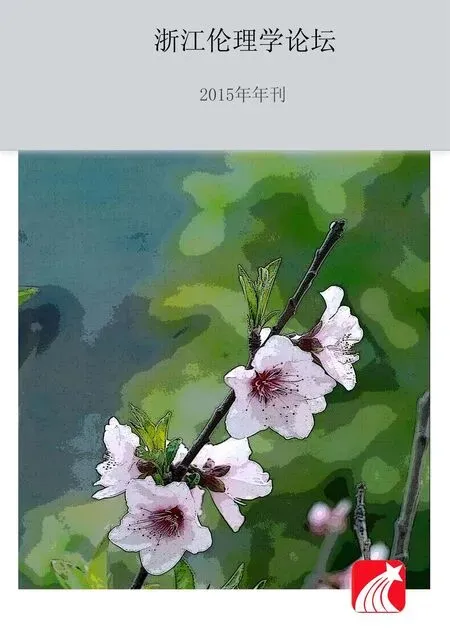论道德教化①
肖会舜
论道德教化①
肖会舜②
教化不仅在于使人成其为人,更在于使人超越其个体性,成为普遍性的精神存在,从而获得真实的自由。笔者追溯中西方语境中的教化概念,明晰教化的实质,对传统道德教化与现代性道德教化进行批判性分析,旨在寻求适应现代伦理精神的道德教化。
教化;伦理实体;现代性
教化,在中西方文化中都源远流长:一方面,由于个人只有经过教化方才与动物区别而成为人;另一方面,也只有经过教化才能使人脱离孤立的个体,即塑造具有普遍性精神的个体。教化实际上就是使主体实体化和实体主体化,把个体塑造成具有精神性的类存在,从而进入人道或人文的世界。
一、中西方语境中的教化
在中国古代,教化首先是指一种政治—伦理举措,所谓“明人伦,兴教化”是也。《说文解字》释“教”为:“上所施,下所效也。”即是说,教化是通过政治教化来实现的,它要求统治者有一种较高的道德情操并承担一种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的道德责任,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荀子·王霸》)。所以董仲舒说:“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汉书·董仲舒传》)因此,从教化的目的来说,一方面,教化是为了维系传统社会的正常秩序并使人和谐相处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教化具有人文意义,即通过教化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人之所以能够从动物界抽身,就在于人能够创制规范并赋予这种规范以生命的意义与人道的价值。人对于整个自然宇宙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渺小的,只有通过道德教化,开辟一个内在的人格世界,才能开启人类无限融合及向上提升自我的向度。“人只发现自身有此一人格世界,然后才能够自己塑造自己,把自己从一般动物中,不断地向上提高,因而使自己的生命力作无限的扩张与延展,而成为一切行为价值的无限源泉。”①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1页。自然性的人是有限的,但通过道德教化所开创的人格世界是无限的,它能够通过对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天道”“天理”的契合而实现与“天地参”。
从教化的内容来看,“教”不是灌输抽象的客观知识和形式规范,而是“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教以人伦”就充分体现了德性生成条件的各种人伦关系之间的互动,伦常礼俗不仅具有超越性,更具有现实性与客观性。如果说“教”体现的是人的向上的维度,那么“化”则指向道的下贯维度。没有“化”之一维,则“教”必流于空疏。“道”化而成“德”,“道”以“德”的方式呈现出来方可谓“化”也。《说文解字》释“化”为“教行也”,可谓精当。“化”是通过政治—伦理措施使“道”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得到落实,使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受到共同体价值的型塑与精神气质的改变,畅行于社会的人伦规范、政教措施获得了理性的认肯与情感的支持,并进驻人的心灵,甚至作为一种无意识或潜意识而成为人的“第二天性”,正所谓“化民成俗”是也。教化是关乎人的整个伦理性存在的,它是人的心灵感受到共同体的普遍价值并以这种公共本质提升个体性的存在,获得生命的意义。“个人全部内在的经验、感觉、情绪和思想在接触外界的过程中,与外在的即他人的经验、感觉、情绪和思想等等联系了起来,个人的这一切内在之物必须让他人意识到,它以扩展了的形式显示着完整的人类本性,因为它本身即已为精神力量的种种扩展的、具体的努力所渗透。”②[德]威廉·冯·洪堡:《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页。因此,教化不是单纯的对人的理智进行教化,而是对人的整个存在特别是人的情感进行引导和塑造,并固化为人的精神品质。“教”的目的在于“化”,“化”是指人的内在气质、欲望品质得到了彻底的转变,即人的情感、理智、意志能够以某种普遍性的价值为指引,“从而被塑造成型了一种深厚的、有着超出本能的个别性状态的、与他人甚至外物相通的旷达胸襟的精神品德,而且还截断了倒退到野蛮、粗鄙状态的回路”①詹世友:《道德教化与经济技术时代》,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恰如荀子所说:“长迁而不返其初则化矣。”(《荀子·不苟》)管子也说:“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管子·七法》)由此我们可知,从本质上讲,教化乃是对人的情感的教化,使个别性的情感秉持理性的普遍性。当然,情感、欲望并没有因理性化、普遍化而丧失自身,而是使之具有与人相通的向度。这就说明教化不是单纯的理智教化,而是融理性于其中的情感教化。
古希腊的思想家们也认为德性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学习和教化获得的。教化的希腊词“paideia”就是教人以德行,使某种普遍性的价值支配着人的思想和行动的意思,“教化的基础是一般意义上的支配人们生活的价值意识”。据词源学的考察,“paideia”最初的涵义是“儿童的教养”(child-rearing),“它通常指人类身心一切理想的完美,一种完全的kalolagathia,即nobleness(高贵)和goodness(善),在智者时代,这个概念用来意指真正的理智和精神文化”②杜丽燕:《人性的曙光——希腊人道主义探源》,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84页。。总体上讲,西方语境下,教化更强调一种“形式”(form)并赋型于人心之上,因此在教化方式上,它更强调一种理智教化。因为在他们看来,理性与经验、感觉、欲望是绝对对立的,这种二分结构导致其主张通过理性对激情、欲望的绝对统治来获得灵魂的提升。德语“Bildung”一词也充分展示了教化的意义。史密斯(John H. Smith)通过对赫尔德关于“Bildung”概念的追溯,指出教化概念的意义与范围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单个事物形式(form)的提升;(2)教育(education); (3)人类文化形成(the formation of human cultures)的过程和成就;(4)“人性”概念的历史演变(the historical unfolding of“humanity”);(5)通过按照每一存在者都争取它的理想的有机形式的原则(principle)统一所有自然世界的科学的观点。③John H.Smith:The Spirit and Its Letter:Traces of Rhetoric in Hegel's Philosophy of Bildung,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p.48.
可见,“Bildung”的主要含义是通过一种普遍性的形式对人的自然性的提升,使这种自然性符合人性和理性普遍性的概念。伽达默尔指出,“教化”一词从词源上说,最初起源于中世纪的神秘主义,以后被巴洛克神秘教派所继承,再后通过克洛卜施托克那部主宰了整个时代的史诗《弥赛亚》而得到其宗教性的精神意蕴,最后被赫尔德从根本上规定为“达到人性的崇高教化”(Emporbidung zur Humanität,英文为reaching up to humanity)。①[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9—20页。可见,教化本身就是一个赋形的过程,人最初是本于神所造就的,因此,对于人来说,教化就是使人性通过改变、提升以分有或合乎神性。不过,经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神性下堕为人性,而且人性丧失了精神的丰富性和完整性,因为人性要么直接等同于人的自然欲望,要么通过科学理性或工具理性来认识人的存在,从而把人肢解为没有任何精神和高贵气质的动物,法国启蒙思想家拉美特利的格言“人是机器”可谓道出了近代启蒙思想的人性观。神性或超越性的失坠,使得教化由此丧失了其根基,自由与必然陷入了二律背反的矛盾之中。德国人文主义者(如歌德、席勒、施莱尔马赫、赫尔德以及洪堡等)敏锐地意识到“Bildung”概念在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中的重要地位。洪堡指出:“当我们讲到德语Bildung(教养)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同时还连带指某种更高级的、更内在的现象,那就是情操(Sinnesart),它建立在对全部精神、道德追求的认识和感受的基础之上,并对情感和个性的形成产生和谐的影响。”②[德]威廉·冯·洪堡:《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6页。这样,教化(Bildung)就不仅只是形式(Gelild),而是内在地包含着“形象”(Bild),形象既可以指摹本(Nachbild,英文为image),又可以指范本(Vorbild,英文为model),而形式概念则不具有这种神秘莫测的双重关系。③[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1页。
正如伽达默尔所认为的那样,“教化”概念在精神科学中有着核心的地位。因为从本质上说,精神的存在是与教化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之为人的显著特征就在于他能够从其动物性的生蛮状态走出来,脱离直接性与本能性的东西。而且,人还应该从其个别性的状态中走出来,使其精神的各个方面都习得一种普遍性,他不应该沉湎于他天生所是的那样子,而应成为他所应是的那样。“人类教化的一般本质就是使自身成为一个普遍的精神存在。谁沉湎于个别性,谁就是未受到教化的。”④同上,第23页。教化之所以能够从其直接性的本能存在中抽身出来,就在于它本质上具有精神的理性。不过,精神的理性是一种教化的理性或生命的理性,它并不是通过理智而把“感觉”抹杀掉,而是使人的感觉欲望获得一种普遍性的形式,即获得一种“普遍的感觉”。也就是说,教化“它是一种这样的教育,引导个体把多样的特殊经验内在化,以便通过系统化并作为一般概念来表达并超越它们的特殊性。”①John H.Smith:The Spirit and Its Letter:Traces of Rhetoric in Hegel's Philosophy of Bildung,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p.19.
二、教化的实质
上文已经追溯了“教化”概念在中西方语境中的内涵。那么,“教化”的实质是什么?或者说“教化”要成就什么?黑格尔一语中的:“教化的意思显然就是自我意识在它本有的性格和才能的力量所许可的范围内尽量把自己变化得符合于现实。”②[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4页。黑格尔所谓的“符合现实”实际上指的就是具有精神的普遍性,即要尽可能地把人本身所具有的理智、情感、意志提升到普遍性的层次。但是这种普遍性的提升并不是要把人本身所具有的自然性根除殆尽,而是借助于教化所提升普遍性层次使其能够与他人、社会、历史在精神上进行沟通。自然性并没有丢失,而是保存在普遍性当中,在特殊性中将普遍性体现出来。人只有经过教化才能获得现实性,个体不再是作为单独孤立的个体而存在于世,因为人乃一社会性的存在,即我是作为“我们”之一员而存在的。“我们个体存在的个别性、特殊性、独立性只是相对的个别性,它不仅产生于包容它的统一性中,而且只能存在于其中。”③[俄]C.谢·弗兰克:《社会的精神基础》,王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8页。没有绝对的个体,个体总是受社会共体的熏染而成为定在和现实的,社会共体既是个体成长的基点,但成为社会的个体也是其归宿。黑格尔也指出:“个体的力量在于它把自己变化得符合于实体,也就是说,它把自己从其自身中外化出来,从而使自己成为对象性的存在着的实体。因此,个体的教化和个体自己的现实性,即是实体本身的实现。”④[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4页。实体的普遍性和公共性是个体的本质,个体只有成为实体的一部分才是其自我实现。
不可否认的是,在具体的教化方式上,中西方文化之间甚至各学派间存在着差异,有的认为人只有通过朝向不变的存在即理念或神才能获得教化,而有的则从经验、历史的角度出发,强调对情感、欲望的节制,使欲望的满足获得一种合理性与内在价值的支持。不管怎么样,道德教化都是通过对人的感性直接性的一种延迟、反思,使人获得一种普遍性的视野,从而使人能够站在一个超出自身即具有“他者”的向度来安排自己的个人生活与社会交往,并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获得社会的认肯以及个人德性的提升。伽达默尔指出:“教化作为向普遍性的提升,乃是人类的一项使命。它要求为了普遍性而舍弃特殊性。但是舍弃特殊性乃是否定性的,即对欲望的抑制,以及由此摆脱欲望对象和自由地驾驭欲望对象的客观性。”①[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3页。可见,教化所实现的普遍性其实是自由的表现,人不再受自然性的宰制,而是能够以精神的普遍性价值来决定并创造自我。此外,教化是没有自身之外的目的,因而“也不存在任何服务于达到道德目的的单纯合目性的考虑,而手段的考虑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的考虑,并且自身就可以使决定性目的的道德正确性得以具体化”②同上,第437—438页。。在教化这里,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是内在的、有机的。这与对天赋的自然素质(talent)单纯的培养不一样,自然素质的训练和培养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单纯手段。而经过教化的东西,已然成为人自己的东西了,它已融入了人的存在。黑格尔说:“个体在这里赖以取得客观效准和现实性的手段,就是教化。个体真正的原始的本性和实体乃是使其自然存在发生异化的那种精神。因此,这种自然存在的外化既是个体的目的又是它特定存在;它既是由于在思维中的实体向现实的过渡,同时反过来又是由特定的个体性向本质性的过渡。这种个体性将自己教化为它自在的那个样子,而且只因通过这段教化它才自在地存在,它才取得现实的存在;它有多少教化,它就有多少现实性和力量。”③[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2页。可见,正是通过教化,人的个别性存在向其本质性提升,而人的自在的本质也是通过个别性表现出来从而获得实在性和现实性,但教化后的个别性,就不仅仅只是个别性而已,而是体现了实体性的个别性。
其实,教化就是扬弃自然的自我从而获得现实性。但不幸的是,人们以为自然的特殊性或个别性的存在才是现实的,才是“我”的。现代性及其后现代性就是强调一种感性上的充分自我感,并把这种自我感看成真实的自我。个性在他们眼里就是特殊性,就是标新立异,就是与一切实在、他人相区别,并且竭力使这种特殊性取得实在性。其实这毋宁是取消了“我”性,因为“我们的精神生活只有通过交流、通过为我们及其他人所共有的精神要素的循环才能实现”④[俄]C.谢·弗兰克:《社会的精神基础》,王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9页。。没有他人意识的渗透,单纯的自我感只能是虚幻的,自我意识只有借助于交流才能得到丰富并获得现实性,个性不在于与他人格格不入,而恰恰在于能够被他人理解并接受。所以黑格尔说:“如果个体性被错误设定为由自然和性格的特殊性构成的,那么在实在世界里就没有一个一个的个体性的性格,而所有的个体就都具有彼此一样的存在了。”他还说:“自我的目的和内容则完全属于普遍的实体本身,只能是一种普遍的存在。一个自然的特殊性,如果竟然成为目的和内容的话,那也只有是无力量的和不现实的东西。”①[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3、42页。这一点,C.谢·弗兰克也指出,即使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某个东西、那个表现了我们个人的“我”之最根本、最独特的东西也并非来源于孤立的“我”这个封闭的、独立狭小的范围,而是来源于精神深处,在那里我们与其他人在一个终极统一体中融合在一起。俗语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点对于单个的个人也同样适用,最有独创性的、出类拔萃的人也是最具“全人类”性质的人。只有拙劣的艺术家才在作品中处处突出其特异性、单纯的“我”性,这是一种“伪”个性,真正的艺术家乃是在作品中展现人性中真正普遍的东西,即“我们”性的东西。
对于个人来说,其心灵情感受到教化即指个人的整个精神气质得到了具有普遍性的伦理规范和价值理念的型塑,这种型塑不是暴风骤雨式的,而是潜移默化式的。性与习成的方式使这种普遍性的价值成为了人的第二天性。“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礼记·经解》)“化”就是一种工夫,“化”实际上是使人的心智秩序得以确立,人的整个灵魂、心灵状态得到了彻底的改变,(广义的)理性在心灵各部分中居统帅地位,能够协调好与情感、欲望的关系,使整个的心灵不再拘于“意”“必”“固”“我”,而是具有普遍性的情理,克服、战胜了个别性的狭隘私欲,能够站在与他人甚至天地相“通”的立场来看待自我,获得“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醉名》)的博大胸襟。“化”更是一种成就,它使人的德性结构化为人的精神品质和性格质素而不是沦为一种偶然的善行,偶然的善行在受到极大利益诱惑或威胁逼迫时就会返回到受教化前的粗鄙状态。而由教化获得的“通”感是一种圣人气象,《说文解字》释“圣”为“通”,实为确当。孔颖达疏:“圣者,通也。博达众物,庶事尽通也。”有学者称:“儒学所谓‘性与天道’的形上本体,乃是在实存之实现完成历程中所呈现之‘通’或‘共通性’,而非认知意义上的‘共同性’。因此,这‘通’性,非抽象的实体,而是一种把当下实存引向超越,创造和转化了实存并赋予其存在价值的创生性的本原。”①李景林:《教化哲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绪言第14页。故而可见,教化并不是要把个体的特殊性泯灭,而是提升着人性,使人性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内得于己,外得于人”(《说文解字》)。受到教化的心灵在世界中不再被物役所宰制,而是获得了一个无限性或不朽,它把自我投身于宇宙大化流行当中以获得无限大全的背景支持。教化就是要达到“自己把握其自己的自我”,“它不是把握别的,只把握自我,并且它将一切都当作自我来把握,即是说,它对一切都进行概念的理解,剔除一切客观性的东西,把一切自在存在都转化为自为存在”②[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0页。。而且,教化的真理是获得自我意识与实体的统一,或者说是普遍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真理不是单个的存在物,而是单一物和普遍物、个体性和实体性的统一,或者说必须既是自为存在也是自在存在。
最后,我们还必须指出,由教化而获得的人格是一种健全的人格,它是一种“有生命的平衡”。也就是说,教化的目的是使人心中的情感和理智相互渗透,是情感化的理性或理性化的情感。没有理性的情感是自私的、狭隘的,无法与他者的情感相通,但没有情感的理性是没有生命、没有灵性的。单纯的理智必然是机械而抽象的,没有生命情感的灌溉,理性必然会退化成为毫无生气的逻辑形式。健全的理性必然是要照亮(enlighten)生命的。所以黑格尔指出现在道德教化的工作在于扬弃那引起固定的思想从而使普遍的东西成为现实的有生气的东西。因此,现代教化的实质在于如何使这种抽象的理智概念重新焕发出灵性的跃动和生命的情感感受,使我们的精神不再由于缺乏理性而狭隘,也不再由于缺乏情感而干涸。所以,教化的目的是成就一种健康的精神。这种精神的特点用弗洛姆的话说就是:“有爱与创造的能力……有自我身份感,这种身份感来自自身的经验,即自己是力量的主体和主动者的经验;能理解自身之内及之外的现实,即能够发展客观性及理性。”③[美]E.弗罗姆:《健全的社会》,孙恺祥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4—55页。
三、超越“伦理的专制”和“道德的独裁”
传统的道德教化有其强大的历史根基。社会秩序与心智秩序的同构性使得传统教化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从文化传统、生活实践、人性自然的地基上进行的,日夕熏染,习于向善,进而成就善德。因为作为传统社会规范性力量的“礼”不是理智思虑的结果,它是充分体现了伦理精神的典章制度,“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非天降也,非地出也”,而是本于人情、人性的,“礼作于情”是也。而且,传统社会中伦理生活的整体性与连续性也使其教化范式表现出“润物无声”的特点。不过,我们必须承认,传统的道德教化范式有其自身的弊病,必须向现代教化范式转化以适应时代状况及其要求。传统道德教化总体上体现出一种较强的道德观,这种较强的道德观人为地制造了人伦规范(义)与肉身欲求(利)的二元对立。而且,在传统社会中,“我们”具有绝对的统治力,以至于“我”的合理性要求也被剥夺了。“我们”在传统社会中无所不在,而“我”却始终处于缺席的境地。而且,传统伦理更多地具有自在的、直接的性质,它还没有与自为意识结合起来,亦即还没有在伦理自身内经历分裂,没有与特殊性结合,还处于“自然性伦理”阶段。
现代性道德教化在于从“我们”中解救出了“我”,这不能不说是启蒙以来的一项成就。“我”不是由“我们”得以说明和确立的,“我们”却是由“我”而获得存在的合理性。“我”与“我们”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之间不存在着一条神圣的存在之链,也就是说,“我们”不是“精神性”的存在,而只是“无内容的单纯自我相关”。正是在这一思维的支配下,道德完全成为自我决定的东西,它没有任何特定的内容,只是一种“自为的、无限的、形式的自我确信”。因此,在道德中,“我”也只是一意识主体,没有任何规定性,也不达到任何定在,这样一种形式的自我确信也容易从普遍性过渡到特殊性,因为这里所谓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本身同出一源。“当自我意识把其他一切有效的规定都贬低为空虚,而把自己贬低为意志的纯内在性时,它就有可能或者把自在自为的普遍物作为它的原则,或者把任性即自己的特殊性提升到普遍物之上,而把这个作为它的原则,并通过行为来实现它,即有可能为非作歹。”①[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42—143页。所以,当普遍性本身只是自我自为意识单独决定时,它又有可能造成一种“道德的独裁”。“道德的独裁”是自以为纯洁,并将自我特殊性的意志提升到普遍性之上,要求他人也遵循这种虚假的普遍性,而当他人不服从时,则以道德之名对他人进行强制。导致“道德的独裁”的根本原因在于,道德的观点不要求任何定在或好的后果,因为任何定在如果不是对道德真纯的玷污的话,至少任何定在并不构成道德的实质规定或必然要素。
传统的自在伦理可能导致“伦理的专制”,因为它缺乏个体自我意识的反思,亦即缺乏特殊性环节,甚至把特殊性看作与伦理普遍性截然对立的东西;而自为的道德却也可能导致“道德的独裁”,因为它只是个体自我意识的反思,仅仅把道德停留在隐密的内心世界,它不要求有好的定在或后果,但是这种抽象的良心只是自己知道自己、自己决定自己,它是他人所无法洞彻的。所以当把特殊性提升到普遍性之上并要求它实现时,就可能无视他人的特殊性而导致“道德的独裁”。“伦理的专制”主要就是表现在传统社会,在那里,个体没有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它必须成为实体的一员才有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实体本身存在的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它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对自然伦理的反思本身就是不道德的,所以在伦理专制的社会,个体的特殊性是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没有个体的特殊性环节,自在的“真实的精神”永远只能是处于浑沌未萌的状态,即“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层次。更为可怕的是,伦理的专制使得个体仅仅具有偶性而已。所以,强调对自在伦理的绝对服从肯定不是教化,因为人在那里是没有自我意识的,这无论如何都是对人性的戕害。从自在的伦理世界中走出并进入自为的道德世界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一种进步,因为个体的自我意识第一次真正觉醒了。一切自在的东西都必须放在理性的考量之中,只有经得起理性普遍性检验的才有存在的合理性,自然性的伦理在科学理性的考量下丧失了其天然的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是说单纯自为的意志就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因为经过理性反思而建构的道德原则或道德规范并不一定是周全的,而且当理性与情感感受处于绝对对立的立场时,道德也就成了“心怀厌恶之感而去做道德之事”了。在个体理性的反思下,“道德”确实获得了普遍性,因为它必须经受住逻辑的不矛盾律,但是,形式的普遍性却也忽视了个体的情感。这样一来,道德原则或道德规范又变成一种没有生命、没有精神的东西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代以来的道德教化总体上说是失败的:一方面,在道德世界观中,只要个体有良好的理性反思能力就必然能够做出合理的行动似的,所以道德教育也仅只是“脖子上的教育”(education for the neck up)。殊不知,“脖子上的教育”只能造就没有“心肝”(heart)的道德知识专家,而无法塑造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灵魂。这里所说的普遍性不是形式上的普遍性,而是一种“品质的普遍性”①詹世友:《道德教化与经济技术时代》,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8页。,即情感、气质的普遍化:个体的情感受到了普遍性价值的型塑,使得个体的情感与理智能够相互渗透乃至化通,从而使个体的生命变得更深厚与灵慧,他能够感他人之所感、想他人之所想,也就是说,能够以宽容、开放、平等的姿态与他人沟通、交往。而现代性的道德教化乃是没有情感的,因为情感在他们看来是无法普遍化和通约的,而作为特殊性表现的情感也只能是无尺度的,所以知与行的分裂乃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没有伦理实体的环境支持,道德就仅仅作为主观性的东西,而这种主观性如何获得普遍性以及客观性本身就是可疑的了。这样一来,道德也只能是以规范的形式出现,而且道德也可以说只是一种惩戒性的规范。所以这也导致现代道德教育只是培养个体机械地遵循规范,而不是把个体的生命提升到一个普遍性的层次,培养一种普遍性的道德人格,使个体在尽义务的同时自然而然就能做到行为合宜、情感合度。最后,“道德的世界观”只不过是一种否定的自由,它所要实现的无限不是在有限的基地上进行扬弃之而实现的,所以它也就根本不考虑人性的有限性以及环境的复杂性,只是为尽义务而尽义务。
正是基于对传统“伦理世界观”与现代“道德世界观”的分析,我们认为必须实现伦理与道德的辩证统一,即倡导一种走向伦理精神的道德教化,也就是说,自然性的、直接性的伦理世界经历自我意识的道德教化而向自身返回,从而实现一种自由性的伦理世界。只有在这样一种伦理世界中,才能实现了意志与其概念的同一。正如黑格尔所说,“伦理是客观精神的完成,是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本身的真理。客观精神的片面性在于,它部分地直接在实在里,因而在外部东西、即事物里,部分地在作为一种抽象普遍东西的善里具有其自由;主观精神的片面性在于,它同样与普遍东西抽象地对立而在其内在的个别性里是自我决定的”①[德]黑格尔:《精神哲学》,杨祖陶译,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9页。。所以,作为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统一的“伦理”既摆脱了自然性伦理的自在性,又摆脱了主观性道德的自为性,从而实现了自在自为的自由。相比较而言,现代性道德教化的最大任务也许并不在于使人摆脱“野人”状态,而在于使人摆脱“蛮人”状态②“野人”和“蛮人”的区分出自席勒。席勒认为,人可以以两种方式使自己处于对立的状态:一种方式是“感觉支配了原则”而成为“野人”,另一种方式是“原则推毁了感觉”而成为“蛮人”。“野人”视自然为他的绝对主宰,而“蛮人”则嘲笑和谤渎自然,他总是成为他奴隶的奴隶。所以在席勒看来,“蛮人”比“野人”更可鄙,因为有教养的人总是把自然当作自己的朋友,尊重自然,只是约束自然任性而已。(可参见[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36页。),因为“蛮人”是无法获得与他人、与社会的内在精神统一的。现代社会是特殊性支配着普遍性,从而以形式的普遍性来确保特殊性的实现。正如黑格尔在分析市民社会阶段时所指出的,具体的人作为特殊的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且特殊性原则只有在普遍性原则中才达到其真理性和现实性,因为市民社会“相需相求”的结构要求个别性的满足以他同时满足其他人的欲望为前提,所以在市民社会中,特殊性是受到普遍性限制的,而且个体也自觉到了这种限制并努力促成普遍性的实现。虽然特殊性原则与普遍性原则是结合在一起了,但这种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并不是“伦理性的同一”,因为它不是作为自由,而是
作为必然性而存在的,因为特殊性若不与普遍性相结合,特殊性是无法实现自身的。由此可见,重建“伦理性的同一”乃是当今道德教化的重中之重。传统共同体已一去不复返,我们现在要做的只能是重构“伦理性的同一”;它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而且精神性的大全只有通过特殊性才能实现自身。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在社会利益高度分化中重建人的心灵的秩序,培养一种人的“品质的普遍性”。这种“品质的普遍性”就不仅是对规范、制度在形式上的遵循,更是秉持一种普遍性的价值觉察和人道情怀,使人能够在一切具体领域的具体活动中实现道德精神和价值内容。
①本文系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道德自我的伦理根基——教化论视野下的现代性道德哲学批判》(编号12YJC720041)阶段性成果。
②肖会舜,哲学博士,绍兴文理学院法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伦理学原理、政治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