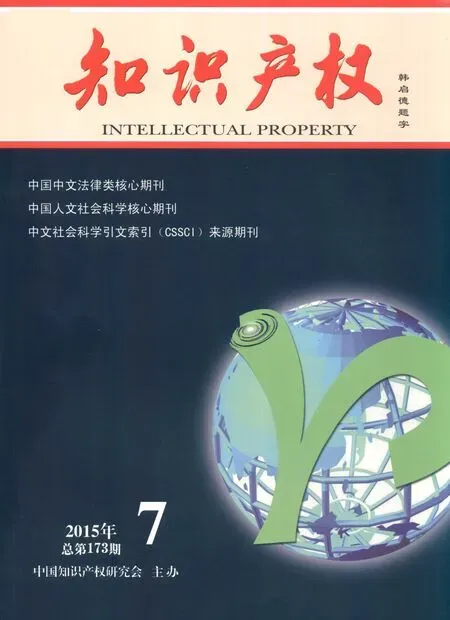服务商标侵权行为的入罪考量
周 洁
服务商标作为商标体系中与商品商标并列的重要标识,其在经济领域和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性不容置疑。近年来,随着家政、餐饮、教育培训、旅游、商品房销售、婚纱摄影等各类服务业的迅猛发展,一些社会认知度较高的服务商标受到假冒和侵权的案件与日俱增,涉案金额和造成的社会危害也引人注目。然而,侵权人除了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或接受行政处罚之外,鲜有因假冒他人注册服务商标而受到刑事追责的。关于服务商标侵权行为的入罪问题以及对我国刑法中商标犯罪法条的理解和认识,在我国一些学者的论著中有所涉及且观点各异。就我国刑法中商标犯罪的立法规定是否涵括了侵犯服务商标权的行为,以《刑法》第213条为例,赞成的学者认为,该条可以适用于严重假冒服务商标的行为①赵秉志著:《侵犯知识产权罪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张明楷著:《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730页;袁博:《假冒服务商标同样可以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载《中华商标》2013年第4期,第41-44页。,否定者则认为假冒服务商标的行为不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②马克昌著:《经济犯罪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2页;杨靖军、鲁统民 :《假冒服务性商标不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载《人民司法》2008年第8期,第56页。。同时,关于严重侵犯服务商标权的行为应否进入刑法规制的视野,学者也存在认识分歧③大部分学者认为,刑法应肯定和明确对服务商标的保护,如田宏杰:《商标的刑法保护还需完善立法》,载《检察日报》2003年7月17日,第3版;陈婵婷:《服务商标应成为商标犯罪的对象》,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11期,第64页。刘宪权、吴允锋著:《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理论与实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6页。赵赤著:《知识产权刑事法保护专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第291-292页。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侵犯服务商标权的行为没有定罪的必要,见霍文良、张天兴:《侵犯商标权犯罪的司法认定》,载《知识产权》2014年第6期,第31页。。为了客观地了解当前我国服务商标侵权的现状,笔者查阅了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ww.court.gov.cn/zgcpwsw/)上公开的近五年服务商标侵权案件的裁判文书,对这些侵权案件的行为类型、侵权人的主观过错、权利人的维权成本、侵权人的赔偿数额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由此展开对严重侵犯服务商标权行为入罪必要性的考察,以期就该问题的争议提供现实层面的考察视角和具体论据的支持。
一、服务商标侵权行为的现实考察
经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近五年来全国各地人民法院做出的服务商标侵权案件的民事裁判文书进行查询、浏览,剔除重复上传的文书和不属于服务商标侵权的裁判文书,从2010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文中分析的服务商标侵权案件裁判文书共94份,其中2010年3份、2011年6份、2012年17份、2013年33份、2014年35份。需要说明几点:第一,虽然有学者坚持认为我国刑法相关条文可以适用于严重侵犯服务商标专用权的案件,但是在现已公布的裁判文书中,没有查阅到与假冒服务商标有关的刑事判决,文中所有的裁判都是服务商标侵权案件的民事裁判文书。有学者在论文中曾提到一个真实的假冒服务商标的刑事案件,检察院以假冒商标罪起诉到法院,但最终被法院驳回。④杨靖军、鲁统民 :《假冒服务性商标不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载《人民司法》2008年第8期,第36-38页。第二,由于各地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的上传是一个动态过程,所以这个数字一直是处于变动中的,文中有关裁判文书查阅的时间截至2014年12月31日。第三,我国裁判文书的网上公开具有一定的随机性,本文假设所有上传的判决和裁定没有经过有关法院刻意的选择和甄别,从而使样本具有说明实践中服务商标侵权行为样态的意义和功能。
通过对近五年间的服务商标侵权案件裁判文书的分析,发现这些侵权案件涉案的服务商标包含了商标局公布的服务商标11个大类的所有领域。从涉案商标的影响力来说,其中有很多是服务行业中的全国知名商标,甚至有一些属于驰名服务商标,如餐饮领域的“海底捞”、商品销售领域的“苏宁”电器、美容美发培训领域的“沙宣”,娱乐领域的“钱柜”,婚纱摄影行业的“维纳斯”,验光配镜领域的“宝岛”眼镜,商品房建筑销售领域的“星河湾”服务商标等。
(一)服务商标侵权行为类型分析
就侵权行为类型而言,这些服务商标侵权案件可以分为如下三类:第一类是企业字号侵犯商标权,即行为人在工商部门登记的企业字号与他人注册的服务商标相同或近似造成侵权,判决样本分析显示:企业字号侵犯商标权的比例2010年为1/3,2011年2/3,2012年10/17,2013年15/33,2014年24/35,五年的平均数为54.6%。这一类侵权行为在服务商标侵权案件中比例最高,这与服务业的经营方式有关。第二类是商标标识使用侵权,即行为人在使用自己已经注册的服务商标或经授权使用他人注册服务商标的过程中,超出自己注册商标核定的使用范围或者以拆分、组合等方式改变自己有权使用商标的显著特征,足以造成与他人注册服务商标的混淆和误认,因而侵权⑤如2011年,好又多咨询服务公司与四川阆中生活超市有限公司侵犯商标权一案,2014年方某某与浙江千岛湖鱼味馆有限公司、淳安县千岛湖金刚刺酒厂侵犯商标权一案,和2014年吉某某与浦某某、青岛客必思味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第三类是其他形式的侵权,在分析的侵权案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近几年出现的楼盘名称侵犯他人服务商标权的类型⑥公开的判决显示,从2012年开始,陆续出现了房地产企业在其建设的楼盘上使用他人注册服务商标相同的名称而侵权的案件,其中2012年有3起,2013年有2起,2014年有3起。。以上所有这些侵权行为类型的具体表现,既有较为常见的在服务场所、服务招牌、服务工具、服务人员的服饰和生产的商品上使用与他人相同或近似的服务商标,也有在广告宣传中使用与他人相同或近似的服务商标,如在广告、网络宣传、推广(如在百度搜索⑦如2014年上海等势线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首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被告在百度客户推广中,使用“ETW”、“ETW国际”和“ETVV”字样,判决认定被告主观上具有借用原告的信息和声誉提高其网站点击率的故意,客观上也确实会使原本想访问原告网站的潜在客户却被误导访问被告网站,增强了被告在同行业中的竞争力。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ww.court.gov.cn/zgcpwsw/sh/shsdyzjrmfy/shspdxqrmfy/zscq/201406/t20140601_1310265.htm,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12月25日。)中使用与他人服务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识造成对他人注册服务商标的侵权。
(二)服务商标侵权行为主体的主观过错分析
通过对近五年来服务商标侵权案件的分析,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可以分为如下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行为人客观上对他人的在先权利不知情,主观上不存在故意,或者主观故意难以证明。以字号侵权为例,在我国,由于企业名称登记管理与商标审核体系和标准的差异,以及企业与服务业经营场所的地域性,登记在后的企业经营者可能出现其企业字号与他人服务商标的雷同,然而,企业经营者在企业名称登记之初及使用企业字号的过程中也许并不存在侵犯他人商标权的故意,如果服务商标权人也不能证明其注册商标的宣传和知名度已经辐射到了侵权人企业开展业务的地域范围内,即很难查明行为人对他人注册商标权存在主观上的明知和应知,因而认定行为人不存在侵权的故意。⑧如在兰某与罗某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的(2013)成初字第1862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就从原被告双方经营所处的地域、原告对商标的宣传力度和知名度,以及双方之前互不认识,认定被告不存在攀附诉争注册商标商誉的故意。http://www.court.gov.cn/zgcpwsw/sc/scscdszjrmfy/ms/201404/t20140415_771015.htm,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12月28日。第二种情形,行为人对他人的在先权利存在明知和仿冒的故意,在进行企业字号登记或者相关服务业的宣传和经营中,故意选用了与同行业较为知名的服务商标相同或相似的商标。这里的“故意”包含对他人注册服务商标的“明知”和“推定其知道”。在近五年的服务商标侵权案件中,判决书认定行为人对侵权行为存在明显主观过错所占的比例为:2010年1/3、2011年1/2,2012年2/17、2013年8/33、2014年16/35,五年的平均数为31.9%。在查阅的案件中,“明知”比较典型的表现为,行为人与商标权人先洽谈后侵权或先合作后侵权⑨如2011年温州鹿城区小荧星艺术业余学校与永嘉县瓯北镇小荧星艺术学校商标侵权案,2013年兰某某与杭州小拇指汽车维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小拇指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天津市华商汽车进口配件公司不正当竞争、垄断纠纷案,2014年上海爱迪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昆山爱贝英语培训中心侵害商标权纠纷案,被告均是在加盟合作协议终止后,未经商标权人授权和同意,故意申请使用与他人注册服务商标相同的字号进行企业名称工商登记造成相关社会公众在选择服务时发生认识上的混淆,故意侵犯原告的商标权。,以及对知名服务商标的假冒,行为人的主观“明知”一般可以通过推断得以证明。为了认定侵权人的主观过错,人民法院在一些判决中对于应知的推断也有很详细充分的论证⑩详见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闵民终字第1133号 厦门苏宁公司与苏宁云商公司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http://www.court.gov.cn/zgcpwsw/fj/ms/201401/t20140101_189296.htm,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12月28日。。
(三)服务商标侵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考察
《TRIPS协定》第61条明确要求“成员方至少应当对具有商业规模的故意假冒商标或者盗版,提供刑事程序与刑罚予以惩处。可采取的刑事处罚应当包括监禁或者罚金,足以起到威慑作用,并保持与此相似罪行所处刑罚一致。”其中的“商业规模(commercial scale)就是指以营利为目的并达到一定规模”。[11]刘科:《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61 条之“商业规模”》,载《刑法论丛》2010 年第4 卷,第252页。
从服务商标侵权案件的分析看到,以营利为目的商业规模化和公开化是其尤为突出的特征。在服务商标侵权案件中,许多假冒服务商标的行为人采用了公司化或者企业的经营模式,具有一定的注册资本、专门的服务营业场所、成套的服务设施、明确的服务招牌,他们往往直接打着假冒的商标招牌,通过长时间的公开宣传、营业、提供服务、销售服务产品、招揽服务对象、树立商业品牌、获取违法经营收益[12]如2011年的一起教育培训侵权案件中,侵权人经营的学校规模很大,拥有三个校区,开设了多种班级、科目,拥有30余名专业、专职教师。其他如对阿瓦山寨、海底捞、维纳斯摄影、苏宁电器、星河湾等服务商标的侵权行为,行为人的经营规模也都十分可观。,这也是服务商标侵权与商品商标侵权的显著区别所在。正如有学者所言:“服务商标无法像商品商标那样直接将商标缀附于商品或者服务本身,而是要通过广告、招牌等方式使用商标,因此假冒服务商标行为的公开性更强。”[13]霍文良、张天兴:《侵犯商标权犯罪的司法认定》,载《知识产权》2014年第6期,第31页。根据《TRIPS协定》的精神,对于这些蓄意假冒他人服务商标,侵权行为持续时间较长,且获利数额较大,已经达到了规模化经营的侵权行为,即应予入罪,给予相应的刑事处罚。但有论者主张,因为服务商标侵权行为的公开性,所以“不管是被侵犯商标权的受害人,还是执法者,都容易及时发现、及时处理;不管是证据的收集还是查处、打击都更容易实现。因此其他法律能够解决的问题,刑法则保持谦抑”。[14]同注释[13] 。本文对此不能认同。服务业的经营往往开始于特定地域,然后随着服务商标的授权或商业加盟发展到其他地域。服务商标的权利人并不能很容易地发现全国其他地域的侵权行为,等其发现时,往往侵权行为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因此,本文以为,相较于相对隐蔽的商品商标侵权行为,对于这种公开化、规模化地恶意侵犯他人服务商标权的行为,体现了行为本身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较明显的主观过错,因此,更有运用刑法定罪处罚的必要。
尽管受我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开制度实施时间较短因素的制约,各地各级人民法院公开的案件往往新近裁判文书多于以往裁判文书,但是从2010年到2014年底,服务商标维权民事诉讼案件数量逐年递增,甚至翻倍增加的信息,还是可以说明我国实务中服务商标侵权案件的基本趋势。而在近五年来公布的判决中,与“海底捞”餐饮服务商标有关的侵权诉讼有3起,分布在安徽、内蒙古和广西三地,广州星河湾实业发展公司提起的维权诉讼有6起,涉及四川、浙江、江苏、福建、河北五省(发生在河北省的有两起)。“商标权相关法律的立法目的首先是确保消费者能够根据商标识别功能选择商品或服务;其次是保护经营者因投资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而获得的良好商业信誉,防止经营者付出的努力因他人的假冒和仿冒行为而无法获得经济回报,以此维持正常的商业竞争秩序,鼓励经营者努力改进产品质量和提高服务水平。”[15]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就北京蓝图伟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杜冠平、北京同学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盛大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安徽商报社不正当竞争纠纷做出的(2013)东民初字第00030号民事判决书中的表述。http://www.court.gov.cn/zgcpwsw/bj/bjsdezjrmfy/bjsdcqrmfy/zscq/201406/t20140617_1500875.htm,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12月20日。毫无疑问,服务商标侵权行为既侵害了商标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也严重侵害了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利益。导致消费者支付了相应的报酬,却未能获得自己意欲获得的服务,其行为足以扰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犯罪行为不同于侵权和违约行为,因为刑法涉及公法。”当一个侵权行为使具体的被害人的利益受损,而且也使社会受到了伤害,包括“对社会公众权利的侵害和对社会责任的违反,这里所指的社会是一个有着社会凝聚力的整体和共同体”[16][美]约书亚·德雷斯勒著:《美国刑法精解》,王秀梅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那么这一行为就有被作为犯罪规定的必要。
二、服务商标侵权行为的规范考察
考察行为人侵权的经营规模、违法经营数额或违法所得数额以及其他情节严重的表现就是认定侵权行为社会危害程度的一个重要量化标准,也是决定对于行为人采取何种责任追究方式的重要依据。
(一)服务商标侵权行为的规范依据
通过对近五年来服务商标侵权案件裁判文书的样本分析,看到目前我国服务商标侵权案件的实际情形为发生领域广、行为多样,且存在近三成主观故意明显的侵权案件。就这些侵权案件的规范依据而言,首先,我国《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商标管理条例》中都有对服务商标保护准用商品商标的原则性规定和禁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具体规定;其次,在具体侵权事实的认定和赔偿数额的裁判中,适用较多的是最高司法机关出台的一些司法解释和国家商标局等部门颁布的一些部门规章。再次,就我国刑法的立法规定来看,现行刑法中有关商标犯罪的立法规定都采用了“商标”的统一表述,没有特意明确但也没有区别对服务商标与商品商标保护的不同,应该认为也是坚持了与其他立法一致的对服务商标保护准用商品商标的相同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查院于2004年和2007年先后发布的两个《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文简称两高《解释》)中有对认定商标犯罪的有关规定,既未特意明示排除对服务商标的保护,也没有对服务商标犯罪的认定做出特别的规定。与刑法立法的不明朗相关,实务中将严重侵犯服务商标权的行为完全排除在定罪量刑之外,最终造成了对服务商标刑法保护事实上的缺位。这使得那些侵权行为中主观恶性大、情节严重、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服务商标侵权行为有升格入罪的必要,却面临无法可依和法律规定不明确,实务部门不予入罪的尴尬。目前以民事制裁为主、行政处罚为辅,但刑事追责缺失的规范治理模式,造成了事实上对服务商标保护与商品商标保护上区别对待的局面。
(二)服务商标侵权行为规范体系检视
在近五年的服务商标侵权案件中,从已公开裁判的总体分析来看,商标权人主张的赔偿数额与判决实际支持的赔偿额往往相差悬殊,而侵权案件屡禁不绝、此伏彼起。如四川海底捞餐饮公司于2012年和2013年相继提起和获得赔偿的三起诉讼中,主张的赔偿额和最终获赔额的情况分别为:20万元比6.7万余元,10万元比2.5万元,和10万元比1.5万元。其他类似判决如阿瓦山寨商标案件中50万元比8万元,成都维纳斯婚纱摄影案件中44万元比13万元,广州星河湾实业公司的商标侵权诉讼中25万元比5万元。这些侵权案件,因为被告多是异地侵权,原告须赶赴异地取证、公正、起诉、参加庭审,往往需要支出巨额的律师费、差旅费和诉讼费用,而被告的侵权时间有的持续数月半年,有的则有三四年之久,非法获利丰厚,但是法院判决最终支持的全部侵权赔偿数额都与原告的诉求相差甚远,既没有满足弥补损失的需要,更未达到惩罚性赔偿的效果。虽然在商标权人追究侵权人民事赔偿责任的同时,也可以请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侵权人给予行政处罚,但是由于对相关案件行政处罚的情况无法同时获得具体的数据信息,对此,这里不予评论。需要强调的是,权利人到处起诉、打假,但是侵权行为仍屡屡发生,屡打不绝。商标权利人自顾不暇、入不敷出,由此凸显了单纯通过追究商标侵权人的民事责任和现有的行政处罚不足以遏制和震慑此类违法行为。逐年递增的服务商标侵权案件数量和不断拓展的侵权行为领域都在说明服务商标侵权行为的频发和严重性,虽然我国目前存在相应的民事追责和行政处罚救济措施,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刑法介入的必要性。而且在《商标法》等法律反复强调和重申我国的商标包含服务商标和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准用商品商标的立法规定,在严重侵犯商品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可以成立犯罪并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前提下,就没有理由对于同样遭受假冒和仿造的服务商标不给予刑法上的同等保护。
我国于2013年修订后颁布实施的《商标法》第63条对商标侵权赔偿数额的计算方式重新做了规定,增加了责令侵权人提供与侵权有关的账簿、资料的规定,吸收了司法解释中参照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的计算方法,引入了1-3倍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并且将法定赔偿额的上限从原来的50万元提高到了300万元。《商标法》关于赔偿数额的这些变化从侧面说明了国家对于商标权保护力度的加强。但是基于法律的一致性和刑法的最后保障性和严厉性,在强化《商标法》对服务商标保护力度的同时,刑法也应对服务商标的保护有所明确,以构筑权利保障的最后堤坝,防范和惩戒严重的服务商标侵权犯罪行为。
三、服务商标侵权行为入罪的刑法考察
根据对实践中服务商标侵权案件行为类型、主观过错、社会危害性以及目前规范治理效果的考察,对于行为人在经营过程中故意侵犯他人注册服务商标权的行为,包括字号侵权、商标侵权以及使用侵权等假冒他人服务商标的行为,生产假冒服务商标商品的行为以及伪造、擅自制造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他人服务商标标识的行为,结合我国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对相关商标犯罪规定的入罪条件,对于其中情节严重,达到法定追诉标准的,即应予入罪。
(一)假冒服务商标行为的客观入罪条件
服务商标犯罪的行为方式,包括假冒注册服务商标的行为、销售假冒注册服务商标商品的行为和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行为这三种侵犯服务商标专用权的行为。这些行为方式的共性在于其会引起消费者对服务或商品提供者的混淆和误认,消除或模糊服务商标应有的明确标示服务来源的意义。我国现行《商标法》也已经将混淆理论作为判断商标侵权的标准规定了下来。打击假冒服务商标的犯罪,其旨在明确服务商标不得假冒、仿造使用的法律观念,保护商标权人的商标财产权,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为服务品牌的创立与发展提供稳定安全的法律保障。因此,客观上假冒服务商标的行为与假冒商品商标的行为一样,都必须达到足以误导消费者混淆服务或商品来源的程度。
假冒服务商标行为的客观入罪条件,除了具备行为特征之外,还需达到情节严重的入罪标准。根据两高《解释》中规定的商标侵权案件的追诉标准,在近五年的侵权判决中,认定行为人构成侵权,且存在侵权故意,赔偿数额在3万元以上的案件数从2010年到2014年的五年中分别为:1件、3件、4件、6件和12件,约为五年全部案件数的27.7%。对这部分恶意侵犯他人服务商标权,其行为足以达到他人对服务来源的混淆和误认,且情节严重的,即应依法入罪。
(二)假冒服务商标行为的主观入罪条件
我国刑法不仅在总则中规定了抽象的犯罪故意与过失,而且在分则大多数的具体犯罪罪状的描述中也明确规定了犯罪成立的主观要件,对于分则没有明确犯罪主观方面要件,尤其没有明确规定过失实施某一行为构成犯罪的,根据总则对过失犯罪的原则性规定,那么构成该罪就要求具备主观上的故意。我国《刑法》分则对于商标犯罪在第213条和215条的罪状描述中没有明确规定其主观要件,对此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构成假冒商标罪应该具有主观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17]刘宪权、吴允峰著:《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理论与实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页;赵国玲著:《知识产权犯罪调查与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本文也倾向于认为,既然法条没有明确过失可以构成这些犯罪,那么行为人过失实施了侵犯他人注册服务商标权行为的,应该不成立犯罪。
对于假冒服务商标犯罪的行为人主观故意“明知”和“推定其知道”的认定应结合具体案件情形掌握。所谓明知,即行为人认可或有证据显示行为人对他人的在先商标权有认知,如前面对服务商标侵权行为主观过错的分析中所列举的,行为人曾经与商标权人有过加盟谈判最终未果,或者双方有过一定时期的合作,合作期满后在相同或类似服务上未经对方授权和同意,使用与对方相同或近似商标中的文字作为企业名称,或实施其他假冒他人注册服务商标的行为。除了明知,还有“推定其知道”,即“应知”,但其意义不在于强调行为人有主观上的注意义务,而是“对于行为人知道状态的一种推断,是推定行为人知道,其法律效果与行为人明确知道并无区别,是根据一般社会常识推定其应该知道”。[18]皮勇、黄琰:《论刑法中的“应当知道”——兼论刑法边界的扩张》,载《法学评论》2012年第1期,第54页。对于侵犯商标权犯罪的行为人,可以适用“推定其知道”,依据是行为人对于涉案的商标有特殊的认知。因为作为从事某一服务行业的行为人,往往会由于商标权人对自己商标的宣传以及侵权人自己业务经营关系和关注程度而对该行业内已有的一些服务商标,尤其是其中一些社会声誉较好、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商标是知道的,这是“推定”赖以存在的基础;然后在此基础上,推定其未经商标所有人的授权和同意,使用与他人注册的服务商标相同商标的行为具有主观上的故意和恶意。得出这一推定结论必须要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根据近五年服务商标侵权案件裁判文书样本的分析,有近三成判决认定侵权行为人存在主观上的“明知”或“推定其知道”而故意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这些行为已经具备入罪的主观条件。
(三)服务商标侵权行为相关罪名考察
我国《刑法》中有三个有关商标犯罪的法条,即第213条假冒注册商标罪,第214条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和第215条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其中第213条明确规定,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商标的行为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商标”显然可以包含商品商标和服务商标,但是“商品”不能包含服务,因此有必要对该条做扩展和明确,以适用于未经商标所有权人的许可,在同种商品或服务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商标,情节严重的行为,这样就可以使该条较好地同时适用于假冒商品商标的行为和假冒服务商标的行为。《刑法》第215条则因为没有限定于商品商标,因此不需要做任何修改和明确就可以直接适用于法条所述相关侵犯服务商标的行为。
服务商标进入我国《商标法》保护视野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而服务业各门类发展的强劲势头和市场竞争的需要使得服务业经营者越来越重视服务商标的注册和保护,同时服务业竞争中服务商标侵权行为的频发也客观上需要法律对服务商标给予更为充分和有效的保护。服务商标侵权行为造成的危害并不比商品商标低,从侵权行为的商业规模化、经营方式的公开化和造成的社会危害的角度分析,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当依赖刑法以外的其他手段不足以遏制、防范和惩戒严重的服务商标侵权行为时,即有必要动用作为后盾法的刑法来维护和保障与服务商标有关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