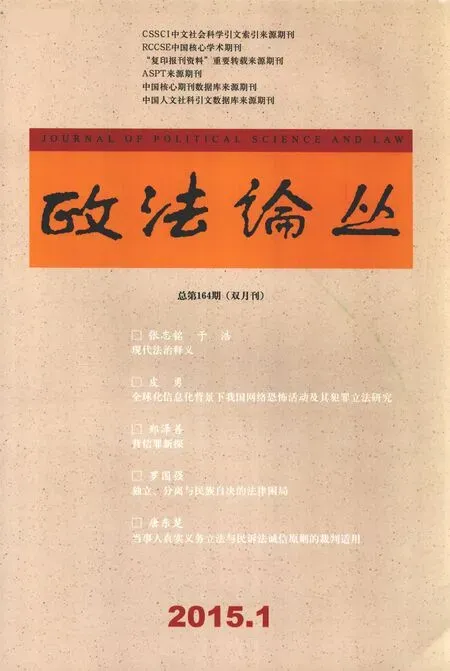我国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规则适用之实践观察与反思*
张海燕
(山东大学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我国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规则适用之实践观察与反思*
张海燕
(山东大学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我国《婚姻法解释(三)》首次规定亲子关系诉讼中的推定规则,该规定结束了长期以来各界关于能否适用推定认定亲子关系的争论,将亲子关系诉讼中的事实推定上升为法律推定。然而,观察三年来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规则的适用状况,发现裁判者对其适用范围、适用条件以及原告范围等问题理解不同,导致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现象频现。对此,既要在理论层面使裁判者明确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的逻辑结构和法律效果,正确处理推定与亲子鉴定在亲子关系认定问题上的适用关系并合理配置双方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义务;又要在民事立法层面建构完善的亲子关系推定及强制认领制度,保障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规则的有效实施。
亲子关系诉讼 推定 亲子鉴定 原告范围
我国2011年8月13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下称《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明确规定了亲子关系诉讼①[1]P216中的推定规则,其内容是“夫妻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并已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一方的主张成立。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该规定结束了我国长期以来学界和实务界关于能否适用推定认定亲子关系问题的争论,将亲子关系诉讼中裁判者所适用的事实推定上升为法律推定,为裁判者的司法裁判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对于实现亲子关系诉讼的高效化和裁判者认定事实的统一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通过对我国《婚姻法解释(三)》施行三年来亲子关系诉讼中裁判者运用推定规则做出裁判的案例②进行分析,笔者发现裁判者在适用推定规则时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导致实务中同案不同判现象频繁出现。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实践中反映出来的问题进行反思,分析制约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规则实效发挥的具体因素,寻求可能的解决举措,以期能够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予以完善。
一、检视我国亲子关系诉讼中适用推定规则存在的问题
我国法院在亲子关系诉讼中适用推定规则认定亲子关系是否存在这一待证事实的三年时间里,笔者发现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一)因对亲子鉴定程序启动条件把握不同而导致推定规则适用范围不同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通过DNA亲子鉴定否定亲子关系的比率几近100%,确认亲子关系的比率也达到99%左右。[2]P54因此,在涉及判断是否存在亲子关系的诉讼中,不论当事人还是裁判者都很倚重DNA亲子鉴定,尤其是裁判者,其更希望能够获得程序合法的DNA亲子鉴定意见,以实现最大程度上正确认定亲子关系是否存在这一待证事实之目的。然而,司法实践却告诉我们,很多情形下,亲子关系诉讼中的一方当事人会基于各种理由拒绝进行亲子鉴定。此时,为保障人权,多数国家和地区禁止对拒绝亲子鉴定的一方当事人进行强制性鉴定,[3]但裁判者又必须对当事人诉请的亲子关系是否存在这一事实进行认定。于是,推定便成为各国裁判者认定亲子关系是否存在的一种重要手段,其表现形式可能是法律推定也可能是事实推定。
在民事诉讼中,关于待证事实的认定,通常存在两种行之有效的方式:一种是通过适格证据进行证明,另一种是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进行推定。对于亲子关系是否存在这一待证事实而言,这两种方式具体表现为通过进行亲子鉴定获得鉴定意见这一直接证据来认定以及通过法律推定或事实推定来认定亲子关系是否存在。那么,这两种方式之间的关系如何?我国司法实务中的适用情况又是如何?笔者通过对《婚姻法解释(三)》施行三年来我国法院在亲子关系诉讼中适用推定规则的10个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实务中关于亲子鉴定和推定的适用关系非常明确,即首先应当寻求并依靠亲子鉴定意见来证明亲子关系是否存在,在亲子鉴定意见缺位的情形下,才考虑适用推定规则来认定待证事实。当然,这一点也可以从《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的“另一方拒绝做亲子鉴定”是适用推定的一个条件的规定上得出。然而,不同法院对于亲子鉴定程序启动条件把握的宽严程度却不尽相同,有的法院采行较为严格的标准,认为亲子鉴定程序的启动必须经双方当事人同意且必须由鉴定人当面提取鉴定样本,一方当事人单独进行的亲子鉴定所获得的鉴定意见不具证据资格;有的法院则采行较为宽松的标准,承认一方当事人单独进行的亲子鉴定所获得的鉴定意见具有证据资格,除非对方当事人能够提出有效反驳。法院对于亲子鉴定程序启动条件把握的宽严程度不一,必然会影响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适用的范围大小,两者作为裁判者认定亲子关系是否存在这一待证事实的不同手段,在适用范围和作用大小上具有此消彼长的内在紧张关系。
(二)对于亲子关系诉讼中适用推定时原告应提供的“必要证据”理解不同
《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规定亲子关系推定适用的一个条件是原告须提供“必要证据”。至于何为“必要证据”?最高人民法院未做明确界定,故司法实务中就出现了裁判者对于“必要证据”标准的不同理解,表现在结果上就可能会出现上下两级法院对于同一案件的不同裁判。[4]比如,《人民法院报》曾刊登过这样一个案例:1995年,苏明琪、李晓明在江苏南通相识并成为朋友。2000~2001年,苏明琪在南通仍与李晓明有交往。苏明琪与李晓明未有婚姻关系。2001年,苏明琪在南京产子,李晓明未在场。2001年7月19日,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出具《出生医学证明》,载明新生儿苏的母亲姓名苏明琪及其身份证号,父亲姓名李晓明及其身份证号。李晓明得知苏明琪生子后,曾托人带1,000元现金给苏明琪。从孩子出生至今,李晓明未支付过抚养费。2011年7月,苏明琪以李晓明对苏不履行生父责任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孩子苏系苏明琪与李晓明的亲生子;2.确认苏明琪抚养苏;3.李晓明每月支付抚养费500元。诉讼中,苏明琪提出亲子鉴定申请,李晓明拒绝,鉴定未能进行。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原告提供的《出生医学证明》系单方办理且未得到被告的认同,故认定原告未能提供必要证据证明被告与苏之间存在亲子关系,故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到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该法院审理认为,上诉人提供的其与被上诉人关系亲密的证据、其子的《出生医学证明》等证据已经符合了提供必要证据的要求,判决撤销原判,支持了其诉讼请求。③可见,“必要证据”的确定是决定能否在亲子关系诉讼中适用推定的第一道门槛。但实务中界定“必要证据”标准的缺位势必导致裁判者在程度不同的心证状态支配下做出结果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对于证据证明力的评价。
(三)对于亲子关系诉讼中原告范围的理解不同
《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规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诉讼的原告为夫妻一方,而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存在诉讼的原告则为当事人一方,未明确列出原告的具体范围。观察并分析我国司法实务,需要确定亲子关系是否存在这一事实的民事诉讼案件类型主要有离婚纠纷、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抚养费纠纷和确认亲子关系纠纷四种类型。④下文笔者将区分两类亲子关系诉讼来观察其原告范围情况。第一,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的诉讼。涉及该类诉讼的案件类型主要有离婚纠纷和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在这两类案件中,原告是夫妻一方或具有同居关系的男女一方,但根据《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其原告只能是夫妻一方。由此,实务中便表现出了理解和适用上的不同:有些法院严格依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只允许夫妻一方提起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的诉讼,有些法院则相对比较宽松,也允许具有同居关系的男女一方提起此类诉讼。此外,实践中还存在一种情形,即夫妻或同居关系以外的其他第三人提出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的诉讼,比如,所涉子女或生父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的诉讼,再如,因涉及继承或房屋拆迁补偿等因素,夫妻、子女或生父以外的其他利害关系人请求确认特定主体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的诉讼。对此,不同法院做法亦不相同。第二,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存在的诉讼。涉及该类诉讼的案件类型主要有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抚养费纠纷和确认亲子关系纠纷。《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仅规定此类诉讼的原告是当事人一方,未明确规定其具体范围,导致实务中法院的做法五花八门,有法院认为仅指所涉子女,若是未成年子女,则生母或其他监护人为其法定诉讼代理人;有法院认为包括所涉子女以及生父和生母;还有法院采取更为宽泛的做法,除所涉子女、生父生母外,还包括其他第三人,比如该子女除生父生母以外的其他监护人或者继承或房屋拆迁补偿情形下的其他利害关系人。
前述法院对于亲子关系诉讼中原告范围的不同理解,表现在实务中便是不同法院掌握的亲子关系诉讼的门槛高低不一,相关主体开启法院大门的难易程度也不尽相同,其结果必然会出现宏观视角下同案不同判的司法混乱状态。之所以会产生如此窘境,直接原因是前述《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关于原告范围或者过窄或者语焉不详的不科学规定,但本质原因却是实体法关于亲子关系诉讼中适用推定所需配套制度的缺位,这便使科学设定原告范围问题成为一部司法解释所不能承受之重!
二、正确解读亲子关系诉讼中的推定规则
(一)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的法律属性
亲子关系诉讼中的推定是推定体系中的一种类型。根据关于推定分类的传统观点,推定被区分为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在我国,亲子关系诉讼所适用的推定长期以来处于事实推定的层面,《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的出台标志着其上升到法律推定层面。不论法律推定还是事实推定,其本质都是裁判者在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情形下认定事实的一种方法。亲子关系诉讼中的推定亦是如此,其是裁判者在缺乏适格证据证明亲子关系存在或者不存在的情形下认定事实的一种有效途径。推定被创设的理由具有多元化,是立法者或司法者出于对概率、政策、经验、公平、逻辑和便利等因素的单一或综合考量,其目的在于实现某项社会政策或者保护某种社会利益。[5]因为并非所有推定均建基于概率之上,故并非所有推定均可被反驳,特定情形下存在不可反驳的推定。不可反驳的推定主要存在于婚姻家庭、劳动雇佣和证券交易等领域。[6]比如,美国1965年《加利福尼亚证据法典》第621条关于婚生子女推定的规定,其内容为“不论其他法律规定如何,妻子与丈夫同居所生的子女,只要该丈夫具有性能力且能生育,则该子女被结论性地推定为婚生子女”。⑤如同婚生子女推定,亲子关系诉讼中的推定也具有很强的社会政策方面的色彩,任何国家和地区关于其内容的规定均能体现和彰显其所欲推行的某项社会政策或所欲重点保护的某种社会利益。在我国,《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规定的亲子关系诉讼中的推定在性质上是一种可以反驳的法律推定,其被创设主要建基于两个因素:一是逻辑关系上的高概率,二是保护相关利害关系人获悉亲子关系是否存在这一血统真相的权利。
(二)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的逻辑结构
推定是指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断出另一事实的一种制度。无论法律推定还是事实推定,其内在逻辑结构均包括三部分:小前提(基础事实)、大前提(法律规范或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和结论(推定事实)。我国亲子关系诉讼中的推定在性质上是一种法律推定,其应当符合推定的内在逻辑结构和运行规律,是一个裁判者从基础事实推断出推定事实的过程。在亲子关系诉讼所适用推定的逻辑结构中,推定事实的判断非常简单,指的是亲子关系的存在或者不存在;然而,其基础事实是什么呢?从《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的内容表述来看,人们容易产生这样一种认识,即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的适用需要具备原告已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且又拒绝做亲子鉴定这样三个前提条件。笔者认为,如果仅从条文语义来看,该认识具有一定道理。但如果将这三个前提条件认为是亲子关系诉讼中所适用推定的基础事实,那么,这种认识就有失偏颇甚至是错误的。
一般来说,推定的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主从关系和互不相容三种关系。[7]P495在亲子关系诉讼所适用的推定中,其基础事实是指与亲子关系存在或者不存在这一推定事实存在因果关系、主从关系或者不相容关系的一个(或一组)事实。具体而言,对于亲子关系不存在这一推定事实,能够从逻辑上得此推断的基础事实有女方受孕期间男方未与女方发生性关系(比如男方出差在外)或者男方无生育能力或者女方受孕期间与丈夫(或同居男友)之外的其他男性发生过性关系等事实。对于亲子关系存在这一推定事实,其基础事实可能有女方受孕期间与男方发生过性关系或者男方与所涉子女具有密切关系等事实。可见,前述《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规定的三个条件并非亲子关系诉讼所适用推定逻辑结构中的基础事实,最多可以在字面意义上将其认为是裁判者最终适用推定的前提条件。裁判者只能根据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的基础事实,才可以进行《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规定的亲子关系存在或者不存在的推定。至此可以得出,我国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的逻辑结构为:大前提是《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的规定,小前提是女方受孕期间男方没有或不能与女方发生性关系或者女方受孕期间曾与男方发生性关系的基础事实,结论是亲子关系存在或者不存在这一推定事实。在该逻辑结构中,核心问题是基础事实的确定。对此,我国目前规范性法律文件未做明确规定,如何判断,仍属裁判者自由裁量之范畴。
(三)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的法律效果
推定是裁判者在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情形下认定事实的一种有效方法,其在客观上减缓了对待证事实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的证明负担,改变了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程序性权利义务配置并进而在最终意义上改变了当事人之间实体性权利义务的分配。推定的法律效果是推定适用后所引起的双方当事人程序层面权利义务的变动,亲子关系诉讼中适用推定规则的法律效果便是亲子关系诉讼中因适用推定引发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程序性权利义务的变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亲子关系诉讼中的推定通过改变原告的证明对象减缓而非免除了其证明负担。从逻辑结构观之,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的适用首先改变了原告的证明对象,使原告从对于亲子关系存在或者不存在这一事实的证明改变为对于能够推断出亲子关系存在或者不存在的基础事实的证明。在具体的亲子关系诉讼中,亲子关系存在或者不存在是较为抽象、难以证明的事实,相比较而言,女方受孕期间是否与男方发生性关系这一基础事实则更为具体、更易证明。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的适用便是将原告本应对抽象的、证明难度较大的亲子关系是否存在的证明负担转变为对于更为具体的、证明难度较小的女方受孕期间是否与男方发生性关系这一基础事实的证明。证明对象的改变只是减缓而非免除了原告的证明负担,原告仍需对基础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基于此,我国《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规定的“原告已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的语言表述中,原告提供必要证据所指向的证明对象应当是指能够推断出亲子关系存在或者不存在的基础事实,而非亲子关系存在或者不存在这一推定事实本身。
第二,亲子关系诉讼中的推定赋予被告对于推定事实的反驳权。基于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均衡配置的考量,推定的适用在大大减缓原告证明负担的同时,也应赋予被告相应的对抗性权利,以防止因对原告程序性权利的过分倾斜而导致当事人之间实体利益的反向失衡。又因推定多以高概率作为其创设基础,故各国一般会赋予被告对于推定事实的程序反驳权,允许被告可以通过提出相反证据来推翻推定事实。若推定事实被推翻,则推定的适用便被阻止,原告需要重新对待证事实进行举证,否则,将承担不利后果。我国《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规定的亲子关系诉讼中适用推定需要“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这一内容实际上表明了两层意思:一是我国亲子关系诉讼中的推定是可以被反驳的,二是被告可以通过提出相反证据来对亲子关系是否存在这一推定事实进行反驳。换言之,在亲子关系诉讼中适用推定规则时,与原告被大大减缓证明负担相对应,被告也被赋予一种通过提出相反证据反驳推定事实的程序性权利。至于被告可以通过提出哪些相反证据来行使其反驳权,笔者下文将予详述。
三、完善我国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规则的具体思路
(一)明确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适用的前提条件是亲子鉴定的缺位
如前所述,在亲子关系诉讼中,裁判者对于是否存在亲子关系这一待证事实的认定,主要有通过亲子鉴定意见进行证明和适用推定(法律推定或者事实推定)两种方法。我国《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明确规定了亲子关系的法律推定规则,故实务中在通过推定认定亲子关系是否存在时适用的便仅是法律推定。笔者在本文第一部分曾指出亲子鉴定意见对于亲子关系是否存在这一待证事实而言,具有很强的证明力。一般情况下,其能够使裁判者直接形成关于亲子关系存在或者不存在的内心确信。故该方法是裁判者认定待证事实的首选方法,也是保证裁判者所做裁判最具正当性的一种事实认定方法。然而,该方法的适用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那便是必须获得适格的亲子鉴定意见这一直接证据。亲子鉴定意见作为鉴定意见的一种,其成为适格证据的核心是亲子鉴定程序的启动需要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之规定,鉴定程序的启动方式有双方当事人协商、法院指定和委托鉴定三种。前两种发生在当事人申请鉴定的情形下,而委托鉴定则发生在当事人未申请鉴定时。关于鉴定程序的启动是否必须取得双方当事人同意,民事诉讼法未设明文,我们只能从鉴定程序的三种启动方式中进行推测。在当事人申请鉴定的情形下,当事人协商确定鉴定人的言外之意是双方当事人都同意进行鉴定,法院指定鉴定的前提是当事人双方协商不成,即双方协商了但未达成一致意见,此时,我们可以双方当事人在同意进行鉴定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只是未能在选择由谁做鉴定人这一问题上取得共识。在当事人未申请鉴定的情形下,法院可以在必要时依职权主动委托鉴定,此时鉴定程序的启动与当事人同意无涉。可见,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之规定,鉴定程序的启动是否须取得当事人同意需根据具体情况分析,无法简单说是或者不是。
亲子鉴定涉及亲子关系是否存在这一事实的确定,其欲确定的对象具有很强的道德伦理色彩,还涉及被鉴定人的隐私和尊严等人格权方面的内容,具有不同于一般鉴定的特点。鉴于此,世界各国和地区大多采取禁止直接强制的方式获取不同意鉴定一方当事人的检材进行亲子鉴定。[8]P60我国亦是如此。亲子鉴定程序的启动应取得相关主体(被鉴定人或其监护人)的同意,如果相关主体不同意,则不能强制启动亲子鉴定程序,否则通过强制亲子鉴定程序所获得的亲子鉴定意见会因不具合法性而被非法证据排除。正是在此意义上,我国《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规定了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适用的一个前提是“另一方拒绝亲子鉴定”,该规定意蕴有二:一是不能直接强制当事人进行亲子鉴定,亲子鉴定的进行须征得被鉴定一方当事人(或其监护人)的同意;二是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适用的前提是待证事实不能通过亲子鉴定意见进行证明,亲子关系是否存在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在亲子关系是否存在这一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情形下,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两种解决办法,一是适用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由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就待证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承担不利后果,二是运用推定规则,在法律规定或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的涵摄下从基础事实推断出待证事实。比较两种方法认定出来的案件事实与案件客观真相之间的关系,因推定多建基于两事实之间的高概率基础之上,其在结果上与案件客观真相相符合的可能性远远高于适用证明责任分配规则认定的事实与客观真相的相符程度。因此说,推定是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困境下保证裁判者所认定的事实与案件客观真相最大程度上保持一致的优位选择,或者说推定是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困境克服之优位选择。[9]
由上,在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适用的前提条件是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不能获得适格的亲子鉴定意见这一直接证据来证明亲子关系存在或者不存在。而适格亲子鉴定意见的核心是其取得须获得相关主体的同意,该同意可以发生在诉讼程序开始之前,也可以发生在诉讼程序进行过程中。只有在经相关主体同意的亲子鉴定缺位情形下,推定作为一种克服亲子关系是否存在这一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困境的优位选择才能被适用。
(二)明确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适用时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义务配置
根据推定的逻辑结构和法律效果,我国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的适用可以分为两步:第一步,从基础事实推出亲子关系是否存在这一推定事实,这一步的关键是原告需要对基础事实进行举证证明;第二步,被告提出相反证据反驳推定事实,这一步的关键是要明确被告提出的相反证据需达到何种程度才能推翻推定事实。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适用的这两个关键凸显了当事人双方程序性权利义务的均衡配置,裁判者需要明确双方当事人在程序层面权利义务的享有和承担情况。
对于原告而言,因为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的适用,其获得的权利是证明负担被大大减缓,不需再去证明亲子关系是否存在这一抽象事实,只需提出必要证据证明基础事实的存在。原告负有对基础事实的证明义务。那么,其对基础事实的证明需达到何种证明程度呢?我国《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规定原告应当提供“必要证据”来证明基础事实,而何为“必要证据”?笔者认为,此处“必要证据”的意思是指原告提供的相关证据对于基础事实的证明能够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能够使裁判者形成关于女方受孕期间是否与男方发生性关系这一基础事实的内心确信。
对于被告而言,因为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的适用,其获得了对于推定事实的程序反驳权。被告的该项反驳权在逻辑上发生在裁判者根据基础事实推断出推定事实之后,是被告对裁判者做出的对己不利的推定事实的一种不同意的行为选择,当然,其也可以选择放弃行使反驳权,主动接受对己不利的推定事实的存在。被告反驳权的行使是通过提出能够达到一定证明程度的相反证据来完成的。而被告提出的相反证据需达到何种证明程度才能推翻推定事实取决于被告提出的相反证据的法律性质。从逻辑三段论的角度来看,被告对于推定事实的反驳可以从三方面展开,一是通过证据直接或者间接反驳作为结论的推定事实,二是反驳大前提(法律规定或者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三是反驳作为小前提的基础事实。[10]P4我国亲子关系诉讼中的推定,因是法律推定,具有适用上的强制性,被告不能反驳此时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定,故被告只能通过反驳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来行使其反驳权。对于基础事实,原告负有证明责任,其提出的证明基础事实存在的证据在性质上属于本证,需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相应地,对于基础事实不承担证明责任的被告提出的反驳基础事实存在的证据在性质上属于反证,反证的证明标准较本证要低,不需达到高度盖然性的程度,只要能够动摇裁判者对于原告提出的本证所欲证明的基础事实形成的内心确信即可。对于推定事实的反驳,被告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直接方式是被告通过亲子鉴定意见等直接证据反驳推定事实,但根据《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的内容可以看出其指涉的情形亲子鉴定是缺位的,故直接方式无法为被告所采行。间接方式是被告通过证明能够推出推定事实不存在的事实来间接反驳推定事实。此时,被告对于该事实负有证明责任,提出的证据是本证,应达到高度盖然性的程度,使裁判者形成关于该事实的内心确信。
(三)应在立法层面落实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适用所需的配套制度
我国各级法院在适用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规则时之所以会出现前述认知上的不同进而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存在,究其原因有三:一是裁判者本身对于推定这样一种特殊的事实认定方法欠缺正确认识;二是《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之规定存在不明确、易生歧义之处;三是立法层面欠缺适用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规则所需的相应配套制度。相较三个原因,笔者认为第三个原因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亲子关系诉讼中适用推定规则所需的配套制度是亲子关系推定、亲子关系推定之否认以及强制认领。观察世界各国和地区,上述制度或者通过民法予以规定,或者通过民事诉讼法予以规定,唯如此,亲子关系诉讼中的推定规则才能在司法实务中得以有效实施。而我国目前无论民法还是民事诉讼法均无关于上述制度的规定,而该任务的完成是一部婚姻法司法解释所无法承受的。笔者认为这才是导致我国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规则适用问题丛生的根本原因。对此,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完善。
1.在民事实体法或程序法中规定亲子关系推定⑥及其否认制度
我国《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第1款规定的是亲子关系不存在的推定,该款内容的有效实施是以民事实体法中规定的亲子关系推定制度为前提的,其本质是一种通过诉讼方式对于亲子关系推定的否认。
长期以来,很多国家和地区在立法层面区分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将亲子关系推定窄化为婚生子女推定,比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目前民法中仍然规定的是婚生子女之推定。⑦我国《婚姻法》虽未规定婚生子女推定制度,但却进行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之区分。⑧然而,随着世界各国对于子女利益的强化保护,取消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之区别已成必然之势,如1960年《埃塞俄比亚民法典》就直接使用“亲子关系推定”语词,并将其范围界定为有婚姻关系的男女与其所生子女之亲子关系的推定和非婚同居的男女与其所生子女之亲子关系的推定两部分;[11]再如1998年修改后的《德国民法典》第1600条[12]P495-497和2005年修改后的《法国民法典》第三章(第318~342条)[13]P98-101也取消了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的区分。对此,笔者认为目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对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遵循的是平等保护原则,故再对两者进行法规范层面的区分规制已无实益,应改传统之婚生子女推定为更加科学的亲子关系推定。
而何为亲子关系推定?笔者认为,在取消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之区分后,亲子关系推定是指在特定情形下推定子女与父母存在法律上亲子关系的一种制度。[14]P134因子女与生母的亲子关系因子女出生而确定,不易产生纷争,故亲子关系推定主要指涉子女与父亲之间的亲子关系。在此,笔者认为可借鉴德国、法国和埃塞俄比亚等国的先进立法经验来建构我国的亲子关系推定制度,具体内容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胎或者出生的子女,以其母亲的丈夫为父亲。非婚同居期间受胎或者出生的子女,以与其母亲同居的男子为父亲。依法采用人工生殖技术生育的子女,以同意采取该方式生育子女的男女为父母”。[15]P277-278亲子关系推定制度的创设,体现了各国立法者对于家庭安定和子女利益双重价值的追求和保护。然而,因为亲子关系推定也是一种建基于高概率之上的推定,必然存在例外情形,故为保护相关主体对于真实亲子关系的知情权,各国立法又赋予相关主体对于亲子关系推定的反驳权,其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推翻依法形成的亲子关系推定。我国《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第1款的规定便是我国关于相关主体对于亲子关系推定进行反驳的规定;我国台湾地区则通过其《民法》第1063条和《民事诉讼法》第589条的子女否认之诉进行规制。多数国家和地区往往通过民法或民事诉讼法来具体规定有权否认亲子关系推定的主体,如2004年修改后的《德国民法典》第1600条规定法定父、生母、子女以及特定情形下的亲生父有权提起生父否认之诉;⑨2007年修改后的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063条规定夫妻一方或子女有权提起子女否认之诉。⑩[16]P243-246我国《民法》和《民事诉讼法》均未涉及亲子关系推定否认之诉的主体,《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第1款仅规定了夫妻一方,范围过窄,这便导致了前述司法实务中出现的诉权主体混乱的情形。因此,我国应借鉴他国先进做法,在通过民法或民事诉讼法设定亲子关系推定制度时,亦应同时规定亲子关系推定之否认制度,并将享有否认权的主体界定为法定父(或推定父,包括与子女生母存在婚姻关系的男子或与子女生母存在非婚同居关系的男子)、生母、子女。之所以赋予子女原告资格,是因为目前各国基本就获悉血统来源是子女的一项人格权这一观点达成共识。笔者认为生父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不应成为亲子关系推定否认之诉的主体,[16]P252理由如下:如果赋予生父原告资格,将会破坏他人的婚姻安定、家庭和谐以及影响子女受教养的权利,故生父之获悉血统权应让位于位阶更高的婚姻家庭安定以及子女最佳利益保护之利益;又因亲子关系推定及其否认制度之创设,均为追求婚姻家庭安定、子女最佳利益保护以及尊重获悉血统真实这一人格专属权,故该制度所涉及人员应以具有特定人身关系的主体范围为限,而不应无限扩及到其他以追求财产利益为目的的利害关系人,比如前述继承利害关系人和房屋拆迁补偿利害关系人。
2.在民事实体法中规定强制认领制度
我国《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第2款规定的是请求确认存在亲子关系的一种推定,该款内容的适用应以民事实体法上的强制认领制度为前提,其目的是使未受亲子关系推定的子女确立与亲生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
民法上对子女的认领,专指生父对子女的认领,具体内容是指生父对未被推定为具有亲子关系的子女的认领,使该子女成为与其具有亲子关系的子女。根据生父对子女认领意愿的不同,生父对子女的认领可以分为自愿认领和强制认领。自愿认领出于生父的主观自愿,自然不会产生诉讼,故与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存在的诉讼无涉。强制认领则是指经生母指认的生父不愿承认子女为其亲生时,相关主体可以诉请法院强制生父予以认领的制度。强制认领又被称为确认生父之诉,其指涉的实际上就是我国规定的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存在的诉讼。然而遗憾的是,我国现行民法并没有关于子女强制认领制度的任何规定,由此,《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第2款规定的亲子关系存在推定的适用就失去了实体法上的制度依托。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有权提起强制生父认领之诉的原告有子女的生母或其他法定代理人以及子女。[15]P279我国《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第2款未明确规定原告范围,这导致实务中法院在认定原告时无法可依并进而出现各行其是的混乱局面。对此,笔者认为,我国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存在之诉中的原告范围应与各国关于强制认领之诉中的原告范围保持一致,界定为生母或子女之其他法定代理人以及子女。然而,我国司法实务在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存在诉讼中出现的一种特殊情形也值得我们深思,即生父欲认领子女但生母拒不同意的情形,此时生父应否被赋予诉权主体地位?笔者认为,该问题的回答应当秉持保护子女最佳利益和维护婚姻家庭安定的理念,如果子女已经生活于另外一个家庭并已与生母的丈夫(或者同居男友)之间形成事实抚养关系,则不应当赋予生父原告资格;但如果子女并未处于另外一个家庭中,则生父获悉子女血统的人格权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第2款规定的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存在之诉与强制生父认领之诉虽具密切联系,但又不完全相同。
四、结语
我国《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首次以法规范形式确立了亲子关系诉讼中的推定规则,该规定有利于实现亲子关系诉讼中的裁判统一并进而提高此类诉讼裁判结果的正当性,具有重要的实践应用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然而,由于我国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配套制度的缺位,以及裁判者对于推定内在逻辑结构和法律效果的认知欠缺甚至错误,导致该规则在适用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对此,笔者认为需要从两方面入手寻求解决办法:一方面,应当促使裁判者形成关于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理论的正确认知,明确其适用前提、逻辑结构以及法律效果;另一方面,也是最根本的,应当尽快通过完善民事实体法或民事诉讼法确立亲子关系诉讼中适用推定规则所需的亲子关系推定及其否认和强制认领等配套制度,否则,仅仅一部婚姻法司法解释囿于其规范权限,肯定无法承担起在我国建构完善的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规则这一重要任务!
注释:
① 亲子关系诉讼又被称为确认亲子关系存否之诉,是指原告请求确认特定人间法定亲子关系存在或不存在的诉讼程序。
② 作为本文分析样本的案例来源于北大法宝数据库中列出的十个涉及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规则适用的案例,具体为:1.文德振与岳俊杰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案,(2013)平民二终字第522号。2.姚甲诉姚乙解除收养关系纠纷案,(2013)长民四(民)初字第436号。3.李某与陆某抚养费纠纷案,(2012)浦民一(民)初字第22309号,(2013)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821号。4.李XX诉韩XX离婚纠纷案,(2013)市民初字第824号。5.周林胜与董云霞抚养权纠纷上诉案,(2013)三亚民一终字第333号。6.王某某诉徐某某抚养费纠纷案,(2013)徐民一(民)初字第888号。7.许某棠诉郑某羡婚姻家庭纠纷案,(2012)龙民初字第2359号。8.卢怀莉诉易善博抚养权纠纷案,(2011)信浉民初字第526号。9.姚如龙诉喻发家等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案,(2011)安法民一初字第700号。10.苏明琪诉李晓明子女抚养纠纷案,(2011)通中少民终字第0005号。
③ 具体参见(2010)崇少民初字第0032号;(2011)通中少民终字第0005号。
④ 在这四种诉讼类型中,前三种在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中都有规定,第四种确认亲子关系纠纷未出现在该司法解释中,但司法实务中已存在,如2011年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1)常鼎民初字第1087号判决书。
⑤ 但该州《民法典》第7004(a)(1)条规定的婚生子女推定却是可以反驳的。
⑥ 此处的亲子关系推定是民法上的一项制度,不同于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亲子关系诉讼中所适用的推定。
⑦ 《日本民法典》第772条规定的是婚生子女推定;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063条规定的是婚生子女之推定及否认。
⑧ 比如,我国《婚姻法》第25条第1款专门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
⑨ 旧《德国民法典》第1595条a规定法定父之父母有提起否认子女之诉之权利,但1998年修法时该规定被完全废除。因为法定父之父母对于财产的继承期待权有可能会侵犯到作为家庭核心的子女利益,故应受到限制,且以此逻辑类推,提诉权人将会无止境地扩及于其他有继承权顺位之人。另一原因是否认之诉中的“否认权”是一项高度人格权。另,旧《德国民事诉讼法》第640条g,法定父提起否认子女之诉讼后死亡者,得由法定父之父母承受而续行诉讼。该规定后被删除。现行《德国民事诉讼法》第640条第1项及第619条规定,法定父提起否认子女之诉讼后死亡者,诉讼程序亦视为当然终结,无由法定父之父母或其他有继承权人承受诉讼之可能。
⑩ 我国台湾地区立法关于子女否认之诉的诉权主体也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具体内容如下:2007年之前的《民法》第1063条仅规定夫妻一方享有诉权;2007年修改之后的《民法》第1063条增加了子女作为诉权主体;《民事诉讼法》第590条规定继承权受侵害之人也可作为诉权主体;2003年大法官释字第587号在明确子女应享有诉权时也明确生父不能提起子女否认之诉,但最高法院2005年度台上字第578号判决则对生父能否提起否认之诉之态度有所松动;最高法院2006年度台上字第1815号判决则肯定亲生父以外有继承权利害关系之第三人,得提起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之诉。
[1] 郑学仁. 亲属法之变革与展望[M]. 台北:元照出版社, 1997.
[2] 刘开会. 实用法医DNA检验学[M]. 西安:西安出版社, 2000.
[3] 张海燕. 亲子关系诉讼中亲子鉴定适用问题研究——兼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2条[J]. 山东社会科学, 2013, 5.
[4] 叶自强. 亲子关系推定的许可与禁止——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二条的评析[J].政治与法律, 2013, 8.
[5] Edmund M. Morgan, Some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Presumptions[J], 44 Harv. L. Rev. 906 (1931).
[6] Mason Ladd, Presumptions in Civil Actions[J], 1977 Ariz. St. L.J. 275 (1977).
[7] 陈荣宗,林庆苗. 民事诉讼法[M]. 台北: 三民书局, 1996.
[8] 许士宦.父子关系诉讼之证明度与血缘鉴定强制——以请求认领子女之诉与否认婚生子女之诉为中心[A]. 民事诉讼法之研讨(九)[C]. 台北:民事诉讼法研究基金会,2000.
[9] 张海燕. 推定:案件事实真伪不明困境克服之优位选择[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2.
[10] 刘英明. 中国民事推定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11] 罗杰. 埃塞俄比亚亲子关系的推定与否认制度及其启示[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3.
[12] 德国民法典(第2版)[M].陈卫佐译注.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13] 法国民法典[M].罗结珍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4] 陈其南. 文化的轨迹下——婚姻家族与社会[M]. 台北: 允晨出版社, 1986.
[15] 王丽萍. 亲子法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16] 吴从周. 再访否认子女之诉[A].民事法学与法学方法(第四册)[C]. 台北:新学林, 2010.
(责任编辑:张保芬)
Practical Analysis and Rethink about Presumption Rules in Parenthood Litigation in China
ZhangHai-yan
(Law Schoo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The Judicial Explanation III of Marriage Law stipulates the presumption rules of the parenthood litigation in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which has put an end to the controversy that whether the presumption rules can be applied in parenthood litigation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and has elevated factual presumption to legal presumption in parenthood litigation. However, after the three years’ application of presumption rules in parenthood litigation, there exists a phenomenon that judges hav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towards some questions such as the application scope of presumption, the application conditions of presumption, the scope of the plaintiff and so on, which lead to different judgments for similar cases occurring frequently. In view of this,on the one hand, judges should definite the presumption’s 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legal effect to make sure the appli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presumption and paternity testing on the issue of cognizance of parenthood can be correctly dealt with and the parties’ procedur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can be rationally allocated; on the other hand, perfect parenthood presumption regime and forcible claim regime should be constructed through civil legislation to guarante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esumption rules in parenthood litigation.
parenthood litigation; presumption; paternity test; scope of the plaintiff
1002—6274(2015)01—111—09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实体法和程序法双重视角下的民事推定制度研究”(12BFX071)的阶段性成果。
张海燕(1979-),女,山东寿光人,法学博士,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研究方向为民事诉讼法、民法。
DF721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A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