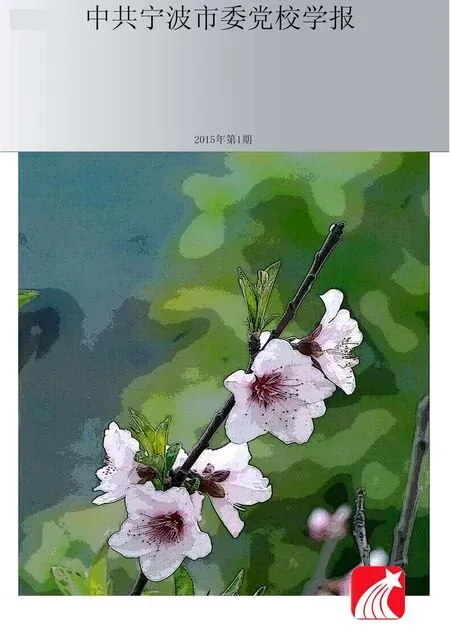“可道”与“不可道”
——老庄“道”论探析
郭美星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浙江宁波315012)
“可道”与“不可道”
——老庄“道”论探析
郭美星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浙江宁波315012)
在先秦道家看来,“道”没有明确的形体,超乎世俗认知,非人类的“视”、“听”、“抟”、“言”等所能认识和把握,因而指出“道”不可道。然而,老庄并没有放弃对“道”的阐发,而是采用了特殊的方式来帮助世人理解“道”本身。即以道与万物之关系为言说的起点;以天道、地道、圣人之道为言说的参照;以似、若、几、或、近、比等为言说的语辞;以“寓言”、“重言”和“卮言”为言说的方式;以得道者对战争、百姓、为政等方面的看法为言道的标尺;以道与德之关系为言道的归宿。
老庄;道;常道;可道;不可道
老庄哲学之核心为“道”,这是几千年来不争的事实。然而,对老庄之“道”的认识,却在历史中呈现出诸多的不同。造成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这不仅涉及到老庄著作的版本问题、各段落以及部分篇章之间的错漏、真伪问题;甚至还与读者的断句差异乃至个人悟性的高低等方方面面相关联。为此,两千多年来,国人对道家之“道”的认识仍处于恍恍惚惚的状态之中。
近些年来,自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被引入中国以来,对道家之“道”的研究也自然而然的采用了新的方法。在对“道”的认识上,有从本体论角度论述者,还有从工夫论、境界论等角度论说者,成果丰硕。应当说,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为我们后人理解道家哲学提供了方便。然而,正如庄子所言,道“可传而不可授”(《庄子·大宗师》),对于这些从文字层面上所呈现出来的“道”,究竟多大程度上接近了道家之“道”的本义,新的言说方式是更进一步的超越了老庄的言说方式而加深了世人对“道”的认识和掌握“为道”,“体道”的方法,还是反而在知识层面上遮蔽了道家之道的色彩,为语言的包袱所奴役,使得“道”成为离世人越来越远的“身外之物”呢?
在通行本《老子》中,首章就对“道”提出了根本性界定。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对于此语的解释,学界可谓众说纷纭,不仅各版本之间存在差异,而且在句读上也存在不同。譬如帛书本《老子》就是这样记载的:“道,可道也,非恒道也。”这与通行本相比,明显多出两个“也”字,并以“常”为“恒”。至于后一种不同,国人尚且可以接受,有解释说是这种变化是为了避汉文帝刘恒讳而为之,这也颇为符合中国的传统,对语义的改变不大。不过,按照中国古代汉语的语法结构,“也”用在句末则表示判断和肯定,也就是说,按照帛书本的理解,这句话可以翻译为:“道,是可以言说的,但不是寻常能说明白的。”也有将这句话解释为:“道可以(被认识)由人们述说,(但人们述说出来的道)并不就是客观永恒的道。”[1](P3)所以帛书本与通行本《老子》在“道”是否“可道”这个问题上显示出差别。
当前,一般将“常道”理解为永恒不变之道。也有将“非常道”理解为,“道是可以认识与表述的,但认识、表述与认识对象之间永远有差距,故非常道。”[1](P1)陈鼓应先生在老庄哲学研究领域,可谓是一大权威,他将这句话翻译为:“可以用言词表达的道,就不是常道。”他还引用前人的话语作为论证,他指出,朱谦之先生曾说:“盖道者,变化之总名。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虽有变易,而有不易者在,此之谓常……程颐在《周易·程氏传》中释《易》之〈恒卦〉时指出:‘天下之理未有不动而能恒者也,动则周而复始,所以恒而不穷,凡天地所生之物,虽山岳之坚厚,未有能不变者也。故恒非一定之谓也,一定则不能恒矣。惟随时变易,乃常道也。’”[2](P74)成玄英也说:“常道者,不可以名言辨,不可以心虑知,妙绝希夷,理穷恍惚,故知言象之表,方契凝常。可道可说,非常道也。”(《道德真经玄德纂疏·卷一》)对于“常道”究竟是否“可道”,我们不妨先看一下老庄是怎么说的。
一、常道不可道
《老子》全书所要探讨的就是那个恒常不变之“道”,然而“常道”又是不可言说的,对于这个问题,老子是这样认为的: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第二十五章》)
“道常无名。”(《老子·第三十二章》)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抟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徼,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後。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老子·第十四章》)
老子指出,那个被勉强“名”之为“道”的东西,没有明确的形体,非人类的“视”、“听”、“抟”等所能认识和把握,它超乎世俗认知,无法加以描述。但如果说它是绝对的空无,却又并不正确,事实上,“道”在无中又显示出有。对于这个勉强名之为“道”的东西世人尚且难以认知,更何况那有无之间变化不定的“常道”又岂是世俗言语所能言说和界定清楚呢?老子在第四十章说:“反者道之动”,在第二十五章又将“道”描述为“周行而不殆。”由此可见,“道”随时随地处于变化当中,不受时空的限制。也就是说,不管世人用怎样的语言,概念说明它,描述都不足以显示它的真实,而且说的越具体、描述得越形象,就与真实离的越远。
然而,老子又十分肯定的是,那个被老子称之为“不可致诘”,超越了人类一切感觉知觉作用的“道”,又可以为人类所把握。在他看来,“道”贯穿古今,在那变化不定中又有一个永恒不变之物,为此,只要世人认识了这个“变中之不变者”也就认识了“常道”。否则,世人就会如《庄子·天下》篇中所言,只能“各得其一察焉以自好。”
对于“常道”的不可言说性,《庄子》是这样认为的,他说: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庄子·齐物论》)
“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庄子·齐物论》)
庄子一方面指出,“道”原本是没有分界的,浑成一体。语言原本是没有定说的,只是因为世人为了争一个“是”字而划出许多的界限。另一方面,他也强调大道是不可称名的,大辩是不可言说的,大仁是无所偏爱的,大廉是不逊让的,大勇是不伤害的。道浅显易知就不是道,言语争辩就有所不及,仁常拘守一处就不能周遍,正直过分就不真实,含意伤人的勇敢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勇敢。
庄子还总结性的指出:“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也就是说,在庄子看来,“道是真实有信念的,没有作为也没有形迹的,可以心传而不可以口授,可以心得而不可以目见。它自为本,自为根,在没有天地以前,从古以来就已存在,它产生了鬼神和上帝,产生了天和地,它在太极之上却不算高,在六合之下却不算深,先天地存在却不算久,长于上古却不算老。”面对这近乎飘渺,“不近人情”的言语,谁又能在短短的数语中识“道”、体“道”呢?
从庄子的言说中可以看出,“道不可言”除了表达出无限世界不能用有限语言表达外,还有一层更具体的意思是,人们习惯于从自己的偏好之心出发,各“师其成心”以观物,“以己为是,以他人为非”。庄子说:“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庄子·齐物论》)在庄子看来,在“道”顺畅运行的世界里,呈现的是一派素朴的景象,没有善恶、是非的区别,是非的彰明,正是“道”的“所以亏”,“道”亏缺的原因,正是“爱”生成的现实条件。正是因为有了是非,有了喜好,故有了彼此胜败的分别。言说亦随之不自然,正如庄子说:“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若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庄子·齐物论》)也正是随着这一趋势的蔓延,世人“成心”日重,庄子说“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庄子·齐物论》)所造成的后果是“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庄子·齐物论》)
也就是说,在老庄看来,“道不可言”并不是道与言绝对对立,而是言说者常用一颗沾染了是非、善恶、喜好之成心看物造成了无限的世界与有限状态下的对立。为此,老子提出了“不言之教”(《老子第二章、第四十三章》)的言说方式,后经庄子的继承发展。庄子提倡“无心之言”、“忘言”之言。庄子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外物》)正如有学者所言:“庄子说道不可言,提倡‘无心’之言,根本的原因,乃是道不可以固着于任何具体的形象和明确的概念。这不是因为道神秘,而是因为对此世的思考方式根本怀疑。”[3]
值得肯定的一点是,不管道家之“道”是否可以言说,只要言说者能够站在大道的基础上,超越世俗“成心”,以“无言”也好,“忘言”、“无心之言”也罢,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无限接近那个不变之道本身。事实上,从《老子》和《庄子》全书的文字来看,他们都在做着相同的事情,都在尽可能的用各种方式和方法来阐述这个难以言说的“道”,为世人认知。为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握住老庄言说中表达出来的那个“道”;另一方面,更要透过言说之“道”本身来体悟那个言语之外的亘古不变的“常道”。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契合先秦道家哲学之本义。
二、可道之道
关于“常道”不可言,学术界对此已有大体一致的看法,从老庄已有的言说来看,“常道”是超越的、无限的,言说是此世的、有限的,有限的语言无法表达无限的世界。然而,难以表达并不意味着不表达,选择沉默的方式应对。综观《老子》和《庄子》这两部著作,可以说都是做着相同的工作,即用道家的方式阐述道家的哲学,尤其是那个难以言说的“道”。具体而言,老庄的言说方式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道与万物之关系为言说的起点
我们知道,尽管《老子》开篇就阐述了“道”“玄之又玄”的本质,然而“道”也并非全然方外之物,相反,它与这世间的万物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为了强调“道”的重要性,老子从“道”与万物的关系入手,为世人明“道”、得“道”提供论证。老子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
“夫唯道善贷且成。”(《老子·第四十一章》)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老子·第三十四章》)
“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
之所保。”(《老子·第六十二章》)
在老子看来,“道”不仅是生化万物的根本,而且广泛流行,无所不至,在万物既生之后,“道”又是万物的庇荫,善于辅助万物并使它完成而不显示出自身的伟大。正如陈鼓应先生所言:“道生长万物,养育万物,使万物各得所需,各适其性,而丝毫不加以主宰。”因此,“道”不仅是万物之本,万物莫不遵道而行,而且万物离开了“道”,将不得以生。这就为万物(包括人在内)知“道”,行“道”的必要性做了一目了然的述说。
(二)以天道、地道、圣人之道为言说的参照
老子指出,“道”泛存于万物,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也就是说,天、地、人三者,都以“道”为效法的对象,三者所具有的特征实为老庄哲学中“道”所具有的特征,只是各自拥有不同的名称而已。在天则曰“天道”,在地则曰“地道”,在人则曰“圣人之道”,在万物则曰“万物之道”。凡此种种道名,皆无外乎是“大道”内化于万物之后的一个名称,其本皆源自于那永恒不变的大道。此外,道道相通,同根同源,也就是说,只要掌握了其中之一者,以此类比,即可知本矣。为了让世人看清并参透那“玄之又玄”的“大道”,老子透过对天道、地道、乃至圣人之道的描述为参照,以此来加深世人对“道”的认识。老子说: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老子·第七十三章》)
“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老子·第七十七章》)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第七十九章》)
“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第八十一章》)
“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老子·第九章》)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老子·第十六章》)
通过上述引文可以看出,老子凸显了“道”与世不争、万物平等、毫无偏爱、利益群生、长久不衰等特点。同时,老子所期望的是世人以此三者为参照去领悟那万物背后不变的大“道”。
(三)以似、若、几、或、近、比等为言说的语辞
然而,不管是天道也好,地道、圣人之道也罢,在老庄所生活的那个被称之为“礼崩乐坏”,“大道废弃”的社会环境中,圣人已离世远矣,又何以得悉“天道”与“地道”呢?为此,为了让世人有幸透过世俗的障碍得窥道之一孔,老子在阐述大“道”之时,还常常采用“或”、“若”、“似”、“几”等含有非确定意思的词语来言说那不可言说的大“道”。老子说: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老子·第四章》)
严复先生在其《老子道德经评点》中指出:“此章专形容道体,当玩‘或’字与两个‘似’字方为得之。盖道之为物,本无从形容也。”卢育三也说:“道好像无边无际、虚而无形的大容器。在老子看来,凡是有形有象的东西,如盆盆罐罐、坑洼湖泊,都是有限的,总是可以装满的,只有无边无际的虚无怎样也装不满。这就是说,在无中潜藏着有,可以容纳无限的有。这似乎是用形象的语言描摹无限。”此二人可谓道出了老子的本义和苦衷,用一种形象的语言、非确定性的言语企图达到对无限的把握,正是老子所热衷于采用这种方法。在全书中,面对言语的局限与困境时,类似的字眼常有出现。
“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老子·第六十七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第八章》)
老子并没有从正面诠释“道”的内容,正如天下之人都对老子所谓的“道”持怀疑态度一样,然而,正是这样的怀疑与不解,才是世人得以体“道”的前提。为了打消这种疑虑,老子还借用比喻的方法。在老子看来,有限世界中的万物最能恰当的代表道之特征的当属水,水和“道”一样有着利而不争,柔弱谦下等特点。正如李贽所言:“水之善固利万物而不争者,何以见其不争也?众人处上,彼独取下;众人处高,彼独处卑;众人处易,彼独处险;众人处顺,彼独处逆;众人处洁,彼独处秽。所处尽众人之所恶,夫谁与之争乎?不争故无尤,此所以为上善也。”水,作为世间寻常之物,世人都可以认知,因此,通过这种贴近生活的比喻,一方面可以拉近道与人的亲近感,同时也给世人一种更直观的感受,为体道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参照。值得注意的是,水毕竟是水,而道终究是隐藏在水之后的那个形上者。所以,世人还需透过比喻、透过若、似、几、或等言语去看清背后老子所意图指明的那个不变之物。
(四)以“寓言”、“重言”和“卮言”为言说的方式
与老子的言“道”方式相比,庄子的“数万言”中,也形成了较为独特的言说方式,这种言说甚至给中国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参考价值。概括而言,借用庄子《寓言》篇中的话说,他采用了“寓言”、“重言”和“卮言”这三言的方式。与前两者相比,寓言和重言是引述名家誉老之言。关于什么是“卮言”,郭象注曰:“夫卮,满则倾,空则仰,非持故也。况之于言,因物随变,为彼之从,故曰日出。”成玄英注曰:“卮,酒器也,日出,犹日新也。天倪,自然之分也,和合也,夫卮满则倾,卮空则仰,空满任物,倾仰随人,无心之言,即卮言也。”成玄英又曰:“卮,支也。支离其言,言无的当,故谓之卮言也”。今人边家珍《〈庄子〉卮言考论》中则说卮言是“合道之言”。在笔者看来,“卮言”就是得道之人,以道为本,因时、因地、因人,随缘论“道”而已,这种言说最大的特点就是以言说的方式,讲述超越文字本身的内容,“以万变言不变”。甚至,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寓言”和“重言”从本质上讲都是“卮言”的一种。
应当指出的是,“卮言”之所以能够成立,必须具备的一个基本原则正如郭象所言,即是“无心之言”也。在庄子看来,不管是世俗的大言也好,小言也罢,都因有“成心”的介入而不见道本。故唯有无心之言,方能超越世俗见解,做到不固执,不自负,不以为既有的言述是完美不可更改的。这与老子言道之基本原则相同的是,言者必须是已经得道之人。
正是得益于卮言的广泛运用,所以我们才能够从《庄子》书中奇特的比喻,丰富的想象力,以及那“恢诡诱怪,汪洋悠肆”的言语中目睹如《齐物论》篇中“隐几而坐,仰天而嘘,盈焉似丧其耦”,“得闻天籁”的南郭子綦。《德充符》篇中的“唯松柏独也正,冬夏青青”的兀者王胎等高绝形象;又见那天马行空,任意自然的思路,从鲲鹏之喻到孔回言谈;从庄生梦蝶到齐同万物;从道进乎技的养生之法到大宗师中至人形象。凡此种种,让我们目睹了庄子从一个视角跳到另一个视角,从一种思路跳到另一种思路的逍遥与洒脱。
(五)以得道者对战争、百姓、为政等方面的看法为言道的标尺
如果说,老子对于“道”仅仅只是采用比喻、“正言若反”等“负的方法”为言说的方式的话,这还不够全面。事实上,老子对于“道”也曾采用过稍显正面的方式来表达。这种表达,就是老子笔下关于得道者对社会人生百事的态度中体现出来的。老子说: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老子·第三十一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军之后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老子·第三十章》)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第四十六章》)
战争,是老子生活的时代中常有发生的事情,兵革作为不祥的东西,大家都憎恨它,所以有道的人,不使用它。凡是气势壮盛的就会趋于衰败,这是与道不相符合的,与道不符就会消亡。由此凸显出,“道”所内在具有的提倡和平,反对强势,主张柔弱处下的特征。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老子·第六十五章》)
在“道”与“民”的关系上,在老子看来得道者是采取一种“愚”即“朴”的方式,而非“明”即“知”的方式,凸显“道”朴素的特征。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老子·第四十七章》)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形。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老子·第二十四章》)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第三十七章》)
老子通过对“有道者”、得道之人对社会人生百态的看法作为世人为人处事、行政、交往的标尺,从正面凸显出“道”的特征,为世人认识大“道”又开了一扇窗户。
(六)以道与德之关系为言道的归宿
我们知道,老庄之所以言“道”,并非故作清高,以求“立言”于世。相反,更多的是,他们看到了社会无道之后的混乱,看到了世间的疾苦和百姓的哀鸣。本着利益万物的心态和圣人本有的胸怀,他们提出了“道”的学说。其最终目的,是希望世人能够以此“知道”,“体道”、“行道”,让社会回归有“道”的状态当中。为此,在论“道”之余,老子说的更多的是“德”。所谓“德者,得也。”归根结底,得的是“道”,这也是老庄道家学说的最后归宿。在此,我们先看老子是如何阐发“道”与“德”之关系。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老子·第五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第二十一章》)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抟。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老子·第五十五章》)
在老子看来,“道”生养万物之后,又内在于万物,成为万物各自的本性,即“德”。正如《庄子·天地》篇所说:“物得以生谓之德。”万物所得之“道”就是“德”,“德”是“道”在具体事物中的体现,是事物所以如此的根据,“德”以“道”为准绳。也就是说,在万物生成过程中,先有“道”而后有“德”。然而,在“体道”的过程中,又需先有“德”,而后有“道”,“不德”即“不道”。老子在阐述其“道”的学说时,最根本目的是为了让世人由“德”进“道”,最终达到道德的合一。
三、结语
总之,世人只有透过老庄言说的方式、独特的思维、类比的方法和强为之言的处境才能真正读懂老子所体悟的“道”,也才能真正把握《老子》书中所蕴藏着的那亘古不变的“常道”。认识到《老子》“道可道,非常道”的表达,实际上为“道”在世俗言语、乃至常人所谓的理性之外预留了一个空间,也正是这个被预留下的空间,为道家哲学乃至国人思想、行为的内在超越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形上之道在世间的言说中、在大道已废的社会环境中不被彻底的蹂躏提供了保障,更为“道”的崇高性与在世人心中的敬畏感提供了可能,这也就为“道”真正约束人,使人信仰提供了可能,为世人行道、体道提供了可能。
[1]孙以楷.老子注释三种[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
[2]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颜世安.庄子言说与道——兼论《逍遥游》的叙述风格[J].学术月刊,2000,(2).
责任编辑:梁一群
B223
A
1008-4479(2015)01-0060-06
2014-11-0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逻辑发展研究”(课题编号:12BKS044)的阶段性成果。
郭美星,中共宁波市委党校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诸子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