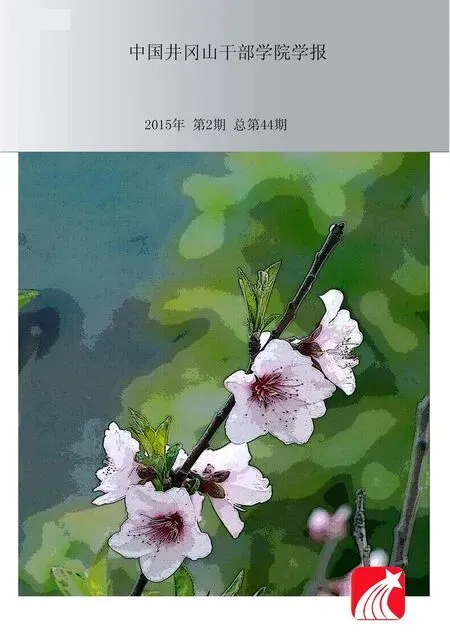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的妇女运动
□赵耀宏 薛 琳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的妇女运动
□赵耀宏 薛 琳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中国共产党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成员,其领导的妇女运动也成为世界妇女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创立之初就广泛地接触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并着手培养妇女干部和创建妇女运动组织。中共“六大”后,随着中国革命重心开始由城市转向农村,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借鉴苏联经验,在中央苏区艰辛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妇女解放道路,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
共产国际;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妇女解放
中国共产党初创之际就关注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共领导下,中国妇女逐渐成长为革命生力军,推动中国历史车轮前进。中国共产党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成员,其领导的妇女运动也成为世界妇女运动的重要部分。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建立的中共妇女部,成立伊始就提出:“我们自不能不与国际无产阶级同志携手。我们更不能不受世界无产阶级祖国的妇女共产国际的教导与指挥。”[1]P185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特别是中共“六大”后,中共妇女运动渐渐走向成熟。旧时的赣南、闽西妇女,深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压迫,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依据“苏联模式”和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开始摸索中国妇女自己的解放道路。经过五年多的艰辛实践,中共领导的苏区妇女运动取得了可观成绩,“妇女摆脱了封建残余的桎梏,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与男子同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权利”。[2]P215
一、共产国际对中央苏区之前中共妇女运动的开启与发展
根据1919年3月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吸收女工参加社会主义斗争的决议》,其成员有“一项紧迫的任务”,即:“必须全心全意吸收无产阶级妇女入党,并采取各种方法,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方面以新的社会风尚和共产主义的道德伦理精神教育妇女。”[3]P3281923年1月上旬,共产国际远东局甫一成立,就指示马林等人:“监督这些国家的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2]P435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革命先贤们开始更广泛地接触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并着手筹建妇女运动组织,中国妇女从此踏上了解放通衢。
(一)共产国际与中共庆祝“三八”妇女节活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魏金斯基不仅帮助中国青年革命者建立组织、学习理论,而且将“三八”国际妇女节庆祝活动引入了中国。随魏金斯基1920年一同来华的成员,就有库兹涅佐娃(维金斯基之妻)和马马耶娃(秘书马马耶夫之妻)。甫抵上海,他们就创立了培养干部的“外国语学社”,并在其中举办马克思诞辰、“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等庆祝活动。[4]P57-58据亲历者许之桢回忆,“第一次庆祝纪念‘三八’节也是在这里举行的。高君曼(陈独秀夫人)在会上发表了演说”。[5]P59
如果说这次庆祝还只是小范围秘密活动的话,到了1924年春,随着国共合作空气的日益浓厚,中共庆祝“三八”节就成为了公开的群众性活动。据杨之华(瞿秋白之妻)回忆:“在当年三月八日那一天,广州第一公园开会纪念‘三八’,就有很多的群众参加。”参加集会的女学生和社会各界女代表共约千人,会后代表们整队游行,并有十余人乘着汽车散发传单,高呼“反对资本家对于妇女的压迫;同等工值!参与政治!革除多妻制度!保护劳动育儿妇和孕妇!革除童养媳制度!禁止畜婢纳妾!废除娼妓制度!”等革命口号。这次群众性庆祝“三八”妇女节活动,“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作为大革命发源地的广东,“大多数妇女群众就开始认识了国民革命”。[1]P585
(二)共产国际与中共早期妇女运动的兴起
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政党名义提出的妇女运动决议案,表明刚刚组建的中国共产党已将妇女运动纳入社会运动之中”。[6]P195《决议》提出:“现在妇女在世界上开始得着解放地位的,就只有苏维埃俄罗斯。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获得了完全平等的权利。”《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第三国际”的支部,按照第三国际第三次大会议决“加入第三国际的各党,必须在各级党委会下面设立妇女工作部,并指派一名党委成员领导该部工作”[7]P846之要求,决定尽快成立中国共产党妇女部。中共“三大”后,向警予担任新成立的妇女部第一任部长。按照共产国际“二大”提出的“所有党报都要指定妇女担任‘妇女版’的编辑”之要求,[8]P94中共“二大”《决议》中提出“亦须为妇女特辟一栏”。[7]P846同年9月13日创刊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专设妇女运动一栏;1923年,向警予创办《妇女周报》并担任主编,这些刊物发表了一系列妇女运动文章,宣传和引领妇女运动。随后不久,在1924年1月,邓颖超等在天津创办了《妇女日报》,向警予专门发文祝贺,称赞其“是中国沉沉女界报晓的第一声”,这对养成妇女“最缺乏”的“政治的常识”和“社会的关心”是“再好也没有的”。[9]P564
中国劳动妇女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剥削和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毒害,她们不仅生活极为窘迫,在思想上也极为愚昧落后,共产国际捕捉到了妇女运动的重点对象——工厂女工,“无组织、无觉悟,容易受人欺骗。一到紧急关头他们或是竟不能加入斗争,一同来反抗压迫者”。[1]P74、75为改变这一现象,就必须要加强劳动妇女的教育,开通她们的思想,渐而塑造她们的斗争目标。为了完成妇女思想启蒙的使命,就需要知识女性的加入,因此,共产国际妇女部专门在1923年发表了《告中国女学生书》,指出:“中国女界之花,女学生革命家,实有极重大的责任,就是做中国女工的前导者,努力奋斗,经由民族的独立以达到自己的解放。”[1]P74、751923年、1924年,邓颖超所在的天津女星社先后创办了女星第一补习学校和女星星期义务学校,对贫民妇女进行文化教育;广东女界联合会也创办女子工读学校、女佣学校,专事劳动妇女教育工作。[1]P176知识女性的加入和劳动妇女的渐次觉醒,为女党员数量的增加创造了条件。在1922年6月中共只有4名女党员,到“三大”时也才13人,但“四大”之后,中共女党员人数快速增长到300名,占全体2500多党员人数的12%。[10]P115-116
这一时期,共产国际采取了多种方式以加强对中国妇女运动的指导。共产国际借助各类会议以同中共交流妇女运动经验、统一认识。中共代表参加了1924年7月召开的第三次国际共产主义妇女大会,并向国际妇女部汇报了本国妇女运动的情况;[10]P96而国际妇女部也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出席了中共“五大”。同时,共产国际也积极探索通过设立课程和培养干部等方式,从理论层面加强对中国妇女运动的指导。例如,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等学校中就设有妇女运动的相关课程,中共的早期妇女干部向警予、杨子烈(张国焘之妻)、周月林等人都曾受训于此。
(三)中共六大强调突出农村妇女运动
受共产国际影响,中共早期十分强调妇女运动的“无产阶级化”,把发动城市女工作为重点,对农村妇女并未给予足够重视。1926年7月,中共中央虽然决定“将来的农妇运动在中国妇女运动上一定要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并要全党“开始严重注意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此时“不能有怎样具体的计划”。[11]P231在1928年6月至7月召开的“六大”上,中共提出了比较明确的农村妇女运动政策。由共产国际帮助中共起草的“六大”《妇女运动决议案》,[12]P497在这“中共成立以来最为详尽的一份关于妇女运动的文件”中,[13]P396专门将“农民运动与妇女工作”列为一节,指出“农妇受压迫最甚,这是引导她们参加革命的基础”、“她们必须参加苏维埃”;《决议案》强调“农民妇女乃斗争着的农民中最勇敢的一部分”、“党的最大任务是认定农民妇女乃最积极的革命的参加者”。[14]P437、P358-359由于此时毛泽东等人已在井冈山开辟了若干红色区域,所以在《妇女运动决议案》专设“苏维埃区域中的妇女工作”条目,提到:“苏维埃政府成立时,应立即颁布解放妇女的条例,以实现在妇女中宣传的各种口号。”[14]P440随着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精神逐渐传回国内,并用于指导中国红色区域的建设,上述关于妇女运动的许多设想逐渐从文字和口头落实到了具体的妇女运动实践中。
二、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妇女政治权利保护机制的建立
在1930年春夏之交,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意见,于上海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并成立了“中央准备委员会临时常务委员会”。[15]P88-89“准委会”制定的《苏维埃宪法》、《土地法》、《劳动法》和苏维埃成立之初颁布的《婚姻条例》等重要文件,为妇女解放确立了坚实的法律保障。这些法律的实施“使妇女能够从事实上逐渐得到脱离家务束缚的物质基础,而参加全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16]P238
(一)借鉴苏联“宪法”保障妇女政治权利
苏维埃是工农民主专政性质的政权,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因此,“在苏维埃政府成立的第一天,就应该公布解放保护妇女的法令,给予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法律上、教育上与男子同等的待遇”。[1]P79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得益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直接帮助,起草中大量借鉴了苏联“宪法”内容的法律文件,提出了多项保护妇女权利、推进妇女解放的内容。[17]P96在1931和1934年两个《宪法大纲》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方面都强调“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凡上述苏维埃公民在十六岁以上皆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同时,在宪法中设置专门条目保护妇女,“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彻底的实行妇女解放为目的,承认婚姻自由,实行各种保护妇女的办法”。[18]P6、11、8、12基于“实现代表广大民众真正的民权主义”而构建起来的法律框架使苏区妇女“从中世纪的奴役下获得了自己的解放。”[19]P56诚如共产国际后来所总结的那样,“中国妇女,自有历史以来就处在奴隶的地位,从没有参加政权的机会,而苏维埃特别保障妇女至少要占代表成分中25%。”[19]P458随着妇女政治上的不断觉醒和经济上贡献的逐渐加重,妇女代表在各级政权中的比例也随之提升,例如,上才溪乡苏维埃,妇女代表比例为57%,下才溪乡苏维埃,妇女代表比例接近65%”。[20]P148妇女不仅参与立法机关,而且参与到了“裁判部”这样的司法机关。例如,在江西省裁判部就设置女指导员,江西第二劳动感化院也有专门检查女监犯的女检察员,公略县的东固区有妇女充当看守员,在中央司法部还有一些受过司法训练即将参加裁判工作的妇女学员。[1]P308
(二)借鉴“苏联模式”提出中华苏维埃婚姻法
苏维埃政权自成立后,就把推翻封建礼教压迫、解放妇女为己任,并将保护妇女婚姻权利的“婚姻法”作为工农政府的首要立法工作。借鉴闽西苏维埃政府《婚姻法》和寻乌县《党和苏维埃对妇运的指示》的经验,1931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实行男女婚姻自主的民主进步的婚姻法规”。[21]P200经过两年多的实行、修改、完善,1934年4月8日苏维埃政府又颁布了修订后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婚姻条例》和《婚姻法》的颁布与实行,有力推动了苏区妇女解放运动,也为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注入了巨大能量,毛泽东称赞道:“这种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打碎了数千年束缚人类尤其是束缚女子的封建锁链,建立了适合人性的新规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之一。”[22]P332
在制订婚姻制度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吸收了苏联在婚姻和家庭立法方面的许多经验。这种借鉴展现在二个方面。一方面,婚姻家庭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相较资本主义国家将婚姻家庭法作为民法的组成部分,苏联基于马、恩对家庭婚姻、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将家庭法列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中国苏维埃政权也接受了这一设计。另一方面,则是二者都有着相同的立法原则。苏联婚姻和家庭立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婚姻是夫妻间实质上的自由结合、夫妻平等、一夫一妻制、保护母亲和儿童的原则。这些原则也存在于《条例》和《婚姻法》中,如: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第1条);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第2条);男女结婚须双方同意,不许任何一方或第三者加以强迫(第4条)。[23]P81、82
(三)创建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
“为了保障妇女权利,严厉打击一般违反婚姻条例的政府和其负责人”,[10]P291苏维埃中央政府于1932年4月决定成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该委员会之目标是“使劳动妇女能切实的享受苏维埃政府对于妇女权利之保障,实际取得与男子享受同等的权利,消灭封建旧礼教对于妇女的束缚,使她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实的解放,以领导他们积极的来参加革命。”其主要工作是“调查妇女的生活,具体计划改善妇女生活的办法”。[24]P56生活改善委员会是苏维埃政府联系政府和妇女群众、具有调查研究和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的协调咨询机构,它“是直接受苏维埃政府指挥,接受苏维埃对妇女工作的决议和各种法令等,拿到下层广大劳动妇女中去完全实现,经常调查下层妇女一般生活状况与广大妇女的要求,计划经常的日常工作,怎样去改良妇女的生活,怎样去实现妇女要求,特别是苏维埃政府下的一种建议的组织。”[24]P239-240中央政府的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为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员周月林,她经常骑马下乡,发动妇女们“废除童养媳”,开展“放脚”、“剪发”运动,宣传《婚姻条例》。[25]P23在她的带领下,各级委员会积极行动,向苏区各地派出巡视员调查妇女生活状况,对侵害妇女权利的现象交各级政府主席团讨论后纠正。例如,于都、宁都、胜利等县,就因违犯保护妇女法令而撤换了工作者。[26]虽然委员会自始至终只运行了两年多时间,但其“创造性的开展工作”,特别是解放苏区妇女——“坚决地实行婚姻条例”的工作,得到了共产国际方面的积极评价。[19]P140
三、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妇女经济生活的改善
共产国际“二大”提出:“私有制是男人比女人优越、男人统治女人的最重要、最深刻的根源。”[8]P77苏维埃政府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破除各种封建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经济。得益于这些法律,苏区的女工和农妇“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开始积极参加苏维埃中国的一切社会活动”。[19]P560
(一)借鉴苏联经验保护妇工权利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始就高度重视女工的劳动权益保障。在“二大”《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中就提出要为“争得平等工价、制定妇孺劳动法”、“保护女工及童工的利益”而奋斗。[27]P87、88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认识和提出女工权利的保障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早至1926年年末,共产国际就要求中共大力向工人宣传“实行劳动法:八小时工作日,每周休息一天,规定最低工资额”、“实行社会法:卫生检查和劳动条件,住宅问题,对疾病、伤残、失业等实行保险,保护女工和童工,禁止女工上夜班,禁止工厂使用不满十四岁的童工。”[10]P178共产国际曾经亲自为中华苏维埃起草《劳动法草案》,甚至有人称1932年1月1日生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为“王明劳动法”。[28]P7、8
在“王明劳动法”中,专设“女工青工及童工”一章,对女工提供特殊保护。主要内容包括:“凡某些特别繁重或危险的工业部门,禁止女工青工及童工在里面工作。”“禁止女工在任何举重过四十斤之企业内工作。”“十八岁以下的男女工及怀孕和哺小孩的女工,严格禁止做夜工。”“所有用体力的劳动女工,产前产后休息八星期。工资照发。”[24]P326-327虽然《劳动法》执行的时间较短、范围有限,加之当时紧迫的战斗环境,但是这一立法仍然为保护女工在内的苏维埃工人工作权利、改善他们的劳动待遇与社会福利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诚如共产国际所说,“苏维埃政权还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为工人开办社会保险,对农民实行国家和社会救助并把人民的教育和保健提高到中国前所未有的高度。”[2]P215
(二)鼓励农妇积极投身苏区建设
毛泽东在分析农妇问题时指出:“她们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身自由,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29]P240痛苦根源于封建土地所有制,根除了这一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就奠定了农妇解放最坚实的物质基础。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规定:“雇农、苦力、劳动农民,均不分男女,同样有分配土地的权限。”正是“平均分配一切土地”,这一“消灭土地上一切奴役的封建的关系及脱离地主私有权的最彻底的办法”,[18]P370、371使广大农妇一改从前对男子的经济依附,毅然走出家门,服务于“苏区内政治上和经济上最重要的和最主要的事情”——“红军底军事胜利”,[19]P357积极参加苏区农业生产劳动,“每每是站在最前线,表示出她们的英勇与特殊作用。”[1]P78
由于大批青壮年男劳力参加红军,后方生产重担就落在了农妇肩上。据统计,上才溪有女劳力559人,占劳动力总数的89%;下才溪有女劳力435人,占劳动力总数的65%。因此,春耕时,她们组织耕田队、开荒队、宣传队;秋收时,她们组织割禾队、突击队,举行革命竞赛。“在耕作之中,妇女表现着极大的积极性,晚上开会讨论,白天到田里工作,永远是那样紧张,没有丝毫的疲倦。……兴国的妇女本来会犁田耙地的只有几个,自从参加生产以后,她们竞争着学习,经过去年春耕,每区能犁田耙田的有20多人,个别的区竟有80多人了。”[1]P380恩格斯极富洞见地指出:“妇女的家务劳动现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已经相形见绌;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30]P181列宁也指出:“要彻底解放妇女,要使她们同男子真正平等,就必须有公共经济,必须让妇女参加共同的生产劳动。这样,妇女才会和男子处于同等地位。”[31]P47-48苏区彻底的土地革命根本改变了几千年来不公平的社会分工。农妇获得了土地,走出家庭,开始“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在苏区的社会生产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正是如此,她们获得了与男人同等的地位,实现了真正的解放。
四、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妇女社会文化的发展
苏维埃政权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将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置于“文化革命”的高度。[19]P384妇女解放不仅要打碎外界有形的政治、经济枷锁,而且还要冲破她们头脑中无形的思想牢笼。思想启蒙与解放,不仅是妇女运动兴起的标志,也是妇女实现最终解放的必由之路。各级苏维埃通过“文化革命”唤醒了苏区妇女的阶级觉悟,她们“再不做奴隶,也不是‘货物’,更不是‘玩意儿’,她们已经是独立自由的人了。”[1]P376她们开始自觉地保护自己的权利,积极投身苏区建设。
(一)提升妇女的文化水平
从当时苏区的社会实际来看,“文化革命”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妇女文化教育。妇女教育除了有正规的学校教育外,还有各类妇女半日学校、组织妇女识字班、家庭临时训练班、日间流动识字班等灵活的办学形式。据统计,兴国夜校学生15740人中,女子10752人,占了69%。兴国识字组组员22519人,女子13519人,占了60%。学龄儿童20969人,女童8893人,已入到小学的3981人。[1]P383妇女不仅自己得到了教育,而且投身到更广阔的社会教育活动中,许多妇女开始担任小学和夜学校长,在长冈乡九所夜校中就有五个女校长。[29]P308还有的知识妇女当上了教育委员会与识字委员会的委员。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对妇女思想解放取得的成绩,称赞道:“妇女群众要求教育的热烈,实为从来所未见……在兴国等地妇女从文盲中得到了初步的解放,因此妇女的活动十分积极起来。”[22]P330
除了关注普通妇女的扫盲教育外,各级苏维埃也非常重视妇女干部的培养工作。1930年6月25日,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决定:以郭桂香为训育主任、张伊犁为教务主任,并由七名教员共同组建妇女干部训练班。[32]P89同时,江西省妇女部通过举办妇女训练班,培养了约200名左右的积极分子。除培训外,“老带新”这样的“传统”干部培养方式,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例如,危秀英、李美群等人就是在蔡畅的“手把手”帮助下,逐渐成长为妇女干部的。[33]P106随之,一批妇女干部成长了起来,到了1933年,江西苏区16个县,就有县级妇女干部27人,兴国县64个乡中,有30多名妇女担任乡苏主席的职务。[34]P231
(二)学习苏联经验建立幼儿园
创办幼儿园是实现妇女解放的重要环节。恩格斯强调:“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30]P181列宁指出:“非生产性的、最原始、最繁重”的家务劳动是“极其琐碎而对妇女的进步没有丝毫帮助的劳动”,因此苏维埃要“创办食堂、托儿所这样一些示范性的设施,使妇女摆脱家务。”[31]P48中共“二大”《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中就提到苏联建立的“儿童养育院”。蔡畅对苏联建立的“儿童养育院”给予了高度称赞,她说:“政府命令妇女除哺乳之外,一切抚育琐事,由国家所设之儿童养育院负责的人员担任,母亲可不必管理,以闲暇时间为研究学问或参加政治工作,从此苏俄妇女的生活得着不少的改良和幸福。”[1]P317“儿童养育院”的理念逐渐为中共所接受,并成为自己的政策。在“六大”《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中,明确提出要在女工中“组织儿童院和幼稚院”以照顾她们的特殊利益。[14]P436在中央苏区庆祝“三八”节的活动中,中共中央指示“各级党、团、工会的组织”要将“托儿所”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与苏联妇女生活的情形”向妇女们宣传,指出:“公共食堂、公共洗衣所、托儿所的普遍设立,使她们已经彻底的从厨房工作以及家事压迫下完全解放出来了。”[1]P360在1934年春,苏维埃政府颁布了《托儿所组织条例》,通过建立托儿所来“代替”妇女所担负的一部分婴儿教养责任,其目的是:使苏区妇女能从繁重的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更多的投入苏区公共事业,也使幼儿能“更好的教育与照顾,在集体的生活中养成共产儿童的生活习惯。”[24]P371苏区托儿所学习苏联,派专门看护妇女照顾儿童,规定“每个至少要管理3个小孩,每所设主任1人。”而苏联的比例则为“每四个小孩有一个保姆看护。”随后,江西省瑞金、兴国等县创办了一批托儿所。有学者指出:托儿所既鼓励了青年农妇“团结”和她们“对自己事情的地方性安排”,它也通过提供看护妇的岗位为那些“处于新活动的主流之外”的老年妇女,“赋予了新的地位”。[35]P98
五、结语
中央苏区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作用是复杂的,这一时期就是毛泽东评价共产国际所说“两头好,中间坏”和周恩来称之“两头好,也不是没有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所说的“中间”。
在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帮助中共制定了《宪法》、《劳动法》、《婚姻法》等法规,为中国妇女的政治解放确立了有效保障。同时,共产国际一系列的决议和指示,推动中共实行了广泛的土地革命,使农妇得到了自己的土地,使其掌握了摆脱经济压迫的条件,提高了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此外,基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中共将“妇女解放”、“男女平等”这些理念传入封闭了几千年的中国农村,使农妇得以思想启蒙,同时帮助妇女摆脱家务劳动束缚,大量农村妇女走出家庭,开始投身公共事务和社会生产,成为党的一支重要依靠力量。这些都是共产国际为苏区妇女解放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共妇女运动对苏区妇女生活的巨大冲击。远在苏联的王明因“中共中央不怕一切困难,不顾任何复杂,坚决不移地执行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四中全会所决定的总的政治路线”、“对共产国际总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16]P346而对国内部分领导人大加赞赏。“紧跟”国际指示,使中共脱离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踏上了“左”倾之险途,随之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超出当时社会承受度的妇女政策。例如,虽然我们强调战争动员要顾及“解决她们的实际困难问题”,但这只是苏区中央局为实现“号召她们一分钟都不要放松扩大红军与归队运动”目标而采取的措施。[1]P305这种目的与手段的倒置,使苏区妇女在扩红工作上态度差异很大,在有的县出现了“不能够鼓动丈夫兄弟去当红军,甚至有不少的落后妇女,还有阻止丈夫儿子去当红军的事情”。[36]P92又如,“婚姻自由”后,妇女身体获得了解放,但随之而来的是离婚率上升和通奸案件频发,有农民感叹“革命革割革绝,老婆都革掉了”。对这一问题,蔡畅也坦言:“我们在农村地区的口号不再是‘婚姻自由’和‘妇女平等’……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把女权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结果引起了农民的反感。”[37]P164
中国作为“东方国家”和“后发展国家”,其不同于苏联的文化传统、发展阶段、社会结构和国际地位决定了我们必然要走一条与苏联不同的妇女解放道路。“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38]P115中国妇女解放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妇女的实际,更要靠中国同志探索一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妇女解放道路。
[1]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14卷[Z].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3]编辑委员会编译.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Z].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4]周蕾.革命、仪式与性别——国际妇女节的传入与国民革命时期的国际妇女节[J].妇女研究论丛,2011(3).
[5]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6]顾秀莲主编.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卷)[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8.
[7]编辑委员会编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Ⅱ)[Z].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8]编辑委员会编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Z].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9]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Z].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10]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编.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第1册[Z].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8.
[1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1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第7卷[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纪念中共六大召开80周年学术探讨会论文集[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1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15]王乐平.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的工作和历史贡献[J].党的文献,2010(1).
[16]余子道,黄美真编.王明言论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7]石仲泉.我观毛泽东[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18]厦门大学法律系,福建省档案馆选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
[1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16卷[Z].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20]江西省妇女联合会,江西省档案馆选编.江西苏区妇女运动史料选编[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
[21]余伯流,凌步机.中国共产党苏区执政的历史经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22]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23]李秀清.新中国婚姻法的成长与苏联模式的影响[J].法律科学,2002(4).
[24]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1937[Z].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25]陈刚.红军女干部周月林的传奇人生[J].党史博览,2008(2).
[26]月林.江西各县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联席会议之总结[N].红色中华,1932-11-01.
[2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Z].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28]刘洪清.苏维埃劳动法寻根[J].中国社会保障,2011(7).
[29]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2]张雪英.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33]郑伟章.优秀的女革命家——蔡畅[J].求索,1982(6).
[34]黄惠运.中央苏区社会保障述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35]〔美〕凯塞L·M·瓦尔克.中国共产党与中央苏区妇女运动[J].党史研究与教学,1992(2).
[36]汤水清.乡村妇女在苏维埃革命中的差异性选择——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J].中共党史研究,2012(11).
[37]〔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中国人征服中国人[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38]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贺文赞)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Women’s Movement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ZHAO Yao-hong XUE Lin
(CELAYDepartmentofTeaching&Research,Yan’an,Shaanxi716000,China)
The women’s movement led by the CPC,an important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women’s movement of the world.Under the guidance of Communist International,the CPC,since its establishment,studied Marxist theory of women liberation and set out to cultivate women cadres and create organizations for women’s movement.With the shift of the center of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the city to the countryside since the Six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the Party,with help from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learning from Soviet Union,worked hard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exploring in the road of women liberation that conformed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ina and made a series of achievements.
Communist International;Central Soviet Area;women’s movement;women liberation
2015-03-12
赵耀宏(1963—),男,陕西延安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薛琳(1981—),男,天津市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性教研室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D231
A
1674-0599(2015)02-004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