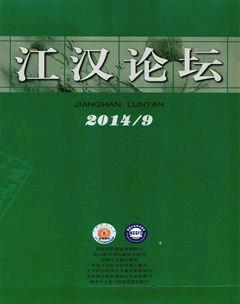《大江报》与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
付登舟
摘要:《大江报》是晚清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的机关报,从诞生到被查封,三起三落,充满传奇与坎坷;以鼓动革命,推翻满清为主旨;风格独特,无所顾忌,敢于直言,成为革命报刊的先锋。该报以湖北新军官兵为主要宣传对象,深入军营,广泛动员,号召革命,为武昌首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大江报》;辛亥革命;舆论动员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9-0105-04
辛亥革命前夕,随着全国政治形势的不断发展,革命思潮风起云涌,革命报刊在长江中下游流域迅速涌现。《大江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最具影响的报刊之一。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该报一直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很有研究的必要。
一、《大江报》始末:三起三落
《大江报》前身为《大江白话报》,于1911年1月3日创刊(于汉口),是湖北革命团体创办的第二个机关报。湖北革命团体的第一个机关报为创刊于1909年10月8日的《商务报》。在这里之所以提及此报,是因为《大江报》与《商务报》可谓一脉相承:一是《大江报》所代表的是与《商务报》一样的革命团体;二是《大江报》报人几乎是《商务报》的原班人马;三是《大江报》承袭了《商务报》的报刊主旨及风格。实际上《大江报》成为《商务报》被封杀后的续刊。《商务报》由于群治学社的革命活动被镇压而停刊,此后,新成立的文学社谋划重组舆论机关报,开展革命宣传,苦于缺乏资金,一直没有进展。1911年1月3日,“詹大悲利用黄梅人胡为霖提供的500元资金。重组革命机关报《大江白话报》,日出一大张,馆设汉口新马路52号。胡为霖任经理,詹大悲、何海鸣分任正副总编辑。馆中人员从编辑到校对悉为《商务报》的旧侣。以灌输国民常识,提倡革命真理为宗旨,鼓吹革命”。
《大江白话报》出版不到一个月,汉口英国巡捕无故踢死人力车夫吴一狗,次日复枪杀示威人员,群情激奋,舆论大哗。江汉关道为讨好侵略者,谕令各报勿登录,“并特地以手谕关照《大江白话报》,勿言车夫伤死,以图掩盖真相。《大江白话报》立予拒绝,连日以头号字标题,公开揭露。其社论《洋大人何敢在汉口打死吴一狗》,严厉谴责英国侵略者的暴行,抨击武汉当道”。时各报畏于权势,噤若寒蝉,独《大江白话报》无所顾忌,大张挞伐,“一般社会颇为欢迎”,从此声誉大著。《大江白话报》“抗言时政”,言论激烈,在吴一狗案中独立抗争,为社会所瞩目,经理胡为霖之父担心事态扩大,“旋胡为其父招归”。报馆资金来源中断,随即停刊。
此后,詹大悲、何海鸣筹集到3000元,易名为《大江报》改用文言文,日出两大张,声明“提倡人道主义,发明种族思想”,明确提出推翻满清政府主张。1911年7月17日,《大江报》刊登了何海鸣的著名时评《亡中国者和平也》,九天后,《大江报》又刊登了《大乱者救中之妙药也》这一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时评。两篇惊雷般的革命时评,使清政府极端恐惧和仇恨。1911年8月1日鄂督瑞潋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扰害治安”的罪名,饬令封闭《大江报》,随即清军警包围《大江报》馆,逮捕詹大悲、何海鸣,报馆立被查封,酿成震动全国的“大江报案”。
《大江报》被封消息公布后,舆论大哗,群情沸腾,各报纷纷发表文章表示愤慨与同情。武汉报界公会和社会团体纷纷集会,强烈要求释放詹大悲、何海鸣。瑞潋慑于民情激愤,只好匆匆收场,改判刑事处分,监禁一年半。《大江报》自此事件后,享誉全国。
汉口光复后,詹大悲、何海鸣被营救出狱,旋出面组织汉口军政分府,仍然十分重视舆论宣传工作,于1912年6月1日,在汉口后花楼街重组《大江报》,何海鸣任经理,凌大同、戴天仇(即后来成为国民党头号理论家的戴季陶)为主笔,扬言“卷土重来”,以监督中华民国政府为己任,担当鄂省舆论的代表。《大江报》复刊后不久,就刊登了社会党首领江亢虎的一篇宣扬“社会主义”的文章,并配合时评,大肆宣扬。黎元洪即据此为口实,大举镇压革命党人,耸人听闻地指责《大江报》“专取无政府主义,为乱党秘密机关,擅造妖言,摇惑人心,废婚姻之制度,灭父子之大伦,无国家、无家族、无宗教、无男父。近乃益肆猖狂,毫无忌惮,至有除去政府,取消法律之邪说,实属大逆不道,悖谬已极”。8月8日,《大江报》遭到军警查封,并通电缉拿何海鸣、凌大同归案,“就地正法”。事发后,何海鸣逃往上海避难,凌大同不幸被捕。9月,黎元洪以不宣布真实姓名和罪状的法西斯手段,将凌大同杀害。自此,《大江报》画上了它三起三落坎坷悲壮的“圆满”句号。
二、《大江报》的基本主旨:鼓动革命
“中华民国之创造归功于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之实行及宣传之两大工作。而文字宣传之工作,尤较军事实行之工作为有力而且普遍”,冯自由的论断充分肯定了报刊对鼓动革命,推翻满清政府所起的巨大作用。《大江报》自创刊之日起,就肩负起文学社赋予的使命,走在革命舆论的最前列,大肆挞伐满清政府昏庸腐朽,丧权辱国,鼓动民众从睡梦中醒来,振救危亡之中国。
1911年4月8日,革命党人温生才以手枪击毙广州将军孚琦于广州街头,事后,因巡警郑家森出卖,温不幸被捕,于15日遇害。各报均“痛诋暗杀者之无意识”,独大江时评鼓吹之不遗余力,对此事进行连续报道,并发表温生才的文章,鼓吹他的“叛逆”行动。“吴一狗事件”发生后,各报噤若寒蝉,独《大江报》无所顾忌,大张挞伐抨击武汉当道,文章指陈:“外人这样虐待我们,与当局的腐朽是分不开的。”
1911年7月17日,《大江报》刊登了何海鸣的著名时评《亡中国者和平也》,说:“政府守和平,即示割让之意。国民不甘,伏阙上书,不足以动政府。有时大张联合之雄风,倡导种种不承认、不纳税之要挟,然亦藏头缩尾,其和平更甚于政府之对外人。”时评揭示立宪派叩头上书的改良主义作法无补于事,警告国民如不亟起革命必招致亡国。该文还指斥清政府的宪法大纲是“摧抑民气之怪物”。九天后,《大江报》又刊登了署名为“奇谈”的《大乱者救中之妙药也》这一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时评。该文实为章太炎的弟子,同盟会员黄侃到汉口,下榻詹大悲处,与《大江报》同人把酒谈论时势,有感于当时社会沉沦浑噩,席中捉笔,草成一文,与何海鸣的时评交相呼应。此文的标题更令人拍案叫绝,其全文如下:“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痈一朵,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形见人人欢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创巨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
作者以悲悯忧愤的情怀,揭示清政府已病入膏盲,不可救药的现实,唤醒国人从沉梦中醒悟进行革命。中国要有一个“极大之震动”和“极烈之改革”;只有“大乱”即革命,才是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向四万万同胞发出了踊跃投身于民主革命的号召。
1911年7月31日,《大江报》大胆刊登离布畏译论《论社会主义定义十五条》,辑录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塞佛列等人的理论要点。“次日续载。约13条。旋遭官方禁阻,不迄而罢。此为武汉报界较为系统传播介绍社会主义思想之肇始”。
武昌首义后,《大江报》卷土重来,何海鸣任经理,凌大同、戴天仇为主笔,将《大江报》再次推到了革命的风口浪尖。
凌大同崇拜自然进步理论,是一个狂热的社会主义理论灌输者,他宣称的“社会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的代名词。《大江报》接二连三刊登凌大同公然鼓吹无政府理论的文章,持论激昂,且在《讨袁檄文》中有“国民四万万,窃国一独夫”等语,昭示了《大江报》人何等的胆识和气魄。戴天仇的文章,洋洋洒洒,气势恢宏,歌颂孙中山之伟大,揭露袁世凯之奸伪,为《大江报》呐喊助威。他曾为反对袁世凯政府向英美德意四国银行大借款发表过一篇短评,全文是:“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寥寥数语,从财政总长,国务总理,到临时大总统,革命元老,漫骂一尽,可谓奇文。他还口头创作了一组狂言,日:“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此言后来在报界流传甚广。
三、《大江报》的突出风格:“敢言”斗士
舆论是革命的先导。任何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或政治行为,势必伴随着大规模的舆论准备和精神动员。面对清政府的黑暗、腐朽以及对舆论的钳制,能够敢于直面现实,大胆对当局种种怪象予以揭露、抨击的报刊虽然不少,但其气势之恢宏,胆量之惊人,报道之猛烈,文章之犀利,影响之深远,当数处于中华腹地汉口的《大江报》。当时,在上海最具影响力之一的《时报》曾作如此评价:“《大江报》创办之初,不过一小报形式,适遇英租界车夫吴一狗案发生,该报均据实登载,不为隐讳,一般社会颇为欢迎。后逐扩充办法,改为两大张,不分皂白,专以骂字为主义,其对于军界攻之尤力,而端老四(按:指铁路督办大臣端方)来鄂,该报曾著时评讥讽,并牵涉老妓王佩兰及官钱局董达夫诸人,若辈因之恨之入骨,然敢言之名,惟该报首屈一指。”
1911年5月。清廷明令铁路国有化,邮传部在湖北成立粤汉、川汉铁路公司后,强行收回这两条商办铁路,旋又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这一举动,激起了各省的“保路运动”。《大江报》一向遇事敢言,连续报道与评论,抨击参与出卖和接收路权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督办端方及洋务人员郑孝胥,还揭发本省藩司余诚格通过“度之公所”,以高息向洋人借得巨款的内幕,并设法觅得借款合同副本,在报上披露。端方南下,道经湖北的那几天,“几乎无日不作讥讽之评论”。其昂扬激烈、毫无顾忌掩饰的报道,震撼了当时的舆论界,也震撼民心,尤其是让武汉当道心惊胆裂,并对《大江报》恨之入骨。
《大江报》是革命派团体文学社的喉舌,而文学社的基础在新军,《大江报》的不少报道和评论是面向新军,直接以新军的下级士兵为对象的。它经常站在下级士兵的立场,同情他们的遭遇,反映他们的疾苦,诉说他们的不平。它大胆地揭发了新军长官“视兵士如奴隶,动辄以鞭挞从事”;镇统“吞蚀军款百万有奇”:标统、协统“花天酒地,广置姬妾”等事实;并点名指责新军第二十九标标统李襄邻克扣军饷。《大江报》这些报道与评论,不畏强暴,振聋发聩,改变了内地报刊在清朝政府的高压下不敢大胆放言的状况,引起了全社会的瞩目。《大江报》所以能以“敢言”的风格展现于世人,最关键的源于主笔詹大悲、何海鸣等人的不计个人安危、心系天下的胸怀,得益于他们卓越的胆识与才华。
《大江报》案发生后,詹大悲在庭审时,“据理力争,批驳一切不实之词,力数反动当局破坏言论自由的罪行,法官无言以对,为保护革命同志,詹大悲勇担责任,拒绝交出时评作者,并谓我本发行兼编辑人,一切责任均皆我负”。董必武在《詹大悲先生事略》中评价说:“君言语妙天下,能言人所欲言而不敢言,故《大江报》风行一时。”
何海鸣因《大江报》“敢言”而入狱,在狱中,尽管备感凄凉无助,依然不忘忧国忧民。他曾在狱中作诗云:“此身尚在余忧患,有泪偷弹为老亲。我纵凄凉人更苦,留得心血事平民。”还有一首“临江仙”是这样写的:“一夜西风侵病骨。雨声啼到天明,几何辗转睡难成,飘零身世感,脉脉不胜情。年小年华轻一掷,秋来兀地心惊,无聊热血满腔横,残身无足惜,憔悴念民生。”
四、《大江报》的诉诸对象:新军士兵
晚清时期,在全国各地涌现的革命报刊如雨后春笋,然而从报人的身份来看,《大江报》报人与其他报人相较,显然多了一重身份,他们不仅是革命报人,而且是革命军人,他们既拿笔杆子,同时又拿枪杆子,这在当时的报界是绝无仅有的。再从《大江报》的宣传对象来看,其他报刊的着眼点主要是士农工商及学界的普通民众,而《大江报》却把新军士兵作为它的主要受众群体。
在武昌首义爆发前,文学社之所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得到稳步和迅速的发展。社员遍及新军各校营,除了它有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一脉相承的组织基础外,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团体机关报《大江报》及报人团体。
《大江报》报人团体的军人身份实与湖北的革命传统相系。早年孙中山在外国组织兴中会,参加革命组织的“什九是湖北人”。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先后在乙巳、丙午两年参加的湖北同志,姓名列在本部名册上的共有一百零六人”。这些革命分子回到湖北,发展志同道合的朋友,秘密开会结社,组织了军队同盟会、将校研究团、益智社等众多小团体,又渐渐地聚零为整,成为发动武昌起义的基本力量。新军广募新兵时,文学社革命党人把这看作打入清军的机遇,“俱认定要想革命,必须运动军队,要想运动军队,非亲身投入行武不可”。刘复基、蒋翊武、何海鸣等都是基于此种认识而加入新军扛起了枪杆子。
他们亲身行武,为的是以军人身份作掩护,动员新军士兵,宣传革命思想。当时新军士兵绝大部分出身于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工人和贫苦知识分子,入伍前饱受饥寒冻馁之苦,入伍后又受军官虐待欺压,在心灵深处渴望革命、推翻满清。从而改变处境,因此极易接受革命思想。为了争取这部分下级士兵,《大江报》在文学社的领导下,对他们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宣传动员。在武汉地区新军的每个基层单位,几乎都设有报纸分销处,除每营赠送免费报纸一份外,还在士兵中发展个人订户。为了加强和新军士兵的联系,鼓励他们投稿。“关于军中各种事实,一经投稿必即刊载”。《大江报》尤其鼓励新军中的文学社社员写稿。在1911年3月15日召开的文学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即曾通过一项决议:“社员采访之新闻及其言论,务请《大江报》尽量登载。”与此同时,《大江报》还在新军士兵中发展了一批特约记者、特约编辑和特约通讯员,如新军第三十标前队士兵张挞伐,就是它的特约记者。正因为这样,《大江报》和新军士兵的关系十分密切,士兵们把这个报纸当作自己的报纸,有什么事情都愿意找它商量,“每日到报社之士兵同志,户限为穿”。当报社经济发生困难时,“军中同志月出资少许,由各标营代表汇送报社,以助经费”。在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宣传活动中,像《大江报》这样深受新军士兵喜爱并建立这么亲密关系的报纸是难得一见的。
《大江报》在新军士兵中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在它的宣传教育影响下,不少新军下级士兵都愿意和它“共图革命”,文学社在新军中发展得很快。1911年1月文学社初成立的时候,在新军中只有八百多个社员,半年以后就发展到三千多人,基层组织遍及于第二十九标、三十标、三十一标、四十一标的马、炮、工各营队。到了武昌起义的前夜,湖北新军一万五千士兵当中,“文学社诸同志占湖北全军十之八九”。但目前多数的文章认为只有五千人左右。武昌首义一举成功,如果不能得到百分之八九十士兵的支持,尤其是在刘复基、彭楚藩等主要起义的领导者、策划者、组织者被捕牺牲后,依然能将起义有序进行,是很难的一件事。由此推断。辛亥革命的当事人、文学社的重要骨干章裕昆所言不虚。
《大江报》在文学社领导下于新军中一系列的精心策划与实施,彻底动摇了清政府在湖北的根基,甚至连根拔起,这绝非一日之功。《大江报》在正确的理念指导下,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通过《大江报》这一最具影响力、号召力的媒介,最终完成了对湖北新军的革命洗礼并使之转向革命。没有文学社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大江报》面向新军士兵的鼓动与宣传,辛亥首义不可能在武昌爆发,也不可能一举而成功。
《大江报》的源流比较复杂,但没有间断,与相关革命报刊一脉相承。虽然它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其作用甚大,这源于它的革命宗旨,源于它诉诸新军官兵这一重要对象,源于它敢于揭露时局、敢于讥讽时政的“斗士”风格。为辛亥革命作了重要的舆论动员工作,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