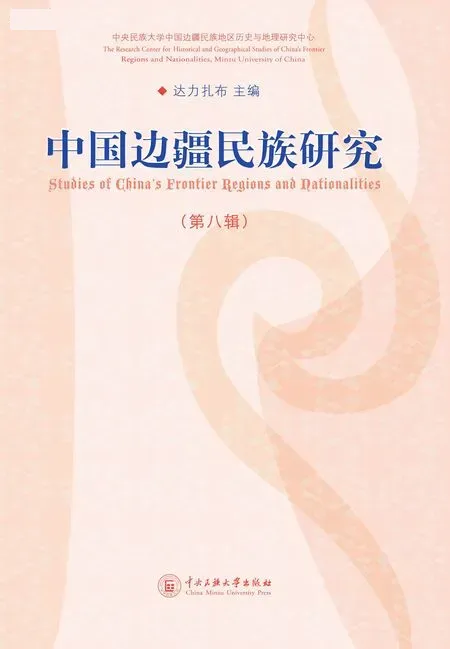阐释拓跋早期历史的一部力作
——重读《拓跋史探》
尤 李
内容提要:本文概括归纳了田余庆先生的《拓跋史探》一书的学术贡献和治学方法,指出此书在探讨拓拔早期历史方面的独到见解,以及在研究方法上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最后提出一些值得进一步讨论和补充的问题。
《拓跋史探》系田余庆先生对北朝史经过精细研究、认真打磨之后推出的一部力作。这部论著出版之后,在学术界引起不小的反响。不少学者对田先生的学术观点进行回应或商榷,写出不少书评。笔者攻读硕士学位之时,曾经拜读过田余庆先生的《拓跋史探》一书①田余庆:《拓跋史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如今,时过境迁,田先生的《拓跋史探》又出版了修订本②田余庆:《拓跋史探》(修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对原书做了较多改动和补正。笔者阅读这部经典论著的修订版,又有全新的感受。
学术界对北魏王朝的“子贵母死”制度、“离散部落”问题探讨颇多,已经取得不错的业绩。田先生却对这些前人做过不少研究的“熟题”继续探究,极力钩沉常见的、十分零散的材料进行精深的考证和分析,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抓住了北魏政治史上“子贵母死”、“离散部落”和“国史之狱”这三个看似毫不相关的政治事件的发展主线和内在联系,来重新阐释拓跋早期的历史。
尽管田先生长于治政治史,但他在讨论拓跋部早期历史之时,十分注重地理环境对部族发育、政治进程的重要影响。他从地理环境来分析拓跋部都城的变迁,从政治中心的变迁来分析部族关系、政治形势,从拓跋部落领袖的墓葬来分析拓跋部早期的活动范围以及其中隐含的政治事件。田先生在《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③原载《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4期,此据《拓跋史探》(修订本),第99-201页。和《文献所见代北东部若干拓跋史迹的探讨》④原载《燕京学报》新第13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此据《拓跋史探》(修订本),第232-251页。两文中对一些重要地名(如“东木根山”、“平城”、“新平城”附近的拓跋史迹)进行仔细考证,并由此牵涉出背后更大的历史问题,追踪拓跋振兴的轨迹。田先生的这种学术风格实与近些年兴起的学术热点“环境史研究”及“社会环境史”的取向⑤参见王先明:《环境史研究的社会史取向——关于“社会环境史”的思考》,《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24-29页。在此文中,王先生谈到:学术界开始注重生态环境对社会历史演变、社会变迁的作用,人物、历史事件与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内蕴相通。只是田先生并未明确宣称自己运用这类分析框架,而是将这种理念融入自己的论证和分析过程中。
田先生还从全新的角度解读出土材料。田先生多次利用碑刻的题名来论证部族关系、族群关系、人群分布以及各种政治势力的消长,还对《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提出独到见解。田先生通过对内蒙古和林格尔出土的东汉壁画墓中宁城图的细致入微地分析,来论证东汉护乌桓校尉的职权、农牧交界处的一条东西交通线。田先生还透过内蒙古凉城出土的“晋乌丸归义侯”金印、“晋鲜卑归义侯”金印和“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等官印资料,来探究此中包含的拓跋、乌桓共生的历史趋势①《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拓跋史探》(修订本),第133、145页。。而且,田先生对拓跋猗卢残碑的分析,不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还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政治形势来给这方石刻定性,揭示出它所蕴含的深刻内涵,点出其所体现的拓跋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及其所牵涉的相关问题②《关于拓跋猗卢残碑及拓本题记二则——兼释残碑出土地点之疑》,原载《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1辑,此据《拓跋史探》(修订本),第252-262页。。
田先生虽然自谦不太熟悉人类学理论,但他在行文中,仍然将这些理论贯穿于自己的分析之中。探讨北魏后宫的“子贵母死”制度、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时,田先生多次论及北族部落中的习惯法、“族外婚”制、“收继婚”制对拓跋君位继承及其与乌桓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如他在《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一文中对道武帝的母后贺兰氏的死因的分析③原载《国学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此据《拓跋史探》(修订本),第37-41页。,在《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④《拓跋史探》(修订本),第157-163页。、《文献所见代北东部若干拓跋史迹的探讨》⑤《拓跋史探》(修订本),第249-251页。两文中对桓帝祁后事迹的探析。这些均堪称传统文献考证与人类学理论相结合的典范手笔,颇具启发意义。
田先生对拓跋部与其姻亲部落的复杂关系、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的精彩分析也同时给予我们这样的启示:在研究民族史时,不要仅仅拘泥于“汉化”-“非汉化”模式,北方各部族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也是其发育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环。但是,这类历史进程往往留下的材料很少,有些史实需要仔细钩沉,甚至加以适当的推测。
另外,田先生以普根父子为例,论及在北魏建国之后,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追尊先人之时,普根父子因为与道武帝本人所继承的拓跋法统没有关系,而未被追尊⑥《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拓跋史探》(修订本),第158-161页。。道武帝追尊先代之君,实即对祖先的历史、皇统世系进行重新改造,等于重新建构一套他所想象的权力传承的“谱系”、他所认可的共同的“历史记忆”,并对他不认同的“过去”进行“选择性遗忘”。这种分析范式又与研究民族主义的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⑦详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理论不谋而合。这类裁减、整理“历史记忆”、对某些不赞成的“过去”进行选择性遗忘,还体现在北魏历史上的两桩“国史之狱”。田先生的《〈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国史之狱的史学史考察》一文采用细腻的笔法一步一步地剖析出道武帝诛史臣邓渊和太武帝杀史臣崔浩的隐情,进而点出历代史家必须思考和寻求为学和自处的两全之道①《〈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国史之狱的史学史考察》,原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此据《拓跋史探》(修订本),第202-231页。,真是发人深省!作为史官,邓渊和崔浩如实记录北魏的开国史。但是,在他们生活的时代,拓跋部已经从部落联盟首领体制进化到专制集权国家阶段。在新的历史时期,汉化的鲜卑人也开始讲究人伦、礼制、君主专制。部落联盟时代因君位传承无序造成残酷丑恶的争权夺利、强后利用外家部落干政、拓跋部在其姻亲部落的庇护之下一步步发育成长等事,用鲜卑人汉化之后的道德、法度来衡量,其实是讳莫如深、极为碍眼的。而且,道武帝在建立君主专制政权之后,逼死其母后贺兰氏、赐死其妻独孤氏,并强制离散其母家贺兰部落、妻族独孤部落,就是欲将后族的势力排挤出权力核心,从而巩固君主专制,同时防止后族干预皇位继承,建立“父死子继”的有序传承制度②《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拓跋史探》(修订本),第24-41页;《贺兰部落离散问题——北魏“离散部落”个案考察之一》,原载《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此据《拓跋史探》(修订本),第52-66页;《独孤部落离散问题——北魏“离散部落”个案考察之二》,原载《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此据《拓跋史探》(修订本),第67-81页。。实际上,贺兰部、独孤部③尽管贺兰、独孤二部之中又分为支持拓跋和反对拓跋的势力,但是,支持拓跋的贺兰部酋领贺讷、独孤部首领独孤(刘)罗辰对拓跋部落发育成长仍然贡献巨大。均为缔造北魏政权的大功臣,拓跋部能够建立国家,也是这些姻亲部落庇护、抬举和扶持的结果。但是,为了巩固专制政权,道武帝一再打压这些姻亲部落(包括杀母杀妻)。他心里想要的其实是一部拓跋部“一枝独秀”的、体面的国史,说得直白一些,就是将拓跋部的某些内斗事件、受姻亲部落卵翼的历史“遗忘”掉。而邓渊不明就里,未按照道武帝的心意裁减某些“丑事”,结果被冤杀。在太武帝统治时期,鲜卑人的汉化程度更深,汉人的礼法制度、伦理道德在朝野的影响力更大。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太武帝命令对自己有大恩、历经多年仕宦生涯、又身居高位的崔浩参与撰修国史。崔浩人虽聪慧,蒙受多年皇恩,但就因为修史时对太武帝所谓的“务从实录”之辞揣摩不到位,书写了拓跋建国初期的一些“不典”(这里指按照汉人的价值观念判定为“不典”)之事,没有完全搞清楚人主究竟想保留什么、想掩盖什么。结果,崔浩一不小心就栽倒在修史之事上,不仅自身惨遭屠戮,还酿成崔氏一门之祸。其实,这两桩“国史之狱”,归根结底还是如何对“过去”进行选择性的“记忆”和“遗忘”,对材料进行适当地剪裁,编撰成统治者接受并认可的“国史”的问题。只是北魏史臣邓渊和崔浩均不谙此道,这不能不令人感叹。
研究民族史,尤其是时代较早的民族史,最大的难题即史料匮乏。虽然近年来考古材料不断涌现,档案资源持续刊布,利用民族语言来研究本族的历史日益受到重视,突厥文、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蒙古文、满文的材料为北方民族史的研究注入了活力,运用本族的一手材料来探讨民族历史与文化成为重要趋势④参见清格尔泰、刘凤翥等编:《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史金波:《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与国学》,《国学研究》第2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近年来,西方兴起“新清史”学派。这一学派强调清朝统治中的非汉族因素、满洲特性,从边缘的观点审视清史,在研究方法上重视汉语之外的文献资料,特别是满文档案的使用,体现“去中原中心”的理路。详见[美]罗友枝著,张婷译、李瑞丰校:《再观清代——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但系统的汉文史料仍然非常重要。田先生的《拓跋史探》就是以考证和剖析汉文文献材料为主,从坊间习见的史料的只言片语记载中,运用自己出色的功力,勾勒出一部全新的拓跋历史。汉文文献,特别是正史中的民族史记载,尽管难免有去取失当、叙述偏颇的缺点,但这毕竟是系统的材料,史臣经过仔细搜讨,精心编排和斟酌,准确度较高,史料价值不容否认。因此,对这些汉文材料进行仔细研读,反复咀嚼,钩稽发覆,仍然能够推动民族史研究。
笔者在研读《拓跋史探》过程中,发觉有些问题尚有进一步讨论或补充的余地,兹缕列如下,以求教于方家。
在《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一文中,田先生论及文明太后冯氏的侄女冯昭仪(后因得孝文帝的盛宠,被立为皇后,即史书所称的幽皇后)有抚养皇子元恪之意,而其生母高氏在从平城到洛阳的途中暴死。高氏之死疑窦丛生,或云冯昭仪派贼将高氏害死。之后,冯氏将元恪取为己子,进行抚养。当时,元恪已经13岁,不可能对后宫中的倾轧一无所知。但是他取代其兄长成为太子之后,不念及生母被害之事,却对养母幽皇后尽礼。田先生认为这是元恪屈从于后宫中强后的淫威①《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拓跋史探》(修订本),第46-47页。,这诚然是真知灼见。笔者认为,以当时的背景观之,元恪之所以这样侍奉幽皇后,恐怕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魏书》载元恪“为皇太子,三日一朝幽后,后拊念慈爱有加”②[北齐] 魏收:《魏书》卷13《孝文昭皇后高氏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35页。。后宫中的生存竞争十分残酷,元恪的生母高氏生前在宫中的地位并不高③《魏书》卷13《孝文昭皇后高氏传》,第335页。。元恪本人想坐稳太子之位、将来顺利登基,讨好最受父皇宠幸的幽皇后,让这位强势的“母亲”充当自己的保护伞,这对他的政治前程有益无害。史载幽皇后欲“如文明太后辅少主称命”④《魏书》卷13《孝文幽皇后传》,第333页。。显然,她的如意算盘是欲通过掌握太子来把握未来的政局,以此擅权。因此,《魏书》所称元恪对幽后尽礼、幽后对元恪“慈爱”也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情。幽后与元恪之间,实因政治利益而结成同盟,外部则表现为含情脉脉的“母子”关系。
在《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一文中,田先生论及前秦灭掉拓跋部建立的代国之后,秦主苻坚采纳燕凤的意见,对拓跋部首领及部众宽大处理,没有强制迁徙离散拓跋部落,而是将其一分为二,分别划给铁弗、乌桓独孤统治。这是为各方乐于接受的处置策略,因为燕凤洞悉代北地区拓跋、铁弗、独孤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处理方法对保全拓跋部意义重大⑤《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拓跋史探》(修订本),第176-177页。。田先生的分析颇有见地。笔者对此问题只想补充一点:前秦君主苻坚做出这样的决策,恐怕不仅仅是听从燕凤的一番说辞,他本人对代北地区的局势也当有深思熟虑。对于前秦来讲,如果严厉处置和极力削弱拓跋部,必定会给同在这一区域的铁弗、乌桓独孤的发展提供机遇,造成这两支部族势力坐大。这样,对前秦来讲,铁弗和乌桓独孤也将成为新的难缠的对手。这无异于前脚办了一只狼,后脚却养了两只虎。因此,苻坚对亡国的拓跋部采取宽松政策、不对其过分削弱,也很可能有利用拓跋残部来牵制铁弗、乌桓独孤势力的考量。
田先生在讨论代北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中,对“赤沙种”、“赤山乌桓”的族属进行了详细梳理和考证,通过扎实的文献材料,得出了赤沙种当属乌桓,即赤山乌桓的结论①《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拓跋史探》(修订本),第181-184页。。这固然极为正确。对此问题,笔者只想从其他角度补充一些证据。“沙”在上古音中属山母、歌部,上古拟音为[∫ea]②郭锡良编著:《汉字古音手册》(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页。;“山”在上古音中属山母、元部,上古拟音为[∫ean]③郭锡良编著:《汉字古音手册》(增订本),第301页。。在上古语音系统中,这两个字属于同一声母,只是韵部略有差异。清代学者孔广森将上古的韵部分为十八部分,包括阳声九部(即元部、耕部、真部、阳部、东部、冬部、侵部、蒸部、谈部)和阴声九部(即歌部、支部、脂部、鱼部、侯部、幽部、宵部、之部、叶部),并说“此九部者,各以阴阳相配,而可以对转”④[清] 孔广森著:《诗声类》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页。。所谓阳声就是以鼻音收尾的韵,所云阴声即指以元音收尾的韵。孔广森认为:阴声和阳声的主要元音相同,可以互相转化,称为“阴阳对转”,这是汉语语音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阴阳对转的其中一种情况就是“歌元对转”⑤王力的《汉语音韵》一书专门分析了孔广森建立的阴阳对转理论(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31-132页)。。那么,在上古时代,“沙”与“山”的读音极为相近,二字的韵部可以对转。因此,汉文典籍音译的“赤沙”与“赤山”极可能所指相同。
另外,“赤山”在乌桓人的信仰世界中具有特殊地位。乌桓人相信“死者神灵归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死者魂归岱山也”⑥[刘宋] 范晔:《后汉书》卷120《乌桓鲜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80页。。赤山也成为乌桓部族的象征之一,对其意义重大。因此,史籍中常常出现的“赤山乌桓”是否也与这一独特的信仰或象征符号有关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