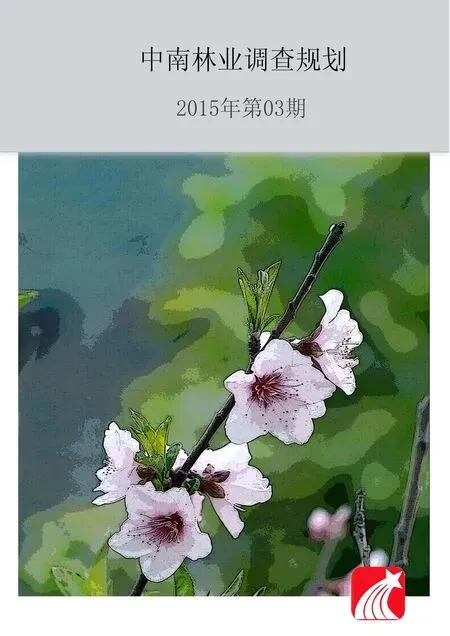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现实思考与制度设想
谢国来
(国家林业局中南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长沙 410014)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现实思考与制度设想
谢国来
(国家林业局中南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长沙 410014)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已历时十多年,在当前继续深化林权制度改革的要求下,对林改的得失进行理性思考显得尤其重要。针对林改中存在的过于注重“均山到户”、人为割裂山林、低价圈地现象严重等隐患,进行讨论并指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产权制度的创新与突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保障在于农村基层集体组织社会治理法治化与民主化;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引导规模经营。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思考;制度设想
林业产权制度是林业生产关系的核心 ,是各项林业政策的基石。长期以来,集体林权制度虽经历数次变革,但产权不明晰、经营主体不落实、经营机制不灵活、利益分配不合理等问题仍普遍存在,严重制约了现代林业的发展。200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发布,中国从此开启了新一轮林权制度改革的脚步,率先在福建、江西两省实施改革试点;到2006年,福建、江西林权制度改革基本宣告完成,受到党中央的高度评价和重视;2008年6月8日,备受瞩目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正式出台,宣布在全国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要求用5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明晰产权、承包到户的改革任务,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健全服务、规范管理,逐步形成集体林业的良性发展机制,实现资源增长、农民增收、生态良好、林区和谐的目标。
当前,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否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呢?专家、学者还是有争论和不同看法的。一致的观点是中外林业产权制度的研究者认为我国尤其是集体林区产权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林地产权制度问题,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势在必行;一些研究者或者林改制度的实施者认为林改达到了或者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观点,或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揭示林权改革制度设计的缺陷,或从改革的实际成效出发来佐证林改制度设计的不足[1]。
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已历时十多年,对林改的研究和评价成果很多,在当前继续深化林权制度改革的要求下,对林改的得失进行理性思考显得尤其重要。
1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进程
1.1 “林业三定”开启林改大门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广大农村中推广并广泛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8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将“分田到户”翻版到集体林区形成“均山到户”的林业“三定”,即稳定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1984年,“林业三定”集体林权改革在全国正式启动,1984年底95%的集体林场完成了山权和林权的划定工作[2],全国80%的集体林分到户[3]。
“均山到户”之后,并没有向国外那样形成有效的自主治理管理模式,反而引起集体林区农户对森林资源的乱砍滥伐,同一时期实行的农村地区“均田制”,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效果。主要原因是:一方面是农民对政府信任度、产权制度缺乏稳定预期,或者说产权不够清晰而产生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宏观制度变迁的背景下微观经济主体的一种理性行为——短期套现获利[2]。1987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南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管理坚决制止乱砍滥伐的指示》,意味着本来与土地承包生产责任制同步进行的林业“三定”政策彻底夭折了。
1.2 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200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发布后,很多关注林权改革的人士都认为,这是新一轮林权改革起步的一个信号。《决定》明确提出:“加快推进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可依法继承、抵押、担保、入股和作为合资、合作的出资或条件……放手发展非公有制林业。国家鼓励各种社会主体跨所有制、跨行业、跨地区投资发展林业,凡有能力的农户、城镇居民、科技人员、私营企业主、外国投资者、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的干部职工等,都可单独或合伙参与林业开发,从事林业建设。”福建省再次启动了以“明晰所有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确保收益权”为主要内容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4年,江西省开展了以“明晰产权,减轻税费,放活经营,规范流转”为主要内容的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到2006年,福建、江西林权制度改革基本宣告完成,全国林权制度改革全面启动。200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颁布并明确提出:“加快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促进林业健康发展”,宣告在全国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1.3 两次林权制度改革比较
从改革对象和改革内容上来看,两次改革都属于以森林、林木和林地为对象的土地产权制度变革,都以林业生产关系调整为核心,在改革的目的、维护林地所有权和稳定林农承包经营权等问题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两次改革的差异不仅表现在改革所处的社会政策环境条件上,更主要体现在改革的目标理念、方式方法、政策措施和具体效果上[4]。
对于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效,笔者持不乐观观点。从本质上看,本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仍是“林业三定”的延续,没有根本性的区别,仅仅是完成了“分山到户”的工作而已。根据厦门大学蔡晶晶[1]关于“分山到户”与“公有产权”两种模式的研究结论,不论是产权的分置或统合,都无法保证我国森林资源的永续发展,都是两种不完善的政策选择。因此,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单一的政策机制来解决全部问题,更大的挑战在于广阔农村基层集体组织治理模式的根本性的改变。
2 问题分析
2.1 未从根本上解决集体林权产权问题
国家林业局原局长贾治邦曾经强调:《意见》“最核心的内容是明晰产权,就是在坚持集体林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依法将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通过家庭承包方式落实到农户,确立农民作为林地承包经营权人的主体地位。”为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决定》明文规定:“已经划定的自留山,由农户长期无偿使用,不得强行收回。”“分包到户的责任山,要保持承包关系稳定。”《意见》也明确提出:“已经承包到户或流转的集体林地,符合法律规定、承包或流转合同规范的,要予以维护;承包或流转合同不规范的,要予以完善;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依法纠正。”这就形成了现在集体林地产权形式多样化,包括了自留山、责任山、集体统一经营的林地、家庭承包的林地、其他方式承包的林地、流转林地等。它们的权利关系更加复杂,有的是长期使用权,有的是承包经营权,也有的是租赁经营权,特别是使用期限的不一致,必然导致一地多证,人为地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经营期满后,林权如何处置并没有明确,产权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2.2 过于注重均山到户,人为割裂山林
1981年颁发的 “林业三定”政策和现在的《意见》,都强调要“均山到户”,国家林业局张建龙局长强调,新一轮集体林权改革首先要“确保农民平等享有林地的承包经营权……一定要均山均林到户,把集体林地的使用权和林木的所有权,能均山均林的要到户,不能均山均林的,要均股均利”。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但在林改中的做法大同小异,“还权于民、还利于民”的模式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可和推行。林地、林木有好有坏、有远有近、有上有下,为了公平顺利地把山林分到农户,人为地把整块整块的山林条条块块割裂开来,均分给各家各户,造成森林、林地破碎化、分散化,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一是山林越被条条块块细分后,林权证的四至边界就越不准确,容易造成新的纠纷,特别是遇到林地被占用征收时,补偿费用都是以平方米为单位计算的,边界的不清晰引起纠纷是必然的;二是流转难度增大,山林分的越细,承包户意愿与诉求越多 ,意见越难统一,整体流转的难度越大;三是制约了林业集约经营,分散经营既制约了林权流转,也制约了规模经营,成本高涨,效益低下,严重挫伤林农积极性,森林质量越经营越差。
2.3 政府部门角色定位难,成为林改最大障碍
任何一项改革从本质上说都是对既有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一方面,林业长期以来自上而下的政府管理模式遏制了林农自身的自治能力和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的参与,政府的强势介入必然使个体对政府的依赖性增大,减少个体间合作和自我治理能力的培养。集体林权改革后,不论是个体分散经营、集体经营还是公司经营,在林权体系不稳定情况下,资源使用者均寻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1],忽视森林资源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危及森林资源的可持续经营。另一方面,新一轮集体林权改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必然体现精英的意愿,各级林改政策的执行者甚至是政策的制定者,作为经济理性人,首先考虑的是其自身利益最大化。我国长期以来的政府部门职能定位不清和权力扩大化,各级林改政策的执行者尤其是政策的制定者,关注更多的是规范林农的行为、管理的便利性,忽视的是自身的责任和权利的制约。政策的好坏关键在于执行,执行走偏了,再好的政策也会变成坏政策,但恰恰是执行者体现了各级政府部门的意志。中国林业经济学会秘书长陈根长曾经认为:“真正阻碍林权改革推进的力量就在林业局大院内!”
2.4 低价圈地现象严重
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以来,低价圈地、林权非正常集中现象越来越引起了研究改革成效的学者和专家的注重和担忧。研究成果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林农自身的原因。长期以来山林的收益很低,林农对山林没有依赖关系,对林权没有过高的期望值,自己经营还是别人经营无所谓,甚至漠视;分散经营成本高,效益低,林农投资积极性不高;林农对林改政策、林权认识不深,对政府缺乏信任度,必然追求山林短期效益,地租就是最直观能兑现的短期效益,所以不少林农把山林一转(转租、转包、流转等)了之。
二是乡村集体组织——村委会代表了政府组织,村委会干部作为地方政府代理人,掌握着与村民完全不对等的信息优势和较强的资源获取能力(博弈能力),首先考虑的是其自身利益最大化,改革一定要能给自己带来好处;其次,由于乡村治理制度的不完善和监督机制的缺失,一些村干部在个人利益驱动和外来资本的怂恿下,利用其信息和职位优势,投机钻营,谋取私利。[5]
三是地方政府的干预。出于地方经济产业发展需要,特别是林业产业工程建设规模化的招商引资要求,一些地方政府往往插手干预林地流转,林农的山林自愿或不自愿地被流转了。
3 制度设想
3.1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关键
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农民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但“长久不变”究竟是多长?《意见》规定:林地的承包期为70年。但同时又规定:自留山由农户长期无偿使用,不得强行收回,不得随意调整。事实上,林权的形式非常多样复杂,林地使用权被赋予了不同含义,期限有长有短,人为制造麻烦。如何才能从根本解决集体林地产权问题呢?最佳途径是林地使用权(承包权)长期固化。林地使用权(承包权)长期固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必然加快,农村人口越来越少,最终结果是集体林权高度集中,甚至出现无人所有的极端状况。
这一途径下的林权制度设想是,林地权属划分为林地所有权、林地使用权(承包权)、林地经营权。保持林地所有权集体所有性质不变;林地使用权(承包权)“长久不变”,没有时间限制,是林农平均初始分配权,可继承,可流转,可抵押。使用权(承包权)的流转、抵押需要制定相应的规则和约束条件;林地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则完全市场化,在双方平等自愿的条件下通过合同约定取得,只要进行产权登记即可。林地经营权可以转让,但不可抵押;林木所有权跟林地经营权捆绑,不再单独发证,因为林木的变化太快,短轮伐期速生丰产林几年一个轮伐期,给林木所有权单独发证难度大、成本高,更没有必要。
3.2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保障
政策的关键在于执行,执行的关键在于各级政府。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如何保障政策执行不走偏,让好的政策惠及广大林农?
首要问题是社会治理的法治化。一是政府行为法治化,在法律框架下制定游戏规则,当好裁判,才能保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大方向上不会走偏;二是明确政府职能定位,制约政府权力,杜绝行政干预市场活动行为;三是政府行为服务化,鉴于森林的商品属性和社会公共服务属性,政府对森林经营既不能事事包办,也不能撒手不管,只有建设服务型政府,才能充分发挥政府指导引导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服务的职责性、高效性。当前被广泛推广实施的林权流转、产权交易、抵押贷款、资产评估政策均存在较大的隐患和风险。比如,造林大户、公司用承包的林地进行贷款存在很大的金融风险,产权交易中心和林权流转资产评估要求事实上阻碍了林权的合法交易。比较简单易行的防范措施:一是林地使用权(承包权)与林木所有权可以抵押贷款或融资,但林地经营权不可抵押;二是林权交易中心更名为林权交易登记中心,仅作为林权证发放登记管理机构,不直接参与市场交易活动;三是为了保护广大林农的切身利益,林业主管部门可以定期发布林权流转、交易的指导性保护价格。
其次是农村集体基层组织社会治理的民主化。集体林区的出路在林地高效规模经营,但事实证明,大户承包经营、集体或公司统一经营都没有让林农正真得到实惠,基层村组织的运转举步维艰,公益事业和公共设施几乎荒废。如何解决既能规模经营又能避免现有形式规模经营的弊端呢?国外学者提出了共有产权体制的解决办法。这种共有产权形式不同于我国农村的集体产权制度之处在于,它强调“按份共有”而不是“统一总有”[1]。这一切都有赖于林农在农村集体组织中具有知情权、表达权、决策权等,只有在法治保障前提下,实现农村基层组织社会治理民主化,才能真正走上具有广泛参与、共同决策的共有产权、集体规模经营健康发展之路。
3.3 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引导规模经营
改革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导致一部分人受益,一部分人受损,作为推动林业经济和农村发展的重要途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纠纷和冲突。因此,集体林权改革要让绝大多数林农受益并接受。只有利益分配均衡了,体现了分配公平原则,才不会造成新的纠纷和冲突,林改中的一系列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林业三定”和现在的《意见》,都强调要“均山到户”,就是要保障林农的初始平均分配权。 “均山到户”后,分散经营成本高、效益低,不愿投入,又与集约经营发展方向相矛盾。《意见》提出新一轮改革的核心是“明晰产权”,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落实处置权,保障受益权,不是单纯再搞均山到户,而是突出了权利到户,这是最重要的进步。要着重推行“均权均利到户”,对已经“均山到户”的,要引导林农以林权入股,对不能“均山到户”的,要引导林农“分股不分山、分利不分林”,走股份合作规模化集约经营道路。为此,林改配套政策和措施必须做到政策(包括项目、任务、计划、资金等)要透明,信息要公开,服务要到位,要让所有参与林业经营活动的公司、集体组织、个人获得公平发展的机会,也要为林农出谋划策,切实解决林农经营上的困难。
[1] 蔡晶晶.“分山到户”与“共有产权”——权衡森林资源治理的两种不完善选择[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13(1):23-27.
[2] 温铁军.我国集体林权制度三次改革解读[N].经济参考报,2009-08-12.
[3] 降蕴彰、杨妮.学者称新一轮集体林权改革对矛盾有所回避[EB/OL].北京:中国改革杂志.(2008-09-10). http://news.sina.com.cn/c/2008-09-10/111516266673.shtml.
[4] 刘苇萍、王社权.新一轮集体林权改革与林业“三定”的比较研究——以江西省遂川县为例[J].林业经济,2007(11):20-26.
[5] 周文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背景下的纠纷与村治——以江西睦村林改实践为例[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2.
TheRationalThinkingandSystemImaginationoftheCollectiveForestRightsReform
XIE Guolai
(Central South Forest Inventory and Planning Institute of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Changsha 410014,Hunan,China)
The reform of collective forest rights system has been carried on for decades,the rational thinking of the gain and lost of the reform is vital under the keep pushing the reform forward circumstance.These main hidden problems of the reform such as too focus on the average hill field to each family,divide the hills forest by purpose,enclosure with low price were analyzed.Then pointed out that the key to collective forest rights system reform is the innovation and breakthrough of the rights system; the guarantee for the reform is leg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of the management for the villages; improving the profit distribution system,and guiding the large-scale forest management.
collective forest rights system;reform;thinking;system imagination
2015—08—25
谢国来(1965—),男,湖南临湘人,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林业调查与规划设计等工作。
F 326.2
A
1003—6075(2015)03—0001—04
10.16166/j.cnki.cn43—1095.2015.03.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