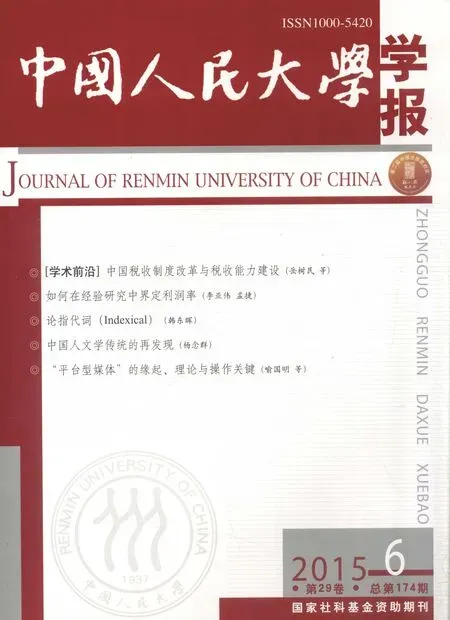汉唐时期北方游牧部族部落南迁的经济地理因素
贾衣肯
汉唐时期北方游牧部族部落南迁的经济地理因素
贾衣肯
汉唐时期北方游牧部族部落南迁,多至蒙古高原游牧经济生态圈南缘的阴山—河套地区,合黎山、龙首山和燕山—滦河上游及大小凌河流域一带。这里为北方游牧部族部落冬南夏北的游牧生产活动提供了春冬牧场。适于游牧生活的自然条件及近邻农耕地区和商贸路线的地理位置,为游牧民的生存、生活提供了必要的保障,成为不同时期北方游牧部族部落南下迁居这一带的经济地理因素。
北方游牧部族部落;南迁;经济地理因素;游牧经济生态圈
蒙古高原及其周边地区是汉唐时期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等部族部落的主要活动地域。高原中部即今蒙古国南部和我国内蒙古北部是东西长约2 000公里、南北宽约1 000公里的戈壁砂砾地,在古代被称为“澣海”、“大漠”或“大碛”。汉文传世文献,通常以大漠为界,把蒙古高原南北地区分别称作漠南、漠北。[1](P1-2)蒙古高原海拔在一千米以上,为海洋湿气难以到达的内陆高原,属于温带半干旱与干旱气候区。干旱、雨水少且不稳定是这里的气候特征。戈壁沙漠、沙漠草地和干旱草地构成了主要的地貌景观。这里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决定了人们只能以游牧的方式生存、生活。
就汉唐时期千余年的历史来看,生活在漠北的游牧部族、部落,曾不断南迁,即越过戈壁砂砾地带,南下到今阴山一线。以往学术界的讨论主要是围绕迁徙的原因展开的,如归因于游牧地区的气候变化、游牧民繁衍导致的人口压力、游牧各族之间的战乱,等等[2]。近年来学术界则从游牧经济社会本身的特点来探究,如有学者认为游牧经济对自然环境(尤其是雨量的多寡)的高度依赖,及其不能自给自足的特性,使游牧经济相对脆弱、单一,而依赖于辅助性产业(农作、狩猎、采集、贸易和掠夺)的补足[3](P135);有的学者则强调游牧经济与社会比重的失衡(牧场与畜群头数之间、人口与牲畜之间以及人与牧场之间的平衡)[4](P130-141)。但这些认识,主要着眼于游牧民自身及其迁出地的各种因素,对其南下指向的迁入地因素甚少关注。换言之,游牧民为什么主要是向南迁徙?而且迁入地选择的是阴山一线呢?
一、北方诸游牧族的南迁活动
纵观汉唐一千年间北方游牧民族移动,可以发现他们主要是越过戈壁沙漠,南下至漠南地区。
秦统一中原时,匈奴是当时北方最为强悍的游牧部族,占据着以河套及大青山为中心的地区。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二年),匈奴被秦王朝逐出了这一地区。秦末汉初,中原纷乱,匈奴又乘机迁回故地,灭东胡、败月氏,控制了东起辽东、西至西域南北道诸国、北起贝加尔湖、南抵秦昭襄王长城的广大地区。[5](P6)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至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间,汉武帝几次发动征讨,又将其逐出漠南地带,并在河西地区、阴山山脉以北建障塞亭燧*西汉昭帝时又于辽东郡、玄菟郡(今东北地区南部及朝鲜北部清川江出海处的番汗附近)边筑长城。,招徕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的乌桓,南迁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即今燕山—滦河上游以及大小凌河流域之地[6](P362),为汉侦查匈奴动静。
匈奴退居漠北后,内乱不断。公元前53年(汉宣帝甘露元年),呼韩邪单于不抵郅支单于攻势,率部众数万骑南下归汉,迁居漠南阴山—河套地区*《汉书·匈奴传》载:“呼韩邪从其计,引众南近塞……是岁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朝三年正月……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单于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五原塞在今内蒙古大青山西端、乌拉山南麓及阴山南坡地带,光禄塞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明暗乡小召门梁古城一带,受降城在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东阴山北。林干认为,南迁后的呼韩邪部众驻牧于朔方鸡鹿塞(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为时八年之久。可见,当时呼韩邪部众主要分布于阴山—河套地区。[7](P349、975、1618)[8](P19)。此后,呼韩邪部众得到西汉的扶持和帮助,人丁孳茂,广布于汉上谷以西至敦煌塞下[9](P3804),与上谷以东的乌桓部落共居西汉北境。
公元1世纪中叶,漠南匈奴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内乱迭起,乌桓乘机攻破匈奴,匈奴不得不放弃漠南而北迁。48年(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匈奴日逐王比以未能继立为单于,率所属八部四五万人南下,至五原塞归附东汉,迁居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等缘边八郡,助汉戍边。与此同时(49年),光武帝沿用西汉武帝策略,招抚乌桓,许其由五郡塞外迁入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等十郡障塞之内,以与边塞匈奴相制衡。
随着乌桓不断南下,其北边的鲜卑亦由辽东塞外之鲜卑山(即今科尔沁右翼中旗西哈勒古附近的大罕山)迁至乌桓故地饶乐水流域,又南下至东汉五郡塞外。1世纪末,漠北匈奴在周边势力的打击下溃散,部众或西奔,或南下至云中、五原、朔方、北地、辽东等汉郡投降*《后汉书·南奴列传》:“章和元年……北庭大乱,屈兰、储卑、胡都须等五十八部,口二十万,胜兵八千,诣云中、五原、朔方、北地降。”此外,匈奴十余万落归附辽东太守,与鲜卑杂居。[10](P90-91)。于是鲜卑大规模南迁西徙,进驻匈奴故地。至2世纪中叶,鲜卑兴盛,首领檀石槐建庭于高柳(今山西省阳高县)北三百里之弹汗山(今内蒙古商都县附近)歠仇水(今东洋河)[11](P310),“乃自分其地为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夫余、濊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各置大人主领之”[12](P2989-2290),统归于己。至此,鲜卑占据了东汉辽东至敦煌塞外之地。汉末以降,中原北方除魏晋短暂的安定时期,基本上处于战乱之中。其间,塞外鲜卑诸部落更行南下,迁入关中以北(及关中)、六盘山、陇山以东、陇西、河西地区[13](P20-29)[14](P81-88)以及黄河南北地带。
4世纪末鲜卑拓跋魏兴起,不断攻伐漠北柔然等诸部落。429年4月~8月,太武帝拓跋焘俘获高车、柔然30余万人[15](P98),10月“列置新民于漠南,东至濡源(今河北东北部滦河),西暨五原、阴山,竟三千里”[16](P73)。所置“新民”多为高车人[17](P214)。
6世纪中叶突厥击溃柔然,称霸漠北而南临周、齐。周、齐莫能抵抗。隋初于朔方、灵武郡筑长城[18](P59),说明突厥此时已占据隋长城以北阴山—河套地区。基于自身对突厥进讨无力、又难以防守的情况,隋朝对突厥采取“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策略[19](P97-105),以削弱对手实力。585年(开皇五年)漠北突厥沙钵略可汗与所辖部落迁居漠南白道川(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西北,阴山南谷口北),597年(开皇十七年)驻守北方的突利可汗(即染干)率部众南迁度斤旧镇,而后归附隋朝,迁居夏(治今陕西省靖边县东部百城子)、胜州之地(治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20](P536-537)
隋末唐初中原北方割据势力为在逐鹿中原中取胜对手,纷纷北面称臣于突厥,与之结援。618年(武德元年)李渊将河南地让与突厥,并赂之财帛,以与突厥结好,瓦解西秦对长安的攻势。于是,处罗可汗之子郁射设率万余家人迁居河南地。[21](P152-161)
随着北方割据势力渐次消亡和唐朝的强大,内部矛盾重重的突厥在与唐朝的对抗中很快衰落。630年(贞观三年)唐朝与漠北铁勒诸部联手进攻突厥,突厥不战自溃,颉利可汗被俘,其部众十余万人降唐,被安置在河南地。至7世纪70年代(高宗咸亨年间),突厥诸部落降唐者甚多,唐处之于丰(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西北)*一说在五原县西南黄河北岸。、胜、灵、夏、朔(治今山西朔县)、代(治今山西代县)六州。[22](P58)
8世纪中叶回纥(鹘)取代突厥兴起于漠北,势力东及兴安岭和西辽河、滦河上游地带,西至阿尔泰山[23](P5-10),南抵阴山、贺兰山、河西走廊及合黎山和马鬃山一带[24](P88-98)。9世纪初,回鹘中衰,内乱不止,840年为黠戛斯击溃。以庞特勤为首的十五部人西迁葛逻禄,而以乌介特勤为首的回鹘十三部南下至唐天德军(内蒙古乌拉特旗西北)和振武军(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北境附唐。[25](P27)
可见,匈奴、乌桓、鲜卑、高车、柔然、突厥、回纥(鹘)诸族,或因自身发展、内乱南迁,或为中原王朝招徕、离间、战败而徙,或为漠北他族所迫而南下,但其迁居之地主要都在阴山—河套、燕山—滦河上游、大小凌河流域以及合黎山、龙首山*合黎山指甘肃张掖市至高台县以北山地,龙首山山脉是横贯河西走廊东段北侧的山岭。—河西走廊—祁连山一带。
二、农牧过渡带与迁入地的选择
汉唐千余年间,漠北游牧部族,不同民族、不同背景下的南迁,大都选择了同一地区。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里位于中国农牧交错线以北*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提出的龙门、褐石一线。史念海认为,此线基本走向是从今陕西径阳、白水、韩城诸县、市,达于黄河之滨,由龙门山东越黄河,经山西屈县南,循吕梁山东麓东北行,至于今山西阳曲县北,东南绕今盂县南,东至太行山,再循太行山东麓,过燕国都城蓟之北,东南达于渤海之滨。[26](P512-547),气候比较干旱,缺乏农作条件,适合畜牧业生产活动。
阴山—河套地区,在春秋战国时主要分布着戎狄和诸胡[27](P284-291),秦汉时期主要分布着以匈奴为主的北方诸部落。599年率万余人投归隋朝的突利可汗因屡遭雍虞闾可汗攻袭而被隋安置在夏、胜两州之间,“任情放牧”[28](P1334);唐初郁射设部众万余家迁居河南地,及之后唐以河南地为安置突厥的中心地区,使之“不离本俗”,保持游牧生活方式[29](P240),说明直到隋唐时期,这一带为宜牧之地,适于游牧经济活动。此外,阴山—黄河地形险要,且有水网纵横交错、地势平坦,适于耕作。王莽时称“五原北假,膏壤殖谷”[30](P4125),唐时丰州有“田畴良美,尤宜耕牧”[31](P2978)之称。汉之“五原北假”和唐之丰州大致相当于今内蒙古河套西北部及其以北地带,可知这一带为宜耕宜牧之地。同时,阴山地区草木茂盛,禽兽多,可牧可猎,还可提供牧民制作弓矢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木材。*《汉书·匈奴传》:“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可以说,这里有游牧民生活所必需的草场,还有可种植粮谷的膏壤及可供狩猎和获取生活用材的山地,以及丰沛的水源。
阴山—河套以西,合黎山、龙首山山北为宜牧之地。尤其是龙首山北坡,在古时都是比较好的草场。龙首山树林茂密,溪流不断,植被丰富,在汉成帝时为温偶駼王的驻牧地。[32](P36)当时,汉向匈奴索要这里“生奇材木”之山地时,温偶駼王以“匈奴西边诸侯作穹庐及车,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为由[33](P3810),拒绝了汉的要求。这一带匈奴世代驻守,在西部匈奴经济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南面是河西走廊及祁连山山脉,为宜耕宜牧之地。在汉武帝时,这一带为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的驻牧地。《史记索隐》引《西河旧事》称:“(祁连)山在张掖、酒泉二界上,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34](P2909)这里水草肥美,且有丰富的木材资源,是冬夏皆宜的牧场。阴山—河套以东的燕山—滦河上游、大小凌河流域和西辽河(西拉木仑河)及其支流老哈河流域为森林草原地区,有可供放牧的草原地带、可狩猎的山地森林和适于耕作的河谷地带,在汉唐时期主要分布着乌桓、鲜卑、契丹等森林草原游牧部族部落。
其次,这一带近邻中原农耕地区和商业贸易路线,便于游牧民获取自己不能生产而为日常生活必需的谷物和生活用品等。
游牧民虽然从事一定的农作,但很有限,还需通过与农耕地区的交换获得更多粮谷,以及自己无法制造出的一些生活日用品。*例如乌桓、鲜卑主要通过向中原输出上好的动物皮毛,换取绢帛、米粮、金属工具和铁等物;匈奴牧民多驱赶牛羊到汉边境交易。阴山—河套地区以及燕山—滦河上游、大小凌河流域地带近邻发达的中原农耕地区,便于牧民通过贸易或当贸易受阻时采取掠夺手段从中原获取生活所需之物。而处于合黎山、龙首山与祁连山之间的河西走廊为东西交通和商业贸易之咽喉,便于牧民获取所需物资,补给生活。如唐在朔方军西受降城(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乌加河北岸)专门设置了“互市”,供双方进行交易。唐朝每年有数十万匹缯采输往突厥,而突厥也有相当数量的马匹卖给唐朝。绢布缯采与马匹之间的交易,在当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中原王朝还对边地的贸易制定了正式的相关法令:“诸外蕃与缘边互市,皆令互市官司检校。其市四面穿堑及立篱院,遣人守门。市易之日卯后,各将货物畜产,俱赴市所,官司先与蕃人对定物价,然后交易。”*参见仁井田陞:《唐令拾遗》715-716页,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这条《关市令》是据《白氏六帖》复原的。
与漠北草原游牧民相比,生活在东北大小凌河—西辽河流域的诸族部落更倚重狩猎。野马、原羊、角端牛及貂、豺、鼲子等动物皮毛是其特产*《后汉书·鲜卑传》:“又禽兽异于中国者,野马、原羊、角端牛,以角为弓,俗谓之角端弓者。又有貂、豺、鼲子,皮毛柔蝡,故天下以为名裘。”,为游牧民冬季御寒及日常贸易所需*《后汉书·乌桓传》:“乌桓自为冒顿所破,众遂孤弱,常臣服匈奴,岁输牛马羊皮,过时不具,辄没其妻子。”可见除了一些珍稀动物皮毛,牛马羊皮也常输入漠北地区。,对于漠北游牧民有着特殊的经济价值,同时也用来与中原地区或漠北游牧部落交易。如奚的牧地南端与中原农耕地区相接,他们以进贡的方式,向中原王朝赠送名马、动物皮毛,还在边地与中原进行贸易,换回自己所需要的生产、生活用品。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市)就是当时一个重要的经济贸易中心。
在农耕区与游牧区之间,存在着一条东西向的商贸通道,如擅长经商的粟特人就是活跃于这条商道上的著名商人。他们组成商队,长途贩运。*关于粟特人的商业贸易,具体参见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游牧族正可通过控制这条商贸通道,从中获利。因此,这一带对于北方游牧部族部落的经济价值,不仅仅在于适于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还在于南边有可供贸易或掠夺的农耕地区。
三、游牧经济与地理气候
就自然条件而言,蒙古高原及其周边地区是一个大的游牧经济生态圈。在这个生态圈内,有游牧经济所必需的广大草原,它的广度足以在不同季节提供牧畜所需水、草等资源;还有可供游牧民狩猎与获取制作车具、穹庐、弓矢之木材,且能在冬季得到水、草资源及避风寒场所的有森林的山区,以及可得到游牧经济所缺乏的外来资源的边缘地带。
牧民在蒙古高原的游牧方式依地形、水源、牧草情况有所不同,总的来说是高低纬度之间南北向的移动[35](P47),即夏天往北,冬天往南。在山区又可见夏季往高山而冬季向低谷的垂直迁徙,及夏季在河湖边,冬季转往山麓的游牧。如此,游牧民随季节更替往来于春(冬)、夏(秋)牧场。牧民通常在每年的4、5月份由冬牧场开始向北迁移,7、8月到夏牧场,从9月开始逐渐向南移,最后回到冬牧场。春季是牲畜体弱和接春羔时期,春(冬)牧场多选在向阳开阔、植物萌发早,且有当日或隔日饮水条件的地方,多选在放牧圈内最暖的地方即最南端,同时又是降雪最少,向阳背风,靠近定居点的地方。夏牧场多选地势高爽、通风防蚊,接近水源,牧草丰富的地方,一般处于放牧圈最北端;秋牧场往往选在开阔的川地或滩地。牧民不仅随季节转换牧场,还根据草场与牲畜状况,在每一季牧场驻牧期间做多次迁移,在满足牲畜对草、对水的需求的同时,保护牧草资源的再生能力,保持自然生态平衡。[36](P94-95)牧民这种随季节转换牧场的迁移活动基本上是在相对固定的区域内进行[37](P100-103),即草原游牧部族部落都有各自相对稳定的牧场和活动空间。史籍中关于柔然“冬则徙度漠南,夏则还居漠北”[38](P103),对诸族部落“逐水草迁徙”*参见《史记·匈奴列传》《后汉书·乌桓传》《魏书·序纪》《周书·突厥传》《隋书·铁勒传》《旧唐书·回鹘传》。,“然亦各有分地”[39](P2879)的记载,都形象地反映了古代北方游牧部族部落因时而动的经济生活形态。
在诸族部落这种随寒暑季节变化南来北往的游牧圈中,燕山、阴山—大青山及合黎山、龙首山山地位于最南端,为游牧民提供了避风寒、度过牲畜羸弱期的春冬牧场。匈奴兴盛时期,其势力南越阴山及于鄂尔多斯地区,东南抵燕山—滦河上游以及大小凌河流域*从公元前119年西汉夺得匈奴左地,招徕乌桓迁居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之地,可知此前这一带为匈奴据有。,西南逾合黎山、马鬃山,至河西走廊—祁连山地带。匈奴诸部落在漠北的分布是“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穢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史记·匈奴列传》)*汉上谷郡为今河北省怀来县,上郡在今陕西省榆林县,代郡在河北省蔚县一带,云中郡为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月氏分布于东起今祁连山以北,西抵天山、阿尔泰山东麓的地带,氐居甘肃陇南地区及周边地带,羌分布于今青海东南部及甘肃甘南等地。不久,匈奴攻打月氏,使之西迁伊犁河、楚河流域,而占有月氏故地。,即以左贤王为首的匈奴诸左方王及将领居汉上谷郡以东至穢貉、朝鲜以北的地区,以右贤王为首的匈奴诸右方王居上郡以西的地区,单于驻牧地居中,在代﹑云中郡以北之地。诸部落季节性的游牧生产,应是按这一区域划分进行。匈奴单于在漠北鄂尔浑河流域设北庭[40](P23),在漠南大青山脉迤南置南庭[41](P88-91),即是顺应蒙古高原夏北而冬南游牧的生产、生活需求而为。单于南庭北依大青山,临黄河,踞拥河南可牧之地,可谓春冬驻牧御寒之佳地。左、右贤王亦应如单于,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设有南庭(《史记·匈奴列传》)*西汉在河南之役后,发动河西、漠北之战,夺得河西地区和匈奴左地,史称“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由此知,匈奴除了单于,其他诸王在漠南也设有王庭。,为冬季驻跸之所。此外,鲜卑檀石槐三分领地,在漠南弹汗山歠仇水建王庭,复兴后之突厥骨咄禄—頡跌利施可汗在黑沙城(在今呼和浩特北面)设南牙[42](P60),无不与其南北迁徙的游牧经济生活有关。可以说,这是北方草原牧民循环往复、南迁北移游牧生产活动经济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结语
蒙古高原南缘阴山—河套地区、合黎山、龙首山—河西走廊—祁连山以及燕山—滦河上游及大小凌河流域一带,既处在游牧区的南端,又处在农耕圈的最北端;既适于游牧,又便于游牧民从中原农耕地区及河西走廊商贸通道获得生活所需的定居社会产品。因此,在不同时期北方游牧诸族部落强大时鼎力相争、衰微时情愿投附中原王朝而迁入的,都是这一地区。 漠北游牧民族可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方才迁出,但若无迁往地适于其生存、生活的环境,其南迁便会没了着落。中原地区富庶、先进、发达的经济生活及其相关政策,也只有在这一前提之下,才会对游牧民的南迁活动产生影响。
[1] 达力扎布编著:《蒙古史纲要》,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2] 萧启庆:《北亚游牧民族南侵各种原因的检讨》,载《食货月刊》复刊第1卷第12期,1972。
[3] 王铭珂:《游牧者的抉择》,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 青格力:《十七世纪卫拉特南迁原因再探讨——兼论游牧社会“集中与分散”机制》,载余太山、李锦绣主编:《欧亚学刊》,第10辑,北京,中华书局,2012。
[5] 余太山:《匈奴的崛起》,载余太山、李锦绣主编:《欧亚学刊》,第5辑,北京,中华书局,2005。
[6][9][11][20] 王钟翰:《中国民族史》(上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7] 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8] 林干:《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简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
[10][17] 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2]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
[13] 周伟洲:《中世纪西北民族关系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4] 周伟洲:《西北民族史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15] 周伟洲:《敕勒与柔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6][38] 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18] 朱大渭:《北朝历代建置长城及其军事战略地位》,载《中国史研究》,2006(1)。
[19][21][29] 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2] 马长寿:《北狄与匈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3] 华涛:《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4] 杨圣敏:《回纥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5] 贾衣肯:《汉唐时期中国北方游牧部族迁徙活动的方向和目的地》,载余太山、李锦绣主编:《欧亚学刊》,第9辑,北京,中华书局,2009。
[26] 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
[27] 田继周:《中国历代民族史:先秦民族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28] 魏征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
[30][33]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31] 刘昫编:《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32] 王宪宗、王传胜:《 〈汉书·匈奴传〉“斗入汉地”考》,载《丝绸之路》,1994(6)。
[34][39]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35] Anatoly M.Khazanov.NomadsandtheOutsideWorld.W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4.
[36][37] 韩茂莉:《历史时期草原民族游牧方式初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4)。
[40][42] 马长寿:《突厥人与突厥汗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1] 黄文弼:《前汉匈奴单于庭考》,载林斡编:《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北京,中华书局,1983。
(责任编辑 张 静)
The Economic Geographical Cause on Northern Nomads’ Southward Migration in Han-Tang Periods
JIA Yi-ken
(Institute of Histor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Beijing 100732)
Northern nomadic tribes in the Han and Tang periods mostly moved to the Yinshan-Hetao region,the Heli Mountain,Longshou Mountain,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shan-Luanhe areas and the Large and Little Linghe River basic areas,which was the southern margin of nomadic economic ecosystem of Mogolian Plateau,where they set up their winter camps during their seasonal migration.The grassland,mountains and rivers here in the region provided ground for the nomadic production activities of the northern nomadic tribes.The natural conditions,neighbor farming area and trade routes were convenient for nomads to get grains or other daily necessities.These economic geographical elements played a key role on the nomads’ southward migration.
northern nomadic tribes;southward migration;economic geographical elements;the nomadic economic ecosystem
贾衣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