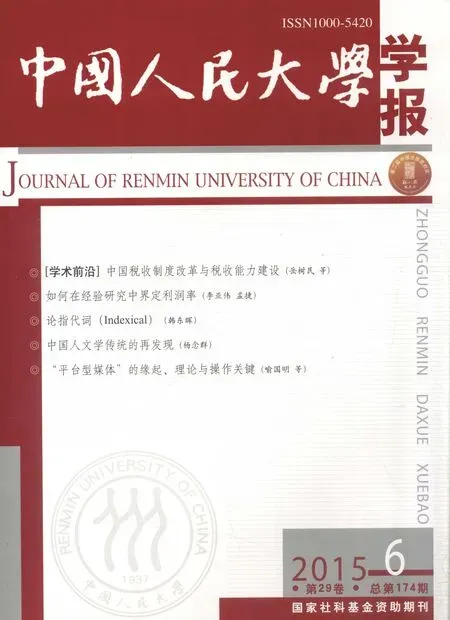法典化的智慧*
——波塔利斯、法哲学与中国民法法典化
石佳友
法典化的智慧*
——波塔利斯、法哲学与中国民法法典化
石佳友
民法典是“良法”和“善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立法先行的关键是提高立法质量。就此而言,波塔利斯的法典化思想中的许多内容对于今天中国的民法典制定具有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法典的民族性强调法律必须适应它所针对的人民的特征、习惯和情况,必须尽可能地保留民族的法律传统。家庭是民法典的支柱之一,立法者对家庭制度的极端重要性必须具有足够的敏感性。法典的开放性要求立法者避免预见一切和规定一切的企图,保持对判例、学理、习惯等其他法律渊源的开放性。而法典的实用性要求行文上采取清晰、简洁和易懂的文风,对科学性和逻辑性的过分追求可能损害法典的生命力。法典体现着智慧、正义和理性,法典化的智慧尤其表现为对过度的避免和立法的谦卑与节制,明确立法权力的边界。在立足中国实际并借鉴比较法经验的前提下,未来的民法典将可能是法治中国所能“给予和接收的最伟大财富”。
波塔利斯;法典化;民族性;开放性;节制精神
中国民事领域的法典化工程如今进入到一个十分关键的阶段:在法典化进程启动近二十年后,立法机关成功地制定了《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一大批民事法律;但人格权、民法总则等重要法律仍然付之阙如。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未来的民事立法工作注入了新的动力,并指明了其方向与出路:“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2015年5月和7月,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组织起草了“民法典总则”和“民法典人格权编”的专家建议稿。这些都标志着中国民法典编纂工作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为了编纂一部高质量的民法典,我们有必要充分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尽管我国立法和法学研究历来注重对比较法的借鉴,然而,这些借鉴主要是教义学意义上的,侧重于对国外具体制度的比较;而从法哲学层面在整体上对国外法典化思想的参考,是比较稀少的。随着我国法典化进程的加快,对比较法的借鉴参考显得尤其必要。就此而言,法国民法典的核心起草人波塔利斯关于民法典的法哲学思想,就是我们当下推进法典化事业十分宝贵的思想财富。波塔利斯关于民法法典化的法哲学思想,集中体现于其在民法典草案审议过程中的数篇演讲中,尤其是其于1801年所发表的《关于民法典草案的说明》。在立法史上,“这一声誉卓著的文本无论是在风格还是在内容上,都可以作为法典起草者对法典的主要原则导向、对其启示源泉的选择以及对民法在社会中的角色的概念等在理论上的正当性依据。”[1](P455)
在中国民法法典化事业进入到一个关键时刻的今天,重温波塔利斯两个世纪前的法典化思想的意义在于:其一,法国民法典被公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民法典,波塔利斯的演讲则集中宣告和阐述了现代民法最为基础的一般性原则。其二,尽管民法史上曾出现了多部伟大的民法典(如德国民法典)可以与法国民法典媲美,但是,“关于民法典草案的说明”在法律史上的地位却可谓空前绝后和独一无二,因为在法律史上不曾再有另一部对民法典精神进行系统的法哲学阐释的类似文献。其三,波塔利斯关于民法典的许多思想,是对孟德斯鸠等思想家学说的总结和提炼,具有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意义,在今天看来,其中的许多内容仍然具有浓郁的现代气息,因为它“包含了民事立法的一般性公理……在立法大量膨胀的今天,其中的许多思想仍然值得我们深思,许多建议值得认真去倾听和采纳。”[2](P106)
一、民法典与法律传统
立法必须顺应社会的演进,预测社会的需求,并适度超前于社会的发展:立法既不是革命性的颠覆,也不是一成不变,但立法必须尊重传统。孟德斯鸠曾生动地这样形容:“有些时候我们确有必要修改某些法律,但这种情形很少。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只能以颤抖的手去触碰它。”[3](P129)这就是说,法律当然可以修改,但其修改应当经过深思熟虑,绝不可轻率地修正或者废除已有的法律。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的著名论断是:人受气候、宗教、法律、施政的准则、先例、习俗、风尚等多种因素的支配,其结果是由此而形成了普遍精神。只要民族精神与整体原则不相违背,立法者就应该尊重这种民族精神;民族的习俗和风尚与他们的法律关系密切。所以,法律应当量身定做,适合于它所要适用的民族,只有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一个民族的法律才可能适合于另一个民族。只要民族精神与政体原则不相违背,立法者就应当尊重这种民族精神,因为“只有当我们自由自在地依照天赋秉性行事时,才能做得最好”。[4](P15、357、373)这就是说,不可将人置于某种抽象的环境之中,不要去追求法律形而上学的完美,要从整体角度看待人性,尤其要注意到每个民族的独特性,注意气候、地理环境和种族等的影响,尊重本民族的特性。这与今天所说的法的“地方性”特征是一致的。孟德斯鸠的研究也被视为政治人类学和法律人类学的肇端,具有浓厚的启蒙思想的特质。从这样的视角出发,立法者必须了解民法典所要服务的“民族的风俗、特征、政治与宗教形势”,应当“评估在每一种情形下,在每一个地区中,决定公理应当多元地适用于每一个民族、由此应制定不同法律的特殊的物质上和道德上的原因”。由此,好的法典起草者“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主义者,而是一个民族学家或者人类学家”。[5](P87)
受这样的思想影响,波塔利斯富有哲理地告诫说:“切不可忘记的是,法为人而立,而非人为法而生;法律必须适应它所针对的人民的特征、习惯和情况……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最好的法律是最适合于该民族的法律。由此,不可能为不同的民族制定同一部法律,也不可能将所有的人民改造为同一个民族。”[6](P23)因此,法典化必须基于“民族的风俗、人情和条件”而进行,以使法典在未来成为“理性的典章”。显然,我们从波塔利斯身上可以看见孟德斯鸠“历史相对主义”的痕迹。所以,他认为:“有必要保留一切没有必要废除的东西,法律应当珍惜习俗,如果这些习俗不是陋习的话……只有在不革新是最糟糕的时候,才必须要变革。”[7](P17、20)此点与历史法学派有共通之处,二者均强调法律形成的历史维度。但是,与萨维尼不同的是,波塔利斯强调立法者的介入,在有必要进行改革的时候,他仍然认为立法必须进行必要的变革,这种意志主义哲学显然比历史法学派更为积极。正是由于对传统的尊重和对立法连续性的考虑,民法典的起草人在民法典中广泛保留了以前的习惯法的内容。
作为对传统的尊重的表现,法国民法典“实现了成文法与习惯法的折中,在所有可能的场合去协调它们的规则”。[8](P42)这种折中和协调具体表现为,法国民法典中的合同、债法制度、所有权与物权制度几乎都是源于罗马法,而家庭法、继承法则主要沿袭了原来的本土习惯法。做出此种选择的原因在于,起草人认为本土的习惯法与外来的罗马法之间更多的是补充关系而非竞争关系,前者适用于那些与各民族独特的风俗和习惯有密切关联的领域,而后者则适用于应由普适性原则和永恒的理性来调整的部门。正因为如此,有法律史学者形象地指出,“尽管按照起草者关于民法典结构的思路,民法典被分为三编;实际上,民法典只应该被分为两编,反映出自然法和实定法的并立”[9](P18),以分别对应于成文法和习惯法两个部分。
对自身传统的尊重及强调立法的民族性,这对于我国当前的民法典制定工作同样具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我国的立法和学理界一致认为,我们应起草一部具有中国特色、可以与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等伟大法典相媲美的中国民法典。“民法典必须体现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因为只有最民族化的民法典才是最有生命力的民法典”。[10](P49)也就是说,中国的民法典应反映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继承优良的中国法律传统,而决不能是外国民法典的简单翻版。根据法律社会学和法律人类学的研究,法律传统是“深刻植根于历史且由历史所决定的社会主体行为的整体,包括法律的性质,法律在社会以政治性方式组织的过程中的作用,组织法律体系的最好手段,或者法律制定、适用、学习、完善和思考的方式。法律传统的概念与法律体系和法律文化密切相关;它将法律体系置于文化的视野中”。[11](P47)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必然要求对中国民法传统进行总结、提炼和传承。
遗憾的是,我国很多民法学者存在着这样一种误解甚至偏见:中国不存在自身的民法传统[12](P1138),对于今天的民法典编纂来说,在传统中国的法律文化中没有可资借鉴的资源。理由在于:根据韦伯的法律理性理论,礼法合一的传统中国法律显然不是形式理性的法律。然而,作为法典化工程最终目标的民法典,无疑是形式理性的最高成就,法典法体系具有高度的恒常性和可预见性。因此,民法法典化的使命与性质,决定了其不可能取法于中国法律传统。这些误解和偏见的错误之处在于:一方面,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中存在着大量的民法资源,如物权制度、契约制度、家庭和继承法等,其中的部分制度甚至具有很强的现代性气息;另一方面,传统中国法律其实是超越了形式理性、实质理性的区分,而且同样具有很明显的形式主义理性,是恒常和可以预期的。[13](P181-183)
正是由于上述误解和偏见的存在,使得尊重和发扬传统的原则在我国立法中很难得到真正贯彻。以典权为例,它被公认为是中国传统民法“土生土长”的一项他物权制度,是传统中国为数不多的不动产物权之一。典权构造精妙,曾被国外学者类比为不动产质权或附买回权之买卖,或者被形容为“向作为一种担保制度的近代质权发展中的一种过渡形态”。[14](P294-295)但是,典权的内涵比这些西方制度更为丰富和精巧:出典人以出典不动产的租金来充抵典权人借款的利息的安排、回赎、绝卖、找贴等制度的设计,充分体现出务实、公平与智慧,并具有济弱等促进社会正义的功能;民间还发展出“值十当五”等规则;典权在精神上被认为更接近传统中国的“圣王之道”而非“霸王之道”,有利于实现社会正义。[15](P217)总之,从各个方面看,它完全符合上述关于法律传统的定义和特征。正因为如此,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中没有规定典权,被后来的学者批评为“不明我国习惯,贸然起草,自难免闭户造车之讥也”。这一疏漏后来在1929-1931年《“中华民国”民法》(第911-927 条)中被弥补。这说明立法者“在参酌外国法律趋附民法潮流的同时,并没有忽略中国的民法传统”。[16](P226)新中国成立后,最高人民法院也曾就典权问题颁发了数个司法解释。
然而,这一在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物权制度,在2007年《物权法》的文本中并没有出现。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些学者从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出发,认为典权在现代社会中没有实际效用,已然“没落”。[17](P113)这一看法的错误在于,台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与大陆差异巨大,“典权没落”这一论断如果有些许道理,也只能适用于大陆地区某些一线城市,因为这些城市中由于近年来房价的高涨,不动产的租金远高于借款利息,以房屋出典来借款的情形在城市中自然很少出现;而且城市私有房屋可以有抵押等融资渠道,自无出典之必要。而反观农村,农民的宅基地不允许自由转让,地上所建房屋也无法向银行进行抵押融资,且农村的房租低廉,因此,以房屋出典来借款融资,自然有存在的合理性。尤其需要看到的是,随着农村承包经营土地流转制度的发展,典权未来所适用的对象将从房屋重新回归为土地,出典完全可以成为农地流转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典权制度在农村将大有作为。《物权法》最终将典权排斥在外,“并不代表典制从此将在我国的社会经济的舞台上销声匿迹”。[18](P101)成文法对脱胎于长期习惯法中的制度的排斥,也折射出立法者对于传统和历史的价值缺乏必要的敏感性。
二、家庭在民法典中的地位
孟德斯鸠曾形象地说:“一个美好的家庭是暴风雨中一只笃定的方舟,它由两个锚所固定:宗教与习俗。”[19](P145)在波塔利斯心目中,家庭在民法典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说:“什么是民法典?它是指导和确定属于同一地域范围内的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家庭和利益关系的法律的集合。”[20](P92)尽管从形式上看,法国民法典中并未为家庭法设定单独一编,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波塔利斯对家庭法的高度重视。他认为家庭与所有权共同构成民法典的两大支柱,因为家庭法旨在指导和确立社会关系:“家庭由婚姻所组成,它是国家的苗圃……家庭存在于基督教创立之前,早于一切实定法,它既非一项民事行为,亦非一项宗教行为,而是一项自然的行为,立法者为之倾注了注意力,宗教将其奉为圣洁。”[21](P18)无疑,社会的良好秩序取决于家庭的稳定,因为社会绝不是由孤立和分散的个人所组成,而是所有家庭的集合;家庭同样是独特的小社会,这些小社会的集合就组成了国家,这一大家庭包容了所有这些小的家庭。“家庭是良好品性的圣殿:正是在其中,私德逐步培养为公德。”[22](P103、104)波塔利斯借用了卢梭在《爱弥儿》中的措辞,家庭是一个“小小的国家”:“只有美好的私德才能保证美好的公德;正是通过家庭这个小小的国家,人们才爱上这个伟大的国家;正是家庭所培养的良家父、好丈夫和好儿子,我们才得以造就好公民。”[23](P43)尽管囿于时代的局限,波塔利斯在家庭上持一种威权主义、机械主义和悲观主义的保守看法,主张家庭以夫权和父权为中心,但他对家庭制度的政治意义有着充分的认识:“我们的目标在于将品性与法律相关联,传播家庭的精神——无论人们怎么说,它是如此有利于国家的精神……社会的持久和良好秩序极大地取决于家庭的稳定,它是一切社会的肇端、国家的胚胎和基础。”[24](P25、28)这就是说,家庭的精神在于培养美好的私德,而家庭立足的基石在于家庭团结,这是社会团结和国家稳定的前提。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家庭历来被赋予特殊的重要性。例如,儒家文化特别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意思是说:把自身修炼好,就可以把家管理好;把家管理好了,就可以出来治理国家乃至天下。正是基于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习近平主席强调指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25]他关于“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的论述,在当代中国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国家发展和社会秩序和谐的基础,就是和睦团结的家庭。正因为如此,我国《宪法》第49条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可见,宪法为国家设定了保护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的义务,如果立法未尽到这些保护性义务,则构成国家对保护义务的违反。
从这些角度来反观我国有关的婚姻立法和司法解释,令人忧虑的是,起草者们有时候缺乏对于家庭制度重要性的必要敏感性。以引起广泛社会争议、带来巨大观念冲击的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为例,这一司法解释所触及的是婚姻财产制度这一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基本民事制度。首先,婚姻财产制度这一基本制度其实只应由法律来加以调整,不应以司法解释去规定,因为基于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分工,司法解释只针对“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第2条)。其次,该司法解释为了与《物权法》不动产登记制度之间实现“体系协调”,硬性在婚姻法领域适用《物权法》的规定。这一做法的问题在于,家庭法与作为财产法的物权法同样是民法典的支柱,地位相同,并不存在谁贯彻谁的问题,作为非财产法的《婚姻法》本来就没有必要与作为财产法的《物权法》保持“体系协调”或者“接轨”。[26](P6)第三,《物权法》第8条规定:“其他相关法律对物权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因此,就婚姻财产制度而言,《婚姻法》作为物权法的特别法,完全可以做出例外性规定;相应地,物权法“在家庭财产关系面前应当保持一定的谦抑和理性,对婚姻家庭法在调整家庭财产关系过程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给予尊重和谦让”。[27](P87)
由此,不难理解该司法解释何以为许多人所诟病。根据其第10条,如夫妻一方婚前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后贷款购房,房屋仅登记其一人为产权人,但房屋贷款在婚后由双方共同偿还,则离婚时如协商不成,“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这一规定的问题在于,在城市甚至许多农村地区,如恋爱双方在婚前购买婚房,实践中的习惯多是这样:在双方家长的支持下,男方出首付款购房、女方出资装修和买家具作为嫁妆,婚房通常登记在男方名下,但婚后双方共同还贷。然而,婚后房屋在不断升值,而装修和家具则由于使用而不断贬值。按照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如离婚则房屋只能判归男方所有,对女方只做适当的货币补偿。这一做法确实对女方有失公平。因为不容否认的是,非登记一方参与房屋价金的支付、参与共同还贷、为婚姻住宅的保值增值的实质性贡献等,都是对房屋的重要贡献;而该司法解释却“把非产权方配偶的参与共同还贷以及共同出资仅仅界定为一种‘借贷’行为,这种理解不仅没有尊重既成的婚姻生活规律,有违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而且抹杀了婚姻作为伦理共同体的特性,否定了夫妻通力合作的价值,使得美好的婚姻沦落为冷冰冰的契约关系”。[28](P130)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得婚姻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充满利益的衡量和算计,进而导致婚姻赖以立足的基石——信任关系——被摧毁,最终损害家庭团结这一极其重要的基本原则。司法解释出现上述偏差的原因,是由于作为司法解释起草者的法官们对婚姻财产制度的极端重要性缺乏深刻的认识,以一种纯粹的“技术理性”去处理这一具有基础性意义的民事基本制度。
三、民法典与其他法律渊源
民法典的开放性,主要表现在对法典之外的其他法律渊源的开放性,这些法律渊源主要有判例、习惯、学理、道德和宗教等。因此,强调法典的开放性,必须反对成文法(法典)中心主义,成文法并非法律的唯一表现形式。波塔利斯深知法典本身的局限性,认为“许多的事项必然交由习俗来调整、交由有知识的专家来讨论、交由法官来裁断”。在波塔利斯看来,成文法在双重意义上存在着不足:一方面,成文法必然是不完备的,因为立法者无法预见一切。他指出:“社会的需要是如此的多变,人们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的积极,他们的利益是如此的多样,他们的关系是如此的宽广,以至于立法者不可能预见一切……如何能控制时间的流逝?如何能阻止事件的发展或习俗的悄然演变?如何能事先知晓和计算唯有靠经验才能告诉我们的那些东西?预见力的范围能够扩展至那些思想所无法企及的事务么?”[29](P6)所以,民法典必然是“成文法与习惯法的折中”。波塔利斯认为,只有很少的事情可以由一部有确定内容的法律来决定,大部分争端都是基于一般原则、学理和法律科学而予以解决的;民法典不但不能离开这些知识,相反,还需要它们作为补充 。因此,一部法典不能被视为“以先知的方式”为其民族预告了全部永恒的真理,所体现的仅是最高的社会权威。法典必须规定一个社会在漫长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习俗和惯例。法律应与时俱进,随着社会习俗的演进而不断动态发展。
另一方面,成文法在颁行以后也必然面临很快过时的问题。波塔利斯认为,一部法典,无论看上去有多么完备,自其颁布伊始,就会有数以千计未曾预料到的新问题摆在法官面前。法律制定之后就一直保持其最初的形式,而人的活动却一刻也不会停止。这些变动不居的行动不断地产生新的问题和新的结果。动态的社会演进必然超越静态的法律条文,使之变得相对过时。由此,在波塔利斯看来,民法典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立法者本身的预见能力,而是取决于作为司法者的法官,因为“在有法律之前就已经有法官,法律无法预见法官日后可能碰到的所有情形”。故此,“要特别警惕规定一切和预见一切的危险企图”[30](P108),民法典必须引入判例作为补充,为法官留下弥补法典漏洞的可能性。必须明白的是,“民法典的精神也是对于法官的信任,和对判例有朝一日会成为几乎与法律同等地位的法律渊源的某种直觉”。[31](P46)他还认为,法律、道德和宗教之间应该结成“必要的联盟”,以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正是在这个意义,波塔利斯说出为后人所经常引用的著名论断:“我们所留下的空白由经验去相继填补,人民的法典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成形,严格说来,它们并不是被制定出来的!”[32](P108)
这对于当下中国的民事立法是需要反思的问题,因为我国的民事立法在开放性方面表现得十分不足。这种开放性的不足,首先表现为对其他法律渊源的严重压制甚至排斥。以《物权法》为例,第5条规定了极为严苛的物权法定原则,物权的种类和内容仅应由法律规定。此处的“法律”是否包含行政法规,尚且不无疑问,而从允许创设物权的法律渊源中明确加以排除的,则显然包含判例、习惯、法律一般原则、学说和当事人契约等渊源。然而,他物权特别是担保物权领域存在着大量的所谓非典型担保形式,并不会由于《物权法》没有规定而在实践中消亡。反之,由于融资的需要,这些非典型的担保形式会在体制外不断地发展和演化,将它们长期排除在《物权法》的调整和适用范围之外,其实并不利于法律安全。
以习惯为例,习惯之于民法典的重要性,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编纂历史就是极好的例证。波塔利斯承认法国民法典是“成文法和习惯法的折中”,习惯法几乎占据民法典的半壁江山。而在德国民法典起草的过程中,习惯同样深受起草者的重视。反观我国的民事立法,对习惯普遍表现出一种十分轻视的态度。以《物权法》为例,由于涉及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事项,习惯无疑是重要的法律渊源。然而,我国《物权法》却表现出对于习惯的排斥,《物权法》通篇仅有两个条文提及习惯(第85条相邻关系、第116条法定孳息的收取)。这无疑是让人十分费解的:很难想象以不动产为调整对象的用益物权体系中(如地役权),我们会不需要求助于习惯这一重要的法律渊源。至少对于物权法而言,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文法尽管是主要的法源,“但无法独立完成全方位的调整任务,在不同层面或程度上离不开非出自立法者的其他规范的协力”,这些补充性的法源包括有关政府机构的规定、民间习惯以及政策。[33](P135)故此,“基于中国民族结构的多元性、社会发展水平的多层次性、城乡的差异性和成文法固有的局限性,最合适的做法应当是确立民间习惯的补充渊源地位”。[34](P111)
四、民法典的行文风格
法典化的主要目标之一应该是法律的简化,法典应在一个内在一致的整体中规定简单的规范,而不是建构起一个理论体系。由于法国民法典的四名起草人均为法律实务家(律师),因此,他们对于法典的学理化倾向保持了警惕。由此,波塔利斯在1800年起草的民法典“序编”草案中曾规定“法律作出命令、许可或禁止”,以区别于法学理论。波塔利斯对此解释说:“我们认为,区分法学和立法是明智的……一切定义、教育、学说等,都属于法律科学的范畴;一切严格意义上的命令,都属于法律的范畴。”[35](P100)正是基于对立法和学理的区分,1800年法国民法典“序编”草案曾规定:“立法的第一效果是终结一切理论推演,就其所规定的事项提供确定性。”
强调法典的实用性的原因在于,法典的立法风格必须适应于它所服务的人民,因为法典的宗旨是保障法律安全。因此,法典结构和法典措辞的清晰性是法学家和普通人共同的信念,而非仅为法学家能理解。民法典的用语应当简单和通俗易懂,具有确定性、简洁性和清晰性。就此而言,我们仍然有必要回到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对立法者的谆谆教导:“法律的文风应该简约…… 法律的文风应该朴实,平铺直叙永远比拐弯抹角好……法律的用词要做到让所有的人都理解为相同的概念……法律不能让人难以捉摸,而应该能为普通人所理解。法律不是高深的逻辑艺术,而是一位良家父的简单道理。”[36](P693-695)这就是说,法典中必须区分“那些有可能和必要向一切人解释清楚的东西和那些必须使用严谨用语的东西”。法律措辞“是某种特殊语言的独特应用”,它要使“公民和法学家喜欢最为平实和最为丰富的法律思想”。[37](P308)这无疑是受到了笛卡尔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法国民法典的用语具有哲学般的简洁、平实易懂的特点。惹尼认为这是1804年民法典在立法技术上最富有成就的特点,是法典的人文主义的最典型特征;著名作家司汤达尔也高度赞扬法国民法典是“艺术、辞辩和法律之母”。[38](P290)茨威格特和科茨在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比较后指出:“从文风和措辞来看,法国民法典是一部杰作。民法典由于其清晰和易于铭记的规定、没有交叉引用和俚语,常常被人所称颂,这些都极大地促成了民法典在法国深受民众欢迎。据说司汤达尔每天阅读民法典,以锤炼其文风;保罗·瓦莱里称民法典是法国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而相比之下,德国民法典晦涩枯燥和充满教义色彩的用语风格,就要逊色得多了。”他们还列举了数例,比如“契约应当信守”这一普遍性原则,在法国民法典中是著名的第1134条(“依法成立的契约,在当事人之间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而在德国民法典中则是第241条:“由于债权人—债务人关系的存在……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这里,“债权人—债务人关系”和“履行”显然是典型的教科书式表述。[39](P91-92)
此外,法典及其措辞的科学精神,与其对真理和数学般的精确性的追求相适应,但是,这一命题的背后想法其实是对法官自由裁量的限制。这显然不利于法典生命力的延续。由此,对于关注点不是“真理”而是“正义”的法典解释者来说,法律的科学精神应逐渐消退和让位于法典的实用性。正因为如此,基于保持法律的实用性,在普通法系中,“法律作为一个学科,从来没有取得科学的地位,它始终操之于法官和实务家之手”,因为高度科学精神的法典会导致“教义学式简约主义,损及法律的复杂性”。[40](P137)
在我国,立法起草的格局从过去的“行者主导、部门立法”发展为今天的“立法主导、学者参与”,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由于学者本身没有任何部门或者行业利益,立场超然和独立,所以学者们所起草的规则也更为公正和客观,没有利益上的倾向性。但是,必须看到,“学者立法”也有其局限性:受制于其所长期从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学者立法往往具有过分的理论偏好和教义学色彩,容易将法学理论与立法相混淆。我国许多立法的起草都十分强调科学性和体系性,而这常常导致立法措辞对普通民众来说晦涩难懂。例如,《物权法》中同时存在着“不发生效力”(第9条)、“不发生物权效力”(第20条、第31条)、“不影响合同效力”(第15条)等不同的表述,而一般公众显然难以理解这些表述其中的差别。再如,许多民事立法中大量使用“法律另有规定的”这一提法,而各法对此的处理却不尽相同。以《物权法》为例,有14个条文中存在着“法律另有规定的”的提法,但是,《物权法》有时候规定“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物权法》中有四处,《侵权责任法》第5条和第29条也是采用这一措辞),有时候却又规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物权法》中有十处),两种表述究竟有何区别?从效果来看,它们都是说明如特别法有例外规定的,应优先于作为普通法的《物权法》而适用。立法有意采取不同的措辞,是否意味着前者中特别法已经存在,而后者中的特别法尚未出现?这样差别化表述的意义令人费解。
立法措辞的模糊引人困惑,还有其他的实例。例如,《物权法》第107条规定:“所有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有权追回遗失物。该遗失物通过转让被他人占有的,权利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损害赔偿,或者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让人之日起二年内向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此条中,“或者”这一选择关系连词的使用令人困惑:在请求无权处分人损害赔偿与要求受让人返还原物之间,并非为选择关系,所有人只能择一行使,而应为并列关系,允许同时主张,因为处分人明知遗失物为他人所有却仍然转让,其主观显然为恶意,应承担赔偿责任。[41](P83)也就是说,所有人既可要求无权处分人赔偿损害,也可以要求受让人返还原物。
五、法典化的节制精神
波塔利斯说:“法律并不是纯粹充斥着强制力的律令,它浸透着智慧、正义和理性。”[42](P4)其实,这同样是源于孟德斯鸠。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写道:法律并非是纯粹只充斥着公权力的律令。[43](P363)首先,“智慧”是对经验的尊重,表现为一种务实主义的态度,不能盲目革新,必须反对教条主义;民法典不可能是与旧的法律传统完全决裂的革命性作品,所以波塔利斯说,民法典是成文法与习惯法两种法律传统相互折中和妥协的产物。其次,立法者的智慧也表现为对于简约与复杂辩证性关系的精妙掌握,法律应该尽可能的简单、清晰和精炼;对简单与复杂辩证关系的处理本身也体现出立法者的务实主义精神。
法典的“正义”则表现为对于源自于自然法的正义、公平等基本价值的永恒追求。孟德斯鸠曾精辟地指出:“法律并不必然是正义的,但正义者必成为法律。”[44](P27)受此启发,波塔利斯提醒说:“立法者的条文应当服从于自然法,如同法官的判决应当符合立法的要求一样。”[45](P15)切不可忘记的是,立法“并非是人手之作品,在一切的成文法之外还存在自然法,它源自于永恒的正义,人们不得违背之;它支配着一切的个人和民族、一切的民众和君主,后者的立法者不过是也只能是它的忠诚的代言者。没有了自然正义,法律就会变动无常、难以确定和主观臆断,也就没有了一般性的共同规则,这也就没有了良心和严格意义上的义务”。[46](P15)
而法典化的“理性”则表现为对于过度的避免和立法的谦卑与节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写下了广为引用的著名论断:“我这么认为——而且在我看来,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节制精神应当是立法者的精神……道德上的善和政治上的善一样,始终处于两极之间。”[47](P682)波塔利斯显然对此深为认同,他在演讲中直接引用了这一论断。在他看来,立法者的理性应该是避免过度行为。法典不能是抽象的理性建构,而是要适用于所有人的具体的规则。如果说大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主义是理想主义和教条主义,那么民法典的起草人显然与这样的思潮保持了距离,是相对主义者和务实主义者。[48](P39)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典的起草者如果意识到其所立法的作为空间和限制,必然采取某种节制精神。这种立法的节制与谦卑精神体现在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多个方面。例如,虽然法国民法典的起草人受到了18世纪诸多哲学、文学和艺术思潮的影响,但是,1804年民法典的起草人却与当时所盛行的浪漫主义保持了距离。浪漫主义发端于英国和德国,18世纪中期传入法国,以反理性、反启蒙、强调本能与情感为特点,在法国以夏多布里昂、雨果和巴尔扎克等为代表。尽管人文主义思潮使得法国的法律与文学之间一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影响,但法国民法典却并没有染上浪漫主义的色彩,民法典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是节制、分寸和自谦,这与浪漫主义精神正好相对立。[49](P16)
民法典所要求的这种智慧、正义和理性精神,是我们应当借鉴的。我国现行的一些民事立法,对于有关各方利益的保护并不均衡,欠缺足够的正义精神。例如,《物权法》第74条关于车位的规定,将车位的归属问题完全交由开发商和购房者以契约形式去解决(出售、附赠或者出租),实际上等于默许了车位归开发商所有和支配,因为无论是“出售、附赠或者出租”车位,其主体都只能是开发商。虽有“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的原则约束,但其缺乏确定性和实际效果。在这种语境下,购房者对车位显然不可能享有话语权,而只能听任开发商的处置。由于国家对于小区车位的配建比例并未出台全国统一标准,致使在许多城市的小区中,车位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稀缺状态。考虑到车位本身在地理位置上的不可替代性,无论是出租还是出售,其价格都基本上由开发商单独决定,购房人无法与其协商。这也使得一些开发商以极高的价格将小区车位拿出单独处分(出售或出租),而这显然损害了业主的利益,有违正义精神。恰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对于小区车库权属问题的解决不能完全奉行绝对的市场自由原则,为了平衡购房者与开发商之间的利益,需要加强立法干预。”[50](P78)现行立法的如此规定是造成近年来部分一线城市小区车位价格暴涨的重要原因。
再如,《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一款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然而,第5条却又规定:“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从立法精神上看,第5条与第2条之间显然是相互矛盾的:第2条要求对于侵权事故应尽可能适用《侵权责任法》,而第5条却承认某些特别法应优先适用。正因为如此,《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完全赔偿”原则,对于许多损害事故却无法适用,因为它们实行“限制赔偿”原则。例如,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规定,对于铁路交通事故,应适用《铁路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而不应适用《侵权责任法》。同理,对于航空损害,也无法适用《侵权责任法》,而应适用《民用航空法》和有关的行政法规或规章。恰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侵权责任法》既不能代替原有的零散立法,也不能将它们有效地整合起来……法院等司法机关基本上还是应用那些独立的单行立法。”[51](P80)这显然限制了法律本身的适用范围,削弱了法律本身的价值,大大减损了法典化的意义,因为单行法外在于民法典大量衍生,是典型的“去法典化”。[52](P99)
立法节制和谦卑精神的欠缺,在我国同样不能忽视。波塔利斯指出,法律的使命是“高瞻远瞩地确定法律的一般公理,确定由此导出的、具有丰富内涵的原则,而不能降格为去规定每一事项所可能产生的问题的细节”。[53](P8)法典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起草者的“综合”能力和判断力所能达到的高度,换言之,“构想的艺术、摄取本质的能力、涵盖其他的冲动,恰如立法的天赋会产生法律的特殊语体,法律的高度使其能以很少的语词表达许多的内容。由此,立法如同格言,简约原则既是智慧的产物,也是书写的规则”。[54](P7)从这个角度来说,要特别警惕由于过分立法所导致的立法膨胀,它将损害法典化的效果。孟德斯鸠说:“如同无用的法律削弱了必要的法律的效果一样,那些应该避免的法律也损害了立法的效果。”[55](P697)受此启发,波塔利斯说,“不可制定无用的法律,它们会损害那些必要的法律”;不可忘记的是,“管得太多就会管得太糟”。[56](P6)
就此而言,《合同法》第67条可以是一个反例。该法第66条已经规定了“同时履行抗辩权”,在双方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情况下,应当同时履行,因此,一方未履行的,对方可拒绝其履行要求。而随后的第67条规定的所谓“后履行抗辩权”,其实是多余和无用的。因为根据“举重以明轻”的法律解释规则,在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情况下,一方未履行,对方可拒绝其履行要求;那么,在存在着先后履行顺序的情况下,如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当然更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因此,即使声称“后履行抗辩权系我国合同法首创”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其“是从同时履行抗辩权中派生出来的一项制度”[57](P129-130),是完全可以通过法律解释手段推导出来的规则,没有必要以单独的条文在立法中另行规定,它的出现只能说明我国在法律解释理论和技术领域的不成熟。
毋庸置疑,波塔利斯所处的时代与当代的后现代社会已不可同日而语。法典化工程在今天所面临的是19世纪所不曾遇到的障碍。究其原因,古典法典化运动所赖以立足的四个基本的“范式”——法律单一主义、政治单一主义、演绎和线性理性以及漫长的时间性,如今都已发生了深刻的变革。[58](P304)但是,今天重读波塔利斯的法典化思想,我们从中仍然能获得许多富有教益的启示,因为其思想远比人们所想象的更为复杂,其中的很多方面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尤其是他关于民法典的许多精辟分析,“为民法典的荣耀树立了一座伟大的丰碑” 。[59](P459)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2014年《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重要论述:“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一部好的民法典,无疑是“良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民法之于善治和法治,意义攸关。早在两个半世纪以前,孟德斯鸠就如此精辟地指出了民法的价值:当公共机构需要某个个人的财产时,不应根据政治性法律来采取行动,这正是民法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在慈母般的眼里,民法视每一个个人如同整个国家。”[60](P580)作为民法典的起草者,波塔利斯以其一贯的哲学风格,对其凝聚着传统与时代智慧的杰作予以充满激情的礼赞:“好的民法是人类所可能给予和接受的最伟大财富”,因为民法“是善良风俗的来源、繁荣的守护神、公共秩序和个人秩序平和的保障……它是民族道德的来源,属于公民自由的组成部分”。[61](P4)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立足中国实际并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的前提下,未来的民法典将可能是法治中国所能“给予和接受的最伟大财富”!
[1] Jean-Louis Halpérin.“Jean-Etienne-Marie Portalis”.In Olivier Cayla & Jean-Louis Halpérin(dir.).DictionnairedesGrandesOeuvresjuridiques. Paris:Dalloz,2010.
[2][54] Gérard Cornu.Droitcivil,Introduction,Lespersonnes,Lesbiens. Paris:Montchrestien,2003.
[3] Charles-Louis Montesquieu.Lettrespersanes. Paris:Le Livre de Poche,2006.
[4][19][36][43][44][47][55][60]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5] François EWALD.“Rapport philosophique:une politique du droit”.InLivreduBicentenaire. Paris:Dalloz,2004.
[6][7][8][20][21][22][23][24][29][30][32][35][42][45][46][53][54][56][61] Portalis.“Discours préliminaire sur le projet de Code civil”.In Jean-Etienne-Marie Portalis,DiscoursetrapportssurleCodecivil,Centre de Philosophie politique et juridique,1989.
[9] Jean-Louis Thireau.“Fondements romains et fondements coutumiers du Code civil”.InDroits,Paris:PUF,2006(42).
[10] 赵万一:《中国民法典制定的应然与实然》,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3(1)。
[11] Antonio Gambaro.Rodolfo Sacco & Louis Vogel.Ledroitdel’Occidentetd’ailleurs. Paris:LGD,2011.
[12] 茅少伟:《寻找新民法典:“三思”而后行——民法典的价值、格局与体系再思考》,载《中外法学》,2013(6)。
[13] 黄宗智:《清代以来民事法律的表达与实践:历史、理论与现实》,卷二,载《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14] 岸本美绪:《明清契约文书》,载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15] 黄宗智:《清代以来民事法律的表达与实践:历史、理论与现实》,卷三,载《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16] 李秀清、何勤华:《外国法与中国法——20世纪中国移植外国法反思》,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17] 徐洁:《典权存废之我见》,载《法学》,2007(4)。
[18] 张翔:《论典制习惯及其在成文民法上的重构》,载《法律科学》,2008(1)。
[25] 习近平:《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5-02-18。
[26] 杨大文:《略论婚姻财产关系法律调整的价值取向——由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引起的社会反响谈起》,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1(6)。
[27] 赵敏:《谦抑语境下家庭财产关系的物权法适用——以〈物权法〉与〈婚姻法〉的对接为切入点》,载《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
[28] 田韶华:《婚姻住宅上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法律保护——兼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的涉房条款》,载《法学》,2011(12)。
[31] Pierre-Yves Gautier.“Pour le rétablissement du Livre préliminaire du Code civil”.InDroits. Paris:PUF,2005(41).
[33] 常鹏翱:《多元的物权法源及其适用规律》,载《法学研究》,2014(4)。
[34] 尹凤桐:《论民事习惯法与民法典的关系》,载《山东社会科学》,2009(9)。
[37] Stéphane Guy.“La codification:une utopie?”.In Revuefrançaisededroitconstitutionnel. Paris:PUF,1996(26).
[38] Frédéric Audren & Jean-Louis Halpérin.Laculturejuridiquefrançaise,entremythesetréalités,XIXe-XXesiècle. Paris:CNRS Editions,2013.
[39] K.Zweigert & H.Kötz.Anintroductiontocomparativelaw.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40] Geoffrey Samuel.“L’esprit de non-codification:le Common Law face au Code Napoléon”.InDroits. Paris:PUF,2005(41).
[41] 鲁叔媛:《我国遗失物拾得制度之完善》,载《政治与法律》,2009(9)。
[48] Pierre Serrand.“La loi dans la pensée des rédacteurs du Code civil”.InDroits. Paris:PUF,2005(42).
[49] Philippe Malaurie.“Le Code Napoléon et le romantisme”.InDroits. Paris:PUF,2005(41).
[50] 张忠野:《车位、车库权属制度比较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3(12)。
[51] 孙宪忠:《防止立法碎片化、尽快出台民法典》,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3(1)。
[52] 谢鸿飞:《民法典与特别民法关系的建构》,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2)。
[57] 李虎、张新:《主从给付义务关系可以产生后履行抗辩权》,载《法学》,2007(8)。
[58] Yves Cartuyvels & François Ost.Criseduliensocialetcrisedutempsjuridique. Bruxelles:Fondation Roi Baudouin,1998.
[59] Rémy Cabrillaco,Lescodifications.Paris: PUF, 2002.
(责任编辑 李 理)
The Wisdom of Codification——Portalis,Philosophy of Law and the Chinese Codification of Civil Law
SHI Jia-you
(School of Law,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The civil code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rule of law”and“good governance”.The key issue of codification lies i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gislative quality.It’s of instructive significance for us to review the thoughts of Portalis on codification,as many of them are quite relevant for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codification project.The cultural nationality of the civil code implies that it must comply with the traits and habits of the people and preserve the legal tradition as much as possible.The family is one of the pillars of the civil code,the legislators should therefore be fully aware of its importance to the society.The openness of the civil code means that it is open to other sources,especially the case-law,doctrine and customs.The practicality of the civil code entails the clear,concise and intelligible style of its provisions.The excessive emphasis on the scientific and logic character of the code will compromise the vitality of the code.The codification embodies wisdom,justice and reason,which in particular implies the spirit of moderation and the avoidance of the excess.Consequently,it’s of importance to define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legislative acts.Based on the Chinese reality and reference to the comparative law,the future Chinese civil code could be “the greatest asset” given and receiv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Portalis;codification;nationality;openness;moderation
石佳友: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北京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