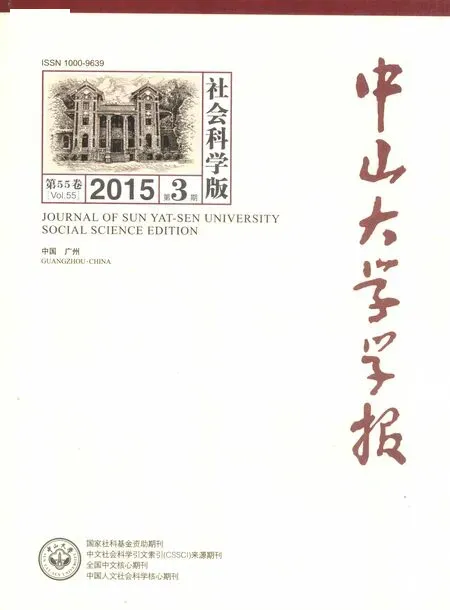“心学真宗”:论万历时期的王学与佛教之关系*
王 格
“心学真宗”:论万历时期的王学与佛教之关系*
王 格
明万历时期,王学处于鼎盛状态,佛教宗风亦自此重振。这固然是心学思想的内在诉求和导向,而明代官方意识形态的基础性作用更不可忽视。这一时期有两种具有代表意义的编撰文献:佛教居士周梦秀所编《知儒编》,用以证明“学佛可以知儒”;王学士人周汝登所编《佛法正轮》,用以证明心学统三教、儒佛不二。这两种文献因为流传原因在以往研究中未引起足够重视,但由此切入可以考察其中最重要的儒佛关系观念,进而考察当时“心学杂禅”的指责以及王学士人对此的回应。总体来说,王学影响的扩大实际上促进了宗门重振运动,促进了民间信仰和劝善活动的流行,同时使得儒家自身矩矱亦变得模糊,因此难免引起不同教派各方面不同的反应。
王学; 佛教; 心学
清代四库馆臣曾说: “盖心学盛行之时,无不讲三教归一者也。”①*[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24页。宗教的“综摄”(又称“融合主义”,Syncretism)主张带来的一致论,或者扩大地说,与之相关的一些“异同”问题之争论与比较,其实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同宗教和思想文化的交流对话过程中一个必然存在的组成部分。在中国佛教史上,大概自佛法初传中土便已存在,例如《牟子理惑论》。“三教论衡”则成为自北朝后期、唐代以至宋初一项重要的官方乃至宫廷论题;与此相应,民间文化方面则结合诸多民间信仰,从仪式到思想上都日趋融合。可是,宗教史上的问题永远充满各种复杂多面的社会和政治面向,需要我们立体多维度地去考察和把捉。
一、“真乘之教与王法并行”的思想史背景
首先,与“三教合一”主张紧密联系的,其实是“异端”与“正道”的问题。“异端”一词在儒学史上的使用,可以上溯到孔子说的“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2·16),但是其确切意旨似难以彻明②*在“三教合一”的思想背景下,对于《论语》此句,王学学者周汝登采纳了一种特别牵强附会的解释:“孟子以仁、义、礼、智为四端,反此者为异。”见其《四书宗旨》,萧天石辑:《中国子学名著集成》第20册,台北:中国子学名著集成编印基金会印行,1978年,第304页。。孟子则有大举“辟杨、墨”的宣言,甚至称“杨、墨之道不息, 孔子之道不著”(《孟子·滕文公下》6·9),这可以视为早期儒者对异教的口诛笔伐。因此,朱熹《论语集注》云:
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③*[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7页。
然而,秦汉以降的中国,其实并无杨、墨学派的真实传承,其道已息;宋明儒学中被指为“异端”的,一般是佛教与道教,这至少可以追溯到韩愈,因为韩愈继承孟子的激烈态度,曾说“佛、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因此更要努力辟佛,以期“全之于已坏之后”*[唐]韩愈:《与孟尚书书》,屈守元、常遇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352页。。除了少数的例外,宋代理学家们大都表示过充分认可韩愈这一论断,并认为,当世儒者肩上的任务,就应该像孟子辟杨、墨一样去大举批判佛、道二教。
可是,虽然宋明理学家们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辟佛”,但这也许只是出于一些忧道护教的儒家知识精英们的一厢情愿。因为与此同时,不论主张直接融贯的“三教合一”,还是主张三教功能分割、而最终归宗于“三教一致”的各种调合论主张,在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中有更为广泛的流行、接受和认同;何况,一些宋儒的排佛论本身即基于业已受到佛教影响这一思想史前提,并且也遭到了另外一些知识精英相应的反驳,其中包括有来自儒家内部的一些重要学者*[日]酒井忠夫著,刘岳兵等译:《中国善书研究》上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06—207页。。
有明一代,由太祖、成祖等所奠定的官方基调,即明确强调三教合流。其中,对于儒佛关系,有所谓“真乘之教与王法并行”。可是归根到底,正如酒井忠夫所归纳:“太祖的三教论其实就是以儒教为中心的儒释一致论,其出发点就是以儒教为中心,由儒佛仙三教共助王纲治理天下,并在此基础上实行三教一致政策。”这与宋代以来中国社会所流行的“三教鼎分合一思想”明显有所区别,而成为明代“三教合一”思想和行为所具有的官方政治正确性的基础*参看John D. Langlois, Jr. & Sun Ko-kuan: Three Teachings Syncretism and the Thought of Ming Tai-tsu,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3. 1(1983. 6), pp. 97—139.;朱鸿:《明太祖与僧道:兼论太祖的宗教政策》,《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8期,1990年6月;[日]酒井忠夫著,刘岳兵等译:《中国善书研究》上卷,第207—214页。。正是有了这一政治正确性的保障,杨起元才可以在大胆歌颂朱元璋的基础上,宣称佛、道二氏亦并为“正道”:
高皇帝至圣哉!以孔孟之学治世,而不废二氏也。二氏,在往代则为异端,在我明则为正道……大抵一统持于上,而皇极建矣,虽有好恶而不能害:此天纵高皇,为万古纲常教化之首君也!*[明]杨起元:《证学编》卷1《笔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90册,第281—282页。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这一“最高指示”的保障,“三教合一”也不太可能在明代中后期那样昌盛。
不过,另一方面,明太祖等奠定的诸多国家宗教政策,实际上是要加强国家对于宗教思想和意识形态等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整个明代前期三教几乎同时衰颓,甚至腐化、堕落的局面:这几乎是明代中晚期三教有识之士的共识,而教风重振运动也就几乎同时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参见[日]荒木见悟著、周贤博译:《近世中国佛教的曙光:云栖祩宏之研究》中文版序言,台北:慧明文化,2001年,第9—19页。。
在这样的双重背景之下,“三教合一”这一号召在明代中国既具有了充分的政治正确性,三教人士之间又具有时代任务和使命上的可比肩性,为了拯救现世人心的衰颓堕落,他们可谓志同而道合。因此,在明代中后期,伴随着儒、释、道三教的重振运动,“三教合一”成为了声势浩大的社会思想潮流。其中当然存在各种形态,根据蔡淑闵、魏月萍等学者的分析,在王学重要学者中,王畿、罗洪先、管志道、焦竑等不同学者的三教论皆呈现为诸多不尽相同的丰富形态,各家有自己独特的论述,其间亦不乏意见相左的争执*蔡淑闵分为“严明三教”“三教同道”和“三教合一”三类,见其《圣学的追寻与传播:阳明学派游学活动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年;魏月萍大致认可和继承了这一归类,见其《从“良知”到“孔矩”:论阳明后学“三教合一”观之衍变》,《中国哲学史》2008年第4期。不过,正如魏文的进一步分析所认为,对王学学者不同的三教观进行这样过于简单的分类,其实是很难恰如其分的。。虽然论述形态各异,在广泛的儒家群体中,最为主流的“三教合一”形态,恐怕必然仍是太祖朱元璋式的三教合一*比如,管志道就对太祖朱元璋的三教政策和指导思想大为满意和称颂,见《答吴侍御安节丈书》,《问辨牍》元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87册,第658—659页。。
事实上,学者们的研究已经充分证实,在王学中,王守仁、王畿等核心学者有关“三教合一”的相关论述皆坚守这一原则:王守仁“力图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将佛、道二教合理地容纳到儒家思想中”,王畿则是在“继承了这一基本精神方向的基础上”的“更为自觉和深入”*彭国翔:《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250—272、438—441页。。相对而言,虽然王艮及其家学涉佛并不明显,但泰州后学以罗汝芳、杨起元等为代表的学者则显得更肆无忌惮,其中不仅往往杂糅三教之思想与行为,更有诸多民间信仰之汇入*[日]酒井忠夫著、刘岳兵等译:《中国善书研究》上卷,第215—231页。。
二、万历时期“儒佛一心”的两种代表性编撰
精于观察儒佛互动关系的日本学者荒木见悟早已敏锐地注意到,在周汝登等人的王学编撰行为中存在有若干细微处,如《王门宗旨》卷3开头,作为“阳明语抄”之“奏疏”类的第一篇,就采用了王守仁《谏迎佛疏》一文*[明]周汝登:《王门宗旨》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942册,第314—317页;《王阳明全集》第2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12—315页,标题下注明“稿具未上”。。荒木在此看到了这篇上疏与以往韩愈《论佛骨表》等儒家辟佛文章之间存在有微妙的差别,并且注意到周汝登对该文有过高度赞扬*[日]荒木见悟:《周海门の思想》,氏著:《明代思想研究》,东京:创文社,1972年,第237—238页。就王守仁此疏而言,读者可以明显看到,王氏在此袭用《孟子》式的劝谏修辞,即顺势推本而最终达到劝谏的目的。其具体表现为:先从正面肯定皇帝“好佛”之心入手,推本其心,在文中三次提出强调“好佛之心”要“务得其实”和“务求其本”;因此,在疏文中,王守仁并没有批评佛教如何不好,反而说佛教很好,可只是尚不及儒家之道,特别是行之中国;在此,佛教不再视作与儒学之取向相悖离,不再有你死我活之“辟”;尽管王守仁似乎坚持儒、佛尚存高下之别,可是在价值和方向上,“儒佛一致”论的取向已经十分明确了。所以,《王门宗旨》的编撰者作为对佛教友好的儒者,自然要将这样文思并茂的文章收入*此外,尚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12卷本《周海门先生文录》第9卷为关涉佛教的内容,在周汝登的文集其他版本中无此一单独分卷,其中篇目并入相关卷帙中。。可是,在晚明儒佛会通大思潮中,这样零散的选编和评论显然是不够的。
(一)周梦秀的《知儒编》
事实上,早在万历四年(1576),周汝登从兄周梦秀就已编有《知儒编》一书*该书在台北“国家图书馆”有藏,为明崇祯九年(1636年)刊本。本文以下主要依据台湾法鼓佛教学院善本古籍数位化成果,网址:http://rarebook.ddbc.edu.tw/sutra/D60n9021_001.php。。该书的奇特在于,内容为禅语而书名曰“知儒”。作为被周汝登称为“苦行头陀”的虔诚居士佛教徒、又极力高唱“儒佛一致”论的周梦秀,在此声称其所要倡导的是张九成所标榜过的“学佛知儒”*不过,在历来僧史中,“学佛知儒”一语最有名的出处一般是北宋宰相居士张商英的《护法论》。。其自序交代:
编禅语也,而称“知儒”者何?语悉儒而禅者,张子韶谓“学佛知儒”,因有取乎其言。夫学佛,何以知儒也?程伯子云“《中庸》言‘无声无臭’,犹释氏言‘非黄非白’”者,是何物耶?……顾此在儒门未甚剖破,而禅宗家极力举扬,灯灯相绍,专明此事。故欲通儒脉,须借禅宗……余单取宰官居士所参证者,类作宰官居士之津梁……所谓“学佛知儒”,其或不谬者矣。嗟乎!问礼、问官,孔子犹从乎老氏;辞杨、辞墨,孟子不逮乎庄生……兹编之行,或通儒之所不废也。
如序文所示,《知儒编》中所选录文字,皆是“宰官居士”求教于僧人而进行佛教参证的典故,除开头有“波斯匿王”和“东印度国王”各一条外,其余大抵皆中土历代及不知名的国君、士大夫、文人等,其中当然包括张九成,也有张商英。周梦秀认为,经由这样的历史案例作为“津梁”,更能让“宰官居士”们明白张九成的“学佛知儒”说之不谬,其目的在于讽劝今世“宰官居士”们去学佛。因为在周梦秀看来,《知儒编》中所编,是历史上的“通儒”榜样,孔孟犹有所不及者;学佛可以知儒,前贤之迹既如此,今人舍此更何求?管志道称“空空子之辑《知儒编》,讽儒者之参禅也”*[明]管志道:《题〈知儒编〉》,《惕若斋集》卷3,明万历二十三年序刊本,日本内阁文库藏。,可谓深得其要。
可见,在佛教徒周梦秀那里,“儒佛一致”的背后恐怕仍是一种佛教本位主义。所谓“欲通儒脉,须借禅宗”,这里所谓的“学佛知儒”亦并非并列,而是学佛自然知儒。被黄宗羲称为“鸠合儒释”的管志道对此表示不能苟同。针对周梦秀的做法,管志道为儒学立场做了不遗余力的辩护。他不仅明确指出周梦秀该编中所选录“多禅者钳锤儒流之语”,而且称“夫参禅固可以知儒,而禅之蔽,亦不可不稽也”,借此对禅家流弊进行了深入稽查和剖析,并认为救此蔽者为程朱理学。面对晚明思想界“骎骎乎以狂风荡孔矩”,管志道认为“今日不难于知禅,而难于知儒;不难于稽儒之蔽,而难于稽禅之蔽”,“学佛知儒”的前提是要“脱尽禅门气息”*[明]管志道:《题〈知儒编〉》,《惕若斋集》卷3。。据冯梦祯日记载,多年以后周汝登刊行《知儒编》赠给他和杨起元*[明]冯梦祯:《快雪堂日记》“丙申”,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100页。,而杨撰写《〈知儒编〉跋》,大概提笔即书,敷衍一番大义之后,竟误称“余年友海门周先生汇集是编”*[明]杨起元:《知儒编跋》,《太史杨复所先生证学编》卷3,第355—356页。按,杨起元所云“年友”,即1577年同批中进士者,尚有邹元标、冯梦祯等。可参见Zhao Jie: Chou Ju-teng (1547—1629) at Nanking: Reassessing a Confucian scholar in the late Ming intellectual world,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1995, pp. 24—27.。如此跋语自然未免过于草率。
周梦秀所追溯的“学佛知儒”论提出者是张九成。在南宋,朱熹曾时常对张九成十分不满并进行过严厉的批评。一次因为洪适在浙江会稽要出版张九成的经解,朱熹厉声痛斥此举,认为“此祸甚酷,不在洪水夷狄猛兽之下,令人寒心”*《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2《答石子童》,《朱子全书》第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924页。。面对王学士人类似的做法,明中期的程朱学者罗钦顺亦如是鸣鼓攻之:
张子韶以佛语释儒书,改头换面,将以愚天下之耳目,其得罪于圣门亦甚矣。而近世之谈道者,或犹阴祖其故智,往往假儒书以弥缝佛学,律以《春秋》诛心之法,吾知其不能免夫!*[明]罗钦顺:《困知记》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4页,第81条。
可是,到了明万历时期,以周梦秀为代表的“儒佛一致”发展至巅峰造极*[日]荒木见悟:《周海门の思想》,氏著:《明代思想研究》,第237页。,在“以狂风荡孔矩”的风潮之下,对张九成的做法已经不是“阴祖其故智”而已,而是公然标榜之。周汝登不仅将“张九成”列入《圣学宗传》,而且为张芝亭等三人《唱和无垢诗集》撰写题序。根据该题序的交代,该诗集为三人唱和张九成《心传录》中咏《论语》绝句诗,而周汝登对张九成之诗评价颇高*[明]周汝登:《题唱和无垢诗集》,《东越证学录》卷9,《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65册,第590页。。当然,这可能与张九成为浙江先贤也有些关系*后来刘麟长在任浙江提学副使时,编有《浙学宗传》(1638年序刻)一书,其中将所谓“浙学”的本土渊源推为张九成。见其《浙学宗传》,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1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
其实,在晚明时期,很多士人学者都表达过对“学佛知儒”的认同见解。焦竑就曾这样说:
孔孟之学,尽性至命之学也。独其言约旨微,未尽阐晰,世之学者又束缚于注疏,玩狎于口耳,不能骤通其意。释氏诸经所发明,皆其理也。苟能发明此理,为吾性命之指南,则释氏诸经,即孔孟之义疏也,又何病焉!*[明]焦竑:《答耿师》,《澹园集》卷12《书》,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82页。
焦竑将佛经视为“孔孟之义疏”,便是“学佛知儒”的最好体现。而且,由“泛滥佛老”而“返归六经”的学思历程,在宋明理学家中往往是公开的常态。不过,这并不等于理学家们就会认可“学佛知儒”;相反,所谓的“返归”,往往被描述为一种“知今是而昨非”,“辟佛”的态度因此正好得以成立。对于“学佛知儒”的主张,黄宗羲则有一套独特的批判。黄氏认为,应该反过来,是“学儒知佛”;而且即便是“学儒知佛”,也分为两类学者:
昔人言“学佛知儒”,余以为不然,学儒乃能知佛耳。然知佛之后,分为两界:有知之而允蹈之者,则无垢(张九成)、慈湖(杨简)、龙溪(王畿)、南皋(邹元标)是也;有知之而反求之六经者,则濂(周敦颐)、洛(二程)、考亭(朱熹)、阳明、念庵(罗洪先)、塘南(王时槐)是也。*[明]黄宗羲:《张仁庵先生墓志铭》,《黄梨洲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34页。按,括号内文字为引者所加。
并且,黄宗羲还曾批判憨山德清等未整合佛教内部资源*[加拿大]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张华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0页。。在儒、佛两家之学的关系上,黄宗羲所要认可的是采取“知之而反求之六经”这一路径的“学儒知佛”者,因为黄宗羲这里所要表彰的“知佛”,其实是对佛教的真正扬弃。因此,在对佛教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上,黄宗羲显然认为江右王学的学者方可接续周、程、朱、王以来的儒学之正统。
(二)周汝登的《佛法正轮》
相应地,周汝登也曾认为朱熹与佛教之关系不能过于简单地看待:
先生最为辟佛,而又未尝不参寻游戏其间,其中固不可测也。*[明]周汝登:《圣学宗传》卷9“朱熹”,《续修四库全书》第513册,第175页。
可是,周汝登对此的诠释显然要与黄宗羲大相径庭。周汝登于1603年有《佛法正轮》一书编成,该书又名《直心编》。正如周氏门人方如骐所述,此书在于展现“儒、佛异者迹,而不异者心”,进一步以“心学”为宗,周氏批评世儒辟佛者往往滞于“分合之迹”,而应当是去“判明其不同之迹,而不讳其不二之心”*[明]方如骐:《直心编引》,[明]周汝登:《佛法正轮》卷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第3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5—106页。。如果说辟佛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那么周汝登式的“不辟佛”则是将此“榻”变成了至大无外而至小归于一心的“须弥芥子”,将佛学精神积极纳入到王门心宗之学以内。周汝登在其《佛法正轮引》中,则以江、河的比拟,形象生动地说明他认为儒、佛二者的“不可合”又“不可分”:
何以明之?譬之水然。水有江有河,江不可为河,犹河不可为江;必合而为一,虽至神不能:此儒禅不可合也。江河殊矣,而湿性同,流行同,利济同,到海同;必岐而为二,虽至愚不许:此儒禅不可分也。不可合者,因缘之应迹难齐;而不可分者,心性之根宗无二。*[明]周汝登:《佛法正轮引》,《佛法正轮》卷首,第112页。
宗旨惟一而因缘教法有别,此本是华严学中“称法”与“逐机”的题中义,亦与程朱学之“理一分殊”在结构上若合符节。据记载,与周汝登交往颇为密切的高僧湛然圆澄正好也曾以“天”“人”做譬喻,针对周氏本人有类似的评论:
曰:他是道学耶?禅宗耶?师曰:道学。曰:恁么,则不合也?师曰:在天而天,在人而人。*《湛然圆澄禅师语录》卷6,《禅宗全书》第52册,第86页。
这里所用“天—人”之譬喻,似乎终显出一丝高下之别,大概是作为佛教本位主义信仰者的圆澄有意如此。相对而言,作为儒者的周汝登表现得更为圆融,认为该编“示以自足之道,而消其旁求之心”*[明]方如骐:《读〈佛法正轮〉纪》,《佛法正轮》卷首,第106页。,充分体现出周氏“在没有放弃其自身儒家身份的前提下,对佛教表示了最大限度的欣赏”*彭国翔:《周海门与佛教:历史与思想》,《近世儒学史的辨正与钩沉》,台北:允晨文化,2013年,第357页。。
《佛法正轮》全书分上、下两卷,选录若干片段,间以“论曰”作点评,与其《圣学宗传》的“蠡测曰”类似。此外,周氏门人方如骐有《直心编引》及《读〈佛法正轮〉纪》“十条”,置于卷首的周汝登《佛法正轮引》之前。
上卷为《佛门诸语》,共18条,录禅宗语录对白。从所选文字及“论曰”来看,周汝登颇有批判和摒弃其所谓“二乘”的意思。他对普通佛教中的布施供养、西方净土、诵经求福、谈空行有等流于形式的观念和行为皆有所批判,而倡导最为高妙无著的根本第一义佛教禅法“真宗”。在儒、佛等如何归一心这一问题上,周汝登认为“知不外求,而后能通于儒佛之旨”,学者须落实己之一心,“入道惟一”而“真功不二”*[明]周汝登:《佛法正轮》卷上,第120、121、123页。。
下卷为《儒门诸语》18条、《玄门诸语》4条及别附3条。与上卷体例略有不同,下卷仅仅是分别在这三部分的结尾才总附以“论曰”。其中《儒门诸语》多为儒学中人正面评论佛教之语:
已上诸儒,皆深明佛理者。此理既明,信亦可,辟亦可。明理之信,信此正轮,绝不狥其形迹;明理之辟,辟彼二乘,绝不废乎真宗。*[明]周汝登:《佛法正轮》卷下,第131,132,133页。
《玄门诸语》等则是周汝登所认为的道教人物论心契道之语,以此指出“真儒之妙悟”“玄门之极则”和“佛法之正轮”三者“惟是一心”,而“一是实名,三皆为虚”*[明]周汝登:《佛法正轮》卷下,第131,132,133页。。附录3条,则是迷途知返的问道、悟道公案,周汝登认为“皆在自心”;与《知儒编》不同的是,这里的得道者不必非得是僧人*[明]周汝登:《佛法正轮》卷下,第131,132,133页。。
周汝登在《佛法正轮引》末尾有这样的交代:
孔子之旨,阐在濂洛以后诸儒,故录取程门及杨、邵诸诗,而示之儒;如来之旨,阐在曹溪以下诸师,故摘取《坛经》及诸宗语数条,而示之禅……儒门之语别见,而此禅家语也,号之曰“佛法正轮”。*[明]周汝登:《佛法正轮引》,第113页;又见《东越证学录》卷7,第550—551页。
可见,《佛法正轮》是有意配合其《程门微旨》《邵杨诗微》二书而编撰,而此三本小书大概编于同一时期。总体来说,这样的做法,当然较其从兄周梦秀的《知儒编》来得保守、稳当、温和许多。
在《圣学宗传》中,周汝登对杨简的数条语录有过这样的点评:
自信无前,摘抉前哲,如禅门中所谓“呵佛骂祖”,是真学佛祖者,尤难与拘挛者道也。*《圣学宗传》卷11“杨简”,第217页。
周汝登的哲学追求浑一而无滞著,故时常批判拘谨小儒或僧侣往往执于一偏。《宗传咏古》马之骏序云:
禅家倡颂,每以谜语藏机;海门先生《宗传》,辄用微言阐其奥:其为广狭、幽朗,何啻千里?*[明]马之骏:《宗传述古小引》,上海图书馆藏之江大学无名氏抄本。
对于这样的高下之判,也许周汝登会付之一笑。因为如《佛法正轮》中所示,在周氏看来,以“谜语藏机”,大概也只能算佛教之“二乘”而非“真宗”。王守仁曾反复说“吾党志在明道”,周汝登这样的“直心”与“正轮”的宗旨,以及对佛、道等的态度,正是王学“志在明道”理路的顺适展开。
三、“心学杂禅”的指责与回应
儒者而被指责“杂禅”,这一问题其实与理学思想之诞生的思想史契机本身有关:理学自始便与中国佛教,尤其是华严、天台以及禅宗三派的思想,既是竞争者,也是受益者。因此,“杂禅”问题自理学产生,便已存在,随着理学影响的扩大而愈演愈烈。当程朱一系的理学思想终于取得官方正统地位之后,另一支思想更为开放的“心学”便往往成为众矢之的。这里的“众”,往往一方面包括来自程朱学者的攻击,另一方面也有来自佛教宗门对儒门终究采取过分留恋、乃至滞着拘泥于世间事物态度的蔑视;当然,宗门的这一态度经常也会同时指向程朱学者。那么,心学与禅学这样纠缠始终的“剪不断,理还乱”之暧昧,其表现究竟在哪些方面?
概括地讲,心学所强调的“心”所具有的至高无上地位(“心体”)来自孟子性善论的主张;而其“无”的形上本质以及“无”的工夫、境界论,则也许更多来自老、庄思想以及玄学的思考。而在佛教传入以后,“一阐提皆可成佛”的平等观和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的思想资源,则先于宋明理学,早在唐代天台、华严以及禅宗等中国佛教思想中,已经统合以上本土思想资源,成为了中国佛教的“心学”*“心学”一词首先其实是自佛教内产生出来的,参见[日]荒木见悟著、李凤全译:《心学与理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面对这样强大的中国佛教思想,儒学在经过对宋代理学心、性、理、气等理学思想概念进行精致辨析、分疏和整合的洗礼的同时,儒学中一些对支离知识无助于世道人心的学者,决定要采取更为开放的路向——这一路向抛却知识的束缚甚至遮掩(抛却的不是知识本身),以归宗本心之无功利的真实呈现,由此而亦归于“心学”,这是儒家式的心学。所以,如果更广泛地讲,借用荒木见悟的语辞,“心学”实际上构成了中国近世(自宋以降)思想的“土壤”,近世中国儒、释、道皆在此土壤上生长*[日]荒木见悟著、廖肇亨译:《佛教与儒教》,台北:联经出版,2008年,第4页。。在“本心”所昭示的中国思想土壤之上,就儒、佛而言,对现世人间社会道德伦理秩序的态度曾一度是其区隔所在;但这一区隔在明代后期随着宗门改革运动和居士佛教的空前繁荣而日趋模糊,再加上晚期帝制中国对佛教这样“遗世独立”的宗教团体始终具有的高度警惕所带来的政府宗教政策与指导思想,儒学式的家庭社会伦理以及国家政治也就逐渐浸渍深入到了佛门思想中*参见江灿腾:《晚明佛教改革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儒家心学势必更加难以与佛教宗门思想划清界线,于是,在持正统思想的保守批评者看来,他们这些人简直就是沆瀣一气,共同煽动起了社会的种种不良。
既然对陆王心学的指责之声早已纷至沓来,就王学而言,明代程朱学者对王畿、王艮、罗汝芳等“入禅”的指责更满地皆是,这自然就需要有所回应。据记载,在南京的一次讲会上,周汝登这样回应“心学杂禅”的指责:
问:“象山、阳明之学,杂禅是否?”先生曰:“子还体认见之?亦随声和之者?夫禅与儒,名言耳。一碗饭在前,可以充饥,可以养生,只管吃便了。又要问是和尚家煮的,百姓家煮的。”*《南都会语》,《东越证学录》卷1,第437,437页。
这里周汝登的表述,有点类似当今全球化时代里随着对人类多元文化的认识和自觉、而日渐流行于世的“宗教多元主义”(Religious pluralism)价值观。可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怎么看待可能会危害人类的“邪教”?
或曰:“是饭便吃,将无伤人而不觉乎?”先生曰:“伤人者,只恐不是饭耳。若是饭,岂得伤人?尔欲别其是饭非饭,须眼看口尝始得,不可悬度。”*《南都会语》,《东越证学录》卷1,第437,437页。
如果转换一下语辞,可以说成是,宗教上的多元主义并非要陷入一种价值相对主义;是饭非饭、伤人与否的价值判断仍然存在其中。周汝登的态度更接近于在多元宗教中采取一种高度弱化了的效益主义原则和尺度:只要有益无害,即可。周汝登这样一种“儒佛一致”的论调,与王守仁的思想也是一致的;对类似的问题,后者曾说:“子无求其异同于儒释,求其是者而学焉可矣。”*[明]王守仁:《赠郑德夫归省序》,《王阳明全集》第1册,第254页。不过,有关“是饭非饭”的问题,或者说诸种宗教的价值到底诉诸何种尺度来衡量,仍是一大难题;在此,周汝登并没有为今天的人们带来更好的启发和解决,他亦只诉诸儒门固有的价值观作答*《南都会语》,《东越证学录》卷1,第437页。。至此,我们方可以理解周汝登对“杂禅”的态度。虽然自黄宗羲以来,周汝登往往被正统的历史叙述指责为“纯粹是禅”,而细究原始文献,学者们已经发现:周汝登不仅个人一直坚持儒门身份,从未做出过类似于同时代李贽、杨起元、袁黄等纷纷公然宣示佛教徒身份的举动;他也从未被丛林人士列入《居士传》中,佛门龙象湛然圆澄更是明确地指出周汝登是道学家而非禅者*可参见陈慧麒:《会通儒释:以周汝登为中心对明末阳明后学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论文,2009年;彭国翔:《周海门与佛教:历史与思想》。。
与天下所指斥的“心学杂禅”现象相应、而相对较少被人们注意的,则是“禅学杂儒”。正如上文所述,万历以降,佛门大德高僧多借王学讲学之力为宗门复兴运动推波助澜,于是,不仅与王学混杂相处,而且甚至多用功儒书,对儒家经典极力表彰和阐扬。明末刘宗周等对于这一类的“阳明禅”,则有其独到的观察和意见。在1638年给其诸门人弟子的一封书信中,他认为在此现状之下,正可以借助王学而使得佛者归儒。其论述看起来十分特别而有趣:
今之言佛氏之学者,大都盛言阳明子,止因良知之说于性觉为近,故不得不服膺其说,以广其教门,而衲子之徒亦浸假而良知矣。呜呼!古之为儒者,孔孟而已矣,一传而为程、朱,再传而为阳明子,人或以为近于禅;即古之为佛者,释迦而已矣,一变而为五宗禅,再变而为阳明禅,人又以为近于儒:则亦玄黄浑合之一会乎?而识者曰:“此殆佛法将亡之候,而儒教反始之机乎?”孟子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今之言佛氏学者,既莫不言阳明子,吾亦言阳明子而已矣……阳明子者,吾道之祢也。今之言佛氏之学者,招之以孔、孟而不得,招之以程、朱而又不得,请即以阳明招之。佛氏言宗也,而吾以阳明之宗宗之;佛氏喜顿也,而吾以阳明之顿顿之;佛氏喜言功德也,而吾以阳明之德德之,亦曰良知而已矣……夫学者而不知有良知之说则已,使知有良知之说,而稍稍求之,久之而或有见焉。则虽口不离佛氏之说,足不离佛氏之堂,而心已醒而为吾儒之心,从前种种迷惑一朝而破,又何患其不为吾儒之徒乎?*[明]刘宗周:《答胡嵩高、朱绵之、张奠夫诸生》,《刘宗周全集》第3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49—350页。
刘宗周此番论述显然有些过于乐观而且迂阔,其所难以自圆其说的是:按其逻辑,则佛家完全也可以反过来这样说儒家。那么,究竟是谁家“将亡”,而谁家“反始”:若以此相争,则儒、佛之间愈难解难分矣。不论如何,有一点可以确认:刘宗周不去全力批判混合的现状,是因为在其看来,眼下王学与禅学所表现出的“玄黄浑合一会”的现状,只在途径和手段上,其将达致的目的地则是崇此而息彼。因此,明末的刘宗周已经转而严守起作为“异端”与“正道”之佛、儒界限,他甚至借用孟子的句式称“阳明子之道不著,佛、老之道不息”*《刘宗周全集》第3册,第350页。。
【责任编辑:杨海文;责任校对:杨海文,许玉兰】
2015—02—25
王 格,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北京100871)。
B248.2
A
1000-9639(2015)03-011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