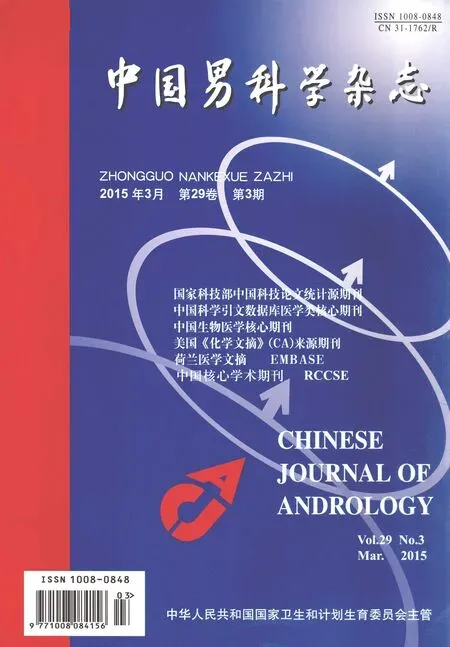慢性骨盆疼痛综合征(CPPSCPPS)疼痛的发病机制研究进展
丁华洋梁朝朝. 安徽医科大学(合肥 3003);.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
·综 述·
慢性骨盆疼痛综合征(CPPSCPPS)疼痛的发病机制研究进展
丁华洋1梁朝朝2
1. 安徽医科大学(合肥 230032);2.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
一、CPPSCPPS的定义和疼痛特点
慢性骨盆疼痛综合征(CPPS)为Ⅲ型慢性前列腺炎,出现持续或反复发作性盆腔疼痛,且至少持续或反复发作6个月,常伴有消极的认知、行为、性行为和情感后果,与下尿路病变、性功能障碍、肠功能紊乱或妇科疾病相关,缺乏感染或其他明显的病原学证据[1]。CPPS疼痛的部位主要分布于会阴部、腹股沟、肛周、阴囊、大腿内侧及睾丸等部位[2],均分布于膀胱尿道神经支配的腰、骶神经支配的区域。
PPS疼痛具有疼痛部位的多变性和疼痛发生的持续性、难治性等特点。临床上常见一些慢性前列腺炎(chronic prostatitis,CP)患者经治疗后,前列腺组织炎症消失而疼痛症状仍然存在或者加重,推测引起前列腺疼痛的原因与支配前列腺的L5-S2脊髓段神经继发性病变导致的持续性神经牵涉痛有关[3]。
二、CPPSCPPS疼痛的发病机制
(一)细胞因子
细胞因子是机体内的免疫细胞和炎症细胞产生的、调节局部和全身免疫、炎症反应并参与组织修复过程的小分子蛋白,主要以自分泌和旁分泌产生[4]。慢性前列腺炎/慢性骨盆疼痛综合征(CP/CPPS)的病理过程常伴有众多炎症因子的变化,它们在前列腺局部炎症的病理变化可能对前列腺炎的发生发展和转归发挥重要作用[5]。
1. TNF-α:主要来源于巨噬细胞和单核细胞,具有抵抗细菌和病毒等感染,促进组织修复,引起肿瘤细胞凋亡等较广泛的生物学活性。He等[6]研究表明,Ⅱ型和ⅢA型前列腺炎中高浓度TNF-α与白细胞计数之间呈正相关,ⅢB型前列腺炎患者EPS 中TNF-α的浓度与正常对照组无明显差异。由此可知,TNF-α可用于鉴别炎症性和非炎症性前列腺炎。在前列腺局部,TNF-α可激活单核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刺激其合成IL-1、IL-6和IL-8,进而促进炎症发生。最近的研究发现,TNF-α可能是疼痛超敏和自发性疼痛的潜在原因。
2. IL-8:一种强效的中性粒细胞趋化因子,主要由IL-1、TNF、LPS等诱导单核细胞、内皮细胞、巨噬细胞和成纤维细胞等合成和分泌,并可诱导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从血液向炎症区域聚集。Khadra等[7]研究发现,IL-8在CP/CPPS患者的精浆中含量比健康人群明显升高,IL-8的含量与NIH-CPSI疼痛、排尿症状和生活质量评分明显相关。
3. IL-1:又称淋巴细胞激活因子,主要来源于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和内皮细胞,参与机体免疫调节,与疼痛的产生密切相关。IL-1β(循环中发现的IL-1活性大都是IL-1β多肽类型)是一种旁分泌型细胞因子,在炎症和组织修复中具有重要作用,推测可能在前列腺炎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IL-1β通过促使血管细胞和内皮细胞表达黏附分子,引发单核细胞、T淋巴细胞和多形核白细胞从血管渗出,侵入前列腺组织以及诱导炎症细胞、内皮细胞和成纤维细胞等分泌细胞因子,促使炎症级联反应扩大等一系列免疫炎症反应,使细胞产生大量的前列腺素E2,引起CPPS患者疼痛等诸多生物学效应。
4. IL-6:由单核细胞、活化的T、B细胞及血管内皮细胞等产生,能使B细胞前体分化产生抗体,与集落刺激因子(colony stimulating facter, CSF)协同,促使骨髓源细胞的生长和分化,增强自然杀伤细胞的作用。Stancik等[8]对109例CP/CPPS患者进行了抗生素治疗,治疗前有86例患者的精浆中和37例患者手淫后的尿液中IL-6浓度增高,经抗生素治疗后,59.6%的患者精液、尿液中IL的浓度明显下降,其中ⅢA组中52.8%的患者IL-6浓度下降,ⅢB组中有73%的患者IL-6浓度下降。ⅢA型患者精浆中IL-6浓度和疼痛、排尿症状、生活质量以及总评分存在正相关性,表明ⅢA型患者的疼痛症状、排尿障碍和生活质量的影响可能是由免疫反应诱导,进而引起前列腺充血水肿以及疼痛。
5. IL-10:由Th2辅助细胞亚群产生,可限制单核巨噬细胞对免疫介质的释放,减少TNF-α和IL-1的释放并降低其活性。He等[6]研究发现,ⅢB型患者EPS 中IL-10的水平和TNF-α呈正相关,而IL-10的水平和IL-2呈负相关。Miller等[9]研究发现,CP/CPPS患者的精液中IL-10和TNF-γ浓度较对照组显著增高。精液中IL-10的浓度和患者NIH-CPSI呈正相关,IL-10的浓度越高,患者的疼痛症状越严重。PGE2:主要由巨噬细胞合成和释放,在物理、化学等炎症介质刺激下产生。Koval等[10]研究发现,PGE2与CPPS疼痛症状密切相关。Pontari[11]研究发现,CPPS患者EPS中PGE2的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经治疗后症状改善的患者的EPS中PGE2水平则下降,认为CPPS患者的疼痛症状由氧化应激作用增强导致PGE2水平升高而引起。神经生长因子(NGF):中枢神经系统NGF主要来源于星形胶质细胞,激活后可以产生大量NGF。CPPS疼痛可能是由于前列腺慢性炎症引起IL-6和IL-8等炎性因子的表达,进而引起IL-10和NGF的表达,再由NGF直接作用引起。Hedelin等[12]通过对CP患者精液中的NGF和炎性介质的测定,发现CP患者精液中的NGF水平较对照组显著升高,用McGill疼痛问卷调查(MPQ)、多项人格调查表(MPI)和国际IPSS评分分析,发现NGF与CPPS疼痛程度存在正相关性。
(二)离子通道
离子通道是细胞膜上一种特殊的两亲性膜整合蛋白,具有离子选择性和门控特性,通过残基侧链选择性与离子相互作用,发挥专一性通道屏障功能。大电导钙离子激活的钾离子通道(large conductance Ca2+-activated channels,BKCa)是一类超家族具有多种生理功能通道的蛋白,其功能多样,不仅在调节可兴奋细胞,包括神经细胞动作电位的复极和发放频率、细胞膜兴奋性以及平滑肌细胞收缩性、神经递质释放等中起重要作用,而且还参与了免疫、细胞增殖分化[13]、细胞凋亡调控等过程。Kim等[14]对大鼠前列腺分泌上皮细胞进行分离培养后采用膜片钳记录分析,发现是电压依赖性钾离子通道,并证实此钾离子通道是BKCa,可受某些药物(ATP、UTP、Ach)影响引起细胞内Ca2+浓度变化,从而调节钾离子通道活性,并且在前列腺液的分泌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离子通道功能的异常可能会引起前列腺上皮细胞K+、Ca2+等电解质代谢异常,细胞外高钾可引起平滑肌细胞膜去极化,促使细胞外Ca2+内流,进而引起前列腺及周围肌肉收缩异常,产生疼痛症状。由此说明,BKCa通道与CPPS疼痛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组织细胞中钙离子浓度升高会引起炎症和疼痛,细胞质内钙离子浓度的升高是一些促炎因子激活和释放的必要条件。Nadler等[15]报道在CP患者的EPS中,促炎因子IL-1β和TNF-α的水平均升高,这可能与钙库调控的钙离子通道(store-operated calcium channels,SOCs)的激活有关。神经元上的电压门控钙离子通道(voltage-gated calcium channels,VGCC)主要作用是调节去极化而诱导钙离子内流,进而触发细胞内钙离子依赖的一系列生理反应,如神经递质的释放、神经元兴奋性的调节和基因转录等。多种神经调质,如谷氨酸、去甲肾上腺素、乙酰胆碱、γ-氨基丁酸、P物质等,参与疼痛的传递与调控。VGCC的变化可能影响这些神经递质的释放,进而引起前列腺痛。Fossat等[16]研究表明Cav1.2通道(L型VGCC亚型)大量存在于脊髓背根神经节中,在生理性伤害感受和慢性/神经性疼痛中发挥重要作用,且L型VGCC阻滞剂能增强阿片样物质的止痛效果,因此,钙离子通道在CPPS疼痛中也起重要作用。目前,普遍认为Nav1.3、Nav1.7和Nav1.8等钠离子通道与疼痛有关。Samad等[17]研究表明,用含有ShRNA的腺相关病毒敲除Nav1.3注射到分支神经损伤模型大鼠的腰部背根神经节(dorsal root ganglia,DRG),结果显示L4DRG的Nav1.3的敲除明显减弱了神经损伤所致的机械疼痛阈值,表明Nav1.3与神经性疼痛关系密切。Laedermann等[18]实验观察到在分支神经损伤模型中,Nav1.7的电流振幅明显减弱,然而Nav1.7的阻滞剂明显减轻此模型大鼠的疼痛行为,表明Nav1.7参与了神经性疼痛的形成。Thakor等[19]研究发现在神经病性疼痛模型中,受损的DRG神经元及毗邻未受损神经元中Nav1.8表达水平均下降,而受损的神经纤维及毗邻未受损的神经轴突中Nav1.8表达明显增加,同时特异性Nav1.8阻滞剂明显改善了疼痛行为,表明Nav1.8在神经病理性疼痛的发生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三)化学因素
某些化学因素可刺激尿道括约肌频繁地过度收缩或者痉挛,导致膀胱出口梗阻,造成前列腺部尿道压力增高,尿液反流入前列腺,尿酸诱导无菌性化学性前列腺炎,产生排尿异常和骨盆区域疼痛症状。阎鹏[20]在对113例Ⅲ型慢性前列腺炎患者的EPS液尿酸测定的研究中,将113例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分为2组,其中ⅢA组59例,ⅢB组54例,另设正常对照组21例,3组分别进行NIH-CPSI评分,治疗4周,分别测定EPS中的白细胞计数和尿酸浓度,推测EPS中尿酸的水平可能与CPPS疼痛相关。机体内代谢产生的尿酸可经肾小球滤过,但98%可被近曲小管重吸收,当尿酸盐结晶沉积在组织中,可引起炎症反应。同样地,当EPS中有高浓度的尿酸时,也有可能引起前列腺的炎症反应,进而产生化学性刺激,导致骨盆区域疼痛[21]。
(四)解剖因素
正常情况下,血钾浓度是尿钾浓度的10倍,由于尿路上皮构成的天然屏障,阻止K+渗入上皮下,然而病理条件下尿路上皮通透性增高,K+从上皮外组织中渗入上皮下,刺激神经引起疼痛症状。Parsons等[22]研究发现,CP与间质性膀胱炎(interstitial cystitis,C)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可能的发病机制、甚至对治疗的反应都极其相似,因此,推测两者可能有相同的致病因素和相同的病理生理过程,即下尿路上皮功能障碍。Eisenberg等[23]对多名CP患者进行钾离子敏感试验(Potassium Sensitivity Test,PST),发现CP与间质性膀胱炎一样存在下尿路上皮功能障碍,机制可能是CP患者上皮细胞的通透性增加,而腺泡内增高的K+又可通过具有功能障碍的上皮细胞间隙渗入到基质中,再加上尿液中的K+渗入到组织间隙,刺激神经纤维末梢引起疼痛。Parsons等[24]在临床药物试验中发现,硫酸戊聚糖钠(PPS)能修复膀胱黏膜上皮,并且能够改善IC患者的临床症状,同样也能够缓解CPPS疼痛的症状。这提示,IC和CPPS都存在着下尿路上皮功能障碍这一相同的解剖因素。
(五)神经调控
病理性疼痛的显著特征是在病灶去除或者损伤愈合后疼痛依然持续存在很长时间,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赵晖等[25]研究发现,高达92.2%的CPPS患者其慢性疼痛状态和盆底功能障碍存在相关性,表明神经机制可能参与了CPPS疼痛的发生发展。临床上常见一些CP患者经治疗后,前列腺组织炎症消失而疼痛症状仍然存在或者加重。Ishigooka等[26]在大鼠模型上发现,没有使用坦索罗辛的大鼠前列腺炎模型组P物质的免疫反应区域在大鼠脊髓的L5-S2节段,推测CPPS疼痛原因可能在于支配前列腺的L5-S2脊髓节段的继发性病变,P物质在CPPS疼痛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部分CPPS疼痛可能是一种L5-S2节段脊髓病变引起的持续性神经牵涉痛[3]。大量实验研究表明,脊髓初级中枢氧化应激也与CPPS疼痛关系密切。Kullisaar等[27]通过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患者尿中-异前列腺素含量,发现BPH与ⅢA、ⅢB、Ⅳ型前列腺炎都存在明显的氧化应激现象。Schwartz等[28]研究发现,外周刺激所引起的痛觉过敏和痛超敏与相应节段脊髓背角氧化应激密切相关。这提示,神经调控在CPPS疼痛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展望
CPPS在男性青壮年中发病较为广泛,严重影响着患者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目前,CPPS疼痛的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清楚,虽然已经认识到上述发病机制对CPPS疼痛的影响,但其确切的发病机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随着免疫学、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等先进技术的迅速发展,对CPPS疼痛的发病机制不断深入研究,可望对CPPS疼痛的症状提出更为有效的治疗方法。
致谢:本文由卫生部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201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1170698;81370856);安徽省科技攻关项目(12010402128)基金项目资助
关键词慢性骨盆疼痛综合征; 疼痛
参 考 文 献
1 Baranowski AP, Mandeville AL, Edwards S, et al. J Urol 2013; 31(4): 779-784
2 Engeler DS, Baranowski AP, Dinis-Oliveira P, et al. Eur Urol 2013; 64(3): 431-439
3 Tang W, Song B, Zhou ZS, et al. Chin Med J ( Engl) 2007; 120(18): 1616-1621
4 de Oliveira CM, Sakata RK, Issy AM, et al. Rev Bras Anestesiol 2011; 61(2): 255-259, 260-265, 137-142
5 安立文, 魏学智. 黑龙江医学 2011; 35(1): 17-20, 59
6 He L, Wang Y, Long Z, et al. Urology 2010; 75(3): 654-657
7 Khadra A, Fletcher P, Luzzi G, et al. BJU Int 2006; 97(5): 1043-1046
8 Stancik I, Plas E, Juza J, et al. Urology 2008; 72(2): 336-339
9 Miller LJ, Fischer KA, Goralnick SJ, et al. Urology 2002; 167(2 Pt 1): 753-756
10 Koval' chuk LV, Gankovskaia LV, Mazo EB, et al. Zh Mikrobiol Epidemiol Immunobiol 2007; (5): 57-61
11 Pontari MA. Curr Urol Rep 2007; 8(4): 307-312
12 Hedelin H, Jonsson K. Scand J Urol Nephrol 2007; 41(6): 516-520
13 Zhang YY, Yue J, Chen H, et al. J Cell Physiol 2014; 229(2): 202-212
14 Kim JH, Hong EK, Choi HS, et a1. Prostate 2002; 51(3): 201-210
15 Nadler RB, Koch AE, Calhoun EA, et al. J Urol 2000; 164(1): 214-218
16 Fossat P, Dobremez E, Bouali-Benazzouz R, et al. J Neurosci 2010; 30(3): 1073-1085
17 Samad OA, Tan AM, Cheng X, et al. Mol Ther 2013; 21(1): 49-56
18 Laedermann CJ, Cachemaille M, Kirschmann G, et al. JClin Invest 2013; 123(7): 3002-3013
19 Thakor DK, Lin A, Matsuka Y, et al. Mol Pain 2009; 5: 14
20 阎鹏. 陕西医学杂志 2012; 41(5): 609-610, 626
21 Lochman JE, Boxmeyer C, Powell N, et al. J Consult Clin Psychol 2009, 77(3): 397-409
22 Parsons CL, Albo M. J Urol 2002;168(3): 1054-1057
23 Eisenberg ER, Moldwin RM. World J Urol 2003; 21(2): 64-69
24 Parsons CL, Rosenberg MT, Sassani P, et al. BJU Int 2005; 95(1): 86-90
25 赵晖, 申吉泓, 陈玉平, 等. 中华男科学杂志 2008; 14(6): 530-532
26 Ishigooka M, Nakada T, Hashimoto T, et al. Urology 2002; 59(1): 139-144
27 Kullisaar T, Turk S, Punab M, et al. Prostate 2012; 72(9): 977-983
28 Schwartz ES, Kim HY, Wang J, et al. J Neurosci 2009; 29(1): 159-168
(2014-12-05收稿)
doi:10.3969/j.issn.1008-0848.2015.03.014
中图分类号R 6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