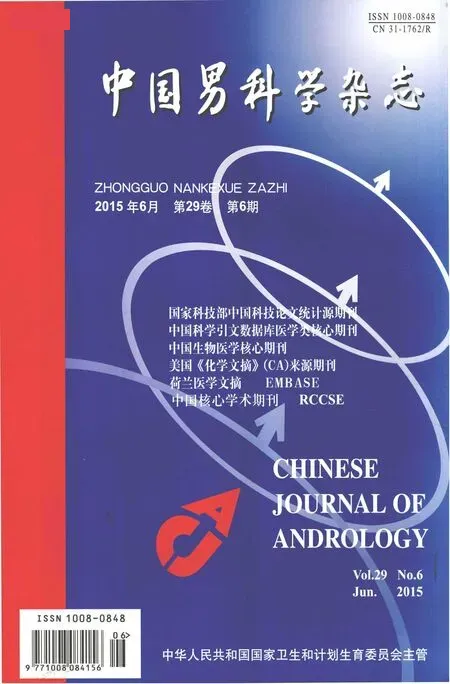精液细菌培养、解脲支原体、沙眼衣原体培养在IVF-ET中的临床意义
杨 昊 综述 滕晓明 审校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上海 201204)
精液细菌培养、解脲支原体、沙眼衣原体培养在IVF-ET中的临床意义
杨 昊 综述 滕晓明 审校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上海 201204)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是目前辅助生殖领域治疗不育不孕症的常用手段,也是近年医学研究关注的热点。但长期以来,这种技术成功率始终较低,其原因除了种植率较低以外,还存在妊娠后流产以及早产率高等。而导致这些原因的因素有很多方面,其中微生物学的感染可能是其中之一。微生物是存在于自然界的一大群形体微小、结构简单、肉眼不能直接看到,必须借助光学显微镜或电子显微镜放大数百至数万倍才能看到的微小生物。微生物包括病毒、细菌、螺旋体、支原体、衣原体、放线菌、真菌和原虫等[1]。其中在辅助生殖领域,男女双方行IVFET之前会进行一些微生物学方面的常规检查如HIV、乙肝、丙肝、RPR、细菌、支原体、衣原体。近期国外有研究表明女性卵泡液中如有微生物是导致IVF不良结局的潜在因素[2]。国内也有许多针对女性生殖道微生物感染导致IVF-ET的结局不佳的研究[3-5],但是对于男性精液中微生物学检测的研究相对较少,精液中常规进行的微生物学检查为细菌培养、解脲支原体以及沙眼衣原体培养,本文将分别对这三项较为常用的精液微生物学常规检测对于IVF-ET结局的影响以及其临床意义进行综述。
一、精液细菌培养
近年国外有研究表明用于IVF-ET的精液污染率较高[6],文章中提出许多精液污染(如细菌污染)主要可能源于男方取精前手部清洁效果不佳,这点值得我们深思和注意。同样国内学者陈静华等[7]研究也表明,进行IVF-ET治疗的男性中,细菌感染率高达67.2%,且菌种复杂,其中以革兰阳性球菌及杆菌为主,其中致病性较强的溶血葡萄球菌、粪肠球菌等均有较高阳性率。近年国外有学者通过五年的回顾性研究696例生育能力低下患者的精液标本发现,加德纳菌是分离最多的一种细菌。与对照比较发现,在加德纳菌感染的样本中精子数量、活动率以及形态等情况较为恶化[8]。这表明准备进行IVF-ET治疗的男性精液中细菌培养的阳性率较高,那么这些细菌是否会影响到IVF-ET结局?
较早的国外研究认为精液中的细菌对于精子功能以及IVF结局并无显著影响[9]。Liversedge等[10]的研究也表明,精液中细菌的存在并不影响IVF的受精率、卵裂率以及移植胚胎数。但也有研究表明在IVFET过程中,若精液发生微生物污染,可能会导致卵子不受精、受精卵不分裂、胚胎死亡等,导致IVFET失败[11]。如果精液中细菌对于IVF结局产生影响,那么具体的机制是什么?
研究表明精液中的细菌可能通过改变精液的理化性质、或者直接影响精子功能以及生精功能从而影响到精子的活动力与存活率,最终可能影响到IVFET的结局[12,13]。较早国外学者研究表明,提出精液中的微生物不利于精子与透明带的结合,从而影响到精子的受精能力[14]。
近年国内有研究结果表明,精液培养阳性可能影响到卵子受精率,但对胚胎发育及妊娠结局影响不大。研究推测感染的细菌可能只是对精子的受精能力有所影响,但并未深入影响到精子的核物质及其他活性成分,而成功受精的卵子会在冲洗后移入新培养液中继续培养,脱离了可能存在潜伏细菌的精液,不会受到精液细菌的进一步干扰,因而其胚胎发育与男方精液细菌感染的相关性减弱,甚至不受男方精液细菌感染的影响[7]。
不过在IVF-ET的实际操作过程中,精液是经过处理的,所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细菌可能带来的影响。研究表明建议在实施IVF-ET过程中,不仅要对精液标本采用上游法和梯度离心法进行分离洗涤,还要对有些病人进行系统的抗生素治疗后,再进行人工助孕,最大程度地避免细菌污染导致IVF-EF失败[15]。
二、精液解脲支原体培养
解脲支原体(Ureaplasma Urealyticum,UU)又叫溶脲脲原体,是一种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无细胞壁的革兰氏阴性原核病原微生物,也是整个生物学界中尚能找到的能够独立营养的最小型微生物[1]。解脲支原体是男性泌尿生殖系统感染中常见的病原微生物。研究发现,UU感染后可能引起精子质量降低,精子畸形率增高以及产生抗精子抗体。那么UU具体是如何影响到精子的质量以及受精呢?
男性感染UU后,UU可吸附于精子的头部和体部,通过与精子表面的受体特异性结合,造成精子畸形率增高以及结构破坏,降低精子的活动力,同时产生神经氨酸酶样物质,蔽盖精子识别卵细胞的部位,影响其穿透卵细胞的能力,从而干扰精子与卵子的结合,易导致IVF-ET失败[16]。UU感染引起白细胞异常,而白细胞异常可通过引发活性氧(ROS)水平增高等途径,使精子DNA发生氧化损伤[17],UU也与抗精子抗体的产生密切相关[18],可能的机制是UU感染导致生殖道黏膜及血睾屏障损伤,引起精子的自身抗原进入血液循环,从而触发自身免疫应答产生抗精子抗体。冯耀等[19]研究显示:UU感染能够降低精子膜功能的完整性,从而进一步降低精子胞浆内钙离子的水平。细胞内Ca2+浓度的变化在精子成熟、运动、获能和顶体反应等生理过程中均起着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国内还有研究认为UU感染可能与IVF异位妊娠有关[3]。
但也有国外的研究[20]表明在行IVF-ET的男方精液检查中,UU阳性与阴性之间受精率以及临床妊娠率都没有显著差异,并认为对于支原体阳性的男性患者行IVF之前也可能没有必要进行抗生素的治疗。这点也得到了国内一些研究的支持,近年的一些国内研究表明UU感染对IVF -ET的妊娠结局可能没有影响[5]。今年最新的研究得出类似的结论,认为男方生殖道UU培养阳性对IVF的受精率、卵裂率、临床妊娠率及流产率均没有明显影响[21]。马丽丽等[22]对于解脲支原体对IVF-ET结局的影响进行过综述,并且给出建议对于UU阳性而无临床症状的患者,行IVF-ET助孕前不必要投入大剂量抗生素治疗,无需等待UU转阴后启动周期。
虽然之前的研究较多认为支原体感染与IVF-ET最终的结局并无显著相关性,以及提出行IVF-ET不必要投入大剂量抗生素治疗,无需等待UU转阴后启动周期,但这种结论有待进一步更深入更大样本量的研究以及统计分析,但站在循证医学论证的角度来看,就目前已知的国内外许多研究的确表明支原体感染对于IVF-ET最终的结局影响不大。
三、精液沙眼衣原体培养
沙眼衣原体(Chlamydia Trachomatis,CT)是一类能通过细胞滤器,有独特发育周期、严格细胞内寄生的革兰氏阴性原核病原微生物[1]。
有研究发现[23],感染CT者精子浓度、活动力以及精子畸形率与未感染者相比无明显差别,因此认为男性感染不会影响精子功能,从而不影响IVF-ET中正常的受精。推断可能是病原体通过性生活传给女性,引起后者发病造成不孕。但也有研究表明,男性生殖道感染CT 后通过影响精子的运动从而影响卵子受精[24]。可能的机制有CT感染的精液细胞检测发现引起活性氧(ROS)增高,诱发精子DNA损伤,另一方面ROS可以引发精子膜上的多聚不饱和脂肪酸发生脂质过氧化反应,导致精子膜结构与功能损害,导致最终的受精过程受到影响,最终导致IVFET结局失败[25]。CT不仅可以吸附在人的精子表面,进入精子内部,进行大量繁殖,造成精子膜和顶体的破坏,降低精子的受精能力而影响到IVF-ET的结局[26]。男性感染CT后可引发生殖道炎症,有可能侵入睾丸内的生精系统,直接影响精子发生与成熟以及导致精子畸形,精子畸形率较高则可能影响到IVFET的受精率[27]。
CT 感染是否会影响男性的生育能力的问题目前还存在争议。但回顾之前相关的国内外文献可以发现对于精液中存在CT,研究更倾向于IVF结局CT感染者需要临床治愈,复查确认CT转阴后再进行IVF-ET。
结 语
综上所述,针对以上三项精液的微生物学检测在IVF-ET中的临床意义,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可供临床参考:(1)对于行IVF-ET的男性进行精液留取之前需叮嘱其加强手部清洁,除此之外做好取精室的卫生消毒,从源头上避免不必要的污染。(2)对于精液细菌学阳性的患者,需要对其进行系统的抗生素治疗后,再进行IVF-ET,同时精液标本采用上游法和梯度离心法进行分离洗涤也能较为有效地去除病菌。(3)对于支原体阳性而无明显临床症状的患者,可能没有必要一定进行大剂量抗生素治疗,甚至可以无需等待UU转阴即可启动周期。(4)对于CT感染者则需要临床治愈,复查确认CT转阴后再进行IVF-ET。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精液中的微生物可能会由男方传入女方体内,所以治疗时如男方精液中发现有微生物感染,需男女双方同时进行合理地治疗。不过精液在行IVF-ET前需要经过洗涤处理,这样也是可以较为有效地去除致病菌以及支原体衣原体等,减少这些有害微生物对于之后IVF-EF结局的影响。最后,对于精液中发现有害微生物,我们应合理对症地对夫妻双方进行积极治疗,并且应用合理规范的精液处理方法,最大程度地减少精液中有害微生物可能带给IVF-ET的不良影响。
精液/微生物学; 受精, 体外; 胚胎移植;解脲支原体; 衣原体, 沙眼
1 蔡凤, 主编.微生物学.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56-60
2 Pelzer ES1, Allan JA, Waterhouse MA, et al. PLoS One 2013; 8(3): e59062
3 李矛, 周灿权, 庄广伦. 生殖与避孕 2002; 22(4): 216-219
4 杨惠林, 李蓉. 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 2005; 13(12): 743-744
5 孟艳, 王嫜, 刘嘉茵. 临床皮肤科杂志 2012; 41(1): 7-10
6 Krissi H, Orvieto R, Ashkenazi J, et al. Gynecol Endocrinol 2004; 18(2): 63-67
7 陈静华, 张宁锋, 王文军, 等. 中国实用医刊 2011; 38(12): 33-35
8 De Francesco MA, Negrini R, Ravizzola G, et al. Eur J Contracept ReprodHealth Care 2011; 16(1): 47-53
9 Bussen S, Zimmermann M, Schleyer M, et al. Acta Obstet Gynecol Scand 1997; 76(10): 964-968
10 Liversedge NH, Jenkins JM, Keay SD, et al. Hum Reprod 1996; 11(6): 1227-1231
11 Cottell E, McMorrow J, Lennon B, et al. Fertil Steril 1996; 66(5): 776-780
12 Merino G, Carranza-Lira S, Murrieta S, et al. Arch Androl 1995; 35(1): 43-47
13 Nabi A, Khalili MA, Halvaei I, et al. Iran J Reprod Med 2013; 11(11): 925-932
14 Hewitt J, Cohen J, Fehilly CB, et al. J In Vitro Fert Embryo Transf 1985; 2(2): 105-107
15 王韵一. 中国男科学杂志 2008; 22(1): 58-59
16 Núñez-Calonge R, Caballero P, Redondo C, et al. Hum Reprod 1998 ;13(10):2756-2761
17 孙忠凯, 郭凯敏, 刘睿智, 等. 中国实验诊断学 2009; 13(3): 379-381
18 林珠, 闵玲. 国际医药卫生导报 2010; 16(6): 712-714
19 冯耀, 黄宇烽. 实用医学杂志 2009; 25(18): 3074-3076
20 Kanakas N, Mantzavinos T, Boufdou F, et al. Fertil Steril 1999; 71(3): 523-527
21 谢伟, 张海英, 檀大羡, 等. 广西医学 2012; 34(9): 1157-1159
22 范宇平, 潘家坪, 胡烨, 等. 中华男科学杂志 2014; 20(1): 59-62
23 马丽丽, 刘春莲, 徐仙. 宁夏医学杂志 2013; 35(1): 75-77
24 Vigil P, Morales P, Tapia A, et al. Andrologia 2002; 34(3): 155-161
25 Gdoura R, Keskes-Ammar L, Bouzid F, et al. Eur J Contracept Reprod Health Care 2001; 6(2): 102-107
26 万长春, 汪泓, 郝宝金, 等. 中华男科学杂志 2003; 9(5): 350-351
27 郭永忠, 史冰洋, 叶峰山, 等. 中华男科学杂志 2003; 9(9): 708-709
28 陈俊清. 中国实验诊断学 2009; 13(7): 960
(2014-12-08收稿)
10.3969/j.issn.1008-0848.2015.06.017
R 446.144; R 6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