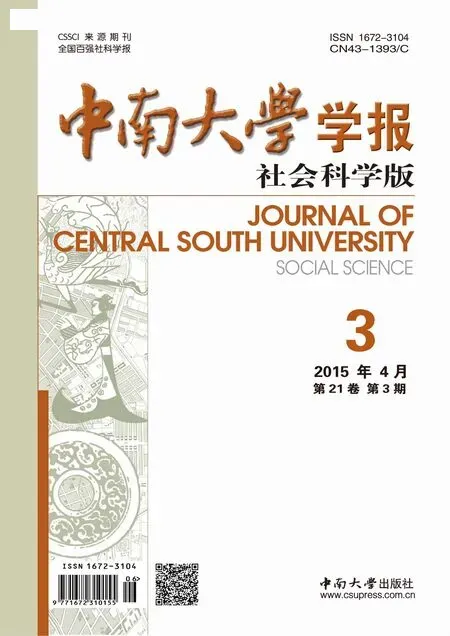可能式“V得C”和“VC了”的文白层次
王自万
(河南警察学院警察管理系,河南郑州,450000)
可能式“V得C”和“VC了”的文白层次
王自万
(河南警察学院警察管理系,河南郑州,450000)
历史文献中的可能式“V得C”和“VC了”语义相同而语用价值有别,分属于文白两个不同的层次,反映了通语和方言口语中实际存在的两种说法。这两种可能式自产生后在南北方言中的发展脉络并不相同,二者并不存在先后替代的关系,今天部分北方方言二者并用是受语言之外的因素影响而造成的,并非语言系统内部因素发展的结果。
可能式;“V得C”;“VC了”;文白层次
可能式“V得C”和“VC了”在汉语方言中的分布大致呈互补格局,“V得C”主要分布在南方,“VC了”主要分布在北方,两种可能式并用的地方很少,只在少数北方方言中存在(钱曾怡1995[1],张安生2005[2],曹志耘2008[3])。北京话采用“V得C”式,不同于北方普遍使用的“VC了”式,显得很特别。柯理思(1995[4]、2006[5])认为:“北京话的例外表现只能从其特殊的形成过程寻找原因。”王衍军(2009)[6]认为“VC了”结构“最迟在明末清初之际于山东方言中已经出现,而且此时该句法格式在方言中与[V得C]式能性述补结构并存并用”。本文拟通过语言事实说明“V得C”和“VC了”分属于文(书面语)白(口语)两个不同的层次,北方方言口语中的“VC了”可能式从元明时期开始在书面作品中有所反映,“V得C”式自产生后在北方方言口语中一直都未普遍使用。近代以来,二者在共同语和方言中的发展结果并不相同,不同的演变过程和北京话的特殊成因可以解释北京话和普通话何以不用“VC了”,而用“V得C”。
一、近代汉语文献中“VC了”可能式的语用特征
(一) 元杂剧中的“VC了”可能式
关汉卿杂剧中已经存在可能式“VC了”的用例,如《窦娥冤》中:
行医有斟酌,下药依《本草》;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元曲选》1500页①)
此处“医不活”和“医死了”相对应,均表示可能意义而非已发生的事实。从上下文来看,“了”的读音和“草”相押韵,二者读音应该接近。
在关汉卿的另一部杂剧《救风尘》中,有一个可以作结果和可能两种理解的“VC了”的例子:
(正旦上,云)小闲,我这等打扮,可冲动得那厮么?(小闲做倒科)(正旦云)你做甚么哩?(小闲云)休道冲动那厮,这一会儿连小闲也酥倒了。(《元曲选》200页)
这段对话末句中的“酥倒了”既可以理解为表示能力,也可以理解为表示已然发生的事实。从上下文来看,问句“可冲动得那厮么”(可V得O)问的是可能,将答句理解为表达可能的形式没有什么说不通。但文中还出现了“小闲做倒科”这样的情景介绍,这样看来答句中的“VC了”也可以做述实来理解。笔者倾向于理解为可能,因为这里和上一例“VC了”可能式有着共同的语用特征。
从使用主体来说,这两例“VC了”都出自下层民众之口。《窦娥冤》中的用例见于赛卢医的四句定场诗当中,赛卢医是一个江湖游医,在剧中角色类型属于“净”,这个角色通常是脾性恶劣的反面人物,《救风尘》中的“小闲”是雇佣来临时帮忙的,类似于仆从的身份。从语用环境上说,以上两例“VC了”均出现在非叙述性语言中。《窦娥冤》中赛卢医的定场诗从说话口吻来看是一种插科打诨的自我介绍,是表明人物身世行动的独白,而《救风尘》中小闲的话语则是纯粹的对话。
(二) 明清小说中的“VC了”可能式
现今发现的明清时期使用“VC了”可能式的小说数量不多,在仅有的已见用例中该结构的语用特征与关汉卿杂剧中基本相同。比如,在王衍军(2011)[7]列出的《醒世姻缘传》中11处“VC了”用例中,有8例出现在对白句中,说话人分别是掌柜的、狄周媳妇、狄员外、素姐、大奶奶、吴学周、寄姐等人,其中3例是教书先生(吴学周)、员外、掌柜的说的,其他5句都出自妇女之口。《歧路灯》中的2例分别出自“滑氏”“王氏”与人的对话当中,也是出自家庭妇女之口②:
惠养民笑道:“等黑了,街上认不清人时,我去给你买去,何如?”滑氏道:“再迟一会月亮大明起来也认清了,不如趁此月儿未出,倒还黑些。你去罢。”于是向床头取出二百钱,递与惠养民。(39回,222页)
巫翠姐道:“你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买一件圈圈子,就弄下一场官司。像我当闺女时,也不知在花婆手里,买了几十串钱东西,也不觉怎的。我到明日叫花婆子孟玉楼,与我捎两件钗钏儿,看怎的!”王氏道:“咱也打造起了,花婆子从来未到过咱家,我从来不认的,何必叫他捎呢?”(55回,318页)
王衍军(2009)[6]所引的《儿女英雄传》中两例分别出自“老爷”和“太太”,前者为叙述语言,后者为对话。笔者检索该书共发现8处“VC了”用法③,7例用在对话中,说话人全都是妇女,用例如下:
(十三妹)想了一想,便对大家说道:“……如今诸事已妥,就便这和尚再有些伙党找了来,仗我这口刀,多了不能,有个三五百人儿还搪住了。……”(第9回,106页)
安太太道:“这两桩事都不用老爷费心,公馆我已经叫晋升找下了。”老爷道:“一处不够。”太太道:“找得这处很宽绰,连亲家都住下了。”(第13回,164页)
褚大娘子是个敞快人,见这光景,便道:“这么样罢。”因合他父亲说:“竟是你老人家带了女婿陪了二叔合大爷回去,我们娘儿三个都住下,这里也挤下了。”(第20回,269页)
张姑娘道:“不用费事了,两分铺盖里都带着梳洗的这一分东西呢。我们天天路上就是那么将就着使,连大姐姐你也用开了。”④(第20回,269页)
太太道:“还要房子作甚么?那边尽办开了。赶到过来,难道不叫他三口儿一处住吗?”(第23回,316页)
正在为难,便听舅太太笑道:“这么着罢,叫他先跟了我去罢。连沐浴带更衣,连装扮带开脸,这些零碎事儿索兴都交给我,不用姑太太管了。你们那天要人,那天现成。”因指着何小姐笑道:“不信,瞧我们那么大的件事,走马成亲,一天也办完了。这算了事了?”⑤(第40回,670页)
二、同一作品中两种可能式各自的语料性质
(一) 近代文献用例和方言中的实际说法的关系
在有“VC了”使用的历史文献中,包括关汉卿杂剧和明清小说,均同时使用“V得C”可能式,那么文献中的这种情况是否能够说明当时方言中也并用这两种可能式,再结合今天北方方言中这两种形式的分布状况,能否得出二者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的结论?笔者认为,要想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弄清近代汉语书面文献语言的性质和同一作品中“V得C”和“VC了”两种可能式各自反映的语言事实。
关于近代书面文献语言的性质,很多学者都做过相似的论述。如胡明扬(1989)[8]谈到:“我国自秦汉以后形成了一个以古代汉语为基础的文言文传统,这以后在宋元时期又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白话文学作品的书面语传统,因此现存的文献绝少有纯粹反映当时当地口语实际的作品,即使是最接近口语的作品,也总掺杂大量的传统成分,再由于汉字很难确切地反映口语的实际音读,普遍存在着用传统的同义或近义语词替代新兴的方言语词的现象。”蒋绍愚(2005)[9]指出:“近代汉语的作品,绝大多数是用通行全国各地的共同语写成的,纯粹的方言作品为数不多。但由于作者受自己方言的影响,在一些用共同语写的作品中也有多少不等的方言成分,呈现一定的方言色彩。”袁宾(1992)[10]认为近代汉语文献语言的两个特点是“口语和文言相间杂”与“常常带有方言色彩,反映了口语的地域性”。笔者认为,可能式“V得C”和“VC了”从语义功能上来说是相同的,都表达述补结构VC的可能意义,从语言系统经济性的角度来看,不可能用两种完全同义的不同结构式(且都是述补结构),二者出现在同一作品中很可能代表了不同层面的语言事实。
(二)“V得C”和“VC了”分属的两个层次
在这些作品中,“V得C”的比例占绝对优势,这种形式不仅出现在作者的叙述语言当中,也出现在人物的对话当中。以《歧路灯》为例,“V得(的)C”结构在普通民众口中也说,是否说明该结构也存在于当时的河南方言民间口语中呢?笔者认为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文学作品的叙述语言大多反映当时的通语,作品中有些人物的对话语言可能也不是当时民间方言的真实反映,这些人物往往有着较高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等特征。
从“V得C”式的产生发展来看,“V得C”产生定型于唐宋时期,这种结构相对于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来说反映了当时的口语,广泛见于唐代变文、宋儒语录当中。而唐宋时期的通语是此后白话文所使用文学语言⑥的前身,“V得C”结构作为一种正统的书面语言中的一种形式在民间创作、文人加工的话本、小说中得以传承,即便是在具有浓厚方言色彩的《歧路灯》《醒世姻缘传》和《儿女英雄传》这样的白话小说中也占有绝对优势。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河南、山东和北京方言区的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说的是一种形式,到了文学作品中很可能改用另一种形式,这就造成在舞台上、小说中的人物说出他们生活中并不使用的“V得C”,这种现象也是口语转化为书面语过程中常见的做法。不同阶层的民众都使用“V得C”的事实恰恰反映了这种结构作为文学语言具有通语性质和书面语特征(“文”层)。
“VC了”可能式的语用特征说明该结构的确是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用语,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口语最能反映当地方言实际,尤其是家庭妇女的日常对话,通过采用富有特色的地域方言来塑造鲜活人物形象也是文学作品常用的方法。因此笔者认定这些作品中的“VC了”用例反映了当时这几地方言中的实际说法,是和通语中的“V得C”相对应、体现其方言特点的一种特殊结构。具体来说,关汉卿杂剧代表的不仅仅是元大都话的面貌,而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北方话,《醒世姻缘传》《歧路灯》分别带有当时山东、河南方言特点,《儿女英雄传》则是带有清末北京话的特点,其中包括属于北京话但不是共同语的成分,即北京土话。在这些方言的历史上,都存在“VC了”可能式,这种结构具有方言性质和口语特征(“白”层)。
三、“V得C”“VC了”近代以来在方言中的发展
(一)“V得C”的发展
梅祖麟(1994)[11]认为,可能式“V得C”结构最初发生于以长安为标准的唐代北方方言,当北方方言在晚唐宋初时期变为全国的共同语时,该结构也散播到其他方言。从今天方言现状来看,南方大部分地区方言(含西南官话,不含闽语)使用“V得C”式,但在华北很大一部分地区方言当中,是排斥这种可能式的,有很多地方与“V不C”相对的肯定说法只用“能VC”(柯理思1995[4],乔全生2000[12]),一些地区则使用与之对应的“VC了”结构。即便在该结构产生地,今天这种形式的使用也受很大的局限,西安方言中可能式“V得C”仅在疑问句中可以使用,不在肯定句中独立用来表达可能意义(王军虎1997)[13]。根据曹志耘(2008)[3],在东北大部分地区,基本不存在“V得C”和“VC了”这两种可能式⑦。
由此可见,可能式“V得C”从产生到今天,在北方一些方言(非通语)中并未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接受。在反映12世纪北方方言基本面貌的金刻本《刘知远诸宫调》中,“述语+可能补语”构成可能性述补结构肯定形式的只有“VC ( O )”,其中的C包括“得”“过”“跌”“住”等动词,但没有“V得C”形式(杨永龙、江蓝生2010)[14]⑧。而通常认为,“V得C”可能式从唐末变文开始萌芽,至宋代已经开始独立使用,可以不依赖于语境而表达可能义,用例在通语中随处可见,但此时的《刘知远诸宫调》中却没有使用,足见当时北方地区某些方言中没有“V得C”可能式的事实。
由此我们反观该结构和北方方言的关系,认为可能式“V得C”是在通语、而非纯粹的北方方言中产生的(当然,这种通语带有北方方言的某些特征),在北方的一些区域,“V得C”可能式自产生开始至今都不存在于老百姓的方言口语当中。
在南方,“V得C”可能式在方言中得以广泛传播。北宋末年的宋室南迁,加剧了北方通语对南方方言的影响。由于北方地区政治形势的变化,北方汉语方言在全社会的语言声望逐渐下降,作为标准语基础方言的地位也发生了改变,与之相伴随的是南方官话地位逐渐上升。有研究认为,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南方话,直到清末,南方官话的地位都高于北方(鲁国尧1985[15]/2007[16],张卫东1998[17])⑨,而“V得C”可能式是存在于这种官话当中,同时,该结构在南方的方言口语中也广泛存在。
北京话的情况也许是个特例。从唐代开始,北京一直是北方重镇,元代起又成为首都,北京特殊的城市地位决定了北京官话相对于其周边北方方言,受共同语和文学书面语言中的影响也会更多,北京话中的“V得C”可能式就是受这种影响而形成的。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加上明代迁都带来的南京话的影响,以及20世纪初期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新中国成立后的推广普通话运动,造成了北京话中“V得C”可能式的一统地位,而作为和周边华北地区方言相协调的北京土话(其中含“VC了”可能式)则逐渐衰微。在今天的北方方言中,省会城市济南(钱曾怡1995)[1]、石家庄(袁家骅等2001)[18]以及山西、山东、河北的一些县市方言中,存在可能式“V得C”,这都可以视为在共同语和权威方言的影响下,该结构在北方话中的发展,在并用“VC了”的地区,“V得C”只能作为方言中的外来层次而存在。
(二) “VC了”的发展
“VC了”可能式最迟在元明时期的北方汉语中已经形成,当时在华北地区有着广泛的分布。清末《儿女英雄传》中的“VC了”可能式用例,说明当时的北京方言中有这种形式,至少说是不排斥(即不常说、但能听懂)这种广泛分布于华北地区方言中的说法。此后,北京话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该结构逐渐趋于消亡,现代北京话中没有可能式“VC了”,但我们还能在今天的北京话中,看到某些曾经存在“VC了”可能式的痕迹。
可能标记“了”的前身是用在复合句中前一小句末尾作补语的虚化动词“了”,其发展过程是“先后关系标记——假设关系标记——可能标记”(王自万2012)[19]。从现代北京话的某些特征来看,北京话具有产生这种可能式的条件,北京话中曾经存在一个这样的“了”。陈刚(1957)[20]证明北京话中有一个用在祈使句、条件分句、假设分句末尾的“了”(lou);马希文(1982)指出北京话中有一个做补语的动词“了”(lou)[21];胡明扬(1987)说“喽”有人写作“咯”,大概是轻声的原因。“喽”也可以是“了”的一种变体,用在比较土的家常语体中,带有亲昵和玩笑的意味。[22]这些记录反映了20世纪中后期的北京话的状况,应该是直接继承了清末北京话的说法。
而在今天河南、河北、山东等地“VC了”仍有广泛的分布,在很多方言中依然是唯一的一种可能补语结构形式。但由于从北宋之后中原官话地位逐渐下降(何九盈2007)[23],该结构未成为通语中的形式,在一些区域中心城市及靠近京津的地区,也逐渐让位于可能式“V得C”,只在方言口语层中有使用。
这种形式在现代汉语书面作品中几乎见不到任何用例⑩,究其原因,一方面和该结构属于方言口语(“白”)层次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可能标记“了”和完成体标记“了”、语气词“了”无法在书面上区分有关(在口语中是靠不同的读音来区别)。但是现有辞书中对北方口语中的这种可能式还是有所反映的,在《现代汉语八百词》“下”条目中谈到[24]:
“动+得(不)+下[+数量+名]”格式可以表示能(不能)容纳一定的数量。有时不加“得”,仍然表示可能。
不就二十斤吗?这个口袋装下了︱这屋子大,再来几个人也睡下了。
“开”条目(第330页)下也列有这种用法。
这屋子十个人也住开了|书摆开了,还要不要书架。
但观察这种无“得”的可能式,末尾都有一个“了”,这里的“装下”是和“了”一起表示可能意义的,其中的“了”为必不可少的可能标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VC了”可能式。⑪
另外,《现代汉语词典》词条“开”(第五版754页)[25]下有一项解释为:
趋向动词,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后,表示容下:屋子小,人多坐不开|这张大床,三个孩子也睡开了。
此处“睡开了”也是“VC了”可能式,这些例子中能够充当补语C的词语仅限于“下”和“开”,这两个词在《儿女英雄传》中也多次出现在可能式“VC了”中C的位置上,所以这两部词典中记录的“VC了”可能式反映的是北方方言的实际用法,属于北方话口语(“白”)层次的内容。
四、结语
早期的“VC了”可能式主要出现在社会底层民众的日常口语当中,体现了方言中不同于共同语的表达方式,这种可能式自产生起一直未取得正统的书面语地位,始终属于“白”的层次。“V得C”可能式自产生开始,就成为了近代白话文学的标准书面语言,也逐渐发展成为民族共同语中的表达形式,属于“文”的层次,在北京土话中逐步取代了“VC了”,使得今天北京话在这一点上不同于其周边的北方话。
可能式“V得C”和“VC了”属于文白两个层次,前者属于共同语、文学语言、书面语言,后者属于方言、生活语言、口头语言,二者并不是同一语言系统中存在先后继承、替代关系的两种形式。北京话中“VC了”的消亡和移民、权威方言的影响等因素有关。北方部分地区方言混用两种可能式亦是由于这种外在因素的影响所致,并非语言自身内部要素的发展结果。
注释:
① 页码据《元曲选》,(明)臧晋叔编,中华书局1989年重排版。下同。
② 以下两例王衍军(2009)有引用,笔者核对了齐鲁书社1998年版《歧路灯》(李绿园著,昭鲁、春晓校点)原著,加注了该版本中的页码。
③ 王衍军文中引用的第一例(“老爷”的叙述语言中用例)本文未重复列出。以下所标页码依据文康著,周树德、吴效华校注《儿女英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④ 据《儿女英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73页注释:“用开了”是“够用的意思”。根据我们的理解,此处“用开了”也是“VC了”可能式,相当于“能用开”“用得开”,表示有限的物品能够为多人轮换使用。
⑤ 我们觉得此例中的“办完了”和“算了事了?”都是可能式,相当于普通话“办得完”“算得了事?”。
⑥ “文学语言”是加工、规范的书面语,不同于“文艺作品的语言”。详见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增订三版)上册第2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⑦ 仅辽西(迟永长2002)、哈尔滨(尹世超2002:328)有“VC了”可能式,未见东北地区方言有“V得C”可能式的报道。
⑧ 原文页下注说:有一例似乎是“V得C”,但前面有缺文,不知确切意思。
⑨ 这些文章谈的主要是标准语音的问题,笔者认为语法格式也存在同样的标准问题。
⑩ 只有雅洪托夫(1958:163)认为《新儿女英雄传》中一处和“赶不上”相对的“赶上了”是“VC了”可能式,但根据上下文看,该处“赶不上”用在假设句中,不一定包含“不能”的意思,或“不能”的意思很不明显,而只表示做了某个动作,但没有取得某种结果(刘月华1980),那么与之相对的“赶上了”也未必就是可能式。
⑪ 因为可能式之后不用动词后缀“了1”(赵元任1979:206、朱德熙1982:132),如果认为这里的“了”是接在可能式上的句尾语气词“了2”,句子的意思衔接上有问题,“这个口袋装下了”相当于“装得下了”,意思是“换了很多口袋都装不下,现在这个可以装下了”,这种理解和前面的“不就二十斤吗”很难相适应。
[1] 钱曾怡. 《济南方言词典》引论[J]. 方言, 1995(4): 242−256.
[2] 张安生. 同心方言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295.
[3] 曹志耘. 汉语方言地图集·语法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71.
[4] 柯理思. 北方官话里表示可能的动词词尾/了[J]. 中国语文, 1995(4): 267−278.
[5] 柯理思. 北方方言和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从几个具体的事例谈起[C]// 邢向东. 西北方言与民俗论丛第2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102−117.
[6] 王衍军. 《醒世姻缘传》中的[VC了]式能性述补结构试析[J].暨南学报, 2009(3): 117−129.
[7] 王衍军. 《醒世姻缘传》中的[VC了]式能性述补结构[J]. 方言, 2011(3): 284−286.
[8] 胡明扬. 《西游记》的助词[J]. 语言研究, 1989(1): 54.
[9] 蒋绍愚. 近代汉语研究概要[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324.
[10] 袁宾. 近代汉语概论[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22−25.
[11] 梅祖麟. 唐代、宋代共同语的语法和现代方言的语法[C]// 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247−285.
[12] 乔全生. 晋方言语法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161.
[13] 王军虎. 西安方言的几个句法特点[J]. 西北大学学报, 1997(3): 32−33.
[14] 杨永龙, 江蓝生. 《刘知远诸宫调》语法研究[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0: 231.
[15] 鲁国尧. 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J]. 南京大学学报, 1985(4): 47−52.
[16] 鲁国尧. 研究明末清初官话基础方言的廿三年历程——“从字缝里看”到“从字面上看”[J]. 语言科学, 2007(2): 3−22.
[17] 张卫东. 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J]. 深圳大学学报, 1998(3): 73−78.
[18] 袁家骅等. 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1: 52.
[19] 王自万. 汉语方言可能式研究[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2.
[20] 陈刚. 北京话中lou和le的区别[J].中国语文, 1957(12): 33−34.
[21] 马希文. 关于动词“了”的弱化形式/·lou/[J]. 中国语言学报, 1982(1): 1−14.
[22] 胡明扬. 北京话初探[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94 .
[23] 何九盈. 论普通话的发展历史[C]// 汉语三论.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7: 117−195.
[24]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567.
[25] 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Z].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754.
Literary and oral strata of potential complements “V de C” and “VC le”
WANG Ziwan
(Department of Police Administration, Henan Police College, Zhengzhou 450000, China)
The potential complements “VdeC” and “VCle” which coexist in the same historical literature are not synonymou structures in one language system, but rather belong to the different strata of the Literary and the Oral. The two types of potential complements reflect two different structures in common language and northern dialects. Ever since they emerged, they have had different development effects in regional dialects of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The coexistence of these two structures in some northern dialects is caused by the authorative dialect where “Vde C” comes from.
potential complements; “V de C”; “VC le”; the literary and the oral strata
H17
A
1672-3104(2015)03−0274−05
[编辑: 胡兴华]
2014−11−07;
2015−03−05
2014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开封方言变韵调查研究”(2014-gh-743)
王自万(1972−),男,河南开封人,文学博士,河南警察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汉语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