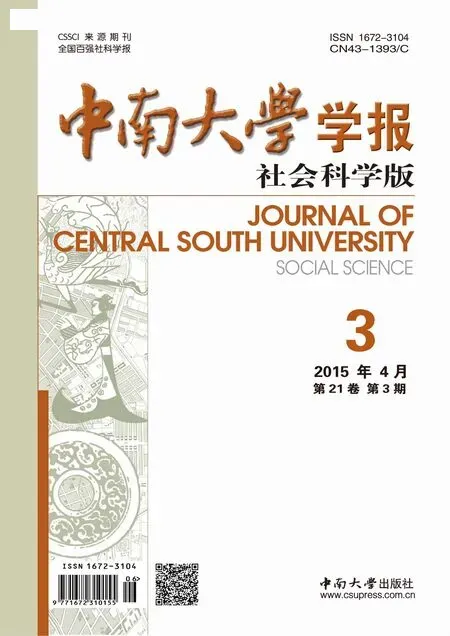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中经典文本的建构
周才庶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与法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中经典文本的建构
周才庶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与法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人们对于经典的期待视野在于,经典是权威、典范的作品,在人类文化发展中有着久远的感染力量。在中国电影产业化的进程中,出现了群选经典化的趋势,这是观众能动作用加强的结果,也是电影经典建构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新问题。电影产业中经典文本的建构不仅由学术精英进行指引式判断,而且参照大众的评价。大众并非缺乏文化积累的群体,他们往往能够提供质朴的观影体验。电影产业中经典文本的建构是对文化资本进行选择和分配的结果,经典作品将是文本必然性与文化任意性相结合的产物。
电影产业;经典;群选经典化;大众;文本
当代中国电影产业飞速发展,电影的产量和票房逐年增加。在资本运作的电影产业中,如何评判产生电影经典?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突出现象:一方面,专业的影评人员或者电影从教人员列出一些经典影片,进行“经典影片鉴赏”, 并出版一些所谓经典电影鉴赏的书籍,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经典电影作品赏析读解教程》、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10年出版的《世界经典电影鉴赏》、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世界电影经典解读》等。另一方面,观众自发地将某些影片称为“经典”,在网络上出现经典影片的排行榜,或者产生一些“经典影片推荐”表单。关于电影经典的遴选显得非常热闹。与此并不一致的是,对电影经典建构的系统讨论尚未出现。
电影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生命,尚缺乏代代传承、世纪积累的厚重感。在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讨论电影经典会显得过于急迫,极易遭受质疑。有的学者认为对经典的预言要在作者死后两代人左右才能被证实,经典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形成的。讨论当代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中的经典影片似乎是一件冒险又不识时务的事情。但是,当代影片中的一部分会在将来成为经典,而且在观众大量介入电影场域的背景下,经典的建构必然有所变化。面对新的文化生产环境,断定或预言哪些作品能够成为经典并非要务,更重要的是认识电影经典建构的可能性和特殊性,进而更好地理解当代的文化氛围与社会结构。
一、对于经典的期待视野
什么是“经典”?从字源上来看,“经”指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后引申出“常道”“规范”等义。《礼记·中庸》“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1](1630),《孟子·尽心下》“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2](2780),《文心雕龙·宗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3](21)。“典”本是记载帝王言行的史书,在形制上大于一般的书,也有人称之为“大册”。《说文解字》:“典,五帝之书也。”“典”引申为“常道”“常法”,指传授法则和规范的书籍。“经典”旧指作为典范的儒家载籍。现代汉语中“经典”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或泛指各宗教宣扬教义的根本性著作。[4](598)辞海对“经典”的解释是一定的时代、一定的阶级认为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著作;古代儒家的经籍;也泛指宗教的经书。[5](1164)
与汉语“经典”对应的英文canon最初与宗教有关,被视为《圣经》或与《圣经》相关的各种正统的、记录了神圣真理的文本,后引申为教规,再度引申为典范、法规、标准等义。18世纪以后,canon超越了《圣经》经典的范围,延伸至文化领域,比如指文学的经典。《新牛津英语词典》将canon定义为“特定作家或艺术家的真正作品”,如莎士比亚经典;以及“被认为是永恒地确立了最高典范的文学作品”[6](267)。经典被归为某些特定作家创作的作品,它们凭借自身的文学特质和价值而优于其他作品。
可见,在中文和英文中,“经典”这个词可以指与宗教相关的典籍,也可以指具有权威性、典范性的作品。人们对于经典的期待视野在于,经典是被权威认可的作品,有无可置疑的文化光环和永恒价值,在人类文化发展中有着久远的感染力量。然而许多作品并非生而经典,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蜕变过程。
文学经典的建构和重建一般是由知识分子进行,他们从历代积累的大量文本中,选出小部分公认的精品,然后加以传播和世俗化,这是一种精英式建构。张隆溪指出:“在最一般的意义上,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在于它不仅属于某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而且能克服历史距离,对不同时代甚至不同地点的人说话,因此经典‘没有时间性’。”[7](179)他所谓的“无时间性”是指经典在长期的历史理解中能随时作为当下有意义的事物而存在。经典能够超越特定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接受者将自己的感悟与经典所能给予的体验相互融合。文学经典是被权威遴选并被世人所常用的名著,经典能经受不断的重读,经典具有不断被阐释的潜力。
在经典的解构和重构浪潮中,美国学者布鲁姆带着一种怀旧情绪和伤感情怀写下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此书列出了莎士比亚、但丁、乔叟、塞万提斯等26位经典作家,辨析这些作家作品经典的特性,即那些使他们成为文化权威的特性,书写这些作家的崇高性和代表性。布鲁姆将新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和女性主义称为“憎恨学派”[8](3),指责他们为了实行社会变革而颠覆现存的经典。布鲁姆并不认同由社会体制的力量来重估经典,他始终站在文本的审美价值角度来对传统经典进行解读和捍卫。他认为应该回到文学的自主性想象中去,回到个体孤独的心灵中去,让读者反观深层的自我,与终极的内在性沟通。“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渗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思维、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8](23)“西方经典不管是什么,都不是拯救社会的纲领。”[8](23)布鲁姆强调经典的文本特征及审美力量,从文本内部的规律而不是从社会学维度对经典建构进行分析。文学经典的建构是学术精英按照严格的艺术标准建立的,经典作品会给以后的作品造成一种“影响的焦虑”。
文学经典的建构也会给电影经典的建构造成一种“影响的焦虑”,正如文学不断地给电影施加压力。电影经典的建构很大程度上是在位移文学经典建构的特征,比如对文本审美力量的重视、对外在社会力量的考虑等等。然而,当代产业化进程中电影经典的建构已然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经典建构,它非常顾及大众评价,观众大规模地参与到作品的评判中。大众有巨大的经济资本比如票房,有重要的社会资本比如票选。艺术作品一向需要观众的接受,观众也一向有自己的好恶评判,不过在传统的经典评判中,大众与之并无太多的牵扯,这是知识分子的事情。但在网络等新媒体快速发展之时,在电影产业化的进程中,大众的评判进入到经典的建构中来。知识分子手中所掌握的经典配置的权力受到严重的质询和挑战。在产业化进程中,电影经典的建构已经不是纯粹由学术精英进行的指引式判断,而是有意无意地参照大众对影片的群体化反应。
二、群选经典化的趋势
自2002年以来,中国电影正式走上产业化改革与发展的道路。电影产量、票房、观众人次迅速增长,影视基地、影院的建设全面推广,中国电影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面貌。在电影产业的发展历程中,观众的地位日益凸显。观众不仅通过票房、网络评分表现出对影片的喜好,而且通过杂志、网络等大众媒介发表评论,造成一定声势。观众群体介入电影场域中,以购买、评分、点击、下载、评论等方式对电影产业施加影响。观众通过网络平台或影院的相关活动可以自行评选出年度或历年最受欢迎的影片,使得这些影片的接受范围进一步拓宽。观众在接受维度对经典影片的遴选产生了一定作用,这是群选经典化的趋势,也是当代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2002年的影片《英雄》(张艺谋执导)票房4 250万元,截至2015年4月,该片在豆瓣上的评价人数超过9.7万,在时光网上评价人数达到11.9万以上。2003年的影片《无间道》(刘伟强、麦兆辉执导)票房3 600万元,该片在豆瓣上的评价人数超过10.7万,在优酷上的播放次数超过759万。2003年的影片《手机》(冯小刚执导)票房4 500万元,该片在豆瓣上的评价人数超过8.6万,在时光网上评价人数为6千多。2006年的影片《云水谣》(尹力执导)票房3 600万元,该片在豆瓣上的评价人数超过7.9万,在时光网上评价人数为5千多。2007年的影片《集结号》(冯小刚执导)票房1.8亿,该片在豆瓣上的评价人数超过9.1万,在时光网上评价人数达到10.8万人以上。这些影片的受众反应大多良好,同时它们也进入教材,不同教材往往以它们为典范进行影片鉴赏。电影是面对受众的,电影只有被观看和接受,其生产过程才算真正完成。在传统的文学接受过程中,受众往往是以一种私人化的体悟来面对文本,继而由一些专门的评论者来发表评论,也就说受众并没有在公共平台展示出规模化的受众反应。如今,受众并不是默默无闻地面对影片,他们通过大众媒介强势地宣扬自己的喜好,大众媒介也为观众的宣泄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观众一方面可以在影视网站上参与评分、发表评论,另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博客、微博发表意见、实时传播,在公共领域公开地展示出他们的反应。
赵毅衡在《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中指出,当今文化中有大众群选经典化和批评性经典重估两种经典评估方式,分别沿着组合轴和聚合轴这两轴展开。组合轴和聚合轴是符号文本的两种展开向度,组合轴是符号组合成一个有意义的文本的方式;聚合轴是符号文本每个成分背后可供比较与选择的各种成分,聚合轴上可供选择的因素是作为文本的隐藏成分而存在的。批评性经典重估,是在符号聚合轴上的比较选择操作,它由知识分子担当和传承。知识分子面对历代前辈的作品进行比较和斟酌,确立经典。大众群选经典化是在组合轴上进行的,“大众的‘群选经典化’,是用投票、点击、购买、阅读观看等等形式,累积数量作挑选,这种遴选主要靠的是连接:靠媒体反复介绍,靠亲友口口相传,靠生活轶事报道”[9](389)。他认为,群选经典是无须批评的,与金庸小说迷讨论金庸小说的质量几乎是不可能的。群选经典这种方式,不是供批评讨论的,而是供追随的,其他人无法对之进行分析性的辩论。群选经典的连接,使得某些艺术的命运取决于它能否在大众的组合连接中给人提供快感满足、提供个人欲望的在场实现。群选经典使得大众在意义漂浮的后现代社会中找到共同爱好的组合,得到社会归属的满足感,从而驱除孤独个体的漂浮感。群选经典的扩散,使得经典阅读产生了危险。“文学场向组合轴倾斜趋势,如果没有遇到阻抗,最终会导致聚合倒塌消失,于是整个文化成为单轴运动:经典无须深度,潮流缺乏宽度,剩下的只有横向的线性粘连,只有粉丝式的群体优势。”[9](392)
索绪尔把聚合轴称为“联想关系”,是凭记忆而组合的潜藏的系列。聚合轴可以说是一种选择轴,其功能是比较和选择,也就是说聚合轴为符号文本的组合提供了丰富的潜在资源。从文化上来看,在聚合轴上进行符号选择需要有足够多的文化沉淀和知识功底。赵毅衡认为,不同于知识分子在符号聚合轴上的操作,群选经典化是在组合轴上进行连接,这种连接缺乏丰富和深层的知识内涵。也就是说,大众只是在一种平面化的维度进行挑选,他们的知识构成和文化积淀难以在纵深维度提供聚合挑选。
文化生产领域被知识分子分成严肃与通俗两个部分,两者有相似的特征,都是虚构的创作,但它们在价值方面又被区分开来。严肃的作品被认为是高雅脱俗的艺术类型;通俗的作品被认为是切合大多数平庸乃至贫乏口味的类型。精英群体被对应于严肃的作品,而大众则被对应于通俗的作品。传统认为,经典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只是知识精英的旅程,无关大众的欣赏评判。一旦大众介入进来,将使得知识分子的经典建构权威破溃,经典将失去神圣的光彩。大众,似乎只是一个盲目而低劣的群体,只会点击、跟从、崇拜,并表达无来由的爱恨。面对他们,知识精英莫非只能带着不可言说之痛退回到自身的伟大思考之中?大众,莫非只能揣着麻木而迟钝的心灵去尾随精英的评判?大众的体验是一种危险因子,必须被逐出经典的建构圣地么?在当下的文化发展状况中,大众能够确立文化的世俗权威,而这种世俗权威影响着经典的建构。因此,群选经典化并非经典建构的堕落,而是给经典建构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单只是大众流行性不会为经典化提供充分的理由,否则每部曾经流行过的作品都可以被看做‘经典’的了。”[10](377)在大众流行中筛选下来的经典必然有超出仅仅使之流行的素质。
综观关于电影的大众评价,我们能发现诸多简洁、表层的评论,带着感性色彩,释放粗野的霸气。比如“真他妈过瘾”“NND真好”“牛着逼”“那句台词太猛了”等一些缺乏分析而纯粹是表达感受的评价。更多的则是大众对影片的内容、画面,对导演、演员做出平凡易懂的评价。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1](2479)如果说精英式的评判是对文本进行了思想和文句的雕琢,那么,大众化的评判则带着“质”的朴野直接生成了判断。从表面上看,大众评价是一种数量化的无深度运作,事实上,大众评价是在袒露着最原始的喜好。大众的检验不带有学术派别之间的斗争,不介入意识形态的偏好,它更多依附于文本自身感动人心的力量。“世俗经典的形成涉及一个深刻的真理:它既不是由批评家也不是由学术界,更不是由政治家来进行的。作家、艺术家和作曲家们自己决定了经典,因为他们把最出色的前辈和最重要的后来者联系了起来。”[8](433)“伟大的风格就足以证实作品的经典性,因为它们具有感染力,这种感染力正是对经典形成的实际检验。”[8](433)知识精英往往是文化机构或权力机构的组成成员,他们有意无意地设置术语的壁垒,树立文化的权威,他们对经典的建构正是从美学到政治的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协商性结果。大众评价则是一种草根式的规模效应,它们更多的是基于文本的非功利判断。电影属于大众文化,电影的消费是大众化消费,因此,时下对于电影的美学和文化的裁决,是大众的裁决。
大众评判更多的是基于文本本身的力量,由文本来决定影片的经典地位的强度就加大了,由评判者来决定经典地位的力度就有所衰弱。群选经典化的介入,事实上督促电影生产者从文本出发进行生产,而不是过多地去讨好政治权力的因素。这样,在另一个层面上就形成了一个问题,电影的生产考虑到大众的喜好和评价,就将逐渐疏离学术权力、政治权力的书写,是生成诸多商业化的因素来讨好观众。或许,这不过是从一个囹圄走向另一个囹圄。群选经典作品的意义并不在于让人们体会自己的孤独,而是将自己的孤独与它者的孤独联系起来,构成一种群体化的感受和认同。大众并不是深沉地去面对伟大作品,而是化解日常生活中琐碎的烦恼和无聊的空闲。批判式的经典建构基于知识分子对作品的深层感知,知识分子个体将文本对象与自我的学术生命结合起来,经过一段孤寂而严肃的阅读体验得出评判。不同知识分子之间的评判经过争论和制衡,加上政治因素、社会因素等外力的作用,历经时间检验和历史沉淀,使得经典作品破茧而出。群选经典化的介入,使得大众的观影经验成为经典谱系的参照因素,大众狂欢和大众认知对经典建构起到了干预作用,一种无关政治、无关学术的生命冲动得以彰显。因此,电影经典的建构应该是知识分子和大众群体共同决定的结果。
三、电影经典:文化资本的选择与分配
电影经典的建构是在电影场域内对文化资本进行选择和分配的结果。一方面某些影片的经典地位在教材中得以确立,另一方面,随着大众参与到文化消费中,群选经典化呈现为一种新的趋势,经典的建构越来越考虑到大众的喜好。
当代电影产业中的经典评判来自于票房、受众评价、教材等多种途径,而根本上来自于体制化的裁决,主要以教材加以确定。某些影片进入教材,它们就获得了与过去受到认可的作品相匹配的价值。某一部教材对影片的遴选与其他教材的选择相配合,形成有意义的组合段,教材的连贯性选择与配合构筑起影片在体制内的地位。美国学者杰洛瑞所著《文化资本——论文学经典的建构》一书从社会体制和语境中考察经典形成的问题,认为经典问题的关键在于学校课程设置中文化资本的分配。学校控制了社会应当如何读写,学校也是一个创造阶级差异的场所,学校复制了社会的秩序,带上了各种不平等的烙印。学校通过课程教育、撰写教材、颁发文凭等方式成为一个真正有权力分配文化资本的地方。经典的形成也反映了阶级的利益,经典成功地为某些特殊的社会利益代言。杰洛瑞运用布尔迪厄“文化资本”这个为人熟知的概念,对教学大纲中经典的重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把经典的建构当作文化资本的形成与分配问题,从社会体制和语境来考察经典的形式,其研究思路完全不同于美国新批评家布鲁姆立足于文本的思路。杰洛瑞从体制和历史的规律来看,认为经典的意义不在于文本之内,而在于文本之外。
事实上,电影文本作为文化资本的承载客体,是文化价值的储藏地,文本之外的评奖、评分都围绕它进行。对经典文本的遴选,既是对内在于文本的审美价值的遴选,也是对外在于文本的政治价值的遴选。教材在选择与排除作品的过程中却越来越考虑到影片在大众中产生的效应。我国当代影片《英雄》《十面埋伏》《甲方乙方》《大腕》《手机》《天下无贼》《云水谣》《集结号》《无间道》《功夫》等等,在观众中影响广泛,同时也得到了教材的分析。因此,当下电影产业中经典的建构,不仅是知识精英通过教材等体制化方式加以确定,而且应参照大众通过新媒介对影片的选择和评价。在大众对影片的接受产生群体性的轰动反应之时,一方面知识精英们有意无意地对照或接纳大众的能动反应,从而将之纳入体制化的经典建构中来;另一方面大众也形成自身的话语方式和判断方式,从而流传一些“民间版本”的经典谱系,比如网络上出现的“经典影片100部”,它们在论坛、微博、微信、QQ上得到链接与转载。之于电影经典,文化资本选择和分配的主体既来自于强势的知识精英,也来自于广泛的大众群体,因此,关于经典的文化斗争是多方面的,一是来自知识分子内部的严肃正义的较量,二是来自大众内部叽叽喳喳的争吵与辩论,三是来自于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争锋。电影经典的建构作为一个文化事件,产生各种彼此交锋的势力。
布尔迪厄认为文化具有任意性。为何特定的文化形式被激发,没有理论上的原因,而是一种文化任意性。为什么某种口音或审美判断属于上层阶级,而另一种口音或审美判断属于工人阶级;为何某些文化被认定为高级文化,另外一些则被指认为通俗文化。文化内容与实践在历史上是任意的,某些内容被选定,没有理论上的原因可以加以说明,是特定的社会结构决定的。在布尔迪厄看来,受社会排斥的艺术家在尘世中遭遇不幸,可能在彼世受到选择。尘世中的商业成功可能在彼世遭遇谴责。经济上的失败可能与另一种成功的形式结合在一起。这种选择不具有必然的理由,是由社会结构所造就的。
布尔迪厄关于文化任意性的观点旨在说服人们放弃对艺术家的卡里斯玛型崇拜。不要充满理想主义地将艺术家简单地看成是创作者,他亦处于特定的场域之中,一定的社会关系造就了艺术家的身份和地位。布尔迪厄通过挖掘社会场域对一个艺术家的创作以及经典文本诞生的作用。认为哪些文本和艺术家被遴选,是一种文化任意性。同时我们要指出,在考虑社会结构的同时,不得不考虑到艺术家或文本的自身水平,考虑到他们特定的审美价值。固然,同等水平的两个文本,基于不同的社会状况,文本A可能被极大地认可,乃至建构为经典,文本B可能淹没于尘世。A与B的不同境况由社会结构决定。但是,如果文本A本身的艺术水准太过低下,它便无法进入经典选择的范围。所以,经典的选择并非不具备必然的理由,而是必然有一定的理由,它是文本水平和社会结构相互妥协的产物。
文化等级的区分特别是经典的建构,确实具有偶然的因素,也就是布尔迪厄所谓的“文化任意性”。同时,我们也强调另一种底线,即成为经典的影片必然达到了良好的制作水平和艺术水平。既然经典的建构不是僵死或封闭的过程,而是一个开放且带有一定任意性的过程,文化资本的选择和分配不是平均的,那么,建构主体比如知识精英和大众就凸显了其能动作用。“知识分子受到教育的整体逻辑的培养,这种培养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去处置那些从历史中作为文化继承来的作品,换言之,去处置一笔他们需要凝视、尊敬、歌颂的财富,同时,这一事实也赋予了知识分子某种威望。总之,作为累积而成的财富,注定要被展出,注定要产生出象征性的红利,或者产生出仅仅是自恋性的满足感,这笔财富显然不同于你为了产生某种结果而投资在研究中的生产性资本。”[12](36)知识分子必须面对以往的知识经典,占有、阅读和思考它,这成为知识分子的劳动,同时这种劳动也成为他的财富,使他们获得威望。知识和成就要被展出,产生现实的物质效应以及精神上的满足感。在这种习惯的作用下,知识精英以他们的知识威望和文化财富去审视当代电影产业。他们试图树立一些供后人凝视和敬仰的影片,于是,在当下的影片集群中寻找能与继承下来的文化经典相匹配的作品,并对这些影片进行解读和定位。另外,大众则依据自己的喜好,通过消费(产生票房)和评价(产生评分)产生链接式的效应,传达对影片的看法。相比之下,大众与电影保持一种粗野的关系,他们根据自己的感官愉悦和情感满足进行判断。大众的网络评分和评价,对影片的观看次数和下载次数已经呈现出重要的参考意义。群选经典化就是电影经典建构的一个新特征。
四、结语
电影产业为通俗文化产品提供了更庞大的生存空间。我们不该再以父辈的严肃传统来对抗新兴的文化形式,而是要建立一种既不孤傲也不卑微的文化立场。电影经典的建构,受到文化资本的支配,既有影片本体因素的考虑,诸如场面调度、拍摄手法、叙事力度和思想深度等方面,又有外力的调配,诸如舆论造势、得分评奖、教材认可等方面。电影经典不同于在漫长的文化传统中所沉淀下来的文学经典,不同于我们在四书五经中所体会到的精深广博,也不同于我们在唐诗宋词中所体验的吟咏涵蓄。受大众追捧的影片未必能够深刻地展示人类精神的张力,未必刻意地锤炼一种不朽性,它们甚至可能排除智力的斗争,而只在感官层面上达到极致而已,比如在画面和音效上得到一种极致的美感或震撼感。从文学经典(阅读的形式)到电影经典(视听的形式),经典的建构有所转折。艺术生产和艺术消费的规模化,使得经典不再局限于过去的精英化作品,群选经典化促使了世俗经典的出现。世俗经典不是由批评家、学术家和政治家来决定,它是由生产者和接受者自己决定。
电影经典的建构处在一个不朽的旅途之中:新的经典不断加入进来,而旧有的经典会淡化、退出,经典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依据不同的判断和见解会发生变化。“文化水准不能精确地进行定义,首先因为它总是不断进展,而每一种对作品新的理解总会改变之前对它的理解,通过吸收包含在作品中不断增长的信息量,重复的理解成为约束作品‘原初性’的一种途径。”[13](72)文化水准不能精确地被定义,对影片水准的考量也难以有一个精密的计算方式,这始终是一种情感判断和审美判断,不同接受者都有权利表达不同的感受。然而,不是所有的感受都能获得一种合法性的地位,或者能够为影片确立经典地位而真正效劳。感受成为评判,直至成为权威话语,需要历经一个艰难的过程,这正是文化资本分配的结果。文化资本的分配是一个革命过程,包括知识话语和大众话语的博弈,包括影片生产者和价值评判者在各自领域对地位的争夺等等。比如《疯狂的石头》《失恋33天》《人在囧途》等小成本电影在票房上取得成功,在大众中呼声颇高,吸引了不少研究者对之加以剖析,确立了影片及其生产者在当代电影场域中新的地位。这种小成本电影类型所代表的文化资本对某些社会团体来说意味着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同时它也表示其他个人或团体所拥有的文化资本的贬值。影片地位的构建,始终是一个争斗的动态过程。类似地,电影经典也会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和社会环境中不断得以重构。
因此,资本运作下电影经典的建构是一种文化资本分配的结果,这既是知识精英的劳动,又是大众群体的选择。当代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中必将产生经典作品,未来我们会看到中国电影产业中的一个经典谱系,这些作品一则具有很好的文本价值,二则契合社会价值的导向。至于哪些作品能被称为经典,这本身并没有固定的答案,它们将是文本必然性与文化任意性相结合的产物。文本必然性在于影片本身要有较好的质量;文化任意性在于社会外在条件对它的选择,比如获得电影大奖、取得极高票房、赢得极好口碑、引起极大争议等,最重要的在于影片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某种需求。经典的建构是动态的过程,不同的社会结构遴选产生合适的经典作品。这个经典谱系会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中根据不同需求产生略微的变动。
[1] 仪礼·礼记[C]// 十三经注疏.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2] 孟子·尽心下[C]// 十三经注疏.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3] 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4] 现代汉语词典[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5] 辞海[Z].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
[6] Judy Pearsall. 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Z]. Oxford, 1998.
[7] 张隆溪. 中西文化研究十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8] 布鲁姆. 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9] 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0] E·迪恩·科尔巴斯. 当前的经典论争[C]// 文化研究精粹读本. 陶东风.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11] 论语·雍也[C]// 十三经注疏.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12] 布尔迪厄.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包亚明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13] Pierre Bourdieu, Alain Darbel, Dominique Schnapper. The love of art: european art museums and their public [M]. Translated by Caroline Beattie, Nick Merriman,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The construction of classic movies in the Chinese film industry
ZHOU Caishu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s,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People’s expectation horizon to canons is that they must be authoritative and canonical with inspiring and far-reaching power in human development. And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film industrialization, a new trend arises that masses take par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lassic movies, which reveals both the audience’s active reinforcement and a new problem the construction must face. Under capital oper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classic movies not only goes under the guidance and judgment of the academic elite, but also refers to the views of the mass, who, not a group without cultural accumulation, tend to provide some unvarnished judgments of their movie experiences. The construction of classic movies is the result of choice and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and the classic movies are the products of textual inevitability and cultural occasionality.
film industry; canon; the trend of mass selecting canon; the mass; text
J9
A
1672-3104(2015)03−0229−06
[编辑: 胡兴华]
2015−02−10;
2015−04−0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中国道路研究”(14AZD04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数字化语境中新世纪以来的文艺审美实践研究”(13BZW027);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新信息技术环境下电影产业的文化资本研究”(KYF125615009)
周才庶(1985−),女,浙江温州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与法学院讲师,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文艺学,文化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