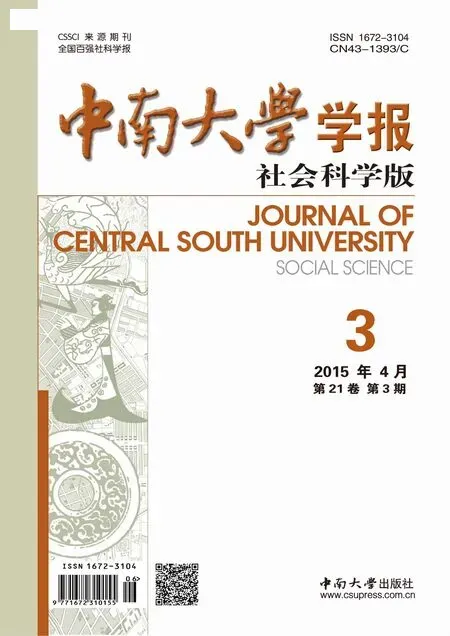中央苏区后期革命动员的困境与对策
——兼论王明“左”倾错误对中央苏区革命动员的影响
王连花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湖南长沙,410006)
中央苏区后期革命动员的困境与对策
——兼论王明“左”倾错误对中央苏区革命动员的影响
王连花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湖南长沙,410006)
中央苏区后期,由于人力、财力和物力有限,加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中央无视苏区的实际困难,提出不切实际的动员目标,运用过于形式化的动员方式,采用“关门主义”的动员策略,实行过“左”的动员政策,致使中央苏区的革命动员工作陷入困境:部分农民抵制“扩红”运动,抗拒频繁的物资征用,抵触不断扩大的阶级斗争,甚至逃离苏区。为挽回革命动员的颓势,满足当时残酷的革命战争的需要,党和政府不得不启用更为强硬的高压政策和更为有力的激励政策,对民众实行再动员。
中央苏区;王明“左”倾错误;革命动员;高压政策;激励政策
在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建立稳固的革命政权,领导苏区人民取得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如果从社会动员角度来说,那就是社会动员的深入性、充分性与无微不至性。从1932年至1934年,中央苏区共大规模“扩红”三次,吸收红军约27万人;共发动大规模“借谷”运动三次,筹集粮食100万担以上;共大规模发行公债三期,筹集公债400万元余。[1]再加上征收税收、发行纸币、募捐等,苏区人民为革命战争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正如约翰·霍恩所说:“对于所有的国家,大规模动员都有可能成为一段痛苦和不愉快的经历,他会带来抱怨、紧张、反抗和冲突。”[2](192)特别是1933年初,以王明为首的“左”倾中央迁到中央苏区,推行一系列“左”倾动员政策,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到中央苏区后期,各种负面问题的不断积聚,最终演化为强大的“反动员”力量,致使动员疲软,陷入困境,中共中央不得不启用更强有力的措施,对民众实行“再动员”。
一、王明“左”倾错误与革命动员的极端化
1933年1月,受王明控制的“左”倾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中央苏区的“左”倾冒险主义愈演愈烈。“左”倾中央片面夸大苏区和工农红军的力量,过于乐观估计革命斗争形势。1932年3月,王明在《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宣扬“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是“两个中国的对立”,即“国民党中国”和“苏维埃中国”,而且“两个中国”的发展呈现四大趋势:“苏维埃中国正在扩大和统一”,“国民党的中国正在缩小和分裂”,“苏维埃政权日益壮大和巩固”,“国民党政权日益削弱和崩溃”。[3]过于乐观的革命形势估计导致王明在革命动员形势上盲目自信。他无视苏区的实际困难,提出不切实际的动员目标,采用过于形式化的动员方式,推行过火的阶级斗争,给中央苏区革命动员工作带来严重危害。
(一) 动员目标和动员内容上的不切实际
在军事动员上,“左”倾中央严厉批判邓、毛、谢、古等人认为的“在边境地区扩大红军数字太大是不可能的”正确意见,提出“要扩大百万红军”,“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过高目标。在土地政策上,王明反击毛泽东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的正确做法,盲目提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动员口号。为贯彻过“左”的土地政策,临时中央开展查田运动,并愈演愈左,致使各地纷纷出现乱划阶级成分,严重侵犯中农利益,消灭富农经济的现象。在妇女运动和工人运动方面,“左”倾中央为片面地调动妇女和工人的积极性,制定了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经济政策,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规定:“禁止女工在任何举重过四十斤之企业内工作。若在某种特殊工业或工作过程中,必须包括一部分女工,女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通常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二”,“所有用体力的劳动女工,产前产后休息八星期,工资照发,使用脑力的机关女职员(如女办事员与女书记),产前产后休息六星期,工资照发,如小产(堕胎)休息两星期,工资照发。(附注)女工产前产后的休息期内,及小产时的工资,由厂主负担。如若设立了社会保险处已经成产,则经过社会保险处发给”。[4](624−625)在工人运动方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也有许多不适合产业极不发达的实际情况的条文,如规定“通常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16岁至18岁青工不超过6小时,14岁至16岁的童工不得超过4小时”,“除每周休息一天外,工人每年连续工作6个月以上者,至少有两个月例假,工资照发,除新年、五一放假外,其他上十个纪念日均放假一天,片面强调工人福利,规定雇主除支付工人工资外,还要支付全部工资额的10%~15%作为社会保险基金”,“雇主要发给工人工作服、手电筒、牛乳等劳保用品”,“工人参加社会工作,无论时间久暂,都不得克扣工资”等等。[4](626)这些规定虽然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保护妇女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增加他们投身革命的热情,但是,却没有考虑到城乡之间、企业之间、公私营之间的差异和区别,没有考虑到工厂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对革命根据地的民族工商业造成打击,致使民族工商业纷纷倒闭。
(二) 动员方式上的形式化和过激化
为达到不切实际的动员目标,实现脱离现实的动员内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中央把共产国际的动员经验神圣化、绝对化、形式化,一切照搬照抄。在白区,他们盲目地动员工人、学生无条件地罢工、罢课,导致党在白区的秘密组织绝大部分暴露和遭到破坏。在入党问题上,他们生硬照搬苏联的经验,强调党员的工人成分,以“突击”的方式不加鉴别地动员大批工人加入党内,他们甚至要求地方党组织到工厂门口,趁工人上下班时举行演讲活动,扩大宣传,发展党员,这就使一些并不具备条件的工人被“突击”拉进党内,有的还进入机关担任要职。由于他们缺乏相应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难以胜任工作,影响了革命工作的开展。
临时中央所采用的动员方式也出现过激化,过火化问题。为排除异己,压制不同意见,“左”倾中央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1931年,刘少奇在白区与“左”倾路线进行斗争,却被斥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其中央职工部部长兼全总党团书记的职位也被撤销。1931年至1932年,“左”倾中央又指责毛泽东,污蔑他的正确土地革命政策为“富农路线”“狭隘的经验论”,是向地主和富农投降,因此,他也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被剥夺其在中央苏区的领导权。1933年2月,苏区中央局又发动对邓、毛、谢、古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使大批经验丰富、敢于抵制错误路线的党政干部受到打击迫害。在肃反运动中,“左”倾中央大搞逼、供、信,把大批反对或不支持“左”倾路线的干部和战士,都打为AB团、改组派、第三党,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以至于有的迫害致死。在查田运动中,“左”倾中央推行过激的政策和手段,如将中农上升为富农,将富农上身为地主加以打击。在查阶级时,往往向上追溯二、三代甚至三、四代,出现将一些贫苦农民划为地主,对其进行没收财产、开除工作、政治歧视等错误做法。这种“左”倾政策的推行严重侵害了群众的利益,使一部分中贫农担心自己错划阶级而惶惶不可终日,影响了他们革命的积极性。
(三) 动员策略上的“关门主义”
“关门主义”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左”倾中央妄想以极端化的动员方式推动乡村革命动员工作的开展。这种过激化、过火化的动员方式不但不能达到动员效果的最大化,反而导致一系列狭隘与偏激的政策策略,把一部分本应该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向国民党反对派,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关门主义”主张把“斗争”绝对化,“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在苏区,有的地方把地主家属驱逐出境,对所谓‘稍有反动能力的’就将其处决。湘赣苏区的酃县,竟然把“十六岁以上三十岁以下”豪绅家属的壮丁不论男女都杀掉了,使地主富农走投无路,或上山为匪,或逃亡白区,或替国民党提供情报,为国民党做内应。在国统区,“左”倾中央不承认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否认国民党内部所存在的革命因素。如1933年,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领导的十九路军发动了著名的抗日反蒋行动“福建事变”,“左”倾中央不但不去做团结、教育和争取工作,反而污蔑其是“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致使十九路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崩溃瓦解,中国共产党也失去了一个发展革命力量的绝好机会。
如果说在经济封锁的前提下,苏区有限的社会资源是革命动员走向困境的客观原因,那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动员路线——以极端化、绝对化、狭隘化的革命动员方式去盲目追求脱离实际的动员内容和目标的实现,则是乡村革命动员走向困境的主观原因。主客致因的两面“夹击”,一步步地把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动员逼回“低谷”。到中央苏区后期,军事的连连失利又成为革命动员态势迅速下滑的直接诱因,各种社会问题逐渐凸显,群众的不满、怨恨、反制情绪不断增强,最终演化为强大的“反动员”力量,致使乡村革命动员疲软,陷入困境。
二、农民的抵触与中央苏区革命动员的困境
中央苏区革命动员陷入困境,农民表现出对革命不再具有饱满的热情和积极的态度,并且产生了不满、恐惧甚至怨恨的情绪,在行动上也表现出对动员的逃避、抵制甚至反抗。虽然,这些不满、怨恨的情绪一再被掩盖,但仍然随处可见。
(一) 无休止的“扩红”运动与农民的抵制
残酷的革命战争、前线的巨大伤亡,需要源源不断的兵力供给。据初步统计:第一次反“围剿”红军至少损失10 000人,第二次反“围剿”约损失10 000人,第三次反“围剿”损失约9 800人,第四次反“围剿”损失约12 000人,第五次反“围剿”损失至少30 000人。[5]而当时中央苏区总的土地面积不过七八万平方公里,总人口不过四百多万,除去老弱病残妇女,能成为兵源的也不过几十万人,供给十分有限。[6]为最大限度地解决供求矛盾,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后期,“扩红”运动日益极端化和激烈化。当时,党和政府多次下发文件,规定:“条件始凡属16岁到45岁的男子,除地主富农家中成员和明显残废有严重疾病者以外,不管是独生子还是家庭有什么特殊困难,都是被‘扩红’的对象。”[7](19)如果说“扩红”初期是号召自愿报名,那么后来则“动员子女多的家庭继续报名,接着就让二三十岁的青壮年逐个报名”,“由于上级催兵逐步加紧,深入动员做群众工作也就没有余地了”。[7](19)为完成“扩红”任务,部分基层干部甚至采用欺骗收买,强迫命令的方式,激起了民众的不满和抵制。
逃避是农民抵制“扩红”运动的一种方式。中央苏区农民“有的躲起来,有的逃到外地去,有的即使被扩进来,还没有送到区政府就又跑掉了”,“如果是已经送到部队连续三次开小差再被捉回就按逃兵论处要被枪毙。但即使如此,也还是有开小差的”。[7](19)“江西全省动员到前方配合红军作战的赤卫军模范营、模范少队在几天内开小差已达全数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过四分之一,所逃跑的不仅是队员,尤其是主要的领导干部也同样地逃跑,如胜利、博生之送去一团十二个连,逃跑了十一个团营连长,带去少队拐公家伙食逃跑。永丰的营长政委也逃跑了,兴国的连长跑了几个,特别是那些司务长拐带公家的伙食大批的逃跑。”[8]
为抵制“扩红”,有的农民装病、甚至自残自杀。当负责“扩红”的干部到农民家里做说服工作时,有的农民就假装生病,如果被识破,他们则采用极端手段,弄假成真,发展到自残。“有一个农民,怕当红军,故意将自己的生殖器弄坏”[9],或者干脆“投塘跳河自伤自杀”[7](19)。在1933年12月的“扩红运动”中,除洛口、龙岗、兴国、公略等县的成绩较好外,其余各县任务都没有完成,全省“扩红”人数仅达原定数目的五分之一。
农民对“扩红”的抵制和畏惧心理,又易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一部分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为破坏革命,总是想方设法地进行捣乱。他们有的利用群众对“扩红”的畏惧情绪,散布“你们去当红军一定会杀你的头”的谣言,有的利用群众的畏惧心理,敲诈勒索,贪赃枉法,叫“群众拿二十元大洋给他,可以不去当红军”[10],有的甚至带着一帮民众反水,逃跑……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扩红”工作的进行。
(二) 生活境况日益恶化与农民的忧虑
反“围剿”战争的后期,中央苏区经济上的问题十分突出。1933年夏初,各苏区就开始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粮荒。如中央苏区,“在上杭、汀州、于都以及瑞金,都感觉到粮食的缺乏”[11]。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号召群众采摘笋子、苔齐、艾子、黄秋菜等植物来渡此难关。湘鄂赣苏区,“许多地方禁运谷米,甲县乙县,划成界限,许多地方发生粮荒,米价飞涨,有钱无市”[12]。和粮食相比,一些日用品的供应更显紧张,如布匹、食盐、药材等生活必需品,达到极其匮乏的地步。1933年底,毛泽东曾经对生活必需品的匮乏忧心忡忡,“暴动前平均每人每两年还能做一套衫裤,暴动后平均每人每年能做一套半,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今年情形又改变,因为封锁,布贵,平均每人只能做半套,恢复到暴动前......暴动前每人平均每月吃盐一斤,今年十一月每人每月只吃三两二钱,即暴动前五个人的家庭月吃盐五斤者,今年十一月只吃一斤。”[13]随着战争的继续和封锁的加重,这些问题愈加严重。1934年年中,“米每元五斤,盐每元一两五钱,柴每斤二角”[14]。为解燃眉之急,苏区出于无奈,只能大搞“熬硝盐”运动,硝盐质地不纯,含有大量的杂质和其他有害物质,被食用后,许多士兵群众发生中毒事件。
农民生活境况的急剧恶化,逐渐削弱农民的革命热情,当频繁的征用威胁到生存底线时,中央苏区的农民开始忧虑生存,疏离政府。
农民对生存的忧虑,对政府的抵制,表现在对频繁物资征用的抗拒上。反“围剿”战争后期,许多地方出现了强迫命令式的物资征用方式——借谷运动中的“指名硬要”或“平均摊派”,节省运动中“沿家抖米”,导致许多农民以极端的行为来抵抗政府的强制。“在长胜欧底乡因为指名摊派,使有些群众哭起来;胜利县用摊派方法强迫群众‘硬要借,以致发生两件群众自杀的严重事件’。”[15]西江赤鹅区朱田乡苏,“有个工作人员要一个雇农买十块钱公债,雇农答应了,第二天又要加上十块,这个雇农又满口答应了,第三天又要加上十块,共销三十块。雇农说:‘我没有钱!’这个工作人员说:‘你不销三十块就是地主。’在这个命令强迫之下,结果使雇农吊颈死了。”[16]群众以“自杀”来抗拒物资的征用,不仅说明了当时群众所掌握的物资极其匮乏,而且说明压迫性的动员方式已经在群众之间造成恐慌。
农民对生存的忧虑,对政府的抵制方式还表现为逃离苏区。既然苏区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那么群众很可能就通过躲避,甚至“外逃”的方式,去寻求解脱或生活景况的改善。江西乐安的一位地方干部曾致信“苏区中央局”,忧心忡忡地指出:“昨到招携(乡),匆促间得知下列的严重现象......善和区分配运输员,区委区苏派模范队包围了乡村拉夫,群众登山,模范队开枪示威,群众两天不下山,区苏令人去捉。”[17]这是群众对令自己忧虑、恐慌的动员方式的逃离。更严重的是,苏区的一些实在活不下去的群众还选择了“外逃”的方式。如李一氓曾回忆:在长征之前的半年内,苏区有些地区“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都参加了红军,那些年纪大的,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陆续地跑出,到国民党那边去投亲靠友......这种逃跑现象各县都有,特别是那些偏僻的山区里面,跑起来人不知鬼不觉”[18]。据统计,杨殷县在4月份逃出的群众达到2000人之多。[19]而1934年2月,万太县就有2 600名群众逃跑,3月份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20]
美国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在《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这样说过:“剥削并不足以引起农民的反叛,真正引起爆炸性局势的是外界对其生存原则(即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的侵犯。在剥削过程中,如果农民的剩余物资与向统治者转移的物资的某种平衡被打破,威胁到农民的生存底线,那么农村爆发革命的可能性就会加大。”[21]中央苏区的农民也遵循这样的规律,虽然中央苏区群众对政府的离心离德,还不至于演变为暴动,事实上政府对苏区群众严密的掌握也不容许此等现象的发生。但是他们的哭诉、他们的外逃、他们的自杀等等消极的、悲观的行为向人们述说了他们对极端的革命动员的不满。
(三) 不断扩大的阶级斗争与农民的恐惧
阶级斗争本是调动群众革命积极性的重要手段,毛泽东正是从阶级斗争中,从“打击地主”“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22]中看到了农民的力量,群众也正是从阶级斗争中找到了自己“翻身做主人”,扬眉吐气的尊严和自信。但是,如果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超出它应有的限度,则会出现打击面过大,损害人民群众自身利益的问题。中央苏区后期,临时“左”倾中央政府一方面深入开展查田运动,最大限度地剥夺剥削者的财物,另一方面开展肃反运动,打击消极分子、投机分子、怠工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为动员扫清道路。但是,迫于过“左”化动员政策的压力,查田运动和肃反运动中均出现了“扩大化”“绝对化”的问题,从而造成农民的恐慌。
所谓查田运动,是指苏区在土地分配之后所进行的一次群众性运动,其目的在于清查漏划的地主、富农,并按照当时的土地法来没收和分配他们的土地、财产。[23]据杨会清的研究,推动查田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集中苏区的经济力量,更好地为战争服务。[24](167)由于战争消耗巨大,查田运动也显得任务紧迫,压力巨大。过于频繁的查田运动开展,不仅使苏区内部的剥削者被剥夺一空,而且这一运动越到后面越走向荒唐,“有些是把仅仅放几百毫子债,请过年把长工,或收几担稻谷,而极大部分是靠自己劳动过活的中农,当富农打了,有的甚至完全没有剥削别人,仅仅是多有几十担田山,生活比较丰裕的中农,也当富农打了……还发现了有些地方把手工业主、商人、‘流氓’,当地主富农打了。”[25]这给整个中央苏区造成了恐慌,农民的行为也变得荒唐起来。有些农民担心自己被划为地主富农,而要求改变自己的政治身份,“瑞金城区竟有中农跑到苏维埃来请求改变自己的成份,请求改变为贫农,他们说:‘中农危险得很,捱上去就是富农,改为贫农咧,隔富农就远了一点’。”[26](8)有些农民“为了避免被打成地主、富农,贫农群众也不愿多分田,不愿多做工,苏区因此出现了生产停顿,田地荒芜乃至‘木子无人收,山林无人进,有大部分人失业’的情况”[24](238)。中央苏区革命战争源源不断的消耗需要经济生产的支撑,需要农、工、手工业的大力发展,群众的这种消极、推诿和怠工行为无疑会使苏区经济雪上加霜。
中央苏区的肃反运动也出现过“扩大化”“简单化”的错误。肃反的对象五花八门,不仅包括地主、富农,包括“AB团”、“罗明路线”者、“自由主义”者、“托洛斯基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官僚主义”者、“贪污腐败分子”,还包括由于完不成上级指标而被指控有罪的落后分子、消极分子、怠工分子等等。群众有完不成动员任务而被打击定罪的,西江赤鹅区朱田乡苏有一个工作人员要一个雇农购买三十块公债,雇农在购买二十块后,说“我没有钱”,“这个工作人员说:‘你不销三十块就是地主。’”[16]干部也有完不成动员任务而被打击定罪的,“宁化县开展了反机会主义、官僚主义消极怠工的斗争,全县统计撤销三十二个突击队长,二十三个突击队员,改选了八个乡主席,十四个代表,三个支部”,安远县天心区的“一个会议中撤销了七个部长,县委每一次活动分子会议打击了五六个机会主义分子”,万太县“一月扩大红军突击中,县区干部撤职或开除党籍的近四十人”。[27]如此过“左”的、经常化的肃反运动,在苏区形成了过于紧迫、沉闷的政治气氛。
三、党和政府革命动员政策的强化和调整
农民对过“左”的革命动员所产生的恐慌、怨恨、失望之心,他们抗拒政府、逃离苏区甚至自我了结的极端行动,汇集了一股较强的“反动员”力量。这股“反动员”力量的逐渐膨胀,给正常的革命活动形成牵制。为消解革命的反动员力量,党和政府不得不启用更为有力度的措施,对民众实行再动员。
(一) 更为强硬的高压政策
这里的“高压”政策是指党和政府对阻碍革命动员工作开展,影响动员效果的行为和责任者所采取的惩戒性政策措施,使其在暴力的震慑下服从于革命工作大局。这是党和政府,面对革命动员的困境,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再动员”手段。
实行志愿兵役制向义务兵役制过渡是党和政府进行“扩红”再动员的一项重要措施。中央苏区最初实行的都是志愿兵役制,强调当兵的自愿原则,但是,1932年后,面对着革命战争的严峻形势和“扩红”工作打不开局面的情况,开始实行向义务兵役制的转变。1932年9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扩大红军问题训令》特别要求,“目前虽是自愿兵役,但应立即开始宣传义务军役以准备将来的转变,并使广大工农群众认识当红军不仅是义务,而且是工农阶级的特有权利”,决定让“满十八岁到四十岁之工农群众全体加入”赤卫队,“以建立将来实行义务兵役制”。[28](175)这就使参加红军成了苏区青壮年男子义不容辞的责任,无论自愿或不自愿,青少年男子都必须参加红军。
采取的另一种政策措施就是对破坏乡村革命动员的反革命分子、落后分子、消极分子、怠工分子实行更有力的打击。1933年12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红军中逃跑份子问题》的命令,首次规定了对各种逃跑分子的处罚方式,要其赔偿军衣军鞋及群众的损失,剥夺其选举权,情节严重者(如拖枪逃跑分子)甚至处以“枪决”。命令认为,“逃跑是红军和革命战争的恶敌人,反逃跑斗争是保障红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工作”[29],因此规定了对以各种方式逃跑者进行轻重不一的处罚。
对于在“扩红”、筹款、筹粮等工作中出现问题、或者不称职的领导干部实行撤换、处罚,是苏区政府惯常采用的方法。首先,对在“扩红”、筹款、筹粮中,有贪污浪费行为的领导干部进行撤换、处罚。1932年12月,毛泽东和项英联合签发《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规定“凡是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的地位贪没公款以图私利者”[30]必须依法处罚。1933年,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又发出《怎样检举贪污浪费》的文件,规定了六条反贪污浪费的意见。其次,对工作不力、不称职的领导干部进行撤换处罚。在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中,经常可以看到党和政府对在“扩红”、筹款、筹粮中工作不力的领导干部进行批评,如批评有些干部抱有“‘扩红’把人扩尽了”的消极悲观思想,而不积极宣传发动群众;批评有些干部仅仅停留于口头宣传,而不深入群众,扎扎实实地作动员工作;对情节严重者则作撤换处理,“把旧人员中那些不中用的分子淘汰出来,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31]
对于其他反革命、蓄意破坏革命的顽固分子,苏区开展了一波又一波更严厉的“肃反运动”,号召把一切反革命分子从各级机关中清洗出去,同一切破坏苏区革命的反革命分子作严酷的斗争。据统计,在苏区的西江县,仅1934年5月的中下旬,“即捕获了几百名反革命分子,仅判处死刑的即有二三百名。(城市区在红五月中共杀了三十二名反革命,破获了AB团、暗杀团、铲共团、社民党、保安会的组织,共捉了四个暗杀团长、两个AB团长、数十名连长、排长、宣传队长等)。”[32]西江是人口仅数万人的小县,半月内即出现如此之多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和反革命组织,这是肃反扩大化的表现,但也说明了中共的“高压”力度。
为了控制舆论,中央苏区还对信件、消息传播进行控制审查。为优待军属,红军与家属通信,是不需要贴邮票的,“红军与家属通信,由直属机关盖章,不贴邮票,可寄回家。红军家属寄信到红军中,则由当地政府盖章,亦不贴邮票,可寄到红军机关中转发”[28](189)。但通信内容,苏维埃政府有权检查,“苏维埃有权检查和取消防(妨)害扩大红军的信件”,“督促红军家属写鼓励红军的信”[33],鼓舞其斗志,禁止有打击士兵信心、动摇士兵意志的内容出现。士兵也不能利用信件散布军队的负面消息,如军队的艰苦生活,战事的失利情况等。党和政府对红军与家属通信内容的控制,是防止关于军队的负面言论引起群众恐慌,妨碍扩红运动的顺利进行。
这些更大强度的打压做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革命动员的艰难行进。但是,它的有些措施,在构建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关系上,却是失败的——它更加加重了群众负担,易激发民怒,扩宽了政府与群众的关系裂痕。再一次借助暴力,实质上是当时处于进退两难、左支右绌的政府不得不采取的无奈之举。
(二) 更受重视的引导激励政策
如果说高压政策是受限制的,那么激励和引导政策则不会受限。其实,“来自厌战情绪和政府与人民离心离德的危险比政坛上反战派的危险更为直接,这使得通过劝说而不是强制来改变主体民众的意志更为重要。”[2](209)
在一切“强迫”“命令”“欺骗”“利诱”等动员方式的弊端充分暴露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政治动员、说服教育的作用。1933年8月,党和政府认识到“强迫命令欺骗利诱的办法是造成一部分人开小差和群众不满意的现象”,要求改变“扩红”动员的方式,以说服教育的动员方式“克服强迫命令的动员”。[34]1933年9月,洛甫在总结以往领导方式的出现的问题,即“强迫命令的声浪,是更加叫喊得响亮了”时,要求采用新的领导方式。“领导群众的主要方式是说服群众,使群众相信我们的主张的正确,使群众执行我们党所提出的每一任务。”[35](10)他认为,新的领导方式具体来说,首先要加强“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35](10);其次要“在实际上来解决群众中所发生许多困难问题”[35](13);再次,“在每一宣传鼓动之后,在说服群众的过程中,善于组织群众”[35](13);最后,“利用每一个过去的经验”[35](15),总结成功经验,吸取失败教训,以更加健康地开展动员工作。
党和政府也曾对查田运动的扩大化进行了反思和纠正。1933下半年,毛泽东在《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中,要求在“查田运动”中开展两条战线斗争,“既要开展反右倾的思想斗争……同时也要开展反“左”倾的思想斗争”,“要把侵犯中农的危险唤起全体党员的注意,要严厉打击任何侵犯中农利益的企图,对富农的不正确观念,也无疑要影响到中农去”。[26](8)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是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剥夺富农,消灭地主。这就为保护中农的利益,防止过度侵犯富农,提供了一定依据,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群众生产生活的积极性。可惜好景不长,党内正确意见马上被“左”倾冒险主义者所压倒。1934年3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又一改态度,发出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训令》,认为“纠正过左的错误,是阻碍开展查田运动并给地主、富农以反攻的机会,因而是错误的”[36]。这样,“左”倾错误又进一步发展起来,怀柔政策又被高压政策取而代之。
在军中,稳定红军和妻子的婚姻关系,维系士兵与家属之间的联系是提升士气,促使红军安心作战,稳定军心的重要措施。“红军在服务期间,其妻离婚必先得本人同意,如未得同意,政府得禁止之。”[37](324)这条措施一直得以在中央苏区延续。中央考虑到有些红军在前线牺牲,“其妻子不知”的情况,也为维系士兵与家属之间的亲情纽带,使其从中获取精神慰藉和鼓舞,对这条规定实行的前提条件进行规定:加强士兵与妻子之间的通信,“红军政治部须通知每个苏区籍之有妻子的红军战士,至少每三月与其妻通信一次。不会写信的由团政治处督促连政治指导员代写”[37](324)。及时统计牺牲的战士,并通报家属,“红军政治部对于每次战役牺牲了的苏区籍红军战士,须迅速统计......遥寄该县政府内务部。县内务部接到此表,即分别按抄送区苏政府,转付乡苏通知本人家属。”[37](324)规定时期内战士有信回家,而“其妻要求离婚者”“须得本人同意才能离婚。否则,政府则禁止之”。[37](325)这既巩固了战士战斗决心,又保护了妇女的合法权益。
另外,进一步慰劳红军、优待红军家属,奖励先进,鼓励发展生产等,也是党和政府引导激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看出,中央苏区后期,党和政府为打破动员困境,把高压政策和引导激励政策紧密地结合起来,艰难地推动着革命动员工作的进行。但是,军事上的连连失利似乎扰乱了中央决策的脚步,高压政策、引导激励政策的使用经常出现自相矛盾的现象,高压政策似乎加剧了民愤,激励政策刚刚实施又马上被抛弃,最终,它们都没能挽回苏区革命动员的颓势。在严峻的军事形势下,社会资源的极端调动,必将给群众日常生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能否顶住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和政府能否取得战争的胜利,以及能否让群众获得实际利益。很明显,当时战事失利的中央政府是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因此,它无力协调与应付极端动员所造成的种种负面影响,无力阻挡各种反动员力量的汇聚。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兵员枯竭、物资紧缺、战事失利的极端困境中,被迫转移,踏上长征之路,宣告了中央苏区革命动员的最后失败。从1931年冬到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坚持了近3年时间。在此期间,中央苏区革命中的动员与反动员,反动员与再动员,从最初的和风细雨式的交锋发展到后来的一场场激烈的拉锯战,我们可以从中感觉到苏区为革命所做牺牲的伟大、贡献的光荣和最后的无可奈何。
[1] 余伯流, 何友良. 中央苏区史·上[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 873.
[2] 约翰·霍恩.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的政府、社会和动员[M].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7.
[3] 王明. 王明言论选辑[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286−289.
[4] 许毅. 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5]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训练部编.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资料汇集·之二·五次反“围剿”[Z]. 内部发行, 1959: 59.
[6] 石仲泉. 中央苏区与苏区精神[J]. 中共党史研究, 2006(1): 77−86.
[7] 刘守仁口述, 田惠整理. 兴国“扩红”[J]. 党史纵横, 2006(6): 19−20.
[8] 中央档案馆, 江西档案馆. 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1934)[Z]. 内部发行, 1992: 107.
[9] 本报讯. 耐心说服的好例子[N]. 红色中华, 1934-09-21, (6).
[1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宁化县委员会文史组. 宁化文史资料·第6辑[Z]. 内部发行, 1985: 28.
[11] 亮平. 怎么解决粮食问题[N]. 斗争, 1933-05-10, (5).
[12] 本报讯. 为调节民食接济军粮[N]. 红色中华, 1933-03-06, (5).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350.
[1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4)[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204.
[15] 本报讯. 实行布尔什维克的突击[N]. 红色中华, 1934-07-05, (1).
[16] 本报讯. 严厉镇压地主富农活动[N]. 红色中华, 1934-02-16, (1).
[17] 中共中央书记处. 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1: 352.
[18] 李一氓. 李一氓回忆录[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156.
[19] 董必武. 把检举运动更广大的开展起来[N]. 斗争, 1934-05-26, (5).
[20] 本报讯. 人民委员会为万太群众逃跑问题给万太县苏主席团的指示信[N]. 红色中华, 1934-04-10, (2).
[21] 詹姆斯•C•斯科特.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农民的道义经济学[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261.
[2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3.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275.
[24] 杨会清. 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乡村革命动员模式研究[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8.
[25] 刘少奇. 农业工会十二县查田大会总结[N]. 斗争, 1933-11-12, (12).
[26] 毛泽东. 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N]. 斗争, 1933-08-29, (8).
[27] 罗迈. 把突击运动期间党内斗争上表现出来的缺点与错误纠正过来[N]. 斗争, 1934-03-17, (6).
[28] 厦门大学法律系, 福建省档案馆选编.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4.
[29] 本报讯. 关于红军中逃跑份子问题[N]. 红色中华, 1933-12-12, (1).
[30] 傅克诚. 中央苏区廉政建设[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26.
[31] 本报讯. 给各级党部党团和动员机关的信[N]. 红色中华, 1934-5-23, (3).
[32] 本报讯. 西江县——红五月扩红突击中的第二名[N]. 红色中华, 1934-06-07, (2).
[33] 江西档案馆. 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4: 571.
[34] 本报讯. 工人师少共国际师的动员总结与今后四个月的动员计划[N]. 斗争, 1933-8-29, (17).
[35] 洛甫. 关于新的领导方式[N]. 斗争, 1933-09-30.
[3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375.
[37] 中央档案馆, 福建档案馆. 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苏维埃政府文件·1931—1933[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Dilemma and countermeasure of the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 in the late Central Soviet: and the effect of Wang Ming “left” errors
WANG Lianhua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CPC School in Hunan Province, Changsha 410006, China)
In the late Central Soviet, the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 was trapped in dilemma due to the limited manpower, financial and material resources as well as views of the Left with Wang Ming as the representative who turned a blind eye to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proposed some unrealistic goals for mobilization, resorted to rigid means, employed “closed-door” strategy, and implemented the “left” policy. Such dilemma included some farmers’ resistance to the campaign of “expanding the Red,” to the frequent requisition of supplies, and to ever-increasing class conflicts and their fleeing from the Soviet as a result. To restore the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 of the downturn and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brutal revolutionary war of the time,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had to launch a tougher and more powerful coersion policy of incentives so as to remobilize people.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Wang Ming “left” errors;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 coersion policy; incentives
D23
A
1672-3104(2015)03−0144−08
[编辑: 颜关明]
2014−05−26;
2014−09−06
王连花(1983−),女,湖南衡阳人,法学博士,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革命动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