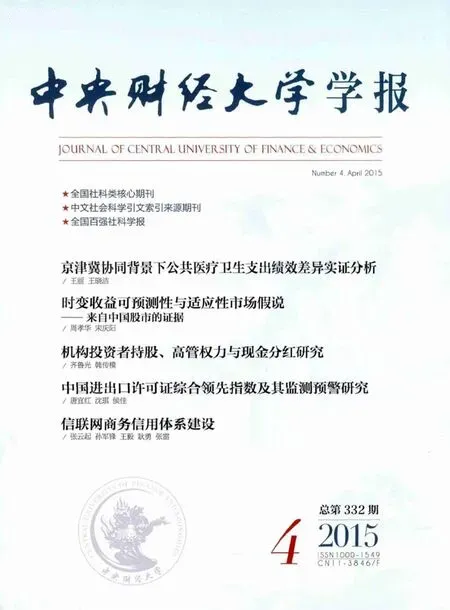教育公平的政策导向与财政策略
——美国联邦政府的政策实践与启示
冯国有
教育公平是我国教育政策的主题,尤其是近年来,我国推进教育公平的力度不断加大。2005年教育部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对教育公平进行较为详细的阐述,提出要把义务教育工作重心进一步落实到办好每一所学校和关注每一个孩子健康成长上来,有效遏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学校之间教育差距扩大的势头,积极改善农村学校和城镇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逐步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2006年,根据 《宪法》和 《教育法》,国家修订颁布了 《义务教育法》,再次强调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2010年国务院颁发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均衡发展是义务教育的战略性任务,要建立健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保障机制,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均衡配置教师、设备、图书、校舍等资源。2012年国务院颁布了 《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提出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基本目标是:每一所学校符合国家办学标准,办学经费得到保障。教育资源满足学校教育教学需要,开齐国家规定课程。教师配置更加合理,提高教师整体素质。学校班额符合国家规定标准,消除“大班额”现象。率先在县域内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县域内学校之间差距明显缩小。到2015年,全国实现基本均衡的县(市、区)比例达到65%;到2020年,全国实现基本均衡的县(市、区)比例达到95%。应当看到,我国追求教育公平的政策经过多年实践,政府教育财政投入大幅度增长,教育不均衡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2011年所有省(区、市)通过了国家“普九”验收,全国用25年全面普及了城乡免费义务教育,从根本上解决了适龄儿童少年“有学上”问题。但随着教育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百姓对教育的需求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有学上”,实现教育机会的公平,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好学”,实现教育结果的公平。而我国的现实状况却是义务教育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还存在明显差距,公众不断增长的高质量教育需要与供给不足的矛盾依然突出,尤其是对教育结果公平满意度很低。如何通过相应的教育政策和财政策略,办出人民满意的教育,实现所有适龄儿童少年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取得满意的教育结果值得研究。
美国联邦政府对教育公平的政策经过多年的实践,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虽然中美两国的政治体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两国政府在注重公共服务和财政绩效,以及追求教育公平、回应公众实际需求意愿方面有共通之处,毕竟政府都是受纳税人委托,通过公款支出为公众提供他们所期望的教育服务。而且,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和经济大国,追求并希望在国际化中获得未来人才竞争的优势,了解和借鉴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教育成功的实践也是必要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着眼于未来我国教育公平的政策目标追求,系统分析美国联邦政府教育结果公平的政策导向及财政策略,可以为我国促进教育公平发展的财政政策完善提供一定的启示。
一、美国教育公平政策的新导向
一般而言,教育公平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机会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联邦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法案,比如 《国防教育法》(1958)、《民权法案》(1964)、《初等与中等教育法》(1965)、《残疾儿童教育法》(1975)、《教育巩固与促进法》(1981)等,投入了大量的教育资金,建立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联邦教育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目标是推进了美国教育机会公平的进程。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美国教育财政政策目标的重点是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公平问题,反映在教育财政上是解决教育领域财政资源的公平与充足问题,州与学区间教育经费的差异明显缩小,教育过程公平的实现范围不断拓展。
2001年国会通过2002年实施的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简称NCLB)法案标志着美国教育政策目标开始转向追求教育结果公平。2009年,奥巴马政府针对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更加务实的教育及财政政策,实施了“力争上游”(Race to The Top,简称RTT)政策,提出了让“所有儿童都成功”的政策目标,以期通过提供高品质的教育促进教育结果公平的实现,提升了教育结果公平的层次。结果公平作为美国教育公平政策实践的新导向,强调的是联邦政府的财政资助对学生学业成绩、学生未来发展的作用,更强调美国教育改革发展对国家战略、全球竞争力的战略意义。
(一)NCLB法案:教育政策追求结果公平的开始
2002年,美国联邦政府实施了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该法案突出强调了缩小学生学业成绩的差距,强化州与地方政府教育结果公平的绩效责任。该法案的主要内容:(1)建立州学生学业评价标准,将阅读和数学作为学业成绩评价核心课程进行州统考;(2)学生学业成绩评价面向所有学生,要求在2014年100%达到熟练程度;(3)设立年度进步奖,对学生学业成绩改善的州和学区进行奖励,对没有达标的学区、学校进行干预;(4)利用教育券计划、特许学校等市场选择形式,倒逼学区、学校改进学校绩效,提高学生学业成绩;(5)公开州、学区、学校学生学业成绩及相关信息,充分发挥社会和公众的舆论监督作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第一次将财政资金与学业成绩联系在一起,强调根据学校完成目标的情况以及接受绩效问责的结果进行的财政分配。[1]联邦政府希望通过强化结果公平的绩效责任来消除学业成绩差距,使所有的学校、所有的学生在阅读和数学学业上都必须达到相同的学业标准。[2]
联邦政府教育政策目标之所以转向教育结果公平是基于美国基础教育质量分化做出的选择。根据2000年的学术能力测验结果,12年级的黑人学生中只有16%能够熟练阅读,3%在数学上达到熟练水平;拉美裔学生中有20%能够熟练阅读,但也只有4%在数学上达到了熟练水平。[3]这种状况与联邦基础教育长期以来经费资助的模式有密切的关系。美国自1965年的《初等与中等教育法》颁布以来,向所有处境不利的儿童提供了大量特殊的补偿教育与财政资助,以“TitleI联邦教育资助项目”为代表的大量联邦教育资金大多投入到“处境不利儿童”的教育项目。这种只管投入不问结果的教育财政支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弱势群体教育公平的实现程度。在一定意义上,《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强调绩效责任也是对过去教育财政支出模式的反思和改革。到2007年,4年级的阅读和数学、8年级数学的黑人学生以及拉美裔美国学生学业成绩均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分。[4]
(二)RTT政策:教育政策追求结果公平的深化
2009年,奥巴马政府开始实施了力争上游政策,提出“人人都能成功”的政策目标,更加务实地推进教育结果公平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完善标准,改进了学生学业成绩评价体系和绩效评价体系。即追踪学生学业成绩的进步,衡量学生是否为上大学或就业做好了准备,是否促进学生个性化学习方式的发展;对于那些需要改进的学校采取扶持政策,而不是简单地处罚。(2)加大教育改革的财政投入。签署 《2009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在教育上投入1 000亿美元,用于学校教学改革、缩小成绩差距,使各种不同背景的学生达到较高的学业标准;将50亿美元投入“力争上游”和“有效方法与创新投资项目”。[5](3)重新界定学校重组。 2012年,奥巴马政府对全国50%以上不达标的学校实行豁免,可以不履行法案规定的核心条款,但学校和学区必须保证要为学生升学和就业发展设置新的目标,必须把对教师和学校的评价与学生的标准化考试成绩挂钩。[6](4)开发绩效考评数据系统,有效地使用高品质、适时的数据,包括通过对整个政策和项目的评估与绩效测量。联邦教育部投入资金开发学生学业考评系统和学生成绩数据系统,用于监测学生成绩进步、教师改革教学、学校及联邦政府教育政策调整。
至此,美国教育政策进入了追求更加务实、高层次的教育公平阶段。结果公平是每一个受教育者真正需要获得的教育公平,是国家实现教育公平,进而实现社会公平的根基。为了真正实现教育结果公平,近年来,联邦政府采取相应的策略,充分发挥了财政保障职能。
二、推进教育结果公平的财政策略
为了进一步推进教育结果公平政策目标的实现,美国联邦财政采取了一系列的财政策略,包括按照优先次序编制教育预算、赋予州和地方政府使用经费较大的自主权、公开教育支出形成的教育结果绩效评价信息等,以保障教育结果公平目标真正落到实处。
(一)策略1:按照优先次序编制教育预算
判断一个国家教育政策目标并不仅仅是看政府文件中的表述,更重要的是看政府预算对该政策目标的资金保障,尤其是对优先项目的选择。在教育资源约束的条件下,每个财年政府围绕着实现教育结果公平政策目标要优先解决的领域,进行优先项目编制和教育预算保障。联邦教育优先项目预算纳入美国总统预算,它是联邦预算的重要内容,体现联邦政府国家政策的重点,是联邦资金投入优先保障的支出项目。根据联邦预算过程,政府不同部门在预算编制阶段都会提出预算优先项目,总统教育预算优先项目来自联邦教育部根据国家教育政策重点提出的资金项目要求,是对教育领域法定支出拨款和自由裁量拨款的综合运用,反映出联邦政府教育财政支出项目的重点选择,也反映了政府的教育政策的导向。
联邦教育预算数据显示,联邦教育预算的优先项目重点投向了NCLB法案的项目实施,确保不让一个孩子掉队。2006年联邦用于NCLB法案项目支出达253亿美元,占联邦教育预算总支出560亿美元的45.18%;2007年NCLB项目支出为244亿美元,占联邦教育预算总支出的42.12%;2008年NCLB项目支出为245亿美元,占联邦教育预算总支出的46.78%;2009年NCLB项目支出为245亿美元,占联邦教育预算总支出的42.23%。从2006年到2009年,联邦教育预算总额每年基本保持在560亿美元到592亿美元之间,其中每年用于(NCLB)法案实施项目的资金均在40%以上。这些项目主要包括,提高学习落后或退学学生的学习成绩,提高学生阅读与数学能力;改善处境不利学生的教育质量;培训教师教学技能,加强教学研究;奖励学生学业成绩进步的州、学区和学校;建立学生学业成绩测评数据系统;增加和改善特许学校;扩大学生家长择校权等。
2015年,奥巴马政府教育预算优先项目选择凸显其追求务实的教育结果公平政策导向,目的在于通过提供高品质的教育,促进教育结果公平。比如,优先投入164.758亿美元,通过一些新创的项目,以及与已有项目的组合来着力解决缩小学生学业成绩问题;优先投入15.95亿美元用于“投资创新”项目、“高中再设计”项目、“STEM创新提案”①“STEM创新提案”,是美国联邦推进的以改变学校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方面的教学状况而设立的创新项目。“STEM”是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Mathematics,即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英文缩写。,以改变美国学校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的状况。优先投入30.35亿美元支持低绩效学校实施转制,实行新的学业成绩评价,提升学校教师和领导力,提高教师的教育实践水平和学校管理水平;优先投入25.95亿美元发展高品质的学前教育项目,保障教育起点公平等。
(二)策略2:赋予州和地方政府使用经费较大的自主权
赋予州和地方政府使用经费较大的自主权是联邦政府根据美国地方教育自治特点,以及考虑州与地方教育经费需求和实际情况不同而做出的策略选择。联邦体制下的美国,宪法并没有授权给联邦政府直接干预教育的权力,举办教育是州和地方政府的权力。比如2004—2006年,夏威夷州为捍卫独立的教育领导权,曾宣称不要联邦政府的经费资助;弗吉尼亚州和犹他州也通过州议会的立法拒绝按联邦政府的意志实施教育改革。[7]但同时由于各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许多州与地方政府对联邦教育拨款又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依赖。比如,1999—2000年,阿拉斯加州、亚拉巴马州、路易斯安那州、新墨西哥州、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密西西比州等,联邦教育拨款占这些州教育经费支出均超过了10%以上。[8]研究人员在分析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考察经费投入与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综合了4个具有代表性的州的情况发现:即使在各州的拨款增加15%,地区资源利用率提升15%的情况下,联邦政府对堪萨斯州的拨款须增加18%,纽约州须增加129%,加利福尼亚州须增加547%,密苏里州须增加1 077%,才能实现“良好”的绩效目标。[9]
对州与地方政府而言,既能得到联邦政府教育拨款,又在资金使用上较少受联邦干预是其理想追求。联邦政府为适应这一状况,建立了灵活使用联邦教育拨款的关系链:联邦制定教育政策目标—提供资金资助—州与地方政府签订教育绩效问责协议—州与地方政府灵活使用联邦教育拨款—联邦以结果进行考核、决定奖惩。比如,2001年的 《州和地方资金转移法案》增加了对联邦资金使用灵活性的条款,允许州和地方无需批准便可以转移不超过50%的联邦资金,用于提高教师质量,或者改善教育技术、创新性项目,或者建立安全无毒学校等项目上。2002年 《州和地方灵活性示范法案》资助项目达到150个,参与的学区5年内可以自主使用联邦资金提高学生成绩,并以成绩协议作为交换。[10]赋予州与地方政府使用联邦拨款的自由裁量权,充分调动他们参与联邦教育结果公平绩效问责的积极性。
为遏制地方政府及学校的投机行为,保证结果公平评价的客观性,联邦教育结果公平政策实行教学与学生学业评价的分离,有效促进联邦教育拨款的有效使用。在结果公平评价体系中,(1)学生学业标准由政府、民间组织或研究机构共同制定。2010年,全美州长协会和州首席教育官理事会共同发布的《共同核心州立标准》,是由州首席教育官理事会(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CCSSO)和该协会最佳实践中心(NGA Center for Best Practices)共同开发。[11](2)教育结果评估系统是政府委托民间机构开发。如,2010年10月,联邦开始为“更智能平衡评价联盟”开发与 《共同核心州立标准》相匹配的3~8年级以及高中学生英语语言艺术和数学的综合评价系统提供了为期4年、额度达1.6亿美元的发展基金。[12](3)以社会化考试的方式进行学生学业成绩测定。如美国的学术评估考试(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俗称SAT考试)、托福考试等。
(三)策略3:公开教育支出形成的教育结果绩效评价信息
2002年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要求州、学区、学校发布教育支出形成的教育结果年度绩效报告。年度绩效报告必须满足:呈送的对象要清晰,呈现的信息要全面,提供的信息能够进行比较,并要与其他的绩效问责文件相协调等具体要求。[13]学校绩效报告必须系统公开采用的绩效目标,公开学生实现这些目标中取得的实际学业成绩、学校努力及成功缩小绩效差距等信息。[14]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为例,州政府公开的教育结果评价信息包括评估结果(如学生参与率、学生达到熟练水平百分比、高中合规毕业率、确定的高中毕业率增长指标、变化的高中毕业率增长指标、四年制团队毕业率等)、评估标准、评估方法、评估流程、评估各个相关利益群体(如县、学区、学校、特许学校、低收入学生、英语学习者、残疾学生、族群划分的学生团体)的数据文件,以及 《初等和中等教育法案》(ESEA)法律文件,这是公开教育结果评价信息的基本依据。①参见 《2012—2013加利福尼亚州教育问责进步报告信息指南》,加州教育部网站。公开的信息不仅有报告类,还有数据类,每一个教育机构、每一个相关利益者,乃至社会的每一个公众不仅可以在官网上可以查阅,公众还可以向相关部门申请文本,如果申请者不能阅读英语文本,还可以申请获得不同语言的文本。
联邦政府不仅要求州、学区、学校的绩效报告信息公开,同时也给予学生家长“用脚投票”的权利,倒逼地方政府有效使用联邦教育拨款,不断改进绩效。例如,家长可以根据学校绩效报告进行市场选择,参与教育券计划、特许学校计划,离开原来学校,但经费仍然要由地方政府额外负担。
三、美国联邦政府教育公平政策新导向与财政策略的启示
美国联邦政府对教育结果公平追求的政策导向是政府对公众公共教育利益诉求的明确回应。就教育公平而言,追求教育机会和教育过程公平的最终目标是获得教育结果的公平。对公众而言,最关心的、可以直接感知到的是教育结果。从“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到“让所有儿童都成功”都凸显出联邦政府对教育结果公平政策目标的追求,相应地,教育财政支出目标锁定教育结果公平也是实现政府财政支出绩效最大化的体现。对中国大部分地区而言,教育公平正处在从机会公平转向过程公平,发达地区的政府已经开始对教育政策目标进行调整,追求教育结果公平的政策目标离我们也并不遥远。
(一)“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本质是给人民满意的教育结果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中央政府对人民承诺多年的政策目标,但每年的“两会”上教育仍然是热点问题。人民并不否认政府对教育财政投入大幅度增加的事实,而财政投入教育的结果却倍受诟病。从根本上讲,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是对学生基本素质的培养,为学生未来的升学和就业做准备。学生的学业成就是获得未来成就的基础,社会和家长最关注的也正是学生的学业成就,人民满意的教育就在于政府在现实条件下,能够根据国家教育标准,为每一个受教育者提供水平大致相当的教育结果。接受教育者不希望把时间耗在所谓的拥有教育机会却不能拥有真正意义上教育结果,更不满意获得地区间、城乡间、学区间有数倍差距的教育结果。教育机会和过程公平是追求教育结果公平的必经阶段,但这三个阶段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并非一定等到教育机会和过程公平实现之后才可以谈教育结果的公平。其实,美国教育机会和过程公平至今也没有完全实现,但联邦政府以教育结果公平作为政策的导向,恰恰是引导地方政府教育财政投入关注教育结果公平,以教育结果公平的实现程度作为政府教育拨款的依据。在这一政策导向下,教育机会和过程公平的目标实现在加速,政策注重教育结果公平的“提纲挈领”的“纲”在发挥作用。我国实现教育机会和过程公平的财政投入不断增长,但教育机会和过程公平实现的程度并没有同比增长,关键问题在于要改变现行的政策导向和政绩考核标准。考核政府花钱绩效的标准不是仅仅考核政府花钱办了什么事,还要考核政府花钱办了哪些百姓满意的事。中央政府教育政策应有明确的导向,以教育结果公平实现的程度来考核教育投入结果,以公众对实现教育结果的满意度作为配置教育财政资金的主要依据,才可能办出人民满意的教育,真正实现以结果为目标的教育公平。
(二)以结果公平为导向赋予地方政府和学校财政支出自主权
在教育财政管理过程中,当政策目标清晰后,实现政策目标的方式就可以灵活选择。相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地方政府及学校因为更了解本地的实际和公众的教育需求,更能提供有针对性的公共服务,也更便于公众对于财政支出效果进行监督,因而应该赋予地方财政支出的自主权。分税制改革以后,我国大部分地区教育发展依赖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但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占比过高,抑制了地方政府和学校根据实际做出决策的行为。尽管近年来,中央政府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合并,也减少了一些地方政府配套,但有关专项管理制度改革相对滞后,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和学校在教育硬件投入上只能重复建设或豪华建设。从根本上说,专项财政支出的目标具有单一性,况且,有些教育专项属于中央政府的不同部门,多个专项之间并不一定是构成总目标的有机体。这就需要用一个总目标统领专项,根据总目标实现的关联性配置教育财政资源。一个学校的资源配置应该根据与学生学业成就关联性的大小进行先后、多少的配置。如果地方政府和学校缺乏财政支出自主权,就不可能对教育资源进行统筹配置。美国联邦政府的教育拨款也是以专项的形式进行分配,但在资金使用上赋予州、地方政府和学校较大自主权,条件只有一个:实现联邦政府教育结果公平的政策目标。改革我国教育领域的财政支出体制与转移支付制度,首先,中央与地方政府应明晰实现教育公平政策目标事权的划分。对于保障全国性义务教育公平的事应该由中央负责,如保障全国所有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保障所有适龄儿童获得最低标准教育服务的基本条件,保障所有适龄儿童有机会获得国家规定最低标准的教育服务。明晰事权是明确财权的前提,是财政支出体制改革的基础。其次,建立与地方政府财力和教育责任相适应的、科学规范的教育转移支付制度。一是以教育结果公平为导向,确定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学生实现教育结果公平的转移支付模式,加大对贫困地区、农村地区、特殊需要学生的拨款权重。二是以教育结果公平作为绩效考核标准赋予地方统筹使用拨款的自主权,引导地方政府按照与学生学业成绩的相关度配置教育财政资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签订教育结果公平实现程度协议,要求地方政府及时全面地公布教育结果公平及财政支出相关信息,以此获得教育拨款使用的自主权。
(三)财政诱导、信息透明、社会参与是实现政策目标的有效途径
在推进中央政府教育财政政策目标上,相对于美国教育分权的联邦政府,我国的中央政府具有优势;相对于行政命令,财政诱导更具优势。理论上讲,在我国,中央政府权威和财政诱导有机结合更是具有无可比拟的政策推进优势。但对地方政府而言,中央政府行政命令是“不得不干”,而财政诱导会使其“自觉和积极地干”。因为“中央点菜、地方买单”政策执行方式有时会挫伤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从根本上讲,财政诱导就是政策目标加上财政支持,中央政府在明确教育政策目标的基础上,配以财政资金支持,地方政府以实现目标作为承诺,获得中央政府财政拨款。如果中央政府以教育结果公平作为财政拨款要实现的政策目标,并赋予地方政府和学校相应的经费使用自主权,可以加快我国教育公平进程。
信息透明是社会参与的基础。信息透明的关键是学生学业成就信息的透明和财政支出的信息透明。社会参与,一方面可以满足公众教育利益诉求和实现教育选择权;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公众对公开的信息进行评价,来监督地方政府教育财政支出及学校绩效的改进。在中央政府强调教育结果公平的财政政策导向条件下,赋予地方政府及学校财政拨款使用自主权的同时,辅以信息透明和社会参与,将会有效地遏制权力的滥用、资金浪费及腐败等问题。因为有了信息透明和社会参与,教育政策目标的实现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事情。如果将教育结果公平评价的标准、学生学业成就的考核方式及教育财政支出绩效披露都纳入到社会参与的范畴,实现中央政府教育政策目标将会形成一个有众多推动力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