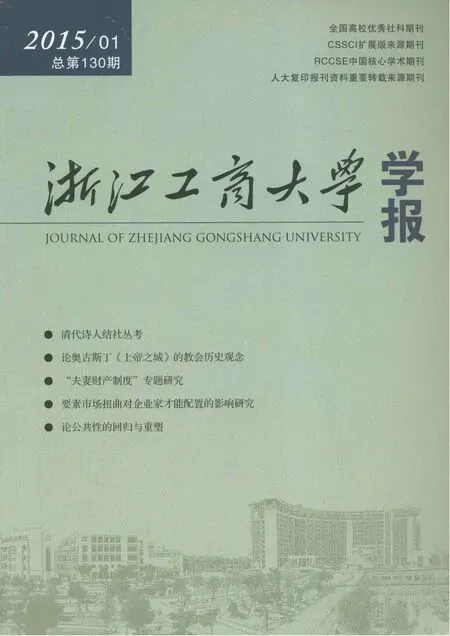论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教会历史观念
石敏敏
(浙江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杭州 310018)
论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教会历史观念
石敏敏
(浙江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杭州 310018)
摘要:《上帝之城》第十五和十六卷围绕“复活之子”的观念,论述了“希望求告上帝的名”与教会论之间的关系,阐释了教会作为地上之城的羁旅的含义。本文指出奥古斯丁历史哲学视野下教会的福音性本质,即教会是流动着的爱的会幕。奥古斯丁又把这种福音性的爱进一步表达为公民的责任,告诫教会不仅要警惕他自身与世俗的权柄之间的关系,而且要警惕以在天的权柄即在上帝之名下拥有权柄介入世俗共同体的界限。奥古斯丁以他对教会的福音性理解诠释了“为我们的上帝”的历史性。
关键词:教会;流动的会幕;“为我们的上帝”;公民
《上帝之城》可谓鸿篇巨制,所涉主题无所不至,中心议题则聚焦于教会与历史。《上帝之城》的所有批评和辩护都围绕教会论开展。奥古斯丁从批评罗马共和政体入手,跟着讨论真正的共和政体与上帝的国度的关系,循此论述教会的历史形象及其预表,结之以上帝的国度与和平的观念。整部《上帝之城》凡二十二卷,以基督的预表(旧约)、降临(新约)和审判为叙事脉络,诠释基督的形象与教会的意识,经由教会彰显上帝的经世,突出教会的现实性,阐释教会的历史性。虽然奥古斯丁所谓的无形教会在《上帝之城》中时隐时现,占据一定份量,然而有形教会才是该书真正的主题。耶稣基督的形象被主要地表达为教会与历史的关系,呈现出教会的历史性和存在性。
第十五和第十六卷是《上帝之城》的中枢所在。从第一卷到第十四卷,奥古斯丁把笔墨主要用于对希腊罗马文化、哲学和政治的批评,既指出罗马城的毁灭源于罗马文化的缺乏羞耻感,也指出希腊罗马文化中优秀部分得益于罗马哲学家能够领略神意。以此为主旨,前十四卷用无形教会诠释上帝的一般启示,显示特殊启示之前,其他民族和文化受无形教会的护佑。无疑地,奥古斯丁认为普遍启示对异教民族是不完整的。在解释《创世记》前几卷时,奥古斯丁也把无形教会用于解释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
自第十五卷开始,《上帝之城》描述两城的起源,呈现教会的历史,烘托出教会的异象。前第十四卷属于哲学和文化批评,指出无形教会的超越历史的品性;第十五卷则把有形教会作为全书后半部分的重心,它是论述的焦点。奥古斯丁用很长的篇幅讨论无形教会,只是为了说明有形教会应当如何效法上帝之城,指出永恒之城在世的形式。也就是说,奥古斯丁的教会论重心在于历史中的教会形象,展示教会的肉身形式和历史所披戴教会的位格特性,使得教会论不沦为空洞的神学语言,不溺于浪漫主义的脆弱性。在论述历史的教会时,奥古斯丁以为基督教之所以能够避免历史上各种思想流派没落的命运、避免道德解释的局限性,主要是由于教会是福音的主体。正因为教会历史性的福音性主体特质,奥古斯丁认为基督教的首要性并不是追求或者讲求超越性经验,而是彰显教会在历史中的荣耀,这也是《上帝之城》开卷史诗般的宣言所表达的意旨,“无上光荣的上帝之城,或是在时间的穿梭中,因信得生,在不敬的人们当中旅行;或是稳稳地坐在永恒的宝座上(现在她正满怀耐心地期待着那宝座,直到‘公义要转向审判’,然后靠了那最终的辉煌胜利和完满的和平,终将获得)”。[1]6
一
有关教会的谈论与有关基督的谈论密切相关。《上帝之城》第十五卷从三个方面谈论耶稣基督:应许之子、复活之子和受难之子。奥古斯丁主要是从复活之子来讨论教会的地位。耶稣基督是复活之子,教会是耶稣基督升天后历史之中的复活之子,教会是耶稣基督在历史中的复活的形象。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教会之于历史的关系在于建立盼望。复活者耶稣基督把复活所激起的盼望经验遗传在历史之中,以期消除历史的罪性,实践对于必死之人的救赎。第十五卷有关上帝之城的其他种种表述例如客旅、“为主而不是为奴”和公民等等,都是基于复活之子的观念,进而指向历史的罪性脉络。因着耶稣基督是复活之子,耶稣没有因着历史惯性成为历史有限性所支配的被动者,也不是历史罪性的造成者;因着教会是复活之子的形象,教会以复活为异象,教会在历史中的具体使命以复活为最终的关联对象和目标。教会唯一的目的就是仰望耶稣基督,并如同耶稣基督,克服死亡投在教会身上的影子,即克服俗世共同体的特性。因着教会是耶稣基督在历史中的复活形像,因着教会是复活之子,教会与历史的关系不同于其他俗世共同体与历史的关系,后者受历史的主导,而教会则主导了历史。也就是说,教会成了历史的界限,[1]255教会为历史设限。透过教会为历史设限,历史不再被表达为人的荣耀,而要显出上帝的荣耀,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形象。
因为教会是复活在历史中的耶稣基督,教会不享受世俗的权力,不以世俗权力为享受对象,也不受俗世权力的支配。教会的权柄既表现在不受制于世俗的权力也不表现为掌握世俗的权力。在世俗生活中,人们习惯于为保护自己而支配别人,人们也因了避免不受别人支配而筑城。城和塔是地上之城的权力象征,筑城的人以人的方式使用权力。凡地上有权的人,都透过各种形式为他自身筑城,筑各种各样的城,包括筑自己的坚固的家园。城和塔既表现社群关系,还表现俗世的权力格局,它透过各种交换形成支配模式。地上之城的人因为是建立在有限的生命之上,不是建立在复活的生活之上,因而惧怕死亡。他们筑城正是要拒绝死亡,而保证自己的安全。他们害怕自己为奴,而凡害怕自己为奴的人通常已经为奴了,他们已经以各种方式在为奴。他们怕失去自己的生命,这个时候他们就做了自己生命的奴隶;他们害怕财产被人剥夺,这时候他们就成了财产的奴隶;他们害怕被别人囚禁,这时候他们成了自己自由的奴隶。这就是地上之城的“权力”中的“为奴”。[1]229-230凡为奴的,都从肉身而来,因为为奴的首先就做了肉身的奴隶,服从于他自身的淫欲,自然使他自身生活的其他部分也服从于这种淫欲,这是地上之城的生活方式,其权力来自于地上的欲求。凡以地上之城为生活的,就生活在为了肉身的权力冲动中,这样的权力只是一种为奴的权力。
作为复活之子的教会不为自己筑城,教会也不为自己筑城,显示了教会共同体与历史的特殊关系,这就是教会是历史的界限。教会不将自己表达为历史之中的驻留者,它仿佛随时准备着要离开历史,就是奥古斯丁反复说的教会只是地上之城的客旅,只是在这个世间长长的日影中走过的游子。然而游子,那沿着长长的日落沿着阳光行走的游子不失去日影,他们从不失去光辉,因为他们只是照着那敞开的阳光行走,他们不试图囤积光阴,也不囤积权力。教会的权力恰恰不是试图去拥有地上的权力,它不以任何方式拥有地上的权力,却以全部方式拒绝地上的权力,拒绝以参与地上权力的方式拥有地上的权力。教会更要警惕地上之城的权力无所不在地渗透在教会之中,它们千方百计地诱使教会成为权力之奴。
教会想要避免陷入俗世权力的危险,避免地上之城的权力诱惑,就只能“希望求告上帝的名”。如果说教会有什么权力,有什么真正与俗世权力相区分的权力,那就是“希望求告上帝的名”的权力,这是教会作为复活之子的唯一权力,是教会所拥有的唯一的权力。“上帝的名”之所以是一种权力,是因为一切创造原本都奉上帝的名所造,因为“求告上帝的名”就是从权力向受造物寻求转回向上帝寻求。求告上帝的名是真正的权力,因为它寻求上帝创造的权力而重新创造。教会既然是复活之子,是除去了旧恶和原罪的重生之子,就必须得牢记这种位份,而教会只在奉上帝之名时才握有免于诱惑的权力。要奉上帝之名必须先“希望求告上帝之名”,因为只有“希望求告上帝之名”才能够不仅自身会奉上帝之名,还会兴起后裔求告上帝的名。
奥古斯丁非常强调“希望”这个词。“希望呼求上帝的名”[1]229-230的重点不仅在“上帝之名”,还在于“希望”。正是“希望”这种寻求的状态,它使得教会不自以为已经就是上帝的教会了,更必须要成为上帝的教会和兴起教会。希望求告上帝的名,是求告上帝兴起教会的传统和更多的后裔。这样的求告上帝之名,正是求告上帝新造的秩序,使这个秩序成为历史的秩序。上帝正是这历史秩序的始终,从而历史以上帝为主。当教会谨记上帝是主时,它就不会为奴了,因为教会它是子,是继承了产业的子,它也就得以免于地上之城的诱惑。它因着求告上帝之名成为世界的主,成为历史的主。地上之城的人正是因为不求告上帝之名,把自己与上帝分开,没有获得“上帝之名”的权力授予。由于受造物与它冲突令它不安,因此它要筑城。这就是求告上帝之名的的吊诡之处。教会求告上帝之名,它就自然地成为这世界的客旅,不以世界为实在;不求告上帝之名的人,却使得世界以他们为客旅,因为他们担心被世界抛弃。复活之子教会以抛弃世界的方式进入世界,这是教会的责任,也就是福音了。基督教的本质就是福音,就是那复活之子已经在历史中成为客旅的信息,就是要让这信息成为地上之城的界限。“希望求告上帝的名”成为教会“历史”的前设。
教会求告上帝的名使得教会成为上帝的教会。在这里面,奥古斯丁阐释了非常重要的观点,因为教会成为教会在于求告上帝的名。那么何以求告上帝的名使教会成为教会呢?因为当教会求告上帝的名时,教会不再会滥用人的自由。教会毕竟由人所组成,举凡人组成的机构,都会带着傲慢的可能,而所谓的傲慢,乃是对自由的滥用。傲慢的人首先是滥用他自身的自由,滥用他自身对于他人的他者关系,把自身对于他者的关系变成自身对于他者的占用关系,而不是平等的聆听和取予关系。其次傲慢是滥用他者的自由,因为他者的世界受那个滥用者的剥夺,受他者的压制。而教会成为教会最大的危险就是滥用自由,因为滥用自由的人都只信任他自身的抉择,只信任他自身的自由中而来的秩序。滥用自由的本质就在于他只信任秩序从他的决定而来,以致于他成为他人的自由,因为他的秩序成为他人的秩序。正是在这里面,教会求告上帝的名可以避免教会任用他自身的而实际上是由他自身的人意中作出的决定。[1]260-261教会成为教会,就是求告上帝的名。因为求告上帝的名时,教会放弃了他对于自身的自由的任意运用,放弃了他自身为人所做的任意设定。教会必须放弃这些权力之后才能够成为教会,因为教会在放弃了这些权力之后他求告上帝的名,只遵循上帝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教会成为教会就是只聆听上帝,就是任由上帝的权力在他身上显现。由此而论,教会必不会成为地上之城的奴隶。教会在遭受逼迫时,仍然有上帝的权力在他身上,而它自身的在地上之城的磨难成为了一种荣耀,成为一种尊严,成为一种超过迫害和死亡的自由;同样当教会在一个充分地得到合法尊重的国度里面,教会同样不会滥用它的权力,因为它的权力仅只是福音。福音使教会得自由,因为福音是教会唯一合法的自由,而福音正是教会所求告的上帝的名。
二
奥古斯丁以教会为复活之子,以地上之城为死亡之子。复活之子的教会不再为奴,在于教会不滥用人的自由,而在于接受上帝的救恩。自由来自于救恩,使得人自身的自由重获法度,一种天国的法度。正是因为如此,教会乃是地上之城的客旅。地上之城的人却不欢迎他来作客,相反,地上之城总要兴起对于教会的逼迫。该隐杀亚伯,正是地上之城之于教会作为客旅的含义。该隐因为嫉妒而杀亚伯,[1]235诚然该隐嫉妒亚伯而不是他自己的祭物被上帝接纳,然而更深的意思则是该隐嫉妒亚伯身上的自由,亚伯有一种来自于天国的自由。[1]229因为这种天国的自由,亚伯、塞特和以挪士所代表的教会形象主动地作了客旅。因此复活之子视地上之城为客旅,视世间的历程为客旅,乃是主动地拒绝历史对教会的拘禁,基于内心所不能忘怀的警醒,即他们不愿意受世界的设限,而要穿戴自由之身。他们主动地以这种天国的自由尺度这地上之城的羁绊,他们看到这世间所造成的只是羁绊。他们正是因着这种积极的自由而规避地上之城的消极自由。因着这种消极的自由,死亡就成了自由的最大约束,因为他们惧怕并逃避死亡,他们害怕那毁灭的到来。也正是因为这种天国的积极的自由,教会及其构成者不以羁旅为无意义,不如那些地上之城的人在享受他自身所谓的或者说单纯地来自于他的自由的时候却发现自由的无意义,因为在这样的自由里面,总有罪的形状。无意义正是罪的形状。相反,客旅者却发现了他们在羁旅中的意义,就是成为教会,有荣耀披戴,有永不动摇的应许与他们同在。正是因为复活之子,教会成为应许的实底,成为耶稣基督之后可以得见的荣耀,历史的上帝的肉身。
客旅的含义,与上帝给教会的应许及自由的不滥用内在相关,均指向教会的属性和使命。教会诚然不属于地上之城,然而它不是以逃避而不属于这个世界,不是因为逃避而是客旅,它是因为成为教会而是客旅。[1]324当教会越来越成为教会的时候,教会就越来越展示出它在这个世界中的客旅的性质。相反,当教会始终只是这历史的肉身时,教会就越来越像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因为当教会越来越具有后者的形状时,教会越来越像这个世界,教会失去了或者部分地失去了福音的性质。教会之成为教会乃是基于对福音含义的真实理解,因为福音的本质关联上帝的自由。越能体会上帝的自由,必越能明白上帝的福音并且把它领受为生活方式。正因为如此,福音是复活之子的历史的形态,因为福音靠着教会传播开去,而福音之所以能够传播开去是因为福音里面有上帝的自由,因为有上帝的自由就不再迷恋于地上之城的自由,在本质上来说也不迷恋于在地上之城掌权的自由,不迷恋于在地上之城所获得的任何支配权的自由,不以获得地上之城的任何形式的支配权为教会的象征。复活之子既挣脱了死亡的权柄,也挣脱了一切所谓的生存的世俗形态的权柄,而后者本质上都属于死亡。因此越能够成为客旅,就越来越成为教会。这样的教会只以宣讲上帝的福音为其自由的唯一形式,而不宣讲任何与福音的教导相反的东西。
教会以复活之子为形像,意味着教会以福音性为目的。而在所谓的福音性里面,教会必须理解它的基本含义之一即客旅。客旅是福音性的主要含义之一。为客旅的人,它不置办自己的产业,也不为自己置办产业。它不是为了定居在一个地方而事生产,它是为了享有那风景,享有与种种具体地方的距离而生活。为客旅的人乃是在传递种种美好的东西的人,把它带入不同地域,让他们知道一种与他们所固定的生活方式所不同的异质的生活方式。客旅者既没有自己的产业,却又传递着他们在旅行途中所获得的美好的产业。这就是客旅者的生活了。教会之为客旅,正在于教会成为福音性的表达。教会不是要独有其所获得的奥秘,真正的奥秘必是社群性的,必是为他的,因为这是客旅中所获得的“好”的真正的本质,“好”的本质在于它的共有性。[1]300因此福音的教会不是它固定的产业例如拥有教会的房子,例如拥有多少信徒、再例如拥有多少财产,而在于它是移动者,不断地外显着那种福音的动力,只有复活之子才具有这种动力。教会就这种福音性的本质而言在于它的群体,教会就是因着福音并为着福音才真切地体会到群体之好的重建。[1]319-320正是在这个地方,教会是移动的会幕,上帝则是“为我们的上帝”,正如教会乃是客旅。在移动的会幕和客旅之间,所构成的真是教会之成为教会的那种动力,那种动力持续地敦促着教会向着复活之子在使徒身上、在众门徒身上、在历史身上昭示出来的异象。
教会的福音性在于它的流动性、在于它的不断地旅行,这是奥古斯丁用客旅一词对于教会之为福音性的更深入的诠释,也是对于教会的共同体特质的更深入的诠释,更是对“为我们的上帝”的深入诠释。[1]293-294教会以福音为结成的共同体。教会之成为教会是在流动中形成它的权力或者说权柄观念和运作的,而与其他任何形式的共同体所基于的本质不同。民族的共同体以血缘和婚亲为权力关系的基本内容,国家共同体先是以民族或者众家族,继而以区域,最后才以法权为基础。现代意义的文明国家观念最终蜕变以法权为基础,是来自于基督教的自然法观念,而基督教的最初的自然法观念就表现在教会中。因为教会的法权以福音为本质,以不同种族和区域的人因着福音结成的法权观念为基石。这种法权关系完全是因为基于聆听一位道成肉身的上帝为聚集,这种权柄基于聆听同一位主而结成。一个在历史中作为的上帝如同奥古斯丁透过历史观念的教会所论述的,乃是为万民的“我”的上帝,以他的名而聚集的教会本身就是这种普遍法的权柄观念的基础,他挣脱语言、肤色、国别、党派、血缘、财产、观念、文化、情感等关系,也挣脱了由所有这些方面所结成的权力关系以及权力关系的运用。[1]280-282基督教的福音性道出了基督教神秘主义的本质,即如何超越个人的限制而成为他人的祝福,这是福音性显出客旅的表征。在这种法权观念里面,每个人都成为与他人有共同体关系的人,成为一个流动的人,成为他人的好消息,成为一种福音,复活了他从复活之子身上得着的复活。在这样的法权观念中,人不是因着人的差别而分离,而因着他所事奉的神的差别(职事)而关联。
三
既然教会知道它只是地上的过客,那么教会似乎应该从社会运行的机制中退守出来。教会似乎只应保持对社会的距离,而不应该介入社会。若以此而论,奥古斯丁的教会论就支持如下观点:教会是与社会无关的另外一个世界?首先,奥古斯丁确实主张教会非国家化。这体现了奥古斯丁与君士坦丁的区别,也可以看到自隐修主义以来,早期教会尽力矫正君士坦丁以来的政教关系观念,形成新教会论。沙漠修士退入沙漠,既是出于灵性的理解即只跟从一个主(上帝),也是出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即存在着主导教会的另一个主(罗马帝国)。奥古斯丁揭开了西方基督教教会观念的另一个传统。奥古斯丁所谓基督徒和教会只是地上的过客,正来自沙漠修士所推动的教会运动,反思教会的国家化,包括教会独立、不受国家和其他社会机构的节制,也不接受其权力赋予。如果只是这样,又一定会带来另外的问题,即教会成为与社会无关的隐修士,教会对于社会没有任何责任,从而造成另一种形式的个人主义,一种教会的个人主义。评论者们在论述奥古斯丁的教会观时,或者倾向于把奥古斯丁的教会观国家化,或者把其教会观个体主义化。然而奥古斯丁的选择并非非此即彼。他试图阐释教会第二方面的内容,即所谓的“社会”维度。
奥古斯丁用“公民”这样的观念表达教会成为教会,教会作为复活之子的第二方面。[1]232-233教会还需要明白他是一个“公民”。奥古斯丁的“公民”所指为何?这经常引起误解。奥古斯丁的“公民”观念从批评西塞罗的共和政体开始。奥古斯丁赞同西塞罗的论述,即共和政体是最好的政体,天国降临的时候,其形式想必也是共和政体,有君王、有天使和圣徒们组成的元老院诸如此类。这样的政体心、意、情合一,形成完善的共同体。[1]230-231然而奥古斯丁又追问看似完善的地上的罗马共和政体即罗马帝国没落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敬拜除上帝之外的所有神灵。在这一点上,奥古斯丁倒转了西塞罗的“公民”观念。[1]230西塞罗的公民观念是一个地上之城的公民观念,他们的公民不敬拜上帝,以致于他们的公民不能够真正成为公民。要造就真正的公民,就不能够不敬拜上帝,公民观念从敬拜上帝而来,奥古斯丁的说法就是教会应当希望求告上帝,公民观念当从希望求告上帝而来。所谓的公民是对于上帝的求告,并且激起更多的人求告上帝。与西塞罗不同,奥古斯丁是在上帝之城、在教会内使用公民观念,而他认为这才能够真正确立起公民观念,成为地上之城如西塞罗所说真正完善的共和政体。[1]234
何为教会的公民?何为教会的公民性?前一个问题涉及教会的治理,后一个涉及教会在地上之城中的自我表达;前一个问题又是后一个问题的基础。奥古斯丁确实不曾有所讨论教会的治理问题,《上帝之城》全书并不是要表达教会治理,而是讨论教会与历史和政治的关系,或者说教会如何在历史中就是教会的政治问题。或许在奥古斯丁的时代,教会的建制即主教制已经清楚且无争议地得到了运用,不再需要讨论。然而教会治理与公民问题却是一个新问题,奥古斯丁虽然没有专题讨论,然而《忏悔录》第十三卷仍然有所论及。他以隐喻的语言表达了如何在教会中成为公民。教会中的公民或者教会中基督徒应该最能够表达自身为公民。在教会中既有统治者也有被统治者,然而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他们都依据圣灵而是统治者,也依据圣灵而是被统治者,[2]331公民之为公民在于他们都依据圣灵,因为他们只事奉一个权柄或者权力;同时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他们都无权裁决对方,统治者无权裁决被统治者,被统治者也无权裁决统治者,他们都只能依照圣灵而裁决或者被裁决。《上帝之城》谈到天国这种类型的裁决并不是一个难事,因为依照圣灵进行裁决表现了公民的成熟。一个基督徒在教会中表现为公民,就是仅依靠圣灵而裁决并且被裁决,因为公民的身份来自于对圣灵的接纳。由于基督徒是依法照圣灵而被建立的人,教会成员是具有新心的人,他们具有新心而各从其类,有宏大的光体,也有小的光体,然而他们只是处在不同的职份之中,只是不同职份者的配合关系,是合乎肢体的配合关系。公民基督徒清楚事事依照圣灵而彼此配合。这种基于新原则而“各从其类”,[2]331柏拉图《理想国》称之为社会分层,只是去掉了《理想国》所特意加在社会分层的高贵和低等原则。
无论如何,公民基督徒明白他们从圣灵而来并且求圣灵的果实,而不是求他们自身的果实,《理想国》从处在不同社会层次的人寻求他们自身的果实。教会中的公民遵守共和政体中君主制的形式,真正的君主是上帝,职位上得到分工的主教或者其他的神职人员则是依照君主的授权即圣灵而负责肢体的协调,而好公民则依照那位真正的君主成为秩序的构成者。在教会共和政体里面,一个公民,不只是一个法权意义上的公民,还是一个灵性意义上的公民,[1]202-203他们如同亚里士多德所说,不仅是好的统治者,还是一个好的被统治者,他们行事有度,充满理性、依着灵性的法度而是一个好的社群。这就是教会内部的公民表达。
那么何为教会的公民性?这个完全由公民构成的教会具有公民性。教会的公民性是教会的重要主题,因为它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公民性。依照奥古斯丁的说法,教会不能够去裁决众生之事,[2]因为教会是一种灵性的权威,是对于肢体内的权威,还因为上帝早已经在对于众生分别为圣,分别加以召唤了。教会必须放弃对世界的裁判权,后者是国家和地上之城的法律的事。教会又如何在地上之城表现他的公民性呢?教会的灵性也不受地上之城的裁决,正是教会的公民性所在。教会的公民性仍应从教会的灵性进行解释。教会要从它的强有力方面表现出他的公民性,或者说教会的具体性,这就是他的不受地上之城辖制的灵性。它不以它自己的福音为耻,正是教会的公民性。地上之城有关教会灵性和信仰的所有指责,以及加给其信仰的诸多方面的限制,都不足以令教会以其福音为耻,反而因着这种指责而愈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以及历史中的上帝的作为。因此,教会的公民性具有一种君主的性质。这正是教会在地上之城中最吊诡的地方,在一个公民社会中或者无论在一个臣民社会中,一个没有世俗权威的教会却具有并且表现出君主般的尊严。
四
教会不是地上的城,也不会在地上建城,教会是流动的会幕。[1]234这当然不是说教会不植堂,而是说教会不以地上的造物为产业,也不寻求地上的产业。[1]202-203教会是流动的会幕,是说教会以他的群体为产业,以他聚集的人为产业,在福音的使命下不断形成更大的聚集。教会的产业就是它所聚集的群体。这样的聚集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只以地上之城为客旅,旅行在大地之上。他们不仅不以教会的物质性形态(教堂等)为产业,也不以他们自身的物质性(例如身体和职业)为产业。奥古斯丁所谓不在地上筑城,既不是如同地上之城的人建城以寻求他们自己力量的庇护,也不是把城视为封闭的空间,要向外人封闭福音。教会既以大地为羁旅,他们就向所有空间展示福音。他们不筑城,他们向大地开放,表明他们是整个世界的公民,是地上之城的过客,是上帝之城的公民。他们是大地的旅行者,他们向所有的相遇者讲述上帝的故事,心中所怀想的却是天国之旅。他们虽然是浪迹无所依凭的游子,却已经有可以永恒安居的家园。[1]203-204
教会之为教会,视其移居的轨迹以及不断移居的进程为其果实。无论移居的轨迹还是移居所得的果实都是福音。教会成为教会的判定标准不只在于他们宣讲的福音,还在于这福音是否不断地成为他人的福音。教会要使自己成为福音的社群,这样教会就不会停止成为教会;基督徒要成为基督徒的群体,这样基督徒就不会停止自己成为基督徒。过客或者客旅的理念就是基于这种流动的会幕,基于教会群体的性质。因此一个教会之成为教会,在于教会身上的复数形式;一个基督徒之成为基督徒,也是基于他自身身上的复数形式。他们的复数形式就是他身上有弟兄姐妹形像的显形;而他身上的弟兄姐妹,是因为他爱他们如同爱自己,因为教会身上的复数形式是多个自我的形像,并且都是如同爱自我那样爱他们,这就是奥古斯丁所谓的邻人之爱。[3]37-38而之所以能够按着自我来爱其他的自我,是因为福音的联结,福音联结的是耶稣基督的形像。一个教会是否成长为教会,一个教会是否是客旅,并不单纯在于他把自己舍了,还在于他是否爱了别人,把别人当另一个自我来爱。把别人当另一个自我来爱,是教会之爱的特点,[1]225-226这样的爱不是占有和支配,而是享有。[3]37-38因为每个人爱自己都是因为享有他自己,而不是要支配他自身。同样,当一个人和一个教会把另一个人和教会当作另一个自我时,他也是在享有他们。享有他们,把他们当作另一个自我的,这样的教会的爱乃是流动不息的爱,是能够不断成长为教会的爱,他真正地视世界为客旅。
教会成为世上的客旅,是因为它为它所承担的爱而一味流浪。它的流浪则使爱流转,要使身外之身越来越能够扩展。所有这些都是基于福音的理解。既然教会是一种福音,它就是一个动词,一种活动,一种行为。教会作为动词,他表现为流转,越流转也就越复数。爱自己很重要,然而知道爱他人如同另一个自我,这就是爱流转的奥秘。天上之城的公民就是这流转之爱的公民,他们承载了爱,也流转了爱。因为在爱里面有真正的关切和平等,因为这样的人他们都爱了天上的福祉。教会把这样的一种爱流转,使得共有或者共同分有这种爱的人,有共同的法度。[3]48这种共同的法度使他们成为共同体,因着共同体他们共有身份,就是上帝之城的公民身份。这一切都是因福音的缘故,因为把他人当作自我来爱就是爱身上的福音,是福音使得诸自我都载有爱并且成为爱的表达。当教会成为爱的表达时,福音就是教会的奥秘。作为天上共和之城的教会,真正实现了地上之城的理想并且超出了它们,因为地上之城的共和政体也是为了永久的和平,是为了在共同的法权下享有幸福的生活。然而只有在天上之城里面,只有在公民身份完全实现的情况下,才可能拥有幸福的生活。[1]86,267-269幸福的生活乃是共同体永久和平的法权,是这种法权里面公民意识的充分彰显。
教会成为教会,其所根基的唯一权柄是福音,[1]229-230福音的本质则在于重建爱的法度。[1]225-226在新的爱的法度里面,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的自我,就犹如奥古斯丁所说的千眼的基督,他们也是千眼的人,因为每个人看见许多个自我的他者都作为他的自我被爱着,爱再也没有遮蔽。这是福音神秘之所。福音的神秘不是神秘主义者的神秘,而是灵修者的神秘。爱没有因着诸多的自我而减少,而是因着愈多的自我而增多。这就是爱的复数,也是爱何以是爱的共同体并成为共同体联结的原因。因此,爱就是奥古斯丁所说的曾经被地上之城遗失的希伯来语,[1]290-291爱是上帝的话语。所谓的生活在上帝之城中的,生活在作为上帝之城的教会中的,就是传讲着上帝的话语并在上帝的话语中成为流转上帝的话语的人。教会使经历福音的人按着新的法度随着历史流转,使地上之城的人们得见上帝之城,使地上之城的公民得见天上之城公民的形象。教会不放弃对地上之城的责任,教会不放弃它在历史中的责任,因为这是上帝在历史中作为的主要目的,不放弃上帝的话语流转于地上之城。[1]271-272教会在历史之中正是上帝在历史之中的持续进程,他要把上帝的国度带给地上之城,要让福音成为地上之城的轮廓。
参考文献:
[1]奥古斯丁.上帝之城[M].吴飞,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2]奥古斯丁.忏悔录[M].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3]奥古斯丁.论基督教教义[M]// 奥古斯丁.论灵魂及其起源.石敏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陶舒亚)
On the Idea of Church History of Augustine inTheCityofGod
SHI Min-min
(SchoolofMarxismStudies,ZhejiangGongshangUniversity,Hongzhou310018,China)
Abstract:In his The City of God vol. 15 and 16, Augustine discussed the idea of “the Son of Resurrection”, expou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ope to pray in the name of God’ and the doctrine of Church, and discoursing the meaning of Church as a stay of the city on the earth. This assay indicates the evangelical nature of the church in the view of 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Augustine, namely church being the flowing Tent of love. Augustine further expressed this evangelical love as the responsibility of citizens, warning the church not only against the relationship of itself and the world power, but also against the limit of interference the heaven power in the world power in the name of God. Augustine explained the historic nature of “God for us” according to his understanding of church from the view of gospel.
Key words:Church; flowing Tent; “God for us”; Citizen
中图分类号:B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5)01-0033-08
作者简介:石敏敏,女,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西方哲学史和基督教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希腊化和中世纪早期的哲学主流研究”(10BZX046)
收稿日期:2014-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