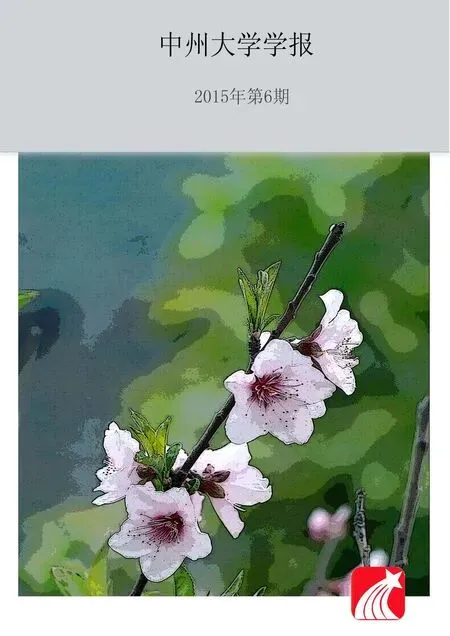灰暗的突围
——读墨白长篇小说《欲望》
魏华莹
(郑州大学 文学院,郑州 450001)
灰暗的突围
——读墨白长篇小说《欲望》
魏华莹
(郑州大学 文学院,郑州 450001)
墨白的长篇小说《欲望》,将欲望叙事与近三十年的时代背景紧紧缠绕。解读这部作品,剖析作者如何呈现一代人的欲望,不仅可以发现作者对人生、人性的总体反思,对于一代人的成长史、精神史也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欲望》;断裂;突围
2013年,墨白的长篇小说《欲望》出版。这部57万字的作品,故事时间跨越30年,被分为红卷、黄卷、蓝卷,讲述谭渔、吴西玉、黄秋雨三个同年同月同日生且为同乡同学的人生故事。设定这样的巧合,是为了从不同角度阐释同一背景的人如何“沉溺”于欲望的汪洋大海。诚如作者在后记中讲述,“对权力的欲望,对肉体的欲望,对生存的欲望,欲望像洪水一样冲击着我们,欲望的海洋淹没了人间无数的生命,有的人直到被欲望窒息的那一刻,自我和独立精神都没有觉醒”。欲望书写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重章华彩,也许是因为“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存在价值”[1]171。从《废都》到《我爱美元》《私人生活》《一个人的战争》,对本能的欲望书写成为摆脱意识形态压抑后重要的文学现象,也留下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横断面作品。墨白耗费二十年心力,将欲望叙事与三十年的时代背景紧紧缠绕。解读这部作品,去剖析作者如何呈现一代人的欲望,不仅可以发现作者对人生、人性的总体反思,对于一代人的成长史、精神史也会有重要的意义。
一、进城故事
在访谈中,墨白多次提到自己是属于“90年代”的,这和他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大量的文学作品有关,也和个人的生活轨迹转变有关。《欲望》的书写同样始于20世纪90年代,故事开篇,就讲述小学教师谭渔在1992年春天结束了34年的乡村生活,进入了城市。
谭渔立在城市繁华的街道边,城市的五光十色使他眼花缭乱,他站在街道旁,如同一个旁观者。一辆接一辆小轿车从他身边飞箭一般穿过,粉绿色淡黄色的高层建筑在阳光下依次立在街道的两旁。许多衣着漂亮入时的女郎和潇洒的男士骑着摩托车或者轻便车如水一样在阳光里流动。这一切都使谭渔感到亲切,这使他想起了颍河镇。那座肮脏的小镇在他的记忆里突然变得是那样地猥琐,在城市的眼睛里那小镇如同一个身穿旧棉袄蹲在阳光里取暖的老农。是有点像老农。谭渔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现在也是城里人了![2]96
“进城”故事在当代文学中一直是个重要话题,从《陈奂生上城》到“高加林进城”(《人生》)。在长期的城乡二元对立结构中,进城也成为一代乡村青年“奋斗”的目标及摆脱贫困生活和“耻辱”身份的象征。谭渔的进城,使我们不得不想到作者墨白,想到他的人生在这一年发生的重要转变——1992年,墨白从工作了11年的颍河镇小学调入周口市文联《颍河》杂志编辑部,此前,是长久的贫困孤独的乡村生活。
1976年的春天,我高中没毕业就外出独自谋生。在我出外流浪的几年时间里,我当过火车站里的装卸工,做过漆匠,上山打石头,烧过石灰,被人当成盲流关押起来。那个时候我身上长满了黄水疮,头发纷乱,皮肤肮脏,穿着破烂的衣服,常常寄人篱下,在别人审视的目光里生活。我师范毕业后,又回到了那个偏僻的小镇,在那个只有十个班级的小学里我一待就是十一年。[3]4
青少年时期的穷困,小镇生活的孤寂,以及不言放弃的心灵,谭渔(墨白)凭借自己的努力奋斗,终于从颍河镇来到城市,心中难免欣慰。对于谭渔,抑或对于墨白,他们是通过“写作”走入城市,惟有写作和文学能带来自信,然而,“进城”之后的故事却已然不是理想中的情节。谭渔面对城市建筑的挤压时,是靠手中的《莽原》杂志(刊载了他的一部中篇小说)得到勇气和自信。当他一手提着挎包,一手拿着发表自己文章的《莽原》杂志,进入文学编辑部时,却发现自己的时间和现实的时间已经错位,外部世界已经悄然发生改变。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时代激情早已经烟消云散。在偏僻的乡镇小学,谭渔还能和志同道合的同事结成“诗社”,互相交流习作心得。然而,当他真正走入文学的“中心”——编辑部,却发现文学已不如他想象的那般神圣。编辑部里的同事忙着四处挣钱,“这个社会没钱不中!没钱你就活得寒碜,没钱你就进不了国王大酒店!”这样的话使他感到吃惊,因为被自己崇高的文学理想所鼓噪,他不认为自己活得有多苦,仍然认为世上再也没有比搞文学创作更有意义的了。
昔日辉煌的文学杂志纷纷改刊,谭渔素来钦佩的编辑汪洋忙于组织中学生爱情诗大奖赛,寻求市场和发行量去赚钱,因为其所供职的内部刊物,“全靠政府给的这点事业费,就这点事业费,明年给不给还是个谜,现在不正提倡断奶吗?”谭渔无话可说,心中突然生出一种伤感来。对他来说,“文学就是他走进城市的精神支柱”,[2]86但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那个曾经惊涛骇浪的文学大潮,那景象、劲势、气概、精髓,都已经无影无踪,魂儿没了,连那种‘感觉’也找不到了”[4]。
20世纪80年代是属于文学的年代,是被许多文人知识分子所留恋的“中国的浪漫时代”。据诗人徐敬亚称,到1986年他策划“现代诗群体大展”时,全国光诗社就有2000多家,“自谓诗人”百十倍于此数。校园之外,人们对文学也是热度不减。由建筑工人北岛、待业青年顾城、纺织女工舒婷等人支撑的油印本民间文学刊物《今天》,在校园内外都受到追捧。[5]在墨白供职的偏远乡镇小学校园里也有着温暖的“诗社”:
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正是新时期诗歌的繁荣时代,大批的民间诗歌团体纷纷在诗歌报刊上亮相,十分壮观。那个时候我们小学的几个青年老师也成立了一个文学团,叫“南地文学社”,而我们当时主要是进行诗歌创作。那个时候我们不但订了大量的文学刊物,比如《收获》《十月》《人民文学》《世界文学》《外国文学》《苏联文学》《文艺报》,那个时候的《文艺报》还是以刊物的形式出刊的,同时我们还订了许多诗歌刊物:《诗刊》《星星诗刊》《诗歌报》《诗选刊》等等。所以我对新时期的诗歌进程是十分熟悉的,而且我本人也写诗,我自己有两本手抄本诗集,装订得像正式出版的书籍一样,从封面到版式都是我自己设计的。[6]87
“现代社会不是由相互层叠、边界清晰的群体构成,而是由同时具有多角色、多参照标的个体组成。根据社会条件和历史情境,他们根据自身个体或集体的以往经历来选择参照和身份认同的不同形式。”[7]3当谭渔或墨白拿着《莽原》杂志进入城市之后,却发现文学的无力以及金钱的吞噬力量。作品中,谭渔一次次重返锦城,寻找过去的记忆,当文学的支柱坍塌之后,在编辑部(城市)找不到认同的他只有退守到自我的小小空间。所以在小说中,我们才会看到谭渔一直在拒绝“时间”。
他每天就在这间没有阳光的屋里翻开作者的来稿,给作者回信,画版,读校样,接待业余作者,空闲下来的时候他就读点书,读点新到的期刊,读点报纸。到了夜间,他又要构思自己的小说,用力爬格子。他屋里没有电视,没有录音机,没有收音机,甚至连一个闹钟也没有,在这里他几乎丧失了时间的概念,他几乎成了一台机器,在城市里一个极小的空间里生存着。“我多像一只鸟呀,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这种想象又一次把他拉进现实里,孤独感再次袭来。[2]117
我们可以看到《欲望》故事的游离。红卷中谭渔的故事是以时间为概念界定的,如1993年元月8日、1995年12月3日、1996年11月6日、1992年春天、1998年深秋。此后的黄卷、蓝卷就变成了人物和空间,时间已然消退。当看到谭渔试图用理想主义来对抗世俗,孤独地在文学的小道上挣扎,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墨白一再强调重回颍河镇,去绘制自己的文学地图,“人们面对如此众多的他人,而这些人都是陌生者,他必须越来越退守到自身当中以便能够应付得来,这种从他者处退缩就像一只蜗牛缩回到自己的壳里。”[8]73也许,这种撕裂感不仅仅属于墨白,它也属于阎连科,属于余华,属于那样一代离开精神故土从而在文学故事中追忆的写作者。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阎连科重返“耙耧山脉”的努力以及余华与北京的重重隔阂。所以墨白才会说:“我是一个游离于主流之外的写作者。由于我的生活经历,在我言说个人的时候同时去言说现实是身不由已的事,那是我骨子里散发出来的一种气味,我无法改变。我是以个人的言说来辐射现实的。”[6]36
二、断裂之后
不管怎样,随着20世纪90年代城市化进程,进城故事的绵延越来越广。“1985——1990年只有1.5℅的农村人口转移出去。”[9]4“1990年我国城市只有467个,而到1995年则增加到640个,1999年更达到668个,城市以每年几十个的惊人速度在增长着,而我国城市人口从1990年的1.1825亿增加到1999年的2.3亿。”[10]这一时期,进城故事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转换,也意味着历史时间的断裂。之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延续已久的“超稳定结构”,20世纪90年代以来,却是一个迅速“断裂”的社会。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夹缝中的人:一方面是难以融入的城市,一方面却是无法回归的乡土。一定程度上,进城也意味着和之前的人生经验告别,谭渔离乡之后,虽然有对城市不尽人意的不满,却发现自己和乡村的迅速隔膜:
现在,呈现在他面前的颍河镇小学是那样的破烂不堪,我在这样的学校里一住就是十一年吗?他仿佛看到自己昔日的身影在这所学校里走动。可我以前怎么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他面前的两间西厢房同样是那么寒碜,土墙壁破木门,我就是在这样的房子里一住十一年吗?门开了,儿子朝他扑过来,他把儿子搂在怀里,妻子立在他的面前,妻子突然间显得是那样的苍老,妻子抚摸他的手是那样的干燥,这就是和我一块生活了十年为他生儿育女的女人吗?[2]123
与此同时,却是城市经验的匮乏,多年以来,谭渔一直生活在偏僻的乡下,他从来没有过和一个陌生女人在夜间一同走路的经历,这种情景的出现使他有些心慌意乱。
谭渔的心突突地跳几下,他有些紧张。他从来没有进过这样的餐馆,以往他曾经参加过几次外地的笔会,也算见过世面,可那都是现成的,人家上什么他就跟着文友们吃什么,他光知道好吃,却连一个新鲜别致的菜名都叫不上来,他看着文友用筷子点着新上的菜说这是什么什么,他只有汗颜的份儿。现在他一瞅菜谱,那些菜的价钱让他暗暗地吃了一惊,这一顿饭起码要花去二三十块钱,二三十块钱都快顶住他家半个月的伙食费了,他有些后悔,今天真不应该跟着她出来吃饭。[2]105-106
虽然进城之前,有挣钱扬名的豪情壮志,但与城市女人叶秋交往中的不知所措,与商人方圣、李文国惨败的“下海经历”,都使得谭渔无法找到方向,他不得不感慨,“咱没有根,咱的根还在乡下”,“他终于明白,城市的河流仍旧在拒绝他,他们把我们当成一滴油,我只能是一滴油,只能永远地在水面上漂浮,尽管在阳光下他做出了许多美丽的图案,但那条河流却不愿容纳他”[2]119。谭渔“明白这城市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迷宫,他知道他没法走通这个迷宫,我一个文弱书生一个从乡间赶来的农民的后代,在这座迷宫里最终将被折磨得筋疲力尽”[2]111。他只有左右摇摆,随波逐流,迷失自我。
这一时期,随着“进城故事”的延续,发生断裂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时空,更有着社会时间的断裂。相较于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宏大叙事,作品与时代同构,20世纪90年代文学更加关注自我,使得欲望书写以更加合理化的方法进行。以1993年《废都》为标界,冲破种种障碍,写出知识分子的压抑和突围,受到“严肃”批评,随之而来的,却是欲望书写的步步张扬。女性写作者林白、陈染、卫慧、棉棉等更是将欲望写作推向极致化的境地。“这批作家的生存环境和人生体验,决定了她们更多地感受并接纳了当下物质主义的社会时尚与后现代的文化氛围。体现于她们的作品中,不仅性爱欲望的隐秘性和羞耻感已不复存在,而且情爱欲望的书写也不再作为反抗某种观念意识的手段,直接地就构成一种目的,一种不需要意义、仅仅是单纯的肉体快乐而已。”[11]虽然在当时,因写作的大胆暴露而广受批评,但对个体自我的关注以及人性的挖掘更加绵密深入。20世纪90年代的欲望化小说写作“成功地扭转了小说创作中长期硬化成结的国家话语,使国家话语转向个人话语,使代神代政代集团立言,走向代自我立言,从而阻死了那种代历史、群体的名义强加他人的思想之上,并进而为思想控制留下空间的做法。”[12]75
墨白更为关注人心、人性的幽暗之处,如他所言,“我们所有有着乡村背景的人,来到城市,做人的尊严都会受到挑战。在过去的城乡二元对立的国策里,农民失去了作为人应有的尊重和尊严,多年的不公形成了他们自卑的心理。现在他们来到了城里,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他们会感到无所适从。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这么多的农民离开自己的家乡和土地,这个社会是一个动荡的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心理混乱。这个心理混乱,一方面是由于生存的困境带来的,另一方面是由精神的困惑所带来的”[6]32。对于墨白来说,“城市就是在这样的欲望之中无休止地膨胀着,空气中充满了铜臭的气味,但又是那样的冰冷,那样的缺少情感”。“冰冷”也许是我们理解其写作的关键词,那就是无法找到温暖的力量。作品中,谭渔和“红颜”叶秋的交往是少有的温情细节,如叶秋品读他的作品,为他举办的文学座谈会。
在后来的许多日子里,那次有关文学座谈会上的许多细节都被谭渔淡忘了……那天他们一起走出那幢教学楼的时候,叶秋激动地对他说,讲得好,讲得太好了。……叶秋说话的声音化成了一支曲子时常在我的感觉里响起来。在他们分别握手时,谭渔在夜色里拉住叶秋的手,他用了一下力,又用了一下力。那只手仿佛已经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种情感,一种情感的相互传递,这是那天晚上留给谭渔最深的印象。[2]121
但叶秋的身份是城市女人,她虽然被设定为一个不世俗的女人,曾因看不上丈夫的铜臭气而离婚,却有着现代城市的认同法则,她又会这样教育谭渔:“看来只有你这样傻了,你知道现在是啥年代?谁还这样一心一意地做学问?你看人家都在干啥,都在捞钱。”“你想成为大家,就得砍断你的根,你应该远走高飞,你身上的包袱太重了!”心灵之友也是如此的认知逻辑,谭渔唯有以写诗表达自己的孤独,却又发现“没有文字能表达我的忧伤”,终于沉溺于欲望。作品中,越来越多的人在欲望中迷失,有金钱欲(汪洋、钱大用、谭渔)、名利欲(吴天夫、吴西玉)、爱欲(谭渔、小慧、小红、尹琳、吴西玉、五仙女、黄秋雨、米慧等)、表现欲(钱大用)、倾诉欲(赵静、尹琳),尤其是爱欲,更是得到极致书写。
“提高社会等级的欲望的受挫,不仅意味着必须放弃提高生活水平的希望,而且还意味着社会尊重也遭到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自尊的丧失。……拉斯威尔已经证明,一旦‘成功的自我’以前的理想被搅乱以及以前的态度被弄得无目的,旧的冲动便向内转化,并采取自我惩罚形式,从而退化为受虐狂的,或心理上自我毁坏的放荡。”[13]84于是,谭渔和妻子离婚,在情人叶秋之外,他还在小慧、小红的诱惑中自我放纵,甚至自己都发生质疑,“是什么驱使我来这里呢?是爱情吗?我都快四十岁的人了,我为什么还会这样呢?我是一个灵魂肮脏的人吗?”墨白在作品后记中刻意表达:“人的尊严是我写作《欲望》时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断裂之后如何重建自我,如何寻找突围之路,是墨白小说更为关注的内容。
三、突围的可能
众所周知,墨白是学习绘画出身,对色彩有着更为深刻的认知,作品也分为红、黄、蓝三卷。我们记得闻一多那首诗歌《色彩》:“生命是张没价值的白纸,自从绿给了我发展,红给了我情热,黄教我以忠义,蓝教我以高洁,粉红赐我以希望,灰白赠我以悲哀;再完成这帧彩图,黑还要加我以死。从此以后,我便溺爱于我的生命,因为我爱他的色彩。”墨白在《欲望》中以三原色为主轴,调出形形色色的欲望。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每部小说都在告诉读者:“事情要比你想象的复杂。”[14]20种种欲望和放纵不仅没有改善烦恼人生,反而加速自我毁灭,在墨白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欲望导致的悲伤以及死亡:锦的姥姥死去、锦的自杀、锦的儿子小渔的死、汪炳贵的死、车祸撞死的女人、季春雨父亲的死、季春雨杀人及被抓、涂文庆强奸杀人、于天夫死于癌症、七仙女的儿子被绑架杀害、七仙女的疯和死、吴西玉的车祸、黄秋雨死于谋杀以及栗楠因车祸成为植物人等。还有形形色色的离婚与背叛:雷秀梅的夫妻争吵、小慧父母闹离婚、谭渔离婚、陈浩的离婚、叶秋离婚、汪洋离婚;吴西玉与尹琳的婚外情、牛文藻母亲的性丑闻、杨景环闹离婚、陈仙芝闹离婚,以及林林总总的疯狂,如锦的疯、七仙女的疯、牛文藻的疯狂行为等等。
这种无关善恶,没有明确道德指向的压抑性叙事方式也被有的研究者视为“零度写作”,但这又无法涵盖墨白对人生、对时代的发问,对历史的反思。在作品中,他会让小慧来质问谭渔:“什么东西能代表我们的这个时代呢?”在关于历史的叙述中,又有意植入各种历史事件,如刘少奇的死、大跃进造成的信阳事件、艾滋病的泛滥、新疆的阿拉木图、遇罗克的《出身论》、纪念碑的坍塌等等,那些被植入的宏大历史与无法命名的琐碎欲望形成鲜明对比。尽管三部曲以明亮的红、黄、蓝开卷,作品的底色、基调总是灰暗、阴晦的,每个人都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只能在欲望中毁灭。
作家总是“讲故事的人”,不管他用何种方式。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30年中国故事在作家笔下并没有得到有效重建,也有批评家将其称为“介入现实的乏力”,尽管有各种因素,但对社会缺乏同构性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余华才会说出“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阎连科才讲到“现实的荒诞正在和作家的想象力赛跑”。跳跃性发展的社会形态也给更多的人带来不适之感,作家的自我人生都是断裂的,如何来表达多种复杂经验成为令人困惑的命题。这使我们不得不想到墨白,面临着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转型,当众多的先锋作家经过市场规训和自我调适重回现实主义的写作旅程中,墨白却坚守先锋写作,用梦幻、记忆来建构自己的文学世界。“孤独”一直是《欲望》三部曲中挥之不去的话题。墨白和同代人莫言、阎连科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是饥饿生存所带来的没有尊严,家庭成员的“历史问题”所带来的种种挫折,却最有责任意识的一代,因为他们的出生、成长是和共和国同构的,即便是被誉为“海派传人”,最擅长城市书写的王安忆,也自我强调是“共和国的女儿”,所以,他们的故事总是带着极强的社会意识。从这个角度,我们或许可以找到墨白在欲望化城市中,试图以“颍河镇”作为根据地,重建“精神原乡”的努力。
从1980年的9月到1991年的12月,整整十一年零三个月,这段时光我是在故乡的小学里度过的。……现在夏季的太阳还没有升起,城市如林的楼房如海的绿色树冠已经开始增长气温,楼下穿梭般的汽车和远处倾吐灰烟的烟囱,使我感觉到我离那段宁静的乡间生活越来越远了,我怎样才能在这个崇拜金钱和权势的社会里,抵达那段生活清贫而精神富足的时光的腹部呢?[15]79
在这里,作者将外部世界诠释为金钱和权势,而试图抵达理想的内心,生活清贫而精神富足。现代化、城市化既是社会进步,也是资本逻辑、财富逻辑、发展逻辑、理性逻辑的同步建构。对于墨白来说,“文学的问题首先应该是心灵的自省和自救”[16]416。在作品中,灰暗、坚硬、冰冷的城市被欲望、恐惧包裹,只有遥远的故乡是温暖的腹地、理想的所在。因此,作者通过梦境、幻想和记忆来寻找精神自足的力量。“真正的艺术作品,我们时代的真正的先锋派,完全不遮掩艺术与现实之间的这种疏远,完全不减弱两者之间的差异而是扩大差异,并且强化它们自己同所给予的现实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其强化的程度达到使艺术不能有任何(行为上)应用的地步。它们以这一方式履行了艺术的认识功能,……让人类面对那些他们所背叛了的梦想和他们所忘却了的罪恶。”[17]255
所以,他才会用庞大而驳杂的《欲望》三部曲来诠释自己的写作理念,在城市欲望巨大的吞噬力中,谭渔从《裸奔的年代》中的主角,失去乡土身份却难以融入城市的挣扎者,到《欲望与恐惧》中的看客,再到《别人的房间》中黄秋雨的故事揭秘者,通过立体交叉的方式建构一代人的生存困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给一代人带来极大的精神不适,也许是怀恋20世纪80年代的理想主义和人文情感,也许是精神世界坍塌之后重建努力的种种失效,也许是荒诞、碎片化的现实难以言说,导致介入现实的困难。即便在正面直击的作品,如阎连科的《炸裂志》,也以“神实主义”的方式自我命名。《欲望》如何来表达这个时代,作品并不明晰,那不断穿插、跳跃的历史,那灰暗、晦涩的梦境,都在有意模糊我们的阅读视野,但一个个灰暗的欲望故事却也暗合了作者对欲望的理解。从谭渔的精神坍塌,到吴西玉的不知所终,再到黄秋雨的死于非命,都是一个个黯然神伤、悲惨无比的欲望故事。在这个意义上,墨白是有自省能力的作家,他不仅仅囿于讲故事,而是试图以梦幻、记忆等多种方式将个体痛苦和时代痛苦的盖子揭开,对他来说,“一个作家要有勇气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面对自身痛苦的根源,并不断地进行自我的解剖”“我理解的写作应该是这样的:无论世风怎样变化,无论在任何情景下,他们独立的人格都不会被权势所奴役,他们自由的灵魂都不会被金钱所污染,那是因为他们的写作是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是对自己行为的忏悔与反省,他们对媚俗的反抗、对社会病态的揭示、对人间苦难和弱者的同情、对人类精神痛苦与道德焦虑的关注等等,这些因素构成了他们的姿态。”所以,他让人物一遍遍地重访、回到故地,也许对于墨白来说,颍河镇更多地是一种心灵原乡,一种精神富足的灵魂栖息地。那些压抑性叙事所呈现的痛苦尽管隐秘,但努力打开它,使我们认识到内心的幽暗,使我们不囿于欲望的侵袭,来寻找内心深处的纯净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尽管种种突围是灰暗的,但其借喻的世界却是明亮和多彩斑斓的。
[1]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
[2]墨白.欲望[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
[3]林舟.以梦境颠覆现实:墨白书面访谈录[C]//刘海燕,编.墨白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
[4]冯骥才.一个时代结束了[J].文学自由谈,1993(3).
[5]欧钦平.文学远离80年代盛况之后[N].北京:京华时报,2011-03-29.
[6]墨白.小说的多维镜像[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
[7]〔法〕格罗塞.身份认同的困境[M].王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8]〔英〕英格斯.文化与日常生活[M].周书亚,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9]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0]薛小和.城市化道路怎么走[N].北京:经济日报,2000-05-19.
[11]管宁.转型社会语境下的欲望书写与美感形态:对20世纪90年代小说创作一个侧面的考察[J].南京社会科学,2001(12).
[12]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13]〔德〕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研究[M].张旅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14]〔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15]墨白.鸟与梦飞行[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
[16]墨白.梦境、幻想与记忆[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
[17]〔美〕马尔库塞.艺术作为现实的形式[M]//董学文,荣伟,编.现代美学新维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 许峻)
The Dark Breakout ——Thoughts onDesireby Mo Bai
WEI Hua-yi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 China)
Mo Bai’s novelDesireintertwines the desire narration and the past thirty years closely. Interpretation of this book and analysis of the author’s presentation of people’s desire can not only help to find the author’s overall reflection of human nature, but also have positive significance in realizing one generation’s growth and spiritual history.
Desire; fracture; breakout
2015-10-13
2015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990年代‘文学事件’研究”(CWX012)
魏华莹(1981—),女,河南郑州人,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5.06.011
I207.42
A
1008-3715(2015)06-0054-06
编者按:作家墨白是当代优秀的先锋作家之一,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通过跨文体写作进行文体革新实验,并坚守对人性的复杂性、历史问题和现实苦难的反思,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探讨上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高度。今天仍有必要重提立足于反思现实和人性的先锋精神,以建构良好的人文精神生态。本期特设专栏,集中阐释墨白小说的精神引领意义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