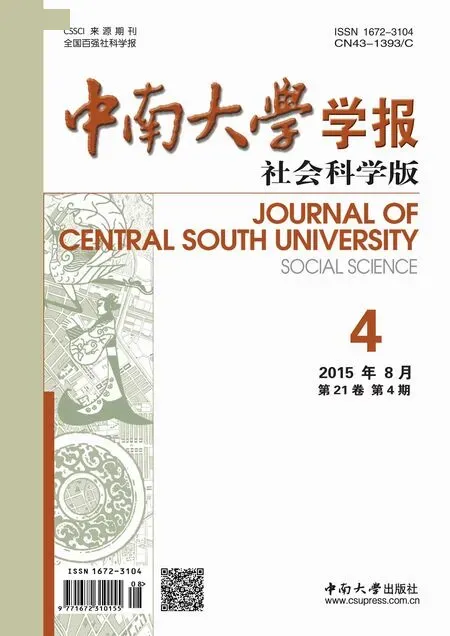影像的民族化:费穆戏曲电影的美学再审视
杨紫轩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3)
影像的民族化:费穆戏曲电影的美学再审视
杨紫轩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3)
在中国电影发展历史中,导演费穆对中国戏曲电影化以及中国电影民族化进程有着突出的贡献。他通过蒙太奇、镜头变换、电影美工、场面调度等一系列手段实现影像表达,将戏曲和电影这两种不同形态的艺术相融合。把古典戏曲中国人对美的追求有选择地保留在电影当中,借用电影媒介创作出独特的富有中国韵味的戏曲电影。
费穆;戏曲电影;民族化;意境美
费穆在早期电影史中被冠以“电影诗人”的称号,是中国电影民族化进程中一位不可忽视的导演。他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同时受到欧洲文化的影响,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使他的影像与同时期其他导演存在异质性。费穆的影片总是透露出学者式的哲理思考,有评论认为费穆影片“风格另成一派”,细腻柔和中“往往哲学气味太深”[1]。费穆的故事片富有哲学气息,具有鲜明的个人烙印和独特的人文情怀,充满着深层的文化内涵。《人生》(1934)、《香雪海》(1934)和《天伦》(1935)这几部电影的精神内核都暗藏费穆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无限眷恋,它们的外在形式都体现了费穆对电影表现技巧和风格的探索,有评论称他的电影“镜头角度和画面构图极有修养”[2]。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费穆在短暂的一生中还拍摄了很多戏曲电影,风格上更加贴近中国传统美学。《斩经堂》(1937)、《古中国之歌》(1941)、《生死恨》(1947)等戏曲电影的拍摄成为他进行美学探索的试验地,他不断地探索将写实的电影与写意的戏曲统一起来。故事片《小城之春》(1948)是早期中国电影民族化最为成功的一部作品,它的成熟体现在运用镜头融合传统美学对于“写意”的表达,熟练结合电影拍摄技巧对中国古典美进行深度阐释。费穆先前的戏曲电影实践无疑对《小城之春》的美学形态产生过关联性影响,所以绕开戏曲电影讨论影像民族化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费穆众多的戏曲电影实践中并不都是成功的,其中《斩经堂》《古中国之歌》都被其认为是失败作品,只有《生死恨》是费穆进行影像民族化实践过程中较为成功的一部作品,也是集中体现费穆电影美学的重要作品,被誉为“在旧中国戏曲电影的探索实践中,成就最高的电影之一”[3]。《生死恨》的舞台剧本是齐如山依据明传奇《易鞋记》改编的,故事发生在金兵南下的北宋时期,一对才子佳人被掳边疆、面临国仇家恨的生死别离故事。舞台剧上演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后,为了警醒当时民众亡国的悲惨命运,唤醒苟且偷生的国人奋起反抗,主创人员在剧本中投入了浓烈的家国情怀。20世纪三四十年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促成费穆采用迂回的方式,召唤个体生命投入到民族国家的抗战中,国仇家恨、民族危机的历史背景促使费穆试图走出一条不同的电影道路。反观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电影,面对西方电影的强势入侵略显疲态,在世界舞台上寻找不到自我定位,费穆的实践对中国电影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民族电影依托传统文化迅速寻找到支点,无疑成为跨出国门的关键性因素,重新审视费穆戏曲电影不仅具有史学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一、戏曲之美与电影之美
任海暄在《戏曲对中国电影艺术形式的影响》一文中将费穆的戏曲电影视作实验电影,认为费穆的实验性体现在虚与实的表达、运动镜头的抽象美和写意性的时空。他论述的三个方面都没有涉及对电影和戏曲本性的探讨,对于两种艺术的差异性也没有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故本文试对戏曲电影美学从表象到本质进行剖析。戏曲美在现实和想象的一念之间,“优孟衣冠,原非实事,妙在隐隐躍躍之间。”[4]戏曲就是 “歌舞”手段加上“写意”方法,重视抽象的意识而不是物质现实。“虚拟”是舞台表达对象的普遍做法,因为虚设性、片段性和临时性,戏曲舞台不可能从外观上“如实”地再现生活对象,也无法表达事物的连贯性和各方面的真实性。费穆认为中国剧的歌唱、说白、动作与戏剧的表现方法,完全包括在程式化的歌舞范畴之中,演员皆非现实之人,观众必须处于迷离状态之中。[5]戏曲中演员不是真实的人而是可供欣赏的艺术品,脸谱、髯口、翎子都是艺术表现手法而非现实之物。虚拟还使创作者不再模拟外部事物,而是通过表演从内心刻画人物,由此带来更深层的审美意味。刘海粟曾评价梅兰芳在《打渔杀家》中的戏曲表演:和西方的戏剧表演相比不能认为“如实”就好,“虚拟”一定不好。刘海粟一语道出在戏曲改良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因为当时在改良过程中创作者往往追求简单化、表面化的真实,这样反而会弄巧成拙。虚拟对于表达对象的原型来说正是“离形得似”,这不是为了模仿表面的真实,而是能够运用各种独特的手段表达人物内心的真实,中国戏曲独有的表达方式是擅长表现而非写实,这正是中国艺术中写意精神的一种重要体现。
吉夫·皮克在对比戏剧和电影的异同时得出这样的结论:“戏剧趋向特殊的、具体的而向一般的、抽象的思想发展。相比之下,电影则倾向脱离一般而趋向特殊化。”[6]这就是说电影重视具象的事物而非抽象的概念和意图,它的媒介属性是真实的、连贯的。这样的观点符合电影纪实派的理论,但是世界电影史中始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电影本性观,其中以爱因汉姆和巴拉兹为代表的“造型派”,强调电影不是对客观现实的机械复制,而是表达与现实的差异。巴拉兹认为电影最大的特点是抒情性,它可以消除观赏者和作品之间的距离并弥合鸿沟。雨果·明斯特伯格认为客观的模样由心理兴趣决定。[7]很多导演就认为拍摄电影的实质是将心理影像变为物理影像,电影不仅是视觉艺术,更是表意艺术。电影的真实与否与观影者的主观内心相连接,而且电影艺术为观影者刻意制造的白日梦,让他们产生参与虚构剧情的时空当中的幻觉。肯定现实的影像是电影的本质基础,但更应强调电影的表意属性是意义和价值的基础。德国表现主义电影的特征是营造特殊效果,所有的布景都以非写实的、夸张的、非日常的形态出现。早在20世纪20年代,表现主义电影《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就已传入中国,这部电影对费穆的另一部故事片《春闺断梦》有形式上的影响。费穆预见到电影不只是客观现实的再现,将电影与戏曲相结合探索影像民族化的实践非常具有前瞻性。
二、费穆的影像民族化探索
关于费穆电影的讨论是随着中国电影走向世界而同步进行的,尤其到了21世纪,随着亚洲电影势力的崛起,中国电影也在寻找自己的民族影像特质,费穆的影像民族化探索给予了现代电影很多启示。电影民族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虚实的结合,要求导演将中国戏曲的特性与现代电影相融合,从脚本、镜头处理、声音处理、舞台布景甚至是灯光都进行相应的改变,最终达到影像民族化的电影美学追求。
(一)虚实结合的拍摄理念
多年以来关于戏曲电影的探索都没有超越费穆的想法,其中大多数均陷入一种狭隘的非此即彼的矛盾中。电影的表现手法是写实的,而“超现实”的戏曲融合进来绝非简单的拼贴,程式化的表演结合写实的电影势必削弱两者的特质,中国的戏曲电影无法像西方的歌舞剧一样拥有过多真实的场景和真实的物体,这使大多数艺术实践都因无法调和二者矛盾以失败告终。费穆认为早期拍摄的《古中国之歌》和《斩经堂》是两次失败的经历,这两次失败几乎让他丧失了拍摄戏曲电影的自信。《斩经堂》早已开始用电影的技术摄制京剧,也采用在“评剧的形式中间参用写实的手法”[8],实现戏曲和电影的交流,但早期创作过程中依然以旧剧为主。夏洛莫夫认为京剧的节奏、情绪的冲突远远超过时代冲突,这样难以调和的矛盾性使编导在拍摄过程中越来越倾向于纪录电影即“古装歌剧电影”[9]。《生死恨》是费穆戏曲电影的第三次实验,此后费穆的电影理念是依照戏曲美学建构的,利用戏曲中古典元素进行电影化的形式探索。香港学者黄爱玲认为,“戏曲电影只是将他所关心的命题放到一个更绝对的处境里去,迫使他更直接地面对中国艺术的特质。”[10]就本体论而言,费穆戏曲电影的属性是“电影的”而非“戏曲的”。其美学建立在西方电影的视听语法与中国传统美学的融合之上,而传统戏曲中“地方的”、非“普适性”、非“全球性”的表达方式正是费穆中西融合的基点。由于戏曲电影的特殊性和技术限制,费穆希望通过镜头处理和剪接使其尽量与平常电影接近。不同于商务印书馆早期的戏曲舞台纪录片,费穆的戏曲电影带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形式而非简单的舞台化影像呈现,利用戏曲“虚拟”建构属于中国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影视美学程式体系,探索中国戏曲影像表达形式。
韩尚义认为:“中国电影的初形态,便承袭了文明新戏的‘艺术’而出现。与其说是中国电影中文明戏的毒,毋宁说是受了文明戏的培植。如果数十年前没有文明戏,中国电影应该立刻向古装戏投降。”[11]在韩尚义看来,戏曲的形式严重排斥故事片写实的景。其实不然。写实派理论家克拉考尔在承认电影的两种倾向之间存在冲突的同时,也指出有大量事实足以证明支配电影手段的两个倾向可以通过各种方法结合起来。[12]布莱希特也承认即使舞台是写实的,也是一种幻觉。戏曲和电影的矛盾在于仅仅把电影的属性归结为单一的纪实性而忽略了电影的其他属性,矛盾的关键是把电影的写实绝对化。电影的特性是多面性的,戏曲的特性也是多面性的,而戏曲的写意性和电影的写实性又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戏曲艺术也是在真真假假之间,电影艺术也如此,二者都存在“实”和“虚”两个方面。在虚实结合的拍摄过程中费穆试图以创造剧中的“空气”为手段融合建构属于中华民族的电影艺术形式。在拍摄方法上他提出四点建议:①由于摄影本身的性能而获得;②由于摄影的目的物本身而获得;③由于旁敲侧击的方式而获得;④由于音响而获得。[13]方法一是取决于电影摄影影像的客观属性,方法二可以理解成对于电影造型性的人为主观性获取,可以看出费穆对待戏曲电影化的态度与西方电影理论造型派有相似之处。从时间上来看都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西方在同一时段提出并试图解决同一个问题,不同的是西方电影形成的两个派别逐渐分道扬镳,电影拍摄走出了纪实和造型两种风格。而以费穆为代表的中国电影艺术家竭力走出一条中国独有的“融合”之路。
(二)虚实结合的表演手段
梅兰芳很早就意识到民族形式的京剧舞台艺术已经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因为经济原因和社会进步,电影作为比较标准的演技纪录机械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所以通过电影媒介的有效传播可以让传统艺术漂洋过海影响到更多观众。这在费穆看来是多种因素共同造成戏曲电影化:“以中国人爱好‘京戏’的兴味之浓,旧戏电影化就有其商业的价值。”[5]费穆的这一席话点出了旧剧电影化背后的商业动机,基于这样的原因,旧戏电影化就显得十分必要。就本质讲,费穆戏曲电影的美学源于中国古典美学的现代化呈现,对表演的要求尤为明显。费穆对传统戏曲表演有自己的看法:“中国剧的生、旦、净、丑之动作、装扮,皆非现实之人。可以说是傀儡、像鬼怪;主观些,可以说是像古人、画中人;然而最终的目的是要求观众认识他们是现实的人。”[5]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从虚拟的人和事物中获得真实,费穆也从本质上把握了电影的表现方式是“绝对的写实”[14]。在关于费穆拍摄戏曲电影的研究当中,可以看出他将两者难以调和的矛盾归结为技术问题。程季华评价电影《生死恨》较之梅兰芳过去拍摄的戏曲影片在各个方面都有新的提高[14],费穆成功地把京剧这种包含了各种艺术形式的综合艺术体系通过电影全面展现出来。
由于电影接近写实,所以费穆要求梅兰芳、姜妙香上淡妆并配合贴片子和头上插戴。这样的创新结合了中西优势,通过蒙太奇组接的戏曲电影既秉承了中国的传统又有开拓创新。在影片开端先展现一个空镜头,由梅兰芳饰演的韩玉娘未见其人,先听其声。接着由空镜头配画外音,打破传统戏曲当中走板、叫板等程式化表演,反而通过电影影像语言来表达韩玉娘在山野之间躲避金兵的仓促感。通过导演和演员表演的配合,费穆让镜头语言和舞台化表演充分结合在一起。梅兰芳在拍摄过程中也体会到京剧特殊的“虚拟”表演方法导致从舞美、化妆到唱念做打都是写意的。“凡声皆歌,凡动必舞”的特性与电影写实特性在表演上产生的矛盾,表演方面采用的原则是以戏曲适应电影。
(三)电影运动镜头的意境美
现存残本《生死恨》可归属为纯粹的电影美学形式,也是视听语言的影像美学形式。阿恩海姆曾经说过:“视觉是选择性的。这种选择一是内容,二是影像的运动形式。”在摄影机的运动中费穆给戏曲表演中演员以造型,梅兰芳的手眼、身段、步法都是戏曲和电影两种艺术形式的结合。梅兰芳把表演归结为“最需要的是自然,最忌的是矜持”[15],而费穆镜头内部的场面调度使梅兰芳远离现实感。同时《生死恨》中镜头运动、场面调度、镜头节奏与音乐的结合恰到好处,运动镜头充满中国韵味,浑然一体好比一幅中国传统写意文人画。在“磨房”的独白段落中,较好地诠释了写意性,画面内是窗外皓月当空,而画外音是韩玉娘的演唱,紧接着剪切到韩玉娘直抒胸臆唱到“好不凄凉”。声音从画外到画内的转换,画面由皓月当空转换为韩玉娘的凄凉倩影,费穆通过蒙太奇创造出意境,完成时间向度与空间向度上的统一。
由于戏曲美学的特殊性,过多的剪辑会影响戏曲的艺术表达,所以在大多数场景中费穆采取“长镜头”和内部蒙太奇,从影像中可以看出费穆通过多使用“中景”“全景”,少采用“近景”“特写”,极力营造传统美学形态。“柴房”段落中韩玉娘和程鹏举的对话,并没有使用同一时期世界范围内最流行的过肩镜头而是巧妙地使用了摇镜头,很明显吸取了中国古典绘画中散点透视的美学技巧。导演试图让欣赏者的目光跟随主体物自由地移动,利用多元的视点避免观众在写实的舞台中陷入叙事的时空并丧失视听的乐趣。同样的手法在一年后的《小城之春》当中再次出现,而这次是为了展示三位主角的复杂人物关系,单就镜头使用技巧而言,《生死恨》为《小城之春》积累了重要实践经验。
(四)脚本增补与唱段简化的技术处理
《生死恨》从京剧脚本到电影剧本经历过大幅度删减,不论是台词还是场子方面都有分有并。为了使《生死恨》更加符合电影的制作规律,在改编过程中费穆极力主张将开头几场比较松散的场面进行删减,力求情节紧凑生动,台词精炼有感情。脚本从二十一场删减为十九场:序幕、被虏、磨房、逼配、洞房、拷打、诀别、潜逃、鬻婚、尼庵、夜遁、拜母、遣寻、夜诉、梦幻、遇寻、宋师、重圆、尾声。其中“被虏”是舞台本中没有的,在这一段落中韩玉娘仓皇出逃、中箭被俘有唱词有念白,增加“被虏”段落营造电影情节冲突,使电影拥有更真实的气氛,让戏曲电影更加符合电影的艺术规律。伏笔的手法常见于追求情节跌宕起伏的现代电影,为的是让电影更加吸引观众。据梅兰芳的回忆,“洞房”这场戏是根据原剧本的情节重新写的。费穆加入“番奴偷听”段落,这样便为后来的情节“番奴告密”埋下伏笔。修改最多的一场是“尼庵”,目的是激起观众对侵略者的愤慨情绪。舞台本中胡公子与老尼串通谋得韩玉娘被改成了胡公子与番奴勾结迫害韩玉娘,“夜遁”也改编成番奴迫害韩玉娘。第十四场“夜诉”和第十五场“梦幻”在舞台上本为一场,但是在费穆的改编过程中却拆分成了两场,虽然台词没有变动,但是艺术呈现效果却极大地变动了。戏曲中虚虚实实随意变换,但在电影中“夜诉”的现实性和“梦幻”的假定性,构成了一对矛盾而无法再用传统戏曲的方式来表达,所以费穆大胆将其拆成了两场戏。通过梦幻和现实的交融表达出个人理想与家国情怀的冲突。
费穆对戏曲电影的声音也进行了深入思考,相对于传统艺术造型美的继承性,费穆在声音处理上却大胆创新。费穆的高明之处在于在改编过程中有意缩减唱段,并将一些段落改为哑剧,还将很多唱词改为了念白。在“拷打”一段,张万户念[扑灯蛾]的牌子与舞台本极不相同,类似这样的处理方法均有利于电影的情节发展,削弱传统戏曲的抒情特性,使情节更加吸引观众。“尼庵”这场中数板被改为了对白,梅兰芳曾经对此提出过异议,但是费穆认为电影不适用自报家门的办法,所以不得不舍弃。由此可以看出费穆把戏曲舞台化中的台词作为重点修改对象,尤其是不符合电影纪实性规律的部分。在梅兰芳看来,费穆把很多戏曲中的场面都改成了哑剧而非京戏,“夜遁”一场就用哑剧的方式展现了韩玉娘逃出尼庵的过程。费穆同时认识到音乐是舞台艺术的必要条件,他采用整体配乐的方法,用音乐烘托气氛,或者用音乐加强舞台剧的节奏感。从戏曲到电影,费穆首先要把握电影影像的第一性,用画面讲故事而不是用言语。
(五)舞美写意性的追求
细读《生死恨》会发现它既不符合西方电影美学形式,也不符合中国美学形式。但以中国文化为视角,便可理解费穆拍摄影片是站在虚实结合的高度把握舞台空间和电影空间的。电影的画框不能成为叙述的局限因素,舞台空间也没有阻碍观众想象的翅膀。费穆尽可能地采用京剧的形式,他主张在舞美方面采用布景并且遵循几个原则:①不主张原封不动搬上银幕。②遵守京戏的规律,利用京戏的技巧,排成一部古装歌舞故事片。③对于京戏的无实物的虚拟动作,尽量避免。④希望在京戏的象征形式中,能够传达真实的情绪。[20]费穆在成片中摒弃传统戏曲“就简”的习惯改用实景布局,采用写实和写意两种形式,不仅有绘制背景还有各种道具。在拍摄中,费穆通过熟练的镜头运动、电影分镜头设计引导观众的视线,以“中景”“全景”追求“间离感”,削减电影的视觉认同的效能,观众更容易专注于演员生动的表演,布景的存在感即可被削弱,观众就在导演的规定中不由自主地注意到剧中的人物和细节,确信演员的力量。韩玉娘逃离尼姑庵的段落中,舞台上是唱流水板、走圆场,费穆认为圆场不适合电影表达,为了符合电影的需要,他还规定了行走的准确路线,在手绘的山水画背景前面布置了若干棵树,让梅兰芳围绕在这几棵树中间行走,这样的方式是借场景结构的调整完成视听品质的提升。再如“磨房”一段,背景上画着蓝天白云、树石草木,茅屋内摆放板凳、石磨、背篓作为装饰。 纺织“夜诉”是电影中的重要场面,唱工有二簧导板、摇板、慢板、原板、散板,但是原本舞台上只用了两件简单的道具。因为追求真实,电影天然排斥虚假,费穆反对电影中出现仿制品,于是道具组找来织布木机,并在桌上点燃一盏油灯营造真实的现场感,这个场景就变换为韩玉娘手摇纺车表演。在这一段中,场景的变化是感动因素的外在方式,费穆通过舞台化的“视像感”成就了浓烈的家国情怀。
基于对电影客观性的了解,费穆最终冲出写实的藩篱走向写意的高度,通过演员表演、服装造型、摄影运动、蒙太奇等方法,逐步研究出一套具有写意性的视听语言,并很好地解决了写实与写意的融合问题,所以,写意性的视听表现在电影中也相得益彰。费穆认为在创作过程中要做到:①制作者认清京戏是一种乐剧,用歌舞片的手法处理剧本;②尽量吸收京戏的表现方法让电影艺术有些新格调;③导演人心中常存一种是作中国画的创作心情。[16]巧合的是在《生死恨》拍摄过程中出现的瑕疵恰好成全费穆对中国画的创作。影片以彩色片为广告宣传,但拍摄过程中由于技术原因导致颜色失真,但一些观众认为“影片的色彩含有我国古瓷古画的意味”[16]。编导们的技术失误使《生死恨》的色彩展现出古典美,阴差阳错地让现代电影呈现出传统文人画的色彩。
三、结语
费穆的中国化导演风格不是表面化的模仿,而是渗透到文化精神层面上的融合。在他看来,拍摄中国电影应站在民族美学的高度之上对影像进行整体把握,“不能追求其他国家的风格,中国电影只能表现自己的民族风格”[23]。要想走出自己独特的电影之路,就应当从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用旧戏来孕育新戏,用旧戏曲培养新电影。在对民族性的充分自信和深刻认同的基础上,费穆通过蒙太奇、镜头变换、电影美工等一系列方法将电影诗化、抒情化,从而建构了中国电影的民族属性。他谙熟电影技巧并站在民族美学高度同时关照内容与形式,将电影的实感与戏曲的虚感相结合。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中国人越来越重视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呈现,在这一点上费穆的电影美学实践给予了中国电影深刻的启示。
[1] 林蜚. 影坛导演谈——费穆[N]. 大公报, 1937-02-07.
[2] 凌鹤. 评《人生》[N].申报, 1934-02-04.
[3]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 当代中国电影(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4] 李渔. 闲情偶寄[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
[5] 费穆. 关于旧剧电影化的问题[J]. 青青电影, 1941: 24−28.
[6] 吉夫·皮克. 用当代人的眼光比较电影与戏剧[J]. 戏剧, 1995(3): 28−30 .
[7] 雨果. 明斯特伯格. 电影心理学[C]// 李恒基, 杨远婴主编.外国电影理论文选,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5 .
[8] 佚名. 斩经堂[N]. 中国电影日报, 1937-10-13(5).
[9] 费穆. 关于梅兰芳五彩电影《生死恨》的通讯[J]. 影剧丛刊, 1948(9): 18−20.
[10] 黄爱玲. 独立而不遗世的费穆[J]. 明报月刊, 1997(4): 36−38.
[11] 费穆. 杂写[J]. 联华画报, 1935(1): 43−45.
[12] 克拉考尔. 电影的本性[M].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1.
[13] 费穆. 略谈“空气”[J]. 时代电影, 1934(6): 26−30.
[14] 程季华. 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二卷)[M].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0 .
[15] 梅兰芳. 拍了《生死恨》以后的感想[J]. 电影, 1949(10): 67−75.
[16] 梅兰芳. 我的电影生活[M].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62.
Nationalization of image: aesthetic re-examination of Fei Mu’s open films
YANG Zixuan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ilms, director Fei Mu ha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making Chinese operas cinematic as well as to nationalizing Chinese movies. Through montage, transformation of lens, art designing, sense control and other series of methods, he integrates the two different art forms of operas and movies. Moreover, he makes a selective detainment in classical operas in pursuit of beauty of Chinese people. By using movie media, he creates unique opera film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ei Mu; opera films; nationalization; artistic conception of beauty
J901
A
1672-3104(2015)04−0192−05
[编辑: 胡兴华]
2014−12−11;
2015−06−11
杨紫轩(1987−),女,河北石家庄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影视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