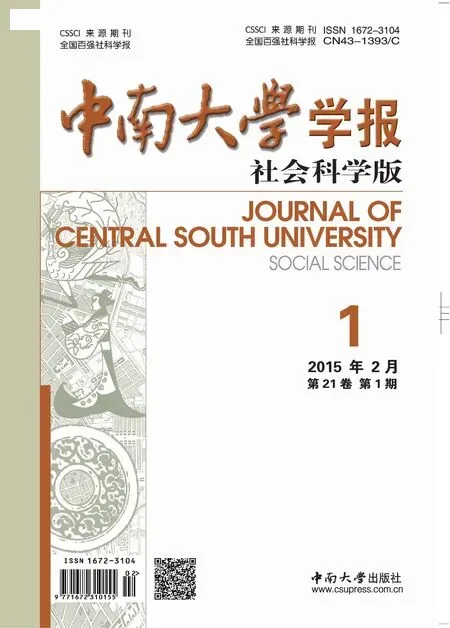刑法与相关部门法的关系模式及其反思
袁彬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100875)
刑法与相关部门法的关系模式及其反思
袁彬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100875)
刑法与相关部门法关系的一元化立场认为,刑法具有从属的、补充的性质,是民法、行政法等相关部门法的保障法。但法律的逻辑起点与价值追求差异、二元化的刑事违法性、刑法侧重事实关系保护的特点和刑罚轻缓化趋势,决定了刑法作为保障法的一元化模式不能适应现代刑法与相关部门法的发展,容易造成刑法对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领域的侵犯。刑法与相关实体部门法之间应当坚持相对的一元化关系模式。只有在法益和行为重合的范围内,民法、行政法规范才能上升为刑法规范。
刑法;相关部门法;从属性;独立性;关系模式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国家的法律部门繁多。但以诉讼程序为参照,实体部门法规范基本上可以被分为三大类型,即刑法(对应刑事诉讼程序)、民法(对应民事诉讼程序)和行政法(对应行政诉讼程序)。因此,刑法与相关部门法的关系在实体法上主要体现为刑法与民法、行政法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刑法与民法、行政法等相关实体部门法的关系,是我国现代刑法实践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一方面,“从1979年刑法典颁布至今,我国刑事立法已在犯罪化的道路上行进了三十余年”[1],刑法立法的扩张导致大量民事、行政违法行为入罪,这在不断挤压民法、行政法空间的同时也模糊了刑法与民法、行政法的界限;另一方面,随着刑法与民法、行政法等相关部门法规范体系的日益完备,各部门法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目的与话语体系,部门法的各自繁盛也带来了不同法规范之间的冲突,并体现在近年来发生的如四川帅英保险诈骗案、广东许霆盗窃案、浙江吴英集资诈骗案等典型刑民冲突案件的法律适用上。
德国著名刑法学家罗克辛教授认为,刑法是“社会政策的最后手段”,只有在其他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才能允许被使用。[2](23)按照刑法的这一原理,刑法只有依附于行政法、民法等其他部门法并作为其他部门法的补充才可能存在[3],民事违法、行政违法是刑事违法的前提。但著名法律学家伯尔曼认为,法律不是一个简单的规则体,它“只有在制度、程序、价值和思想方式的具体关系中才具有意义”[4](13)。“禁止盗窃”规则在民法、行政法与刑法上的意义可能大不相同,其民法意义主要是“恢复原状”“赔偿损失”,但其刑法和行政法的意义则主要是剥夺金钱与自由。不同的制度、价值和思维方式决定着规则的不同内涵与关系。传统的“刑法保障法”立场,无法解释为何有些民法、行政法规范(如契约违反、无责任能力者的看护)不能上升为刑法规范。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刑法与相关部门法的关系置于多元的利益主体和价值格局中,以寻找更有效的解释路径,为刑法“规范效力的合法性”提供更合理的“解释证明”。[5](150)
二、刑法与相关部门法关系的一元化模式
(一) 刑法与相关部门法关系的一元化模式内涵
刑法与相关部门法关系的一元化立场认为,刑法具有从属的、补充的、二次的、副次的、制裁的性质。刑法是以违法行为中的重大者为目标,如果完全可以用其他较轻微的法律来制裁的场合,就不允许科以刑罚。[6](2)只有当一般部门法不能充分保护某种法益时,才由刑法保护;只有当一般部门法还不足以抑止某种危害行为时,才由刑法禁止。[7](30)据此,刑法与相关部门法的关系模式是一元化的,即刑法是其他部门法的补充法、保障法。其依据是刑罚的严厉性和残酷性。“刑法是以刑罚这种残酷的制裁作为手段的,不能轻易使用,只有在使用其他法律不足以对法益进行保护的场合,才将该侵害法益的行为作为犯罪进行处罚,由此而彻底实现对社会秩序的维护。”[8](4)
(二) 刑法与相关部门法关系的一元化模式体现
“法律将各种法律体系融为一体,每一种体系中的各种成分要素,其含义都部分地来源于整个体系。”[4](13−14)它“并不乐于提倡与之相悖的行为,即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受同样的目标和政策的约束”[9](217)。刑法和其他部门法虽然基于自身的体系而具有各自独立的目的和政策,但在法的整体性上,它们是一致的,有着一起维护法的整体秩序的共同义务。刑法与相关部门法的一元化模式认为,刑法和其他部门法必须服从于法的整体秩序。“国家对刑法的期望,就是制止犯罪的机能和通过它而实现的维持秩序的机能。”[10](44)民法、行政法等其他部门法则是通过对民事违法、行政违法等行为的制止来恢复法秩序。在传统的一元化关系模式中,刑法与民法、行政法对法秩序的维护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刑法对民法的绝对补充。刑法与相关部门法关系的一元化模式认为,刑法和民法相互独立而又相互补充,民事责任体现的是对受害个体利益的弥补,刑事责任体现的则是对一般个体利益的保护,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共同构成了对法秩序的整体维护。以不法行为造成他人的损害为例,民事赔偿责任体现的是对被害人受损害利益的赔偿,而刑事责任体现的是防止其他人免受不法行为侵害的抑制,民事赔偿责任不能取代刑事责任。“如果以行为人是否进行民事赔偿作为衡量行为人之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那么法律警戒和抑制的内容就被置换成对民事责任的不承担行为,如此,则使法律的警戒和抑制方向发生严重的错位和偏离,而且会导致刑事责任承担的不平等。”[11]但在违法性上,刑事犯罪必须以民事违法为前提,只有不法行为对被害人利益的侵害上升到了需要运用刑法进行惩戒以防止其他人再受不法行为的侵害时,刑法才能介入。在任何情况下,民事合法行为都不能上升为刑事犯罪,否则将导致法秩序保护的冲突。
第二,刑法对行政法的相对补充。刑法与行政法所针对的都是涉及一般公众利益的不法行为。刑法对行政法的补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对应的行政刑法领域,行政法既是法秩序的建立者,也是法秩序维护的优先选择,只有行政法基于自身手段的限制对部分违法行为制止无效或者效力不足时,才需要刑法的介入。刑法是行政法的补充法和保障法,不到万不得已,没有必要动用刑罚手段。二是在对应的自然犯轻罪领域,行政法是不法行为治理的优先选择,刑法则是行政法的补充。例如,对伤害、侮辱、诽谤等行为,只有行政法因其制裁手段的有限性而不足以制裁该类行为时,才能动用刑法。但在对应的自然犯重罪领域,刑法是法秩序维护的优先选择,行政法是刑法的补充。行政权的特点决定了行政处罚的力度不能过大,它只能适用于危害性不大的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对于故意杀人、抢劫、强奸、绑架、拐卖儿童等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刑法是当然的首选,而行政法则只是补充的地位。从这个角度看,刑法对行政法的补充是相对的。
(三) 刑法与相关部门法关系的一元化模式实现
刑法与相关部门法的一元化关系要求刑法与相关部门法在法律概念、行为模式和法律制裁等方面保持一致。
第一,法律概念的衔接。法律概念包括常用概念、常用的但在法律中有其专门含义的概念、专门法律概念和技术性概念。[12]刑法中的法律概念很多,其中不少概念,如“集资”“恶意透支”“金融凭证”“有价证券”,都与民法、行政法等相关部门法的概念相同或者类似,表明了两者在规范上的竞合。[13]但也有许多刑法概念,如“结婚”“占有”“信用卡”,与民法、行政法等相关部门法上的概念明显不同。法律概念的差异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刑法与相关部门法的衔接。一元化关系模式要求加强刑法与相关部门法在概念上的衔接。
第二,行为模式的协调。这主要体现在空白罪状和不纯正的不作为犯、过失犯等典型的开放性犯罪构成场合。其中,刑法上的空白罪状需要借助其他法律规范来明确犯罪的行为要件,其标志是罪状表述上存在“违反某特定法律法规”。由于所参照援引的非刑事法律规范对犯罪构成起着补充说明的作用,空白罪状具有明显的补充规范性质,是对民法、行政法等相关部门法的补充。[14](11)而不作为犯、过失犯以行为人的作为义务和认识义务为前提,民法、行政法等相关部门法规定的义务是不作为犯、过失犯等开放性犯罪构成的主要义务来源。如不作为犯之作为义务的主要来源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包括宪法、法律(狭义的)、行政法规、条例、规章等。[15](67)可以说,刑法上不作为犯、过失犯等犯罪类型的存在,就是为强制人们履行其应尽的义务,体现了明显的补充法色彩,也是刑法与民法、行政法等相关部门法的衔接手段,刑法与相关部门法的一元化关系模式要求加强它们之间的衔接。
第三,法律制裁的平衡。刑事制裁与民事、行政制裁共同构成了一国法秩序的保障体系。基于刑法的补充法立场,行政制裁的强度不能大于刑事制裁。但目前两者倒置的现象在我国并不鲜见。例如,我国行政处罚上的吊销许可证在处罚力度上可能要严于刑事制裁中的罚金、管制等刑罚,同时作为行政处罚的收容教育要重于作为刑事制裁手段的拘役、短期徒刑。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刑法上的附加刑种类严重不足,导致不同类型的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严厉性倒挂;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对行政权的限制不足,过去长期存在的劳动教养、收容教育就因其处罚严厉却又缺乏必要的司法审查程序限制,导致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倒挂。合理的做法是增设相应的附加刑种类,同时改造收容教育等行政处罚制度。
三、刑法与相关部门法关系的一元化模式反思
刑法与相关部门法的一元化模式对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滥用、最大化地保障公民的自由,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和现实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变迁,现代法律的观念、功能和结构正在分化,逐渐形成了各自独立的思维范式,并在法律思维的逻辑起点、实质违法观和法的价值等方面自成体系。刑法与相关部门法关系的一元化模式正面临着新的矛盾和冲突。
(一) 一元化模式不符合不同部门法的不同逻辑起点要求
逻辑起点是思维的出发点和支点。法律思维的不同逻辑起点导致了不同的法学流派,自然法学以价值为逻辑起点,规范法学以规范为逻辑起点,社会法学以社会事实为逻辑起点。[16]与法学流派不同,现代法律都是建立在事实之上,行为被认为是法律当然的、事实的逻辑起点。
但不同法律对行为这一逻辑起点的侧重并不相同。“民事责任之基本,全在客观之实害,刑事责任之基本,则全在主观之恶性;故依社会进化趋势,以后民事责任当愈为客观化,刑事责任当愈为主观
化。”[17](2)这种认识虽然未免过于绝对,但也的确指出了不同法律之间的逻辑起点差异。例如,我国刑法不承认严格责任,刑事责任的有无及程度与行为人主观过错的有无及程度密切相关;我国民法承认公平责任,在无过错的场合,行为人也要根据公平原则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我国行政法上的强制措施重视行为的危险性,“包含着预防、制止危害行为或事件的发生或蔓延的因素”[18](189)。这导致了刑法与民法、行政法的不同:刑法强调行为的主观责任,无罪过则无刑事责任;民法注重行为的客观实害,无实害即无民事责任;而行政法则侧重行为的危险性,行政手段的种类和强度取决于行为危险性的大小。因此,刑法与民法、行政法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互为前提关系。正如依法成立的合同给相对人造成的损害再大,也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因为他签订、履行合同时主观上没有罪过;实施犯罪预备行为的人主观恶性再深,也不能追究其民事责任,因为他没有造成客观实害。这对刑法与相关部门法的一元化关系模式提出了挑战。
(二) 一元化模式不适应刑事违法性的二元化要求
英美刑法理论认为,犯罪行为有本质恶与禁止恶之分,前者是指某种行为就其自身性质而言是不法的,后者则指违反制定法的作为与不作为。[19](58)德日刑事违法性理论则逐渐由一元的规范违反说、法益侵害说走向了折中的二元论,认为刑法的实质违法性既是对国家、社会伦理规范的侵犯,也是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20](116)犯罪有自然犯与法定犯之分。从形式上看,自然犯和法定犯都可看成是对规范的违反或者法益的侵害。但进一步地看,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实质违法性并不相同。
自然犯属于“本质恶”的犯罪,无论是否有制定法的规定,它在伦理道德上都是不法的,而法定犯的违法性源于制定法的特别规定,它“侵害或者威胁法益但没有明显违反伦理道德”[7](116)。没有实定法的设定就不会有法定犯。这如同没有税法关于纳税的规定,就不会有刑法上的逃税罪;没有金融法关于信用卡的规定,就不会有刑法上的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法定犯的刑事违法是以民事、行政违法为前提,但自然犯的刑事违法性则源于它对作为自然法的伦理道德的违反。
自然犯的行为虽然也可同时构成民事、行政违法,但这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违反伦理道德行为的法律规制,民法、行政法乃至宪法等制定法是否将这些行为设定为违法并不影响自然犯的刑事违法性。正因为如此,杀人、抢劫、强奸等严重违反社会伦理的行为可不经由行政法的调整直接上升为刑法上的犯罪。刑法、民法、行政法对这些违法行为的规制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先后关系。法的违法性判断“应当以各个法领域所固有的目的、政策考虑为基础,针对各个不同法领域,分别进行”[21](130)。要求刑事违法必须以民事、行政违法为前提的一元化关系模式不符合刑事违法性的二元化要求。
(三) 一元化模式不符合不同部门法的价值追求
公法与私法的分立是学理的创造。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认为,“公法是有关罗马国家稳定的法,私法是涉及个人利益的法”[22](33)。现代西方法学家认为,公法主要是调整国家与个人之间关系的法律,私法主要是调整个人之间关系的法律。[23](403)公法与私法对利益的保护差异决定了刑法与民法不同的价值追求:民法强调意思自治、契约自由,注重个人私益的保护;而刑法强调秩序与人权,注重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刑法要达到的效果是对规范同一性的保障、对宪法和社会的保障。”[24](101)这要求立法者既要确保私人契约权利和意思自治神圣不可侵犯,又要有效防止自利行为的失控。[25]这难免会产生冲突或失衡。
按照《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订立的合同经受损方补正后仍然有效。从内涵上看,这里的“欺诈”“胁迫”包括了我国刑法上的诈骗、抢劫、强迫交易等犯罪手段。在受损害方不请求变更或者撤销的情况下,行为人以这些不法手段订立的合同在《合同法》上是合法、有效的。“如果当事人自愿接受该合同的拘束,愿意履行合同,或者用不使合同无效的其他方式补救,如果立法使其无效,那么可能违背了当事人意愿,消灭了一些不应当消灭的交易,不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而且“由受欺诈、胁迫人根据其自身利益的考虑决定是否撤销更有利于其利益的充分保护”,[26]因而允许受损害方事后追认合同的有效性。但被害人事后的宽恕与追认并不能改变行为人既成的犯罪事实。[18](127)刑法对秩序的追求决定了它必须禁止诈骗、暴力、强迫等有损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民法与刑法的价值差异导致了同一行为的不同法律性质。刑法与相关部门法的一元化关系模式显然无法解决这种冲突。
(四) 一元化模式不符合刑法重事实关系保护的特点
按照一元化关系模式,刑法是其他部门法的保护法。如果把其他部门法比作“第一道防线”,刑法则是“第二道防线”,没有刑法作后盾、作保证,其他部门法往往难以得到彻底贯彻实施。[15](8)按照这种思维,刑法对社会关系或者法益的保护应以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的确认为前提。但现实的情况却是“民法上的承认不是刑法保护的前提。不具有民事合法性的事实利益,也是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27]。刑法注重的是对事实关系的保护,该关系是否在其他部门法上受保护,不是刑法保护的前提。财产关系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刑法上的盗窃、诈骗等财产犯罪的成立并不以他人对财物的占有符合民法或者行政法为前提。盗窃违禁品、他人非法占有的财物(如抢劫、盗窃、赌博所得)、警察非法扣押的财物等民法、行政法上不予保护的财物都可构成盗窃罪。此种情况下,盗窃所侵害的依然是财物占有关系,但这种占有关系因其不受民法、行政法的保护,不是一种合法的占有关系,而只是他人对财物的一种事实占有关系。刑法对这种事实上的财物占有关系的保护表明,刑法并不只是其他部门法保护的“第二道防线”,不以其他部门法对事实关系的合法性确认为基本前提。
(五) 一元化模式不符合现代刑法的轻缓化趋势
刑法与相关部门法的一元化关系模式是基于刑罚的严厉性和残酷性。刑罚是所有法律手段中最严厉的强制性制裁方法,“能够不使用刑罚,而以其他手段亦能达到维护社会共同生活秩序及保护社会与个人法益的目的时,则务必放弃刑罚的手段”[28](128)。但如今看来,“这却是一种落后的刑罚观,与现代社会中的刑罚现状有很大的差别,也与我国刑法中的有关规定不符”[29](330)。
现代刑罚的手段日益多元化,并呈现出明显的轻缓化倾向:一是刑罚处罚的行政罚化。许多以保安为目的的行政处罚措施,如日本的“科料”、德国的“禁止驾驶”、俄罗斯的“义务劳动”、我国的“社区矫正”,逐渐上升为刑罚手段并成为刑罚适用的主要方式;二是刑罚处罚的民事罚化。民事赔偿、担保、向被害人赔礼道歉等民事处罚措施逐渐成为影响刑罚适用的重要因素和替代传统刑罚手段的措施。这在降低刑罚惩罚性的同时,也加强了对被害人的补偿和对行为人的风险防范。在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中,行为人甚至宁愿接受刑罚处罚,也不愿接受被害人提出的巨额赔偿要求。因此,在法律意义上,刑罚只是犯罪行为的法律效果,是“区分刑法与其他法律部门惟一的外部标志”[30]。刑法与相关部门法的一元化关系模式不符合现代刑罚的这种发展趋势。
法律的逻辑起点差异与不同的价值追求、刑事违法性的二元化、刑法重事实保护的特点和刑罚轻缓化趋势表明,刑法与相关部门法之间不是单一的保障法关系,民事、行政违法行为不能直接上升为刑事犯罪行为。
四、刑法与相关部门法关系的一元化模式修正
“刑罚的功效在于,从另一个方面与对具有同一性的社会规范的对抗相对抗。”[24](103)从法秩序的统一性角度,作为国家意思的适法还是违法的判断,在全体法秩序可能的限度内不应该发生冲突,违法具有统一性。但从部门法的角度,基于不同的法秩序调整需要,不同部门法的调整范围必然存在一定差异,违法性在刑法、民法、行政法等领域具有相对性,并可能发生一定的冲突: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即便为民法或者行政法所许可,也有成立犯罪的可能性;而民法或者行政法上禁止且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在刑法上也可能不具有违法性或者可罚性。[31]违法的相对性表明,刑法与相关部门法之间并非纯粹的一元主义关系,除了补充性,它们之间也存在独立性。
(一) 私益保护下的民法独立
“追求利益是人类最一般、最基础的心理特征和行为规律,是一切创造性活动的源泉和动力。”[32](220)私益是市民社会的基础。对私益的维护是现代法律的重要任务,对私益的特殊保护决定了民法的独立性。这是因为:
第一,私益侵害是许多公益侵害的起点。公共利益是社会上一般人的共同利益。“公益的维护和提倡,可以说是现代国家积极的任务,也是许多实际政治运作行为所追求的目标之一。”[33](181)不过,除了公共财产、公共场所秩序等可见的利益外,公共利益更多的是从个体私人利益中抽象出来的共同社会利益。例如,抢劫罪的设置是为了保护一般的财产权和人身权,但这里的“一般”是从具体个体中抽象出来的。抢劫罪立法所要保护的一般财产权和人身权是否受到侵害,最终还是体现为个体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是否受到侵害。被害人的私益是否受到侵害是公共利益是否受到侵害的判断起点,也是许多公共利益保护的基础。加强被害人私益的保护对刑法的公共利益保护而言,意义尤甚。
“犯罪是针对社会之害”,是“加害于社会整体的行为而不只是针对特定被害人的行为”[34]。“如果某种行为根本不可能给社会带来危害,法律就没有必要把它规定为犯罪,也不会对它进行惩罚。”[15](44)侵犯私人利益的行为只有同时侵犯了公共利益才能进入行政法和刑法的调整范围。公共利益是连接民法与刑法的纽带。我国《著作权法》第47条规定,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只有“同时损害公共利益”,才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行政处罚,进而构成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而《刑法修正案(八)》第41条也规定,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只有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才可上升为刑法上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可见,仅仅侵犯私人利益的行为被划入了民法的调整范围,只有由私益引发对公共利益侵害的行为才是行政法和刑法的调整对象。
第二,私益保护是公益保护的归宿。“利益是主体所追求的目的,权力和权利则是主体追求目的的手段。”[35](33)在保护手段上,民法是私益保护的主要法律手段,而刑法则以保护公益为己任。不过,从根本目的上看,刑法对公共利益的保护终归要落实到私人利益之上。以故意杀人罪为例,刑法设置故意杀人罪的目的是要保护一般的生命,而不仅仅是被害人的生命。但刑法上的一般生命仍可细化为社会上不同个体的具体生命。刑法通过故意杀人罪立法所保护的一般生命终究要体现为具体个体的生命没有受到侵害。从这个角度看,私益保护是刑法保护的归宿。
在私益保护的目的下,民法与刑法的规范冲突得以存在,并强化了民法的独立性。《德国民法典》第134条规定:“违反法律禁令的法律行为无效,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但该法第54条第2、3款同时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可见,民法允许被害人基于私益补正无权代理行为、以欺诈、胁迫手段或者乘人之危签订合同行为的效力,是基于私益保护的需要,它并不影响刑法对诈骗、强迫行为的责任追究。
(二) 行为差异下的相互独立
基于法目的的不同,作为法调整对象的行为在刑法、民法、行政法上的属性不可能完全相同。在行为差异的范围内,刑法与民法、行政法之间应当各自独立。
刑法、行政法、民法的行为概念差异主要源于刑法、行政法和民法的法目的不同。刑法追求的目标是“欲求允许”,即保障意志载体的意志自由,行政法追求的是福利,民法的目的主要是对已经造成的权利损害和财产损失给予填补和救济,使其恢复到未受侵害的状态。[36](45)从结果上看,刑事和民事不法造成的是实际的损失,而行政不法造成的是通过行政行为所欲达到的更大的福利的不可实现。[37]因此,刑法更注重违法行为已经造成的法益侵害和威胁。犯罪“对法益的侵犯性包括对法益的侵害性和威胁性(危险性)。侵害性是行为造成了法益的现实损害;威胁性是行为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7](97)。责任以损害赔偿为核心,赔偿损失是所有民事违法行为的最后责任,其前提是违法行为已经造成了他人的损失(实害)。[38](186)而行政法强调的是行为的危险属性,行为的危害后果、主观恶性虽然也是行为危害性的判断依据,但并非决定因素。“为了社会秩序的需要,应当对行为本身给予处罚,其目的是威慑,而不是惩罚。”[39]对行政管理秩序的实际或者潜在威胁是判断行政违法行为的关键。
行为概念的差异导致了各部门法规范的不同以及刑法与民法、行政法之间互补关系的有限性。例如,在贿赂罪的场合,因无实际受损害人,行为人就不必承担民法上的责任而只承担刑法或者行政法上的责任;同理,在行为人无过错致人受伤的场合,因无罪责和危险,行为人只需承担民法上的无过错责任,而不须承担刑法或者行政法上的责任。在此范围内,刑法、民法、行政法对其不法行为的调整是完全独立的。部门法内在目的的一致性要求其价值的统一性。“当以国家或社会必要性或目的,以多重意义的,受时代制约和具有争议性的价值观名义处刑时,施刑的手就不能不颤抖。”[40](88)因此,无论此种民法违法、行政违法行为的危害如何严重,也不能将其直接上升为刑事犯罪,除非刑法对行为的属性要求发生了变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刑法作为保障法的一元化模式形式上具有限制刑罚权的作用,但在行为不重合的范围内,它也可能导致刑法对民法、行政法领域的侵犯。从这个角度看,在我国2013年废止劳动教养后,笔者不赞同许多学者主张的据此对刑法进行结构性调整,因为劳动教养制度调整的对象只是具有较大危险性而不具有较明显法益侵害性的行为,它们主要属于行政法调整的范围,而不应将其作为犯罪处理。
可见,刑法与民法、行政法等相关部门法之间具有补充性,但并非单纯地刑法补充民法、行政法等相关部门法,而是基于法整体秩序之保护需要的互补关系,它们之间是一种相对的一元化关系。在法益和行为不重合的范围内,民法、行政法规范不能上升为刑法规范,以防止刑法对民法、行政法领域的侵犯。
[1] 刘艳红. 我国应该停止犯罪化的刑事立法[J]. 法学, 2011(11): 108−115.
[2] [德]克劳斯·罗克辛. 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 犯罪原理的基础构造[M]. 王世洲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5.
[3] [意]杜里奥·帕多瓦尼. 意大利刑法学原理(注评版)[M]. 陈忠林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4] [美]哈罗德·J·伯尔曼. 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M]. 贺卫方, 等译.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5]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 合法化危机[M]. 刘北成, 曹卫东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6] [日]泷川幸辰. 犯罪论序说[M]. 王泰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5.
[7] 张明楷. 刑法学(第2版)[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3.
[8] [日]大谷实. 刑法总论[M]. 黎宏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3.
[9] [美]德沃金. 法律帝国[M]. 李常青译.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
[10] [日]西原春夫. 刑法的根基与哲学[M]. 顾肖荣, 等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11] 杨忠民. 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不可转换——对一项司法解释的质疑[J]. 法学研究, 2002(4): 131−137.
[12] 李希慧. 论刑法的文理解释方法[J].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1995(1): 26−32.
[13] 朱铁军. 刑法与民法之间的交错[J]. 北方法学, 2011 (2): 48−57.
[14] 蔡墩铭. 刑法总论[M]. 台北: 三民书局, 1993.
[15] 高铭暄, 马克昌. 刑法学(第5版)[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16] 张善根. 西方法学流派的逻辑起点及其局限[J]. 求是学刊, 2011(6): 76−81.
[17] 陈瑾昆. 刑法总则讲义[M]. 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4.
[18] 罗豪才. 行政法学[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19] 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
[20] [日]大塚仁. 犯罪论的基本问题[M]. 冯军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3.
[21] 黎宏. 日本刑法精义[M]. 法律出版社, 2008.
[22] [意]桑德罗·斯奇巴尼. 正义与法[M]. 黄风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
[23] 沈宗灵. 法理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24] [德]格吕恩特·雅科布斯. 行为 责任 刑法——机能性描述[M]. 冯军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25] 李兰英. 契约精神与民刑冲突的法律适用——兼评《保险法》第54条与《刑法》第198条规定之冲突[J].政法论坛, 2006(6): 165−172.
[26] 王利明. 无效抑或撤销——对因欺诈而订立的合同的再思考[J]. 法学研究, 1997(2): 67−83.
[27] 黄桂武, 等. 新论财产罪法益—与张明楷教授商榷[J]. 学术研究, 2007(1): 69−72.
[28] 林山田. 刑罚学[M].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5.
[29] 黎宏. 刑法学[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2.
[30] 陈自强. 刑法的调整对象新界说[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2): 110−115.
[31] 童伟华. 日本刑法中违法性判断的一元论与相对论述评[J].河北法学, 2009(11): 169−172.
[32] 张文显. 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33] 陈新民. 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册)[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34] 夏勇. 刑法与民法[J]. 法治研究, 2013(10): 5−9.
[35] 叶必丰. 行政法的人文精神[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36] 魏振瀛. 民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37] 王莹. 论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分野及对我国行政处罚法与刑事立法界限混淆的反思[J]. 河北法学, 2008(5): 26−33.
[38] 张俊浩. 民法学原理[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39] 王文华. 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若干问题研究——以中国与加拿大比较为视角[J]. 南都学坛, 2008(5): 86−89.
[40] [德]拉德布鲁赫. 法学导论[M]. 米健, 朱林译.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Refle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minal law and the relevant department laws
YUAN Bin
(College for Criminal Law Sci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unified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minal law and relevant department laws, criminal law is subordinate and complementary, functioning as the security law for relevant department laws. But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law and value pursuit, normalized criminal illegality, the focus on the fact protection and the tendency of the alleviation of criminal law, all determine that criminal law as the unified model of security law is not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riminal law and the relevant department laws. As a result, it is easy for the criminal law to infringe upon such fields as civil law, administrative law and other department laws, according to the absolute unified relationship. Therefore, relative relationship model should be advocated between criminal law and the relevant department laws. Only in the identical scope of benefit and act, can the rules of civil laws and administrative law be stipulated in criminal law.
criminal law; relevant department laws; subordinate property; independent property; relationship model
D914
A
1672-3104(2015)01−0044−07
[编辑: 苏慧]
2014−05−08;
2014−06−11
袁彬(1976−),男,江西临川人,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