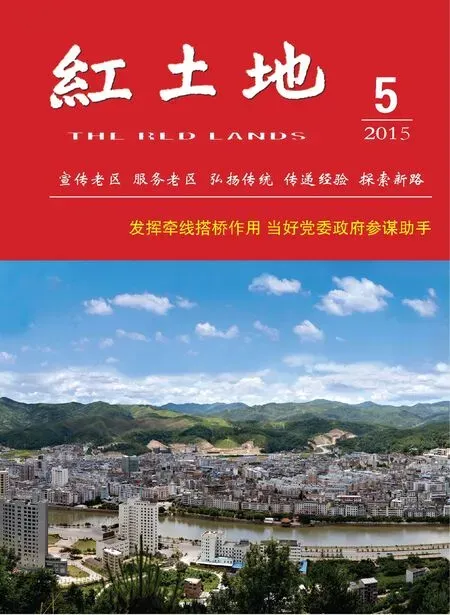陈毅之女:我的慈父严母
丛军
陈毅之女:我的慈父严母
丛军
丛军,原名陈珊珊,曾任中国驻爱沙尼亚大使、中国驻联合国公使衔参赞。
为人随和的市长夫人
抗日战争期间,父亲陈毅和母亲张茜在新四军里相识结婚。1941年,母亲在苏北侉周村生下大哥陈昊苏,小名就叫小侉。二哥生在淮南黄花塘,取名丹淮。三哥生在山东,取名小鲁,小鲁吃羊奶长大,所以小名叫小羊。1950年8月15日,我出生于上海。因为姗姗来迟,父亲给我取名叫珊珊。
已经生了4个孩子的母亲当时还很年轻,才28岁。她很好学,进了上海俄文专科学校学习俄语。
翻译家姚以恩跟母亲是同学,他曾撰文回忆:“有一段时间她是我的同桌,在我的印象中,她是那样的青春秀美。碰到校长姜椿芳上翻译课,她是必到的,而且听得很认真,笔记也做得很仔细。每次被老师点到名,她就满脸绯红地站起来。她没有一点高官夫人的架子,和其他同学一样穿着列宁装,也是和我们一样在学校食堂用餐。她为人随和,经常看到她和女同学们一起说说笑笑。星期六傍晚,陈毅市长常会亲自来接她。”
父亲对孩子很民主
1955年,父亲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母亲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任职,为了配合父亲做好夫人外交工作,她从俄语转学英语。王光美曾如此回忆我母亲:“她聪明好学,多才多艺,对子女要求严格,对自己也很严格,为了节约,外事活动多,服装费不足,自己常拼拼改改,既节约,又体面。”
母亲治家严谨,事无巨细都处理得仔细妥帖,自己的东西收拾得整整齐齐。她对我们的学习要求严格,尤其是对我这个最小的女儿,管得更是严。
有时,我贪玩,学习不长进,母亲不仅批评我,还让我罚站。但是只要父亲在家,迟早会来解救我。他总是先批评我几句,然后就说:“珊珊,下回不能这样子了,你走吧,我要跟你妈妈说点事。”我就哧溜一下推门跑走了。
父亲对我们几个孩子很民主。一次,看完了电影《早春二月》回到家,他召集我们讨论,应如何看待这部电影。对这部电影到底是“香花”还是“毒草”,三个哥哥争论热烈。还有一次,他把我们召集起来,让我们就中共是否应派团出席苏共代表大会各抒己见。
我小学毕业时,考什么学校,父母意见分歧。母亲希望我考解放军艺术学院,因为她1938年参加新四军后分在战地服务团工作,能歌善舞,很活跃。但父亲却说,国家很需要外语人才,女孩子文静一点,学点外语不错。我听父亲的话,报考了北京外语学院附中。

陈毅与家人的合影
擅自改名“从军”
“文革”时,父母都受到冲击。1969年,我参军入伍,在北京军区后勤部261医院当了一名护士。我不希望自己的身份引人注意,没有和父母商量,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丛军”,取木兰从军之意。改完后,才写信告知家里。
后来医院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问谁会玩乐器,我就报了名。因为学过钢琴,我学手风琴很快。这在当时可算条件最好的工种了,演出后,还能吃一碗面条当夜宵。在部队期间,我入了党,父亲很高兴。
1971年夏,父亲患结肠癌,在北戴河疗养。我们陪伴父母,度过了一段轻松愉快的日子。
母亲还特地找出医用英语教材,亲自辅导我学英语。当时,我还不太理解父母的苦心,对今后工作中能否用上外语也心存疑虑,不过还是认真地跟着母亲读书。
痛失父母
好景不长。1972年1月6日,父亲去世。不久,母亲也被确诊患有肺癌。
外交部干部司司长许寒冰到301医院探视母亲,她告诉母亲:“现在有一个让珊珊继续学英语的机会。周总理指示,翻译还是要培养的,想把过去在外语附中学习的老初三学生招回来,送到国外深造,将来回来后就到外交部当翻译。”
母亲毅然决定送我出国留学,以了却父亲的心愿。
1973年末,母亲病重,组织上批准我回国探亲。癌细胞已转移,情况很不好。
一个多月后,在我返回英国之前,母亲把我们兄妹四人叫到病床前,跟我们讲了很长一段话。我们都意识到,这是她留给我们的遗言。
母亲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她对父亲的深厚感情以及她一生都在试图缩小与父亲之间差距的努力。她特别交代我们:“你们要懂得那些纷扰的争斗和虚浮的颂词都不过是过眼云烟,不值得计较和迷恋。在你们爸爸的文章、讲话和诗词作品中,却有一些真正价值崇高的东西,你们不要等闲视之啊!”
母亲弥留之际,丹淮曾问她:要不要喊珊珊回来?她摇摇头。没能给母亲送终,让我一生追悔莫及。
(摘自《中国新闻网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