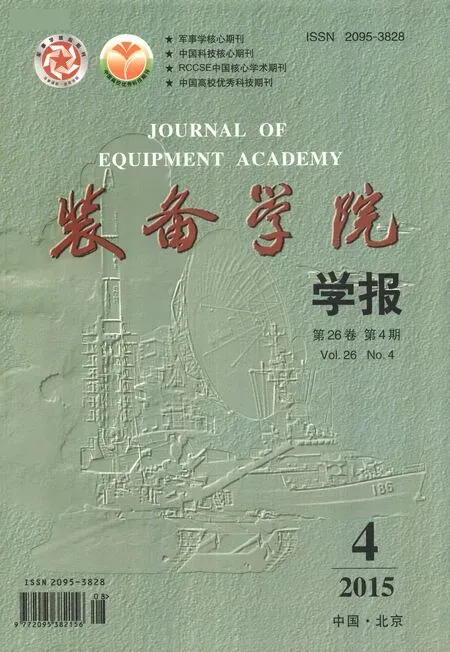美军装备采办管理改革的经验教训
王 雨, 王 磊
(1.军事科学院 研究生部,北京 100091; 2.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 三室,北京 100142)
美国是当前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经过长期改革,目前已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装备采办管理制度。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以及国情军情的差异,美军最新的采办管理思路、制度与做法对我军的参考价值往往并不是最明显的,其在装备采办管理改革中积累的经验、走过的弯路、针对特定问题采取的举措,对全面了解和掌握美国装备采办管理改革历史与现实情况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对我军目前的深化改革论证工作更具启发意义。
1 装备建设管理体制的统一与分散
二战后,美军全面梳理了美军建设与管理各领域存在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各军种自行其是、联合作战能力薄弱,各军种按照各自的思路发展装备,全军缺乏有效的统筹管理。为解决上述问题,美军确立了加强对全军装备建设集中统管的改革思路,但在改革过程中受到各军种较为强烈的抵制。
1.1 军种部先于国防部设立
美军先有军种部,1949年才初步形成国防部体制。二战结束前,美军主要依托陆军部与海军部开展部队管理与装备建设工作,陆军部与海军部作为联邦政府部门,都具有强大的行政权力,且两者之间恶性竞争的问题较为突出,协同作战能力较低。美国国会出台《1947年国家安全法》,要求组建国家军事部,负责对各军种实施指导、管理与控制,并在陆军航空兵的基础上组建空军部。1949年进一步通过了《1947年国家安全法》修正案,将国家军事部改组为国防部,取消军种的联邦政府部门职能,划归国防部统一领导,同时将国防部升格为联邦政府部门,统管全军的军队建设工作。
1.2 各军种权力竞争激烈,各种矛盾难以调和
国防部成立之后的较长时期内,军种强势的权力格局没有打破,国防部难以对各军种实施有效管控,各军种间的利益冲突与矛盾难以调和。这一时期,海军与空军围绕超级航空母舰“合众国号”和B-36战略轰炸机的研制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海军超级航母项目最终被取消,引发海军高层强烈不满,并在国会强烈控诉国防部与空军对海军的不公正行为,引发美国政府高层与民众的高度关注,史称“海军将领的叛乱”[1]。美军第一任国防部长詹姆斯·佛斯莱特面对各军种的强硬态度,难以有效开展工作,同时承受着来自白宫与国会的强大压力。
1.3 国防部强化“自上而下”管理机制,但遭遇各军种抵制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美军在国防部长办公厅设立一系列业务局与直属机构,将原来由各军种分散管理的共性事务收至国防部,如设立国防后勤局、国防合同管理中心、研究与工程署、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等,加强对通用备件与后勤物资采购、全军重大合同履行监管、重大装备研发与采办管理、重大先期技术研究等的统管力度。
1961年,麦克纳马拉出任国防部长后,积极推行规划、计划、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引入“规划计划预算系统”,改变了长期以来各军种主导各自的规划与计划制定、国防部难以有效统筹的不利局面。
此外,美军还积极加强对装备需求的统筹管理。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里根总统倡议下,美军成立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由参联会副主席担任主席,并吸收各军种副参谋长(海军为作战部副部长)参加,审查所需发展的装备是否存在军种间重复的问题、是否充分考虑全军层次联合作战的需要。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出现了许多困难与争议,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会议被称为是“充满仇恨、各军种为维护自身利益进行战斗的战场”。当时的参联会副主席威廉·欧文(1994—1996年任职)对需求审查中各军种毫不妥协的立场以及难以协调装备发展需求的状况深感失望和无能为力,拒绝连任新一届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主席的职务[2]。
基于需求生成中的上述问题,美军2003年启动基于能力的“需求革命”,构建了“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从能力建设的角度加强国防部对三军需求的顶层设计与审查力度,真正形成了“自上而下”的需求生成机制,有效保证各军种装备建设的“生而联合”。
2 信息系统建设的独立与融合
二战后,信息技术持续快速发展,成为武器装备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信息系统作为信息技术物化的最直接产品,受到美军的高度重视,并着力发挥其在现代战争中的神经中枢作用。美军将武器装备分为信息系统与武器系统两大类,并走过了一条先相互独立、后集成融合的发展之路。
2.1 在信息技术萌芽阶段,探索构建专门的信息系统主管机构
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军包括信息系统在内的武器装备都由各军种自行管理,各军种信息系统重复建设问题突出,互联互通能力较差。
1961年开始,国防部逐步加强了对各军种信息系统建设的统一领导。国防部成立了C3(指挥、控制与通信)办公室,负责全军信息系统的建设与管理,1972年1月设立负责通信装备的助理国防部长,1977年3月进一步改组为负责指挥、控制、通信与情报(C3I)的助理国防部长[3],加强国防部对三军信息系统建设的统筹管理。
2.2 信息系统建设长时期独立于武器系统建设管理体制
美军设立C3I助理国防部长后,美军在装备采办领域形成2套管理体系,武器系统建设由采办副国防部长负责,信息系统建设由C3I助理国防部长负责。1996年根据国会《克林杰-科恩法》,国防部设立首席信息官,由C3I助理国防部长兼任,其管理职能进一步强化,除负责信息系统建设外,还赋予其美军信息互联互通方面的管理职权。
美军设立C3I助理国防部长(2003年调整为负责网络与信息集成的助理国防部长),其初衷是为突出信息系统建设,客观上也大大促进了战后美军信息技术与相关系统建设。新世纪以来,美军信息系统与武器系统建设相互割裂的问题逐步凸显,成为美军新时期装备采办管理与改革的主要矛盾:一是信息系统与武器系统在顶层设计、标准体系方面不统一、接口不一致、体系难配套,影响了美军联合作战与互联互通能力的提升;二是在该体制运行过程中,大量装备项目的归口管理部门不够清晰,如美军联合战术无线电系统、转型通信卫星等项目的归口管理部门多次在网络与信息集成助理国防部长和采办、技术与后勤副国防部长之间调整,影响相关装备建设的质量与效益;三是分散的管理体制也分散了管理力量,有限的采办队伍化整为零,降低了专业管理人员整体效能的发挥[4]。
2.3 统管改革不彻底
美军2010年发布《国防部效率倡议》,提出撤销网络与信息集成助理国防部长职位,并于2012年1月撤销完毕,原来由其承担的信息系统采办管理职能,交由采办、技术与后勤国防副部长管理[5]。改革后,原来由网络与信息集成助理国防部长兼任的国防部首席信息官独立设置,国防信息系统局归口国防部首席信息官领导,该局的信息系统采办业务交由采办、技术与后勤副部长监管。
美军上述信息系统采办管理体制的改革带有妥协性与不彻底性。未来美军采办、技术与后勤国防副部长与国防部首席信息官的博弈仍将继续,武器系统与信息系统的集中统管改革仍需继续深化。
3 装备项目管理制度与行政管理模式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
推行全寿命管理是装备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世界主要国家的通行做法。美军通过二战期间“曼哈顿计划”等的管理与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项目管理制度,成为其装备采办管理的基本制度形式。但在实际操作中,美军也存在项目管理机构与行政管理机构的矛盾。
3.1 明确装备项目管理主体,统筹装备采办全寿命过程
美军自二战时期开始尝试推行装备项目管理制度,其后对制度内容不断改革完善。1971年国防部出台5000.1指令《国防采办系统》与5000.2指示《国防采办系统的运行》2份采办法规,明确将项目管理作为实现装备全寿命管理的基本制度形式。
美军项目管理制度的核心是将项目管理办公室作为装备项目采办管理的主体,对装备项目采办全寿命过程实施管理。项目管理办公室下设计划、合同、质量、财务、系统工程、成本价格、试验鉴定、维修保障、系统集成等方面的工作小组,采取“矩阵式”的组织模式吸收相关管理或技术部门的人员参加,形成对装备项目采办的有效管控。
3.2 构建专门的项目管理指挥线,项目管理办公室存在双头管理问题
国防部为加强对项目管理机构的有效管控,在其行政管理体系之外,构建了一条专业的采办指挥线,从上到下依次为国防采办执行官-局采办执行官-计划执行官-项目主任,其中,国防采办执行官由采办、技术与后勤国防副部长担任,军种采办执行官由各军种负责采办的助理部长担任,计划执行官则为各军种内部负责某一专业领域装备管理的主管官员,每个军种下设十余个计划执行官,领导相关领域项目管理办公室开展工作。
美军通过这种制度设计,将军种部长、军种参谋长等从采办指挥线中去除,降低了管理层级,提高了管理效率,并有效弱化了军种部层面的采办主导权,形成军种采办部门直接向国防部采办部门汇报工作的管理制度。
美军这一管理制度的设计是一次重大创新,但也是一种无奈之举,最大问题在于军种负责采办的助理部长既接受国防部采办、技术与后勤副部长的采办业务指挥,又受军种部长的行政领导,且军种部长等行政管理部门对项目管理机构的组织管理仍然具有重要影响,一旦2个部门意见不一致,容易导致军种采办项目管理机构无所适从,削弱了项目管理的有效性。上述问题是美军装备采办由各军种分散实施的体制导致的,目前看,这一问题仍将长期存在,未来美军只有通过加强国防部对各军种的统管力度来加以解决。目前美军正在论证在现有三军种的采办管理体系之外,设立独立于三军种的联合采办执行官[6],负责三军通用装备的联合采办,受采办、技术与后勤国防副部长的直接领导,这将很大程度上削弱军种的采办管理权。
4 降低企业准入门槛与采办过程的有效管控相结合
冷战结束后,美国国防预算大幅削减,国防工业基础面临深度整合。美国一方面推动大型军工企业的兼并重组,另一方面降低企业参与军工科研生产的准入门槛,大量中小企业及非传统承包商加入到装备采办竞争的行列,此外还积极采办商业现货并推行军用标准工作改革。上述改革增加了美军装备采办的弹性与活力,但也在多个领域出现了采办费用严重超支等问题。
4.1 实行开放式的资格审查制度,降低中小企业参与军工科研生产的门槛
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推行国防工业转轨,实施军民一体化的调整战略,积极鼓励中小企业参与国防采办竞争。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美国逐步建立了一整套面向市场竞争机制的承包商资格审查制度,降低了中小企业参与军工科研生产的门槛。
美国建立了以注册制度、名录制为主体的武器装备承研承制单位资格审查制度体系。联邦政府建立了中央承包商注册系统(Central Contractor Registration,CCR),承担采办项目的企业都必须到承包商中央注册系统注册,并通过信息平台发布采办需求信息,有效推动企业参与采办竞争。在中央注册系统注册的范围内,美军制定合格投标商名录(Qulified Bidders List,QBL)、合格制造商名录(Qulified Manufacturers List,QML)和合格产品名录(Qulified Products List,QPL),以供国防部、各军种在采办过程中选择使用,为美军选择承包商或者主承包商选择分包商时提供参考。
4.2 推行军用标准改革,优先采用非政府标准
在冷战结束前,美军严格按照军用标准要求开展装备采办工作,对采办的所有装备与物资都制定了详细的标准,即使是采办军民通用性的产品,也需要纳入军品的标准与规范实施管理,如杯子、锤子等。这些军民通用性产品的军用标准大量存在,并要求按照军用标准实施采办和管理,导致相关产品的价格大幅飙升,20世纪80年代曾经出现数百美元的咖啡杯与锤子,装备采办经费从1980财年到1985财年翻了一番[7],引起民众的关注与抗议。
美军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启动了军用标准制度改革,逐步消除长期以来军用标准与民用标准的严格界限,主要措施包括:一是高度重视非政府标准的应用,从标准使用顺序上将非政府标准放在优先地位;二是简化采用非政府标准的程序,使更多的非政府标准能够及时为国防部采用;三是更加重视接口标准的制定,通过引入体系结构设计方法,将接口标准纳入体系结构,有效提升装备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美军通过军标改革,大幅削减了军用专用标准的数量,目前军用标准和规范比例仅占美军所有标准总量的一半左右。
4.3 相关改革带来了采办管理弹性与采办费用超支的矛盾
“9·11”之后,为适应全球反恐战争的需要,美军于2001年和2003年连续对其采办程序实施改革,装备采办里程碑节点由20世纪的5个减少为3个,突出强调采办的灵活性与快速性,给予项目主任更充分的授权,使其更加灵活地管理采办项目。
美军通过上述改革,有效缩短了采办周期,较好满足了全球反恐的应急装备需求。但到小布什政府后期,美军装备采办费用超支问题越来越突出。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对美军采办问题进行了系统评估,2000-2008财年美军重大采办项目平均研发费用超概算比例从27%增长到42%、采办总费用超概算比例从6%增长到25%[8]。
针对上述问题,奥巴马政府提出“均衡战略”的改革思路,强调采办灵活性与过程有效管控的结合,出台《2009年武器系统采办改革法》,要求加强技术成熟度评估与试验鉴定力度,使美军装备采办管理制度更加优化。2015年1月7日,国防部发布新版5000.2指示,细化制定了6种装备采办程序[9],便于美军根据不同的装备类型采取有针对性的采办程序,进一步提高采办管理的有效性。
5 认识与启示
长期以来,美军持续推动装备采办管理制度的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存在改革不充分、不彻底等问题。回顾美军采办管理改革的过程及经验教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与启示。
5.1 改革聚焦矛盾与问题,寻求对立与统一的平衡点
美军装备采办管理改革主要聚焦4方面的矛盾与问题,即采办管理体制的统与分,信息系统和武器系统的独立与融合,项目管理的主导权,过程管控的收与放等。美军的改革符合哲学的辩证法,核心是寻求上述矛盾的平衡点,体制上形成了国防部集中统管与军种分散实施的有机结合,装备体系建设方面形成信息系统与武器系统的融合式发展,全寿命管理方面确定了项目管理机构为主、行政管理部门为辅的管理方式,采办过程管控实现了管理刚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
5.2 改革的核心是管理体制,基本方向是加强国防部的集中统管力度
美国国防部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建立集中统管的装备采办管理体制,但鉴于先有各军种、后有国防部的历史背景,美军目前仍然采用的是国防部统一领导、各军种分散实施的管理体制。这一体制导致美军长期以来存在各军种装备“烟囱式”发展、联合作战能力不强等问题。总体上看,只有国防部对各军种装备实施有效统管,才能从全局的高度有效统筹全军装备体系建设,才能确保装备体系联合作战能力的有效提升。建立国防部集中统管的装备采办管理体制,弱化以至取消军种的装备采办权,符合装备体系建设的发展要求,也是美军装备采办管理体制深化改革的发展趋势。
5.3 改革受部门利益影响,一般遵循先易后难、先机制后体制的改革路径
改革是权力的重新分配,触动的是既有部门的利益,这也是美军采办管理改革充满曲折的根本原因。类比来讲,管理体制如同生产力,运行机制如同生产关系,管理体制相对稳定,体制改革难度要远大于机制改革。美军在长期的采办管理改革中,体制改革难以推进时往往先对运行机制实施调整,待时机成熟再对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实施改革。
5.4 改革过程艰难而曲折,总体趋势保持螺旋式上升
美军采办管理改革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某些领域的改革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部分领域的改革至今还很不彻底。但回顾美军二战后至今的改革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某些领域的改革可能难以一蹴而就,但改革总体趋势是螺旋式上升和持续完善的,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
6 结束语
美军装备采办管理体制机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既有其科学和先进的地方,也有不合理之处。目前美军在装备建设中各军种自行其是、武器系统与信息系统分散等问题仍然存在,国防部对全军装备建设的统管力度仍显不足。我们必须坚持历史的视角、发展的视角、辩证的视角,对美军经验进行参考借鉴,不能认为现有的就是合理的,更不能认为美军目前的制度就是最科学的,避免对美军现有做法进行照搬照抄,必须追根溯源、上升到规律,为我军的深化改革论证工作提供有益参考。
(References)
[1]ANDREW L.The revolt of the Admirals[S].Air Command and Staff College Air University,Maxwell Air Force Base,Alabama,1998:1-3.
[2]DAVID F.The new joint capabilities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system (JCIDS)and its potential impacts upon defense program managers[S].US Naval Graduate School,California,2004:6.
[3]RONALD J.Department of defense key officials 1947-2012[S].Washington:US DOD Historical Office,2013:8.
[4]WILLIAM S.Department of defense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for the acquisi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S].Washington:US DOD Defense Science Board,2009:16.
[5]ASTON C.Disestablishment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networks and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and related matters[S].Washington:US DOD,2012:1.
[6]HOWARD H,MARK L.Proposed leadership structure for joint acquisition programs,ARJ[D].Virginia:Defense Acquisition University,2012:35.
[7]RONALD J.Defense acquisition reform 1960—2009:an elusive goal[S].Washington: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United States Army,2011:118
[8]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Defense acquisition assessments of selected weapon programs[S].Washington:2009:7.
[9]FRANK K.Under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acquisition technology and logistics,DoDI 5000.02,operation of the defense acquisition system[S].Washington:US DOD,2007:9-15.